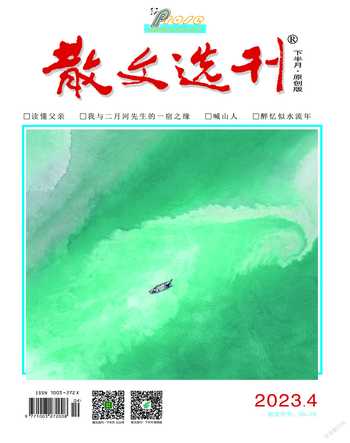西山霁雪
吴海涛
西山晴雪,是与自然界中的雪密切相关的燕京八景中的一景,亦名西山霁雪,此景美就美在“雪”字上。
清代王汝赓诗曰:“西山小住隔尘寰,日日登临兴未阑。大雪又添图画好,新晴闲曳杖藜看。玲珑万树苍髯亚,闪烁千峰白玉寒。最怪懒云堆不起,迷离何处辨烟峦。”诗中的“西山”虽然未必是我生活与热爱之地,但我坚信,二者之美是一致的。
西山不要单说晴雪,和晴雪媲美的还有红叶。老北京把京西的大山统称“西山”,实际是由香山、翠微山、卢师山、虎头山、平坡山、大青山、小青山组成,山与山相连、景与景相映。可以说处处有景,处处有山。
在北京城里居住已二十年了,一生转眼就过去。我虽不算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时间久了,也有了深厚的感情。祖上也曾在北京有地有房,也可称城里的“乡下人”。
乡下人土、乡下人拙、乡下人勤奋,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年轻时闲得难受,往往周日骑自行车在四九城瞎晃。北城人睥睨南城人,自古以来北城多王府,南城多商贩、杂役人员;新时代的北城领导干部和文化学者、教授居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北京人常说的老理儿。时不时地骑上我的自行车,出西直门,过高梁桥、大柳树、青龙湖,看到山美水美,养德养心,更经常骑车到蓝靛厂、稻香湖、香山、八大處,没有目的地“瞎转乱窜”。那时人穷,买不起照相机,一个日记本、一支笔、一双眼,足可收录最美西山风光、开阔眼界。
北京西山文化带确实有深厚的底蕴。自然美和古建筑美的融合,陶醉了我。若你也和我一样,在不同角度欣赏,定会有不同感受。
香山就是天然保障里最有保障的地方。
秋天,看香山的枫叶是我每年的“保留节目”。
看香山的枫叶,要分时间和层次,须慢慢渗入。
深秋的香山和夏日碧绿的景色没有区别,只是天气略感凉爽,没了满身的汗水。常言:看山累死马。虽然看着近,一路骑车的劳累,早就消耗了登山攀顶的体力,留下的只有疲惫,只有望而却步地仰望远景。远远望去,山自有山的脉络,层层之间是树隔离出的深浅。峰岭间被蓝蓝的天空烘托得宏伟和高大。秋天的阳光洒下热情,用浓淡勾勒出远近。仰望着老天赋予大山的神奇,即便在金色的琉璃瓦下,也会增添灵性。这也许正是西山最让我留恋和敬仰的地方。
驻步休息,让我精力旺盛,很快恢复了体力,又提升了登山的信心。忽然想起那首《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然而,越来越慢的脚步让我萌生了坐索道缆车登上峰顶观红叶的想法。
这里的索道缆车,是北京地区第一条。乘缆车游览别具风格,俯瞰香山,全景尽收眼底。有诗云:“黄花深巷,红叶低窗,凄凉一片秋声。”从缆车上俯瞰,条条攀山石径区分了山与山的层次,秋叶已经出现三彩,令人瑟瑟发抖的秋风,考验着这片富有情感的山色,执着坚强的松柏依然显露着青翠的本色,似乎丝毫不惧怕飕飕的秋风,活化石般的银杏变成了金黄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独有红枫,经不住秋的勾引,露出了腼腆红润,那红像一团熊熊烈火,相比于花朵的五颜六色、千姿百态,叶子可能会显得单调,不过到了秋天,百花凋零,此时的青松、银杏、红枫的叶儿便领了风骚。
漫山遍野的红叶陶醉了我,赏心悦目的胜景收进了我的心底。
蓝天不知何时增添了层层叠叠的乌云,沉重的气压让人感觉透不过气。徐徐的风也比登山前大了许多,单薄的衣服再也挡不住秋风。
刚到深秋,天空就飘下了雪花。
香山的最高峰叫香炉峰,雪飘飘而下,慢慢化成雾,缭绕在峻峭的峰脊。飞雪遮挡了遥远京城的全景。雪带来的寒冷让我瑟瑟发抖,遂匆匆坐上了回程的缆车。
雪越下越大,盖住了山顶,覆盖了所有植被。披上银装的山顶显得那么清秀,而翠绿的松柏披上雪后显得更绿,金黄色的银杏上落下的雪更加迷人,而满山红叶,更像京城的一道名菜——糖拌西红柿。
雪花在山腰变成了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沿着弯曲的石板路,在色彩斑斓的夹道树中间走下,回到山脚下的停车场。
暖暖的阳光洒在我身上,“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相似的意境感动了我。抬头向山顶望去,戴上素帽的山峰沉默而安详,温和的外貌像寺庙里慈悲的那尊佛,让我景仰。
天晴了,山上的雪还在。山下的风冷了很多,湿漉漉的马路上少了行人。我想,世间没有任何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劳动获得,只有记忆。
转眼又二十多年了……
——根据课文《乡下人家》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