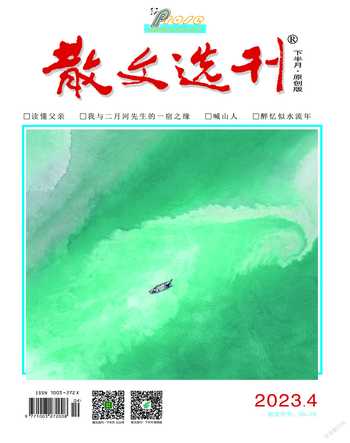补丁衣,那是母亲给岁月“缝花”
罗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们常常感叹时光的流逝,岁月的更替,生活的不易。
好不容易熬到小雪时节,终于下了几天小雨,这让人们真正感到什么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尽管也是冬季,可气温却在20℃以上,人们还是一身短装。
突然,寒风到,温骤降,一夜入了冬。雪花飘,冰棱挂,冬装上场。人们纷纷穿上了保暖衣、羽绒服。于是,便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母亲缝补衣裳的日子,那是一段岁月“缝花”的生活。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每到寒露时节,秋风渐凉,有大雁从北方飞来,母亲便开始为一家人准备过冬的寒衣。
选择一个好晴天,母亲把压在箱里柜里的一家老小的冬衣冬裤翻了出来,在秋阳下晾晒。所谓的冬衣冬裤,其实就是每人一两套破旧的长衣长裤,外加一件破了洞、露了棉花的小棉袄。父母的棉袄自我懂事起就每个冬天都是那一件,由于没有外套(那时叫“罩衣”)穿在外面,乡下人把这种穿法叫“穿禿夹衣”。因为穿了一年又一年,面料上已经油光发亮。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父母结婚时的嫁衣和“郎衣”。
那时候,家里孩子多的,衣裤是老大穿不得了给老二穿,老二穿不得了给老三穿。只有老大隔上三五年可以添置一套新衣衫。我们兄妹的冬衣也是越穿越小,越穿越短,越穿越破。母亲便每一年都要把我们的衣服袖管和裤腿接长一截。小时候顽皮,经常上山、爬树,在山坡上玩“滑滑梯”,衣裤常常磨得千疮百孔,有时还惨不忍睹。母亲没有更多的打骂和责怪,但少不了父亲一顿训斥。母亲却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那时候只有煤油灯。说是煤油灯,只是用煤油照明。父亲就地取材,找几个废弃的玻璃瓶,用棉线捻上一根灯芯,在一块小铁皮上打个孔,穿上棉线,插到装满煤油的玻璃瓶里,就是一盏乡下最常见也最实用的煤油灯。当时农村,一日只吃两餐饭。漫长的冬夜里,母亲张罗着炒些自家生产的瓜子、花生、豆子、红薯片子等,让儿女们晚上当零食。儿女们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各自睡觉。可母亲却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双膝之上托着一个竹制小簸箕(那是做针线活的专用装备),穿针引线,把一家人的衣服裤子缝缝补补。特别是妹妹衣裤上的破洞用不同颜色的小布片缝补好,看起来不像是补丁,倒像是绣了一朵花。因而,尽管衣裤破旧,经母亲缝补之后,倒是蛮好看,也有一种新鲜感。也许,那种情景,才是真正的岁月“缝花”。
记得我上初中时,冬天也只是穿一双解放鞋,一条“哔叽尼”长裤和两件单衣过冬。裤脚也接长了两三次。那件我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旧棉衣,因为我的个子长高了再也穿不成了,才被母亲收了起来。不久前回老家,母亲还找出了当年那件旧棉衣给我看:“这是你读小学时穿的衣服,我舍不得丢,还收哒在柜子里。”这时,我仿佛回到了那个少年时代,仿佛看到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补衣裳的情景。我真想劝母亲,这些旧衣裳就不要再收藏了。母亲却说:“旧衣服好啊,改给孙辈做衣服,做尿片用,小孩子长大了不会糙(磨破)衣服。”在母亲眼里,那不是废品,那是一份珍存的记忆,那是自己青春的烙印;那不是补丁,那是一朵朵岁月的花朵,那是一针针心血的点缀。
后来,儿女们一年一年长大,有的上初中,有的上高中。父母便商量,再省不能省儿女,再苦不能苦后人。我念初三那年冬天,家里不但没有把自家种的棉花送到供销社去卖,还用几年攒下来的布票和一年的收入,到供销社为我们兄妹三人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衣和一套过年的新衣服。裁缝师傅是在邻村请的,上门做了三天。裁缝师傅在剪布料时,母亲再三叮嘱:“要做大一点,要多穿几年。”那件新棉衣,伴我念完了高中,伴我参加工作,伴我结婚生子。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这些过往旧事,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寒冬的冷,什么是生活的苦,什么是父母的爱,什么是岁月的暖。
前些年,听说一个段子,一位城里女孩下乡扶贫,穿着一条膝上有洞的牛仔裤,到一个贫困户家搞慰问,送温暖。一位饱经沧桑的老太太看到女孩的“破裤子”后,激动地说:“孩子,你自己都穿得咯样破烂,还来给我送衣送物,咯吗要得啰。要不我把你的裤子补好后再穿。”女孩听了,哭笑不得。
段子归段子,但老一辈的朴素情感却是真实的。缝补岁月,那才是中国母亲骨子里的一种治家思想,那是她们一生的情感绣结。也许,她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新潮,但她们却知道,可以亲手缝补生活岁月,可以给家人带来冬日温暖,可以让子女留下人生念想,可以让如水的流年岁月“缝花”……
如今,曾经年复一年在冰冷的冬夜里为儿女们缝衣裳的母亲们都已经老了,老得甚至拿不起针线。虽然,她们不能再为儿女洗衣浆衫、缝缝补补、操心劳神了,儿女们也不再需要母亲为他们的破旧衣服打补丁了,但母亲们却常常记得,常常唠叨:“天冷了,地寒了,要多穿衣服,莫冻着了。”
因为,不管儿女们有多大,母亲仍在为你缝补岁月,缝补生活,缝补青春,缝补母爱……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