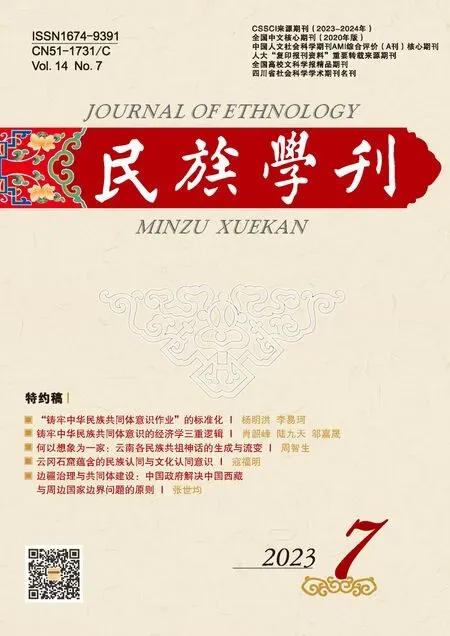何以想象为一家: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的生成与流变
周智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云南 昆明 650092)
在2021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1]神话是历史记忆和社会生境的折射,云南丰富多彩而历史久远的各民族共祖神话中,蕴含着各民族质朴而美好的共同体记忆,揭示了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依存共生状态。云南是我国多民族共祖神话流传最多的省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其中萌发构造的跨族际共祖意识,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生成进程中各民族参与共构的局部历史影像。对于其生成机理的研究,有助于总结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形成的边疆路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的共祖神话
神话是了解特定人群的远古智慧、认知体系、社会发展史等的重要民间叙事。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指出:“神话是关于世界和人怎样产生并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神圣的叙事性解释。”[2]1麦克斯·缪勒认为,“神话尽管主要是和自然相联系,其次和那些显示规律、法则、力量以及智慧特征的证明(神迹)联系,但神话对所有一切都是适用的,没有一件事物能排除在神话的表达之外。”[3]作为“百科全书”的神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体现一个地区各民族间的历史过往和生存状态。R.G.柯林伍德即认为“有一种准历史,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中也找到了它的例子,那就是神话。”[4]
共祖神话是指讲述多个民族源出同一祖先、拥有共同家园,后因各种原因分家分化的同源共祖神话,大多属于自然神话中的创世神话,其中包括开天辟地神话、人类起源神话,以及社会生活神话中的族源神话等。共祖神话是各民族先民运用原始思维创造,并在口头流布中经不同时代不断进行加工而成,展示着各民族同根同源、依存共生、互嵌共享的历史记忆。在此意义上,共祖神话解读近年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重要视角。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华夏边缘》等书中提出根基历史、历史心性等概念,在华夏与边缘区域人群历史互动中形成中华民族格局的理论观照下,对岷江上游羌族的“弟兄祖先故事”,以及英雄祖先黄帝、太伯、蚩尤、盘瓠等神话进行了考证,认为“弟兄祖先”是一种特定“历史心性”下产生的历史叙事,以想象的共同“起源”来凝聚成员是族群认同“根基性”的由来[5]251,合作、区分、对抗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竞争是这类文本产生的主要情境。[6]王宪昭对神话母题及共祖神话有深入系统研究,在对中国各民族神话母题进行归纳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探讨汉族和少数民族神话的共性,认为神话创作思维、民族关系和文化交流等因素影响了神话共性的形成。[7]在其新作《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对多民族同源共祖神话的概念、类型、特征和成因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初步指出同源神话蕴含着中华民族观的自觉,具有现实基础,体现出民族文化互动的高频度。[8]101-103李学敏等指出西南民族“同源共祖”神话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9]王丹立足民族文艺与文化视角,认为同源共祖神话描绘多民族的互嵌共享与聚合发展,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思想,文化根基。[10]另有少量对西南少数民族共祖神话的个案研究,如李斯颖认为云南德宏傣族共祖神话叙事是傣族对历史进行整合和自我调适后形成的一种文化记忆。[11]
既往研究更多关注神话形态和本体研究,或初步从宏观意义上探讨共祖神话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系,但对于各民族何以想象为一家的历史成因、机制及其地方性特征缺乏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未能更深入解读共祖神话背后的历史社会基础。因此,本文拟解析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的地方性表征,探寻其得以建构的成因及影响条件,总结以神话创造和建构为纽带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凝聚过程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
二、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建构的地方性特征
在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都有各民族同源共祖的母题。云南的26个世居民族,特别是云南独有的15个少数民族,主要来源于氐羌系统、百越系统、孟高棉系统民族的先民。诸多民族之间,族源来源分异情况十分突出。但在长期南来北往、东进西来的多向迁徙流动和交往交融中,在云南这片各民族共生并存地域中的交流与交融,促成了各民族之间以共同族源记忆虚构性重构传承认知族际关系的特殊传统。共祖神话充分展示了云南各民族间互助交融的生活图景,从而凸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地方性特征和多样性路径。
(一)云南多民族共祖神话的基本类型
根据王宪昭的统计,目前搜集到含有各民族同源母题的神话305篇,少数民族神话为272篇,其中北方地区民族9篇,西北地区民族9篇,华南地区民族41篇,东南地区民族35篇,西南地区民族178篇,占全部搜集数量的65.4%[8]91,可见,绝大部分集中在云南省。
云南各民族先民对自身起源的探索,形成了精彩纷呈、形态各异的共祖神话,而同出一源是云南地理环境促成各民族间社会关系的艺术表达。云南各民族同出一源的神话类型,主要有“造人”“生人”神话、人类再生型洪水神话、一母所生/兄弟分家等多种母题类型,以及杂糅母题类型。
第一类“造人”“生人”神话中,叙述各民族来源于同一个大神(祖先)造人或同一种自然生人。如基诺族《阿嫫晓白》说道,远古时代没有天地只有水,从炸开的两片冰中走出阿嫫晓白,用身上搓下的泥垢造人,阿嫫晓白教人说话,按照不同话语分成了基诺族、傣族、汉族、布朗族。[12]傈僳族《木筒里出来的人》说,祖先叶木言在金沙江捞木柴时捞到一个木筒,劈开后得一男娃。男娃后来做木人,从鼻孔里吹气变成与他一样的人,留在玉龙山下的成为纳西族的木氏族,来到怒江峡谷的成了傈僳族的木氏族。[13]248-249“生人”神话较多,有人由动物或植物生成、自然感生、人由蛋生成、人从山洞和葫芦中走出等神话。如流传在楚雄大姚县一带的彝族《赤梅葛》的树生人母题,天神盘颇种出的热兹树长大了,生出一对谢泼,生出一双西泼(汉族),一对俚泼,一对腊鲁泼,又生出罗武、撒尼、阿细、阿哲、纳苏、诺苏、改苏各一对。又生出一对傈僳,生出一对摩梭,一对民家(白族),一对哈尼,一对摆衣(傣族)。[14]佤族《司岗里》的石洞出人母题,天神俚和伦创造了天地,又让巨人达能创造了人放在石洞里,人从石洞里走出来,被豹子咬死了三个,从第四个起才活了下来,这个人是佤族,排为老大;之后出来了拉祜族、傣族、汉族。佤族住在了有大椿树的阿佤山上,拉祜族住在竹子多的半山腰,傣族住在了芭蕉树多的平坝,汉族则像大车树一样到处分布。[13]98-100葫芦生人神话在云南各民族中广泛流传,有的是单独葫芦生人,有的与洪水神话结合。如阿昌族《九种蛮夷本是一家》说,开天辟地的时候,只有遮帕麻和遮咪麻两兄妹,婚后生下一粒金光闪闪的葫芦籽,种下葫芦籽后十八年才成熟,破开跑出许多可爱的孩子,遮帕麻和遮咪麻用孩子们第一眼看到的东西取姓定名,成了后来的百家姓;并把他们分发到各个地方定居,成为傣、汉、景颇、傈僳、阿昌、德昂等九种蛮夷的祖先。[13]183-184德昂族《葫芦与人》说道,天王从天宫找回种子,种在海边的葫芦种结出葫芦,暴风雨劈开葫芦后出现103人,有男有女,这些人乘葫芦到陆地后各走东西,便是汉、傣、回、傈僳、景颇、阿昌、白族等民族的祖先。[15]
第二类人类再生型洪水神话基本广见于云南所有少数民族中,从葫芦里走出的几兄弟,兄妹成婚后生育的子女或肉球成为不同民族。彝族《梅葛》讲述洪水淹灭了人种,只剩下两兄妹。哥哥在河头洗身子,妹妹在河尾捧水吃,受孕生下一个怪葫芦。天神戳开葫芦,从中依次走出汉族、傣族、彝家、傈僳、苗家、藏族、白族、回族等九种人。[16]38-58怒族《兄妹结婚》说,洪水后幸存的兄妹俩经过射箭难题后成婚,生7男7女,男的从老大到老七分别是怒族、独龙族、汉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13]186哈尼族《兄妹传人类》讲述,直眼人时代,天神摩咪认为人是怪物,水淹人类。只剩下躲在葫芦里的莫佐佐龙和莫佐佐梭兄妹成亲,妹妹腹部生大哥哈尼族,腰生二哥彝族,手指生三哥汉族,脚板生四哥傣族,耳背生五哥瑶族,都是横眼人,住在山腰、平地、河坝等不同地方。[17]
第三类一母所生、兄弟分化成族母题,即强调各民族的“弟兄祖先”关系。纳西族《人类迁徙记》说,山崩地裂、洪水横流,只有坐在牛皮鼓里的从忍利恩存活了下来,与天女衬红葆白命婚配后一胎生了三个儿子,可是不会讲话。大东巴告知用黄栗树、白杨木、公黄牛等做祭天仪式,三个孩子看到马吃芜菁,一时着急齐声喊出三种声音。一母所生的三个儿子变成三个民族,长子藏人,次子纳西人,幼子民家人。[13]60佤族《七兄弟》说道,古时同一父母所生的七兄弟,爱好各不相同,长大后父母让他们到世界各地找自己该去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本领在湖边、草地、山腰、山顶等找到姑娘结婚生子,十年后回到父母家,爷爷给孙子取名叫汉、白、彝、傣、爱尼、拉祜、佤,后来发展成七个民族。[18]另外还有许多杂糅、复合母题共祖神话,即将造人、洪水、兄妹婚、兄弟分化等结合在一起。
(二)共祖神话表述的基本特征
1.以兄弟共祖为亲缘关系纽带
云南各民族众多的共祖神话尽管母题不一,但均重点描述了各民族间同出一源或一母所生的亲缘关系,以大家庭繁衍分化为隐喻,尤其是以兄弟共祖为最基本的纽带。这些神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各民族的祖先都是同出一源的兄弟,隐喻各民族间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并扩展到地缘关系。而对于兄弟为何分化成各个民族,不同民族的共祖神话中有多种多样的解释方式,如前述纳西族《人类迁徙记》中三兄弟因语言不同分化成藏族、纳西族和白族;佤族《七兄弟》则更为详细地从七兄弟不同的本领、居住空间喜好解释了七个民族的形成和分布格局。
基于长期共居的历史背景,跨越自身族群边界,在尊重他族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共祖神话这一神圣、生动却又饱含情谊的方式, 形成了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亲和亲近,以兄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族际认同传统。
2.以周边共居民族为主要想象对象
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中通常以周边共居的民族作为想象共祖的对象。云南各民族间的共居现象,与历史上民族的形成和通婚,以及云南地理文化环境都有关联性。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羌人向西南迁徙,后来逐渐分化形成藏缅语族各语支。藏语支,包括藏族、独龙族和怒族;彝语支,包括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阿昌等民族。这些民族历史关系密切,文化语言交流深厚。同时,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各民族还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现状,致使各民族在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上有极强的相互认同性。较为典型的普米族神话《洪水冲天》中,就是以周边共居的藏族、纳西族作为想象对象。
在各民族的共祖神话中,以周边民族共居为共祖想象对象,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基本现象。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和差异,有的民族有一定的选择性,只选择特定民族作为共祖对象,而不是涵盖周边所有民族。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其后会在文中作出进一步的回应和阐释。
3.汉族的普遍出现
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中的共祖对象大部分都有汉族。如彝族《梅葛》、佤族《司岗里》、阿昌族《九种蛮夷本是一家》、德昂族《葫芦与人》、哈尼族神话《人和万物是怎样产生的》、基诺族《神秘的茶山》等等,在共祖叙事中都把本族与汉族视为同出一源的兄弟。各民族普遍把汉族视为家人,和历史上汉族不断移民云南紧密相关。秦汉至元代,汉族移民到云南定居的人数相对有限,大部分融入到云南各民族中,甚至出现了“夷化”的趋势。元代在云南设立行省,大量的汉族在云南定居,实现了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实质统一。明代在云南推行卫所制度,大量的汉族军户进入云南,并伴随着军屯、民屯和商屯的同时实施,彻底改变了云南“夷多汉少”的局面。清代继续迁入大量汉族,云南汉族人口持续稳定增加。
正如方国瑜先生总结的,“元代汉人主要住在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在边境亦莫不有汉人踪迹”[19]。汉族移民大量迁入云南,改变了云南的民族结构,汉文化的传播也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随着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的深入,民族感情的加深和共生格局的形成,汉族普遍出现在各民族共祖神话中也是各民族共居共生历史形态的一种表现。
4.同一民族不同支系共祖想象的地域差异
生活在云南同一个地区,特别是同一个坝子的各个民族间的共祖神话,通常情况下会具有共同的母题和同样的故事情节,民族之间通常也互为想象对象。如基诺族、拉祜族、布朗族、景颇族、德昂族等的共祖神话中,具有大致相同的母题,并且互为共祖对象。而同一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支系,往往存在着地域性的差异。如云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族群构成复杂且分布地域广泛,共祖对象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流传于玉溪市新平县的神话《獐子氏族的来历》中,汉、彝、哈尼和傣族同出一源,视为兄弟;而流传于曲靖市罗平县的神话《葫芦里出来的人》中,汉、彝、纳西、苗等民族同出一源。自古以来,云南各民族在历史上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居住地。汉族分布较广,和各民族交流频次较高,而其他民族分布较为不均。因此,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共祖神话因周边民族的分布格局不同而有不同。王宪昭认为这种现象“充分表明民族同源神话中许多带有地域性的特质,不仅体现出神话与地理区位、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也体现出区域性语言特征以及区域板块对神话创作与流传的重要影响,体现出神话作为民间口头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灵活性特征”[20]140,即神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三、共祖想象何以可能:族群生存适应与共生策略
多个民族之间的共祖想象,在神话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云南各民族的神话中普遍存在共祖想象,有的民族神话可能借鉴了其他民族神话的母题,但更多民族的神话有其自身发展演化的内在特性。有学者认为“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由于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密切交往与相互影响,在许多民族神话中叙述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同源关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21]但实际上,我们认为二者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其中有着复杂而特殊的族群生存历史情境和制度、经济、生态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只有回到王朝国家边疆治理开发、族际贸易交流、族群迁移流动、跨文化传播交流与文化认同等多维度交叉的区域史研究中,才能对共祖神话赖以产生的多族群生存样态和区域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更全面、更深入、更客观的认识。显然,云南各民族间的族际共生是共祖神话形成的基础,或者说生存适应中共生关系的调适、选择和博弈促成了共祖神话的形成。但族际联系和关系调适,涉及到诸多因素,并非有了交流与共居的背景,就可以决定共祖的神话想象成为可能。
(一)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理重塑并扩大了各民族交流共生的地理空间
国家整合发展背景下的族际共生关系,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云南族际之间共生认同传统的凝聚与传承,其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最主要生境还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及统一行政化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因为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无一例外“许多族群关系取决于集中化的国家权威的存在”[22]131。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效的边疆治理,对维系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起到了主轴的带动和推动作用。由此,需要跳出族群内部社会政治结构与生产方式的范畴,将各民族共生关系置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和外在社会政治情况变动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而才能真正揭示出外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体系与族群权力关系的运作过程和共生关系的演变趋势。简言之,族际共生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总是在应对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变迁,是一种不断调适的动态关系。
元明清以来大一统政治格局下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治理的有效实施和不断深入,特别是渐次开展的改土归流,打破了以往各土司“开门称臣,闭门天子”封闭割据状况,让各民族在云南拥有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流动性,特别是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边疆并融入边疆,拓展了保障更深入交流的地理共居共生空间。正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两晋时期北方民族关系时注意到:“空间距离是影响族际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古代更是如此。胡汉各族地理位置上相互靠近乃至交错杂居,是两晋时期胡汉族际关系存续和演变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两晋汉人对胡人的认知借助了胡汉彼此空间距离缩小的便利。”[23]明代以后,各民族相对稳定而固定的“大杂居,小聚居”的交错杂居格局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治理中逐渐成形,各民族多向流动交融客观上为彼此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为增进族际认知创造了有利条件,以往那种因地域隔绝而充满野蛮、陌生和不可接近感的传统认知,由于距离的拉近而逐渐在了解中变得鲜活和生动,彼此对待异族的心理状态也渐次改变,神话创造过程中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就有了可以包容且亲近的想象对象。“这种地缘关系的放大和建立更加宽容、宗族边界模糊的认同,也正是国家统治力量对‘国民’进行‘通天下之志’整合的结果”[24]。
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中,绝大多数民族都将汉族作为自己兄弟民族的想象对象,就是明清以后大量内地汉族移民移居云南,深入云南腹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与其他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嵌共居共生格局得以不断形成和稳固,同时也是王朝国家边疆治理客观上重构并形塑族群交流空间及分布格局的结果。
(二)主动学习汉文化和习得汉语言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直接交流
南诏大理国时期,区域性民族政权的建立,曾出现了以大理地区“河赕语”为蓝本的跨族际沟通语言,但是各民族间“皆三译四译,言语乃与河赕相通”。[25]众多族群复杂的语言分异,成为制约各民族交往交流的重要桎梏。“语言的差别给人们的交往设置了极其重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这一屏障所制造的一些客观的障碍因种种社会心理因素而得到加强。”[26]
明清汉族的大规模移居云南,并与各民族广泛地分散杂居在一起,汉文化深入到边疆坝区和山区各民族村寨,以汉文化传播和汉语言的习得为载体,让文化差异复杂的云南各民族,从此有了确实可以依托实现“通天下之志”的语言载体和文化纽带。即使较为偏僻的澜沧县回东一带的拉祜族,在与汉族接触过程中不仅学会讲汉语,还学会了阅读和使用汉文佛经,在语言上也有很多汉语借词,如皇帝、佛礼、香、犁、高粱、铜炮、铜壶、凉粉、豆腐、张、李、正月、腊月等。[27]
汉文化和汉语的传播和习得,极大推进了文化形貌各异的云南各民族间突破历史障碍约束深入交往交流的历史步伐。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之前,云南本土民族之间虽有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与交融,但是整体性的共有文化始终未能全面建构,从而使得跨地域、跨族群的交流活动始终难以在较大范围内有效开展和拓展。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云南以及汉文化在云南各民族地区的有效浸润和传播,使得以汉文化和汉语言习得为纽带和载体,以边地汉文化为特征,构建起了超越各民族文化、各民族共享共用的区域性文化体系的核心。汉文化和汉语言的传播和使用“不仅为冲破各民族特殊多样的文化形貌进行有效交流交融提供了新的文化空间和环境条件,而且为聚合和凝聚云南各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28]周庆生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过程中,存在着跨越族群和地域的通用语言文字共同体,而汉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29]从元明清以后云南历史的实际发展情况看,汉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各民族之间通用语言的载体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汉文化传播看作确立国家威权意志的一种工具,而应该客观看到各民族主动学习汉文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各民族自身为实现对外交流交往的一种利益诉求和发展需求。因为汉文化和汉语言的习得,可以帮助跨越复杂而多样化的族际差异,让各民族能够借助共享的文化载体实现彼此间更有效的交流与交融。各民族兄弟共祖神话的形成与衍变,与各民族交流与共居并存格局和历史样态分不开,而汉文化的传播和汉语言的习得,正是促进各民族深入交流,实现彼此认同的重要载体和纽带。
(三)云贵高原山坝地域结构的聚合力
云南不仅是典型的山区省份,也是垂直地域分异特征最明显的区域之一。坝子是山间的小盆地、河谷冲积平原、较大的山谷等平缓地方。坝子是云南各族人民主要的生活集散地,更是当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生存空间,形成了一个极具辐射能力的坝子社会。正如李永祥认为的那样,“山区与坝区的结构关系,即‘山坝结构’,不仅反映了云南的基本地理特征,也代表了云南特有的民族分布结构,影响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发展。”[30]
从立体布局来看,云南地形山坝相间,坝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水利便利,是稻作农业和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主要居住着汉、回、满、白、纳西、傣、壮、阿昌、布依、水等民族。半山区气候凉爽、坡度较缓,农业生产以玉米和旱稻为主,并饲养黄牛、山羊等家畜,主要居住着哈尼、瑶、拉祜、佤、景颇、布朗、德昂、基诺等民族和部分彝族。高山区海拔较高、气候偏冷、坡度较陡,农业生产以玉米、马铃薯、青稞、荞子为主,并兼营畜牧业,盛产山货药材,主要居住着苗、傈僳、藏、普米、怒、独龙等民族和部分彝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呈立体多样性的多民族混居分布形态,一方面使坝子内各民族受高山河谷的阻隔,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另一方面也使山区和坝区民族间形成不可脱离的资源互换与交流关系,促使彼此形成了互换有无、生计互补的密切联系。族群占据的生态位、经济生产模式与自然条件共同构成了族群生存的小环境。因为在这个小生态环境中,“作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域,山地和谷地是天然的贸易伙伴”。[31]如果族群间能利用不同资源实现交换,族群就可共居并存,而族群间频繁的产品、劳动力和信息交换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使之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由于山地民族和坝区民族生存空间的差异,使得他们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山地民族需要坝区民族的粮食作物,而坝区民族需要山上的茶叶、牲畜等,通常来说山区人民对坝区人民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32]
云南各民族在山坝地域结构中形成坝子社会时,我们也看到了山坝地域结构下对于族群关系的内聚拉力。历史上北方民族的迁徙扩散具有东西南北的多向性,而西南崇山峻岭的山地环境中,南北纵贯、东西并列的高大群山、湍急宽阔的江河往往阻滞着族群的迁移,成为交流互动的天然障碍。因此一旦附着于某个山坝地域环境之中,区域内聚居族群往往就会形成一定的依赖性,同时也会在依赖关系的深化中逐渐局限了族群移动脱离的可能性。“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等诸多族群居住格局形态的地方性表达,正是在地域分异明显的山区和坝区环境中,各民族交错相嵌、相互依存依赖共同构成共生地理景观的真实写照。“‘想像’一个和自己有紧密的血缘关系或是共享相同的语言文化、但是住在远方的群体,是不切实际的。唯有能够看得到、叫得动、平时可以守望相助、危难时能够立刻来救援的人,才是值得去投资情感与时间的群体。在过去交通不便、天然地形形成障碍的情况下,值得依附的群体,必然是住在附近的人。”[33]39因此各民族间“借助神话的诠释与历史上的王权、国家和宗教权威相配合,用以解释整体上的坝子社会与坝子空间的秩序与原则”[34]。但山坝地域环境中基于族群生态位的差异而产生的联系,是否一定会产生共祖神话?很显然未必有这样的必然性。正如利奇在谈到缅甸北部克钦和掸人在山地环境中居于不同生态位而对彼此生活方式和联系产生重要影响时,他依然认为,“对于社会秩序,生态环境是一个限制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因素。”[35]而回到云南民族间的共祖神话,显然山区和坝区民族之间的联系对于共祖神话的产生有重要影响,但这只是诸多影响因素中的一个,并非唯一。
(四)以生存物资交换为纽带,跨越山坝的远距离经济共生链不断形成
由于云南各民族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生产力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差异,居于不同地理区位的民族间一直存在着生存物资交换的需求。特别是明代以来,中央王朝边疆开发力度加大、云南民间商业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各民族间以生存物资交换为纽带的经济共生链愈加紧密。而且随着民族对外交往区域的扩大,跨地域远距离的经济依赖关系逐渐形成。
比如在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就曾形象地描述了楚雄石羊地区以盐的生产和消费为纽带,促进周边各民族聚居共生的历史过程,“傈僳族来煮盐,没有煮成功。汉族来煮盐,头回煮不成,后来仔细想,二回煮成了。大家听说煮出盐,纷纷搬到石羊来。山坡有荞子,山上有大麻,平坝有谷子,平坝有小麦,人户增多了,变成石羊镇。牧羊老人看见了,望着四山咪咪笑。”[16]102-103在红河沿岸哀牢山区,傣族与哈尼族呈立体分布,傣族居住在河谷地带,哈尼族居住在山区。长期以来,傣族与哈尼族都有结“牛马亲家”的习俗。傣族“亲家”常常送米上山,哈尼族“亲家”也经常送柴下山,山上山下互通有无,亲如一家。“这种‘牛马亲家’,既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牲畜繁殖,更把不同民族的两家人,联结成长年互助、相互依存的‘一家人’。”[36]
明代以后,国家边疆开发力度逐渐增强,各族群聚居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以生产生活物资需求交换和贸易往来为纽带,远距离共生链不断拓展。如居住在今石林一带的彝族撒尼人,也通过自己的传说,描绘了撒尼人通过与周边民族远距离交流贸易最终做成初生小女孩衣物和抱被的生动过程,“没有盆来洗,去到泸西买回家……梭子从昆明买,机架从陆良买,踏板索从曲靖买,做成了织布机一台。祥云的棉花好,路南的麻线长,织出一节布,给小姑娘缝衣裳。宜良抽红线,澄江抽黄丝,织成裹布带,把小姑娘背起来。”[37]清乾隆时期,怒江流域一带的怒族人,“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麽些不远千里往购之”[38]。彼此相隔重山,中间还得跨越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怒族人却将纳西族想象为自己的共祖兄弟,显然,两个族群之间跨地域的贸易交往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云南各民族以生存物资交换为纽带的经济共生链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各民族间的共生格局,为各民族共祖神话的产生和演化提供了更远地域和更多元的族群想象对象。
(五)共祖想象对象差异背后的族际选择与博弈
如前所述,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一般是把自身聚居区域周边或者有联系的民族,尽可能纳入到自身的共祖想象体系。如楚雄彝族自治州大姚、姚安、永仁一带的彝族,在其神话史诗《梅葛》中,将汉族、傣族、彝族、傈僳族、苗族、藏族、白族、回族都融在一起。[39]同样来自楚雄双柏一带彝族的神话史诗《查姆》中,传说中将彝族、汉族、傣族等36个民族想象为共祖的兄弟们,明确提出“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的美好愿景。[40]哈尼族的史诗《人和万物怎样产生的》中,周边佤族、傣族、爱尼(哈尼族支系)、汉族都纳入其中。[41]38德昂族的《人类的起源》中,将汉族、傣族、回族、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都视为共祖兄弟。[13]105-106布朗族的《族源传说》中,佤族、拉祜族、汉族、傣族和布朗族是不可分离的兄弟。[41]37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各民族之间的族群共祖想象并非具有完全的对等性。也就是说,同一地域中的各民族,共祖神话的想象对象有差异。如居住在滇西北的纳西族,在古老的东巴经书《创世纪》中将自身与藏族和白族想象为共祖的三兄弟,但其他周边聚居民族并未想象于其中。[42]而在藏族非常重要的珍贵资料《汉藏史集》,说到赡部州之地域与民族类别吐蕃历史上的氏族时,说到汉人、藏人、蒙古人、门巴人是内部四族系,[43]其中并未有绛巴(藏族对纳西族的称呼)。在白族有关传说记录中,也并未见白族、纳西和藏族共祖的具体记载。同时,在纳西族共祖神话中,世代与纳西族交错杂居的傈僳、普米、怒族等民族,并未在其中。而在普米族神话《洪水冲天》中,普米族先民把自己和藏族、纳西族认为是一母同胞的三兄弟。[44]在怒族神话《兄妹结婚》中,怒族先民把纳西族和独龙族、汉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等一起并列为兄弟民族。[13]186与纳西族族源和共居共生关系甚为密切的傈僳族,其族源神话《洪水劫世》中,共祖对象有汉族、彝族、独龙族、怒族,但没有纳西族[45]。从纳西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共祖兄弟神话的建构体系看,周边民族并非完全与共祖想象一致或者一一匹配,甚至出现A民族有B和C,但B和C未必有A,而A民族中没有D,D却把A纳入的情况。此类情况和有的民族将周边民族普遍作为共祖神话想象对象相比,这种有选择的共祖想象,同样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
因此,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我们认为,云南各民族共祖神话的想象体系,并非是一个没有选择的兄弟共祖共生世界,而是存在着复杂而多元的对象选择策略。卡尔·G.伊西科维齐在《老挝境内的邻居们》一文中,曾经特别强调指出:“研究者在考察多族群社会时,必须特别关注不同族群使用的种种策略,无论这些族群是属于族群单位还是教育体系而重新形成的群体。”[22]133但实际上,共祖想象作为“种种策略”中的一种,各民族先民的选择策略显然受特定的族际生境和生存博弈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云南“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地域格局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只存在一个唯一的族群认同,而要具体看该族群到底互嵌于怎样的民族关系网络中,而且自身在这个地方网络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依据自身在地方网络中影响力、控制力以及对于他族资源的需求程度,或许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族群共祖想象对象的差异和不同。如有的民族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不高,来自周边各民族的资源补给互换和支持,对本族群生存都不可或缺,那么可能将共祖神话兄弟圈尽量丰富和扩大,或许是一种较好的拉近彼此情感获取他族支持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有的在多族群生境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其生存博弈和族群共生关系的维持,主要跟周边某些特定民族有关,因此其共祖神话兄弟也就有了特定的选择对象。确实,“不同的种族群体基于历史的和现有的经验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方法策略,来回应不同的社会待遇,并应对群体的生存问题和流动性问题”“不同的种族群体获得有形和无形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周边地区动员这些资源的能力都是不同的。”[46]因此,各民族先民的兄弟共祖想象,需要放在特定的族际历史生境中来具体考察,才能真正揭开共祖想象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不是笼统地简单归因于族群间的共居与共存。
四、想象与现实的互动:共祖神话对族际共生关系历史发展的影响
生存博弈下的地域认同,强化了共生联系和交流,凸显出共居族群彼此认同的强化。共祖神话形成、演变与传承背后的历史镜像,其实也就是族际共生关系不断深化,地域共同体认同逐渐凝聚和提升的历史发展过程。
(一)现实性共生关系是共祖神话想象的起源基础
“神话源于并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是不争的事实,神话叙事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相比,更多地表现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47]。从文化记忆的角度来看,神话研究不仅仅是探究其所叙述的历史事实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阐释其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历史叙述。正如王明珂提出的一样,兄弟祖先是西南各民族诉说共同起源的“根基历史”[48],但这根基性却是各民族在现实性共生关系中不断形成和发展变化的。
自古以来,云南就是一个各民族不断迁移进入,并共同生活的聚居区,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在专属的区域封闭式地自我发展的,而各个民族的历史其实就是同其他民族相互交换、相互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的历史。在各民族迁移流动并不断共居并存的进程中,彼此的交往、联系和融合不断得到加强,形成了相互学习、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密关系。于是,“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新族群认同。”[5]32由此,同根同源兄弟共祖的神话,就是寻求构建这种“新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和现实反映。只有族群边界的模糊与移动,才能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而族际共生认同的强化,恰恰可促成族群边界溶解,成为族群融合的推力,共祖神话的建构与传承传播,恰好成为这一推力不断持续作用的特殊媒介和载体。因此,我们认为云南各民族同根同源兄弟共祖神话,就是寻求构建这种“新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和现实意象,体现着各民族历史上主动寻求改变并冀求稳固共生关系的愿望和期盼。
(二)共祖神话是族际共生关系进一步维系和强化的认同动力
云南各民族以神话的形式促进了共生关系的不断演进,“民族同源型神话以其丰富的母题表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统一的主旋律。”[20]140多民族同源共祖,并且与汉族是兄弟手足,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历史上云南各民族彼此长期共居并存、实现跨族际共生认同的必然结果。其一方面与王朝中央对边疆的治理及制度演进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各少数民族通过不断建构新的集体祖源记忆以主动融入和共构共同体的过程密不可分。因为在决定众多的文化差异中,在哪些群体与范畴的文化是值得保存的议题上,族群运动的努力与成功通常是关键的因素。但由它所建构出来的认同、认知架构,将会回过头来影响当初让运动成为可能的社会与文化结构与条件。[33]172换言之,就云南各民族同祖神话形态所透视出来想象的“弟兄故事”,从共祖神话的神圣性本身而言,“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是互动仪式的核心,它能够打破排外集团间的壁垒,将一个地方共同体的成员捏合进亲密的关系之中。”[49]
很显然,云南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体和谐和团结,是与各民族共祖神话的传承和传播是分不开的。如前述提到楚雄双柏县一带彝族的史诗《查姆》中,不仅将彝、汉、傣、傈僳等36个民族想象为共祖兄弟,而且非常明确地提出“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这样包含天下一家、各族团结和睦之意的朴实理念,其中饱含着云南各民族在复杂多变、阻力横生的历史环境中主动寻求族际团结和睦的诚意和智慧。在一个个题材相异却主题相同的共祖神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各民族共同的呼吁和诉求在神话的传承中不断被强调:各民族是一个个彼此被共生关系所连带且不可分离的母体,彼此之间即使有差异,但同为兄弟手足的“亲缘关系”是建构和处理彼此关系的核心母题。
美国学者伊利亚德认为,神话是原始而神圣的历史,它叙述了事物的产生和存在,论证了人类之所以如此言行的根据。[2]174云南各民族以具有权威性的人类起源神话来建构民族之间的共祖关系,以一种最朴素,也最能直接体现彼此关系的认同方式来阐释这一关系,说明对维护和加强这一关系的决心是神圣而庄严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一份神圣和庄严,才使得这些共祖神话能在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传承至今,为云南稳定和谐的历史民族关系建构和发展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成为助推各民族互识互助形成共同体的认同动力。正如滕尼斯所言,“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50]。
五、融入还是共构:各民族共祖神话创造与传承发展的历史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和发展,既是一个由上而下的开拓过程,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回应和响应过程,也是边疆与内地不断双向凝聚的历史进程。正如翁独健先生所言:“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共同缔造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的伟大国家”。[51]近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学者谈到边疆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时,总喜欢以某民族或某地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为题开展研究,殊不知这样单向的历史认识,未能看清中华民族共同体本就是各民族共同熔铸、共同创造、共同推动、共同建设的历史结果,这个共同体并非某一民族或某一文化独构而成,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缔造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四个共同”的思想和理念,就是对我国各民族共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最好诠释和注明。[52]
早在秦汉时期,《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出的“五帝”世系,记载了华夏和匈奴、越人都是黄帝后裔,同样体现出在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族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以“华夷共祖”思想来实现“大一统”的治理实践。[53]如果说官修的史书记载“华夷同源”,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集团从政治利益的角度强调天下的“大一统”,那么,来自民间口传文学中的“同源共祖神话”,具体就云南这个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边疆地域而言,以兄弟共祖神话为纽带不断深化的跨族际认同,是边疆民族对大一统国家建构历史进程的积极回应,是在大一统国家制度运行中各民族主动寻求趋同并存、以局部整合促进促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努力。在云南各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话中,无论始祖生下的兄弟最终形成哪些民族,其中普遍有汉族的存在,在先祖的起源上,各民族与汉族是兄弟关系,是一家人。这一神话叙事所表达的是云南各民族并未将自己视为中华的“边缘”而被动等待融入,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主动参与共创共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诚挚愿望和智慧表达。
“神话即便被我们定义为超自然的宪章,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可变性是神话的特征之一,只有研究神话的变化,才可能发现这一现象中不变与可变的因素。”[2]265-270云南各民族历史源远流长,其有关族源的神话起源追本溯源定然也是较为久远的历史年代,但为什么在这一古老神话中普遍会出现汉族这一元明以后才大规模进入云南并形成规模影响的民族?其实就是各民族先民利用神话的“可变性”即“变异性”,对现实生境主动进行改良和优化,意图建构区域共同体的历史创造。如果说“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传统中寻求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54],那么丰富多彩的族际共祖神话历史资源,就为我们打开了窥视古人冲破族际隔离和隔阂,如何充满智慧地建构并营造跨族际“共享文化”的又一扇历史之门。
(本文在成稿和修改过程中,承蒙得到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冯智明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庚伦教授、历史与行政学院方天建副研究员协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