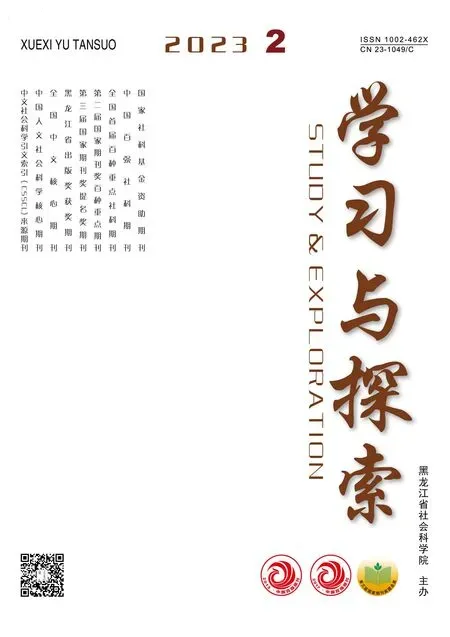记忆共鸣:明中期传奇戏曲历史书写的心理机制
赵鹏程,胡 胜
(辽宁大学 文学院,沈阳 110036)
明清传奇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颇具里程碑意义的一种艺术形式,这一艺术形式正是在明代中期才真正实现从传统“戏文”向文人“传奇”的转变。明中期戏曲的这一转型,不仅是文体特征的转型,实际上也是文本内容的进一步凸显。回顾明中期传奇戏曲的基本内容可以发现,历史题材剧作在明中期戏曲中呈现出一种“聚焦”状态,而且这样一种“聚焦”状态不仅是数量上的聚焦,也是经典作品的聚焦。从数量上看,以《明清传奇综录》所收剧目为例,明万历中期至泰昌间历史题材剧作占比约百分之七十七,而明天启至顺治间则仅占百分之五十一,相差近三分之一。从经典著作上看,像《浣纱记》《宝剑记》等经典剧作皆是以历史题材为特色,时人胡应麟甚至进一步概括道:“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1]426进一步看,回顾明中期文人传奇戏曲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有关剧作不仅在采撷史事,更在史事呈现中诉诸复杂的个体情感。以往的戏曲史研究中曾提出戏曲 “历史心灵化”的概念:“当被制度与环境异化了的情感在历史叙事中展开时,作家早已不是借古喻今,而是借古写心,通过主体的思想意志将历史故事、历史人物强化为个体的情志或情绪诉出,‘我’不仅超越了历史,‘我’亦能动于现实,一种历史为我所化用的崭新观念亦渐次生成,即所谓‘历史心灵化’。”[2]可以说,明中期传奇实际上也呈现出这样一种“历史心灵化”,像《浣纱记》等经典文本,一方面在取材甚至字句上遵循史书,另一方面却又在具体书写中超越历史,能动地表露出对忠奸对立、个人出处等现实矛盾的深刻思考。而且,在明中期传奇文本愈加呈现出“为传奇者若良史”[1]426之潮流,也即愈加接近史书的情况下,也就愈加凸显遵循史实与主体思考的强烈对比,愈加凸显这一“历史心灵化”特征。因而明中期传奇中的历史题材剧作与其说是文本题材上的“历史剧”不如说是文人主体能动的“历史书写”。所谓 “历史书写”,也即创作主体采用历史题材改编、创作传奇文本,又在历史题材中表达文人“文心”思考,进而实现所谓“历史心灵化”。
当我们以“历史书写”为研究视角考察这一问题,便会发现明中期文人传奇戏曲的兴起,不仅是一个在文本层面兼容文体转型、主题凸显的过程,实际上也与文人主体及其更为深沉的内心隐幽有着密切联系。也即是说,“历史书写”及其内在心理机制,实际上正是勾连明中期文人传奇戏曲兴起的重要枢纽。的确,随着明中期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既萌生了颇具时代性的文人主体意识,也延续了明初以“通鉴史学”等为代表的以古鉴今的思想脉络。而当主体意识与以古鉴今的思想线索在明中期汇合,也正为文人内心深处的“历史心灵化”提供契机。进一步看,就明中期文人传奇兴起的内在理路来看,实质上正是文人主体意识所引发的时代记忆,与以古鉴今思想所引发的历史记忆产生“记忆共鸣”。这样一种“记忆共鸣”,一方面与中国古典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历史传统相契合,另一方面又以明中期文人主体意识的崛起为现实动因,进而形成以“历史书写”为外在表征的传奇戏曲文本。因此,我们不妨透过“历史书写”这一外在表征,进一步探索明中期文人传奇戏曲历史书写深处以“记忆共鸣”为特色的内在心理机制,进而发现明中期文人传奇兴起过程的内在思想线索。
一、记忆共鸣的主体:明中期文人的主体意识与著述热情
就文人层面来说,明中期文人主体意识进一步凸显,随之而来的著述热情也得到进一步发扬,这种著述热情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史学、文学著述中,也体现在文人主动投身传奇戏曲等“小道”,进而形成以历史书写为重要特色的创作倾向。
在明中期文人大范围著述活动兴起之前,明初文人著述相对保守,这一方面与明初社会“大一统”的思想专制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文人个体思想中对程朱理学的服膺密切相关。朱熹即曾有“不当汲汲于著述”之论,而明初诸儒更是以此之为榜样,《明史》云:“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3]7222这样一种“守儒先之正传”的思想氛围,不仅是“师承有自,矩矱秩然”的师承规矩使然,时人心中也确有对“轻著述、重躬行”风气的认同,名儒薛瑄就曾言道:“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只须躬行耳。”[3]7229也正是受这样一种时代风气的影响,明代前期各领域的著述活动相对较少。
明中期以后,文人的主体意识日渐凸显,相应的著述热情也随之高涨,明人黄佐《翰林记》总结道:“成化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虽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此天下所以风靡也夫。”[4]随着明中期文人“肆其胸臆”的主体意识发扬,不仅明代前期“笃践履,谨绳墨”的局面逐渐打破,甚至传统经籍也受到影响,以至于“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而且,这样一种“学者多肆其胸臆”的主体意识并非某一个体,而是一种“此天下所以风靡”的时代现象。随着文人世界中的各类著述日渐增多,日渐呈现出一种“会通文史”的著述局面。明中期文人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台阁文学、通鉴史学等单一著述风气,转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文学、史学实践中。像康海、王九思等人既掀起了文学复古的大潮,也转而参与到散曲、杂剧等词曲“小道”的实践中。不惟如此,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他们还表现出浓郁的尚史之风,不仅推扬秦汉史学文风,甚至亲自投身史学实践,编纂《武功县志》《鄠县志》等地方志。与之相类,身处江南的祝允明,则一方面寄情诗文并名列“吴中四才子”,另一方面又展开了多方位的史学实践,或自拟“举、刺、说、演、系”体例以作史论集《罪知录》,或投身《(正德)兴宁县志》等史志编纂。而当时间推移到嘉靖、万历时期,有关士人的著述热情更是空前高涨。他们或像唐顺之一样“述而不作”,纂辑历代史料以成《左编》《右编》《文编》《稗编》《武编》《儒编》等兼及不同领域的资料汇编;或像杨慎、王世贞一样注重考订历代以及本朝史实。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较早投身传奇改创的明中期传奇作家,往往将主体意识与著述相融合。李开先不仅以历史书写融入《宝剑记》,还亲自编纂《章丘县志》《山东盐运司志》等史志文献。他在托名“雪蓑渔者”的《宝剑记序》中表露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仆之踪迹,有时注书,有时摛文,有时对客调笑,聚童放歌,而编捏南北词曲,则时时有之。士大夫独闻其放,仆之得意处正在乎是!所谓人不知之味更长也。”[5]588李开先不仅寄情传奇,更明确表明自己以传奇实现“士大夫独闻其放”的“自放”精神。正如李开先所说“人不知之味更长也”,所谓“自放”又是基于个体内心的“人不知之味”,也即是说,这一“自放”精神又颇具个体独立性。再如梁辰鱼,他不仅以历史书写融入《浣纱记》,更赋予其强烈的主体色彩,他在开篇第一支曲子便自诉道:“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6]449诸如此类,当我们对明代中期传奇戏曲作家的著述情况加以考察可以发现,不仅是像李开先、梁辰鱼、张凤翼等影响颇大的文人名士以历史书写创作传奇戏曲,一些中下层文人也投入其中,这其中既有像姚懋良等几乎被历史埋没的曲家,也有一大批被历史直接湮没的文人作家,尽管我们已经不能知晓其作者姓名,但从《古城记》《金貂记》等明中期剧坛流行的阙名传奇之历史书写便可窥见一二。
二、记忆共鸣的载体:传奇文本共鸣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就文本层面来看,由时代记忆触发的历史记忆,逐渐引起包括传奇戏曲文本在内的各类文本间关于同一主题的“共鸣”。而且,这样一种文本层面的“共鸣”,已经深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学史语境,进而使明中期文人传奇戏曲历史书写之“记忆共鸣”呈现出共时性维度与历时性维度。
共时性维度主要是指各类不同文体间关于同一主题的集中书写,也即同代人之间关于时代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共鸣”。梳理明中期流行传奇戏曲与章回小说可以发现,明代中期既流行有《千金记》《连环记》《古城记》《草庐记》《金貂记》《白袍记》《东窗记》等传奇戏曲文本,也有与之主题相类的《全汉志传》《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水浒传》《列国志传》等演说历代史事的小说文本。进一步看,我们从这些文本中也可发现明中期传奇戏曲之文人性的共时性凸显。例如,同样是由明朝时代记忆引发的“李宸妃记忆”,不仅体现在士大夫征引的朝堂典故中,也体现在《金丸记》等传奇戏曲作品中,更体现在民间社会广为流传的成化刊本《仁宗认母传》乃至《百家公案》等民间通俗文本中。可以发现,这其中显然存在雅俗之别,宫廷、文人视野中更多关注的是以“李宸妃故事”为中心的有关情节,而民间视野中则更多地将其与包拯公案故事相联系。与之相类,同样是由时代记忆引发的关于“吴越故事”的历史记忆,不仅体现在朝堂文士的“卧薪尝胆”的章奏典故中,也体现在产生于文人世界《浣纱记》《五湖游》等传奇戏曲文本中,更体现在《举鼎记》等民间流行的通俗戏曲中。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浣纱记》与《举鼎记》之间显然呈现出不同文本主题倾向,一则以“吴越春秋”的宏大历史背景展现文本深处的个体之思、时代历史之思,一则以伍子胥的英雄事迹展现充满民间想象的“斗宝”等虚构故事。可以说,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兼涉宫廷、文人、民间的“共鸣”,文人传奇戏曲既从民间文学中汲取历史记忆的营养,又日渐成为整个社会的时代记忆。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共时性的“记忆共鸣”中,传统戏文走向了不同于通俗文本的“文人化”道路,进而从“戏文”走向“传奇”。
从历时性维度来看,明中期日渐兴起的传奇戏曲文本,既与同时代各类文本间产生共时性的“记忆共鸣”,也与前代变文、话本、杂剧等不同文本样式间产生“记忆共鸣”。例如,同样是演述“吴越故事”,《浣纱记》中丰富的文人化内涵显然与早期的《伍子胥变文》有所不同。而同样是演述“宣和故事”,文人色彩鲜明的《宝剑记》也与早期的《宣和遗事》等故事文本有所不同。鲜明的时代性,成为明中期传奇历史书写 “记忆共鸣”的一个时代特点。梳理有关故事文本的流变可以发现,在明代文人传奇兴起的过程中,文人群体之所以大量采用前代的故事题材,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故事在民间社会流传的牢固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文人群体对于“因事而作”“因时而著”的文人传统的继承。在明代中期,像纪贵妃事件等“类李宸妃事件”,像杨继盛、杨爵等“嘉靖忠谏群像”,频频出现。而这些颇具时代色彩的事件群落、人物群像,一方面构成了明中期文人的时代记忆,另一方面也直接激发了相应的历史记忆,进而以一种文人化的历史书写融入传奇戏曲,既促进了传奇戏曲文本的文人化,也促进了时代记忆、历史记忆之“记忆共鸣”在传奇戏曲中的文人化演进。
三、记忆共鸣的深层指向:“文心”深处的感性记忆与理性思考
就“文心”层面来看,源自文人著述实践的主体意识,与源自文本间主题共鸣的文人化历史书写,最终在“文心”层面实现“历史心灵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时代记忆与历史记忆的“记忆共鸣”进一步深入“文心”深处。可以说,这样一种“文心”隐幽,已经不仅停留在记忆层面,而是随着“记忆共鸣”的“历史心灵化”,逐渐升华为“文心”深处的个体生命之思与时代历史之思。进一步讲,这实质上是一个由感性记忆层面到理性思考层面的逐渐深化,而这样两重逐渐深入的“文心”之思,也正彰显出文人传奇戏曲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独特之处。
就感性记忆层面来看,明人往往以一种感性的比喻来说明时代记忆与历史记忆的“共鸣”,也即以古人之“酒杯”浇今人心中之“块垒”。这样一种比喻源自魏晋时期,早在《世说新语》中便有“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之说。当明人面对着远比魏晋时期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环境与个体生命历程时,这样一种关乎“酒杯”与“块垒”的感性情感,便更为直接地表现出来,且看明人在不同文体创作实践中的一些表达:
士有异地而相感、旷世而同符者,名位不必一齐,难易不必一致,独其一段嵚崎历落之况,与悲歌慷慨之怀篇什,而人欲出谌吟,而魂如注。千载上冷落既烬之酒杯,千载下翻借以浇热血沸沸之块垒,故不但我见古人式歌且舞,直将古人揖我如泣如诉,盖以天笃者,相取而时地总非所论矣(张吉士《碧山乐府跋》)[7]。
今之所谓南者,皆风流自赏者之所为也;今之所谓北者,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文长之晓峡猿声,暨不佞之夕阳影语,此何等心事,宁漫付之李龟年及阿蛮辈,草草演习,供绮宴酒阑所憨跳!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徐翙:《盛明杂剧序》)[8]。
余幼年即好奇闻。……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学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块磊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吴承恩《禹鼎志序》)[9]151。
嗟乎!我知古宋遗民之心矣。穷愁潦倒,满眼牢骚,胸中块磊,无酒可浇,故借此残局而著成之也(陈忱《水浒后传序》)[9]351。
明中期文人的著述思想,莫不以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尽管张吉士等生活的年代里尚未有汤显祖“情不知所起”的生动总结,但所谓“士有异地而相感、旷世而同符者”的情境便已经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说,这样一种源自“文心”深处的感性表达,不仅实现了作者与古人的“记忆共鸣”,也实现了文人主体之间的“记忆共鸣”,尽管他们所创作的文体有所不同,但这样一种源自时代记忆的情感冲动却是相通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无论是王九思、康海、徐渭、吴承恩等创作者,还是张吉士、徐翙等评论者,无疑构成了一组彼此共鸣的“时代群像”,而文本深处的杜甫、祢衡等一系列历史人物则正构成了一众“历史群像”。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源自“文心”深处的感性情感,直接触发了“时代群像”与“历史群像”的隔空“共鸣”。
这样一种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的感性冲动,直接影响了文人参与戏文创作、改编,最终推动文人传奇走向兴起,我们不妨看几则处于文人传奇兴起不同阶段的戏文、传奇的《家门》开场:
[满庭芳]士学家源,风流性度,平生志在鹰扬,命途多舛曾不利文场。便买山田种药,杏林春熟,橘井泉香。无人处追思往事,几度热衷肠,幽怀无可托,搜寻传记,考究忠良,偶见睢阳故事,意惨情伤,便把根由始末,都编作传吕宫商,双忠传天长地久,节操凛冰霜。借问后房,搬演谁家故事,那本传记(姚懋良:《双忠记》)[10]。
[鹧鸪天]一曲高歌劝玉觞,开收风月入吟囊。联金辍玉成新传,换羽移宫按旧腔。诛谗佞,表忠良,提真托假振纲常。古今得失兴亡事,眼底分明梦一场(李开先《宝剑记》)[5]1131。
[红林擒近](末上)佳客难重遇,胜游不再逢。夜月映台馆,春风叩帘栊。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梁辰鱼《浣溪记》)[6]449。
从传奇戏曲的文体发展阶段看,这三部作品实际上代表了早期文人戏文、文人改编戏文、文人创作传奇几个不同阶段。而从作家身份上看,姚懋良、李开先、梁辰鱼三人,既代表着下层文人、上层文人、中层文人等不同阶层的文人,也代表着北方、南方等不同地域的文人。无论是像姚懋良那样几乎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1)黄仕忠教授曾对姚懋良生平加以考述,认为姚懋良为弘治间人,《双忠记》约作于正德十年之后不久。笔者从此说。另,黄仕忠教授曾征引万历《嘉兴府志》姚氏小传以见其生平:“姚能,海盐人。晚号玉冠道人。少习举业,屡不利,弃去攻医。好吟咏,每谈论,压夺满坐。著医书有《伤寒家秘心法》《小儿正蒙》《药性辨疑》。”参见黄仕忠:《〈双忠记〉传奇为海盐姚懋良所作考》,《文化遗产》2016年第5期。还是像梁辰鱼这样游走于上层文人与市井大众间的中层文人,亦或是像李开先这样出入朝堂的上层文人,他们在投身戏文、传奇实践时,始终是以一种借古人“酒杯”浇灭今人“块垒”的感性情感来展开全剧。可以说,无论身份、地域如何差异,这样一种源自“文心”深处的主观情感却是相通的。更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借古人之“酒杯”,这一过程中却也显示出“历史心灵化”程度的不同。通过上面三则材料可以发现,尽管姚懋良心中充斥着“幽怀无可托”的无奈,但他还是忘不了源自《伍伦全备记》《香囊记》等前代戏文的道德训诫,故而他在自我写心之时也免不了对“双忠传天长地久,节操凛冰霜”的道德褒扬。而李开先《宝剑记·家门》中虽然也有“提真托假振纲常”的道德印记,但仅仅是简单提过,最终落脚到“古今得失兴亡事,眼底分明梦一场”的时代之思与历史之思。再进一步看,梁辰鱼《浣纱记》的《家门》中则完全不见了道德训诫的影子,更多的是文人“文心”的主体抒发。当我们再将这些《家门》与三剧的全剧内容相对读便可发现,一方面是文人“文心”感性记忆的情感深入与纠葛,另一方面则是在这一感性情感深入的同时,理性思考也随之深入展开。
就理性思考层面来看,在这样一种借古人之“酒杯”浇今人之“块垒”的情感冲动乃至感性记忆之外,文人“文心”深处也随之陷入关于个体生命历程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环境的理性思考。如果说关于“酒杯”与“块垒”的情感冲动,直接触发时人心中的时代记忆,进而引发相应的历史记忆。那么,关于“个体”与“时代”的理性思考,则又进一步勾起“文心”深处关于现实“块垒”的反思。而这些“块垒”的根源也正是文人生存的时代环境与个体生命历程。当我们对这些文人的个体生命历程加以梳理,便会进一步发现这一“酒杯”的意义。姚懋良《双忠记》开篇一曲即感叹道“问眼前何物了平生?杯中酒”,进而将其“文心”付诸“搜寻传记,考究忠良”。而当李开先、梁辰鱼等才子文人投身改编传统戏文时,除了感叹“兴废酒杯中”进而“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之外,更是将这一“文心”之思进一步放大:“古来以才自负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5]590的确,明代文人在改编、创作传奇时往往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其中,而要说起这其中最为隐幽“文心”之思,则莫过于关乎“乘时柄用”的“功名之困”。回顾明中期戏曲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少年得意却又罢官归乡的康海、王九思、李开先等人,还是几上春官难第的梁辰鱼、徐渭、张凤翼等人,抑或是像姚懋良一样始终沉郁底层的下层文人,关乎个人出处的“功名之困”始终是他们心头难以抹去的“块垒”。不惟如此,即便是身在仕途,他们往往也会像与冯惟敏一样借散曲、杂剧感叹宦海(如《郡厅自寿》),甚至是像汪道昆一样的仕途通达者,也不免借杂剧以抒发“文心”深处的“功名之困”(如《大雅堂四种》)。的确,正如李贽所论,“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11],面对个体生命历程中难以回避的“功名之困”,明中期文人之所以在传奇戏曲创作中大量采用历史书写,实在是要借此以抒发内心与时代、历史的“记忆共鸣”。
与此同时,在这一感性化的时代记忆、历史记忆之外,文人内心深处又将这一感性记忆升华为关于时代、历史的理性思考。明中期文人所面对的时代环境本就极富戏剧性,甚至这一“戏剧性”也并非是比喻,因为无论是像康海、王九思、姚懋良等面对的正德时代,还是像李开先、梁辰鱼、徐渭、张凤翼等面对的嘉靖时代,本身就是后世戏曲的重要题材。时人虽然也将时代矛盾诉诸《鸣凤记》一类的时代书写,但更多的还是将这些现实矛盾诉诸历史书写,继而呈现出像胡应麟所总结的“近为传奇者若良史焉”[1]426的历史潮流。的确,明代中期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本就难以琢磨,即便是展开思考,也会愈陷愈深。而当感性情感与理性思考相遇,便会使“文心”深处的社会历史之思、个体生命之思显得更为纠葛。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纠葛在“备述一人始终”[12]1的传奇文本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这也正最终促成了文人传奇戏曲在充斥着社会历史之思、个体生命之思的历史书写中走向兴起。回顾明中期兴起的各种新兴文体可见,虽然同样是借古人之事抒今人之情,但在“事”与“情”的关系上,注重叙事的章回小说、民间说唱等艺术形式,显然与注重抒情的传奇、散曲、杂剧有别;而在同样是注重抒情的戏曲文体中,文人传奇又与散曲、杂剧有区别,正如明人吕天成所言,“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12]1。当我们将文人传奇这“其味长”的文体特点,与李开先改编《宝剑记》时的“人不知之味长也”[5]1129的“文心”隐幽相对读,便不难发现,传奇文体实质上更有利于表现文人“文心”深处的个体生命之困及其社会历史之思。
明中期文人传奇的兴起,不仅是一种文体转型过程,也是传奇戏曲之历史书写凸显的过程。这样一种多元化的转型过程之所以能够成立,一方面与中国古代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明中期的文学史、戏曲史生态有关。在明中期的文学史、戏曲史生态中,文人主体意识日渐增强,有关时代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激烈,进而形成一种文本层面的“记忆共鸣”。再进一步看,在“文人”之主体意义、“文本”之载体意义的深处,实质上又有更为深入的深层指向,也即文人个体“文心”深处关于感性记忆与理性思考的纠葛,当这样一种个体“文心”纠葛进入传奇戏曲,便使其文本内涵更为丰富,不仅是要借历史书写之“酒杯”浇洗心中的“块垒”,更是要借历史书写抒发“文心”深处的隐幽,进而使文人传奇戏曲日渐呈现出“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12]1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