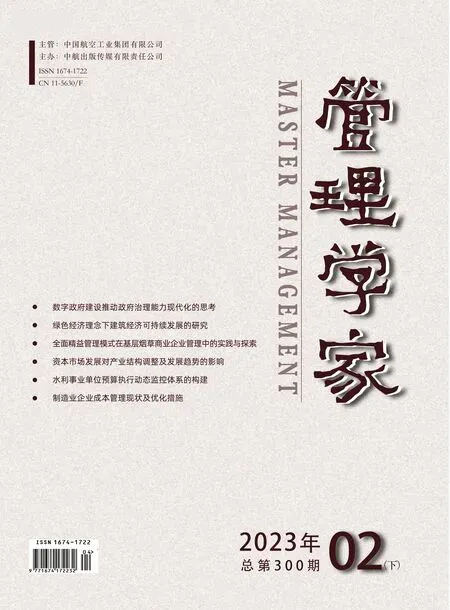风险感知、归因与抵制意愿
——以滴滴打车为例
顾秋英 南京财经大学
关于网约车,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其使用意图,包括信息一致性、胜任力等(Cheng,2018 #131),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文章主要关注一般的风险感知,很少有研究探讨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对危机爆发后个人行为的影响。
笔者认为风险感知与危机责任的归因有关,信任会影响危机事件的结果。因此,提出了研究问题:危机过后,人们对网约车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最后会有什么反应?什么影响了危机责任的归因?风险感知和危机责任的归因如何影响消费者的抵制意愿?
情境危机传播理论(SCCT)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它提供了一个框架,用来理解如何利用危机沟通保护危机期间的声誉资产[1]。
SCCT 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本研究作出了很好的解释:2020 年11 月9 日3 时,南京市虎踞路河海大学附近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行凶者和受害者分别是滴滴平台的司机和乘客,由于车速纠纷,司机刘某将匕首刺入乘客的右臂。这起事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验证实例与佐证,为本研究提出的模型提供了可验证的机会。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框架
网约车的使用行为在我国迅速蔓延,并在使出行更经济和人们生活更方便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但监管不力会产生严重的风险。网约车危机使公众对这些服务的风险认知有了重大转变,可能影响他们继续使用网约车的决定。
抵制行为转变指消费者为惩罚公司推出的不负责任的业务而采取的个人或集体行为,并呼吁其他消费者抵制公司业务,促使公司改变其业务行为。先前关于消费者抵制的研究表明,造成抵制行为可能源于消费者关注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心理动机。
SCCT 理论基于归因理论,假设人们寻找事件的原因,特别是那些消极和意外的事件,并会对该事件产生情绪反应。
SCCT 理论强调危机情境中的三个因素塑造了声誉威胁,包括初始危机责任、危机历史和先前声誉关系。在过去的几年里,危机管理者成功地运用了由SCCT 提供的危机应对策略,保护了组织的声誉。
(一)基本模型
消费者对滴滴的抵制意图的基本分析框架是SCCT模型。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应用此模型,而是引入风险感知,使模型更为完整。信任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应该保护它不受危机的影响。与组织危机中的信任相关的一个结果是在危机后将财务损失降至最低[2]。
对于网约车平台来说,与未来可能需要和使用其服务的利益相关者(消费者)保持信任关系尤为重要。因此假设,信任将预测消费者是否愿意在危机中继续使用组织的服务。
危机发生后,利益相关者通常通过网络社交媒体了解危机,负面宣传往往伴随着不良后果,如信任度降低、不愿意继续使用等,用公众负面评价代替先前关系这一变量改进模型,选择抵制意图作为结果测度,因为这种意图在网约车危机的背景下更可能发生。
(二)模型变量
1.危机历史
就危机历史在现代风险管理中的应用而言,其会导致危机责任、组织信任和风险感知的变化。SCCT 模型将危机历史视为在危机情境中形成声誉威胁的三个因素之一,并假设危机历史强化了危机责任的归因。此外,危机历史与组织声誉既有直接的关系,也有间接的关系。
在情境中,当危机爆发时,类似危机的记忆会降低人们的信任,赋予组织更多的责任归因,因此,提出假设:
H1a:危机历史正向影响危机责任归因;
H1b:危机历史负向影响信任。
2.公众负面评价
公众负面评价是指对一种特定组织属性的宣传,主要导致人们质疑其提供功能性利益的能力,它会影响信任和危机责任。
同时,新闻媒体和互联网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利益相关者多从新闻报道中了解危机。滴滴危机发生后,微博等网站迅速产生大量评论,人们在网上谈论这一事件,并对事件中心的滴滴公司给出了负面评价。负面宣传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比如信任度降低、消费者不愿意继续使用等。
在情境中,公众负面评价是一个重要变量,将其引入模型,取代SCCT 模型中的先前关系声誉。在我们的情境中,如果公众收到更多关于组织和危机的负面信息,他们往往认为组织应承担危机的大部分责任,并降低对组织的信任度。
关于公众负面评价的假设如下:
H2a:公众负面评价正向影响危机责任归因;
H2b:公众负面评价负向影响信任。
3.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是指预测人们对风险事件反应的核心因素[3]。在现代风险管理中,风险感知通常与情绪和信任有关。基于风险感知的负面价值,个体在本质上往往表现出负面的情感反应[4]。
风险—信任单向模型的应用与通过信任意图调节风险的观点一致。滴滴危机爆发后,消费者认为这样的丑闻会对其身体、情感和/或财物造成损害,也会将责任归于滴滴,甚至质疑滴滴组织的可信度。
因此,在模型中引入风险感知的概念,表示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和对社会影响造成的威胁的初步认识。因此,提出假设:
H3a:风险感知负向影响危机责任归因;
H3b:风险感知负向影响信任。
4.危机责任归因
初始危机责任被视为利益相关者认为组织行为导致危机的程度。责任归因对组织具有情感和行为影响[1],并与危机对组织声誉和关系信任的威胁直接相关[5]。
在SCCT 模型中,危机责任归因会影响组织声誉。当利益相关者将危机责任归因于组织时,组织的声誉威胁会增加。
在滴滴丑闻的背景下,消费者认为滴滴应对此次危机负责,倾向于将责任归于滴滴平台而不是司机或乘客,进而对滴滴平台产生更大的反感。因此,借鉴SCCT 模型中的“危机责任归因”,认为当消费者将责任归于危机组织时,他们会降低对组织的信任度,并产生抵制意图。因此,提出假设:
H4a:危机责任归因负向影响信任;
H4b:危机责任归因正向影响抵制意图。
5.组织信任
消费者的信任是指相信产品或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方式能够满足消费者的长期利益。信任是消费者继续使用服务或产品的关键因素。选择信任而不是更广泛的组织声誉作为衡量标准,是因为信任是组织声誉的重要组成部分。
引入变量“组织信任”替换SCCT 中的“组织声誉”,衡量消费者对组织危机的反应。在情境中,对组织的信任度越低,抵制意图的可能性越大。因此,提出假设:
H5:组织信任负向影响抵制意图。
二、方法
采用2021 年2 月(半个月左右)和9 月(两个月左右)两阶段调查的方法,在江苏省南京市开展调查。南京市作为样本城市,因为这起司机持刀伤人事件,对南京市民造成了很大影响。此次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992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628 份。测量采用多项目量表测量了本研究提出的所有结构,在7 分量表上测量结构的项目。
(一)数据分析结果
测量模型检验。测量模型的拟合指标如下:卡方与自由度之比(x2/df)为2.691,小于期望阈值3.0。CFI、IFI 和PGFI 值分别为0.962、0.732 和0.184。RMSEA 为0.052,低于0.08。这些数字显示了测量模型和数据集之间的良好拟合。
Cronbach’salpha 值在0.828~0.947,满足阈值条件,综合可靠度在0.84~0.95,大于基准值0.7。风险感知等六个构念的平均变异数值均大于0.50 的标准。因子载荷范围为0.627~0.940。这两个结果表明,所有结构都具有良好的收敛有效性。
通过比较所有结构的AVE 平方根之间的关系及结构之间的相关性检验判别效度,AVE 的平方根较大,各构念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说明判别效度符合标准。
(二)假设检验结果
公众负面评价越多的人越容易表现出对组织责任的归因(H2a:β=0.18,p≤0.01)。
危机责任归因不受风险感知的影响(H3a:β=-0.09,p≤0.05),但受危机历史正向影响(H1a:β=0.35,p≤0.001),组织信任受危机历史(H1b:β=-0.23,p≤0.001)和公众负面评价(H2b:β=-0.15,p≤0.05)的负向影响,但不受风险感知的影响(H3b:β=-0.03,p>0.05)。
此外,危机责任归因对信任也有负面影响(H4a:β=-0.22,p≤0.001)。抵制意图受到组织信任的负面影响(H5:β=-0.52,p≤0.001),但危机责任归因未能显著预测抵制意图(H4b:β=0.10,p≤0.05)。
从这些结果中可得出结论,除了两个假设(H3a 和H3b)未得到支持,其他所有假设都得到了支持。
三、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围绕“危机情景下哪些因素会影响公众对危机组织的抵制行为”的问题展开研究,将滴滴出行乘客伤害事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SCCT 模型,构建并验证了危机历史、公众负面评价、风险感知、危机责任归因、组织信任与公众抵制行为之间的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危机历史对危机责任归因和组织信任有显著的影响作用。那些对危机历史有更多了解的人往往对网约车的信任更少,并把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组织。
公众负面评价对危机责任归因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当公众感知到更多的负面评价时,会将更多的责任归咎于组织。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公众负面评价对于组织信任的影响并不显著。
风险感知不能预测危机责任归因和组织信任。危机责任归因会影响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当组织的危机责任归因越大,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就会越低。但是,研究结果显示危机责任归因对公众抵制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信任会影响公众的抵制意图。当利益相关者对组织的信任越少,他们越有可能对危机组织采取抵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