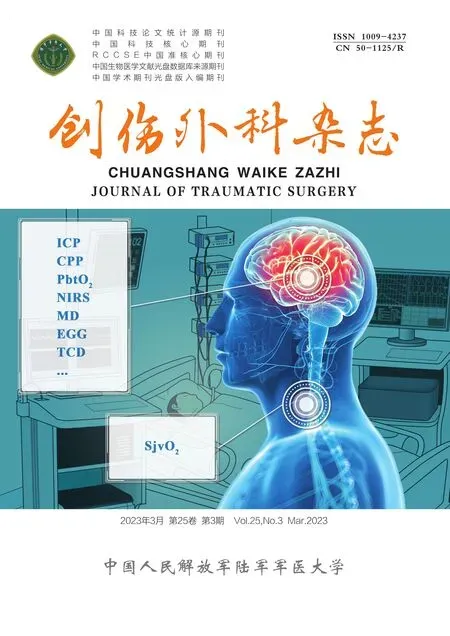袖状胃切除术后骨损害的研究进展
王 强,查斯洛,岑晓霞,张 伟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甲乳疝外科,上海 200003
2019年中国超重和肥胖成人已逾3亿,严重影响健康,每年280万人的死亡与超重有关。随着减重手术的开展,其确切的减重和治愈肥胖相关并发疾病的效果也越发得到肯定[1]。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减重术后以骨流失为表现的骨健康恶化是值得关注的新问题[2-6]。其表现形式为骨转化标志变化(代表性变化为骨吸收生化标志和骨形成生化标志 “非平行性”升高而以骨吸收为主)、骨密度降低以及骨微观结构的变化(表现为骨小梁数量减少及间隔非均一性增宽、骨皮质变薄等)[3-6]。“减重手术,伴随着显著的生化、激素和机械应力改变,带来明显升高的骨折风险”[5-6]。总结分析减重术后骨代谢异常的可能机制,目前认为有以下几种[3-7]:(1)营养成分吸收的变化,包括钙和维生素D吸收障碍等;(2)负重减轻的因素;(3)循环激素水平的变化;(4)体重减轻后肌肉脂肪成分的构成分布改变等。
在不同的减重术式选择中,袖状胃切除术(sleeve gastrectomy,SG)目前逐渐取代Roux-en-Y胃旁路手术(Roux-en-Y bypass,RYGB),成为当前国内外最流行的减重术式[8-10],虽然SG疗效确切、术后并发症少,但越来越多的有关SG后骨损害证据的积累[11-13],提示这种当今最流行的减重术式依然存在损害骨健康的问题。
1 SG对骨健康状态的影响
1.1SG后骨折风险的判断 关于减重术后骨折风险的研究结果其实结论并不一致。与RYGB相比,SG降低体重的效果轻柔,营养摄入与吸收的影响小,从生理角度看,对骨代谢影响应该小。最早的Meta分析提示减重手术可升高骨折风险29%,主要位于非脊柱部位,特别是上肢。主要与吸收不良性而非限制性减重术式相关(RYGB高于SG)[12]。Fashandi等[13]总结了3 439例减重术后(79%RYGB和11%SG)患者在平均7.6年的随访时间中,220例(6.4%)经历骨折。而在调整伴发病和人口统计学因素经1∶1配对,手术患者较非手术患者骨折风险增加2倍(6.4%vs.2.7%,P<0.0001)。骨折发生时间平均为术后(8.2±6.0)年。回归分析提示营养吸收不良型(RYGB)而非限制性(SG或绑带)手术方式是增加骨折风险的独立影响因素。而芬兰的数据(253例RYGB和142例SG)显示术后骨折风险升高5倍[14]。尽管减重手术量迅速上升,但在剔除骨折相关并发症临床资料收集的局限性(如研究对象的混杂性;研究设计的显著区别,包括术式、随访时间、对照人群以及混杂因子的调整;以及骨折发生数量对评价部位风险的效能等),各类减重手术对于骨折风险的增加具有普遍性,而RYGB对于骨折风险的影响更为明显。由于既往对减重手术骨折风险的分析研究中,SG占比偏低,而作为新晋流行术式,SG数量积累虽呈显著上升趋势,但随访超过2年的骨折数据非常有限。随着SG数量积累,特别是长期随访数据的呈现,有望对这一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12]。
1.2SG对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的影响 尽管SG后骨折风险增加的程度尚无明确的数据,但作为影响骨折风险的重要指标,BMD在SG后显著降低却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撑。目前检测BMD有两种方法:双能X线吸光测定法(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检测区域骨密度 (areal bone mineral density,aBMD)。而定量CT能够检测体积骨密度(volumetric bone mineral density,vBMD),后者受检测对象身材体重变化影响较小,从而更为精准地分析减重术后明显软组织体积变化条件下BMD的改变。在减重手术的主流术式中,SG对于消化道的改变较小,因此其对骨代谢造成的损害较RYGB低,特别是腰椎aBMD和全髋vBMD方面的影响[7]。在纳入22项研究、1 905例接受SG的肥胖患者的研究中,发现术后血钙、血25-羟维生素D和血磷升高、甲状旁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PTH)下降,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水平无显著变化,这都提示SG对消化道解剖影响小,营养吸收能够维持,维生素D缺乏现象不明显,但术后BMD仍显著下降,其中全髋BMD下降0.06g/cm2( 95%CI:-0.09~-0.03g/cm2),股骨颈BMD下降0.05g/cm2(95%CI:-0.09~-0.02g/cm2),腰椎BMD无显著改变[15]。Malinici等[16]收集100例男性、97例绝经前和43例绝经后妇女SG后BMD在1年内的时间轴变化趋势,发现在术后1年期间,BMD呈持续性下降趋势。男性在前6个月骨质量损失较绝经前和绝经后妇女均更为显著(分别为2.62%、0.27%和1.58%)。而基于女性患者SG后超重部分减少的百分比(excess weight loss,EWL)减少更多,故难以单纯用负荷减轻来解释骨质量损失。而另一些研究关注了青少年时期,认为研究青少年肥胖人群减重手术后骨积累的指标及骨结构变化有重要临床意义。14~22岁青少年肥胖人群SG后12个月检测aBMD提示股骨颈和全髋分别下降(6.9±1.6)%和(4.7±0.9)%,非手术组分别为(0.5±1.6)% 和(0.2±0.9)%。腰椎aBMD下降(0.3±1.0)%,而非手术组升高(2.4±1.2)%。在12个月观察期间,以主要负重骨胫骨为例,非手术组胫骨远端骨皮质增厚,骨小梁面积减少,而手术组无此变化,骨的显微结构提示SG导致皮质孔隙度增加、骨小梁数量减少和孔隙增大。总vBMD组间没有显著变化,可能是骨小梁孔隙增大、vBMD下降,中和了皮质vBMD上升的效果。在校正BMI变化后,手术导致胫骨硬度指标显著降低。但胫骨强度和受损复合并未因手术而减弱,作者分析SG减轻体重效果平缓,这一指标是否受影响,有待于更长时间的随访确定[17]。
1.3SG后骨转化标志变化状态 动物实验中肥胖大鼠SG后2周与16周对比,血清钙、骨钙蛋白(osteocalcin,OC,调节骨钙代谢,骨钙流失会降低OC水平)水平显著降低;而ALP(反映成骨细胞分化状态,高水平提示骨的钙沉积不足)、I型胶原N端前肽(N-terminal propeptide of type 1 collagen,P1NP,作为代谢产物进入血尿,反映骨形成水平,高水平用于诊断骨质疏松的重要指标)和I型胶原C端末端肽(C-terminal telopeptide,CTX,骨质中唯一的胶原成分,反映骨质吸收的指标,高水平提示骨基质降解增加)升高,同时伴有BMD的降低[18]。肥胖可通过直接或间接抑制成骨细胞功能影响骨代谢,患者在减重术后除CTX、P1NP、血清总OC及非羧化OC均有显著性升高外,反映破骨细胞活性的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5b(tartrate-resistant acid phosphatase 5b,TRAcP5b)也显著升高,而RYGB后升高幅度较SG后更为显著。肥胖导致的CTX/PINP比值升高和TRAcP5b/CTX比值下降提示骨吸收减弱,而手术能够逆转这两个比值,提示肥胖所抑制的骨代谢被减重手术所激活,形成术后的高代谢状态[19]。
2 SG后骨髓脂肪组织(bone marrow adipose tissue,BMAT)含量与构成的变化
BMAT是骨骼内部以特定的方式分布,与白脂肪(主要作用为储脂和能量储备)和棕色脂肪(主要作用为介导生热转化功能)功能截然不同的第三类脂肪组织。BMAT可分为结构性BMAT(cBMAT)和调节性BMAT(rBMAT),两者在分布范围及造血潜能方面不同,对营养状态变化的反应也不同[20-21]。BMAT被认为是新的骨骼完整性的生物标志及全身能量代谢的调节因子,其增加与骨皮质减少、骨密度降低、骨体积下降、骨形成速度减慢及骨质疏松等相关[22]。总结BMAT调控骨的重塑型机制可能为:(1)调控骨髓脂肪细胞和成骨细胞共同前体细胞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化;(2)提供成骨作用中作为能量来源的游离脂肪酸;(3)分泌破骨细胞分化因子(receptor activator for nuclear factor-κ B ligand,RANKL)等因子促进破骨作用。BMAT具有内分泌器官特征,在特殊能量代谢状态下,以自分泌/旁分泌的方式分泌特异性脂肪因子,形成特定的骨髓微环境,调节成脂/成骨细胞种系分化走向,进而影响骨的代谢与更新[23-29]。
研究表明,BMAT与BMD呈负相关,且是骨骼微结构与机械力学指标的负性预测变量。Bredella等[30]发现SG后成年人[(49.5±13.6)岁]腰椎骨vBMD显著降低,而青少年[(17.8±2.5)岁]则降低不明显,两者腰椎BMAT含量均有升高,其变化幅度与体重和BMI的改变呈比例,体重变化越小,BMAT积聚程度越高,且与骨的发育状态无关。SG后在腰椎和股骨干骺端均检测到显著的BMAT积聚,而RYGB对此影响不显著。研究还发现SG术后12个月内体重减轻量与BMAT量呈正相关,以此解释了SG较RYGB降低体重和体脂的效果微弱,反而出现BMAT的积聚[7]。SG后BMAT积聚也可能与负能量代谢状态有关,体内能量代谢状态变化会改变BMAT的成分,并与体内激素水平和免疫调节因子变化有关。短期高热量饮食(热量过剩)可显著增加体重、皮下和内脏脂肪以及BMAT含量,随后的禁食(热量缺失)可使L4腰椎BMAT含量显著增加,且禁食期间体重下降比例与股骨干骺端BMAT变化比例呈显著反比例关系。由此说明BMAT是特殊的脂肪组织库,对外界能量代谢波动作出迅速而可逆的反应[31]。BMAT不再被认为仅仅是骨髓腔的充填组织,在维持骨完整性和调节能量代谢方面有重要作用。BMAT异常积聚在热量限制过程中是这一脂肪组织库的特殊表现。禁食期间,腰椎rBMAT脂肪饱和度指数显著升高,而股骨cBMAT饱和度指数和非饱和度指数及胫骨cBMAT非饱和度指数显著下降,提示BMAT成分变化在能量代谢变化过程中反应不一致[32]。
3 SG后消化道激素变化与BMAT关联的基础研究进展
减重手术后体重迅速降低导致的负荷减轻引起骨质流失和代谢活跃;手术所造成的消化道激素水平变化也会影响钙质吸收以及骨质代谢[33]。RYGB较SG对钙磷吸收与代谢影响更大,RYGB术后血钙和25-羟维生素D水平低而血磷反倒升高,且术后更容易发展成为继发性甲状旁腺机能亢进(secondary hyperparathyroidism,SHPT)[34]。SHPT术后1年发生率,RYGB为33.2%而SG为17.8%;术后5年分别为56.6%和41.7%。SG术后几乎没有钙缺乏的表现,显示这种术式对解剖影响小,从而对营养吸收影响微乎其微[35]。由此可见SG后消化道激素水平的变化,可能是引起BMAT积聚关联的骨质损害的另一原因。
SG影响最为深刻的消化道激素是胃饥饿素酰基转移酶(ghrelin O-acyltransferase,GOAT)/胃饥饿素(ghrelin)/生长激素促分泌素受体(growth hormone secretagogue receptor,GHSR)系统。ghrelin是体内唯一的促食欲激素,经GOAT转录修饰后可在血循环中产生两种类型的胃饥饿素:辛酰化胃饥饿素(acyl ghrelin,AG)和去辛酰化胃饥饿素(des-acyl ghrelin,UAG)。二者的区别在于AG第3位丝氨酸的羟基被辛酸酯化,而这一过程也是ghrelin与GHSR-1α结合的必要步骤[36]。一些临床数据表明,SG术后ghrelin水平明显下降与腰椎BMD的显著下降密切相关[37]。同时也有研究提示无论热量过剩或热量缺失期,血中胃饥饿素均与BMAT含量呈现反比例关系,即显著的胃饥饿素水平下降与BMAT积聚相关[31]。而另有研究表明,胃饥饿素的构成比例也影响骨髓微环境脂化的走向趋势。在大鼠骨髓实验模型中发现AG和UAG均可刺激胫骨骨髓脂肪细胞积聚[38-39],而UAG的作用依赖于GOAT(定位于骨髓脂肪细胞的细胞质和大/小转脂囊泡的内膜)的辛酰化作用和与GHSR受体的结合[38],这也提示SG后胃饥饿素的不同功能状态也会影响骨髓脂肪组织分化与积聚的程度。
BMAT的分化受一系列转化因子调控,其中过氧化物酶体增殖因子活化受体(proliferator peroxisome activatived receptors,PPARγ)是决定脂肪细胞命运的重要环节。胃饥饿素的变化通过何种途径影响PPARγ的功能状态呢?一个有趣的现象是GOAT与PPARγ共同定位于胫骨骨髓脂肪细胞[38],是否提示两者之间的功能联系?前脂肪细胞分化需要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及其激酶的参与,作为脂肪细胞分化起点的PPARγ,其功能调控的复杂信号通路网络中,需要mTOR的参与,即mTOR对外界营养状态和激素水平变化作出反应,影响脂化作用的机制之一就是改变PPARγ转录后的功能调控其表达水平[40-42]。而另一些研究则证明胃饥饿素在肝脏细胞通过mTOR-PPARγ信号通路诱导脂肪沉积[43]。这些基础研究数据提示,SG术后消化道激素的变化特别是胃饥饿素的变化,可能影响SG术后BMAT的成分和功能,具体机制和更为明确的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
4 展望
如本文开头所述,SG目前已是应用最为广泛的减重手术,其最大的优势即消化道改变少、并发症发生率低,但仍有骨健康状态损害等并发症。笔者曾提出有关SG后mTOR异常激活促进糖尿病缓解的假说[44],且在糖尿病大鼠模型下丘脑验证了SG后胃饥饿素水平下降异常激活mTOR通路的现象[45]。进一步可以推导SG后BMAT异常积聚的现象:SG所造成的GOAT/ghrelin轴改变,即低胃饥饿素水平,低AG/UAG比例,造成骨髓局部相对的UAG优势,通过GHSR受体作用GHSR→mTOR→PPARγ,促使骨髓脂肪细胞增殖,并进一步通过内分泌/旁分泌方式形成促进脂化的局部微环境,包括促脂化转录因子PPARγ、脂环素以及促进破骨的RANKL,最终影响骨代谢。即:ghrelin/GOAT-GHSR-mTOR-PPARγ。明确减重新术式SG改变胃饥饿素这一体内唯一的促食欲激素并与另一具有内分泌功能的BMAT微环境变化的相互关系无疑对SG后骨代谢异常的机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这对于在解决治疗肥胖这一世界性健康难题过程中出现的骨健康新问题,进一步提高代谢手术后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作者贡献:王强:收集文献、撰写论文;查斯洛、岑晓霞:协助查找文献、论文起草技术支持;张伟:论文选题及讨论方向、设计论文框架、修订审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