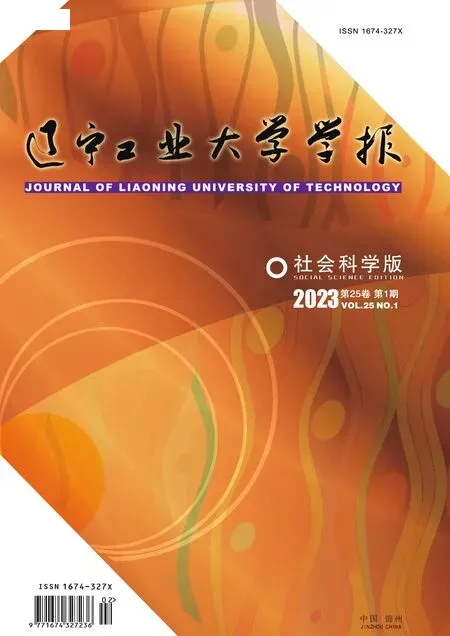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王秀岩,镡鹤婧
本刊核心层次论文
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王秀岩,镡鹤婧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超越了西方感性主义幸福观、西方理性主义幸福观以及西方基督教幸福观,科学地诠释了幸福的基本内容,即幸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辩证统一、创造性与享受性的辩证统一、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幸福思想;基本内容;当代价值
幸福,这个话题是人们一直追求和向往的,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探索和实现幸福生活的历史。人们对于幸福是什么这道思考题,从古至今,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回答,他们受所处时代的影响,站在不同的角度,给幸福下了不同的定义。马克思辩证分析了以往哲学家们对幸福的思考,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全面的幸福思想。总的来讲,马克思认为幸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辩证统一、是创造性与享受性的辩证统一、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一、马克思对幸福的辩证阐释
(一)幸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既批判了西方感性主义夸大物质幸福而贬低、摒弃精神幸福的观点,也批判了西方理性主义片面强调精神幸福,从而忽视物质幸福的观点,认为幸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辩证统一。第一,幸福的物质性是指,为了维持人的存在和发展而对物质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依赖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531衣、食、住等基础的物质生活需要是人最基础的需要,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条件,也是我们幸福不可或缺的基础物质条件。虽然物质需要的满足不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条件,但是,没有物质需要的基本满足人就无法生存,就更不用谈论幸福是什么了。第二,幸福的精神性是指,人的精神世界的存在和发展对精神生活条件所产生的依赖关系。人是理性的存在,也追求精神幸福。马克思曾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46简言之,人不仅能生存,而且还能意识到自己的生存,而动物不能,这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所以,人不仅仅局限于能够意识到物质需要,而且还能够意识到更加丰富的精神需要。精神需要的满足让人们体验到了实现人生价值和理想等更为高级的幸福,也是物质需要的升华。第三,幸福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并没有把两者割裂开来,在强调物质幸福的同时也着重强调了精神幸福。一方面,物质决定意识,即物质性决定精神性。人们的幸福是以物质性幸福为基础的,只有合理的和基本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后,精神需要才会被需要,并最后得以满足。另一方面,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即精神性具有相对独立性。积极健康的精神需要可以为物质需要提供智力支持,推动物质幸福向前发展;消极的精神需要会阻碍人的物质需求的发展,从而阻碍幸福的实现。总的来说,只有把人的物质需要和人的精神需要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物质需要在不断增长的同时精神境界也不断得到提升,继而不断增强人们的幸福感。
(二)幸福是创造性与享受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反对苦行僧式的生活,倡导人们追求和享受幸福,认为幸福是创造性和享受性的辩证统一。第一,幸福的创造性是指,通过创造性实践活动来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幸福。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177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桥梁。人通过劳动能够得以生存,也通过劳动实践不断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体现了劳动的创造性。第二,幸福的享受性是指,通过享受自己或者他人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取得的幸福。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不仅创造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并享受到了物质幸福,而且也创造了精神财富、丰富了精神世界,同时在劳动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不断实现自身价值所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这体现了劳动的享受性。第三,幸福是创造性与享受性的辩证统一。创造性是享受性的前提,享受性是创造性的动力,即创造性是第一性的。在正常情况下,劳动者既在创造的过程中享受幸福又在享受中创造幸福,这是完整的、真正的幸福。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发生了异化,劳动者既失去了创造幸福也失去了享受幸福的权利。“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的手段。”[3]258-259工人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每天都需要劳动,但是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自己,反而被这些劳动产品所支配和统治。由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只感受到了身心俱疲,却感受不到劳动创造所带来的幸福,更多的是感受到不幸。因此,只有克服劳动异化,劳动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和异己力量,劳动从谋生手段变为自主的、积极的活动,工人阶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才能最终实现创造性与享受性的辩证统一。
(三)幸福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既反对片面追求个人幸福注重自己的利益,又反对只注重他人利益忽视个人幸福,认为幸福应该是个人性和社会性的辩证统一。第一,幸福的个人性是指,个人根据自身的需要、欲望来从事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和实现从而获得的愉悦感。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个人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直接体现着个人的需要。没有个人幸福的实现,社会的幸福也无从体现。第二,幸福的社会性是指,对社会共同的利益和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和满足后从而获得的愉悦感。马克思指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0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还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同样,个人想要实现幸福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第三,幸福是个人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分割。社会性的幸福不是简单地把个人的幸福加在一起,而是把个人性的幸福与社会性的幸福有机地统一起来。社会性的幸福是个人幸福实现的基础和保障。在社会的条件下,人们通过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为个人的幸福打下基础;同时,社会的发展水平也决定着社会发展的程度,也影响着个人幸福的实现程度。因此,社会有义务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样,个人幸福的实现也应该把社会幸福放在首位,为全社会的幸福作出贡献。所以,只有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四)幸福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幸福,有人认为能够吃饱饭、有地方住就是幸福;也有人认为身体健康、事业顺利就是幸福;还有人认为在工作岗位奉献自己力量就是幸福……对于幸福的回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第一,幸福的主观性是指,每个人的需求不同,根据意识到自身的不同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和实现后获得的幸福感,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但是,幸福也不仅仅是人的主观感受,它也受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客观性。第二,幸福的客观性是指,对自身的不同需求得到一定满足和实现后获得的幸福感所作出的主观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整体来看,首先,幸福的内容是客观的,它会随着个体需要表现出不同的差异,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次,幸福的主体是客观的,人的意识就是对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而人作为现实的、历史的有意识的人,若没有对幸福的需求,主体也就没有对幸福的需要,也不会有进一步的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最后,幸福本身就具有客观性,是因为物质世界是客观的,它也会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和物质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第三,幸福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辩证统一。首先,客观性决定主观性。幸福不是主观任意的,是有条件的,受客观的物质条件制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和历史背景下,人的需要和欲望不同,然后反映到人的主观意识中,从而决定了人对幸福的追求不同。其次,主观性反作用于客观性。当人的需要和欲望得到一定满足后,又会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和欲望,并激励人们不断地进行实践活动,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达到幸福;反之,如果人的需要和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感受不到幸福,就无法推动实践活动,也不能满足人的幸福。最后,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于实践。幸福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实践活动去实现。人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主体客体化的运动;同时又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自身新的需要来进行新的实践活动,这体现了客体主体化的运动,最终在这两个运动中实现幸福。因此,在实践基础上的主客观双向互动为实现幸福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内涵蕴含着深刻的现实性、明确的阶级性以及鲜明的辩证性。
(一)现实性
马克思幸福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进行了宗教批判,进而揭示了人的本质,深刻地展现了“人”与“幸福”的异化,继而生成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即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指的是人们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世界,发挥自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来不断进行实践和创造,而不是立足于“彼岸世界”通过对神的信仰来实现的虚幻的幸福。“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3在宗教世界里,人们总是信奉来世,认为来世会快乐和幸福。因此,人们就安于现状,把期待放到来世。但是,追究其本质,人之所以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幸福的绝望。宗教剥夺了人这个现实主体的存在,阻碍了人追求现实的幸福。这时,马克思意识到幸福必须突破宗教的束缚,放弃来自宗教虚幻的生活,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用理性的力量,通过实践不断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这样,人们的幸福就在坚实的物质基础的支撑下,坚定自身追求和实现幸福的决心,最终真正地实现主体的现实幸福。
(二)阶级性
马克思幸福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里的阶级性是指,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真正实现全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幸福。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幸福都是片面的和狭隘的,奴隶主阶级的幸福是建立在对奴隶的剥削和绝对占有的基础上实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幸福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对土地等不动产或者占有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实现的;资产阶级的幸福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占有的基础上实现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解放无产阶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幸福。他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4]无产阶级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实现自身的解放和普遍幸福,而不是少数人或者部分人的解放和幸福。因此,要想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实现真正的幸福,只有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这是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独特之处,也让马克思幸福思想更有生命力,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的阶级性特征。
(三)辩证性
马克思幸福思想具有鲜明的辩证性。这里所谓的辩证性是指通过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幸福。幸福是人们总想一直拥有着的永恒的、绝对的,但是站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看到的幸福是发展的、具体的。马克思指出:“即便是最幸福的人也有忧伤的时刻,太阳不会对任何凡人永远露出微笑。”[5]在最幸福的时候也有忧伤的时刻,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幸福思想具有辩证性。幸福是一个主观的范畴,不同的人在同样的条件下会有不一样的幸福感受,自己觉得自己幸福了,那确实是幸福的;但是幸福又是一个客观的范畴,人的需要并不是纯粹的主观,它在人的劳动实践中不断发展,最终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体现了幸福的客观性。幸福是不断发展的,是目的也更是过程,我们只能不停地接近它,而不能彻底地完成和实现它,这体现了幸福的发展性。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来自对幸福的渴望和超越,同时对幸福的追求不仅是对结果的追求,更是对过程的享受。综上,不管是最幸福时刻掺杂着忧伤,还是主观性或客观性、劳动性或享受性,都体现着马克思幸福思想的辩证性特征。
三、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物质幸福观
马克思的幸福思想有利于人们克服错误的幸福观念,树立科学的幸福观。人们对幸福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但是,在追求和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有些人却对幸福观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的价值观受到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出现了只追求个人幸福或者物质幸福,从而忽视集体和精神幸福的现象。说到拜金主义,顾名思义,以金钱至上,以为金钱是万能的,直接体现着资产阶级的幸福观。在拜金主义者眼里,金钱支配一切,什么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金钱和幸福并不相等同,如果将两者等同起来,人们对金钱的欲望只增不减,违法犯罪行为也会越来越多,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享乐主义,以个人快乐为目的,在短暂的人生里及时行乐,重视个人的物质享受。这种观念会导致人们没有理想和斗志,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分析马克思幸福思想关于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有机统一的观点,能够指引人们走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的幸福观,进而引领人们实现最终幸福。
(二)有利于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幸福的源泉,幸福在劳动中实现,劳动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我们每个人都要付出劳动,并且享受和创造劳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得到发展和提高,这就导致了有些人开始沉迷于物质享受。首先,人的幸福不仅仅在于物质享受,而更在于创造,更在于劳动,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可以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幸福和快乐。只有让劳动成为主流,人人通过辛勤的劳动,在劳动中肯定自己、享受并实现自身价值,才能获得满满的幸福感。其次,要营造全社会尊重和热爱劳动的氛围,要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地位。劳动者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影响着劳动的积极性。最后,国家和政府在制定决策中,要从劳动者角度出发,保障劳动者的权益,提高劳动者地位,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
(三)有利于引领美好生活的实现,增强人们的幸福感
马克思的幸福思想在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和向往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时代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幸福感也相应地得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体现着多样化与全方位。但是随着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情况,导致发展不能够完全满足人民的需要,阻碍了人民对幸福感的获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6]这是对马克思的幸福思想的完美诠释。因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幸福思想为指引,逐渐缓和并解决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追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矛盾,提升人民的幸福感,最终实现幸福生活。
(四)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幸福生活提供保障
在新时代,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转化,幸福也有了不同的展开和实现。幸福,站在宏观的角度上,是时代发展的问题,站在微观的角度上,是关系人的生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深刻现实问题。人是社会中的人,个人幸福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离不开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综合进步。就其现实性而言,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社会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影响着个人幸福的实现程度。因此,社会要充分尊重每个社会成员追求和实现幸福的权利,为个人幸福的实现提供和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在理论上,表现为人的类特性得到充分的发展。具体而言,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在通过沟通交流和展现自身能力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还能很好地进行再生产,生产出新的、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因此,只有在全面丰富的社会关系中,个人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交往中,才能进一步获得自身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并最终获得幸福。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2.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十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548.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1: 134.
10.15916/j.issn1674-327x.2023.01.003
A8
A
1674-327X (2023)01-0007-04
2022-09-26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L19BKS008)
王秀岩(1996-),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生。
镡鹤婧(1972-),女,辽宁营口人,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叶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