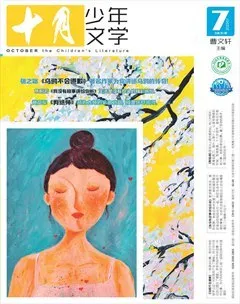【评论】与自我的一次倾心交谈
张之路老师的作品,是照拂着我们这辈年轻人成长的一道光。电影《霹雳贝贝》上映那一年,我才九岁。直至今日,我还能回忆起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时内心的惊讶。小小幼稚的内心里,仿佛被谁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之后若干年,我才理解那是一种叫作科幻的东西,其中既有科学,又有幻想。现在的孩子被五彩斑驳的科技包围着,应该已经体会不到那种心境了。作为中国第一部儿童科幻电影,《霹雳贝贝》是让无数少年萌发科学理想的第一株幼苗,也是搭建起孩子们幻想世界的第一块坚实的方砖。
《乌鸦不会道歉》一文中的科普精神,一如《棋门幻影》(发表于本刊2021年8月)《雨燕飞越中轴线》(发表于本刊2022年10月),这种科普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描述,而是融合了历史的沿革,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利弊上的分析。其中既有科学的陈述,也有对科学本身的反思,从而给科普注入了人文精神。我们不仅能读到仿生学的发展变化,更从中读到百年间人类对动物由陌生、了解、利用、模仿、学习直到敬畏的历史。对自然与科学的双重尊重在文末得以展现,二者和谐共生,共同照亮了人类的进步之路。
从深层次的表达来看,《乌鸦不会道歉》的主线由三个故事组成,这三个故事发生在三代人的身上,但是其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面对选择。
选择是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选择造成矛盾、成就冲突、展现人性。小说在写法上,把情节的切入点放在选择之后,我姑且称之为“选择的后延”,或者是“选择的后遗症”。人物做出某种选择,继而陷入后续引发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在这时,选择都已是过往既定,无法变更,无论对错,它都对现时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本身,如果再掺杂个人情感,就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不安与焦虑。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自由选择是沉重的负担。任何信条、任何主义或者别人的建议,都不能成为你选择的借口,这些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是用来逃避责任的。你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者,你必须为自己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承担绝对的责任。
《乌鸦不会道歉》即是如此。刘子舟选择指出三三妈演讲的错误,生物小组老师选择了告诉老师偷兔子的实情,刘爷爷选择让乌鸦执行离间计任务,甚至乌鸦,也是在一群陌生人群里选择了它最熟悉的一个。选择一旦完成,后续的责任就接踵而至。选择的正确并不意味着背后就是坦途,甚至恰恰相反,越是正确的选择,背后的道路可能愈加坎坷,充满煎熬、磨难。
小说探讨的还不只选择和责任问题,而且包含了某种社会问题——情感表达的欠缺。乌鸦的道歉在文本里成了一种情感表达的符号,让人们思索道歉本身的含义。毕竟在我们熟知的各种文化系统里,道歉都等同于承认错误。三位当事者“我并没有做错”的感受贯穿始终,没有做错事却出于情感的愧疚而造成了自己心理的巨大负担。这种对道歉的责任、情感双重认知,使得内心的愧疚、同情无法表达,纠结成了潜流在文字中的情感暗河。作者选取的情境,全都源自真实的生活,更容易引发读者思索、困惑、共鸣。
好在,儿童文学相比成人文学,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儿童文学不仅提出问题,通常也给出解决方案,《乌鸦不会道歉》一文实际上也给出了某种答案,那就是使“道歉”回归其文字上的本意,即“说出歉疚感”。这样一来,“道歉”就剥离掉了对错、责任,它只回归到表达人的自然情感,从而释放了自己,达成了和解。
《乌鸦不会道歉》是一部精彩的儿童小说,不只在文字间荡漾的科学精神和科普意义,更表现在它的文字简洁而不失细腻,情节现实而满怀情感。正是这种真诚和坦白,用文字纾解了每个读者的内心,让人自然地安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