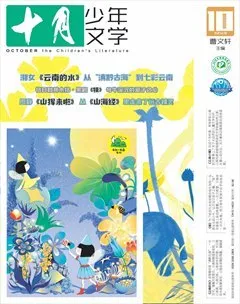春山




没有人说得清楚一些变化发生的时间。
比如冻得坚硬如铁的泥土何时变得松软,枯草上的马牙霜哪天消失,背阴处水塘里的坚冰以怎样的速度一天天变薄,薄到最小的孩子也能轻而易举拆下一块举着,背着太阳端详上面纹路繁复的冰花;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春山的风里何时多了一丝暖意,暖意里裹挟着花开的气息。
水从山肚子里淌出来,凛冽又清澈,经过了山谷、悬崖、缓坡、森林、草地,带着途经的那些植物的气息,溪流边生长的伞形科、唇形科、豆科作物伸展着柔嫩多汁的枝条;亭亭如盖的树木顶端覆着一层鹅黄、浅绿的嫩叶;巨大的微小的蕨类植物蓬松着身躯,慵懒地氤氲出淡淡的雾气;阳光透过密林投射进来,雀子们发出了婉转的鸣啼。光柱中雾气缓缓升腾,丝丝缕缕汇集在山腰、峡谷,云海涌动,高低错落的群山就多了几分仙气。
山的那边依旧是山,层峦叠嶂,不知边际。山风一点一点吹散了雾气,那些镶嵌在碧绿山体上的褐色土地就露了出来,上面也许长着耐寒的茅草和蕨叶,茅草如长剑,蕨叶如盾牌,山风是战鼓,它们相互碰撞,发出金属质地的沙沙沙;也许在去年秋冬交替之时,人们就将这些肆意生长的杂草烧成一片黑灰,此时,新蕨肥硕的芽刚刚拱破泥土,举着小小的拳头挥向天际;也许覆盖着黑灰的土地已经翻开,松软地摊在太阳底下,等待着颗粒饱满的种子。烧荒是为了提高肥力便于耕种,耕种是为了弥补青黄不接之时粮仓的亏空。在春天点下的苦荞种子会在八九月份收获,与水稻一起成为主食,将一年到头周而复始的生活衔接成一个整体。
苦荞地一片连着一片,顺着山势蔓延到森林的边缘,描画出了狭长、流畅的林际线,在那些富于变化的线条附近,仿佛为了过渡茂密森林与光裸土地间的突兀,生长着巨大的杜鹃树,它们枝干粗壮,虬结弯曲向上伸展出万千枝条,如勇猛的巨人,守卫着大地。
当布谷鸟开始交替鸣啼,时间的琴键轻轻弹出一个新的节奏,一朵酝酿了整个冬天的花慢慢绽放了,人类是无法看见花开的瞬间的,目睹的或许有山风、春天的雀子、树端爬行的昆虫、寻找花源的蜜蜂。它舒展着身子,奋力展开攒成一团的花瓣,许多个小喇叭渐次打开,羞怯而娇嫩,明艳又炽烈,明净如洗的天幕下,绿叶上燃起了火焰,仿佛一曲集结号在山间吹响,不过数天工夫,杜鹃花家族便呈燎原之势蔓延开来,这时,山下的村庄里人们举目远眺,轻而易举就能看见那漫山绽放的杜鹃,如火如荼,如霞缭绕,如一片绿色的海洋上骤然燃起一片花火。乡亲们明白,春播的季节已然来临。
当人们在太阳底下奋力点播荞种的时候,寥寥数个身影犹如大地上缓慢爬行的蚂蚁,又如屋檐下竭尽全力布网的蜘蛛,寂寥而渺小,坚韧又认真,他们一丝不苟,将一整年的希望一点一点播入土壤之中;花间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蜂群振动着水雾一样的翅膀,停在花冠上,摇摆着触须探入花吮吸花蜜,将花粉刷到腿上,进进出出、嘤嘤嗡嗡、成群结队、热闹非凡,它们深谙春天的秘密,将这些美丽的秘密从一朵花带到另外一朵,花朵答谢它们满口的甜蜜,满腿的花粉。泥土揣上种子,花朵也揣上了,阳光明媚,微风和暖,新的生命正在孕育。
杜鹃花落了,铺满了小径,如蜿蜒的花溪一点点向林间流去,流到种荞人的木屋附近,农忙的日子他们住在山里,当最后一粒荞种埋入土地,人们获得了喘息的时机,山坡上掰一把蕨菜芽,溪流边掐一把水香菜,山涧里割几簇刺椿头,在溪水里漂洗干净,汆水后凉拌或小炒,将春天吃进肚子里。孩子们也在吃着春天,他们摘下最后的杜鹃花,像蜜蜂一样吮吸花蜜,有人将花朵嚼碎了,微酸微涩的花汁将嘴巴染得一片紫红。
蜜蜂依旧忙忙碌碌,在雨季来临以前,刺锥栗、包头栗、野坝蒿、盐霜、三颗针……数不清的山花会次第开放,阳光透过树梢,细碎的光点洒在林间,在避风又温暖的房前屋后,种荞人为蜜蜂安下家,这些山中的精灵会循着温暖来到避风的港湾,安营扎寨、生儿育女,不久就会繁衍成一个巨大的家族。山中岁月孤寂,它们是极好的邻居,当人们静坐在蜂窝前,便可旁观另一个世界的大忙碌。
我和她曾经打破过这个小世界的大忙碌。那时,她矮我高,我瘦她胖,她脚大我脚小。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她后背挂着背篓,一耸一耸,里面放着苦荞面、米、油、盐,步履轻捷,轻松自若。我什么也没有拿,胸脯是呼哧呼哧拉响的大风箱,两条腿像灌了铅,负重前行,举步维艰。
我们在暮春时节爬上座座大山,穿过茅草丛生的荒地,那些荒地像没有剃干净胡楂的大汉,又硬又扎的草唰唰扫着裤管,又扫过脚面,在皮肤表面留下一道道白色的刮痕;我们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播种后的苦荞地,播种较早的黄土地上万千嫩绿的小苗拍着两个柔嫩的巴掌,一群山雀腾空而起,翅膀划破静谧的空气,发出尖锐的裂声。
我要停下来歇气,她不让,我不走,屁股落在地上变成了个不会动的石头。她指着天上的太阳,说不用过多久,它就落到西山了,那时,山里有熊,有豺,还有狼。我大惊,仿佛地上安了弹簧,迅速弹起,也不知从何处生出了一股力气,迅速追上。不知道爬过了几座山,蹚过了几条河,在到达木屋时,我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上,她冷笑,就这样还敢说要上山?我不服,狠狠白了她一眼。她傲娇地提了水桶向树林走去,树林是往下走的,走到了底便是深峡,那里水声跌宕,激流撞碎磐石的声响从峡谷里升腾上来。
我要死不活地四处搜寻干柴,折断了堆在火塘里,屋里很黑,从被烟熏得黢黑的挂箩里摸索到火柴,火柴头划过擦火皮便碎了,受潮了的它已不受控制。
太阳渐渐偏西,光线里无数金黄的点在跳跃,肚中的鸣叫一阵紧似一阵,我身体倦怠,喝了好多凉水,到后来竟然不觉得饿了。我用胳肢窝夹着火柴头和擦火皮,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个塑料袋套到头上,裸露的皮肤上裹着我的外衣。
我躲在黑暗里远远看着,她迅速地撬开了蜂桶盖。在蜂桶盖滚落的瞬间,群蜂炸裂,如箭般从蜂桶里飞射出来,她掉转身子,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木屋,我们一起关上门,蜂群的喧闹被关在了门外,几只蜜蜂跟着飞进了屋子,犹如无头的苍蝇乱窜,极不友好地围着我们飞来飞去,像是一种警告,又像是一种控诉。我们想起那个叫淳于棼的人,在槐树下睡觉,梦到他去了大槐安国,在那个国家中经历了很多事,睡醒后却发现大槐安国是槐树下的蚁穴。她刚刚掏的蜂巢莫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里也有君王臣民?有日升日落、周而复始、生老病死?现在,因为两个饥肠辘辘的女孩,这个王国遭遇了空前绝后的灾难。
等蜂群散了,她从蜂桶里割了两块蜜,又将盖子盖了回去,嘴里低声咒骂受潮的火柴,如果火燃起来,只要点上牛粪饼子,蜜蜂们就会昏昏欲睡,她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打开蜂桶盖。蜜还有温热的气息,从蜂巢上滴落下来,闪着金黄的光泽,舔一口,甜味在味蕾上狠狠砸了一榔头,又醇又厚,沁人心脾,却不能吃太多,吃多了就会蜜醉,那是一种类似酒醉的感觉,杜鹃花蜜还是酸涩的花粉,我们尝到的是去年冬天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蜜。都说山中百花蜜最为养人,却也不尽然,一种开在火把节前后的花所酿的蜜对人有极强的毒性,我们这里称中毒为“闹”,人们会说火把花蜜“闹”人;由玉米、水稻等粮食作物及山中刺锥栗、包头栗等花粉酿出的蜜,非但不甜,还有股浓郁的苦味,是入药上品,人们称其谷花蜜或苦蜜。
火柴被我的体温焐干了,住山人的木屋里腾起了火苗,火叶子从木柴里龇出,像是在笑,在黑暗逐渐降临的夜晚,它给予人温暖和安全。我们用滚水烫熟了荞面,捏成荞饼,烤熟了蘸着蜂蜜吃,我吃了整整一大块还意犹未尽。
夜里,铺天盖地的声响,有虫鸣,有蛙鸣,有鸟啼,有兽类的嘶吼,万千种,此起彼伏。那些蛙从山涧里一团一团的卵中孵化出来,此时,又在幽深的春山里凸着肚皮鼓着眼睛喷着白沫,一边发出砍柴一样的叨叨叨,一边产下新的卵;虫声清亮,如水流淌,是蝉是蟋蟀还是蝈蝈,数不清的声响道不清的来源,仿佛鸣到了世界的尽头;鸟啼声哀婉,如泣如诉,有猫头鹰的,也有张子方的,张子方是一种全身没毛的光骨碌鸟,躲在最深的大山里。
她说曾经有一头熊死在了这间木屋,那是一头来寻找食物的熊,它掰了许多玉米,在苦荞地上打滚嬉戏,又撕开了一只蜂桶抓蜜吃,最后打开了木屋,从挂在板壁上的包中掏出东西就嚼,它嚼的是猎弹,火药在它口中爆炸。夜总需要一些东西来衬托它的神秘与刺激,更何况在这样的大山之中,方圆数十里,只有两个女孩子。我们将门栓紧紧扣上,又多加了几根顶门棍。我疲惫又紧张,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她那里凑,身下的干草唰唰作响,两人背靠着背陷入睡眠之中,一夜乱梦纷纭,似睡非睡。
清晨,起雾了,白茫茫的一片,天光渐亮,只见那云脚低垂,斜斜地向上飘升,万千缕云雾连成浓重的大罩子,将山完全笼罩住了。我们行在荞地边缘,茅草蕨叶尖上挂着晶莹的露水,人一走过去就被打湿了裤子,眼前出现了巨大的墨色的影子,张牙舞爪,直冲天际,是那些杜鹃树,此时无数巨型影子立在大地上,渐远渐淡,直到完全变成一片苍茫的白色。我们疯魔般在坡上飞奔,仿佛只要跑得再快一些,就能一脚踏入云雾,飞升到另外一个世界之中。
突然,她收住了脚步,迅速转身,向我做出“嘘”的手势。眼前是一棵巨大的杜鹃树,粗壮的枝干斜倚着大地向上生长,千枝万叶间有云雾在顺着风向流淌,在那些枝叶的顶端,赫然停着一群有着雪白羽毛的长尾山鸡,它们悠闲自若地从这根树枝轻盈地飞跃到那根树枝,翅膀撑开,犹如雪白的羽扇,长长的尾巴将顺着风向流动的云雾搅动成一个个小小的旋涡,一束束天光从浓厚的云层里投射出来,天地间万物似镀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金光。我和她一动不动地呆立着,一种圣洁的,纯粹的情感充斥在胸膛,那种超然以我所能认知的一切的美将我彻底震慑,那时那刻,我平凡的生命似乎有了一丝不一样。
这幽深又空阔的春山,这树龄达到几百年的大树,据林业部门的考证,最为古老的杜鹃树已有八百多年,八百多年前,正是中国的宋朝时期,那时,数粒杜鹃的种子随风飘落到了山里的某个地方,扎根泥土,萌芽生长。山中岁月易过,世上繁华已千年,八百多年的花开花落在寂寞的春山里似也就是弹指之间。
很多年后,我读到一段资料,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位名叫乔治·福瑞斯特的英籍植物学家曾经由缅甸北部进入了我们家乡所属的这片林海,并在当中搜罗了大量的植物种子,我们眼见的许多植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漂洋过海,盛开在欧洲的花园之中。这位植物学家最为卓著的成绩是发现了这个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杜鹃树,便是那万千杜鹃中最为古老的一株,他将它做成的植物切片标本运回伦敦,至今依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里。
二十多年过去了,杂交水稻的普及彻底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大片大片的荞地荒芜了,被种上了经济林木,那些卫兵一样的杜鹃树彻底隐入了深林,在春日里将花朵隐秘地开在林间,我被童年的记忆驱使着去寻找那些古老的杜鹃树群落,却再难见当年的盛况,树林中古老的大树正在默默开花或者腐朽,当人们再站在村庄里举目远眺,在花开的时节,只能看见郁郁葱葱的春山,和葱绿色彩里几抹零星的红色。禁止烧荒被列入法律条款,种荞人的木屋糟朽了,坍塌了,曾经的两个少年已经成为中年人。
春山依旧苍翠如初,溪流潺潺,清澈冰凉,云雾依旧千姿百态地缭绕在群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