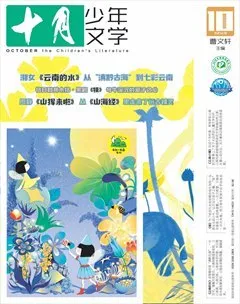水的生命,人与自然诗意的交响
8月的深圳雨水正旺,窗外电闪雷鸣,我一边阅读湘女的中篇散文《云南的水》,一边倾听我居住的楼后深圳河雨水暴涨哗啦啦的声响。有片刻,我陷入到湘女笔下云南丰沛的河流扑面而来的水雾之中,分不清是现实还是纸上的幻觉。我强烈感受到一个在云南大地行走的作家的生命体验。文学为生命代言,水的生命与作家的生命融为一体。如果没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不可能写出这样真切的生命体验的文学。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文学的时代背景,她将云南的水写得气势磅礴而又细腻生动,历史与人文交相辉映,自然生态与人类学知识嵌入式的写作方式,不断设置不同江河的知识点,故事性与历史性兼备,吸引读者层层深入,从中获得丰富的阅读体验。“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在《道德经》中将水彻底人性化了,湘女深谙水之道,她赋予水更多的社会属性与人文历史内涵。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湘女,擅长用儿童的视角进行人与自然的宏大叙事。舒缓的语调在奔涌的江河中,尽显野性的原始张力。她给江河人性化的处理,更加适合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小王子飞身扑去,只揪下金沙公主的一片裙角。他急得哇哇大哭,哭声变成了虎跳峡中的惊天巨浪。从此,12个雪国王子,站成了12座玉龙雪峰,每日翘首东望,眼巴巴盼着公主回来”。王子与公主的故事,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
湘女在自然文学中融入了鲜活的儿童文学表现手法,这样的描写随处可见,“哦,小溪长大啦,成了一条河。它急急忙忙向前涌去。左曲右弯,磕磕绊绊,像个不谙世事的野孩子,蛮撞,活泼”。字里行间充盈着欢乐的想象,活泼可爱的童话思维写活了山川大地,以及人与自然紧紧相依的命运。作家写云南的水,实际上写的是水与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是水与人的关系。
湘女如一位行吟诗人,以赤诚的爱拥抱江河湖水,诗化的语言,优美的意境,大胆的想象,大开大合的整体气象,一字一句读下来,就是一篇自由跳跃的长篇散文诗,读者可以在诗的意境里感受水的温情与水的文明。她在写水的同时,写出了江河的世界性、异域风情,以及少数民族生活等,读起来具有深邃的时间意识,云南水文明的脉络清晰可见。
《云南的水》是大自然、植物、动物的乐园,充满了自然界的风声、雨声与江河声,作家让孩子们听到了如此多密集的水声。孩子们在湘女制造的大自然的拟音中,可以享受到一个水、动物与植物的声音世界。静态的文字有了声响,甚至可以闻到江河水的味道,那是历史的味道,那是祖先对文明的呼唤。一篇《云南的水》,一篇地域水文明的全景式记录,满纸生香,满纸水的流淌。作品有突出的画面感与节奏感,她将一组组的电影镜头画面推向读者,像自然人文纪录片一样好看。通过形象化的描写,让事物具有了动感,简洁、准确的行文风格,仿如一种浮雕式的写作,细致入微,她在历史、自然与情感中自由穿行。
湘女调动了复杂多样的审美,顺着地理与时间的线索来写云南大地的水系,其间历史人物的出场,让水有了时间的纵深感,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体温与山河的壮丽。民间传说与神话写作,也是湘女的重要手段,《云南的水》里有祭龙求雨的民间文化,也有滇池与梁王山悲壮的历史传说。
“你看,一个湖泊从孕育到诞生,得经历多少动荡、挣扎和酝酿啊!”湘女感性的诗意下有着浓厚的思辨色彩。“滇池目睹了人类从原始状态到文明时代的成长岁月,也是云南古文化的发祥地。”她的诠释提升了作品的高度与深度,《云南的水》是她奉献给读者的一篇带有文学人类学意义的优秀作品。我尤为看重她田野调查式的写作,这种建立在大量田野调查基础上的写作,加强了作品的非虚构文学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