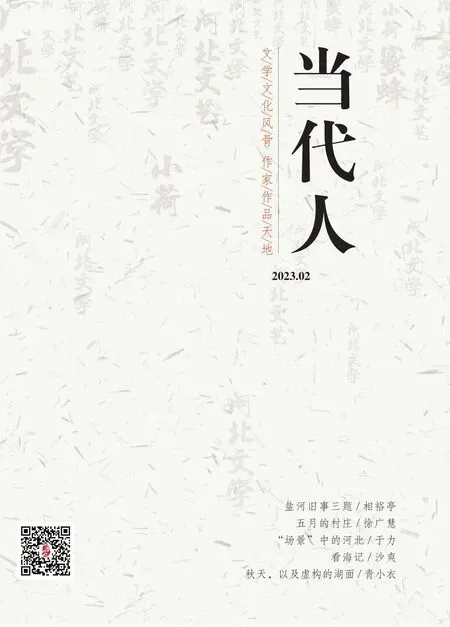鲁滨逊去向不明
◇曹应东
我后来自作主张地把那条狗叫着鲁滨逊。这是有原因的。读初中那几年,每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偷偷地读些闲书。那时,我正好读到《鲁滨逊漂流记》,竟然没心没肺地对流浪这件事情充满了无边的遐想,一听到父亲说起那条狗,就无端地联想起了在书里流浪的鲁滨逊,于是就把那条狗叫了鲁滨逊。父亲大字都不识几个,更不用说知道鲁滨逊是谁了,所以他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名字感到十分奇怪,他问我为什么让那条狗姓鲁呢?我知道,他心里肯定认为如果一条狗要是必须有姓的话,那也应该姓主人的姓才符合常理,姓一个和主人毫无关系的姓那算怎么回事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父亲解释,只有吱唔应付着。倘若解释得不当,就有可能让我不务正业偷着读闲书的事曝光。好在父亲问了几次见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也就不再问了。
鲁滨逊是在小年夜离家出走的。在父亲的叙述中,小年那天大雪纷飞,天地间一片洁白。我想象着鲁滨逊抖擞着那身黑色毛发在那个雪夜踏着瑞雪,迎着北风,长啸一声,飞也似的卷进雪夜里,与漫天飞雪融为一体,与山川草木融为一体,有着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和决绝,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悲凉。
花老板大约是在临近子夜时分到的。山里天黑得早人睡得也早,冬天昼短夜长就更要早些,雪夜就格外要早些。外面冰天雪地的,透骨生寒,屋内如果不生着炭火也是让人冻手冻脚的。花老板的车停下来时总是习惯性地按两声喇叭,尽管那尖锐的声音被纷纷扬扬的雪吸收了一部分,但在这山村寂静的夜里还是显得相当庞大。鲁滨逊在柴房里汪汪地叫了两声,也就不再叫了,它开口叫两声是在通知父亲有人来了,它住口不叫是因为它知道来的人是花老板。鲁滨逊是条聪明的狗。
在鲁滨逊看来,花老板是它十分欢迎的熟人。如果不是柴房的门被反扣着,毫无疑问它会从柴房里一跃而出,摇着尾巴冲到花老板的身边,热情地围着他转圈,讨好地嗅着他的裤脚。山里虽然穷,但野味多,无论城里千般好万般好,这一点无论如何也是比不上的。花老板也许是吃腻了城里的美味佳肴,对山里的野味情有独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打打牙祭。花老板吃剩下的那些骨头尽管并没有多少肉,但对鲁滨逊来说仍然是难得的盛宴。这让鲁滨逊产生了错觉,它一看到花老板,就仿佛看到那些香喷喷的肉骨头。就算是看在那些肉骨头的面子上,鲁滨逊也是没有理由不欢迎花老板的。鲁滨逊就是这样一条思想单纯的狗。
那时,山里的物质生活还十分匮乏,人们的心思都放在一日三餐如何填饱肚子上,以至于见面打招呼都在相互问,吃过饭了吗?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在具体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住在水边有鱼虾吃,住在山边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山里既有野果竹笋能果腹,更有山鸡野兔可尝鲜。那时也没有什么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保护法,只要你能在茫茫大山里弄到这些,那就是你的本事。
父亲能弄到野味,却并不是因为父亲有这样的本事。父亲甚至连猎枪也没有,更不用说什么枪法准不准了;也不是因为父亲会在山上装锁脚弓设置陷阱什么的,他甚至连野兽的脚印还没有完全区别得清楚。但父亲很幸运。你猜对了,父亲有一条会捕猎的狗。那是一只浑身上下毛发漆黑,唯有一双眼睛在闪闪发亮的狗。这条狗后来生下了鲁滨逊,她的毛色和眼睛鲁滨逊都不折不扣地继承了下来,可以说,鲁滨逊简直就是她的翻版。
其实,狗在山里是很常见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两只。山里偏僻,在树高草深处时有野兽出没,如果有一条狗看家护院心里就安定多了。可以想象,当一个山村狗叫的声音连绵成一片澎湃的声浪,在山谷间回荡起伏时,那效果绝对不亚于现在的报警装置被无意间触发。但天生就会捕猎的狗就很少见了。
父亲评价她说,那是一条很特别的狗。在初春一个微冷的早晨,那时奶奶中风偏瘫已经两年多了,爷爷的一只手也在山里伐木时被砸断近一年,才十五岁的父亲别无选择地担起了全家生活的担子。父亲打开门,发现门口蹲坐一只骨架刚刚长开的小黑狗,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的。那只黑狗看到父亲,就站起来朝着父亲不停地摇着尾巴,看上去很是乖巧聪明。父亲把一根吃剩下的红薯扔向那条黑狗,没想到那条黑狗动作出奇得敏捷,凌空一跃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准确地在半空中一口咬住那根红薯。那一刻,父亲在那条狗的眼睛深处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比如聪慧,比如勇敢,比如善解人意。那条黑狗就这样留了下来,和父亲、爷爷、奶奶三个人生活在一起。
三人一狗饱一餐饿一顿地过着日子,眼看着就到了冬天,日子就更加难挨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用一根红薯留下来的狗并不是条普通的狗。还是个早晨,父亲打开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雪,山风呼啸着掠过树林和旷野,身上寒意顿浓。这时,狗低沉的吠叫声在父亲的脚边响了起来。父亲低头,那条黑狗正叼着一只野兔眼神热切地望着他。
每次讲到这里,父亲总是这样深情地说,从那天起,家里总是能时不时地飘出肉的香味来,有了那些香味,冬天也就没有那么冰冷,那么让人绝望了。我听到香味两个字总是很困难地咽咽口水,然后再使劲地点点头。父亲在别的方面反应可能要迟钝些,但烹饪野味却是天赋异禀,自成一派,无论什么野味,只要到了他的手里都能化腐朽为神奇。
如果不是这样,花老板根本就不可能认识父亲的。花老板是城里的大老板,住的是楼房,坐的是轿车,而父亲只是一个山里的穷小子,住的山间茅屋,整日土里刨食,和花老板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八竿子也打不着。按理说,他们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是不可能有交集的。但那些从茅屋里飘出的奇特香味吸引了花老板。当时,轿车正从崎岖的山路上缓缓驶过,花老板耽于美食,素来嗅觉灵敏,一下子就捕捉到空气中有一种味道在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味蕾,这甚至比身边女人身上的味道更让他沉醉,他的心脏就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他猛地喊了一声,停车。车子还没有停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站在路边闭上眼睛,一句话都不说,整个人仿佛木雕泥塑一般。那一刻,他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只看见他的鼻孔一吸一呼,竟然有两行泪滴缓缓从脸颊上滑落……
花老板的车喇叭响第一声时,父亲就听到了。父亲平时睡眠很好,或许是因为年轻瞌睡大,或许是因为白天太累了,晚上只要他头一挨到枕头就能呼呼入睡,连雷都打不醒。但那个小年夜父亲却迟迟不能入睡,这并不是他有预感,早就知道花老板会在深夜造访,而是他的脑海里还在想着白天的事,想着那条被埋在屋后山坡上的黑狗。
中午时分,雪下得像蝴蝶在漫天飞舞时,鲁滨逊披着一身雪花冲进了屋里,猛地一抖,那片片雪花纷纷坠落,白狗终于现出了黑狗的原形。父亲正在诧异,鲁滨逊上前一口就咬住了他的裤脚,不由分说地往屋外拽,嘴里发出呜呜咽咽的叫声。
还真的是应了“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那句话。在山坡上,那条黑狗全身被厚厚的一层白雪覆盖着,仿佛睡着了一样沉静和安详。父亲和鲁滨逊一起把黑狗从雪堆里刨了出来,这时,父亲才看到黑狗的肚子被撕裂开了,黏黏糊糊的肠子拖在外面,从伤口处可以清晰地看到肚子里的内脏,可能是气温太低了,也可能是血流干了,如此巨大的创口竟然没有出现想象中血淋淋的场面,连那些凝固的血也是惨白惨白的。鲁滨逊愤怒地朝着山顶方向连声狂吠,那吠声里充满了悲恸。父亲明白它们大约是在山顶上遇到可怕的猛兽了,黑狗虽然拼死搏斗,但终究力量过于悬殊,敌不过对手的利爪,腹部受到了致命一击。即便是受了这么重的伤,它还是护着鲁滨逊逃到这里才倒了下来。
说来也怪,那时山上野兽远比现在要多,猛兽也多。有一次,村里有个打猎的在山里打猎,等到半夜,看到一只孤狼出现在视野里,正要扣动扳机来个对眼穿,剥下狼皮卖个好价钱。这时,就听到那只狼仰头望月一声长嘶,声音激越,山谷回应,经久不息。他心里一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就停下扣扳机的手。片刻后,一群狼陆陆续续地在他前面不远处经过,竟有二十六只之多。竟然是狼群。
父亲脑海里正想着到底是狼还是老虎或者其他什么猛兽伤的那条黑狗,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了车喇叭的响声,接着又听到了鲁滨逊的吠叫。爷爷在里屋问父亲,娃,听这动静是有人来了吧?奶奶也醒了,用带着浓重睡意的声音问道,这么大的雪,会有谁来呢?父亲答道,是花老板来了。
父亲手脚很麻利。很快,堂屋里的煤油灯已经点亮了,木炭也在火钵里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花老板他们往这边走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拉开半扇门站在门口迎接了,就像城里大酒店的门童一样脸上堆满了笑容。风裹着雪花从父亲的身边往屋里涌,煤油灯不停地扑闪着,忽明忽暗的,父亲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但脸上笑容却更加灿烂了。花老板他们越走越近了。爷爷又在里屋问道,娃,是花老板吗?父亲回答说,是呢,大啊,天太冷了,你就不用起来了。里屋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穿衣服声音,爷爷又在说,娃,这几年要不是有花老板仗义出手帮衬着,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残的残病的病,哪里有饭吃?更不用说看病了。我总不能倚老卖老吧,怎么着也得起来和花老板打个招呼。
爷爷和花老板打过招呼后就回到了里屋。堂屋里只留下了父亲和花老板一行人。一个是花老板,另一个是肤色白晰浑身散发着香气的女人,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胖得眼睛眯成两道缝的司机了,父亲当然都认识,因为每次来都是这三个人。他们每次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父亲给他们做野味。这样的雪夜,花老板他们顶着风冒着雪,不顾危险开着车子穿过冰封的山路来到这里,显然是心血来潮来大快朵颐的。
父亲笑着对花老板说,花老板,你们先坐会儿烤下火喝点儿茶,我一会儿就好。说着对灶屋里指了指,那意思是说自己不能陪他们要去灶屋里忙了。
花老板明显是喝了不少酒,虽然算不上酩酊大醉,但少说也有六七分醉意了。他朝父亲招了招手,示意父亲到他身边去。父亲走了过去。花老板的身材比一般人高大不少,即便是坐着他略一抬手也能轻而易举地拍到父亲的肩头。他拍了拍父亲的肩头,带着几分醉意说道,今天得换个口味。说着,眼神有些迷离地看了看依偎在自己身边的女人,阿离,是吧?那个叫阿离的女人听到花老板问自己,身子就愈发软了起来,恨不能就此化在花老板的身上,声音也是软软的,像是也要化了一般。父亲的脸腾就红了,低下头不去看眼前这旖旎的风光。
那天夜里,父亲花的时间要比平时多出一倍还不止,其中有一大半时间是顶风冒雪去屋外忙活去了,只有一小半时间在灶屋里操刀弄勺,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但好饭不怕晚,等满屋飘荡着一股奇香时,没有人认为等这么长的时间是不值得的,是啊,东西还未上桌,单那顺风飘来的香气就能让人如此身心愉悦,此等美味当真是可遇而不可求。那个胖子和阿离翕动鼻孔一脸的陶醉,已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了;还是花老板见多识广,他吸了吸鼻子,咽下一口浓浓的唾液,用叹息一般的语调轻轻地吟道:人间美味三千种,狗肉能称第一香。微火慢煨醯酱厚,霜刀细切玉脂长。未和樊哙筛开酒,已见济颠翻入墙。方外神仙皆好此,问君何事不来尝?
香气丝丝缕缕地飘到屋外,连那么猛烈的北风也吹不散。鲁滨逊一定也嗅到了,不由得兴奋起来,直着身子用爪子不停地抓挠着柴屋的门,还不时地发出低低的叫声。灶屋离柴屋近,父亲听得很清楚,但他一直装着没有听见,任凭鲁滨逊在柴屋里怎么折腾就是不去放它出来。
桌上的炭火炉子摆上了,一大盆肉端了上来。那盆肉便煨在那炭火炉子上。炉子里的木炭烧得红通通的,散发着炙人的热浪,那盆肉的汤汁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按照花老板的说法,品尝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闻其香,闻香时当闭眼,闭眼人的嗅觉就会格外灵敏,这时,你就可以嗅出无穷无尽的花香果香或者蜜香;第二步,观其色,观色时宜注目,注目人的视觉就会完全打开,这时就可以看到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或者苍茫的群山;第三步,品其味,品味时须凝神,凝神人的味觉才会空前活跃,这时,你就可以尝遍人世间极致的酸甜苦辣和生命里最巅峰的喜怒哀乐。在那个寒冷的雪花纷飞的冬夜,父亲亲手烹制的这盆肉无疑完全符合花老板的美味标准。他们是不是按照这三个步骤品尝的,父亲不得而知,他只知道那盆肉刚一端上桌,三只手六根筷子就迫不及待地伸了出来。一时间,堂屋里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吮吸声、咀嚼声和感叹声。
父亲每次说到这里,都要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父亲说,如果自己那时不进里屋去,可能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但这只是假设而已。就在那个关口,父亲离开了堂屋。等他再返回堂屋时,一眼就看到了鲁滨逊,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
后来才知道,父亲刚走进里屋,鲁滨逊在柴屋又叫又挠的,闹的动静更大了,即便是在堂屋里也听得清清楚楚。这显然是大煞风景。花老板皱了皱眉头,让胖司机把鲁滨逊放了进来。如果父亲在场,无论如何也是要阻止鲁滨逊进来的,但偏偏那会儿父亲不在场。鲁滨逊怎么会把时机选择得那么准?这很让人费解。
鲁滨逊围着花老板他们三个人打着转,尾巴摇得像风车,眼睛里闪着光,看得出它很高兴。它甚至有几次整个身体都立了起来,抬起前肢将爪子搭在花老板身上,用头拱着他。相信花老板也一定懂得鲁滨逊的意思,他抬手拂去了鲁滨逊的爪子,哈哈一笑,很大方地夹起一块肉朝着空中一扔。鲁滨逊欢快地叫了一声,凌空一跃,在半空中稳稳地接到了那块肉。这个动作如此眼熟,父亲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早晨,想起了蹲在他脚边那条脏兮兮的小黑狗,那条狗就是以这样的动作接到了他扔过去的那根红薯的。
倘若花老板能注意到进到屋里的狗比平时少了一条,倘若花老板能因此而进一步联想起桌上的那盆肉,他应该不会不假思索地把那块肉扔给鲁滨逊吧。我曾经这样问过父亲,但父亲却是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他承认自己没有机会就这件事问花老板,因为从那以后花老板就在他的生活里消失了,就像从来都没有这个人一样,就像过去的一切只是一场梦而已。
鲁滨逊张开嘴接到那块肉,稳稳地落在地上。按照花老板的想法,鲁滨逊会满怀感激之情地一口吞下这块肉的。那是一块如此之好的肉,它有着细腻的纹理、紧实的肌肉和劲道的口感,鲁滨逊能吃到这样的肉那是它的福气。出乎意料的是,鲁滨逊在吞咽和呕吐之间迅速做出了选择,嘴从闭合状态猛地张开,那块肉扑通一声就掉了下来。与此同时,鲁滨逊的眼神也不停地变化着。一条狗的眼神在一瞬间那般变幻多端,听起来实在叫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其实,父亲一看到花老板向鲁滨逊扔去了一块肉,就预感到要坏事。他冲过去一把拉开门,想在鲁滨逊狂性发作之前把它赶出去,但已经来不及了。鲁滨逊从温顺到发狂的时间太快了,快到让人来不及做出反应。说时迟,那时快,鲁滨逊张开巨口,獠牙尽露,利爪突起,像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向花老板射去。那一刻,鲁滨逊的嘴里发出凄厉的啸声,那就是利箭离开弓弦时的声音。
父亲后来回忆说,他拉开门后,拥挤在门外的风雪汹涌着灌进了屋内,煤油灯刹时就暗了下来,似乎有那么一瞬间,屋内是一片黑暗。在那看似无穷无尽其实只是短短一瞬的黑暗里,一声惨叫响了起来,那是父亲的惨叫。在千钧一发之际,父亲凭着本能伸手拦住了冲向花老板的鲁滨逊,鲁滨逊那蕴含着仇恨的利齿落在父亲的手臂上,在那么快的速度下,它只有遵循着惯性一口狠狠地咬下去。等煤油灯再亮起时,父亲看到花老板正双手抱着头缩成一团,阿离则和那个胖司机紧紧地抱在一起,俩人瑟瑟如筛糠。父亲在看他们时,他们也正好偷眼去看鲁滨逊,却正好一眼看到拦在他们中间的父亲。鲜血正从父亲的手臂上瀑布一般倾落下来,滴在地面上发出叭嗒叭嗒的响声。
鲁滨逊这时想必已经对整个世界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它只是瞪着它那双无辜的眼睛,眼睛里的泪水如同决堤的江水一样泛滥着。它木偶一样一动不动,只是那么傻傻愣愣地看着,仿佛是在看着父亲,又像是在看着花老板他们。慌乱中,那盆肉不知道被谁打翻了,肉块和汤汁泼洒得满桌都是,几点细碎的炭火滋滋地在汤汁里冒着青烟。在父亲一遍又一遍的回忆中,我也似乎读懂了鲁滨逊的内心,眼前的世界它真的是无法理解呀。是啊,作为一条狗,它确实无法理解。
门里的灯光忽明忽暗,门外的风雪如此猛烈。父亲最先从惊惶失措中醒悟过来,他调整了一下自己脸上痛苦的表情,轻手轻脚地向鲁滨逊走近了几步。他慢慢地向鲁滨逊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想去抚摸鲁滨逊的头,告诉它自己并没有恶意,从而尝试着让它重新回到柴屋,至于后面的事,就交给时间吧,相信时间一定会抚平鲁滨逊心里的创伤。父亲每走近一步,鲁滨逊都警惕地向后倒退一步,等它的后腿碰到门槛时,它就不再倒退了,而是突然悲愤地厉叫一声,扭过头疯狂地冲向屋外,冲进漫天风雪里,片刻就不见了踪影……
父亲再也没有看到过鲁滨逊。如果不是父亲手臂上的那道伤痕至今犹在,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鲁滨逊这条狗,就更不用说那条眼睛闪闪发亮的黑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