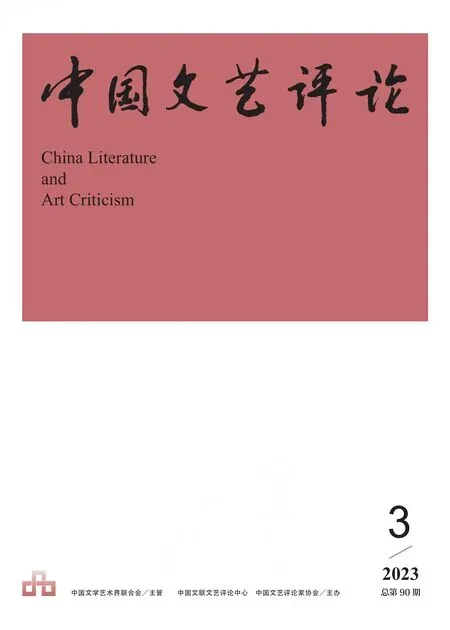他与笑声同在
——访粤语相声表演艺术家黄俊英
■ 采访人:罗丽
黄俊英简介:原名黄建培,1936年生,祖籍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粤语相声表演艺术家。作为粤语相声的开创者,他将北方曲艺形式带入岭南地区,是相声方言化的拓荒者之一,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广东最受欢迎笑星,是南粤家喻户晓的“羊城笑星”“相声大师”“开心果”。1983年,他成立了全国首个相声艺术研究学术社团“广州市相声艺术学会”,通过比赛活动挖掘相声艺术人才和曲艺原创作品,将粤语相声表演艺术形式发扬光大。2007年当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五十家”,2022年荣获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
“唔识黄俊英,你好打极都有限啦。”意即如此名人黄俊英,听者也不曾耳闻的话,便是孤陋寡闻了。对于两广地区的观众而言,黄俊英、杨达等作为粤语相声小品的代表人物,是陪伴大家走过风雨人生必不可少的良朋好友。
我向黄俊英先生发出访谈邀约,他便爽快应承。2022年的羊城盛夏,烈日蝉鸣,在树荫下等待的我们,被驾驶多功能车潇洒而来的黄先生“帅”到了——86岁的他如此矫健灵活,倒车入库一气呵成。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人认出他来,黄先生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亲民随和之中带有自然天成的名家风范。
个子不高,但神情活泼,精干身材里有非凡的大能量,这是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黄俊英,此刻和我们眼前充满活力的不老形象,渐渐重合起来了。从艺七十载,他为观众带来的笑声,并非单纯的“笑料”“包袱”,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人生豁达与浑厚天真。
一、错入戏行,歪打正着
罗丽(以下简称“罗”):黄先生,我们都是听着您和杨达先生的粤语相声长大的。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有您们的地方就有笑声。尤其您在粤语相声作品中塑造的“369”“生神仙”等角色,更是深入人心。往往您一出场,台下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您拥有这么高的语言天赋,是不是有家传呢?请谈谈您是怎样走上文艺道路的?
黄俊英(以下简称“黄”):我确实没有家传,父母并非是从事文艺工作的,父亲做点小生意,帮亲戚的药铺置办药材。我1936年在广州出生。1938年广州沦陷,我们全家迁回广东罗定老家。几年后,我又跟着父母去阳江读小学。不过,我确实自小就展示出语言天赋。我记得到阳江的第三天,就已经能用阳江话和人聊天,很多当地人甚至以为我本来就是阳江人。在阳江读小学期间,我连续五年获得全县演讲比赛第一名。第一次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我才六岁,刚读一年级,连稿也不会看。父亲当时就找朋友写好稿子念给我听,我跟着念了十来遍就记下来了。可以说,能走上艺术道路,记性好、模仿能力强确实帮到我不少。
战争结束,小学毕业的我便和家人一起回到广州。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我经常跟着父母去戏院,渐渐就喜欢上了粤剧。每次看完戏回家,我都很兴奋,甚至跑到床上,拿一条毛巾扎在头上学戏台上的演员做身段。我很快就学会了不少粤剧的唱段,那时候尤其喜欢粤剧大老倌何非凡的戏,比如《红花开遍凯旋门》《情僧偷到潇湘馆》《风雪访情僧》等的主题曲我都会唱。
当年,我也追星。回忆起来,真的和今天的年轻人没什么差别。15岁那年,我曾经一个人独自去香港看马师曾、红线女的演出。那时候,去香港不用证件。我自己搭船到香港,在九龙的酒店入住,然后去普庆戏院买票。看完戏,散了场,我还在戏院门口等红线女出来。
罗:从看戏变成立志学戏,您能拜粤剧大老倌罗品超为师,有什么因缘际会?
黄:当时,我家住在广州西关华林寺一带,那里恰好是粤剧大老倌们聚居之地。我幼年挨饿受苦,深感家贫之困,因此当时小小年纪就特别羡慕那些大老倌们收入高、不为一日三餐发愁,加上本身喜欢看粤剧,就产生了学戏的念头。1951年,我跟随男花旦侬艳香(原名邝惠农)学戏,从基本功练起,每天练声、走圆台、学排场。三个月之后,我就被招到长江粤剧团“做手下”(跑龙套)。谁知才做了一个月,剧团就因效益不好而散了。
正当我为前途踌躇之时,我家有位熟悉的街坊,是名热心的粤剧老艺人,他帮我打听到罗品超先生住在多宝路,便带我去拜访,以谋出路。他是个爽快的人,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情景。当时,他正在家里吃饭,就在饭桌边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对答如流,还现场唱了几句粤剧。他见我真心喜欢粤剧,就直接爽快地让我在五月珠江粤剧团开班的时候,开始跟着他一起学戏。就这样,我成了罗品超先生的徒弟,跟着他进入了有一百六十多人的珠江粤剧团,边学边演。
那时候,剧团的演出是由演出公司来排期的,一般七天为一个台期,演完就拆台、拉箱到另一个戏院演出,演出第一天因为要装台没有日场戏,也不用练功。此外,每天24小时,我除睡觉之外,其余时间都在练功和演出,不敢松懈,怕又断送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图1 黄俊英(左)与师父罗品超
在戏班当学徒很辛苦,我早上5点钟起床练声,吃完早餐开始练基本功,俯卧撑、虎尾、压腿、拗腰、圆台,还有大翻、小翻、级翻、屎瓯、车轮、半边月、撞脚等各种筋斗,一刻都不停。到11点多吃饭时,我的毛巾已经可以拧出水来了。当时体能消耗大,我中午能吃六大碗米饭,午饭后不久,就开始了下午的日场戏。我一般是“做手下”,常言道是“出就出先,死就死先,企就企两边”。日场戏散场之后,吃完晚饭没一会儿,又要开始演夜场戏了,我依旧是“做手下”。没有戏的时候,我就在侧幕看大老倌们演戏,直到整套戏都能背下来。
我知道自己先天在外型上并无任何优越之处,个子小,长得又不帅,因此加倍努力,多学几门技术傍身。除了练功、演出之外,我在午晚饭后的闲余,都会跟“棚面师傅”(音乐师傅)学打锣镲和拉胡琴。一般来说,演出正式开场前半小时,都会由锣鼓下手打“沙的”和大锣,叫“发报鼓”,既是催促观众入场,也是提醒演员化妆。当时,我学完“发报鼓”就继续学打“三五七”(锣鼓点),慢慢就掌握了粤剧音乐的掌板和锣鼓。遇上音乐师傅有时“偷鸡”(偷懒),就让我上去打两场。我还自己学拉胡琴,一有空就跑到棚面拉琴,为戏班里面的“梅香”(女配角)伴奏。这样,我自己可以练乐器,花旦演员又能有音乐伴着练曲,两全其美。
我知道只有学到手的本事才是自己的,有了本事,就有了安身立命之本。当时,珠江粤剧团台期很密,大老倌的收入很高,但我作为手下,每天的戏金只有五角钱,晚上都不敢吃宵夜,经常散了场、冲个凉就去睡觉。我通常要留着钱第二天早上吃早餐,这样才有力气练功。每次看着师父演出结束后收到的一大沓钱,我都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到像师父那样。生存的窘迫感和对成功的期望,有时候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动力。有了奋斗的目标,生活就有奔头,练功自然也不觉得苦了。
二、天降大任,钟情相声
罗:粤语俗语——周身刀,指的是满身本事的人。看来当时年纪轻轻的您,已经是如此了。那您又是因何机缘转行曲艺的呢?
黄:话说回来,我能进入曲艺界是天意。我所在的珠江粤剧团属于民营公助性质的剧团,1956年转为地方国营,1958年与广州粤剧工作团合并为广州粤剧团。两团合并之后,由于人员精简,以我自身的条件,虽然有师父关照着,也难免面临下岗的问题。当时,广东的新会县开展“大跃进”活动,广州所有的文艺团体都要“唱新会”“颂新会”“演新会”,以作宣传。其中,新会的大泽公社在搞“车子化”,要“消灭扁担”。为此,广东民间乐团的黄锦培就写了一首小演唱《万车游行》,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演唱人选。
时任的广州文化局局长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珠江粤剧团有个年轻人叫黄俊英,为人机灵鬼马,什么行当都曾涉猎。为此,他力主把我调到广东民间乐团,让我来唱《万车游行》。当时,我正为面临下岗而彷徨,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来到广东民间乐团,接下了这首《万车游行》。我穿起唐装、脖子上挂条毛巾就开演,一路演一路唱:“万车游行真出奇,气势如虹壮大无比……”还别说,像模像样,节目很受欢迎。这多亏我在珠江剧团学徒时什么行当都学,虽形象不佳,但能唱能演,还会打锣镲、演奏乐器,可谓是“万金油”。曲艺恰好需要“多面手”,因此,给了我施展拳脚的机会。演唱《万车游行》之后,我就留在了广东民间乐团,和杨达、崔凌霄、邓凤玲、刘婉芳等一起四处演出。我们是以唱民歌和小演唱为主,每到新的地方演出,都会学习当地的曲艺作品。到四川,就学四川清音,到河南,就学河南梆子,既学到新的表演形式,丰富了广东曲艺,又能很快拉近与当地群众的距离。
罗:听说1958年您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当时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下观看,也就是在那时,您接触到北方的相声艺术。回广州后不久,您就和杨达等人一起创立了粤语相声。可以跟我们说说当时的情形吗?
黄:1958年,我参加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在长安戏院表演了《万车游行》,节目很受欢迎。周总理看完演出接见我们的时候,还认得我是表演《万车游行》的演员,当时真的让我又兴奋又鼓舞。汇演结束后,原文化部为扩大影响就从参加汇演的节目中挑选了一批优秀节目,成立了两个演出团,一个北上,一个南下,《万车游行》被选为南下演出团的节目。但我要到南宁参加广东民间乐团的演出,因此巡回演出一度由别人来接替我演唱《万车游行》。后恰逢金门炮战,原文化部便通知把巡回演出团改为“全国各界赴福建前线慰问团第五分团”,我应召加入前线慰问团,继续出演《万车游行》。
我很庆幸自己参加了这个慰问团,有了可以“偷师”学习的机会。团中汇集了来自各个省市的曲艺名家:上海的苏州评弹名家蒋月泉、朱慧珍,山东快书艺术家高元钧,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天津时调艺术家王毓宝,辽宁代表团相声演员小立本的节目是《社会主义好》,黑龙江代表团相声演员于世德、李维信合作表演《天上与人间》,还有单弦演员阚泽良,评书演员袁阔成,等等。我在团里是最年轻的,才二十来岁,和这些艺术家一起生活了一个多月,我学了很多东西。实际上,我在北京参加汇演时便接触了相声艺术,又在慰问演出的过程中和一些相声演员深入交流,慢慢了解到相声作为语言艺术的魅力,逐渐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

图2 黄俊英(右)与他的艺术搭档、妻子崔凌霄
到福建前线演出时,我们要深入战壕为战士表演。当时相声节目很受欢迎,团领导就动员各个代表团,问谁还能再出一个相声节目。我和黄锦培大胆地表示我们可以试试,就现学了一段北方的返场相声。这个返场相声很短,也很简单,我们很快就学下来了。第一次演相声时,我用的是普通话,五分钟的“返场小段”,后起名为《文化水平》。里面运用了“形象包袱”的手段,虽然很浅,但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相继在前线为五六个炮兵团演出,让我过了一把“笑星”瘾。巡演结束回到广州后,我便下决心,要继续做相声,而且要做粤语相声。

图3 黄俊英(右)和杨达演绎《一定要你笑》(摄影:楚戈)
罗:这应该是您“一生痴爱是相声”的开端了,原来您第一次讲相声是和黄锦培先生拍档的,那您后来是怎样开始和杨达先生成为搭档的呢?
黄:实际上,粤语相声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普通话的推广,电台广播的相声段子和省外曲艺团体来穗演出的相声节目开始为广州观众所了解,在广州本地的文娱晚会中还偶有业余演员的相声节目。1953年,为配合当时农村的“三包政策”,广州说书学会艺人陈标、王盖华在广东电台对农村广播的节目中演播粤语相声《实行三包》。此外,著名说书艺人侯佩玉、胡千里等也曾在电台演播过十多段粤语相声。从1954年开始,广东话剧团演员张悦楷和林兆明、吴克和蔡传兴这两对“最佳拍档”便大力推广和普及粤语相声。
最初一段时间,尽管已经有吕锦兰、关心民、区少佳、张悦楷、林兆明等前辈跨界参与相声演出,但广东还并没有专业的粤语相声演员。后来,我和杨达搭档的粤语相声组合异军突起,被观众称为“梦幻组合”。从那时起,粤语相声才成为一个有专业演员的独立曲艺品种。
我和杨达相识已久,舞台上下都比较默契,彼此对于相声的想法总是一拍即合。加上广东民间乐团除了我和杨达以外再无男演员,所以我们顺理成章地成为搭档。后来,随着相声发展,我们开始深受观众欢迎,越来越多的演员参与进来,包括崔凌霄、关楚梅等女演员也开始做相声。实际上,我先后和不同的演员搭档说过相声,但最合拍的还是杨达。
罗:您觉得为什么您和杨达先生能够成为“最佳拍档”“梦幻组合”?
黄:我和杨达很有默契,同时又各有所长,是大家公认的“最佳拍档”。杨达说相声有个优点,就是节奏把握得很好。音乐有节拍,相声虽是语言艺术,但也讲求节拍,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该停就停,该赶就赶。该快的地方你讲慢了,就没有包袱了,观众就不会笑;该慢的地方你讲快了,一样是没有包袱,观众同样不会笑。杨达的节奏就掌握得非常好,跟他说相声是很舒服的。比如《文化水平》这个节目,好像只是两个演员在讲述一些文字,但杨达可以让你知道,什么时候适合开口说,什么时候暂时不能开口讲。《接电话》这个相声我也和很多人都搭档过,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及得上杨达,特别是在节奏上。这也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我和杨达,一高一矮,亦庄亦谐,声线十分和谐,又有丰富的舞台经验,说、学、逗、唱皆能,“捧”“逗”兼佳,能编能演。在粤语相声《歌迷与迷歌》中,我加入了粤剧、粤曲、粤语流行曲,甚至包含了当时流行的粤语广告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就曾多次对别人说:“来到广东,我们说不过他们。”
罗:您还记得粤语相声首次向广东观众亮相的场景吗?当时观众的反馈如何?您觉得为什么观众能接受您的粤语相声?
黄:粤语相声的首次亮相,是我和杨达合作的节目《文化水平》。当时观众看得开心、反应热烈,大呼原来相声这么好玩!那时候广东还未出现相声,如果第一次就说教,观众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我们选择了比较浅显的作品来引导观众入门。
说相声,首先要有语言上的优势。我自小就对各种不同口音的粤语方言感兴趣,也可以说是颇有语言天赋的,顺德话、台山话,包括下四府的吴川话等,我都能说,而且说得像模像样。每次我说顺德话,都能让顺德人以为我是老乡。见到广东四邑人,我就用台山话、开平话跟他们对话,他们也都以为我真的是“台山仔”。甚至到粤西廉州、遂溪等地方,我的口音也能以假乱真,让他们都把我当老乡。
我会很多方言,但在作品中,我并不是什么地方的口音都用,我只会加入观众能听懂的。粤语相声主要面向整个粤方言区的观众,所以我说相声时经常会加入广东四邑(台山、开平)话、南(南海)番(番禺)顺(顺德)话、吴川话等各地口音。在作品中,如果加入的各地口音观众听得懂,便会有即时的剧场效果,观众会倍感亲切,演出效果就会很好。相反,如果我讲客家话(客家方言)或潮州话(闽方言),属于粤方言以外的,观众就听不懂。反过来,如果去到粤北客家地区或粤东潮汕地区,他们听不懂粤方言,对粤语相声里面的包袱肯定不会有反应。所以说,有些地方我们相声团是不敢去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我们的相声节目在题材和内容表达上接地气。《广州话趣》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使用了很多观众都很熟悉的粤语。《借电话》说的也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在《一对一》中,我把跟“一”字有关的成语全部串起来,一团和气、一帆风顺、一掷千金、一落千丈、一泻千里……用的都是观众常用的成语,又把市井生活融入其中,所以大家会觉得很亲切,笑声不断。
再一个,我的相声无论是表演、内容题材,还是语言,都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不与时俱进就会落后于社会,就没有生命力。
三、由学而创,名声鹊起
罗:粤语相声的创编,是否经历了“移植—改编—创作”的过程?期间又经历了哪些困难?

图4 黄俊英正在创作相声节目
黄:最开始,我们粤语相声并没有能力原创作品,大多都是移植、改编北方的相声作品。其实,改编是二次创作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在改编中,我们不仅替换上地道的粤语方言表达,还加入了很多有广东地方特点的风土人情。这样一来,哪怕相声的“包袱”浅白,也能让每位观众都笑声不断,我们也过了一把“笑星”瘾。通过改编尝到甜头后,我们便开始潜心探索创作符合广东人口味的粤语方言相声作品。广州话歇后语、俚语都很丰富、很有特色,用粤语方言来“抖包袱”,融入市井生活,大家会觉得很亲切。为了构思,我经常茶饭不思,在被窝里辗转反侧,灵光乍现,便立马掀开被子,开灯记录下来。
20世纪60年代,我和林运洪、杨达一起,以泮溪酒家的点心师傅罗坤为原型,创作了第一个原创粤语相声《老张师傅》,受到观众欢迎。关楚梅原是唱谐趣粤曲的,后来也开始说相声,并从事相声创作。后来,她的儿子关俭良也创作了一些相声作品。
罗:您觉得粤语相声与普通话相声在语言、题材、表演技巧方面,有哪些相同的地方,又有哪些区别呢?
黄:北方相声是我们粤语相声的老师,从历史发展来说存在很大的时间差距。然而,两者在表演技巧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说学逗唱”“三翻四抖”,有很多不同的“包袱”。只是北方相声是用普通话来讲,而粤语相声是用粤语来讲。在内容和题材上,北方相声和粤语相声各取所需,但肯定都要结合各自的语言特色,以及当地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早期粤语相声还没有原创能力,多数是移植、改编北方相声将其本土化,后来我们开始创作,就更多地开始运用广东本地的题材,比如《省港澳大比拼》《广州话趣》等。
作品要源于生活,反映百姓心声,才最能打动人。我们对北方相声本子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普通话和广州方言的音调、发音等都不一样,要进行语言和词汇上的必要修改,才能用粤语演出。我们还根据广东地方特色和生活实际,创作出一大批符合粤语方言观众需求的相声作品,例如《大不相同》《虾仔入城》《学戏》《生死恋》《打破常规》《广州话趣》《食烟歌》《歌迷与迷歌》《快三、慢四、的士高》等。
至于两者的不同,主要是在演员角色的设定上。北方相声是分“捧哏”和“逗哏”的,两人分工明确。而粤语相声则没有规定哪个“捧”、哪个“逗”。我和杨达一起说相声,有时候我捧他逗,有时候他捧我逗,按节目需要而定。到了我们开始原创粤语相声的阶段,大多作品都是争辩型,使得表演双方都有台词、有戏,而不是北方相声“一头沉”的类型。
罗:1983年,您和杨达、林运洪,以及您的夫人崔凌霄牵头成立广州相声艺术团,您任团长,之后相声艺术团独立演出。可以谈谈这个艺术团成立的始末吗?从您开始创作粤语相声到正式成立广州相声艺术团,历经二十多年,这期间粤语相声的发展以及演出情况是怎样的呢?
黄:广州相声艺术团是1983年5月成立的,除了牵头的我、杨达、林运洪、崔凌霄,还有业余相声演员何宝文、邹智雄、郭逢凯等也加入其中。他们本来都是广州荔湾区的小学教师,“文革”期间曾在文艺宣传队讲粤语相声。我们相声艺术团成立之后,他们就放弃了“铁饭碗”,加入了我们。稍后,我的徒弟李艳玲、陈坚雄等也先后加入。我们人员不多,虽然大家经常要包揽台前幕后的一切大小杂事,但是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竟然成为当时票房收入颇高的演出团体。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广州相声艺术团的节目频频在广东本地的电视台和电台中播出,成为各类晚会的压轴作品。相声团的足迹遍及省内外五十多个市县的大小城镇,演出三千多场,观众三百多万人次,成为岭南地区极受欢迎的艺术团体之一。我们经常深入各个乡镇演出,来到工厂,甚至殡仪馆、监狱中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鼎盛时期,我试过一天演四场,场场爆满。还记得有一次在广东四会演出的经历特别让人难忘。中途突然停电,演出被迫暂停,但观众不走、也不起哄,安安静静地等来电后再接着看我们演。后来,演出结束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当时场内坐了一千多人,场外还有许多农民举着火把来看戏。我一生都忘不了这个画面,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的粤语相声带给观众的不只是欢笑,更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图5 黄俊英(右)和何宝文讲相声 (摄影:楚戈)

图6 黄俊英(左)在相声《手机》中与何宝文搭档
我今年(2022年)已经86岁,依然坚持在舞台第一线,因为我知道观众很渴望本土文化、本土演员,这让我很自豪。我离不开粤语相声小品,粤语相声小品也离不开我。只要观众还喜欢我,我就会为这个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刻,今生无悔,绝不封喉,这样才对得起喜欢我的观众。
四、说学逗唱,能编会导

图7 黄俊英(中)演小品 (摄影:楚戈)
罗:黄先生,您把戏曲程式、唱腔对白等元素引入相声表演,此外还涉猎了小品、电视剧等不同表演形式,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能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您在电视系列剧《七十二家房客》和粤剧《七十二家房客》中饰演的警察“369”,每次一登场都能引发观众的爆笑。您有什么表演秘诀吗?
黄:2019年,《七十二家房客》粤剧舞台版在中山纪念堂演出,很多观众是冲着我饰演的警察“369”去的。演出时,前两场没有我的戏份,场面便有些沉闷,等到第三场我一出场,现场就突然掌声如雷,整个戏院都热闹起来。有一位戏曲名家在看完戏之后对我说:“黄先生,警察‘369’这个角色,只有你能演!”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她回答说:“因为您懂得运用相声的包袱去演这个人物。”我听了之后很高兴,因为她说到了点子上。确实,我是用相声的表演技巧,比如相声语言、相声包袱来塑造人物,同时还通过活用戏曲程式给观众增加“笑料”。比如“369拔牙”这一段,“369”被金医生拔去好牙而留下坏牙,大铁钳又夹到舌头。我就运用戏曲程式动作,滚下牙科椅子,连连呼痛,加上愤怒、痛苦、无奈等复杂表情……每每演到这里,观众看完都笑到肚痛。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三翻四抖”。在《七十二家房客》的尾场,警察“369”带着一帮人,跟着局长去接阿香。到了门口,“369”带着几个警察进去搜,怎知阿香一早就被送走了,他找不到,只得出来向局长报告。如果是按剧本来演,那么“369”一出来就说:“报告局长,阿香不见了。”平平淡淡,没有包袱。于是我在演出的时候,就运用了相声的包袱,急匆匆跑出来,对着局长立正敬礼,“报告局长,阿香…阿香…阿香……”这样先紧张又急切地说了几句阿香,激发观众的好奇心,然后才突然用粤西方言说出“搵冇到(找不到)”,令现场一下子就爆笑出来。还有一句“369”对太子炳说的台词,剧本写的是:“炳哥,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将台词改为:“炳哥你放心,我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我没当一回事。”一下子效果就出来了。这些语言细节的处理,都只有一点的差异,却可以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图8 黄俊英唱粤剧 (摄影:楚戈)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小品《盲公问米》中扮演视障人士。当时我在广州一个视障人士的工厂外站了一个礼拜,观察他们的动作、表情。在90年代“生神仙”系列作品中,我扮演不务正业的算命先生,针砭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游医”骗钱现象。我为角色设计了夸张的造型,还糅合了粤剧丑生行当的唱白手段,在唱腔上下功夫,借鉴粤剧、曲艺前辈的“鬼马喉”,赋予人物“阴阳怪气”的语言色彩,使得这个毫不留情拆穿“游医”把戏的算命先生形象马上鲜活起来。
罗:您觉得哪些作品适合作为粤语相声传承的载体?譬如《广州话趣》展示了粤语方言独特的表达方式,能够让观众在听粤语相声的同时,对粤语相声最主要的载体——粤语,有更深刻的理解。
黄:相声是语言的艺术,粤语相声便是以粤方言精华浓缩而成。《广州话趣》中还有大量可以称之为方言教材的段子——大食(食量大)、大贪(很贪心)、大番薯(不灵光)、大乡里(乡下人)、大头鬼(打肿脸充胖子)、大食懒(好吃懒做)、大哥大(老大)、大只讲(只说不做)、大只(体格强壮)、大把(很多)、大头虾(健忘)。这个作品足以展示粤方言尤胜于标准化语言的魅力。在粤语中,关于颜色的形容词何其丰富——红当当(红彤彤)、黄琴琴(黄澄澄)、青BB(青涩涩)、白雪雪(白花花)、金划划(金晃晃)、黑锰锰(黑漆漆)、乌卒卒(黑漆漆),就连关于眼神的形容词都何其丰富——眼碌碌、眼眨眨、眼定定、眼光光、眼掘掘、眼坦坦。
粤语相声的创作演出与时代发展关系密切。作为曲艺门户“尖兵”的相声,一直取材于民众生活,从计划生育、招聘、拍广告、借电话、打麻将、讲手机,到四乡方言、省港澳比拼,作品中既充满亲切幽默又不失金句名言。在《省港澳大比拼》中,比对了广东和港澳生活习性中相似又有差别之处,显示了在改革开放之后,港澳与内地日益缩小的社会差距——港澳叫失业,广东叫下岗,下岗了还有机会再上岗;港澳叫安老院,广东叫敬老院,对老人家要表示尊重;港澳叫幼稚园,广东叫幼儿园,幼稚有贬义;港澳叫救伤车,广东叫救护车,伤字不吉利。
罗:粤语相声一度火爆南粤大地,广州甚至举办过两届广州市群众相声大赛和广州市首届中小学生相声大赛,也出版了不少相声集,但现在少有专门的相声专场,多数是相声小品一起演出,您觉得粤语相声式微的原因在哪里呢?
黄:粤语相声式微,既有外在因素,也有内部原因。首先是人才问题。我以前也收了不少徒弟,像李艳玲、陈坚雄、李月玲等,他们以前也跟着我学了不少相声,积累了一批观众,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徒弟有“担大旗”的票房号召力。演员的票房价值,其实也反映了观众的认可程度。为此,相声演员就要不断努力、专注艺术,不断学习、提高自己,活到老学到老。
另一个是作品的问题。一个好的相声作品,不论是语言还是题材,都要结合生活、与时俱进。我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仍有很多粉丝喜欢,演出经常叫好又叫座。我自己常常认真总结,这么多年来,我创作、表演不间断,总是努力主动去适应时代、跟上时代,比如这几年在相声中灵活运用一些网络语言。相声演员涉猎的领域一定要很广,一定要紧跟时代、常学常新,否则很快就过时了。
2020年疫情期间,相声的现场演出活动受到影响,我便开通了抖音号,玩起了直播和视频。“英俊黄学堂”推出的《万物皆可“热气”?》等视频节目都受到年轻观众欢迎。平时,年轻人爱玩的东西,我都乐意尝试。每当有人请教我的长寿秘诀,我肯定是笑称“不抽烟、少喝酒,多跟年轻人们交朋友”。
罗:您这几年致力于粤语相声的传承推广,收了几个小朋友为徒弟,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您觉得粤语相声传承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黄:近几年,我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授徒与推广粤语相声文化上。受多样文化冲击,粤语相声的演出市场在萎缩。加上粤语相声没有系统的教学模式、成型的教材和专业的教研团队,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始终困难重重。为什么我还在舞台第一线,一方面是街坊支持,这是我的荣幸;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没人能取代我、没有人接班,我真是忧心忡忡。
2019年,我推动成立粤语相声发展基金,通过开展粤语相声进校园、举办粤语相声大赛、组建教研团队编写粤语相声小册子及教材、建立一套规范的青少年艺术培育工作制度等方式,希望培养更多年轻演员、年轻观众。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这项事业后继有人!好在这两三年来,粤语相声进校园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在幼儿园、大学都备受欢迎,这让我稍感宽慰。
最近,我正在筹备2022年底举办的从艺70周年展演,此外还有师徒传承的专场演出。我希望能借助演出的力量,让更多人关注粤语相声文化。我相信,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粤语相声经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一定能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罗:2022年3月,您获得第三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这是个很高的荣誉,又适逢您从艺70周年,可以说,这是对您的艺术生涯的一次很好的总结了。
黄:这一次获得终身成就奖,我很惊喜,这是政府、社会各界对我这一生在艺术上作出的成绩的肯定。其实,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成长都是很艰辛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一届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中,分别作为粤剧、曲艺代表的黄壮谋和我,都是来自当年的珠江粤剧团。当我和黄壮谋一起站在台上时,我感触很深,忍不住就想起当年在珠江粤剧团的时光。黄壮谋比我大十岁,1952年我刚入珠江粤剧团当学徒时,他已经是头架色士(萨克斯领奏)师傅了。重要的是,这个奖不只是对我的肯定,更是政府重视粤语相声、重视本土文化的证明,是让我继续为粤语文化的推广、发展和传承而奋斗的动力。这个奖是沉甸甸的,我肩上的责任也是沉甸甸的,唯有继续努力。
访后跋语:
谈及粤语相声的创作,黄俊英先生常常会突然语气变得严肃,和他在舞台上让人开怀大笑的形象有着相当大的反差。在他看来,创作是极其庄重和诚恳的事情,不容马虎随意。这些年来,他总是用心把各种各样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给观众留下欢笑和难忘的记忆。至今,他演过百多个相声段子、谐趣小品、谐曲说唱,并有大量音像制品广为发行,成为家喻户晓的“笑星”。贴近生活的话题、轻松幽默的演绎、小人物般的心态,黄先生以其粤语相声小品,为粤语地区的广大民众发声,为本地民众百姓代言。作品中接地气的“包袱”、网络语言,正源于他本人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刻体验。
舞台上的豁达自信,源自人生中的豁达自信。在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时,黄先生说他能够看得很淡,也能够放得下,所以人生充满欢笑。而他,也将欢笑通过作品带给观众。祝愿黄先生绝不封喉,与笑同在。
——粤语·女独·伴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