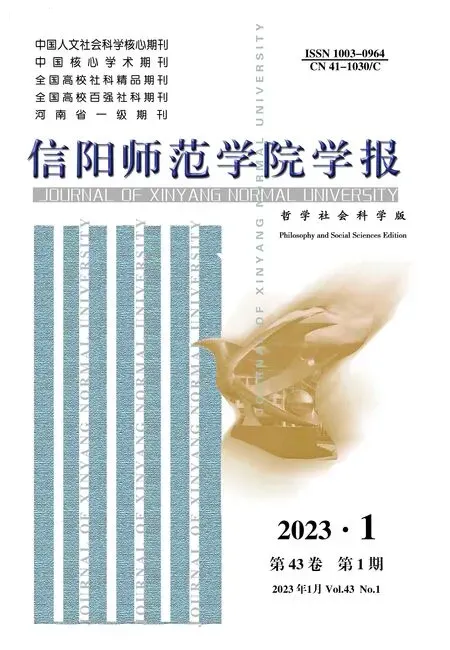战时西南边地书写中的“现代文明”反思与建构
尹 威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西南边地①于抗战全面爆发后,因远离正面战场且因地理位置的屏障优势而构成了其战略布局的重要区域地位。民族抗战使西南边地成为战时活力中心,文学、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实际发展态势因这种战略布局重要性的确立而随之生成了多元化的边地效应。从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讲,“民族国家既是启蒙的产物,也是‘朝向以征服自然为目标的,对社会、经济诸过程和组织进行理智化’的过程的一部分”[1]16。但是战时边地效应的生成并非全然符合这种“组织与过程的理智化”。事实上,这其中运转着矛盾与冲突、同化与反同化等诸多情势。基于此,论文拟从自然文明生态、抗战文化生态、宗教文化生态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战时边地文学中的自然文明生态话语反思
高云览在其《山城的云南》一文中写道:“抗战以前,云南这地方,一向被视为天漠避荒,蛮烟瘴雨的边疆,很少人注意到它,更因为交通和地域的关系,中原和边陲,自然地形成了一种隔阂,我国沿海城市的现代化,可以说很少影响到这古老的边城来。”[2]3-6其实,不单是云南一地,西南诸边地都有着相似的特性。然而,民族抗战的全面爆发打破了现代中国在此之前遵循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秩序,古老边地亦在这“破—立”的艰难态势下探寻出路。就战时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态势来说,先前已有的基建设施在较短的时间内被异族入侵者摧毁。民族工业中心由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大后方进行规模化转移,国民政府决定将西南诸边省作为工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其地域以四川、云南、贵阳、湘西为主;以西康、青海、甘肃、广西、陕西为补”[3]。如此来看,战前始终处于边地区域的诸省份在建设新规划颁布后,随即组织并建构了新的工业发展地带。
由战争带来的西南边地经济的突进式建设及后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这一区域先前所特有的古老、静态、原始的自然文明生态样貌的多重变化。如“工业化云南”的举措[4]使得“这古老边城也随着跳跃起来了,又因为主要城市的沦陷,交通线主要工商业的损失和第二期抗战展开,云南所处的位置,更随着战争的局势而增加其重要性,它成为全国战时国际贸易的枢纽,经济的中心”[2]。这为从经济视角来观照战时云南在文学创作中的面貌呈现提供了背景性材料,战时对经济建设的倡导给边省云南带来的改变,体现在连蒙自这样的小县城内的“西餐馆和咖啡店的应时而生”[5]。据此可知,云南所辖区域内所实施的工业经济建设举措在人们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之深广,此“深广”在凸显现代都市文明的“西化物质符号这一自然的指标”[6]的层面上有着体现。来看桂林战时工业的建设的大体情形,战时桂林工业能得到较快发展的主因“首先是工业比较发达的沦陷区各省工厂迁入广西”[7]39。从迁入工厂总量来看,“抗战期间迁入广西的工厂共32家,大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现代工业企业”[7]41;从工厂迁入的主要区域来说,这些拥有着现代技术的外来工厂迁入地“大多集中在桂林”[7]40;从外省工厂迁入的整体影响而言,这种工厂的迁入“给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刺激了各类工厂企业的开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县城投资建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7]41。而上述情状于贵阳、青海、西康等边地域界内亦有着相近的表现。隶属于战时大后方的这些边地省份地区的工业化发展,虽是在国民政府的事先规划与有目的地引导下而施行的边地集中迁入,但诸多外来工业化实体在较短时段内的集约化入驻,跟其地域内资源开发及相应储备之间构成了明显的不对称,故相应的现实性矛盾也随之产生,且这般局面在彼时的边地诸省的社会规划格局下几乎是难以进行调和的。再加上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迫于战时对诸多经济项目建设成果的急需,这就无可避免地形成了边地省份内工业经济建设所具有的“突击式”发展态势,最终使本就羸弱的国民经济从1938年始出现了蔓延于抗战大后方的严重通货膨胀。
战时工业建设在边地自然生态层面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当时诸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相应的多视角的表现。俞铭传的诗歌《拍卖行》与《煤坑》,鸥外鸥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诗歌可视为其中的代表作。这里以《被开垦的处女地》一诗为例。该诗将战时桂林作为描绘对象,标题用“处女地”这一带有特殊意指的称谓来修饰诗人初见桂林的印象。诗文前半部分反复使用了带有“山”的字句来写“未开垦的处女地”之纯美可爱。而这“山”既是桂林的自然景观标志,也是阻挡外来者的屏障,“狼犬的齿的尖锐的山呵,这自然的墙,展开了环形之阵,绕住了未开垦的处女地,原始的城,向外来的现代的一切陌生的来客,四面八方举起了一双双拒绝的手挡住”[8]53。诗歌的后半部分写“被开垦”的诸般情形,“山动了,原野动了,树木动了,河川动了,宇宙星辰的天空也动了,他们乘坐了列车轰隆轰隆的来了,举起了铁锄了,播下了种子了,开垦这未开垦的土地了,携带者黄的可爱的加州水果也有,携带者黑得可怕的印度植物也有”[8]54。诗人在此想要表达的显然是山城桂林的原始风气被蜂拥而来的香港人所携带的“现代文明”造成的不良影响的隐忧,全诗亦“展现了原本自然的桂林与‘外来的现代文明’的对立”[9],从诗结尾处发出的“注意呵,看彼等埋下来的是现代文明的善抑或恶吧”[8]54的质疑声中可以得窥。
铁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表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映现的是相应文本言说所涉及的社会的工业化程度,同时这种文本设置亦可作为一种符号/隐喻书写来读解。以滇越铁路为例,“滇越铁路通车后,昆明从一个交通落后、相对封闭的边陲城市,一跃而成为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直接发生联系的前沿城市,加快了昆明近代化的步伐”[10]。滇越铁路的开通虽对云南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显见的促进作用,但也导致了云南社会风貌的大幅变化,对底层民众的生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艾芜的小说《人生哲学的一课》对此描述道:“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不断地运来法国的货物和机器,把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国都市,出落成一个标致的摩登小姐了。在她的怀中,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儿:从洋货店里出来的肉圆子,踏着人力车上的铃子,嘡啷嘡啷地驰在花岗石砌成的街上,朝每夜觅得欢乐的地方去。”[11]10-24艾芜对滇越铁路带给云南社会风气转变的描述不无讽刺意味,而“村姑娘”与“摩登少女”的对比,使得边域滇城的现代化转变情势得到了形象化的呈现,“洋货店”亦应时应景成为孕育“都市怪胎”的标志性场所,此般书写代表着作家对现代文明带给边城社会深刻变化的一种反思。
这里亦可借助梁山丁的小说《绿色的谷》中对铁路的描述来跟艾芜笔下的铁路作以比照。前者借多面向的描述呈现出带有层次感的小铁路意象。文中对工人们用炸药和镐头削平凸起的丘冈描述道:“仿佛外科医生削去了不必要的瘤,以至地面露出许多巨石的尸骨”[12]192。而原本“草甸上的苇、艾织成的锦席,如今被横切了一刀,分开了,在路基两旁,摇着窈窕的腰肢”[12]193。当地民众对小铁路的反感在“那个钢铁的怪兽——机关车试探着脚步出现在狼沟的山谷的时候”得以凸显,“终生不出户的庄稼人惊奇地望着它,女人们恐惧地唾骂着:‘现世的魔障,在白天里出现了’”[12]193。在记述小铁路进狼沟的过程时,作者对工人们“充满着乡愁的歌声”进行了两次带有共情诉求的场景交代,借此抒发筑路工人心目中易于引起读者共鸣的“我爱我那破碎的家乡”[12]191的情感内涵:一面是自己热爱的皇天后土;另一面却是自己要亲手将这深爱的谷地用力地“炸开”“切开”“削去”,在这种失乡情感的对照下,表现出的是对铁路这种现代交通工具所承载的掠夺意图的反感与痛恨,流露出这种现代器物带给生活于此的普通民众心理的逼迫、挤压。
跟自然生态破坏于工业建设规模的畸形态势下的实情相较,像铁路这样的现代工业化的标志性器物带给战时边地的既有内部经济生态的转变,又有对传统中国尤其是边地这样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文生态的冲击与重组。从战时民族国家建构的意义上来说,它还可被视作是异族侵略者试图在边地扎根的触角。在边地书写中对于自然生态文明失衡维度的表现,其特质就在于对边地空间内的人与土地所具有的那种原始性的打破,此“原始性”既体现在自然层面上,又体现在精神气质层面上,如“未开垦的处女地”“被削平了凸岗的原野”“被劈开的漫生于山谷中的苇与艾织成的锦席”等意象序列,是对于土地原始性遭受现代文明打破的书写,“村姑”与“庄户人家的女人们”则折射出现代文明对人的原始意识认知空间的转变。从地域的原始性这一层面上来书写现代文明的出现及其对土地与人的影响,更能透射出此等转变所带来的感觉与想象的冲击力。
二、对“外来者”群体抗战文化生态的批判与建构
“外来者”对于边地的在地民众来说是一个“整体”概念,在实际的“外来者”构成人员中,知识分子群体在边地抗战文化生态的对话中的作用更为显著。由于规模化迁徙活动的发生,尤其是众多大城市文化人及许多文化机构的边地迁徙,为具有不同层次文明意识的民众的现实冲突与随之形成的共融情势提供了空间基础,亦使得在此之前已然形成的不同区域内的现代性经验积累有了直接对话的可能。从文化人的边地汇聚的时间先后来看,昆明是其战时汇聚的第一站,其次是桂林文化城的逐渐形成。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于1938年1月做出了关于迁校入滇的决议,湘黔滇考察团的终点地便是昆明。昆明是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众多文化人士首先得以大量汇聚的地方,而桂林、贵阳等地的文化人的边地客居情势在其后才逐渐汇聚起来。边地空间在抗战大后方形成的文化中心地的比重异常显著,重庆、昆明、桂林一度被认为是抗战大后方三足鼎立的文化中心,其中有两地便是基于边地空间而建立的文化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云南、广西等地为了配合一触即发的抗战严峻形势,已在本地掀起了多种形式的文艺活动。以广西文艺界为例,“抗战前夕,广西文艺界先后以南宁《民国日报》副刊《铜鼓》(黄芝冈主编)、桂林《广西日报》副刊《文艺周刊》(祝秀侠主编)、《梧州日报》副刊及国防艺术社主办的《战时艺术》为主要阵地,对《广西文坛往哪里去?》《‘国防文学’与救亡》《反‘差不多’运动》《文艺通俗化》等论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并且还多次组织了文艺座谈会”[13]42。这些围绕抗战展开的文学活动为广西抗战文化的在地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虽说交通闭塞,但其从五四时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时段内的文学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仍然和全国的步子基本一致”[14]103,在文学思潮、文学论争及文学理论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成绩。尤其是发生在1936年8月至12月期间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虽在云南“省内发生的时间比上海等地约晚了十个月的时间”[14]128,但诸如此类基于地方文学与文化而展开的论争,同样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云南文学的兴旺打下了基础,拓宽了道路”[14]129。以此观之,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广西、云南等边地空间在全国抗战形势的影响下,基于自身情况在抗战文化氛围的营建层面上做出了诸多努力,并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也即是说,并非是在大批外来作家及文化人迁徙、流亡到边地以后,本土的抗战文化才得以生成和发展,在此之前其内部已对以地域文化作为基础的抗战文化内容有所积累,而这对于理解边地空间内抗战文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多种现象有着重要的价值。
正是有了这些外来作家迁入之前已然形成的抗战文化意识的存在,才使得边地本土作家在看待外来知识分子的抗战态度时,有了某种比照标准和心理期待。同时,也只有在相当迁入数量的知识分子的前提下,并且这其中要有具备一定文学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才能在当时的边地空间内引起“外来者”与“本土者”两种有着不同地域身份的知识分子之间观念冲突的生成。如何面对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涌入昆明的外来知识分子,昆明本土的文化人士对此迅即给出了他们的评价声音,在《云南日报》上刊载的题为《欢迎临大湘黔滇旅行团》的社论,对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曾经历过的“颓废生活”可能带给昆明抗战界的负面影响表达了批判声音[15]。随后出版的《民国日报》又于同一期刊载了《警告摩登男女》和《与摩登男女相关》两篇文章,在内容上这两文均表现出了力持此前李意文章中所述及的那番“警言”②。云南本土文化人士所言及的“颓废”的意涵,于此更准确地说是在表达一种“具体的文化颓废概念”[16]。“颓废”是现代性的一种表现方式,而由此引申出的颓废心理意识及其生活态度与文学中的颓废表现手法是两种不同的意指概念,围绕抗战文化的边地建设及推进而对外来作家群体产生的些许质疑,实质上是站在此角度上的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否定,也是本土文化人在边地视角下对外来知识分子群体审视态度的心理体现,这背后是不同文化观念的支撑。
初来乍到的外来作家,其自身的文化优越性心态还是较为明显的,这也可理解为“人之常情”。虽为“常情”,而从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在支持抗战的心理统一性的考察向度上来讲,文化层面上的对话与互融过程,显然很有必要,现实中这一情形确实也应势发生了。但事实上这些被视为颓废甚或是与抗战无关的摩登心态等具有现代文明表征的生活方式,并未在客居昆明的外来文化人身上延续性展现,从这些知识分子呈现出的各自努力及其表现出的对抗战的支持力度来说,昆明本土文化人在外来知识分子初踏边地而产生的担忧,多少有点不攻自破的意味。另外,西南联大在长达8年的办学时间内,在现代文学已有脉络的延承、现代知识分子民族抗战情结的凝聚和表达、现代大学教育的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均取得了为后世称道的不俗成就。尤其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并留存下来的西南联大精神,在诸多方面至今仍是激励知识分子履行其应有社会使命的一种重要的内在认可,是激励知识分子不断进取的精神资源。
其实,在知识群体之外,外来至西南各边陲之城的普通民众对边地社会的初始形态也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而这其中当属外来民众对抗战情绪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氛围分裂则更易于触动作家的敏感神经,这些内容为认识边地抗战的众生相提供了书写空间。如诗人鸥外鸥客居桂林时,以《桂林的裸体画》为题展开的组诗创作就形象地刻画出了此地的战时民众群像。来看这首题为《传染病乘了急列车》的诗歌,诗文通过塑造“穿着整洁无垢的洋服的先生”“制造上等家具的木器商”“手握圆规三角尺的建筑师”“‘Yes Sir,Yes Sir’的侍者”“唱着‘Love Me Tonight’西洋恋歌的少爷”及“写着‘我的佐治’的情书的小姐”[8]55等光怪陆离的人物序列,显在而又深刻地表达了诗人怀揣抗战情感而生出的对“当时的桂林受到香港人风气的冲击而表达出的忧心忡忡”[8]56。再如,高云览在其《边疆漫记》一文中所塑造出的“高等难民”形象,亦为阐述“现代文明”的创作主题提供了别样视角。该文写道,这些从沦陷后的香港“逃难”的难民们,“女的红唇烫发,照旧香喷喷。男的西装革履,浑身斯文,没有一点难民相”[21]262。逃离香港来到昆明只是为了“在这边疆享受一下山城的‘伊甸’”[17]261。但此时的山城很显然并不是这些逃难来的“外省人”的“安乐窝”,“这山城将以铜铁铸成城壁,血肉磨亮枪刀,这城壁如枪刀,是准备有一天给敌人的脑袋和颈子来碰的”[17]262。从民族抗战的现实层面上来说,这些拥有先进物质文化的“香港人”群体,在思想意识和实际行动的双重层面上均未参与到民族抗战的时代洪流中去,与此相对应的是,却只顾为自身寻求到了自认为的安全偏居之地而沾沾自喜,在战时语境下的“香港人”形象所折射出的“现代文明”与“现代人”应有的身份之间的现实背离在文本的多向描述中得以凸显,进而映现出了作家对此问题敏锐的批判意识,显现出战时边地文学所应有的社会批判价值。
三、外来宗教文化渗入对边地社会思想的影响
外来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形式,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宗教文化发展进程中有着多面的参与度,对现代中国社会宗教文化的建设有着无法忽视的作用,且是中国传统宗教结构向现代宗教建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作为宗教文化的传播主体的传教士是这一“参与度”及所起作用得以实现的直接因素,外来宗教除了在文化生态的现代建构方面的表现较为活跃之外,在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亦有着一定向度的参与,如西方传教士“在现代文学语言与形式方面的努力”[18]69-95、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新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与相关研究”和“近现代以来的以《女铎》月刊为代表的报刊创办”[24]111-158等文学活动,均能很好地体现出上述所言及的“参与事实”。近现代以来来华的传教士当中,明兴礼、赛珍珠、包贵思等人可视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到显著作用的代表性人物[19]159-234。若沿此理路进行一种谱系化的考察,则众多现代作家在创作中关涉到的宗教因素,事实上也能在外来宗教的多重传播路径上找到相应的影响。
评判战时边地社会里外来宗教的传播意义,主要是从其与当时中国国防稳固之间的关系及在边地社会内所生成的影响两个层面上展开。关于此,知识阶层大体持有两种不同的声音:赞成者认为外来宗教携带的现代性内容能够促使边地社会已有的运行情势发生某些改观。譬如,云南籍作家楚图南关于路南传教士“邓神父”③在促进边地文化事业发展及对边地民众的思想解放等方面做了积极的评价。施蛰存在《路南游踪》一书中也曾以“郑保禄司铎之墓”的标题对神父保罗•维亚尔的中国边地阅历进行记述,与楚图南的评价有所不同,施蛰存只从保罗·维亚尔关于“倮罗族”的“语言文字生活习尚”的研究与《倮罗人》(Les lolos)、《教理问答》等成果着手,从而肯定了“这位西欧的学者孤寂地研究远东一个弱小的原始民族”[20]63-64的生命轨迹。
而对此持质疑及抵制态度的知识分子正是以文化入侵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现象,支持该视角的知识分子认为,帝国主义以强行输入形式进行的多种边地传教行为,其实质在于“阳借传教之名,阴谋分羹之实”[21],带有殖民性,即这些传教行为在边地少数民族国家民族意识的统一性、民众的国家认同趋向层面上,存在有一种分离边地少数民族团结一致抗战的社会隐患。同时,这种隐患还体现在战时国防建设与宗教受众的具体分布两者之间的关系上,而边地区域的战时功能随着中心城市的沦陷而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意义,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上均具有重要意义,边地稳定性无疑是支撑抗战进行的必要因素。
在边地本土作家中,诗人彭桂萼在其时文论著与诗歌创作中对宗教问题都有涉及,对此明显持批判与抵制态度,这在当时诸多持类似观念的在地作家中较具代表性,如在《西南边城缅宁》一书关于缅宁“耶教”发展进程的介绍:
民国十年,加拿大人马锡龄夫妇来缅宁,就县城东门内租借民房传教,隶属于云南省城五旬节会福音堂,是为“耶稣”飞进缅宁的开始。他们苦口婆心的宣讲了一年左右的教义,入其圈套者仅有百多个汉人妇女,故于十一年乃改换对象,另赴城北三十余里的明子山,建盖较宽大的教堂,专门向那些拉祜进攻,并继续把福音小学也设起一所来。辗转经营了几年,教民果然增加到好几百名了。在民国二十年瑞典牧师革乐生任内,他们的拉祜教民毕老大父子因欲骗占民马,自行捣毁教堂,捏报匪情,经县府查明请洋牧师来开了一次外交会议,已知会他们另行迁往安全地带,故现在仅有当地教民自行宣传,洋牧师早没有来了。[22]192-93
从“入其圈套者”“专门向拉祜进攻”“灌输教义”“麻醉教民”等诸种表达,已可清晰地看出彭桂萼对远道而来的这些“洋牧师”的态度。除此之外,彭桂萼还从战时边疆政教活动的角度,探讨了外国来边教会对于现代中国边地的威胁所在,他认为:“凡教会力量所到的地方,多变成了他们的商品消场与统治范围,由宣传宗教信仰的面目,已摇身一变而成为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的急先锋,中国自受他们这种文化侵略的毒害,也就不可涯量了!”[23]26而相近的抵制思想在其《为收回双江勐勐教堂敬告国人》和《收回双江勐勐教堂的理论与实际》两文中也有鲜明表达,这些内容于整体上凸显了彭桂萼在外来宗教问题上所抱持的民族主义倾向。
这种批判意识在彭桂萼的战时创作实绩中也有所呈现,如诗歌《烟花开遍阿佤山》[24]68-75,便运用较为接地气的语言表达了对于“慈祥得如乳娘一样的那主宰命运的老洋人”的尖锐嘲讽。不难发现,彭桂萼始终是站在团结边地所有民众抗战的基点上,来审视这些外来宗教人士在边地空间内从事的文化活动,其借用诗歌形式展开的这般宣传,明显带有抵抗色彩,而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对边地民众那种试图通过外来宗教寻求心灵和肉体所面临的双重苦难的解脱的批判。同样地,对于外来牧师形象的书写在云南作家宣伯超的短篇小说《碧罗山下》[25]75-97中也有着非常形象化的表达,马牧师在傈僳中宣传“上帝”如何拯救负罪人类的思想,而他和“皇帝”派来搜刮钱财的周师爷、穿着马褂的官员实属一丘之貉。傈僳们对周师爷不断抬高的收缴标准与无端恶意的挑衅进行了反抗。被捉之后的马牧师扬言要“请他们的政府直接交涉”,最终这场反抗以傈僳们的失败而告终。傈僳们从信鬼神到信“上帝”的信仰转变,并未改变其受官僚压榨的命运,而马牧师传教言论中的“莫要反抗”“罪在自身”等无理说教观念则带有明显的麻痹边民思想的意图。
四、结语
近现代以来对于“现代文明”的批判一直是知识阶层所聚焦的话题,而在战时边地文学书写中的“现代文明”批判主题是一个自具地域特性的“现代文明”场域,这种特性为此主题的深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角。分析边地文学中众多作家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性话语,其目的大体上是质疑“进步主义视文明为统一的、线性的发展过程的思想,而是从根本上洞察到现代文明的内在冲突、分裂和破碎的情势”[26]。对边地文学书写中“现代文明”主题的批判向度考察,始终要在战时语境下对此进行分析,从宏观层面视之,日、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入侵行径,其实质便是对现代中国已有文明生态系统的一种破毁。从自然文明生态、抗战文化生态、外来宗教文化等细部做出对边地“现代文明”的批判性探究,正是据此为审视这种破坏与摧毁的历史提供出一种反观式视角。这里还需对论述选择的探究视角做出一定的区分,论题主要是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所展开的对“现代文明”批判主题的探究,而“民间视角”下的“现代文明”批判作为知识分子视角的一种补充,客观来讲也是存在的,基于此视角下的成型文本几乎空白的现状,对其存在范围及程度的界定仍是一个难题。然而,通过当时知识分子对同一主题的批判话语建构图谱之中的民间视角描述,还是为这种并未形成独立的批判声音保存了只言片语,它的存在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最为醒目的便是“民间视角”下的关于“现代文明批判”的对应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知识分子视角下的民众启蒙意识的呼应,为解读战时“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之间的思想互动问题再次提供了一种视角。
注释:
① 本文所指“西南边地”依据战时中国地理版图,主要涵盖云南、贵州、广西、西康等地。
② 此处所列举出的同期刊载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署名“源”的文章《警告摩登男女》与署名“文”的文章《与摩登男女相关》,《民国日报》1938年4月14日。此处文献搜寻受研究者王佳的启发,参见王佳《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楚图南此处言及的“邓神父”,即法国传教士保罗·维亚尔(Paul Vial),中文名是“邓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