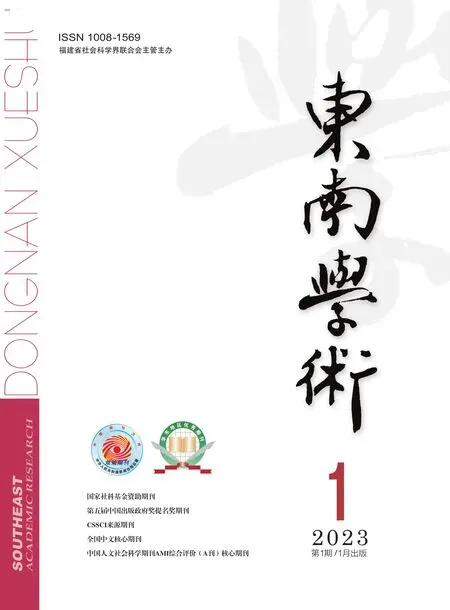价值关系异化:作为商品中劳动交换关系物性结晶的货币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再研究
张一兵
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是他实现第二个伟大理论发现——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经济学论著,也是一部内嵌着丰富方法论变革的哲学论著。应该说,《大纲》所呈现出的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实验中,爆燃起马克思认识中的多重革命火焰,其中最重要的方法论进展为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的创立,并且,马克思从1845年开始抑制的我-它自反性异化概念又重新在经济物相化空间塑形的事物化颠倒关系中出场了,它直接昭示着劳动辩证法基础之上的批判认识论话语的科学回归。在此,本文仅就马克思在《大纲》“货币章”里关于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作为经济物相化初始层面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脱型自身且反向对象化和物性到场的货币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不在场的在场性:作为劳动交换关系反向物性结晶的货币
进入《大纲》的肇始阶段,马克思这里并没有完整地叙述一种经济学理论构境,而是在面对具体的理论争论中进入经济学研究和分析过程的,即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①路易-阿尔弗勒德·达里蒙(Louis-Alfred Darimon,1819—1907):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初为蒲鲁东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法国国会议员(französischer Abgeordneter)。1819年12月17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Lille)(另一说法是出生于1817年12月),1902年10月1日逝世于塞纳河畔的讷伊(Neuilly-sur-Seine)。自1840年开始为《北方评论》(Revue du Nord)撰写文章。作为蒲鲁东的学生,担任蒲鲁东的秘书,并从事新闻工作。1850年担任《人民之声》(La Voix du Peuple)的主编,涉及经济和金融问题。1857年当选为塞纳河第七区议员。1869年被拿破仑三世任命为贸易、农业和工业高级委员会特别专员,负责处理货币问题。代表作有《论银行改革》(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1856年巴黎版)等。马克思在1857年1月10日写给恩格斯信中提及:“我这里有蒲鲁东的学生的一部新著作: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版。老一套。停止流通黄金和白银,或把一切商品象黄金和白银一样都变为交换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页。在“劳动货币”方案中,将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中货币流通与信贷错误地画上等号和夸大银行在调节货币市场中作用,并直接以劳动时间量作为货币改良依托的具体失误。所以,马克思的思考没有从经济表象中的商品或者更深一层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出发,而是直接从货币出发。他没有直接讨论交换价值在流通领域中的客观抽象,而是从交换价值关系结晶为物的货币反向深入到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背后的劳动。这也说明,《大纲》不是一本马克思写给读者看的“作品”,虽然在《大纲》最后,马克思也初步拟定过一个可能性的经济学理论阐释的“五点构想”:一是经济学理论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二是“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关系和阶级结构;三是资产阶级社会“国家形式”;四是“生产的国际关系”;五是“世界市场和危机”。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马克思在《大纲》中的实际发生的写作,显然不是对经济学理论的系统阐释,而是他在经济学研究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实验过程,一些重要的经济学问题都还处于逐步明晰的状态之中。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在《大纲》中的研究性思想实验,显然不同于后来刻意阐释一种经济学理论话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在这个意义上,《大纲》显然也不能目的论式地被视作《资本论》的草稿或初稿,因为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科学地完整透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来海因里希③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1957— ):德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代表人物。留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马克思的《大纲》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出发点”。④海因里希:《重建还是解构?关于价值和资本的方法论争论,以及来自考证版的新见解》,载贝洛菲尔、芬奇主编:《重读马克思——历史考证版之后的新视野》,徐素华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这是正确的判断。也因为资本的通常形态是货币,要说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误认为生产过程中到场物的新型经济物像,就必须说明货币是如何从商品交换中历史性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章”正是对接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那个不可直观的资本关系的史前变身史。请留心,这又会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物像证伪构式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重演。
马克思认为,达里蒙等人的根本错误在于,将资产阶级经济生活中社会关系的本质与感性直观经验塑形中物的现象、实在内容与其颠倒性的表现形式直接等同起来,似乎只要将货币注明为显示劳动量的工具就可以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的根本矛盾。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他们不能理解,作为商品社会本质的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8页。这里,马克思还没有说明交换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拜物教徒”(Fetischist)贝利“把价值看成物和物之间的关系(Verhältniß der Dinge unter sich,外文为引者加,下同),而实际上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人们同他们的相互生产活动的关系在物上的表现即物的表现(dinglicher Ausdruck)”。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8页。本质上,这种Ding(物)的背后是经济事物(Sache)。马克思后来用事物化(Versachlichung)来表征这种此-彼错位关系中的客观颠倒。请注意,这里出现的此-彼错位关系,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此-彼归基关系,即从一般物相化③物相化,这是我在本次研究中从马克思思想中提炼出的新概念。物相一词,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已经使用。在物理和化学等科学研究中,phase又称“物态”,一般指物质分子的聚集状态,是实物存在的形式。通常实物以固态、液态和气态三种聚集状态存在,在特定条件下又会出“等离子态”“超导态”“超流态”等物相。但我所设定的物相化中的“相”不仅仅是物态之意,而兼有实现出来的主体性爱多斯(eidos,共相)之意,因为黑格尔、马克思思想构境中的一般物相化,总是指一定的主体目的(“蓝图”)和理念对象性地实现于对象的用在性改变之中,这是看起来现成事物对象的消逝性的缘起。因为日本学界在日译马克思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时,通用了“物象化”一词,而中文中与意象相对的物象概念本身带有某种主观显象的痕迹,所以用物相概念可以更好地表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透视的用在性实存对象。马克思在自己晚期经济学的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讨论中,经常使用materialisirt(物相化)一词来表达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活动(爱多斯)在塑形对象效用中在物质实在中的消隐。Karl Marx,Grundrissen,Gesamtausgabe(MEGA2)Ⅱ/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2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4-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1988,S.47.当然,人历史地实现自身的主体物相化,人创造出不同历史时间质性的社会共同体组织的社会物相化,工业生产中机器化大生产中的科技物相化和商品市场经济场境中,整体盲目无相化的经济反熵和反爱多斯经济物相化是更难理解的。中那种物体现成性和人的独存性之此在,归基于实践(生产)活动和社会关系场境,而是对不可见的交换关系客观抽象为交换价值,并且进一步反向颠倒为货币(资本)等经济事物的此-彼错位伪境的破境。可以说,Versachlichung(事物化)是继客观抽象之后,历史现象学中第二个重要逻辑构件和科学概念。这种事物化颠倒不仅出现在流通领域中的价值关系事物化(Ⅰ)颠倒地呈现为货币物,也会出现在之后生产过程中资本关系事物化(Ⅱ)颠倒为劳动条件物(原料、厂房和机器等),以及机器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地租、利息等更加复杂的事物化现象。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这里的Ding可视作康德认识论构境中无限后退的“自在之物 ”,而Sache,则是自己的社会关系在特定社会历史先验构架支配下生成的颠倒性物相显现。这一点后来被齐泽克发挥为所谓作为此-彼错位关系伪境中的“崇高对象”的Sache。他说:“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一个马克思未解决的货币的物质特性的问题:不是指货币赖以构成的经验的物质材料,而是指它的崇高性的材料、它的某种另类的‘不可改变且坚不可摧的’躯体,这一躯体在物质性的躯体腐朽之后仍能继续存在——货币的这种另类躯体类似于萨德笔下的受害者的尸体,虽历经折磨仍不改其美丽。这种‘躯体之内的躯体(body-within-the-body)’的非物质性的实体使我们可以精确地定义这个崇高的对象(sublime object)。”④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齐泽克的看法是深刻的,只是他用拉康式的话语将其思辨化了。通俗些解读,即是马克思思考货币的物质性时,已经发现了这种物质性存在的背后隐匿着一种不会随着物质熵化而消失的神秘编码空间中存在的“崇高对象”,这就是经济物相化背后的消逝的不在场价值关系。从铸币到纸币,再到今天的数字化货币,经济事物的肉身可变,但“崇高对象”金刚不坏。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发生的经济物相化不是观念层面上的主观事件,而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被金钱编码的客观现实生活本身,只是这种支配经济生活的辩证运动采取了颠倒式关系伪境和伪在场的方式,这也意味着,社会场境关系赋型中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先验再一次畸变成倒置的经济先验物。这是主体性的劳动辩证法颠倒为经济事物的消极辩证法中最关键的一步。之所以指认它是消极的经济事物的辩证法(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主要因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物相化活动表现出由内部矛盾驱动的从商品、货币再到资本的自我运动,但这种总体性的辩证运动却是在人之外客观运转的。它不仅规制人的全部意识以生成特有的经济拜物教,也通过客观的经济关系伪境直接编码和支配所有人的现实生活。在商品-市场经济所筑模的现实生活中,“钱是好东西”是不需要教科书教化的,一个孩子会在没有钱就不能吃到自己喜欢的麦当劳,没有钱就不能得到比幼儿园小朋友更漂亮的文具中被“强制同一性”(阿多诺语),所有人在生活塑形中感到金钱的力量,这不是观念塑形,而是生活在场性中的现实经济事物辩证法勾连人与万物的关系编码和构序。所以,这种经济物相化的迷雾,绝不是历史认识论能够透视和解码的,它必须通过呼吁请求批判认识论的重新出场。
这样,在《大纲》的“货币章”中,货币是资产阶级经济物相化空间里“第二自然辩证法”中继商品之后出现的第二个重要经济事物,这是经济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第二层面,也是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特殊经济物相化存在论此-彼错位关系伪境的第二层面。应该先说明一下,这里的物性结晶不同于劳动物相化真实塑形和构序商品的用在性使用价值,它仅仅是一种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社会关系场境(作为经济物相化初始层面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脱型自身且反向对象化和物性到场。或者说,这就是作为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出现的第二种经济事物(Sache)。马克思此时针对的是自己在《金银条块》中提点的西斯蒙第提出了那个有启发的比喻,即货币像是人的“与身体分开的影子”(den Schatten vom Körper getrennt),①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8, Berlin: Dietz Verlag,1996,S.22.中译文参见沈渊等译稿,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第1期,第23、22页。这也意味着,货币不是它自身,而是价值的一种“抽象单位”(abstrakten Einheit),不过在西斯蒙第看来,这种抽象只是“纯粹观念性的”(rein ideal)。②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Ⅳ/8, Berlin: Dietz Verlag,1996,S.22.中译文参见沈渊等译稿,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1989年第1期,第23、22页。货币当然不是商品的Schatten(影子),或者一个主观的东西,它真的就是在商品交换场境中到场的经济事物。只是马克思认为,这种经济事物并非它自身,虽然在货币本身的生产中,存在着劳动塑形和构序,如最早磨制贝壳或石片,后来浇铸金属铸币,然而,货币在经济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中生成的经济质性,并不是具体货币生产中劳动塑形和构序物品的用在性,这种用在性的到场本身就是以存在论的失形方式出现的。货币的经济定在只是商品交换场境中生成的特殊经济关系的此-彼错位结果。在马克思的眼里,财富的这个社会定在(gesellschaftliches Dasein),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Jenseits),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事物,商品(Ding, Sache, Waare)。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9页。中译文有改动。Karl Marx: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15,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4,S.565.货币物不是物,而是它所替代的关系场境。这里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货币不是它自身,不是一般物像中的现成性或独立实存性,而是不可见的交换价值关系的自我脱型和错位实体化。经济事物存在论特征,恰恰是遮蔽某种经济定在关系的脱型和错位。这是不同于一般劳动生产物相化和社会物相化的经济物相化起始中的第二个此-彼错位环节。这自然是很难理解的,我们一步步来入境。
二、作为货币本质的抽象劳动的等质性
实际上,马克思告诉主张“劳动货币论”的蒲鲁东主义者,“货币不是简单的物”,或者说,“货币不是它自身的在场”的这种透视,只是马克思自己经济学研究中有特定针对性的思考构境,它同样省略了大量解释学视域中的前提,所以这对于刚刚进入经济学专业话语阅读的读者来说,这一表述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因为除去马克思在《大纲》结尾的“价值”手稿片段①马克思在《大纲》手稿的最后一页,起草了第一章“价值”的初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294页。中已经补充的交换价值关系的历史抽象问题之外,需要事先讨论的问题本身就是十分复杂的历史认识过程。为此,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解释。
比如,我们旅游到英国,在超市结账时拿出一张十英镑的纸币以取得所需要的商品,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经验小事。你现在手上的这张十英镑的纸币,从物理空间的感性经验塑形中,在素朴实在论和传统认识论的构境中,它可触摸,并且可看见印有彩色的图案的纸,然而马克思则想告诉你,这张作为Bekannt(熟知的东西)且可以对象化直观中的纸并不是Ding(物),并且即便将它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物像透视中归基为社会空间中木材通过复杂加工和印刷劳动物相化活动也是不够的,因为它之所以可以买到商品,恰恰因为它的本质是一种建立在自身用在性失形之上看不见的不在场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场境反向对象化颠倒的Sache(事物),这里熟知的英镑只是无法直观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商品价值关系(不在场的经济物相化第一层面中“交换价值”的本体)的“物质的、独立的存在”,它的物性到场,恰恰代表了一种新的不在场的在场性的经济物相化脱型和编码(神秘化的此-彼错位伪境的第二层面)。这是批判认识论剥离的新一层经济伪物像。有趣的是,在今天中国已经出现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远程电子商务支付)中,这种直接的物性到场也被消除(失形)了,金钱物性到场背后的不在场以非物性的数码在场呈现出来。这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数字化历史在场性和数字存在论,其中发生了更加复杂的经济物相化场境关系脱型和转换的此-彼错位象征关系伪境。当然,数字经济编码的现实基础仍然是客观经济财富的在场。具体说,马克思这里是想告诉我们,这张纸之所以可以购买任何东西,神奇之处在于它并不简单是一张有印刷图案的物性的纸张,而它是一种不能直观的劳动交换关系场境在纸张上的物性结晶。这也表示,在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熟知的这个特殊的“物”,在双重物像透视(一般物相化与经济物相化)中不是物,而是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之后用在性社会空间关系场境,在经济交换关系中(以抽象劳动)重新反向对象化后的结果,它是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经济事物。之所以一定要强调这种此-彼错位关系是一种经济伪境,因为由此劳动的辩证法被很深地掩盖在经济物像的事物的辩证法构序之中。所以,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断言:“一切物化都是一种遗忘(Alle Verdinglichung ist ein Vergessen)。”②Theodor W.Adorno, Max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Fischer, Frankfurt a.M,2000, p.286.布洛赫③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 德国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代表作为《乌托邦精神》(Geist der Utopie,1918)、《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 als Theology der Revolution,1921)、《主体-客体:关于黑格尔的笔记》(Subjekt-Objekt,Erläuterungen zu Hegel,1951)、《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1955—1959)等。深刻地指出,“由于物化的产品,人们很容易遗忘生产者;由于人的背后的固定现象,很容易遗忘在他们前面运动着的敞开的东西”①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44页。,这已经深刻地达及了透视一般物相化的构境,可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透视马克思这里揭示的经济物相化此-彼错位关系神秘编码背后遮蔽起来的劳动辩证法。需要指出,货币本身的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从树木到印刷后的纸币)中实现出来的爱多斯(eidos),已经不再是面对人的生产需要的用在性目的(telos),而是面对“值多少”(交换关系)的经济爱多斯(贪欲)。当然这不仅仅是经济学话语,还包含着马克思深嵌在经济学思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不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话语,而是特指面向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发生的经济物相化存在论关系场境中历史现象本质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其实,这里遭遇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物像证伪的否定辩证法的逻辑构式。可是,这并非为唯心主义的精神现象学批判,而是真实的历史现象学的存在论关系透视。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现象学是面对存在论关系场境空间,然而这个存在论却已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才会发生的更复杂的经济物相化存在论,其中,无序返熵的经济物像中登场的各种经济事物的消极辩证法构成了一出人不再是编剧的荒诞戏剧,经济人成了“看不见的手”(理性的狡计)无形摆布的牵线木偶,它扭曲的逐金灵魂则是经济拜物教。并且,这里非直观的经济事物伪在场和倒置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伪境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复杂经济物相化存在论关系场境现实,也是历史现象学需要透视的神秘化迷雾。
这真的非常难以领悟,因为它与生活中素朴实在论的常识经验不一致。这就像每天亲眼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边落下,常识经验中Bekannt(熟知的东西)是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可是有一天一个叫哥白尼的怪人突然说,错了,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我们围绕太阳转。我们会发现,科学透视总是出现在常识的断裂之处(巴什拉语)。第一步,马克思的经济学语境中批判认识论的认知构式从一开始就是与经验常识不一致的,在所有人看到熟知的货币物性到场的地方,马克思透视出它背后的商品使用价值关系的场境存在,这是前面已经熟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此-彼归基关系透视一般物相化迷雾的社会空间场境关系存在论;第二步,不同于商品使用价值(用在性的“为人定在”)的可感性,价值关系(“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不可见社会本质(gesellschaftliche Dasein ——社会定在)却通过此-彼错位的事物性的货币表现出来。这个不可见的gesellschaftliche Dasein,正是齐泽克所指认的“崇高对象”。②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25页。这样,本身不是物的用在性定在的Werthverhältnisses(价值关系——经济物相化初始层面),则从不可见的隐性存在重新颠倒为经济物相化中的可假性直观的经济事物(经济物相化第二层面),这也进入到经济物相化存在论中经济定在关系场境的第二个此-彼错位伪境的神秘层面。这是说,英镑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熟知物像,当然已经不是一般物相化迷雾,而是全新的经济关系场境的物相化和事物化。格雷-蒲鲁东-达里蒙的错误,就是把非物的货币(经济事物)真的当成了物,他们无法意识到,即使把这个物上的十英镑改为“10小时劳动”,也不能改变金钱在市场中的交换本质。以后,我们还会进入马克思批判李嘉图的证伪构境之中,即将这个作为资本的货币购买的机器、厂房和原料当作物的进一步经济物相化中事物化颠倒,以及更深一层的劳动辩证法颠倒中的异化。这是一个需要批判认识论来解码的十分绕人的脑筋急转弯。我们慢慢来入境。
这里,马克思接着要说明的事情,必定还是物性到场的货币背后那个表现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与物品可感的上手物性功能(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使用价值关系)不同,商品的价值关系并非为由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物性的上手效用功能关系,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对自然改造关系的物性塑形和构序结果,它已经是商品本身社会历史负熵质的为我性社会定在,它是可以直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商品(产品)只有在不同商品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的“估价”中才会获得一种“值多少”的非物性的价值(交换价值)的经济定在关系赋型场境存在。马克思深透地指出:“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s Verhältniß),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ökonomische Qualität)。”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9页。这个ökonomische Qualität(经济上的质),正是商品的经济定在关系场境。其实,这一表述很长时间都被仅仅当作一个经济学的话语,而我觉得,这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场境关系存在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延伸,这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人的本质是其“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到《致安年柯夫的信》中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的场境关系存在论论断,在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落地。只是这种场境关系存在论已经隐没在经济物相化多重颠倒的新型存在论关系场境之中,由此,历史现象学的第二重解码才尤为重要。
显然,物品具有不可直观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生成的ökonomische Qualität(经济质),并非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普适性的社会生活现象,因为,它绝不会出现在原始部族生活场境之中,而只会在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的社会赋型中才出现的历史在场性。如果说,物品的“使用价值”已经是复杂社会空间中劳动物相化上手功效关系的物性赋型,那么价值的存在则会是商品在经济交换中才构序出来的特定场境关系存在,它并非物品被直接塑形和构序的客观物质属性,它也不能直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只是构成人们之间不同物品(需要)交换关系的产品通用标识,可是,它也绝不仅仅是一个主观的交换数量,而是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场境关系赋型。然而,商品价值的这种隐性场境关系赋型恰恰是不可直观的。在这一点上,这种不可直观的经济关系场境空间和历史在场性本身已经在超出一般场境关系存在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可知性边界。应该说,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商品ökonomische Qualität(经济质),不是指“面包可吃、书本可读”这样的直观用在性,或者说,不是物品在使用价值上由具体劳动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关系中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质,而是指“面包三磅”“书本十磅”这样的“值多少钱”(价格背后的非直观价值关系编码和构序),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被赋型的等质性,由此入序于经济构式负熵进程。这个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等质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叫“价值是杂多的齐一(Einheit),是不同感性事物的齐一,是诸多使用价值的齐一”。②阿多诺:《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谈话笔记》,转引自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页。这里,阿多诺显然是在故意异轨古希腊哲学中那个著名的感性现象的“杂多”与背后本质之“一”的观念构序。不同的是,价值的“一”是对诸多具体用在性的使用价值夷平为抽象的劳动价值量的“齐一”。这种量化的齐一,也正是资产阶级祛序高贵与下贱质性生存的平等关系的缘起。有如我与查尔斯王子用手中十英镑的货币在伦敦的超市中购买商品,售货员绝不会给查尔斯比我多出十英镑的东西,王子与平民的等级就是在这种不经意发生的交换关系场境中被夷平的。对此,阿多诺说,资产阶级的“平等最初是所有个人在货币面前的平等。货币使得物(Dinge)与人之间质的、人格性的差别消失了。由此,所有参与到市场中的个体都有兴趣看到,社会不是按照传统的原则,而是按照商品生产的需求组织起来的。——交换抽象包含着不是范畴的要素。交换的相互性隐含着个人之间的形式平等。平等的政治观念是政治相互性的理念。人们之间的相互性与交换中对象的相互性是相应的。对象的相互性,即相互之间的可替代性,是自然规律的基础形式,它必须将具体的使用价值自身从中清除出去”。①阿多诺:《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谈话笔记》,转引自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177-178页。货币(价值)的经济质是量化的齐一,物与人的实质差异在货币中转换为无差别的金钱数量,一切对象的相互性和人的可替代性是这种政治平等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解构专制等级的秘密武器。这也表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本身就是透视资产阶级政治概念的基础。阿多诺在索恩-雷特尔的影响下,他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解达到了极其深刻的构境层面。
最关键的问题是,价值代表了什么东西之间的等质?在马克思看来,这不是物与物用在性之间的直接等质性关系,因为这里所说的面包与书本之间、马克思所说的小麦与上衣之间并不存在某种直接的比较关系,这里的等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物相化转化为抽象一般劳动的等质性关系。实际上,这也是那个物品用在性的失形之处。用马克思此时的表述,就是“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vergegenständlichten Quanta von Arbeitszeit)所用的手段”。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8页。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1,Text,Berlin:Dietz Verlag,2006,S.74.马克思这里使用了一个接近新的“对象化劳动”的表述,即“对象化劳动时间量”。Vergegenständlichung,这又是一个无意间使用的重要哲学话语。这里出现了两个重要的构境层,一是劳动时间的概念。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将马克思的劳动时间概念看作承袭李嘉图的一般劳作时间(持续性的量)观念,而实际上,马克思这里的劳动时间是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那个历史时间的进一步具体化。不同于一般物理时间的持续性流逝,马克思发现了现代社会定在中由工业生产物相化构成的生成性历史时间,它是整个工业生产力构序的历史辩证法的本质。在马克思后来的关于科技物相化的研究中,这种劳动时间又进一步分化出非及物的科技信息编码的纯粹塑形和构序时间,这种新型的劳动时间,会成为马克思揭露相对剩余价值盘剥中的不可见隐性历史时间,以区别于绝对剩余价值压迫中被延长的劳作时间(量)。二是对象化劳动时间量的表述。这里,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话语能指中的意义所指的转换,即从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物品使用价值的对象化劳动(Ⅰ),向商品交换关系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对象化劳动(Ⅱ)的话语所指转换。这种新型的对象化劳动,已经是指劳动物相化中的历史时间(塑形和构序用在性)转换为经济物相化空间中的死去的抽象劳动的量化时间,它构成了此-彼错位关系中价值的无形肉身。之后,这个对象化劳动时间量会直接强化为对象化劳动Ⅱ的概念,并与异化概念一同成为历史现象学构境中重要的革命辩证法的构序力量。普舒同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提出,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化事实上就是异化———只要劳动对象化为社会关系”。③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6页。这是不够准确的。对象化(性)就是异化,是黑格尔哲学中绝对观念历史性地外化-对象性异化实现自身的判断,早在《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就刻意将对象化与异化区分开来,而到了《大纲》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劳动对象化概念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语格式塔:一是在生产过程中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对象以生成使用价值的劳动对象化Ⅰ,它当然不会是异化;二是指商品交换关系中抽象劳动颠倒地通过货币实现出来的反向对象化(对象劳动化Ⅱ),这是价值关系和货币权力关系的异化;三是资本关系反向对象化为到场劳动条件和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本家伪在场,这也是异化。这是一个比普舒同的理解复杂得多的批判话语构境。
显然,马克思这时已经在经济学构境中完全接受了斯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也深透地认识到了无序和返熵的商品-市场经济运动中的价值规律,即“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nothwendige Arbeitszeit)”。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3、90页。这里的nothwendige Arbeitszeit(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某一特殊生产领域的每一个别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一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商品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而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特殊生产者和卖者为这一个别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228页。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对其进行更精准的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gesellschaftlich nothwendige Arbeitszeit)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这个社会劳动必要时间,同样也是达里蒙等人的“劳动货币”无法对应的。马克思说,比如麻布与同等价值的一个面包交换,虽然它们(由具体劳动失形/塑形和祛序/构序的对象化所生成的)的使用价值不同,但所交换的 “对象化劳动时间量”(对象化抽象劳动)却是等质的。括号中是我增加的内容,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区分这些规定,在此作为过渡到后面资本是对象化劳动Ⅱ的需要补充的逻辑环节。下同。这样,恰是在劳动交换关系中,“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doppelte Existenz),除了它的自然存在(natürlichen)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rein ökonomische);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3、90页。这里的doppelte Existenz(二重存在),正是后来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所指认的价值形式辩证法的缘起,可是他们不能领悟的是,这种doppelte Existenz(二重存在)的矛盾关系,已经是经济事物的辩证法与劳动辩证法的复杂颠倒关系的表象。马克思这种看法,直接爆裂了一切传统认识论话语可能容纳的界限,一个物品在它可直观的到场“自然存在”之外,还有一种不能看到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的rein ökonomische(纯经济存在),即vergegenständlichten Quanta von Arbeitszeit (对象化劳动时间量)的不在场的在场性。这正是经济事物辩证法中生成的矛盾关系。其实,这已经是第二重不在场的在场性。这是对于一直到康德认识论革命以来的认知主体来说,必定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其实,康德的先天观念综合构架已经是对社会历史先验构架统摄作用的无意识观念映现,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这里所说的doppelte Existenz(二重存在)中商品所谓的“自然存在”是非自然的,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物相化透视中,它是从现成的对象成为verschwindend darstellt(正在消逝的东西),以彰显使用价值的“自然存在”本身已经是有目的的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结果。这是一般物相化此-彼归基关系中第一重不在场的在场性。它只在海德格尔for us“涌现”之意上才是成立的。其中已经内嵌着不同于自然物质实在的劳动(爱多斯)物相化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存在(使用价值),之后这种用在性编码存在反向物相化为新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的纯经济存在,正是劳动的辩证法运动颠倒为经济事物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运动的起点,这就构成了第二重不在场的在场性。价值问题的复杂性和难以理解的矛盾关系构境,就在这里。商品可见的“自然存在”,即锤子可以钉钉子、手机可以打电话这样的使用价值方面,是面对人的直接生活需要的可直悟的社会历史负熵质;而物品在交换关系中获得的脱离人的需要的“值多少”的“纯经济存在”——商品的价值(劳动交换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可直观的,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表现,价值的客观存在方式是更深一层的不在场的在场。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确定为著名的价值形式理论。我以为,这种特殊的双重不在场的在场性,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的复杂矛盾本质,也是马克思将重新吁请的科学的批判认识论的视域,或者说,商品不是直观中的它自身的经济质(价值-“交换关系”),是批判认识论透视层面中的非直观对象。在这一次的研究过程中,我自己不时地为马克思思想实验中的深邃构境所震惊,有时候真切地体会到,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创制中所实现的方法论突破和认识论革命,远在康德、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纯粹学术思辨之上,因为他直面了资产阶级经济王国中谜一般的复杂世界,其中,历史辩证法运动中主体性劳动的辩证法颠倒为人之外的经济事物的辩证法:商品属性的可见与不可见、货币的在场与不在场、资本的物性实存与被遮蔽起来的关系场境,当下发生的经济物相化活动与它在对象中的抽身而去、用在性使用价值自我失形向可变卖性价值的转换、人与人的关系事物化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货币关系与资本关系中发生的多重劳动异化,以及遮蔽经济物相化真相的主观经济拜物教,以真实在场的平等的交换关系巧妙掩盖起来的不在场的合法经济剥削等。然而,马克思这些在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视域中生成的无比精深的思想构境,却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手中变成了人人可弃的教条式白开水,真的令人汗颜和无语。
在商品的二重矛盾存在中,不同于劳动爱多斯直接塑形和构序物品使用价值的可感“自然存在”,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恰恰是一种不可直观的新型经济构式负熵进程中的经济定在。阿多诺曾经说过,“是什么水泥把商品世界粘贴在一起。回答是:消费品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化造成了一个普遍的秩序”。①阿多尔诺:《文化工业理论》,《阿多尔诺基础读本》,夏凡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3页。这是一种全新的存在论中用在性失形后由交换关系勾连人与万物的普遍关联的有序总体。这是对的。这正是价值关系(“交换价值”)最难参透的地方。其实,不久前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指认资本不是可见的物,而是一种非直观的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恰是从这里开始,这种新型的有序性社会定在是在工业生产塑形和构序的一般社会历史负熵进程之上历史发生的,经济物相化和经济拜物教真正的神秘化起源恰恰在这里。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历史负熵的特定经济物相化中的有序性,商品-市场经济王国中的一切人与物都由这种新生成的经济事物辩证法运动中经济负熵构序和链接起来。在一定的意义上,黑格尔所指认的人所创造却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Die zweite Natur(第二自然)正是由此发端的。因为,经济物相化构序中生成的经济负熵质的经济定在,商品、货币与资本这些遮蔽经济关系场境的经济假物构成的复杂经济活动,都是在人之外的自我运动过程,它通过表现出与盲目自然界相类似的现象和似自然性(quasinatürliche)运动规律,将自身构序为人所创造的Die zweite Natur(第二自然),其中经济事物自发整合(integration)运动的辩证法则是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资产阶级推崇的“自然法”)。这是尤其需要界划的。后面还会看到,这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多层次历史转换和颠倒的劳动辩证法运动中多重关系异化自乘的过程。在这里,马克思只是通过理论思想实验的方式来分析这一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及其意识形态伪境的逻辑发生。在后面的讨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说:“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0页。在这一点上,普舒同说,“在马克思的分析构架中,价值是一个批判性的范畴,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特有的财富和生产形式的历史特殊性”,②普舒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第29页。应该是正确的。价值是商品价格背后的根据,这是价值概念和价值规律的经济学缘起。在后来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Widerspruch)”。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76页。价值规律,即斯密《国富论》那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经过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的再神秘化,则成了历史进程背后的“理性的狡计”。黑格尔说:“在这些过程中,客观的东西彼此扬弃自己,主观的目的在此上这些过程的力量,其本身是在它们之外,同时也在它们之中保存自己,这正是理性的狡计。”④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而马克思则是从资产阶级经济构式负熵进程的商品无序生产-市场价格波动等复杂返熵经济现象,以及剩余价值与利润-地租-利息-税收等转换形式的矛盾中,捕捉到这一自发生成的内在经济事物的辩证法构序法则的。马克思认为,“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41页。
三、货币:价值关系客观抽象中的事物化与异化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虽然是客观的,但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的熟知物相中无法直观的纯经济的场境关系存在。对此,哈维说:“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实际上你无法直接看到、找到或感觉到社会关系,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⑥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1卷,刘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这是对的。然而他没有进一步发现,马克思所指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本质是Gestalt(场境存在)。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境中,马克思恩格斯指认过关系性存在是人区别于动物生存的特殊质性,可是从认识论的视角出发,任何“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才能使自身重新个体化”。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1页。这是因为关系作为一种场境存在,通常在关系方的互动活动结束后,这种人所独有的关系场境存在随即消失,如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协作关系,当工人放下手中的工具,停止劳动活动,这种社会结合关系场境随即解构和消境,在下一次生产过程中,再由工具编码模板重新激活劳动爱多斯的主体性技艺和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场境。通常关系场境存在只是通过观念抽象才能把握,同时人们也会将这种生产活动中有序关系场境客观抽象出来,并反向对象化浇铸在工具编码模板(外部持存记载)之中,以便重新激活特定的工序编码。这是第一种客观抽象(Ⅰ)。同理,商品的价值作为一种不同商品的劳动等质关系场境,突现于商品的交换活动之中,商品交换活动是经济物相化空间的基础平台。一旦交换活动停止,这种关系场境自然也就会解构和消境,所以价值也只能通过抽象呈现出来,可马克思发现,商品的价值关系并不是仅仅停留于简单的观念抽象(交换活动中的换算和计数)中(有如西斯蒙第的“观念影子”),也还通过现实发生的商品交换活动将商品中内含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客观地抽象出来。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产阶级的财富一般的“交换价值”的“历史抽象”。这正是不同于工艺抽象的第二种客观抽象(Ⅱ)。如果转换到历史认识论的视角,马克思这里发现的商品交换中历史发生的客观抽象,会成为经济的社会赋型中观念抽象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是由索恩-雷特尔首先关注的。他提出,“一种源自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 Sein)的意识形成是以一种作为社会存在之一部分的抽象过程(Abstraktionsprozeß)为条件的。只有这一事实才使得‘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这一表述所指的内容变得可以理解”。①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8页。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构境十分深刻的看法。阿多诺完全赞同索恩-雷特尔这一重要发现:“先验的一般性(transzendentale Allgemeinheit)不是我的纯粹自恋的自我拔高,不是我的自律的傲慢,而是在那种靠等价原则(Aquivalenzprinzip)而盛行不衰的统治中有它的现实性。哲学美化的并且只归因于认识主体的那种抽象过程(Abstraktionsvorgang)是在现实的交换社会(tatsächlichen Tauschgesellschaft)中发生的。”②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参见Theodor W.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Gesammelte Schriften,Band6,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3,S.180。齐泽克也说:“在思想达到纯粹的抽象以前,抽象就已经在市场的社会效率中开始运作了。”③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23页。这是对的,可是他们没有留意到历史逻各斯边界,其实原始部族生活中观念的抽象基础必定不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市场交换关系抽象。并且相比之生产劳动塑形和构序的一般社会历史先验构架来说,这种经济先验构架已经是第二层级的东西。
在此,马克思对这种不同于观念抽象的经济关系的客观抽象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第一,价值关系的客观抽象基础是使用价值的自我失形。马克思上面所说的麻布与面包作为商品在进入交换时,它们各自有特殊质性的用在性使用价值是无法直接建立比较关系的,交换的前提是“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这是物品使用价值的自我失形,即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起来的麻布能制衣、书可阅读的特殊用在性关系必须消失,不同商品中一般物相化结果的使用价值在自我失形中不得不转换为抽象的“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价值,才能发生比较关系中的量化编码且进行交换。这也意味着,一般物相化生成的商品使用价值是被排除在商品交换关系场境之外的,或者说,经济物相化空间的发端恰恰是缘起于物品用在性的自我失形。“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这亦表明,只能对麻布和面包之间交换关系中客观抽象出来的“纯经济存在”——价值量(对象化劳动时间量)进行比较。这样,商品具体的用在性,只有在失形和错位于抽象的交换价值关系,才能进入到经济物相化空间构序起来的全新存在论场境之中。商品不是自身独有的功用性,而是失形于用在性存在的“可变卖”关系,这就构成作为经济物相化活动中第一个此-彼错位的经济构式关系。这里经济物相化中脱型和构序中的“破”-“立”关系,很像马克思在“工艺学笔记”中发现的劳动生产物相化始于自然存在失形和关系脱型的“破”-“立”关系。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了。这也会是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一般物相化到经济物相化的过渡点。
第二,价值关系客观抽象反向对象化的货币。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这个客观的抽象过程可通过头脑的换算来完成,但是当一个面包与麻布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到与马克思常常提及的一双鞋子、20斤麦子、一件上衣等大量商品发生日益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时,人们在头脑中的简单换算就无法完成这些商品之间价值量的一般等质关系,于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中的一般关系,这个实际的中介就是商品交换中劳动等质关系的客观抽象。开始我们可以用一块物性到场的石头、一只贝壳充当这个消逝的客观抽象(一般价值等价关系结晶)的在场物性中介,如同生产劳动中最早出现的木矛和石斧一类工具编码模板,它也是劳作爱多斯技能和工序编码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在工具之中,在新的劳动生活发生时重新激活已有的手艺和工艺编码,而在商品交换中出现的这些也是经过一定的具体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特殊的石头和贝壳中,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并反向对象化在这些物性中介中,它们在新的交换活动中重新激活不同商品内嵌的劳动时间量的等质编码关系,然而,因为石头和贝壳等物的易碎易损,人们便逐步用更加耐用的金属铸币替代它们,中国的古代商人为了方便携带,会在一些铜片上打孔,这就有了成串的铜钱,人们将客观抽象出来的量化的劳动交换关系编码浇铸其中,于是,一种充当一般价值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也就历史性地粉墨登场了。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指认的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发生的此-彼错位关系的第二层面,也是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经济物相化关系场境存在论的第二层面。只是这里此-彼错位中的“此”不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用在性,也不是货币本身被劳动生产塑形起来的直接用在性之“此”,而是第一重此-彼错位后的抽象的交换价值演进后的一般价值等价物,而错位中的“彼”则成了这种客观抽象直接实体化为完全他性的经济事物(货币)。这样,新的此-彼错位转换中,不仅商品和货币的用在性在一般物相化中的原初劳动塑形和构序被更深地遮蔽起来,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也在转换为物的自我脱型过程中被遮蔽起来,这种经济物相化中从物品使用价值的双重失形和脱型(“破”),恰恰是之后经济物相化中金钱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多重脱型和事物化颠倒(经济构序之“立”)的前提。这是经济物相化存在论中经济事物的支配性自动机制和看起来非主体性统治法则的秘密基础。我以为,这也是黑格尔所指认的Die zweite Natur(“第二自然”)生成中最重要的构序环节。
需要留心关注的不同特点为:第一,货币与前述商品不可见的交换关系场境不同,它是经济物相化进程中可见的到场经济物相化事物,然而,它的到场却是商品中不可直观的交换价值关系场境的真实在场。第二,与将劳动爱多斯技能和工序客观抽象(Ⅰ)并再反向对象化的工具编码模板不同,工具模板是真实通过劳动塑形和构序完成的用在性“传导体”,工具的使用和重新激活劳动技艺并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可货币的出场就不一样了,它的反向对象化并不是将交换活动中的技能和有序性直接塑形为一种用在性,而仅仅是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的关系场境复活。这也意味着,货币本身的物性到场与它所生成的经济关系本质从开始就是不一致的,这是经济事物辩证法(“第二自然辩证法”)中更深一层的此-彼错位矛盾关系:货币不是它自身,作为verschwindend darstellt(正在消逝的东西),是抽象的劳动关系的颠倒物性呈现。这正是马克思用事物化来表征的人与人的关系场境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物相化伪性编码和构序现象。用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话来说,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作为货币使用,而不知道货币是什么。经济范畴反映在意识中是大大经过歪曲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8页。这个意识中“歪曲”,就是我所指认的经济物相化的伪性编码特征,其现实基础就是不断遮蔽劳动关系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不同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里一般物相化活动中爱多斯(eidos)之相实现出来的普通对象性实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经济物相化第二层面是指特定的经济关系——价值转化为物性的货币(之后是资本关系物相化为及其他物性实在),经济物相化的直接目的(telos)是获得的抽象的财富一般,如果这里也存在一种爱多斯,那么,也只是金钱爱多斯。这正是格雷、蒲鲁东、达里蒙等人无法抵达的思想构境层面。甚至历史认识论也无法直接透视这种特定的经济物相化编码伪像,马克思必须重新启用历史现象学基础上的批判认识论构式。马克思说:“一切商品都可以转化为货币,并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因为在它们所采取的货币形式中,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自然形式消失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51页。这就意指着,原先历史认识论作为认知对象的场境关系本身,在使用价值消失的价值关系中已经荡然无存,特别是当客观抽象生成的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再以物的方式出现在流通和生产领域时,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的巨大的认识论障碍就出现了。这是批判认识论出场的必然性。
马克思发现,在货币这个经济物相化事物身上所完成的客观抽象是多义的:一是所有商品内嵌的由劳动塑形和构序起来的特殊用在性场境存在的使用价值都被抽象掉;二是所有的劳动的特殊质性在商品交换中都抽象地转换为一般劳动时间量——价值等质关系;三是这种被客观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必须通过一个外部的一般等价物来表征,就是劳动交换关系场境重新反向对象性赋型的特殊经济物相化事物——货币。与工具编码模板完整在物性持存中保留从劳动生产中客观抽象(Ⅰ)出来的手艺和工艺不同,工具重新在场时会激活和重构原先的手艺和工艺编码,而货币所实现的价值关系的客观抽象(Ⅱ)实体化此-彼错位和重新到场中却同时包含着否定性失形与祛序、经济关系的脱型、转换和他性呈现等伪性编码和构序关系。这使得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愈来愈陷入不可能直观的神秘性中,如果这是一种辩证法,那么将是一种将世界变成经济魔域中各种倒置事物的辩证运动。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Equivalent);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natürlichen Eigenschaften)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Geld)。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9页。
一是货币作为麻布与面包等商品之间交换关系中客观抽象出来的一般等价物,麻布可制衣和面包能吃等商品的(由具体劳动对象化所塑形的)所有“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们被否定和彻底失形了;二是在货币中,不同商品的特殊质性转换为无差别的劳动时间量,它只是这种没有质性的量化尺度;三是这种看不见的(对象化的抽象)劳动交换关系并不能直接呈现自身,它不得不结晶和重新事物化为一个麻布和面包之外的可见的他性物相化中的dritten Ding(第三物)。然而,货币在一般社会物相化空间中的到场,恰恰隐匿了它在经济物相化编码空间中生成的价值关系自我脱型的此-彼错位本质。这种双重社会关系编码空间中的交错,直接转换为掩盖和遮蔽场境。这恰恰是商品经济物相化构序的神秘性缘起。这也意味着,原先作为批判认识论起点的非直观的神秘价值关系,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不是它自身的他物——货币,货币是批判认识论第一个直观认知中的遮蔽性障碍对象,这也开启了批判认识论特殊的认知机制,即不断地在经济物相化空间中出现的他性对象中找出消逝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原型。在此是流通领域中的金钱,之后是脱型于货币的生产过程的资本物,再有分配领域中的利润、地租、利息和税收等可见遮蔽性障碍对象,以及信用关系背后股票证券等更复杂的关系场境。科学的批判认识论将任重道远。
马克思说,此处到场的“这个第三物(dritten Ding)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一种劳动交换活动反复过程中客观抽象出来的Werthverhältnisses(价值关系)。其实,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意识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之谜的钥匙,正是从这里开始转动的。我们从上文可知,价值关系是一种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塑形和构序关系在交换中发生的客观抽象,“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抽象又必须对象化,象征化(vergegenständlicht, symbolisirt),通过一种符号来实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2-93页。这里,我们再一次想到劳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工具,作为劳作爱多斯技艺和工序编码的外部持存记忆,当下发生和消逝的劳作活动场境也是被反向对象化浇铸到锤子或镰刀之中的,那里的vergegenständlicht(对象化)相对于通常人对自然塑形和构序的劳动对象化正好是反向的,货币也一样,不过在这里被反向浇铸进入铜钱的并不是直接可能激活的生产过程中的劳作技能和工序场境,而是间接地象征流通领域中劳动交换活动的等质劳动场境关系,现在,抽象的劳动交换关系反过来事物化为物性对象,symbolisirt(象征化)则是抽象的符码代替实在。这是客观的价值抽象(Wertabstraktion)与象征性的事物化实体的必然关联,其现实结果就是作为商品之间第三者出现的等价物——货币。这里发生的经济物相化构序不是货币本身的使用价值(贝壳、铸币、金银条块和纸币等物的用在性),而是这一物性载体所象征的价值等价关系,这是经济物相化活动中发生的第一个事物化颠倒。相对于之后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关系转换为劳动条件和剩余价值转换形式中的事物化,也可以称之为事物化Ⅰ。可是,当今天我们手中拿着象征财富的一张十磅纸币时,如果它成为我们的认知对象,哪怕我们经过一般物相化的透视,将其还原为劳动塑形和构序前的纸张、油墨,甚至更原初的木料和树木,可上述这一切复杂经济关系编码中的转换都是不在场的。此时,到场的货币已经是在事物化颠倒中经济物相化伪性编码遮蔽的结果。因为这里出现的社会关系自我脱型且反向对象化为物性存在的他性物相化,就是经济物相化的第二层面的创制,也是历史现象学所要面对的经济关系场境存在论的第二层面。经济物相化中创制出来的货币,不是人们劳动爱多斯在货币本身生产中的实现,这种创制的本质是对所有商品中不在场的抽象劳动的替代和遮蔽。由此,人所创制的东西再一次表现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体般的Die zweite Natur(“第二自然”),之后这种经济物相化活动中颠倒地呈现的事物辩证法(似自然性的“第二自然辩证法”),将在资本的自我运动创造的神秘魔域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显而易见,如果想捕捉到货币中复杂的隐性关系存在,靠历史认识论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能够透视与解码事物化颠倒巫术的批判认识论。
我们看到,马克思这样论述商品和这个作为货币出场的等价物的关系:
商品必须和一个第三物(einem dritten Ding)相交换,而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Symbol der Waare als Waare),是商品的交换价值(Tauschwert)本身的象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一张纸或一张皮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priori gefaßten Idee)的实现(事实上,被用作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商品的一个象征又可能代替这种商品本身。这种商品现在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3-94页。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79.
这种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奇怪的颠倒性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场境是这样发生的:一是作为货币出场的ein Dritte(第三物)的本质并不是直接到场之物(金属和纸张),甚至不是一般物相化中的那个劳动塑形和构序的用在性关系(开采金属、生产纸张和印刷的爱多斯之相),况且,此种用在性也不是面对人的生活需要,而是面向金钱关系编码的“谋财”;二是它的到场物性实在仅仅象征着并不在场的抽象的“交换价值”(价值),或者是Symbol der Waare als Waare (商品的商品的象征)的此-彼错位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在商品-市场经济中派生出来的“社会象征”编码关系,虽然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它只是间接地表达所有商品中包含的抽象“劳动时间”;三是这种抽象“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而是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客观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到场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dritten Ding(第三物)。在此所发生经济物相化活动中的第一个事物化颠倒事件为:一个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本身已经是具有社会历史负熵质的物品,在交换活动中成为商品时,它入序于经济构式负熵进程获得全新的经济关系质,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除去“为人”的定在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又获得了“为财”的经济定在形式中的Tauschwert(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这样,这一特殊“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4页。抽象的价值关系(“交换价值”)获得与“商品相分离的存在”——一个不是它自身的经济事物的形态,这就是商品之外的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natürlichen Existenzform losgelöste sociale Existenzform)”。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4页。这里出现的natürlichen Existenzform losgelöste(脱离自然存在形式),也就是前面指认的失形。这也表示,货币作为物,是在不是它自身的Anderssein(他性存在)的经济物相化此-彼错位编码和构序关系中,成为沟通所有商品交换价值的sociale Existenzform(社会存在形式)的他性货币。在1847年完成的《布鲁塞尔笔记C》中,马克思曾经摘录过玛丽·奥吉尔《从古至今信用的历史》(Marie Augier:Du crédit public et de son histoire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Paris 1842)关于货币的“四重虚构(Fiktion)说”。一是并非它自身的“货币代表事物”(das Geld repräsentirt die Sachen),二是商业汇票(Wechsel)替代货币,三是银行票据(Bankbillette)替代硬币,四是纸币(Papiergeld)替代一切。①Karl Marx,Exzerpte aus Marie Augier.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Ⅵ/6,Text,Berlin: Dietz Verlag, 1983,S.939.中译文参见孔伟宇译稿。但奥吉尔并不能说明这种四重Fiktion(虚构)背后发生的复杂异化关系。后来索恩-雷特尔解释说,货币作为“一个物(Ding)不是被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它被交换,它才是物。它的物的构成(Dingkonstitution)是功能性的(funktional)”。②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第129-130页。这个功能性也就是经济物相化编码中生成的关系场境存在。进一步说,“在货币之上表现出来的,是其物质(Material),其版式以及印在上面的符号,也就是那些使其成为一个物(Ding)的东西,从而可以使人放在口袋里,支付和收取。但是使得一个物成为货币的,在价值以及‘价值抽象’的关联与境(Zusammenhang)之中,则是那些除了是它看起来、摸起来和清点起来如何的东西,而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按照其本质是纯粹形式的并且是最高程度上普遍性的即达到抽象阶段的”。③Alfred Sohn-Rethel,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72,S.20-21.中译文参见李乾坤译稿。应该说,索恩-雷特尔的这一分析是透彻而精准的。货币的本质不是它能够看到、摸到的到场实在性,而是它在交换Zusammenhang(关联与境)中赋型的经济关系场境,即齐泽克所说的他性的“崇高对象”,或者拉康意义上的作为所有商品反射性关系(大他者)在场的财富镜像。货币所象征的这种隐性关系场境恰恰是在它的物相化肉身之外的激发无限欲望的“崇高对象”,至于它是商品交换开始时的贝壳,还是金属或者纸张,甚至今天电子数字化的符号都是不重要的。它就是在他处“金刚不坏”的悄悄在场。当达里蒙等人将英镑改写成“劳动货币”时,并没有真正触碰到这一不在场的“崇高对象”之历史在场。
价值是交换中商品反射性镜像认同的关系性手段,抽象的价值关系在现实中必须事物化为一种实体性他者,所以,货币已成为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产品的二次方的他性手段。如果按拉康的镜像理论,这里的镜像关系反向认同的事物化本身已经是一种本质的遮蔽。与拉康所指认的伪自我-伪主体关系场境中的小他者(镜像)和大他者(语言象征系统)不同,货币是商品价值关系以实物的方式生成的他性认同镜像。所有商品都在货币之镜中照出自己的价值,可是,货币是一面他性魔镜,因为它最后从他性镜像关系直接占据了财富的空位,它就成了财富本身。虽然这一切并非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和完成的,但这却是以后劳动交换关系异化为奴役性权力关系——资本统治关系的客观前提。因为“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的形式,成为资本的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95页。这是马克思后面要逐步说明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开始,在批判方法论的历史现象学构境层面,他在《大纲》中再一次启用了原先业已放弃的我-它自反性关系中的异化概念。显然,这是马克思试图克服已经出现在历史认识论中的经济物相化编码系统遮蔽性障碍的努力。马克思说,上述所讨论的货币问题的实质,就是商品交换中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出现的“一般等价物”,“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entfremdet)和商品相对立”。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88页。Karl Marx,Grundrissen,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2)Ⅱ/1,Text,Berlin: Dietz Verlag, 2006,S.74.你没有看错,这正是那个久违的entfremdet!可是,这里我-它自反性关系中主体格位中的“我”只是价值关系(Werthverhältnisses=抽象劳动),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物相化关系脱型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这是《大纲》中出现的第一个异化(异化概念Ⅰ),这是呈现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客观的价值关系异化。这种关系场境异化是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的第二层面,也是历史现象学所面对的经济关系场境存在论的第二层面,在此,这种场境关系异化也是此-彼错位关系中的事物化Ⅰ的本质。在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一次在经济事物的辩证法(“第二自然辩证法”)背后,指认出颠倒的主体性劳动辩证法。应该特别指出,这个异化概念当然已经不是人本主义sollen(应该)的价值悬设与Sein(是)的主观的逻辑自反性,劳动交换关系的客观抽象不是本真性的sollen(应该),货币作为异化的价值关系也不是败坏的Sein(是),它们之间的此-彼错位关系场境转换就是经济物相化中的客观关系场境异化。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在1845年哲学革命之后,第一次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重新使用科学的异化概念。这一异化概念也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继客观抽象Ⅱ和事物化之后第三个重要范畴。以后我们还将看到,马克思还会在“价值异化”的基础上指认出“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异化”和“劳动异化”,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中,他还再一次提出了科学的劳动异化Ⅲ的系统理论。费彻尔在谈及《大纲》中的异化与物化问题时,特意提及与《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构式的关系,他的判断为“在思想进路和论证方式的结构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②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古尔德也认为,“《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早期的作为政治经济学异化理论的完成”。③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这当然都是不准确的断言。因为这抹杀了人本学sollen(应该)与Sein(是)悖反中的劳动异化构式Ⅰ-Ⅱ与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科学的异化概念的根本性差异。当然,他们也都没有注意到劳动异化构式Ⅲ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华丽登场。这是因为马克思突然发现,仅仅用实证科学维度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的方法,是无法透视经济的社会赋型特别是资产阶级经济中所发生的经济物相化编码和构序过程中复杂悖反关系和颠倒的。这是他重新启用异化概念的真正原因,从思想理论逻辑构式的整体看,马克思由此确立了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的最深构境层,同时重新采用了基于异化构式之上的科学的批判认识论。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再一次回到了1844年马克思关于《精神现象学》的思想实验,在那里,异化劳动构式成为批判认识论的内里逻辑。不过在这里,隐性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已经荡然无存。同时,异化概念在《大纲》中的出现,一开始并不一定是刻意的,只是马克思无法表达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这种客观矛盾的我-它自反性颠倒时无意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