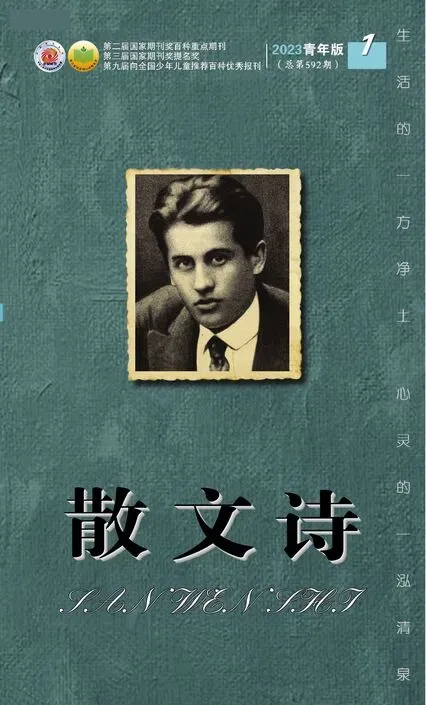达尔维什诗选
[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薛庆国 译
我们也爱生命
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
在两位烈士之间,我们起舞
搭起一座紫罗兰的宣礼塔,或是一棵枣椰树
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
我们从蚕茧上拈来一线丝缕
用它建造我们的一片天空
为这漂泊编织围栏
我们打开花园的门扇,让茉莉花绽放街头
带去一个美丽的白昼
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
我们在生息之地种下速生的植物
我们在生息之地收获死者
我们在长笛里吹入遥远遥远的色彩
在过道的泥土上描画马的嘶鸣
用一颗颗石子,我们写下自己的姓名
啊,闪电,请照亮我们的夜晚,照得更加明亮!
只要有一条活路,我们也爱生命
(译自《更少的玫瑰》,1986)
希望我们被羡慕
那个疾步而行的女人,头顶羊毛毯和水罐,
右手牵一名男童,左手拽着他姐姐,
身后跟着一群受了惊吓的山羊……
那妇人正从狭窄的战场,
逃往一个并不存在的避难地。
六十年前我就认识她。
她是我的母亲,
那时把我落在一个岔路口,
还有一篮干饼、一支蜡烛,
一盒被露水沾湿的火柴。
此刻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位
处于同样场景的女人……
四十年前我就认识她。
她是我的姐姐,
继续着她母亲——我母亲——在漂泊中前行的脚步:
从狭窄的战场,向一个
并不存在的避难地逃亡。
那位我明天将在相同场景中看到的女子,
我也认识她。
她是我的女儿,被我置于诗歌的中央。
我让她学习走路和飞翔,飞越过那样的场景,
但愿她能引发观众的赞赏和枪手的失望。
因为一个精明的朋友对我说:
该是转变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有可能,
我们就该从一个被同情的话题……
转变为一个被人羡慕的存在!
(译自《蝶之痕》,2008)
词 语
词语啊词语……一片片树叶掉落。
一片片桦木树叶,苍白而孤单地
在街旁掉落。那街道
自战争结束便已废弃。友善的乡下人,
或独自一人、或成群结伴地
在都市的人行道入睡。
街上走来一位诗人,
他心头有个天堂之孔,
眼中有一片往昔的草原,
他走在自己的废墟上,
像树叶一样轻飘而行,
也像树叶一样变黄了、红了。
他胡言乱语,像是受到了天启:
旅行中的燕子啊!
在我姐妹之前你已是我的姐妹,
我尚未走远,
我有两翼短翅,有一对飘在风中的时间。
诗人还说:秋日的旅程
已经开始,大地是干渴的。
他祈祷:祖国啊,在我母亲之前你已是我的母亲,
在我父亲之前你已是我的父亲。
然后他安慰自己:
掉落的叶子,小树的叶子,
绝不像尘土般无益,
这是旅程,是回归和意义。
用不着诗人,
去写一首用词轻盈的秋日诗篇,
这片枯萎的树叶,岂不就是词语?
(译自《我不想结束这首诗》,2009)
为了形容杏花
为了形容杏花,花卉百科全书
帮不上忙,字典也帮不上忙
话语会劫持我进入修辞的罗网
而修辞只会伤害意义,赞美创伤
犹如男性想要把持女性的情感
我只是那回声
杏花怎么会在我的语言里闪亮?
它是透明的,犹如一次水汪汪的微笑
从枝头含羞的露珠萌发
它是轻盈的,犹如一个白色的音阶
它是柔弱的,犹如瞬间之念
闪过指尖
可我们就是无法记述
它是浓缩的,犹如一行诗句
却不是用字母记录
为了形容杏花,我该一次次拜访
无意识,由它把我引向挂在树上的
有情感的名词。它叫什么?
这个隐含了空灵诗意的事物叫什么?
我该去穿越引力和话语
以便感受词语的轻灵,当词语变成
低吟的幻影,由我塑造,也把我塑造
透明的,白色的词语
它不是祖国不是流亡地
它是洁白对描述杏花的酷爱
它不是白雪不是棉花,没有那么
清高,没有凌驾在各种事物和名称之上
如果一位作者,成功地写出
一段形容杏花的文字,雾霭就会消散
山峦便会显现,整个民族都会说:
就是它
这就是我们国歌的歌词!
(译自《宛若杏花或更远》,2005)
诗的安排
星辰的意义,
无非在于
它教会我阅读:
我的一种语言在天上,
在人间也有我的语言。
我是谁?我是谁?
我不想在此作答。
也许一颗星将陨落在它的倒影上,
也许栗子树林将托举我,
在夜晚,向着银河扶摇而上,
并对我说:在这儿,留下!
诗篇在上,它可以
教授我它的所愿所想,
例如在神话之间
如何打开门窗,
整理家务。
它还可以迎娶我,过一段时光。
父亲在下,拿着一株
千年橄榄,
既不属东方,
也不属西方。
或许父亲躲过了征服者的侵扰,
他稍稍安抚我,
为我采来一支郁金香。
诗歌正离我远去,
进入一座海港。
那里的水手爱恋美酒,
同一个女人绝不找两回。
没有什么,令他们怀旧感伤!
我还未曾因爱而死。
可当一名母亲看见儿子凝视康乃馨的目光,
她会担心花瓶受伤;
于是她黯然泪下,在一场变故发生前
阻之于未然,
然后她又落泪,把我从布满圈套的路上
活着拽回,所以我还活在此间。
诗歌介于中间的中间。它可以
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
可以用一只苹果照亮两具身躯,
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
令祖国回归!
诗歌就在我手心。它可以
用手工
打理神话的事务。
但自从发现了诗歌,我就放逐了自己,
向它问个不停:
我是谁?
我是谁?
(译自《为何你将马儿独自抛下》,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