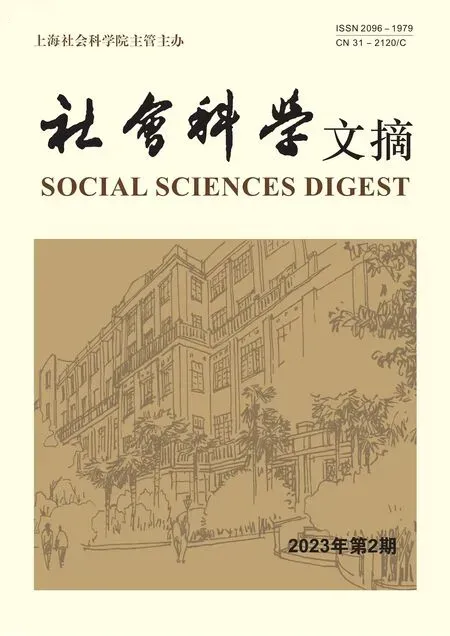未完成的“新文化”:重释鲁迅小说《高老夫子》
文/张丽华
鲁迅写于1925年5月的小说《高老夫子》通常被简单地视为一篇《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其主旨则被理解为对假道学或伪新党的批判。关于它的小说技巧,历来的评价颇不稳定,有认为它对人物心理的表现超过了阿Q时代,也有认为它是艺术上不完整的失败之作。这意味着其诗学机制并未得到透彻解析。与《孔乙己》《阿Q正传》等乡村题材的小说作品相比,《高老夫子》和《端午节》《肥皂》等以都市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是鲁迅面对其当下生活和文化情境的产物,需要在充分语境化的前提下进行阐释。
与《端午节》《肥皂》相比,《高老夫子》在塑造主人公的方式上发生了微妙变化,小说的叙事诗学则呈现出中西杂糅的样态。本文试从解析《高老夫子》的形式诗学出发,通过引入与它具有互文关系的世界文学资源以及1925年前后鲁迅所面对的“当日之时事”,对其主旨和理念进行重新解读。笔者试图阐明,《高老夫子》在写实小说的面纱下,蕴含着对现代中国文化情境的寓言式书写:小说塑造的在“高干亭”和“高尔础”之间游移而分裂的主人公,可读作鲁迅对晚清以降的“新文化”及其未完成性的文学寓言。
从“照镜子”谈起
《高老夫子》开头,有一个主人公照镜子的细节。即将走上讲台的高老夫子,在镜中仔细察看左边眉棱上“尖劈形的瘢痕”。这个照镜的动作,看似和小说情节关系不大,但主人公照镜而引起的不安,却构成了笼罩全篇的基调。这面镜子也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道具。
姜彩燕指出,高老夫子出场时照镜子的场景与芥川龙之介小说《鼻子》有神似之处。鲁迅1921年翻译了这篇小说。《鼻子》开场不久,也有主人公对着镜子察看自己的“长鼻子”,并希望在意念中将其变短的情景。鲁迅在创作《高老夫子》时,应该想到了这篇作品。
芥川的《鼻子》在情节构造上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鼻子》颇有渊源。在这两篇小说中,“鼻子”都是主人公另一个自我的象征。不过,与果戈理小说不同的是,芥川小说还着重描写了主人公因“长鼻子”而感到他人目光无处不在。这种对外界神经质般的察言观色,也是《高老夫子》主人公的重要特点。这显然又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有着亲缘关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中,也有一段主人公照镜子的著名场景,杰符什金因抄错公文被叫到上司办公室,他在镜中瞥见了自己的模样,并引起一连串的悲喜剧。别林斯基曾引述小说这段情节并大加赞赏。巴赫金认为,别林斯基并没有真正领会这段描写在艺术形式上的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杰符什金从镜中看到自我形象并出现痛苦惊慌的反应,是他在主人公的塑造方式上,对其文学前辈果戈理的“革命”。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受到果戈理影响的创作初期,描绘的就不是“贫困的官吏”,而是贫困官吏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主人公的艺术上的主导因素。《穷人》的主人公杰符什金,即时刻在揣测别人怎么看他以及别人可能怎么看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杰符什金从镜中照见自己的形象,既有现实功能,也是主人公在他人目光和话语中感知自我的隐喻。
芥川是被公认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日本作家,而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不浅的渊源。据韦丛芜回忆,他1924年从英译本译出《穷人》并经韦素园对照俄文修改。1925年3月26日前后,他的同乡张目寒将译文送给鲁迅审阅。1926年,《穷人》在未名社出版,鲁迅写了《小引》。鲁迅收到《穷人》译稿的时间,就在写作《高老夫子》前不久。这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从鲁迅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角度,来审视《高老夫子》的小说形式及其新变。
《高老夫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
从鲁迅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角度来阅读《高老夫子》,不难发现,这篇小说的核心情节,其实主要是发生在主人公自我意识中的事件,与外在的现实并不相干。小说在主人公登台讲学前插叙的黄三来访的情节,颇有《儒林外史》风味,但涉及女校讲学这一主干情节时,高老夫子则变成一位十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小说用了两个“忽然”来描写高老夫子从教员预备室走到讲堂的动作,又用了两个“忽而”来标识讲课的开始与结束,形象地写出了沉浸在自我意识中的高老夫子,对外在物理时空感到的错愕与茫然。这段叙述遵循的并非外在的物理时间,而是主人公的心理时间。高老夫子如同梦游症患者,无法真实地感知周遭的世界;而时缓时疾的叙事节奏,也与主人公惶惑不安的内心,形成绝妙的共振。
巴赫金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时而过分拉长、时而过度压缩的叙事方式,归纳为一种“非欧几里得”式的“时空体”(chronotope),即小说的叙事并不遵循严格的叙述历史的时间,而是超越这一时间,将情节集中到危机、转折、灾祸的时刻;而空间也通常超越过去,集中在发生危机或转折的边缘(如入口、走廊等)和发生灾祸或闹剧的广场(通常用客厅、大厅来代替)这两点之上。这种“时空体”超越了经验的真实性和表面的理性逻辑,背后是一种狂欢化了的时间观和世界感受。《高老夫子》对主人公在女校讲学的叙述,其时空体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有着奇妙的契合。
已有的关于《高老夫子》的讨论,都将高老夫子视为一个作为客体的主人公形象,“高尔础”和“高干亭”之间的行为差异,被理解为虚伪、造作和言行不一。这是在单方面地用《儒林外史》的诗学,来理解这篇作品。置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视野中来观察,《高老夫子》想要集中呈现的,并非一个稳固的作为客体的主人公形象,而恰恰是主人公在自我认知上的暧昧性和不稳定性。这篇小说以主人公的讲学和回家为界分为两节。第一节写的是他如何以“高尔础”的身份粉墨登场,第二节写的是他向“高干亭”的回归。对于这一登场与回归,小说均有详细描写。其中出现了两次高老夫子戴“帽子”的动作:“(他)很小心地戴上新帽子”(登场),“他当即省悟,戴上红结子的秋帽”(回归)。这一关于“帽子”的描写,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借用巴赫金的术语,主人公在“高干亭”与“高尔础”之间的游移和切换,岂非一场生动的“加冕”和“脱冕”的狂欢式闹剧?
当高老夫子戴上“秋帽”向黄三家走去后,小说中摇晃不定的叙事安稳下来,空间也转向了室内。《高老夫子》在《语丝》初刊时,两节之间印有明显的分节符,这一分节符不仅区分了情节发展的两个阶段,也切分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时空体:当主人公以“高尔础”的身份登场,如同梦游者一般行进在由过道与讲堂构成的充满危机的空间中时,叙事时空体接近陀氏小说的狂欢式;而当他以“高干亭”的身份汇入牌友的群体后,时空体则回到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传统小说的模式。
鲁迅交织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与《儒林外史》笔法,在《高老夫子》中极为艺术地完成了对主人公的两个“自我”或者说二重人格的形象塑造。在这个意义上,《高老夫子》的情节轮廓与主旨理念,与果戈理和芥川龙之介的同题小说《鼻子》(也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二重人格》),形成了颇有意味的同构关系。那么,鲁迅精心塑造出这一在两个“自我”之间游移而不安的主人公,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我们还需将目光转向小说之外。
女学生与新文化--作为“今典”的《一封怪信》
《高老夫子》的情节高潮是高老夫子与女学生的“看”与“被看”。最终,在不可见的女学生的“凝视”下,他被迫收回眼光,落荒而逃。这一从未真正出场的“女学生”,是小说的一个关键词。
写作《高老夫子》前后,鲁迅每月都会收到商务印书馆寄送的《妇女杂志》。《妇女杂志》第10卷第10号是“男女理解”专号,起源于不久前一桩闹得沸沸扬扬的“韩杨事件”。1924年5月7日,《晨报副刊》发表了北京大学女学生韩权华送登的《一封怪信》。此信是北大历史系教员杨栋林写给韩权华的一封疑似求爱的两千多字的“情书”。韩权华感到被冒犯,将这一“情书”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
《一封怪信》刊出后,立即引起巨大的舆论反响。大学生贴榜发文,对杨栋林的行为大肆讨伐。杨栋林迫于压力,两天后即向北大辞职。《妇女杂志》的“男女理解”专号,正是以此事为契机,向杂志的女性和男性读者征文,以期增进两性的相互理解。在上述报刊舆论中,“新文化”成为一个随时被征用且意义多元暧昧的新名词。费觉天搴出新文化的旗帜,为杨(栋林)的行为寻找根据。而周作人的文章针对的是大学生过激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群众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鲁迅并没有就韩杨事件直接发表意见,但《高老夫子》对《一封怪信》及其引发的报刊舆论,实有着不同程度的反馈与折射。高老夫子作为一个对外界高度敏感的主人公,与杨栋林颇有神似之处;而小说的情节高潮——主人公在女校讲堂上对女学生的看与被看,也不啻是对杨栋林在《一封怪信》中所呈现的心理的传神写照和精神分析。
将《一封怪信》作为《高老夫子》的“今典”来阅读,可对这篇小说产生全新的理解。韩杨事件本身并不特殊,晚清兴女学以来,类似的事件便时有发生。1924年前后,距清末女学堂的开设已近20年,“男女共校”也已在制度上确立。然而,传统的两性观念并没有得到改观,女性仍然在用将私人信函公开发表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声誉。这不禁令我们怀疑,刚刚过去的新文化运动,是否真正形塑了健全且能与新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新伦理和新道德。
高老夫子通常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复古派的代表。然而,置于《一封怪信》及其引发的舆论语境中,这一形象与其说是对新文化的反对者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反思:这位在“高干亭”和“高尔础”之间摇摆不定、造作不安的主人公,正是对当时被作为一个新名词而随意挪用,但却意义暧昧、难以自处的“新文化”的隐喻。
新文化的“拟态”
1925年11月,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对新文化运动的“名目”提出了质疑。鲁迅此论,不仅是为新文化运动辨“名”,更源于他对新文化运动之“实”的观感。新文化运动引入的新观念、新话语乃至新制度,与它们在中国的现实实践之间的分离、分裂或者说变形,正是鲁迅在包括《高老夫子》在内的《彷徨》中的诸多小说所探讨的核心议题。
在《〈热风〉题记》中,鲁迅两次用到了“拟态”一词。“拟态”(mimicry)是一个生物学术语。在拉康看来,生物的拟态并非单纯为了适应环境,而是依据他者的存在形构自身的存在。在《高老夫子》中,主人公正是以想象的女学生、新学堂为潜在他者,多方面地展开了对自我的改造和形构。这是一种典型的“拟态”行为。我们可以将《高老夫子》与《〈热风〉题记》进行互文阅读:如同高老夫子对“高尔础”的角色扮演,当时冠以“新文化”名目的诸多革新运动,在鲁迅看来,亦不过是一种对想象的(西方)新思想、新文明或新制度的“拟态”。
高老夫子之外,鲁迅还花了不少笔墨写了黄三和万瑶圃这两个人物。黄三正是主人公那“欠缺了”的“半个魂灵”;而万瑶圃也不过是他化装为“高尔础”后的另一个“复影”。黄三和万瑶圃的形象,代表了高老夫子潜意识中受到压抑的愿望,他们之间的相似,除了拱手屈膝礼,还有对待女性的态度:无论是前者将女学生视为“货色”,还是后者将女诗人捧为“仙子”,背后均是以女子为“物”的陈腐观念。在小说中,尽管高老夫子拒绝与黄三、万瑶圃混为一谈,但最终仍是他的这些潜意识的“魂灵”“复影”占了上风。
高老夫子在“拟态”与“本相”之间的反差,构成了《高老夫子》重要的反讽结构。如果将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视为新文化的隐喻,那么鲁迅通过具象化地呈现他在拟态与本相、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错位和反差,深刻地揭示了新文化的分裂和它的未完成性。
拉康在“镜像阶段”理论中指出,主体对自己“镜中之像”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认”,它需要穿越想象与真实、他者与自我、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多重界限。鲁迅在《高老夫子》中所描绘的主人公的“拟态”行为及其失败,以十分形象的方式,揭示了镜像认同的误认机制。高老夫子/“新文化”以拟想的西方新思想、新文明、新制度为“镜”,将自己用新皮包、新帽子和新名字装扮一新,然而,这一乔装的自我,如同将一个他者引入自我的形式结构之中,始终与现实的物理时空无法协调:“尔础高老夫子”行进在一个“非欧几里得式”的时空之中,不具备行动的主体性,也无法与任何人产生实际的交流。这是一个空洞的、惶惑的、未能完成的主体。
这一缺乏主体性的、未完成的文化状态,既是晚清以降中国诸多现代性变革的内在隐忧,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依然要面对的严肃课题?小说题为“高老夫子”,“夫子”是旧时对老师的尊称,这也提醒我们,儒家关于师道的礼教已经崩坏,但与新的社会文化情境相适应的师生伦理尚未建立,高老夫子正处在一个真空地带,无地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