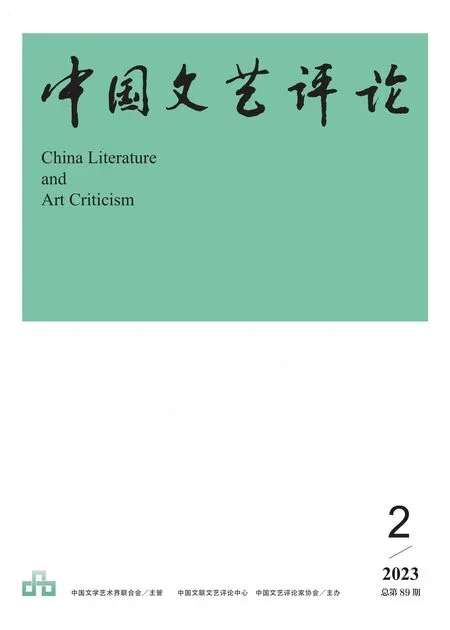通向他界的同盟姿态
——强化艺术与美学的互动机制
■ 黄宗贤
当前,艺术与美学的关系已经由过去的含情脉脉、里应外合,转向了高调的相拥。艺术常常直观地呈现自然与现实中的瞬间面相,感性地表达难以言说的沉思或情韵,以动人的可见之物去彰显那些不可见的实体世界;而理论形态的美学常常以沉思的方式,执着于对人、社会、自然本质的叩问与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因此,我们说艺术是“物化”的美学,而理论形态的美学可以为“物化”的美学注入深刻的内涵。那么,艺术与美学有过什么样的过去?艺术与美学的关系又以何种方式在当下建立同盟?在新时代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美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回答。
一、冥构他界之维
一般认为,美学研究与艺术创造有着不同的学理形态与表征方式。前者致力于探析人、社会、自然中各种审美活动的共同规律,并以逻辑推理、理性认知的方式将其凝结、归纳为普遍或特殊的思想、概念;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一件件活生生的事物,而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黑格尔在《美学》中也曾谈及艺术观照与智性演绎的不同之处,其“在于艺术对于对象的个体存在感兴趣,不把它转化为普遍的思想和概念”[1][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8页。。的确,在通常意义上,我们更倾向于将艺术与美学视为两种不同的形态:感性化的实践与理性化的理论。但紧接着,黑格尔又补充道:“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状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它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人的心灵深处唤起反映和回响。”[2]同上,第49页。可见,艺术的终极价值旨归既非停留于描摹对象的具体感知,也非止步于用理智认知的方式概括出一种抽象的学理。毋宁说,超越自然、超越现实功利、超越自我,去触摸难以言说的心灵世界,去构建自我的精神家园,追逐“诗意栖居”的境界,这是艺术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所在。当然,作为研究审美经验的艺术美学,除了将艺术视为日常生活中救赎人生、慰藉心灵的调味剂以外,其自身也终究是为了从形而上的层面复归精神的原乡,为了到达理想的彼岸,为了构建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艺术活动与美学研究可以说既有区别又有交集,交集于共同的、作用于人的审美诉求、价值取向——理想的精神世界。
那么应该如何去认识这种价值诉求呢?百年前,梁启超给我们作出了回答。出于“新民”的目的,梁启超主张从艺术入手,去改造国民人格和精神,并将其作为人脱离现实苦难而完善精神生活的最佳路径,所谓“超越现实界,闯入理想界”[3]梁启超:《美术与生活》,素颐编:《民国美术思潮论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66页。如是说。在《美术与生活》一文里,梁启超在关于艺术的审美功能与价值的阐述中,提出了三重境界:第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第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第三,他界之冥构与蓦进。[4]同上。显然,这一描述将“他界”定位为人类艺术活动的最高价值追求。在这里,艺术与美学均来源于却又不同于现实生活,但是两者在对现实的观照与回应中,又指向“他界”——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的建构。笔者认为,“他界”可以是文学家的桃源,可以是哲学家的乌托邦,可以是宗教家的天堂净土,当然也可以是艺术与美学的心灵之境和理想之境。“他界”是异于此岸的彼岸,人因心存“他界”而可宁静致远,不至于让生命在此界功利的角逐中成为被欲望支配的肉身。而艺术的“超越”力量恰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支配”而迈向“通往他界之路”。因为人始终有想象的心灵的“他界”的存在,认为此岸永远是不会完美的,这就注定了艺术在人的世界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无疑是超越此界通往他界的永恒的方舟,正如王国维所笃定的,艺术之用区别于功利的“生活之欲”而具有诸多精神益处。这便是王国维“无用之用”学说的根本意旨:认为艺术是“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周锡山编校:《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8-9页。。
然而超越又何尝不是哲学美学最重要的一种价值指向呢?人天然地有一种执着的、不懈的对形而上的追求,正如柏拉图所说,人有“心灵的生殖力”。哲学美学是形而上之学,她们以沉思的方式,超越“物理学之后”,超自然、超感觉,执着于对人、社会、自然本质的叩问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可以说哲学美学的价值与生命同样在于超越。因而,从超越性、形而上的追求而言,艺术与哲学的价值取向与追求是一致的。
需要补充的是,迈向他界、实现超越,并非意味着走向虚无。无论是哲学美学的叩问,还是艺术的追寻,其实质都是在对功利和有限形质的超越中,使人被异化的生命向自己真正的社会存在复归——复归生命的原乡、精神的原乡。没有超越的美学,没有形而上学的深度,就没有精神的高度,就找不到回归原乡之路;没有超越的艺术,没有无用之用的寄托,就难以抵达彼岸,也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二、相交辉映之旅
艺术实践与美学研究都指向超越,那么两者可以互相取代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在生产机制上,美学以纯粹的沉思方式去探索精神性的原则或规律,而艺术则是这一沉思的物化行为;另一方面,在研究范式上,美学可以不关涉艺术,可以在对自然与社会的观照中,沉迷于理性的思辨、逻辑的演绎,对一切经验和意识都存有余地,而艺术无论是表现与再现,她必须是感性的、现象形态上的存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从鲍姆嘉登最初关于美学的定义来看,美学的使命就是关乎与艺术密切相关的感性认知的研究,因而艺术与美学的诞生虽非联姻形式,但两者就如并蒂莲,同根各异。譬如学界对于艺术的观照与探究向来都是多维度多向度的,其关于艺术历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学科领域设置就是例证。但又不得不承认,相较于艺术创作实践,艺术的哲学之思更是早就开启了航程。许多哲人以哲学之思观照打量着艺术,追问着艺术的本质、艺术之于人的生活与生命功用、艺术之于人的意识建构、艺术之于人的精神演绎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英国学者司特斯(Stace)看来,艺术美是概念的具体化,无论是“先经验的”还是“后经验的”、知觉的或是非知觉的,只要被冠以“艺术”或“美”之名,其中都浸润着一种理想;在朱光潜对艺术美的阐述中,认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2]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148页。。显然,艺术、美学与现象世界的关系向来是暧昧的,她们始终契合融化于理想、趣味与情感之间,以至于传统美学遭遇危机之时,艺术哲学的挺进,为其保湿了颜容。
事实上,在西方学术史上,艺术实践与美学研究从来都是在彼此顾盼与观照中谋求发展、互动共进的。古希腊的艺术与美学不仅是含情脉脉的,而且本身就是交相辉映的。柏拉图的《大希波阿斯篇》就专门从艺术活动层面讨论了美的性质问题,而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同样致力于阐明美学是一门关于艺术的学科。文艺复兴后,普鲁士艺术史学家约翰•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也在其《古代艺术史》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艺术的本质在任何方面看都是最崇高的目标”[1]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art, Bristol: Thoemes Press,2001, p.107.,并表示该作并非是一部关于艺术家的历史,而是着眼于风格美学分析,意在集中研究艺术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无可厚非,美学研究活动中的种种功能与价值诉求——理性的话语建构、探索对象知识的确定性推论、提出超越感性的理性推论、提供认识对象的知识框架与理论形态建构——无疑对于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与引领作用。进一步看,若要再将时间追溯到现代,似乎思辨的哲学美学就已经让渡于艺术美学,此时的艺术家、哲学家及史论工作者大多已不再执着于“超越艺术自身的关于美的本质追问”与“业已固化的对象范畴探讨”,而是将艺术、美学密切联系于人类社会文化演进或是生存环境变化等具体的艺术问题之中。法国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在其《艺术哲学》中就提出影响艺术与美学发展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他认为艺术与美学就是在这三要素中进化而来的。种族因素是内部根源,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的推动力量,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影响和制约着艺术、美学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及其走向。另如活跃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其社员更是将艺术与美学的相关问题聚焦于以资本主义现代文化为主的社会政治理论研究中,由此建构起了对科学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体系。
不得不说,现代艺术家、艺术哲学家及史论工作者对那些具体艺术问题的聚焦,不仅让美学与艺术的共生关系昭然若揭,也让其建立了神圣的同盟。
诚然,审美观念、思想的书写可以是感性的形态,也可能是理性的理论形态。但对于艺术与美学两种学科形态来说,并非是先后关系,更不是主从关系。恰如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论是从艺术的生产活动还是从艺术的鉴赏角度来看,其艺术美同时指向了现实环境与心灵情趣所共同营造的一种心物相契的瞬间意象,因而艺术与美学对现实的审美观照从来都是齐头并进、互为印鉴的。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中,艺术之光总是折射于美学幽深的森林里,而美学总是将自身披上感性的外衣。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论”“物化论”“物我同一论”……不正是理论之思与感性之维合二为一而生发的一种境界吗?尽管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思想的特点是感悟式的,其以注重实践主体的心灵观照与情感体验,形成了中国艺术追求肆意彰显的表达方式。但鉴于传统文化中“执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观念,它又绝不滑向狂态与无节制的深渊,而是在追求情感抒发、意趣表达的同时,力求达到文质彬彬、以理节情、情理交融的审美境界。譬如“意境论”中就强调了这一形态特征,它要求艺术在情与理、我与物、心与景之间获取一种适度的平衡,所谓“文以载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即是说。可以说,在中国的文人艺术世界中,理论之思与感性之象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
当然,美学,特别是具有哲学思辨意味的美学,可以沉迷于玄想,而艺术必须将玄想与操作融为一体。如此,艺术也更能满足人理性与感性的双重需要,也使人更能确证自己。因而我们说,美学家不一定只关涉艺术,好的艺术家也必须有形而上的思维与能力。事实上,中外艺术史上的伟大艺术家,无不是行动的诗人或行动的哲人。
三、貌合神离之相
艺术的观念化与美学的感性化、经验化,促使两者有了更密切的同盟之约。正如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所认为的,进入现代,艺术和哲学正在构建神圣的同盟。
1917年,当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将工业制品“小便器”搬进艺术的殿堂之时,便形成了对艺术观念的根本挑战。这种对机器制品的反讽式应用,使所有传统艺术与美学的趣味来源变得空虚,仿佛清空了二者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全部意义,所有的美感特质被整合在了概念、语言、制度以及社会文化因素当中。[1]参见[美]罗伯特•威廉姆斯:《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第2版),许春阳、汪瑞、王晓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7-198页。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表明,艺术将媒介这一本质孤立出来,使其与现代艺术哲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联系起来,以至于思想、观念和精神之于艺术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技术、语言、形式本身。也就是说,衡量当代艺术的价值标准已经不再是技术的精进与样式的翻新,而是是否能以新的媒介语言去表达人的精神观念、回应种种现实性的需求,进而表现出一种对人的异化现象的警觉、反思、质疑、批评、抵御和反抗。因而,现当代艺术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更具“视觉政治学”“视觉意识形态”的特征。
实际上,西方现当代艺术美学的观念与理论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艺术同频共振——实践美学与理论话语的建构共存互动;也强有力地回应了现实性的需求,表现出理论的力量与意义。当西方进入大机器生产时代,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人的异化日趋严重之时,人本主义思潮在艺术美学界就应运而生;当反传统的势头甚嚣尘上,现代主义艺术高歌猛进之时,对其质疑与反思的后现代艺术理论又扬帆起航;当人们沉浸于资本和技术所构筑的虚幻社会的“景观”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美学即快速地彰显出批判与否定的锋芒;当消费逻辑大行其道,娱乐文化成为强势形态后,本雅明、鲍德里亚式的理论警觉与抵御便显得敏锐而有力。
关注现实,关注艺术实践和审美文化的鲜活现场,并以凝视之眼和反省之思观照艺术文化走向,为其纠偏,甚至予以质疑与否定,可以说是西方当代艺术美学的一种重要品质。相较而言,我们的艺术美学、艺术理论在百年现代进程中,缺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鲜明的时代性、本土性和大众性的理论建构。在今天的中国,美学与艺术、美学的理论探讨与审美实践的耦合度还不高,互动性较弱,在某种程度上还处在各自“自嗨”的状态。
在美学研究方面,不可否认,自20世纪初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先驱将“审美无利害”“艺术自律”等学说介绍到国内以来,学界便主要围绕这一理路展开研究,并通过80年代“美学热”的淬炼而渐趋成熟。但问题是,这一现象级的学术活动,也导致美学在很大程度上“书斋化”“思辨化”,习惯了“从话语到话语”。而形势更为严峻的是,其本身从学理与思想资源上来说,就是隔离于现实、远离中国传统与本土文化、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相疏远的。并且,这种象牙塔式的研究活动早已视“实践”概念为虚设。
在艺术实践方面,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艺术思想的主导,实现了艺术的社会作用与政治作用两方面的契合与统一,从而推动了艺术大众化、科学化与时代化的发展,尤其是百年来,也结出了一大批现实主义艺术作品的果实。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当下许多艺术作品所呈现出的浅表与虚无——大多以流行化图像,暗合世俗的娱乐文化,或以貌似深刻的符号组合,实质以虚无性回避对现实问题的干预和指涉。更重要的是,在当下消费主义至上的语境中,在物的诱惑与欲望的重压之下,艺术界也并没有对美学理论本身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而是更多表现出在某种“成功”图式中去借鉴、挪移、篡改、重构某些元素的热情,既无原创性的观念,也无观念视觉化的原创性建构,不管是对于中国传统图像资源还是西方现当代图像资源来说,都大致如此。
因而,如何挖掘原创性,并借助视觉语言进行观念表达、思想传播,就是目前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他们要么依然是炫技,要么制作出貌似深刻实则并无思想的图像。而对于中国范式的“艺术—美学”体系建构的方向,更是无从回答。于是乎,当下中国的艺术、美学与现实也就形成一种貌合神离之象;也就难以避免中国艺术的“大咖”对于国外艺术图像抄袭而引发官司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学理论者面对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时,不仅没有阐释权,而且如普通观众一样一筹莫展。
四、复归同盟之约
如果说赫伯特•里德的理论是一种理论话语霸权,相信艺术家的理论化才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当代艺术与美学却在价值追求与机制建构上有了一种共性而自然的高度耦合性。当下,不管是具身性美学精神的彰显,还是介入性艺术精神的高扬,都表明艺术与美学介入日常生活、介入社会的价值追求越发凸显。
正如在《当代艺术文献系列》前言中提到的,近几十年中,艺术家逐步扩大了艺术的边界感,因为他们寻求将艺术参与进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中。[1]参见Iwona Blazwick, “Preface of Documents of Contemporary Art,” in Claire Bishop ed.,Participation, Lond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Whitechapel and The MIT Press, 2006.p.1-2.介入日常生活,使美学与艺术共同担负起提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使命,也呈现出艺术图像的日常生活化景象,因而关注底层性思想与主题性叙事成为当今中国艺术的一大普遍现象。而介入社会,则能够使得艺术与美学担负起社会批判、文化批评与学理建构的责任。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艺术的批判即拯救。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亟待批判的是艺术、美学与现实的“自嗨”状态,而传承与建构才是最好的发展。因而,将艺术与美学的元素融入社会现实、融入日常生活、融入美感教育、融入城乡规划和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成为了时代的呼唤和未来发展的必经之路。
当今艺术更倾向于人文艺术,其不仅打破了传统艺术的常规概念和媒介界限,也在内容上更多关注新的社会问题,情感上更加注重个人感受的抒发。而当今美学则更多介入当代艺术,它不仅能用系统的、具有建设性的美学体系对当代艺术进行梳理和剖析,还能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哲学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发展,故而完善并强化两者的互动机制也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是身份建构。在当代艺术创作实践中,因为受到人工智能和科学技术的影响,传统的手工创作艺术模式逐渐转向一种多元化的艺术方式,从而引发了对当代艺术美学中艺术家的身份、主体、审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这一急迫形势,使得当代艺术家必须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学者思维,使得当代学者必须有目标地培养自身审美感性化的身份意识。如果依旧用空洞直白无内涵的模式制造艺术,将无法与当代审美评价体系相呼应,也无法创造出引发更多人产生共感的、知性的艺术作品;如果美学家们对鲜活的审美实践和极力介入社会的艺术缺乏敏锐度和观照的热情,依旧迷醉于从话语到话语的解读游戏,特别是执念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译介模式,那么要履行当代美学家的职责必定勉为其难。毋庸置疑,当代艺术与学术的发展,对艺术家、美学家本身的身份建构和审美价值塑造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是培养模式。纵使从20世纪初引进“美的艺术”概念以来,知识界普遍认为美学和艺术不可分割,但在当下艺术专业的教学实施和科研探索中,依旧存在画地为牢的现象。这对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和美学的互动体系仍然具有较大的阻碍。当下的美学现状是人们审美功利化、艺术娱乐化和趣味虚无化,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观需要从解决美学和当代艺术的联合关系开始。因此,一方面,拓展艺术专业的美学视野,提升美学理论的涵养,是解决类似问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美学专业必须强化审美感知力,才能实现回应现实和“超越”的最终目标。
再次,是学科体系。在当代艺术活动中,由于思想性、观念性、精神性凸显,人文学科更多关注视觉文化,而在视觉文化成为各学科交汇之地的情况下,无论是美学还是艺术,学科各自的发展趋势都表明强化互动与交融的重要性。对于近来艺术类学科新目录的颁布,其到底是否会有助于艺术学科与专业的发展和人才质量的提高,还有待观察。因为在形式上,学科目录不仅将艺术的历史、理论、评论研究与创作实践剥离了,而且也突破了中国高层次艺术人才培养目标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格局。由此,无论是从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是从长期以来艺术学科“学与术并重”的整体性模式来说,都应对新目录调整的实际效果有一种警觉。
最后,是美学与艺术的自主体系建构。无论是美学还是艺术的学科归属都肯定了自身的独立性,但从本体论、修养论和实践论的角度来看,二者各有贡献又殊途同归,但都面临自主性理论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
那么应该如何建构?笔者认为应该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何加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重要理论范畴的当代性阐释与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和“天人共美”思想包含了世界性哲学美学、艺术美学的终极追求目标,以“心游物外”作为艺术和审美的基本态度,以道、气、象、神、韵、意、趣等作为基本范畴,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共同构筑着中国传统的艺术美学体系。而我们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又很容易找出其与西方美学的相似性,如老庄的“解衣盘礴”“虚静”和以康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中的无利害性静观就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如何在承传中国传统的艺术美学哲学精神的前提下,在参照西方艺术美学体系的同时,关注艺术功能本身和当代性媒介的转化,是寻求艺术与美学互动发展过程中——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哲学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无法避免的问题。这一问题要求我们应该采用一种跨学科或重构的方式,去建立一种超越艺术和传统美学的研究体系。当然,这一体系应当是综合了与艺术欣赏相关的一切研究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框架。恰如德国当代美学研究者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提到的——“美学本身应该是跨学科的,而不是只有在与其他学科交汇时才展示其跨学科性”[1][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二是如何提升艺术与美学话语回应现实的能力。总体上看,我们既疏远了甚至丢弃了传统,也缺乏回应现实、推进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当代转换的敏锐感和有效途径。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的艺术、美学孕发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无论是乐论、画论、诗论、书论,其意涵与针对性对于解决传统艺术的相关问题来说是有效的。在中国革命年代由政治、文化精英建构起来的大众化艺术、革命美学,对于解决和融合当时艺术、美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来说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艺术美学概念、范畴与话语范式去谈论现代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似乎就完全失效了。因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及美学观念经过百年的发展,在其功能观、价值取向、语言、风格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传统”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很难与之相对应。如我们很难用“道”“气”“意”“韵”等概念去谈论现实主义的艺术,更难去讨论强调介入社会、介入空间的当代艺术。随着当代艺术的主题逐渐与当下社会和人文靠拢,艺术与美学也开始走向大众化、社会化。意大利美学家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主张当代美学和艺术也应该走向普遍大众性、回归本身的立场。而美国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则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来提升艺术及审美互动的社会参与性。这迫使艺术和美学逐渐脱离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走进现实的生活视觉,创造出一种情境性和连续性的当代艺术—美学活动环境。这不仅需要艺术与美学从业者本身的视野下沉,还需要所有的社会大众作为积极的参与个体加入艺术美学活动中,从而对艺术和美学的“互动机制”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加速效应。
三是如何力求研究与书写范式的创新。与西方美学研究范式不同,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形成于先秦时期,并因受儒道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多样形态,因而对不同类型和风格的艺术与美学观念都有很强的解释性和包容性。鉴于此,我们当然应该充分挖掘中国传统艺术美学和艺术文本书写中的“混合型”“集合体”的优势,进而作出当代性的阐释与价值转化。所谓混合型,意旨建构一种史论结合、品评兼容、内在关注与外在审视相结合的民族研究范式与书写方式。这种范式创新有助于我们在艺术的历史中把握规律,以理性的视野穿透史实,从而进行美学的逻辑建构,并对史实和艺术的现状予以价值判断,使批评永远“在场”,重构富有中国特色并具有回应当代艺术实践能力的艺术—美学模式。当然,这种新的范式创新将探索出一种植根于独一无二的中国本土美学体系中的当代艺术发展模式。这是艺术美学的需要,也是艺术实践、艺术史论的需要。
四是艺术美学自主体系建构问题。美学的原乡在哪里?通向原乡的路又该往哪走?艺术美学如何在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领域之外,经营好自家的天地,从而建构自我的身份,这是艺术美学专业不能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生产,艺术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的思考,而艺术永远是伴随着思想前行的。从理论形态上来说,需要解决传统观念的固化问题,通过不断创新去勾勒新的知识体系。当然这就需要我们从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美学(理论)各个层面进行梳理——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不可分割。而从实践形态来看,将理论延伸到创作中是“物化”和“心化”过程的统一,而“物化”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当然,独立自主与跨界融合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相互依存的。目前,新文科战略的实施,倡导以跨界交融的视野和方式去拓展学科新的发展空间。艺术美学的研究,需要在吸收其他人文社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范式中去实现。譬如图像学打破了形式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主张阐释图像的文化意义。其他人文科学和文化公共领域(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符号学等)通过图像研究获得了理论延伸,同时也开辟了图像阐释的不同维度。今天的艺术美学不仅不能强化边界意识,将自身限定在只能抽象地谈论“一般性”理论的范围内,反而应以更大的包容气度,将艺术研究的不同维度与方式集于一体,并不断地吸收其他学科的养料,甚至与其他人文科学进行更多的交叉融合,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话语力度。那么,在融合共通中谋求艺术美学的独立自主体系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相关问题。
总而言之,艺术是实践的美学,美学的聚焦点是艺术,艺术与美学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新时代中国“艺术—美学”的传承与发展,应该从身份建构、培养模式、学科设置以及中国式理论话语体系等方面去完善并通过强化两者的这种互动机制,从而担负起社会批判、文化批评与学理建构的责任。
——评《全球视野下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