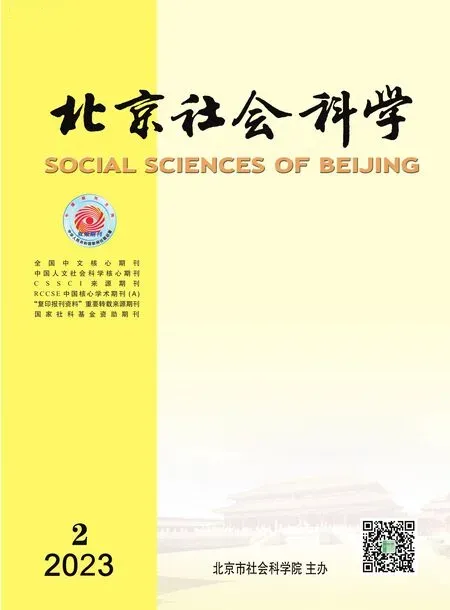何焯赋论及其评点旨趣发微
顾一凡 徐雁平
一、引言
刘熙载《赋概》有“赋兼才学”[1]之说,这不仅是对赋家学识的要求,亦是对评赋者的挑战。何焯作为清康熙朝杰出的校勘学家,学养甚富,在评点赋作、讨论赋学时常有深刻见解,能纠正前代注家之不足。此外,何焯身处明清学术转型的关捩,上承清初评点之学,下启乾嘉校勘之风,评点群书目的不再是论文,而是转向勘误,可视作学风转换的典型。何焯评点尝被诟病不脱八股习气,这是由于他将编选时文选集视作治经求道之法,时文印记下屡见其卓识巧思。因此,考察何焯的赋论,亦有揭橥其评点初衷和意趣的用意。①
二、体制:何焯赋论的核心概念
康熙朝曾设博学鸿词科,延揽文士,加之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试赋的影响深远,一时间,“艺林有志之士罔不嗜古学、敦诗文”,作为典范教材的《文选》,亦“复家弦户诵于天下”。[2]此后,凡“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张之洞尝“举其有论著校勘者”为“文选学家”,[3]何焯因《义门读书记》辑录其评点《文选》的批语,被列于其中。清代文选学家余萧客认为:“义门当士大夫尚韩愈文章,不尚文选学,而独加赏好,博考众本,以汲古为善。晚年评定,多所折衷,士论服其该洽。以今观之,清世为《文选》之学,精该简要,未有超于义门者也。”[4]不单揭出何焯治文选学折衷诸家、精审简明的特点,亦透露何焯所据底本或为汲古阁本。清人徐攀凤称:“义门何先生之读《选》也,率以李崇贤注为宗,评本嘉惠后学,越百年矣。”[5]何焯的确选取李善注本进行评点,并参考五臣注本及各家对《文选》的注解批评,但何焯所涉李注的批语多为驳正补充李善的注解,少有认可之处,认为何焯推重李善注的说法未妥。此外,何焯评点《文选》的时间尚未可知,但其评语中有“余辛巳夏始获尝其盐渍者”[6]云云,又有“惟吾师安溪先生云”[7]之语,知何焯评点《文选》当晚于康熙四十年(1701)。
何焯赋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评点《文选》赋作的批语中。②孙福轩论及清代名家赋论时简要指出:“何焯论赋,其要有两端:一是思想内容方面的美刺、揄扬;二是艺术表现上的铺陈夸张。”“在何焯看来,赋之要义,在于铺陈中寓以讽谕。与形式的‘丽’相比较,讽谕或颂扬的思想永远是第一位的。”[8]然何焯评赋不以铺排为佳,偏好跌宕顿挫的赋作,且对赋家漫用典故、夸饰极为矜慎;③论赋之讽谕亦少有新意,主张“讽刺即在铺扬之内”[9]“铺陈处皆讽谏”[10]“夸饰处皆讽也”[11],即铺陈“极其眩矅”的用意在于“主于讽刺”。值得涵泳的是,何焯论赋的讽谕功用时尤为注重讨论“谲谏”,如评左思《魏都赋》云:“太冲之于魏氏,文与而实不与,可谓得‘主文谲谏’之遗矣。”[12]《景福殿福》“感乎溽暑之伊郁,而虑性命之所平”二句,“先虑燥湿寒暑,而及吴蜀,则无谲谏之迹”,而描述吴蜀覆灭处,“乃即所谓‘翘足而待’,其言若尽乎戏者,愈明其为谲谏矣”。[11]《上林赋》寄希望于“使之自悟,故云谲谏”。[13]谲谏本为婉言规劝之意,在何焯批语中,凡譬喻取巧、滑稽多辩处,皆为谲谏,而铺排渲染则统归于讽谕。何焯之所以如此分别讽谕和谲谏,在其看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乃“作赋之大略也”,[14]“望祲氛,观云物”为赋之“本事”,[15]赋家铺叙胜景以规讽君王是赋作应有之义,而戏言漫写,旁敲侧击,则谲而不正。进言之,何焯对讽谕与谲谏的判定,恰是基于其赋学思想的核心,即作品是否合于赋的体制或法度。
以体制为评赋准绳,首先反映何焯对赋体的思考。其评语所释“体制”不仅涵括赋体裁的独特,亦关注赋作的体貌与体源。譬如祝尧以为《子虚》《上林》“实则一篇”,又云:“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夫》篇来。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艺澌尽,体制遂失矣。”[16]何焯反驳道:“首尾虽以议论问答,然‘车驾千乘’等句,即以赋齐王之猎,后半‘齐东陼巨海’等句,即是赋齐国游猎之地,则亦未尝非赋也。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矣。”[13]在何焯看来,文与赋,并非以辞藻富艳、铺张盛美界定,凡秉持体物之本事,均可视作赋体。
不仅赋与其他文体有体制之分,何焯认为,赋的序言与主体亦须各循其道。苏轼曾批评《文选》将宋玉《高唐赋》“玉曰唯唯”之前视作赋序,认为此划分“与儿童之见何异”。[17]何焯则赞同萧统对赋序的界定:“相如赋首有亡是公三人论难,岂亦赋耶?是未悉古人之体制也。刘彦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则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归余曰乱,犹人身中耳目手足各异其名,苏子则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18]
何焯对赋的体貌,亦取体制为衡量标准。何焯评颜延之《赭白马赋》“妙简帝心”至”有恻上仁”一段,云:“体要淳雅”;并称赞“将使紫燕骈衡”至“敬备乎所未防”一节:“此处不可直接马毙,故作此一段虚景,兼寓颂美国家之旨,得体而有情。”[19]前者着眼赋作的风格与蕴含的情感,后者点出赋家选用的技法和营造的效果,总归于赋作体貌是否合乎体制。
对于赋作之体源,何焯试图寻觅赋家如何摹拟前代名篇的风格体制,融入新意。何焯谈及庾信《哀江南赋》源出潘安《西征赋》时,激赏庾信善于变通,因“瘐赋今事,故尤有关系能动人”[20]。又视《羽猎》拟《上林》,《长杨》拟《难蜀父老》,认为扬雄虽“祖述相如,其奇则相如所不能笼罩,丽处似天才不逮也”[21]。同为宫殿赋,何晏《景福殿赋》“似拟《东都》,亦是讽刺”,故《文选》取何晏之赋而弃卞兰、韦仲之作。[11]何焯不止留意赋家所摹拟的名篇,尤着力揭示其度越前人之处。
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将文体分为体裁、体貌与体要,体要以义为主,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古文家所主张的义法由此继承发展。[22]何焯赋学思想以体制为主脑,不但包涵赋的体裁、体貌和体源,而且兼有体要之义,承载赋之功用。何焯总评《两都赋》时,认为班固“特作后赋,折以法度。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未造之侈,又包平子《两京》之旨也。词藻不如相如,其体制自足以冠代”[23]。又云:前篇极其眩矅,主于讽刺,所谓“述下情而通讽喻”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24]何焯之所以称《两都赋》体制冠代,因其铺陈辞藻,讽斯丽者,近于正雅,且折以法度,颂美国家,又如变雅,《两都赋》兼有赋的两种功用,故体制完满。所谓法度,何焯以为《东都赋》“更造夫妇”至“人伦实始”是“法度”;“则必临之以王制”至“乘舆乃出”,“铺陈处皆言其法度”;“乃申旧章”至“沈珠于渊”亦为“法度”。[25]合三者观之,法度涵盖伦理等级、礼乐典礼与所施政令,既试验赋家学识修养,又看重赋家才智能力,赋的选才功用寓于其中。此外,何焯驳祝尧“先丽而后则,此赋之所以为赋”之说,阐释其“丽则观”,即“讽斯丽者皆则,徒劝斯丽者为淫”,亦点明体物讽谏为赋体之本事、赋用之正途。总言之,何焯以体制评赋,包举赋体与赋用两端,自成体系。
三、校勘:何焯评点的初衷与意义
何焯入直南书房、武英殿后,治学重心移至校勘群书,开清代校勘学风气,其校勘成果通过所撰题跋及手批本或过录本中的评语留存。由何焯评点《文选》赋观之,何焯所下大量评语是为夷考补正选文、李注及他书的讹误失实之处,而非醉心于赋作的精巧与艳冶,对大多数篇目仅作校勘学考察,其评点初心实在校勘。
义门弟子沈彤评述何焯校勘风格为“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说、小学,多参稽互证,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伪阙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26]。其中,辨明正字、参稽互证、探求隐密三点校勘特色正对应何焯点勘《文选》赋所进行的三项工作,即校正舛误、补充注解与揭示内涵。
首先,何焯校正书中舛误,既更正赋作流传中字词的讹变,如据颜师古《匡谬正俗》“副字本为褔字。从衣畐声”之见,提出《西京赋》“仰福帝居”为“传写舛讹,转衣为示,读者便呼为‘福禄’之‘福’,失之远矣”;[15]又力图恢复校者妄改的讹误,如《思玄赋》“利肥遁以保名”,《后汉书》中“肥”作“飞”,何焯以为“飞”字“乃合象词无所疑也之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雌黄。以《七启》校之自审,然不读姚令威《西溪丛语》,未有不反疑古善本为也”。[27]
此外,何焯还指出《西都赋》“隋侯明月”,“隋”当作“隨”;[24]《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蒸当作“烝”;[28]《九辩》“故駶跳而远去”,“駶跳”当作“跼跳”;[28]《七命》“囿棲三足之鸟”,“鸟”当作“乌”[29]云云。其中,何焯评《西都赋》“招白鹇”,曰:“鹇,《后汉书》作闲。注云:招,犹举也。弩有黄闲之名。此言白闲,盖弓弩之属。今以‘揄文竿’句例之,当以《后汉书》为正。”[25]此观点恰与《困学纪闻》相合,《困学纪闻》载曰:“《西都赋》云:‘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二句为对。白闲,犹黄闲也。注云‘弓弩之属’。《御览》引《风俗通》:‘白鹇,古弓名’。《文选》以‘闲’为‘鹇’。”[30]何焯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购得《困学纪闻》,自此“南北奔走亦未尝不偕”[31],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作《困学纪闻笺注》,深悉书中文字,然何焯评语并未援引《困学纪闻》或《风俗通》,而以《后汉书》为依据,益见其谨严审慎。
其次,何焯评点《文选》赋时注重补充前人未注的史实典故,如《景福殿赋》“爰有遐狄,镣质轮菌。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四句,精熟三国史事的何焯于此处援引《魏略》云:“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其祜伊何,宜尔子孙”两句,何焯补充曰:“时继嗣未广,故有斯祝。”[11]《北征赋》云:“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何焯指出:“以行苇为公刘之遗德,必出齐、鲁之经师,注家已不能详矣。”[20]
再次,何焯有意注明赋家作品中的指代内容,如王粲《登楼赋》“白日忽其将匿”,乃是“比汉祚将尽也”;[32]陆机《叹逝赋》“愍城阙之邱荒”,实是“以城阙代亲故”;[33]《洛神赋》“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是“冀得复朝京师而见文帝也”。[34]
何焯评点所据底本似为李善注本,评语中凡称“注”,均指李善注文。较之赋作的传写讹误,李善注文失实之处甚夥,何焯的校勘考证重心亦移至此处。何焯驳正李善注《文选》赋不当处共31条,归纳如次:
其一,驳注法不佳。李善注《东都赋》“体元立制”时,引杜预《左氏传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两句,何焯以为“如体元字,乃杜注用班语,不当引后注前”。[25]李善引《西都赋》及王褒《甘泉赋》注《西京赋》“三阶重轩,镂槛文”,何焯驳之,曰:“班、张相去未远,如何引以为注?况王叔师更在张后耶!”[15]
其二,驳释词不明。何焯评《东京赋》“发京仓”“赉皇寮”曰:“‘京仓’二字出此,以禁财对举,盖指京师之仓也,注未明。”“‘皇寮’犹言‘大寮’,注亦未明。”[9]《羽猎赋》“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李善注为武帝侵三垂以置郡。何焯非之,曰:“此‘三垂’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21]
其三,驳论文有误。李善评《文赋》“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二句,云:“其事既殊,为文亦异。故欲夸目者为文尚奢,欲快心者为文贵当。”何焯则以为“二句语意相承,注谬”。[35]屈原《离骚经》“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李善分别注解为:“言己虽见放流,犹种莳众香,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暮不倦。”“言己积累众善,以自洁饰,复植留彝、杜衡,杂以芳芷,芬香益畅,德行弥盛也。”何焯直言“注颇两意纷杂”,[36]前后略有抵牾。
其四,驳引文欠妥。《东都赋》“乘时龙”三字,何焯以为可引《后汉书》“马八尺以上为龙”与《月令》“春驾苍龙,各随四时之色,故曰时也”注解,而“李注引《易》,非是”。[25]《芜城赋》“寒鸱吓雏”当引“《庄子》‘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注中误引《尔雅》”。[32]《文赋》“潄六艺之芳润”,李善引《周礼》证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何焯不以为然,云:“谓诗、书、易、礼、乐、春秋也。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义求之,不当漫引《周礼》。”[35]
其五,驳不合义理。《洛神赋》李善注云:“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流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何焯批曰:“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又方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夫岂特酗酒悖慢刼脅使者之可比耶?”李善注又云:“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何焯称此“数语俚俗,不复有文义”。[37]
其六,驳考证失实。《北征赋》“造长山而慷慨”一句,李善引《三秦记》“秦名天子冢曰长山,汉曰陵,故通名山陵。”以及《汉书》“高祖葬长陵。”以为长山为冢名。何焯反驳道:“长山当是山之本名,因山为陵耳。如《三秦》之说,自霸陵以下,将何取耶?”。[32]
何焯亦有认可李善注文的评语,如《吴都赋》“指包山以为期”,何焯认为李善注引周处《风土记》“阳羡太湖中有包山”,较王逸注“包山在秣陵东湖中”稍长,且与下文“随接幸乎馆娃”相应,“当从善注”。[12]《魏都赋》李善注云:“邺城北有大邸,起楼门临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馆,故举年号也。”何焯以为“重客馆,故举年号”这条注释“可为故实”。[12]《恨赋》“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两句,李善阐释其文法,曰:“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何焯评曰:“此可标举以为对法。”[35]李善引繁钦《定情诗》“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注《女神赋》“践远游之文履”,何焯赞曰:“同时人语借以互证,当法此注。”[38]
若李善注大致无误,但略有瑕疵,何焯亦予以修补。《魏都赋》“钟簴夹陈”,李善注云:“文昌殿前有钟簴,其铭曰:‘维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又作无射钟。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钟簴于文昌殿前,所以朝会四方也。’”何焯补充道:“魏四年者,操为魏公之四年,于汉则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进操爵位王,故设之以备朝会。”[12]《吴都赋》“重城结隅”,李注仅提及“大城中有小城”,何焯为之增补“唐宋吴郡犹有子城,至明初破淮张始废”的史实。[6]《闲居赋》“以俟伏腊之费”,李善注解为:“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何焯以为此说“未尽其理”:“伏者,藏也。阴气以盛,金已潜伏于火中。庚为金,可以见其自微而著也。”[33]
由此可知,何焯评点与李善注屡有相左,并非壁垒相望,而是何焯精校评点底本的明证,对李善公允妥帖的注解从善如流,对存有微瑕的条目补阙拾遗。除校补李善注外,何焯还厘正五臣注、《后汉书》注以及俞犀月、祝尧的论见,数目相对较少。
何焯校勘尤长于参稽互证,在评点《文选》赋时,凡与之相关的书籍,何焯均留心点勘互校。不单校出他书讹误。如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何焯据此评曰:“老杜云‘二十作文赋’,于臧书稍疏也。”[35]又仿李善征引之法,溯源典故之出处。如《秋兴赋》“且敛衽以归来兮”,何焯按曰:“‘归来’亦有‘秋兴’故实,不独渊明也。”[39]《离骚经》有“周论道而莫差”,何焯以为此句“可证论道经邦是古书之词”。[7]《九歌·云中君》有“与日月兮齐光”,何焯批曰:“太史公‘虽与日月齐光’之语,本屈子之词。”[28]且指出后人化用《文选》典故之例。如《东京赋》“聘邱园之耿洁”,何焯云:“昌黎‘隐君子弥明’之语,出此。”[9]《蜀都赋》“指渠口以为云门”,何焯以为“杜诗‘白帝城中云出门’本此。”[40]
由此观之,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如果对赋文本身的点勘注解尚可视作传统观念上的文章评点,而对《文选》注及相关典籍审慎细微的校正,恰可印证何焯评点《文选》的初衷在于校勘,欲使之为善本。④
四、时文:何焯评点的印记与偏见
何焯晚年遭构陷入狱免官,身故后被雍正指斥行为不端,立身卑污,与胤禩结党,[41]弟子亲友“虑有株连,不唯不能刻集,并存稿亦有畏忌”[42],其评本一时云散。所幸至乾隆中期,开四库馆,招集天下淹通之士校雠编勘,于是何焯学术成就乃大彰于世。[43]至梁启超讲论清代学术史时,以何焯为清代校勘学“创始的人”[44]。有推崇何焯者,亦有呵诋何焯学问的声音。俞正燮、陈康祺师徒在其文集、笔记中讥笑何焯以制艺之法论文,因何焯被追赠侍讲学士,哀叹“义门果何德以堪此”[45],反对世人对何焯治学成就的认可。全祖望亦作《困学纪闻笺注》,其间对何焯以评点八股文的方式注释乡贤著作大有微词,屡屡在笺注中批驳何焯见解。此后,何焯因坠失制艺、故评点成就亦不足观的看法遂成定谳。耿文光称“义门之学,专攻时文。集中杂著,皆论义制”[46],黄侃亦云:“义门论文,不脱起承转合照应点伏之见,盖缘研探八股过深,遂所见无非牛耳。”[47]
何焯前半生与时文联系紧密。康熙二十三年(1684),何焯曾寓居阎若璩家中,二人就曾谈论有明一代的名家制艺。[48]同年,何焯初次参加乡试,落第,此后“南北八试,未尝一荐”[49],但并未消磨对制艺的热情。康熙三十三年(1694),何焯为浙江学使代作《两浙训士条约》,畅论明代成、宏以降的八股文流变。[50]翌年,何焯有感于《复乐记》奸声正声之辨,自悔“日奔驰而道则忘”,于是“尽屏丛说,更取圣人贤人之经读之,反覆乎训故,会通乎条理,得其大体,道本浸出”。[51]不再随俗结撰时文,而是转向纂辑八股文集,将评点时文视作治经求道的路径,并希冀转变当世文风。康熙三十八年(1699),何焯所编《本朝小题文行远集》付梓,是书汇辑“万历丙戌至国朝士子为世称传之文”[52],书前自序云:“儒先既造道,而解经为之义者即以经核乎道之合离焉,继自今乃人及于古矣。”[53]知何焯欲借此书重申时文之义,制艺文章亦可阐释经义,接续道统。同年,何焯又作《义门书塾论文》,教导生徒“今日之科举所言固圣贤之学”。[54]康熙四十一年(1702)后,何焯得李光地推荐,获赐功名,入直内廷,对制艺的需求与热情渐衰,但仍延揽秀士,招收弟子,“欲就举业而引之儒术”,教授时文时以经义儒术为本。何焯尝规劝其爱徒徐葆光:“八股既为时尚,将来略作几篇亦佳,只是解书要紧,舍书无自作好文之道也。”[55]据此观之,何焯对时文的态度,并非借此炫名,而是以之为诠解经义、锤炼文气、效仿圣贤的法门,仅以“专攻时文”看待何焯编选文集、教授弟子的行为,殊为未确。至于全祖望对何焯的批评,当归咎于何焯反复称王应麟为“宏词人”,批评其“华而不实,专尚新奇”[56]“夸多”[57]云云,引得全祖望为乡贤向何焯发难。《困学纪闻》云:“‘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处。但禅学有体无用。”何焯评曰:“乃指仁之为本心,非直本心为仁也。”此论并无不妥。而全祖望则借题发挥,谓之:“盖以时文家当辨圣学耳。”[58]径言何焯为时文家,含讥讽之意,已非实事求是。
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时常留有议论时文的痕迹,譬如何焯以为《西都赋》“‘穷泰极侈’四字,一篇眼目,以下皆发明此句,所以极其眩矅也”[24]。评《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几句“上二破‘箫’字,下二破‘洞’字”[35],颇类评八股文“出题”,点明文眼。评《海赋》“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起得突兀”,[39]又似讨论时文之“起讲”。评《西都赋》“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收此一段,有势有力”,如八股之“束比”。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何焯更是借用制艺术语,评为“六句破题”,[19]或如黄侃所言“不脱起承转合照应点伏之见”。然八股文之起承转合远非寻常文章可比,发展至清朝,时文愈加结构清晰,逻辑顺畅,联系严密,起讲、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大致对应文章的起承转合,若细论之,提比、中比、后比之中又各有起承转合,虚实相衬。[59]何焯醉心制艺之学良久,借用术语或顺八股之口气评文,无可厚非,不当因此忽视何焯对文法和义理的讨论。
何焯评点赋法尤喜赋作顿挫多变,不欲其直,不同于时文一气相生、一脉相贯的标准。如《西京赋》“匪唯玩好”至“实俟实储”,何焯指出此段“带叙小说,疏密相间,顿挫即具其中”。[9]《射雉赋》“屏发布而累息,徒心烦而技懩”二句,何焯评曰:“顿挫。无此二句,‘义鸟应敌’句便接得不生动。”[21]宋玉《招魂》云“魂兮归来,何远为些?”何焯认为“带此一句,势乃不直”。[60]评《招魂》“菎蔽象棋”至“揳梓瑟些”一段,曰:“歌舞之中,忽间以戏剧,总不令文势直也。”[60]《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至“若神僊之髣髴”一节,何焯批曰:“此是夸齐以所无。此段插在中间,叙畋事便不直。凡《左》《史》行文皆然。”[13]何焯所谓顿挫处是连接文章疏密虚实的文字,无此则不免起得突兀,收得浑沦;在夸饰铺叙中亦须宕开一笔,忽间以他事,或一事分作两层,“总不令文势直也”[60]。
何焯以选评时文研治经学,在评点赋作时亦关注其中的深意与儒术。《洛神赋》“黄初三年,余朝京师”,李善注称“《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何焯指出:“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雒阳,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年,犹之发丧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责躬诗》表云:‘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岂缘略也?”[37]又评《洛神赋》曰:“文帝以仇雠视其弟,而子建睠睠如此,不敢稍有怨怼,所以虽终不见用,亦卒能自全。黄初六年,文帝东征,过雍邱,遂幸植宫,为兄弟如初。盖苟尽我所为负罪引慝之道,君父未有不稍为感悟者。后之藩臣往往以不学无术,自即于诛夷,悲夫!”[61]发前人之所未发。《吴都赋》“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二句,何焯认为“公孙、诸葛非徒属对之工,隐乎汉之亡,正得春秋王师败绩于某之意”。[6]《魏都赋》“传业禅祚,高谢万邦”,何焯评曰:“上文方叙开基,此即接叙魏晋禅受,盖著其德浅祚促,自谓可以比隆舜禹,而其实万万相辽也。”[12]纳兰性德《赋论》云:“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62]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以儒家伦理道德观衡量探赜赋作中隐涵的深意,以《左》《史》等经史典籍为参照评点文章义法,取法严正,不应因其时文家的身份而废言。
五、结语
合而观之,何焯以“体制”为主脑评点《文选》赋,不单考察赋作的体裁、体貌与体源,亦关注其体要与功用,兼有对赋体和赋用的思考。在评点过程中,何焯着力勘正赋文、赋注以及关涉典籍的讹误,既可体现何焯校勘特色与专长,又表明其评点以校勘为导向,以考据为初衷。何焯评语带有讨论时文的印记,这与其醉心制艺的治学兴趣有关,但何焯选评时文以治经求道为目的,赋评中不但有顿挫避直的赋论主张,也试图探赜赋作蕴含的经义及赋家作文的深意,当消除对何焯专攻时文的误解,正视其讨论文法的主张。
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何焯评语的校勘初心与制艺痕迹,何焯蕴校勘于评点,是批点八股的惯习与校书编纂的职责结合的产物。此前虽有呈现校勘成果的评点题跋,但多是为获取善本或题识留名;此后评点逐渐从校勘学退却,多用以赏析小说曲本,批与校趋于分离,是故何焯评点更暗涵清初学术范式的转换。
何焯虽承袭评点旧法,却不为专治一经、勘正史籍,其先入南书房校勘内府藏本,后直武英殿纂辑官修类书,批注题识遍及四部,旁及书画,校勘成为何焯学术精粹的集中展现和难以替代的专长。即便晚年卷入政坛风波,仍可以白衣入内廷修书,正缘于何焯校勘勤勉为清廷亟需,校勘禀赋为士人敬重。由此,何焯发掘出校勘的新功用,为校勘者开辟新路,即通过校勘也可治生、交往、扬名、入仕,归根结底,是将校勘从学术研究的初始环节提升为专门之学与立身之本。正因如此,何焯虽在雍正朝声名暗淡,而开四库馆后,何焯的学术地位被重新确认,并经历层累式拔升。不仅因其为最早以校勘扬名的清代学者,更因何焯藉此供奉内廷,修纂钜典,追赠殊荣,不免引发学人钦慕与共情。
注释:
① 关于何焯赋学及其评点特色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秋娟.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J].江南大学学报,2008(6):118-121;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M].中华书局,2021版;等。较之既有成果,本文以何焯赋论为例,探究何焯评点旨归,试图消解对何焯评点之法的刻板印象。
② 今传辑录何焯《文选》评语的著作有蒋维钧辑《义门读书记》、叶树藩海录轩朱墨套印何评《文选》及乾隆四十三年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据赵俊玲考证,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增补文字出自何焯同时学者俞玚,故讨论何焯赋论仍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卷四十八、卷四十九所录文字为准。参见:赵俊玲.今传三种何焯《文选》评点本辨[J].兰州学刊,2008(2):181-183。此外,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凡例》称“义门评本凡三易稿,世所传写,皆晚年所定。初次则支分节解,于初学尤宜。”已知“初次”评语非何焯所下,“三易稿”之说亦不可遽信。由何焯题跋观之,何焯校点群书鲜有多次易稿的情形,多数情况为校勘评点一书完毕后,若再寻得善本残叶,则校改部分章节卷次。何焯评点《文选》的文字至晚年或有删改,但大致应为一时之作。
③ 如何焯以为《南都赋》“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用典未妥,为赋家夸饰漫用。
④ 前文提及何焯所据底本或为汲古阁本,加之何焯在康熙四十年与毛扆交往后多次为其勘校书稿,据此推测何焯评点内容或为校勘汲古阁本《文选》的衍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