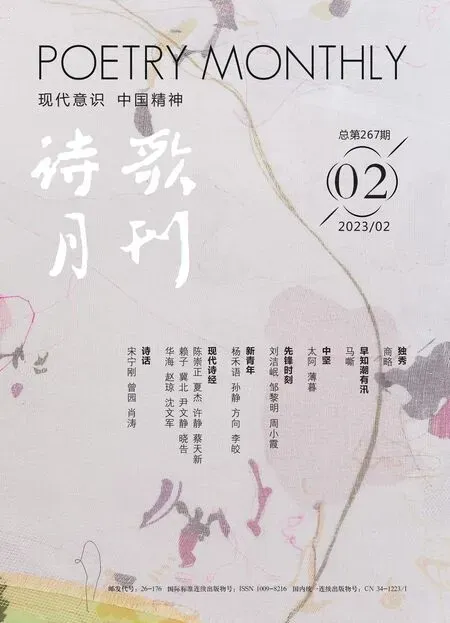甲壳虫(组诗)
太阿
甲壳虫
都说夏日盛大向日葵金黄天空湛蓝。
它在小区园中转圈南风和畅,
影子不比海拔两百米写字楼影子短。
它从头顶凤凰木上摔下来掉在他后脖子上,
他随即抬起手抓住坚硬的壳往地上一甩,
持续转圈晕眩,距离窒息需多久
目测无法计算。
已经四个轮回,夏日学会遗忘打瞌睡
恍惚眯一时半刻便醒——
它又振翅(哦,没看见翅膀)飞上树梢,
继续转转,仿佛等待蝉再次和鸣。
如同计划随风流产,
即使听见久违好消息也不致于狂喜。
一只甲壳虫一个孤岛一瞬间一天,
不知其名不可名状不知所终。
独行
我走在自己前面。
前面林荫路黑暗,暴雨后萤火虫带来微光。
棕榈、木棉、芭蕉、石头上的字、湖,
都是熟悉的,包括蛇的阴影。
但我身上有许多陌生者:
眼睛、心脏、四肢,
白天的热情谈话,夜里的梦中人,
现在都是黑暗的。
我已成黑暗的一部分,
但越来越清晰地看见星星、森林、小动物,
我与它们不同——
我一个人走,一千米、两千米、四千米,
僵硬,出汗,舒畅,想一直走下去,
把夜色走穿。但这是不可能的。
行走是暂时的,我自己是历史性的,
我不能重复,但行走可以重复。
在矛盾的十字路口,我知道拐弯,
找到自己,闭着眼睛回家,
并在隐藏的花朵中发现诗,仿佛生疏的爱情。
菊花或向日葵
一场博弈正在五星级酒店密室中高调举行。
分不清黑白、输赢,
就像现在分不清菊花和向日葵,
在CBD 中轴,巨大棋盘上铺下一匹金黄的布。
人在其中,如漂浮的文字,移动的棋子,
每一步都有古老陷阱。
它的有形边界是钢筋水泥玻璃峰林,
深刻的悲伤来自台风,
但暴雨刚刚培植过肤浅的根。
此刻,阳光放弃辨识声音,我向酒店走去,
迎接凯旋而归的孩子,他马上拥有段位,
而我拥有目不转睛的菊花或向日葵
和一刻惊心动魄的等待。
秋夜
少年快速驱动滑板车,之后
在空中旋转三百六十度——落地的雏鸟。
我努力保持身心平衡,
秋风吹凉后背,不能在台阶上久坐。
我站起来注视广场前最高的楼,
它外表通红,身上的字一个个向上飞升,
企图给黑暗天空以明亮的昭示。
十点整,周围所有建筑外壳都暗下来,
没有月亮,星星缺席,
林中弯曲的路等待夜下降的露珠。
在想象隐蔽处,一只野猫从垃圾堆中
跑出,追着老鼠一样的落叶。
我的灯光跌落在垫高的枕上。
抑郁的季节关闭所有靠北的窗,
崭新计划像新剥橘皮被搁在阳台,
等候黎明东方的光,
直到秋季结束或阳光消遁。
一场晌午的对峙
蓦然抛入野荔枝林,一只雕巨大的翅膀浮起
被侵入的领空,喇叭花顿时失声,
虽然保留了颜色,但湖面已被芦苇夺去。
狗的声音首先撕开丛林、心肺,随即
七八条影子狂奔,在身后二十米开外降速,
保持安静的尾随,缓慢移动,白云一样。
直至眼前道路分岔,铁皮房子林中隐现——
左边土路中央一只大黑狗静卧,
右边碎石路上五只黄狗尖叫同时开始加速。
背靠大樟树蹲下来,捡起一根粗树枝,
往地上一锉,竟粉身碎骨,
却扬不起一粒尘土。而此时所有的狗
都停下来,我再次弯腰拾一根细枝,
除掉枯死的叶,顾不了蚂蚁,
环视一圈,又一圈,找不到任何出口。
大雕又飞来在头顶盘旋,
观看一场晌午的对峙。
我始终无法看清它的圆眼,如同狗眼。
一拾荒人骑摩托车而至,尘土高过秋天。
眼睛对视一秒,“跟我走吧”。轻描淡写。
我像一块黑铁——分捡的垃圾,被带走,
所有的狗集合,礼送我出境。
在中途
不知谁将石片击落于水面,
涟漪从中心向外荡漾,一圈一道年轮,
不管多远,生命最初的搏动在身体里穿梭,
不管哪个阶段,自我没有不同。
而现在,在中途,又一次遭遇水面,
(这是第几次弹起再飞?)
又是涟漪(这是多少道年轮?)
我爱每一次弹跳,更爱每一轮涟漪。
人生就是一次打水漂,
“而今天,已经是今天”,
元旦新年的钟声再次使出全力。
总有惯力用尽沉入水中的那一天,
不去想它,用风和快乐加速度,
这样每一个虚度的日子都有美妙的水花。
九月的空椅子
“从未比在八月更加孤独”。而八月过去了。
九月,无声的椅子,在高高棕榈林中,
让人看见阳光分明的阴影,想到某些字词:
凄凉、懒散、陈旧、远离尘世。
它是他的象征,他的全部境遇。
高耸鼻梁——废城上一面被人遗忘的镜子,
维护着骄傲与勇气。整个人似乎脱离了鼻子,
没有知觉的面孔——桑叶遮蔽的天空。
蚕宝宝到哪儿去了,抽出的丝
幻化为天上的白云——不久前它是乌青的,
落下冰冷的雨滴——秋老虎的眼泪。
他往白云的方向走,湛蓝的裂缝扩展成大海。
现在,就一张空椅子,有肮脏的雨滴,
他用星巴克的纸巾(有着落叶的颜色)不停擦拭。
陷落记
我是如何一步步陷进黑暗的?
四小时,三百公里的时速,偶尔停、顿。
云中的光猪跑了,月的钩儿变成鱼钩,
垂钓于秋风中的微澜。
当光的浮标下沉,
一条河的鱼闪烁半夜的鳞光。
那么多人走过浮桥——光的鱼刺,
肉被白日的鹰叼走了,
我在人群中看不见自己。
感恩
这头快要发疯的驴再次走向湖水,
穿过铁路桥、初冬午后的阳光和金色橘园。
漫山遍野的冰糖橙人们今天开始采摘,
它直接走向那棵花果同树的油茶,
还有一棵在山坡上的橘林中亭亭玉立。
它注意到了脚下泥路中的长鬃蓼,
紫砂岩下的甘菊,两只野蜂嗡嗡鸣叫,
忘记了湖水和被钓上钩的游来游去的鱼。
客观与抽象如感觉变得庸俗不堪,
鱼的浪花白似油茶花。
一切多么奇妙!
幻想岛
始终没有上岛,即使红日落下。
我们绕湖参观了一大圈,最终进入废弃的矿坑,
那么多石壁,我不能像草一样攀援。
那么多装配式建筑,装在山的口袋里,
我不能装进口袋带走一栋。
我也不能住进小熊树屋,
今晚只有一张别人睡过的床属于我,
对视着湖岸某扇落地窗的灯光。
索道上停了几排不知其名的鸟,
我不能像它们从此山的红栎滑到彼山的茶园。
一日三省,来到这个天造的后花园,
人造的乐园,钱塘江与运河一眼望穿。
在钢筋天穹下的大船上,我摆好刀叉享受晚餐,
热带雨林里的大象开始漫步。
现在夜深了,整个身体陷在湖水的波涛中,
变成了一座幻想岛。
几只无角的梅花鹿从荒原中走来,
笼中的鹦鹉争相叫骂晴朗的寒潮,
风在脉动中歌唱我的家园。
黄金一刻
我已走过半个世界,
另一半我将继续走。至于火星,
即使有阿拉斯加帝王蟹我也不考虑去了。
三伏增加一伏,爱并非所向披靡。
黄金一刻,黄金船搁浅在中途的激流岛,
语言的帆沉寂在大海的蓝色漩涡下。
盛夏最后的一朵花
丹凤般停在凤凰木的葱郁中。
当热风的快镜头转换成慢镜头,
第一次与伊朗高压“牵手”,云的问题
“沙沙”地来了:我还是个“苗”吗?
在蒙尘的树下太阳合上我的眼——
泥土中飞起的“知了”吞噬盛大的交响
和我刚走过的人声沸腾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