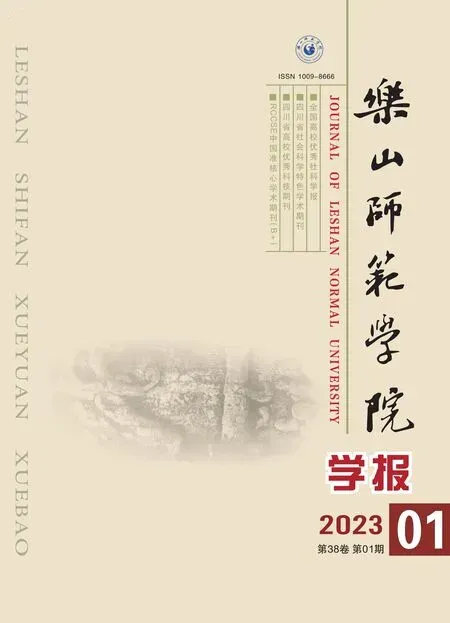苏洵干谒书信技巧研究
陈心怡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北宋崇文抑武,实行与士大夫共商国是的国策,特别重视选士。科举考试无疑是学子们跻身士林与朝廷选拔人才的最佳途径,科举考试包括进士科、诸科和制科,其中以进士科和制科最为重要。《宋史》记载:“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1]2969进士科是常科,有固定的开考时间和频次,制科则根据需要开设,没有固定的开考时间和频次。进士科考试在彻底实行糊名和誊录之前,其录取结果大多依靠荐举和延誉。根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本朝进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时望。真宗时,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2]69制科考试则是必须经过荐举才能参加的。荐举制度的存在给了胸怀大略却科举不第的士人团体进入权力中枢以施展抱负的机会,同时也催生出了一系列文人干谒现象。苏洵就是通过干谒和荐举获得官职,跻身士林的一员。
一般而言,在向某人干谒时,除了递交自己的得意作品,学子们还会附上一封书信以说明自己的情况,这封书信的写作显然至关重要。书信写作有较高的技术要求,既要书写自我,又要考虑对方。干谒书信除了要符合一般书信的创作要求外,还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写作者或饰言攀谈,以情动人;或展现才华,以文动人;或施展抱负,以策动人,其最终目的都是说服阅读者,使其心甘情愿,如获至宝的向朝廷荐举自己,从而获得一官半职。从某种意义上说,干谒书信的创作不亚于一场精彩绝伦的面对面游说,情感运用、叙述内容、叙述方式、叙述时机以及叙述态度等因素在这场书面游说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着结果的成功与否。
一、情感表达
由于苏洵的干谒活动主要以书信为载体,情感表达就显得至关重要,即纵横家所言“内揵”。只有拉近双方情感距离,讨得荐主的欢心,博得好感才能开展接下来的游说活动。苏洵情感表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表达仰慕,抬高荐主身份;叙述交情,贴近荐主心理;描写悲惨境遇,博得荐主同情。
(一)表达仰慕,提高荐主身份
表达仰慕,抬高荐主身份通常是苏洵面对皇帝和位高权重的大臣时所采用的情感沟通方式,也即纵横家最常使用的“飞而揵之”之术。先“作声誉以飞扬之”,大费笔墨夸耀和赞美荐主,满足其虚荣心,讨得欢心之后,再表达自己希望被提携的愿望,达到“钳”的目的。向位高权重者进行干谒,必须时刻注意措辞,一方面要舒徐委婉,不可疾言厉色拂了上位者的面子,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谄媚,以免落人口舌。尤其对以儒家自命的苏洵来说,“士以品重”,自求名利本身就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还要讨得对方欢心,如何进退,如何措辞就显得尤为重要。
《上皇帝书》:“以陛下躬至圣之资,又有群公卿之贤,与天下士大夫之众人,如臣等辈,固宜不少。有臣无臣,不加损益。”[3]281不仅说皇帝圣明贤良,是明君圣主,还夸奖皇帝身边的大臣都是贤臣勇将,不动声色的褒扬皇帝选贤任能,礼贤下士,德行足以网罗天下人才。短短一句话,既讨得皇帝欢心,又没有夸饰的谄媚姿态,堪称进退得宜,滴水不漏。《上余青州书》开篇,苏洵将余靖平生遭遇与古代贤士令尹子文三去相位而不怒相类比,突出余靖的安贫乐道。中间刻画世之俗人骄富贵而恶贫贱的丑态,对比出余靖的不汲名利。最后将贤人君子与公卿大夫作比较,破除世俗以势位权贵论贵贱的偏见,高扬余靖宠辱不惊,志在修德的涵养。苏洵花费了整个文章的篇幅,运用对比、衬托等多种手法,没有一字一句在分析天下形势,关心世间动态,也丝毫未提及自己的文章才能、策略抱负和治国方略,通篇花式赞美余靖“轻富贵而安贫贱”的高贵品质,直到最后才表达出希望一见的要求,可谓极尽吹捧之能事。
都说苏洵文有“纵横”气,然其在使用“内揵”之术时,与纵横家有本质差别。纵横家以“利”诱君主,不仅将有利可图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用作游说他人的武器。苏秦说齐闵王:“臣之出死,以要事也,非独以为王也,亦自为也。王以不谋为臣赐,臣有以德燕王矣。王举霸王之业而以臣为三公,臣有以矜于世矣。是故事句成,臣虽死不丑。”[4]在苏秦的这一段说辞中,他不仅以王图霸业作为诱饵打动齐王,更是直言自己效忠齐王,不惜生命的代价,出于忠心是一方面,更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名利。纵横家对于“利”的追逐是赤裸裸的,但苏洵始终将“利”放在“名”的背后,他耻于言利,耻于自求,尽管通篇夸赞余靖,也只从道德品质入手,不敢言利。《上富丞相书》:“故咸曰:‘后有下令而异于他日者,必吾富公也。’”[3]308苏洵将自己隐于人群,借他人之口对富弼宰相才能予以肯定,既表达了仰慕,又不显得“朝请暮谒,贪而不知愧”。
以干谒为目的,苏洵在抬高荐主身份,飞扬其品质时,还会使用请君入瓮的手段,将荐主塑造成一个身在高位,手握士子仕途命运,同时又礼贤下士、惜才如子的爱才形象,将其囿于陷阱之内,不得不举荐自己,如《上文丞相书》:“伏惟相公慨然有忧天下之心,征伐四国以安天下,毅然立朝以威制天下,名著功遂,文武并济,此其享功业之重而居富贵之极,于其平生之所望无复慊然者,惟其获天下之多士而与之皆乐乎!”[3]314《上田枢密书》:“执事之名满天下,天下之士用与不用在执事。”[3]319
(二)叙述交情,贴近荐主心理
叙述交情,贴近荐主心理,苏洵主要将其用于正式干谒之前已经有过交集且官位不甚显达的荐主。正如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所言:“而富公祐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以遽以言通于其前;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3]328相较于权臣面前的毕恭毕敬,苏洵在面对像欧阳修这样“位差不甚贵”的荐主时,显得从容许多。他与欧阳修的攀谈从评论其文章开始,“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3]328苏洵在欧阳修面前向来以知己自居,他在《上欧阳内翰第三书》中称:“阁下虽贤俊满门,足以啸歌俯仰,终日不闷,然至于不言而心相谕者,阁下于谁取之?”[3]337在知己面前,苏洵偶尔也会放下名声的枷锁,袒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3]337这种内心剖白,从功利角度看,可以视为一种示弱,将自己内心最隐秘角落展示给人,以拉近彼此心理距离,带着知己的面具,施行道德绑架,以退为进,使对方为自己的不荐举产生负罪感和愧疚感。事实上,苏洵也达到了他的目的,欧阳修看过苏洵的干谒信,随即向仁宗皇帝上《荐布衣苏洵状》荐举了他。
诚然,苏洵经过一番游说达到了干谒目的,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认为苏洵与欧阳修的交往是虚情假意,是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实上,从苏洵写给欧阳修的五封干谒信来看,苏洵对欧阳修的荐举始终心怀感激。苏洵得到秘书省试校书郎一职之后,写信给欧阳修表示感激:“执事之于洵,未识其面也,见其文而知其心;既见也,闻其言而信其平生”,“再召而辞也,执事不以为矫,而知其耻于自求;一命而受也,执事不以为贪,而知其不欲为异。”[3]341在苏洵看来,当初欧阳修未见其人就向仁宗皇帝荐举自己入朝为官,可知欧阳修当为知己。既是知己便不必多言,自有心灵相通之处,不管是辞官还是受官,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他认定了欧阳修一定会理解自己的选择,明白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假设苏洵最开始在干谒信中与欧阳修称知己的行为是一种拉近双方心理距离的手段,经过若干年的交往,在第五封干谒信中再论知己必定是有真心在其中的。
如果说苏洵与欧阳修的交往还停留在“内揵”层面,以获得对方信任,求取对方欢心,拉近彼此距离为目的,那么,苏洵对张方平的“内揵”就到了“钳”的地步。至和二年,张方平以在蜀地寻找人才为名,荐举苏洵为成都学官。此次荐举未有结果,然经此一遭,苏洵以为他与张方平已是知己故交。所以,他在《上张侍郎第一书》开头才会说:“明公之知洵,洵知之;明公知之,他人亦知之。洵之所以获知于明公,明公之所以知洵者,虽暴之天下,皆可以无愧。”[3]345苏洵未必不知道他与张方平的交往程度,他刻意强调二人交情之深厚,目的在于希望张方平在荐举自己的同时,还能关照他两个初出茅庐的儿子。“窃见古之君子,知其人也忧其人,以至于其父母、昆弟、妻子,以至于其亲族、朋友,忧之固其责也。虽然,自我求之,则君子讥焉。”[3]345将张方平比作古代的君子,看上去是赞扬,实际上是给他戴高帽,将张方平置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在表达完自己希望汲引的愿望和无助的现状之后,苏洵趁热打铁,将张方平捧得更高:“明公居齐桓、晋文之位,惟其不知洵,惟其知而不忧,则又何说;不然,何求而不克?轻之于鸿毛,重之于泰山,高之于九天,远之于万里,明公一言,天下谁议?”[3]346此言一出,明为褒扬,实则胁迫,将张方平在士林的公信力与苏洵一家的仕途命运捆绑在一起,逼迫张方平不得不就范,“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5]
嘉祐元年,苏洵携二子到达京城,再次写信干谒张方平。此次,苏洵没有像第一次一样,直接叙述与张方平的交情,而是假于他人之口:“子欲有求,无事他人,须张益州来乃济”,“公不惜数千里走表为子求官,苟归,立便殿上,与天子像唯诺,顾不肯邪?”[3]347这话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为自己造势。言下之意,张方平荐举苏洵是众望所归,不荐举就容易引起舆情。接下来苏洵趁着势头再次攀谈:“退自思公之所与我者,盖不为浅,所不可知者,惟其力不足而势不便;不然,公于我无爱也。”[3]347感念张方平恩德的同时,给了对方一个撤退的台阶,通情达理的表示若是能力不够和情势不便时也不必强求,但很快他又用“扺巇”法,将张方平的退路堵死了。“当此时也,天子虚席而待公,其言宜无不听用。”[3]347-348在苏洵看来,张方平此时圣眷优荣,颇得皇帝信任和宠爱,正是荐举自己的好时机,不存在能力不够和情势不便的状况。言下之意,荐举自己不仅是张方平的分内之事,还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三)描写悲惨境遇,博得荐主同情
描写悲惨境遇,博得荐主同情,通常是和前两种手段配合使用的。苏洵博得荐主同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是放低身段。如《上张侍郎第二书》中,苏洵自述听闻张方平回京任三司使,大冬天亲自跑到郑州迎接他:“昨闻车马至此有日,西出百余里迎见。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烈,僮仆无人色。从逆旅主人得束薪缊火,良久,乃能以见。”[3]348苏洵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将自己在大雪天的户外迎接张方平的可怜样貌刻画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闻着落泪,见者伤心。苏洵自述穷困悲惨至此,无非是想引起张方平的恻隐之心,“私自伤至此,伏惟明公所谓洁廉而有文,可以比汉之司马子长者,盖穷困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待其多言邪!”[3]348从苏洵的字面意思来看,他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没有任何出头的希望可言了,为今之计只能像攀缘的凌霄花一样紧紧依附张方平这棵大树。
攀缘之余还不忘叙述往日交情,将往日张方平说他文章像司马迁的言论搬出来。一方面提醒张方平自己文采斐然,是当今不可多得的人才,另一方面暗示张方平切不可忘了当日之情。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记载,他读过苏洵进献的《权书》和《论衡》之后,对苏洵说:“左丘明、国语、司马迁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3]349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对这件事也有记载:“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3]349司马迁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将苏洵与之齐名,是对其文章和韬略莫大的激励和肯定,苏洵引以为傲是人之常情,这一点无可指摘。令人诟病的是,苏洵在与欧阳修的信件往来之中,明确表示对张方平将自己比作司马迁的这一做法感到不满:“顷者张益州见其文,以为似司马子长。洵不悦,辞焉。”[3]334苏洵其后为自己的不悦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诚恐天下之人不信,切惧张公之不能副其言,重为世俗笑耳。”[3]334后又对欧阳修“子之六经论,荀卿子之文也”[3]334的评价喜不自胜。两相对比,不免让人觉得苏洵两面三刀。干谒欧阳修时对其稍加奉承以拉近彼此距离无可厚非,未必需要通过拉踩张方平来凸显俩人惺惺相惜的情感。在干谒张方平时又将此前结论推翻,将张方平对自己的赞美当作胁持对方的筹码,此实非君子所为。
苏洵博得荐主同情的另一种方式是自述年老病弱,恐无年岁以待官职;生活贫困,恐无生计以赡家庭。苏洵二十五岁开始读书,三次科举不中。直到嘉祐五年,才因欧阳修和赵抃等人的荐举得到了授试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此时苏洵时年五十二岁。得此试职之前,朝廷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以年老有病为名向皇帝辞官:“臣不幸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心。”[3]281从苏洵的干谒行为来看,他想入朝为官,加入政治序列的愿望非常强烈,为什么要拒绝朝廷的召试呢?在《上皇帝书》的同时,苏洵写信给好朋友梅圣俞,其中透露了他拒试的原因:“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3]360-361三次科举考试皆以失败告终,苏洵对通过科举入仕已经失去信心。同时,嘉祐元年,经欧阳修等人的推荐,苏洵已经名动京城。若是这次制科考试再不中,苏洵会被天下士子耻笑。他们会觉得老苏是汲于名利之人,还会觉得他名不副实,在士林中的贤名不过虚名而已。由此,苏洵称病是假,保留一个老者的尊严和面子才是真。
嘉祐五年,苏洵父子三人再次进京,对于朝廷的召试,苏洵再次拒绝。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八月“甲子,眉州进士苏洵为试校书郎”,授官原因是“本路转运使赵抃等皆荐其行义推于乡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试,乞就除一官,故有是命。”[6]苏洵对试校书郎这个官职非常不满意,嘉祐六年直接上书韩琦,要求“别除一官”。在信中老苏开门见山的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3]352至于求职理由,苏洵向欧阳修干谒时,还冠冕堂皇的说自己奔走干谒不是求名利,“实为至于饥寒而不择”,是选官程序复杂,恐自己年岁不久,不能施展抱负,做一些有利于家国天下的事情。到了韩琦这里,苏洵仿佛失去耐心一样,不愿再掩饰了,直接说试校书郎的官职太小,俸禄太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实以家贫无赀,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又况忍穷耐老,望而未可得邪?”[3]352
苏洵觉得天下人之所以都想做官,是因为做官可以“纾意快志”,而校书郎工作繁忙,需要不停的受人差遣,劳筋苦骨,催折精神。在诸多官职中,只有京朝官可以“纾意快志”。苏洵想要当朝京官,又不想通过守选、守阙的正常途径来获取,就只有乞求当权者给他一个朝京官做。于是,他大言不惭的说出了这样的话:“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3]353在苏洵眼里,朝廷的官职就像大臣的私人物品一样,可以随意赠送给别人。结合这封信的最后,苏洵“相公往时为洵言,欲为欧阳公言子者数矣,而见辄忘之为怪。洵诚惧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复忘之,故忍耻而一言”[3]353的言论,老苏恼羞成怒,口不择言的形象跃然纸上。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苏洵“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恐怕是溢美之词,苏洵对势位富贵的追求较之同辈士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干谒态度
欧阳修对苏洵产生“守道安贫,不营仕进”的错觉不是他的臆想,苏洵虽于干谒之途奔走不息,但他在交往信件中始终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砥砺名节、耻于自求的隐士形象,极其看重一个求仕者的人格独立,在语言表达上谦逊与锋芒错落,自持与疏离结合,自尊与自负交替,要求对方以礼相待,散发出以布衣交诸侯的卓伟气势。虽以干谒求仕为目的,然苏洵文读起来理直气壮,风骨凛然是不争的事实,苏洵之文气盛已经成为共识,产生这种落差的根源在苏洵的干谒态度。
(一)以“王佐才”自命
宋代与士大夫共商国是的国策极大地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空前膨胀,统治者的倚重激发出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充分体现了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感。这种强大的信念感推动着文人士子们将运用儒家真理参与国家政治,干预政策制定,匡正君主统治的政治热情付诸行动,他们试图用文化权利抵抗政治权利,以“王佐才”“帝王师”的姿态运用儒家的行道手段对现实政治进行干预,甚至于达到以“道统”钳制“政统”的目的。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1]7059和欧阳修“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1]7161的豪言壮语都出源于这种信念感。
苏洵同样有着强烈的“王佐才”和“帝王师”意识,他在干谒书信中数次以贾谊自比。贾谊佐汉文帝,天下和洽,后被谗言所害,贬为长沙王太傅,郁郁而终。苏轼《贾谊论》:“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谊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7]深惜贾谊之不遇,苏洵正是认为自己与贾谊一样具有“王佐之才”,所以在干谒过程中颇为自信。《上韩枢密书》:“太尉执事: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3]301《上皇帝书》:“贾谊之策不用于孝文之时,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余论,而施之于孝武之世。夫施之于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俞孝文之时之易也。臣虽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胜越次忧国之心,效其所见。”[3]292-293苏洵将自己献上的十条治国方略比作贾谊之策,预计这些计策一旦实施便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为国家计,为社会计、为生民计,怀揣着经世致用的理想,保持着忧国忧民的态度,推行着利国利民的主张,苏洵内心必然会产生崇高感和自傲感,我手写我心,这种雄壮的、不可遏制的情感一旦化为文章中的一词一句,定然理直气壮,读起来气势凛然。
庆历六年,举制策不中的苏洵心灰意冷,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开始闭关读书,“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3]520。苏洵在写给欧阳修的书信中详细叙述了这近十年学术生活:“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3]329苏洵觉得胸中之言不能自制,形之于书面的文字都是经世之文,治世之策,而非科举要求的声律辞赋之学。通览苏洵流传下来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单纯表情达意的抒情文章,其核心都是关于经世之术的。欧阳修《举布衣苏洵状》将苏洵文章的特点总结为“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3]521,就文章内容而言,恰如其分。
苏洵的干谒对象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也是其文章的实用价值,他们荐举苏洵时的夸赞也多从“王佐才”入手:“翰林学士欧阳修得洵《权》《衡》论策二十二篇,大爱其文辞,以为虽贾谊、刘向不过也。”[8]雷简夫是苏洵好友,由于他本人经杜衍荐举才步入仕途,所以非常注重提携和奖掖后进。苏洵干谒雷简夫,两人一见如故,雷曾数次上书欧阳修、韩琦等人,称苏洵具有王佐之才,希望他们多加提携。雷简夫《上张文定书》:“简夫近见眉州苏洵著述文字,闻其如《洪范论》,真王佐才也。”[9]108《上韩忠献书》:“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9]107《上欧阳内翰书》:“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尝著《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计。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9]109根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记载,苏洵干谒过的欧阳修、韩琦等人也数次称苏洵堪比贾谊:“因论苏君:‘左丘明、《国语》、司马迁之善叙事,贾谊之明王道,君兼之矣。远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因以书先之于翰林欧阳永叔。君然仆言,至京师。永叔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名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为过也。”[3]522
自信的人有时容易流于自负。晚唐五代兵戈战起,儒家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北宋立国,亟需通过重整儒道来恢复社会秩序,于是在各项制度上都向儒生倾斜。士人纷纷以儒者自命,对阐发儒道乐此不疲。苏洵和天下士人一样,觉得别人对儒道的阐发不符合圣人原意,自己才是真正能够领会圣人意图的人,是儒道正统传人。苏洵在与欧阳修的书信中说:“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扬雄称于世;扬雄之死,不得其继千有余年,而后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将谁与也?”“天下病无斯人,天下而有斯人也,宜何以待之?”[3]334苏洵此言即列出了正统儒学的传承谱系,虽然使用的是疑问句,问“天下而有斯人,宜何以待之?”然此封书信以干谒为目的,意在表明自己就是继韩愈之后的儒学正统传人,理应受到礼遇。儒家一向以济世治国为已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苏洵也说“天之所以与我者,夫岂偶然哉?”[3]317天命攸归,舍我其谁?苏洵自信于其儒道传人的身份,认为自己通过荐举获得一官半职以行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他表现得非常自信,甚至自负,写起文章来也理直气壮,掷地有声。
(二)砥砺名节
受到宋代砥砺名节社会风气的影响,苏洵的自负又与谦逊相交互,形成错落有致、层峦叠嶂的文章结构和曲折往复、委婉舒缓的文学风格。宋代文人尚名节,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倡导之功。《宋史·范仲淹传》:“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1]7095可见范仲淹的言传身教对当时北宋砥砺名节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倡导作用。事实上,当时以名节自重的名士还有很多,司马光称赞富弼的“温良宽厚,凡与人语,若无所异同者,及其临大节,神色慷慨,莫之能屈”[10],韩琦评价欧阳修:“自任言责,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然。”[11]
北宋文人砥砺名节与他们社会主人翁意识的觉醒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只有形成完善人格,达到社会理想境界才能够担负起建立社会话语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参与国家治理,监督政治决策的责任,达到干预甚至压迫政权的目的。正如欧阳修所言:“所谓名士之节,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牵于苟随,而惟义之所处。白刃之危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为,而惟义之所守。其立于朝廷,进退举止皆可以为天下法也。”[12]不管进退出处,砥砺名节都成为宋代士子追求的最高境界。苏洵一向以名节为重,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并序》中称苏洵“君之行义修于家,信于乡里,闻于蜀之人久矣”,“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3]521,可见为了在士林中有良好的名声,苏洵始终身体力行,存好心,行善事。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中也说“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3]521,可见苏洵在士林中的名声操守确实很好。
“内圣外王”一向被视为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生成路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外王”始见于《庄子·天下》,但对此阐发最深刻,践行最积极的当属儒家,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和谐一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至高境界。从孔子开始,内修德行,外施德政就构成了内圣外王之学的主要内容。孔子认为周末礼崩乐坏的根源在于人心的沦丧与麻痹,由此重建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更改社会制度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环境,而应当扭转世人心理,通过修养德行,塑造人格,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水平,改善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也即通过“内圣”达到“外王”。“内圣”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化,到了宋朝,“道统”领袖们将内在的修养外化为行为上的自持名节,以一个人在士林中的名声好坏判断其内心修养的高低。不可否认,砥砺名节对宋代士人自我完善,自我约束具有促进作用,对完美人格的自我要求和督促与承担社会责任自觉性的养成具有一定关联。然而,外在名节与内在修养不具有同一性,在两者之间直接划等号会造成部分士人不注重人格而汲汲于名节的行为,进而在社会上形成舍本逐末,矫情饰言的不良风气。若名节考察在人格评定中所占比例逐渐攀升,名节对人格发展的约束力就会变成枷锁,使人不敢正视内心对名利仕途的正当欲望,对其施行或压制,或伪饰的手段。若被压制的欲望不断膨胀,与对名节的操持激烈抵牾便会扭曲人格,分裂精神,在文章中表现出自持与自负相结合,锋芒与谦逊相错落的矛盾。从正面来说,由此形成的文风曲折跌宕,一波三折,从反面来说,这种人格的冲突表现在文章中不免让读者对作者产生两面三刀,虚伪矫情的认识。
这种欲望与名节的冲突在苏洵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苏洵数次干谒权臣、好友来看,苏洵渴望加入政治序列,参与国家治理的意愿非常强烈,但仁宗皇帝召试舍人院的时候他还是明确拒绝了,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最关键的一点则是他认为朝廷的不信任是对他名节的一种侮辱,既然朝廷不信任他,他宁愿退居山林也不“苟进以求其名利”,这种强烈自尊意识折射出的就是他内心的风节思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技巧拉近双方距离,取信于荐主,苏洵在干谒过程中的态度始终是,绝不会牺牲自己的风节操守换取仕途经济。在被授予试校书郎之后,苏洵写信给欧阳修除了表示感谢,最大的请求是希望欧阳修能以宾客之礼接待他,不要把他当成奔走之吏:“古之君子重以其身臣人者,盖为是也哉!子思、孟轲之徒,至于是国,国君使人馈之,其词曰:‘寡君使某有献于从者。’布衣之尊,而至于此,惟不食其禄也。今洵已有名于吏部,执事其将以道取之邪,则洵也犹得以宾客见;不然,其将与奔走之吏同趋于下风,此洵所以深自怜也。”[3]341-342官场有职位高低,身份低微的小吏见到手握重权的大臣必须行拜见之礼,论道则不为官位名利所限,苏洵希望欧阳修拿出论道的姿态平等的和自己交往,而非像对待下级一样,疾言驱使,充分说明了他的布衣之尊。
(三)掩盖名利欲望
苏洵在数封干谒信中都表达了淡泊名利、耻于自求的态度,如《上韩舍人书》:“洵自惟闲人,于国家无丝毫之责,得以优游终岁,詠歌先王之道以自乐,时或作为文章,亦不求人知。”[3]349“自闲居十年,人事荒废,渐不喜承迎将逢拜伏拳跽。”[3]350即使秉持着“不求人知”的干谒态度,苏洵还是无法否认其内心深处强烈的、无法遏制的参政欲望,所以,他必须采取一些手段掩盖欲望,保持名节。苏洵最常用的手段是博引史实,引经据典的用古人言和古人行来隐喻其干谒意图。中国古代历来有“崇古”的传统,北宋文人在诗文革新运动“回到三代”思想的影响下,更喜欢援引“三代”史实佐证自己的观点。
《上田枢密书》是苏洵以古人言隐喻干谒目的的代表作,文章议论古今,恢弘恣肆。书信一开头就从天命观出发,以为圣贤乃天命之,非人力可以阻挡。“尧不得以与丹朱,舜不得以与商均,而瞽瞍不得夺诸舜。”[3]317以尧舜禅让的故事为论据,让人难以反驳。苏洵说尧舜,实际上是以尧舜比自己,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之意。既是天命之人,如今不得重用,应责有攸归。接着苏洵就从“责”上做文章,他把违背天命分为三种情况:弃天、亵天和逆天。前两种情况“责任在我”,后一种情况“责任在人”。苏洵认为,上天既然选中了“我”,“我”就应该积极进取,替天行“道”。如果“我”置之不理,隐居山野这是“弃天”;如果“我”为了功名利禄卑躬屈膝,曲意逢迎,这是“亵天”。“我”只能尽心尽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抓住一切可以替天行“道”的机会去行事。若是“我”这样做了仍然没有被任用,那责任便不在“我”了。接着苏洵又用孔、孟的干谒事迹对上述三种责任作了区分。春秋战国时,孔子不见于卫灵公和鲁哀公,孟子不见于齐宣王和梁惠王,可他们终生不倦于求仕之路,从不曾感到苦闷和沮丧,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被重用的根源不在自己。孔、孟是天选之人,尽最大努力奔走于仕途,这是顺天而为。所以,他们不以干谒为耻,而上述四个君主“逆天”的责任千秋百代也推脱不掉。
苏洵堂而皇之的讲了一堆道理,表面上看是泛泛史论,实际上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并做出解释,以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苏洵要仕进,却屡试不中,他自比贾谊,愿以布衣为帝王师,不甘心“自卑”“自小”以“亵天”,所以数次奔走干谒。这样做不是渴求名利,是顺应天意,寻找施行大道的途径和机会,不免“弃天”。为不落人口舌,苏洵以孔、孟自比,隐括自己于圣人之列的同时,为自己干谒留有余地,疏解内心的愧疚感和耻辱感。
苏洵用以掩盖名利欲望的另一种手段是以隐士自命。苏洵制策不中,绝意科考,在家读书,潜心钻研数十年,这段经历在他的干谒书信中被反复提及,也让他一直以隐士自命。他在《上田枢密书》中说:“数年来退居山野,自分永弃,与世俗疎阔,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3]319又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途之中,而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3]328苏洵与前人为隐逸而追求清贫不同,他的隐逸生活建立在生活安逸,具有良好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他在数封干谒信中都提到了这一点:“洵有山田一顷,非凶岁可以无饥,力耕而节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予者不忍弃,且不敢亵也。”[3]319有了田产,就没有了口腹之忧,不用再为了温饱奔波。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给了苏洵追求人格独立的空间,也给了他在干谒过程中不卑不亢、不屈不挠的底气。换句话说,苏洵频频在干谒信中展现他富足的田产,是为了显示他与一般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奔走干谒的士人不同,他渴望的是参与政治序列,为国求发展、为民谋幸福,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私利。欧阳修在荐举苏洵时说“为时得士,亦报国之一端”[3]521,欧阳修看重苏洵之才能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欧阳修在苏洵的干谒信中看到了他以裨益朝廷为目的,为生民立命的政治理想和伟大胸襟。
隐士身份为苏洵的奔走干谒披上了美丽的外衣,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纵观苏洵流传下来的所有作品,除了在干谒信中表现出隐士之风外,几乎没有直接表达隐逸情怀的诗文作品。苏洵对于隐士身份的看重远远大于他对隐士情趣的追求,他只是想借用隐士的外衣披盖出仕的真心。苏洵以隐士标榜自己,不仅可以要求各级官员以礼相待,还能使自己游离于官场制度之外,不被世俗权力所规约。以隐士的身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进言献策,一方面可以将自己从屡试不第,汲汲于名利的布衣身份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为自己重新营造一个为公卿排忧解难,为朝廷出谋划策的高士人设。比如《上韩舍人书》,开头指出北宋王朝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的现实情势,指出两制官员为解决革除弊病所做的努力以及未有良策的焦虑状态,接下来就描述自己的隐居的状态,将自己定义为朝廷的解忧人。苏洵反复强调自己无意于仕途,所以无需忌惮上位者的威严,可以用以旁观者的视角指陈时弊,这种态度他在写给文丞相的信中也有所袒露:“不见用于当世,幸有不复以科举为意,是以肆言于期间而可以无嫌。”[3]314
以上,苏洵数次科考不第,渴望通过荐举跻身士林。苏洵的干谒活动通常以书信为载体,而非面对面的游说,由此情感表达在他的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苏洵表达情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表达仰慕,抬高荐主身份;叙述交情,贴近荐主心理;描写悲惨境遇,博得荐主同情。从苏洵的干谒技巧可知,他对势位富贵的追求并不亚于同时代的其他干谒者,然苏洵之文多谈大义,少谈干进,读起来理直气壮,气势逼人,这与他在书信中表现出来的干谒态度有关。苏洵在信中自比贾谊,认为自己有“王佐才”,是继韩愈之后的儒道传人,堪以布衣为“帝王师”,所以他不以自求为耻,表现得十分自信。同时,宋代砥砺名节的社会风气压制着苏洵内心不断膨胀的名利欲望,使其收敛锋芒,不得不引经据典,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隐士自命掩盖自己对仕途经济的渴望,形成自信与谦逊错落,自持与疏离结合,曲折往复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