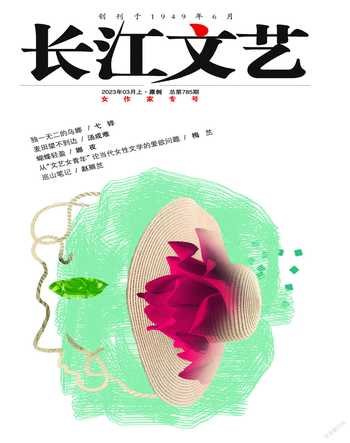巡山笔记
赵丽兰

老木聪
人勤春来早。一觉醒来,屋外的梨花,开白了一树,花碰碰的。那热闹劲儿,着实惊到了老木聪。昨夜,大多都还是花骨朵。真不敢相信,春天已经到了最热闹的时候,山野里暖洋洋的。即便没有雨,春天,该开的花,还是一朵一朵争着盛开。蜜蜂,一头钻到花蕊里,就不肯出来。老木聪在手机上,查看了一下日历,今天惊蛰。
醒树风就刮过好几遍了,梁王山上的树,早就被刮“醒”了。醒得早的树,已经满树葱茏,叶芽儿都长成宽大的叶片了。云南松、华山松、桤木、冷杉……滇重楼、野党参、龙胆草、猪拱菌……獐子、麂子、白腹锦鸡……树木、药材、鸟兽飞禽,都被一阵一阵的风,刮醒了。梨树、桃树,已经开花,一个转身,就会迎面撞到一树一树的花。醒树风继续刮,刮到四月,老君殿附近的杜鹃花也开了。那些爱花的人,相约着驱车上山来,钻到花丛里拍照。人与自然,在悠缓的节奏里,简单而满足。
天是蓝的,干净极了。惊蛰,雷始声,如果真的下一场雨,从天上落下来的水,想必也是蓝色的吧。不然,抚仙湖的水,咋会那么蓝。哈哈,真是突发奇想。生活在梁王山上,抚仙湖畔,真是奢侈,奢侈到常常让人产生许多突发奇想的美好。美好的事情,不只是天的蓝。老木聪看见,两只异色瓢虫叠在一起,正在交尾,忘情地享受着甜蜜。它们在红景天的叶子上一窜一窜地上下摆动,有时,雌虫会俯低前身,把尾部高高翘起来,贴在雌虫尾部的雄虫也跟着高高地翘起来,在背上颠簸着享受美好,玩得很嗨。
老祖说,春雷惊百虫。越过冬的虫卵,就要开始卵化了。虫子是不是已经感知到雷声了呢?谁知道呢,一场风,或许就会吹来一场及时雨。老晏不是说,梁王山的牛,都发情了么,两头公牛,追着一头母牛,跑过了几道山岭。发情的,何止牛呢?两只瓢虫,这么逍遥。
老木聪是菜花坪林点的护林員。菜花坪林区距市区20公里,相较老君殿林区,海拔稍低一点,平均海拔2600米,但仍终年潮湿、阴冷。老木聪每天的日常工作和其他林点无异,一样是巡山管护、苗木抚育和监测火情。每天在山上来回走二十多公里,半个月就穿坏一双胶鞋,一样的铁脚板。老木聪最大的爱好,喜欢喝口小酒。
很久没落雨了,让这个花碰碰的春天,显得有点急促,心急火燎的。梁王山的护林员,都盼着能落一场及时雨,这样,他们就可以等雨下透了,相约着,放心地喝一场大酒,即使醉了,也不误事。杏花春雨中,春酒就可以上桌了。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老木聪想不通老祖说过的这句话,春天,这么金贵的雨,既然比油还贵,咋还能满大街流呢。但是,老祖说的话老木聪都信。上学后,他才知道这话不是老祖说的,是一首打油诗。“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滑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这是明朝才子解缙的一首打油诗。春天,下了一场雨,有人不小心滑倒了,路上的行人大笑。一个又温暖又潮湿的春天就这样来了。小的时候,春雨,就是在老祖念着这首打油诗的时候,一场一场落了下来。
这些天去巡山,老木聪一路走,一路念着“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抬头看看天,天空,连一朵云都没有。这个春天,在梁王山,一直都没盼下来一滴雨。护林的任务无形中就更重了,每天都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巡山,就更不能有半点马虎。
每天天一亮,随便吃点东西,老木聪就出门巡山了。临上山,老木聪都要在梨树下站一会儿。梨树旁,有一尊坟,坟里,埋着他的老祖。老祖过世很多年了,巧的是,就埋在菜花坪护林站旁边。老祖就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直活在老木聪的生活中。
梁王山上,植被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有八百余种植物,其中以草本植物为多,木本植物主要是次生林华山松、干香柏、云南松,灌木丛主要是金丝桃属、小檗属、蔷薇科悬钩子属和蔷薇属。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在梁王山上,一脚踩下去,就会踩到一棵草药。续断、草乌、龙胆草、黄金、老鹤草、珠子参、青风藤、鬼吹萧、小白及、鸡脚参、兔耳一枝箭、防风等中草药遍布山野。因地制宜,老木聪在护林站附近,养了几十窝蜜蜂,品种是中华蜂。蜂箱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平整的草丛中。老木聪养的蜜蜂采的大多是中草药的花粉,酿出的是药蜜。梁王山上的蜜蜂,唯独不采蒿枝花。山外,经常有人来买蜜,夸他的蜂蜜好。有人好奇,问老木聪,养这么多蜜蜂,一年有很多收入吧。老木聪答,钱么,多也使,少也使。在山上养蜜蜂,就是图有个伴,养了么,听听它们嗡嗡嗡的声音,看着它们飞飞玩玩。在山上待久了,人反倒变得简单了。思考问题的方式自觉地切换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鼻子闻到的只有草木散发出来的清香,眼睛看到的只有山野的辽阔悠远。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自然而然就相通了。那些世俗的斤斤计较,反倒不值一提。
夏天,雨水一落地,护林的任务就相对轻松一些。这个时候,老木聪会选择在雨天学习《森林法》《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枯燥与新鲜,得到了相对的平衡,就不会陷入到那种空荡荡的感觉中。时间,也会过得快一些。有时,老木聪什么也不做,就坐在梨树下,听听树林里鸟的声音。有些鸟嗓门大,声音清脆,叫声传出很远,却依然嘹亮明晰。山野里的空气,本身就清甜。何况,还有这么多的蜜蜂相伴。这样一想,周而复始的工作,也就不枯燥了,甚至还带点甜。雨水一落地,就可以喝酒了。醉了,就坐到梨树下,和坟堆里的老祖说说话。有时,老木聪会跟老祖说巡山中碰到的趣事。当然,也会说到来林区偷挖草药或盗伐树木的家伙。直说到繁星满天,或皓月当空。山野之间,那些有趣无趣的事情,在老木聪的复述中,就变成了一个个故事。
这个早晨,往山上走出去二三十米远,老木聪听到有人在梨树下喊,声音带着三月百花盛开的欢喜,以及草木间露水的湿气。来人一边拍门板,一边喊。老木聪、老木聪……我提酒来了,今日我两个整几口。
风将喊声从梨树下送到树林间,继而,穿越一片绿闪闪的华山松,扩散至整个山野。
喝你个鬼,这几日不喝,等雨水落透了再说。老木聪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继续往山上爬。声音有些急促,却又干脆利落。风,吹过森林,哗哗地响。枝叶碰擦,干燥、松脆。黄了的松针落下来,一地金黄。一只鸟飞翔而过,雪白的胸脯贴紧天空,一个俯冲,消失在森林里。扑闪而过的飞鸟,有那么一瞬,老木聪以为是一朵云掉落在了林间。想象着,不一会儿,一场及时雨就下来了。
两个人的一问一答过去,森林里只剩下了鸟的鸣叫。仔细听,会听到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踩着一地金黄的松针,渐渐远去。抬头看天,想,这几日会不会下一场春雨。思绪一分散,啪嗒啪嗒的脚步声,仿佛也不存在,从森林中消失了。这天,老木聪穿了一双酷酷的登山鞋,走起路来,带着一股风。今天,他穿了一身迷彩服,遮阳帽,也是迷彩的。晨光中,走着走着,就走成了森林里一棵行走的树。
这天,提酒而来的,是山下石门村的老晏。老晏除了忙家里的田地活,农闲的时候,就到山上去给牛喂盐巴吃。1996年,附近的村民养了十几头本地黄牛。不知怎么回事,有一天,牛全部走丢在了山上。山深林密,树棵子又厚,走失了就再也没找回来。二十多年来,这群牛,就成了梁王山上的野牛,没人管,也不知道是哪家的,越来越野。逐年繁殖,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头。这三十多头牛,分散成几群,十多头一群。因为怕人,选择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每年打春以后,就开始繁殖。有些牛,为争夺配偶权,相互追撵,撵过几道岭子去。冬天,牛选择在背风处栖息,夏天,为了防蚊子叮咬,专门找炝风处。
牛在山野里行走,碰到新鲜事,都保持警惕,唯独不怕老晏。老晏是这群牛的好朋友,老晏经常带上几包盐巴,爬到梁王山上,在牛经常活动的地方撒些盐巴,等牛来吃。牛吃了盐巴,可以杀死体内的寄生虫,膘就长得又快又厚。牛对老晏欢喜得不得了。远远地,见到老晏,就“哞哞”地唤他。
每次去山上喂牛,路过菜花坪护林站,老晏就去找老木聪摆闲。两个人经常摆着摆着,就来了兴致,就着一碟花生米,喝起了小酒。老木聪有原则,雨水不落地,堅决不喝,怕误事。这一坡的树,都要他时刻保持清醒。说不定一阵风刮过来,就会着火。如果喝醉了,那还了得。在他之前,菜花坪管护站的护林员是老周。整个林区都喊他铁板脚。一次,村民烧秸杆,引起山火。扑火队赶来之前,老周一个人扑进大火里,鞋子烧坏了,烫着脚底板也顾不上。一股缓慢的坚忍藏在老周体内,他的脚在火里被烫伤了,嘴里,却喊不出疼。俗话说,没有帮样,有底样。铁板脚一直是老木聪要追的标杆。老木聪爱喝酒不假,梁王山落不透雨,老木聪决不喝酒,也不假。
这个早晨,老晏吃了闭门羹,也不急。他晓得老木聪的脾性,特别是多少年坚守的原则,雨水不落地,坚决不喝酒。老晏索性靠着梨树坐下来,抬头望天。那神情,仿佛就为了专等一场雨落下来,那样,就有了和老木聪喝酒的充分理由。这个早晨,梨树下等雨,很美,却也有些失落。雨,怕是一时半会儿落不下来。提来的酒,只好一个人喝了。老晏拧开瓶盖,喝了一口。五十多度的包谷酒,有些辣,热热地从咽喉滑入肠胃。一个人喝酒,再香的酒,终不带劲儿。一瓶酒,喝了一半,老木聪还没回来。太阳升到中天,风越刮越大,有些变天了。老晏起身,往山上走去。他始终记挂着山上的那群野牛,前不久,他带着盐巴,去山上喂牛,两头公牛,为了争夺一头母牛,牛气冲天,撵打着跑过了几道山岭。草木牲畜,飞禽野兽都醒了。
此时,老木聪已经爬到山顶。往山下看去,山下的湖泊、村庄、城市、高速公路,以及不远处的宝华寺,笼罩在一层薄薄水雾中。上午还蓝盈盈的天,中午后,便刮起了大风。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惊蛰,春雷始鸣,万物复苏,乍寒乍暖,雨水渐多。山顶上,风更大,卷起一地的落叶。老木聪的迷彩帽,被风吹跑了。帽子像一颗种子,被风吹着,往自己喜欢的地方飞去。老祖说,五月端午,在土里插根棒头,都会发芽呢。哈哈,就快下雨了,让帽子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发芽去吧。山林里,草木禽兽,包括被风吹跑的帽子,都跟人如此相近相惜。
中午一点多,老木聪往山下返回。下个月,就是清明了,护林防火任务又重了,得先提前把一些工作做细做实,防患于未然。沿路,得顺道统计一下林区内的坟墓,查看一下周边的具体情况,并做好登记。每年清明,总是有些群众不听劝说,焚香烧纸,极易引起火灾。在一尊张姓坟前,碰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是前不久回来过年,明天要回广东打工了,来看一下过世的亲人。老木聪嘱咐男人不要抽烟,也不要烧纸焚香,文明祭奠。男人主动掏开口袋给老木聪看,说没带打火机,自己也不抽烟。
下山的路上,老木聪一会儿想想雨,一会儿想想老晏提来的酒。这么好的酒,怎么能让老晏一个人喝呢,真是可惜。想着想着,就想到了老祖。好久没跟老祖讲故事了,因为好久没喝酒了。
风仍然刮得紧,刮来许多云朵。返至半山,一声响雷从山顶上滚过来,咔嚓一声,在头顶上炸开。惊蛰、惊蛰,时令正是太神奇了。一场及时雨,早就从昨夜那场吹开梨花的风、那两只交尾的瓢虫开始了。甚至,老晏坐在梨树下喝酒,也是一场雨开始的前奏。冬春交替,大自然的变化是如此新鲜。雨点噼噼啪啪落下来,打在树叶上。四野一下子都淹没在雨声中。晴的时间久了,一落雨,空气里就浮上泥土的香味,让人很踏实、安全。种子要发芽了,这雨来得真是时候。老木聪听见,树林里有人在欢呼,下雨啦,下雨啦。他甚至感觉到,欢呼的人正手舞足蹈,不亦乐乎。雨点落在老木聪的迷彩服上,一会就湿透了。他甚至不想找个地方躲雨,只想让雨水洗洗身上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尘埃。雨滴顺着脖根骨淋进脊背里,凉凉的,舒服极了。老木聪感觉,他的脖根骨和脊背,在一场雨中,变得新鲜了。有一次巡山,下了一场大雨,森林中,碰到两个捡菌子的女人。两个女人叽叽喳喳一路说着笑着,大雨铺天盖地落下来,也不找地方躲雨。她们说,让雨水淋一淋,才新鲜呢,她们要和草木一样新鲜。两个女人,唇红齿白,已经够新鲜了。雨水淋一淋,水淋淋的,会新鲜得要命。哈哈。
今天的心情都被雨占据了,湿漉漉的,冒着湿气。林子里时不时地会窜出来一只小貂鼠,或者一只野猫,它们的皮毛也被雨淋湿了,光滑油亮。此时,如果老晏提酒来访。是否就席地而坐,在松针上摆一桌,喝上两盅。一场雨落下来,一些思绪突然而至,又突然远离。人的情绪,总会被天气所左右,真是奇怪的事情。怪不得,熟悉不熟悉的人一见面,都拿天气说事。聊天,聊天,原来是这个意思。
前年春天,雨水相较今年,多出二倍。几场春雨后,梁王山上的刺脑包、梁王茶、老白花、沙松尖、蕨菜、金雀花、棠栗花……都争着一个劲儿地长。净莲寺防护站的李大姐,不仅做得一手好菜,酒量还出奇的大。年轻一些的时候,以公斤级论。李大姐在春雨里,就着山野里的野菜,以及春节腌制的腊肉,做了一桌丰盛的菜。百花盛开,春酒上桌。那晚,一桌七八个人,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酒过三巡,有人问老木聪,今晚回去,是不是又要去找老祖讲故事了,千万不要太孤独噶,不然把老祖讲哭了。众人哈哈大笑,都知道这是老木聪的一个典故。老木聪刚来菜花坪护林站的时候,不习惯山里枯燥的生活,孤独得慌。一次,雨水落透了,老木聪就着几盘山茅野菜,喝醉了酒,一个人跑到梨树下和老祖講故事。讲着讲着,讲到孤独处,就哭了。第二天醒来,发现在梨树下睡了一个晚上。后来,整个梁王山的护林员都知道了老木聪给老祖讲故事的事情。再后来,就成了典故。自那以后,老木聪为孤独找到一个安放的空间,孤独的时候,就到梨树下找老祖说话。如此,他的孤独得到了有效的释放和保护,安全而踏实。
是日晚,老木聪翻开笔记本,写当天的巡山笔记。这已经是他来菜花坪守护站的第四本巡山笔记了。每天写得并不多,少则三五行,多则六七行。
3月5日,星期五,晴,惊蛰。一大早,老晏约酒。天干物燥,小心为妙。雨水落地之前,决不会喝一口酒。马上清明了,得防患于未然。清明防火,是一年中防火的重中之重。中午一点多,顺道去数林区内的坟。在老林场附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坟头上跟亲人告别,说是明天就要到广东打工了,也算是提前上上坟。叮嘱他要文明祭奠。他主动掏开口袋让我看,说是没带打火机。周边村子里的群众,防火意识越来越强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没白做。回到半山,一个响雷下来,雨也跟着噼哩啪啦下来了,真是一场及时雨。不想找地方躲雨,让雨淋一淋,人会和草本一样新鲜呢。惊蛰,惊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真是太牛了。
今天一切正常,没有发现火险,也没有安全隐患。
雨水一落地,就等于冬天结束,真正的春天来了。从惊蛰的这一场雨开始,老木聪的心就一直敞亮着。每天,他还是会去梨树下站一站。像是在等待一个什么消息,或者奇迹。梨花谢了,枝头上冒出脆绿的果实,风吹一吹,雨淋一淋,一天一个样。几场雨过去,从最初的拇指般大小,长到酒盅般大小了。长得快的,还没到六月,就有小碗般大小了。有雨没雨,森林里,一切都没有放弃生长。碰到有人来林点,老木聪会摘几个梨,让人家解解渴。
七月,雨水早落得透透的了。每一脚踩下去,都会踩出一个泉眼,像大地上的一只只水汪汪的眼睛。四野一片清明,到处都是鸟的鸣叫。森林里,热气腾腾的。有鸟,会来啄树上的梨。这个品种的梨,皮硬,它们啄不动。
大酒,终是喝了一场。巡山的时候,捡到许多菌子。老木聪主动约的老晏。喝的是头年梁王山上摘的金樱子泡酒,酸甜酸甜的,很是过瘾。说是滋阴壮阳呢。谁知道呢,喝得醉人的酒,都是好酒。两个人在梨树下干杯。梨已经完全熟透了,有的已经掉到地上。老晏说,那两头公牛,最后是个子小那头赢了。两头牛追过几个岭子,个子大那头,可能是太胖了,跑不动,放弃了。母牛已经怀上了小牛,一侧肚子已经明显变大,明年初就生了。
暮色落下来,一壶酒已经喝光。最早的一颗星星,亮了起来。
送走老晏,老木聪回到梨树下,对老祖说,来年,要栽一棵柿花树,让鸟来啄。
大潘
大潘笼着袖子,在瞭望塔的塔顶上站了一会儿,眼睛突然有些潮湿,就快退休了,突然舍不下山中的这一切。
梁王山是滇中第一高峰,大潘所在的林区老君殿,是梁王山最高峰,海拔2820米,年平均气温11.7摄氏度,是梁王山管护站条件最艰苦的林区。昨夜,瞭望台外,风呼呼地吹,屋子里却暖洋洋的。三十多年了,梁王山上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被他爱过了一遍,连那只夜夜哀嚎的猫头鹰,都被他爱了一遍。比起以前,现在护林站的条件好多了。刚刚到护林站的时候,哪有什么房子。一块油毛毡,几根树桩,几个石头,几块席子,搭成个窝棚,就是护林站了。夜里,寒风呼啸,冻醒了,一睁眼,棚顶上,一天空的星星,比灯笼还大。有时,还会听到夜里有各种各样的嚎叫声。风,会找裂口灌进去,有时,会灌进狭窄的墙缝,撞击墙壁后,反转而出,像是人的哀嚎声,听得人心惊胆颤。在梁王山老林场的时候,好几个夜晚,大潘总是听到一阵一阵的怪叫声,从大门那个地方传来。哦……呜呜呜……哦……声音带着颤音,像是一个人带着哭腔,在唱歌,哀哀怨怨,婉婉转转,却又节奏分明。这是大潘在梁王山上,听到的最惊悚的声音了。后来,这声音终于被破译,是夜晚的风灌进碗口粗的空心铁门柱,在圆形的门柱内形成共鸣,撞击柱壁后,又呼啸着冲出门柱。撞击柱壁时产生了哦……呜呜呜……哦……的声音。
夜晚的山林里,常常听到的是猫头鹰的叫声,凄凉、悦耳、阴森,像是封冻的山腹,突然裂开一个口,迸出一个声音,让心猛地一缩,就无端地又慌又疼。有一种猫头鹰,当地人唤作老悲恶(音:wu),叫起来的时候,发出“悲恶、悲恶”的叫声。阴森森地在空旷的夜空响彻四野。刚到梁王山的时候,大潘一听到猫头鹰的叫声,脊背就一阵一阵发凉。如今,听不到猫头鹰的叫声,大潘会觉得那个夜晚少了些什么,空荡荡的。八十年代,山上还有狼,有护林员是亲自见到过。大潘倒没碰上过。听其他护林员说,狼的眼睛,绿荧荧的。抬着头,对着满天的星星,仰天长啸。嗷呜、嗷呜……一声接一声狼嚎,悲怆、孤独,又瘆人又凄凉。
山下的人,总觉得冬天不下一场雪,便没有意义。对大潘来说,一进入十一月中旬,冬天就开始了。雾凇出现在梁王山的时候,已经是隆冬了。一早起来,瞭望塔的窗子和护栏上,都挂上了长长的冰条。大潘爬到瞭望塔的最高处,用望远镜监测梁王山上的动态。再过一星期,就是冬至了。昨天还晴朗的天,一早起来,放眼望去,玉树琼枝,晶莹剔透,满山都是雾凇奇观。雾凇俗称树挂,严寒的季节里,空气中的水气遇冷凝华而成。梁王山上,树木繁茂,每年冬季,都要出现雾凇奇观。一朵粉红的山茶花,刚盛开,就被剔透的冰花裹住了。望远镜里,大潘眼前,满山都是空茫茫的一片白。飞禽走兽,虫蚁鸟儿,都不见了踪影,只剩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
有一年,下了一场大雪。一早起来,大雪封门,门板被雪埋了一半。一场雪,在大潘的记忆里,不是阳春白雪般的浪漫,而是灌注身心的紧张感和危险。他想,他就要被冻死在大山上了,即便冻不死,也会孤独死掉。除了雪落的声音,整个梁王山,万山寂静。雪下了整整三天,第四天,雪停了。第五天,太阳出来了,雪慢慢融化。被大雪封住的门,可以推开一道缝了。大潘侧身挤出门,往森林里走去。被雪覆盖的梁王山显得更加辽远空旷,看上去,显得有些陌生。森林里,随处可见被大雪壓断的树枝,正在咔嚓咔嚓断裂。高一些的松树上,挂着长长的冰凌。矮一些的树木,被雪压得更低了。森林里,被封冻了几天的飞禽鸟兽,也出来活动了。麂子、野兔、小貂鼠……它们蹦跳着穿过白雪覆盖的森林,在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有鸟,从枝头落下来,在雪地上觅食。这些可爱的生灵,像是童话世界里的小精灵。一只灰兔从大潘的身旁窜出去,它机灵的样子,让大潘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不见了。
大潘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雪地上,有一串脚印,一朵一朵的梅花状。左边的脚印明显比右边的脚印浅。凭经验,大潘猜测,这应该是一只受伤的狗,刚刚从雪地上走过去。大潘尾随着脚印,一路往森林里寻觅。果不然,一只小奶狗倒卧在雪地上,伸出长长的舌头,正舔伤口。大潘上前,拍拍它的身子,贴卧在雪地上的那一半身子,已经冻僵了。小奶狗的左脚受了伤,小奶狗有一双清澈的眼睛。可能是因为腿伤,也可能生性如此,它的眼睛温顺得让大潘生出无端的怜爱,感觉那个伤口像是划在了自己的身上。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也是最懂得报恩的动物。看小狗的眼睛,就知道它有多善良。
大潘将小奶狗抱回护林站,给它包扎了伤口。从此,小狗成为了大潘的伙伴,天天跟着他去巡山。小狗从一个小不点,长成了一条皮毛金黄的大狗。大潘给它取了个名字“闪电”。
闪电一直跟着大潘,巡山,守夜,护林,一步不离。夜晚,稍有点风吹草动,闪电就竖直耳朵,保持高度的警惕。它在用它的方式,捍卫着梁王山上的一草一木。闪电跟着大潘巡山,一会儿跑前,一会儿跑后。有时,大潘会带一个随身听。一路上听《大悲咒》。南无阿俐耶,婆卢羯帝……听来听去,闪电仿佛听懂了其中的奥秘。有时,它会停下来,对着空旷的山林叫上一两声,像是获得了森林里的某个秘密,流露出快活、自由和某种趣味。闪电成为了大潘生活中的一部分,闪电也成为了梁王山的一部分,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闪电其实很温顺,不会轻易狂吠,更不会轻易使性子。遇到生人,即便叫上一两声,也行云流水般开合有度。大潘之所以给它取名“闪电”,是因为它以闪电般的速度,救了大潘一条命。夏天,雨水多。常常一道闪电扯过,响雷就从天下砸下来。大潘所在的瞭望塔,常常是雷电重灾区。瞭望塔刚建起来时,没有安装避雷设备。瞭望塔被雷击过很多次,机器设备均遭雷击,烧坏过很多次。一天,大潘巡完山,回到瞭望台,雷升火闪,大雨铺天盖地落下来。累了一天的大潘,坐在一只小木凳上,抱着一只水烟筒,正嘴对嘴,手搂腰,咕噜咕噜吸得快活。闪电突然一纵跳起来,扑向大潘。一个大炸雷砸下来,火星四溅,噼噼啪啪在屋子里炸裂。待大潘反应过来,小木凳已经着火。闪电这一扑,比天上的闪电还快。大潘爬起来,一把抱紧闪电,像是抱住自己的一个亲人。闪电的眼睛里,同样盛满了亮晶晶的光泽。大潘在雪地里救了它一命,闪电是来报恩了。
大潘和闪电的故事,不只这一个。
九十年代以前,附近的村民,经常三五成群潜入林中,盗伐树木。有的村民专挑已经成材的大树砍伐,偷回去盖房子。有的砍灌木枝,偷回去做豆桩,或者做煮饭的烧柴。大潘和其他的护林员,常常为了守住一棵树,每天晚上三班倒,换班值守。村民们大多选择在秋收农闲的时候起房盖屋。每年,秋收一结束,盗伐树木者众。
早起的大潘,抱着水烟筒吸一阵烟,就带着闪电出门巡山了。一入秋,天气就冷了。四野,被一片金黄覆盖。大潘和闪电踩着一地金黄的松针往山上走去。九点多,爬到了山顶。放眼处,山下的人间,清晰可见。秋高气爽,空气清透,抚仙湖、星云湖、滇池、阳宗海,尽收眼底。每天,森林、湖泊、溪水、草木……给予大潘很多新鲜的体验,每天都会有新奇的事情发生。这天,大潘在森林里,遇到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羊羔。小羊羔的身上湿湿的,冒着热气。显然,刚刚从胎胞里生出来,脐带上还沾着血。小羊羔躺在松针上,羊妈妈正一点一点舔着小羊羔身上的羊水。这大概就是舐犊之情最生动的画面了。大潘停下脚步,对着羊妈妈“咩”的唤了一声。羊妈妈和小羊羔都很虚弱,眼神温顺。羊妈妈“咩”的回应大潘一声,继续舔小羊羔身上的羊水。一缕阳光透过高大的华南松照在它们的身上,显得尤为可贵,那是阳光对舐犊之情额外的奖赏。舔着舔着,小羊羔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围着羊妈妈转了半圈,又跌倒在松针上。万事万物皆有因果,这便是小羊为什么跪着吃奶的原由了。羊和人一样,在母爱的包裹下,跌倒,再爬起来,一点一点长大。
每一天的生活,是这样琐碎而美好。每天,在山林间走,周而复始,重复着单调的程序,巡山管护、苗木抚育、监测火情。看似简单枯燥,倘若细心,总是会遇到许多感动。万物有灵,一只羊、一条狗、一只鸟亦然。满山的生灵,和大潘最亲近的,当然是闪电。
今天,没有碰到盗伐和破坏森林的村民,也没什么特别的迹象。倒是昨天,在森林里堵住了附近的几个村民,他们赶着几匹马来林中砍树枝,说是要砍了去做豆桩。那些小树苗刚刚成长起来,还嫩汪汪呢,但看那个头和长势,都是要长成参天大树的好木材。大潘及时制止了他们,没收了他们砍的树枝以及两副马鞍子。盗伐的几个村民也没说什么,返身下山,回了村子。
这天,十一点多,大潘回到瞭望塔,简单吃了点东西。闪电俯卧在屋门前睡觉,头俯在两个前爪之间,一只耳朵竖直,一只耳朵贴着地面,随时保持着警惕性。
突然,闪电一纵跃起来,开始吠叫。警觉的闪电听到了山下的动静。山下,几十个人抬着棍棒,呼啦啦往瞭望塔扑上来。昨天盗伐树木的那几个村民,聚集了村里不明真相的一群人,来瞭望塔闹事。闪电第一次龇起了牙,和来人对视。他们咄咄逼人,撩起棍棒砸向窗子。其中一棒,砸在了闪电的身上。一群人将大潘和另外四个护林员绑架了,要让大潘交出昨天没收的树木和马鞍子。村民押着大潘他们走了十多公里山路,绑到村子里,关了起来。
瞭望塔上,只剩下了闪电。闪电围着瞭望塔吠叫,四野空旷,没有回应。它像一个孤独的败将,急得噢呜噢呜直叫。叫声悲伤而悠长。风穿越树林,刮过来。闪电迎着风,叫了一阵,穿过森林,一路吠叫着,往山下跑去。一步快过一步,低沉的吠叫声,焦灼、隐秘、痛楚。这个中午,对于闪电而言,描述它,速度就够了。它来不及攻击,也来不及愤怒,它只需要保持迅捷的奔跑,将这个消息告诉另一个护林站的护林员。
当天凌晨一点多,大潘他们获救。大潘被打伤,在医院住了两天。他担心山上没人,放不下心来。才出院,又赶回山上。他更不放心的,还有闪电。
几天来,闪电一直蹲在路口等大潘。它的平静和机敏,像是梁王山赐予了它某种优良的品性。一直以来,闪电将尖利的牙齿藏起来,从来不会轻易去伤害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它的宽容和温顺,让它似乎不像是一只狗。抑或,正是它的温顺,让它显得如此卓而不群。它只警醒那些破坏森林的人,让他们自己去反省,去顿悟,最终用实际的行动一起来爱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闪电只有在森林遭到破坏和危险的时候,才会不安地吠叫。平时,总是保持着王者优雅的姿态。遇到投缘的人,闪电会跟他们戏耍玩闹,围在脚边一个劲儿打转,摇着尾巴,欢喜得不得了。玩嗨了的时候,闪电会一纵跳起来,前爪搭在行人的肩头上。临走,咬着行人的裤脚,舍不得。
狗的寿命大概是13年—16年。在大潘的心里,闪电始终健壮有力、精力充沛,永远处于壮年。闪电陪伴了大潘十三年,它跟着大潘每天巡山,听风沐雨,赏花看云。有时,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大潘就跟闪电说话,像是说给闪电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彼此,心心相印。坦诚、依赖,有时也会彼此任性,闹点小别扭。大潘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敞开给闪电,闪电也一样,回应大潘的方式,就是一纵跳起来,将前爪搭在他的肩头上,鼻息间,呼出潮湿热烈的气息。
万物都不可避免地老去。一些树木一年一年茂密葱翠,一些树木老了,倒伏下來,变成泥土的一部分。大潘的头发一年白几根,现在,几乎全白了。闪电,也在不可避免地老去。
闪电是无疾而终的,闪电走的那个夜晚,朗月当空。夜空下,闪电仰头,对着一轮明月叫了几声,平静地倒下去,闭上了眼睛。那时,大潘正在熟睡。
大潘将闪电埋在了一棵松树下。十几年过去,松树已经由一棵小树苗长成了大树。树冠伸向天空,一年长高一点。风一吹,金黄的松针落下,盖在闪电小小的土堆上。巡山的时候,大潘常常会绕道过来陪闪电坐上一阵子,和闪电说说巡山碰到的一些趣事。
12月21日,星期二,阴。今天冬至,冬至大如年。巡山时,去看了闪电,陪它说了一会儿话。老君殿林区,一切正常。现在,老百姓的护林意识越来越好了。森林越来越茂盛。传说,元末明初,梁王匝刺瓦尔密在山上,埋了九库金、九库银。谁知道是真是假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倒是真的。就快退休了,头发白了,山绿了。高兴着呢。
现在,大潘已经退休,回到了石门村。每天,一抬头,就是梁王山。他在满山的葱翠里,分辨出了年轻时的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弓着身,搬起一块石头,正在盖一间守山的房子。他看起来心情不错,他成为了梁王山的一部分。现在,他伸手摸摸满头的白发,仿佛已经被这一部分耗尽了身体所有的鲜活。他眼睛里溢出的亮晶晶的液体,却又成为了更鲜活的另一部分。
华山松结籽了,风,吹落一些落在泥土里,长出了很多小树苗。不消几年,又是一片葱翠的树林。
有时,会在村子里碰到休息回来的老木聪。老木聪说,叔,我去看过闪电了,好着呢。
老木聪养了一条狗,也取名“闪电”。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