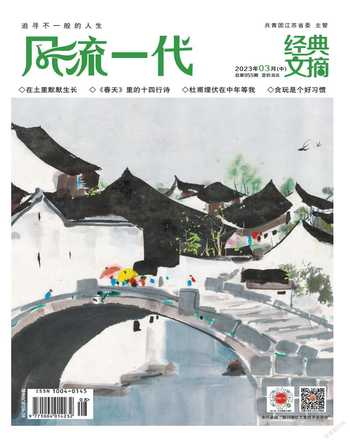《京江送别图》:杨柳依依送君行
愁予

远赴叙州
明代弘治四年(1491)三月,春风又绿江南岸,在京江的一处渡口,一场离别正在上演。
乘舟远去的是原南京刑部郎中吴愈,此时的他将要溯江而上,赶赴四川担任叙州知府。与吴愈惜别的是著名画家、诗人沈周,还有吴愈的女婿,同时也是“明代四大家”之一的文徵明,以及其他好友。
吴愈任南京刑部郎中时清慎严谨,号为称职,任内少冤狱,豪强为之侧目。文徵明在其墓志铭中称赞道:“公省决敏利,庭无留狱,析律祥明,所当必允。苟得其情,虽贵势不避时”。虽不免有过誉之嫌,但可称公允。
也正是因为名声在外,弘治帝初登基就诏令各地举贤任能,吴愈被当时的吏部尚书、侍郎齐名推荐,他虽上疏辞却,然而奏疏还没上达天听,任命他为叙州知府的诏令便到了。
叙州位于四川宜宾,从当时的地缘情况来看,无疑是大明王朝的边陲地带。从苏州沿长江而上,道长且阻,更何况叙州 “去京师万里,俗犷喜讦,吏多并缘为奸”,这样的治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然而吴愈却“不以为望”,欣然起行,受到了一众士大夫的赞誉。
当沈周知晓吴愈即将赶赴四川时,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送吴惟谦(吴愈,字惟谦)守叙州》,这首诗被收录在他的《石田诗选》卷七:“云司转阶例不卑,藩参臬副皆所宜……苦而有味可喻大,历难作事惟其时。”
此诗饱含了不舍与担忧,叙州不仅和江南远隔万里,而且蛮夷相杂,民俗粗犷,吴愈此行必是艰难险阻。但正是如此,沈周又表现出了对吴愈的极大信任与期待,直言 “文翁之任非君谁”?文翁是指西汉的一名官员,曾任巴蜀一代的地方长官,他在任时兴教化,施仁政,去恶俗,极大地促进了巴蜀地区的文教事业。以至于班固在《汉书》中发出了“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赞誉。
沈周此意,是将吴愈比作文翁第二,他深知凭借吴愈的志向与才干,必然不会郁郁愤懑而不作为,叙州得此知府,是百姓之福。诗的最后四句,“山谷老人”指的是宋代诗人黄庭坚,他曾被贬巴蜀,喜爱当地的苦笋,他将苦笋比作谏者,苦笋虽苦但食之有味,忠言逆耳却可以救国。沈周化用黄庭坚的典故,也是在激励吴愈。
相信吴愈也是怀着百般交集踏上的路程,对故地好友的眷恋、对前途艰难的惘然以及对尽忠守职的执念,犹如小舟泛江而掀起的涟漪,久久不能平静。
江风吹乱了吴愈斑白的鬓发,岸边好友的身影愈来愈浅,唯有江边杨柳的那一抹绿色却依然清晰。
这一年,沈周65岁,吴愈年近半百,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见面。双方都想把这次惜别刻在脑海中,沈周则选择了他最擅长的方式。
杨柳惜别
无论具体分别的那天究竟如何,在沈周的印象中,这次分别发生在桃花初放、杨柳依依的阳春三月里。吴愈的一叶小舟,泛于浩渺的江面之上,逶迤连绵的群山分为近山与远山,远山似青黛,若隐若现,近山却如墨眉。
沈周在作画时,明显无意于写实,他中意的是想通过环境渲染与情感烘托来表达对吴愈的惜别之情。画中无论是撑船的船夫,还是这场分别的主人公——吴愈、文徵明、沈周等人,都没有具体的五官勾勒。在沈周看来,古今多离别,他要画的是一种贯通离别的情丝。
因此,在画卷的中央我们分别可以看见杨柳与桃花这两种春日必备的意象。杨柳被用来歌咏送别是中国古代的一大传统,汉朝便有灞桥折柳的习俗,柳不仅谐音“留”,在中国古代,柳树还是一种极具生命力的植物,可以用来驱邪避灾,送别时折柳也是希望远去之人可以一路平安。
桃花虽然没有惜别之意,但是对于多愁善感的古人而言,在桃花烂漫的日子里本是邀上三两好友踏青饮酒的好日子,如今好友却要离去,而偏偏在离别的日子里桃花开得如此烂漫,难免不让人发出“桃花无情”的感慨。或许当吴愈到任叙州又是一年桃花烂漫时,他会莫名地想起这次离别,并顿生物是人非之感。
沈周的另一处巧思在于,浩渺的江面却偏偏只有吴愈的一片孤舟,而这江面又紧挨着逶迤连绵的群山,山长水远,路途险阻,不知归期。沈周对于友人远去的忧愁,借此隐晦地表达了出来。
整幅《京江送别图》,画面简洁,笔法粗犷,留有大量的留白,给观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显得有些“粗枝大叶”,但同时沈周又简中带繁,对杨柳、桃花与群山细致的勾勒,寓情于景,使得画面恰到好处,那股贯通古今离别的情丝跃然于纸上。
沈周的这种简洁而又不失意境的绘画风格被世人誉为“粗沈”,但是沈周多年的绘画历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丰富,“粗沈”的绘画风格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长期独占鳌头。
大隐于市
沈周出生在苏州府长洲县的一个书香世家,世代隐居在吴门,不官不仕,其祖父、伯父和父亲都痴迷于书画,家学极为深厚。沈周在此影响下,从小便酷爱书画,同时他涉猎广泛,经史子集,儒释老黄无一不读。长期的文化滋润和家风传统也使得沈周无意于仕途,终身都游离于官场之外,大隐于市,做了一个逍遥翁。
相比而言,沈周的一生不似李白那般狷狂,他生在明朝还算平静的时期,因此也不像杜甫那般满肚家国愁苦,他无意于仕途,家境优渥,所以苏轼、唐寅在仕途上的不幸,他不曾经历。沈周的一生,犹如春日午后的一潭小泉,恬淡而又平静。
一生埋首于丹青的沈周酷爱交友与游览,他为人宽厚,上到王公贵戚,下到贩夫走卒,他都欣然交往,其性格和阅历在他的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沈周的绘画主题涉猎广泛,明朝人王穉登在《吴郡丹青志》中称“先生(石田)绘事为当代第一,山水、人物、花竹、禽鱼悉入神品”。
沈周的画里既有山河壮丽之美,也有江南水乡之秀,更有文人墨客之雅。他师法王蒙,兼采董巨,以布局严谨,着墨细繁精密著称,世人称之为“细沈”。这一时期沈周的代表作是《庐山高图》,其细致令人惊叹。
到了后期,沈周摆脱了早期风格的束缚,改宗黄公望、吴镇和倪瓒等人,笔法愈来愈简洁。在师法多家的同时,他融入了自己的风格,晚年时的他更是进入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笔法苍劲刚健,意境悠远,“粗枝大叶”之下又不失“天真烂发”,世人称之为“粗沈”。这幅《京江送别图》就是“粗沈”风格的最好解读。
沈周76岁游历茅山时作《西山云霭图卷》,与《庐山高图》相比,简直粗略得不像样——《庐山高图》的庐山细致而有层次,《西山云霭图卷》中的群山却由几笔草草勾勒而成。
弘治十一年,好友吴宽赴京复职,途经丹阳时与沈周话别。不知沈周此时会不会想起七年前的那个春日里,那个孤帆远去的身影。在这之后他画了一幅与《京江送别图》只有一字之差的《京口送别图》,画中沈周与吴宽于舟中对坐,此时此刻恰如当时。
正德四年(1509),83岁的沈周溘然长逝。在这之前,吴宽已经先他一步离去,吴愈却活到了嘉靖五年(1526)。所谓的生离死别,沈周经历了不少,史载他80岁时仍“碧颐飘须,俨如神仙,精神矍铄,作画如常”。在世事無常的纷扰变迁中,他保持住了自己的那份洒脱恬淡,痴迷于丹青,醉心于泼墨,既是他内心意境的表达,也是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
沈周生前备受世人推崇,“明代四大家”中的仇英、文徵明和唐寅都曾接受过他的指导,文徵明称赞沈周是“吾先生非人间人也,神仙人也”。以他为代表的吴派也逐渐压过浙派,独占明代画坛鳌头。他去世后,又被誉为“明代画坛第一人”,明代画坛自沈周出,才展现出明代的气息,以至于效仿者无数。
但曾经写下 “功名大于渊,取之无一足”的沈周想必也不会在乎这些,他只在乎那个春日,杨柳树下依依惜别的好友。
(摘自《百家讲坛》2022年第8期)
——文徵明《致妻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