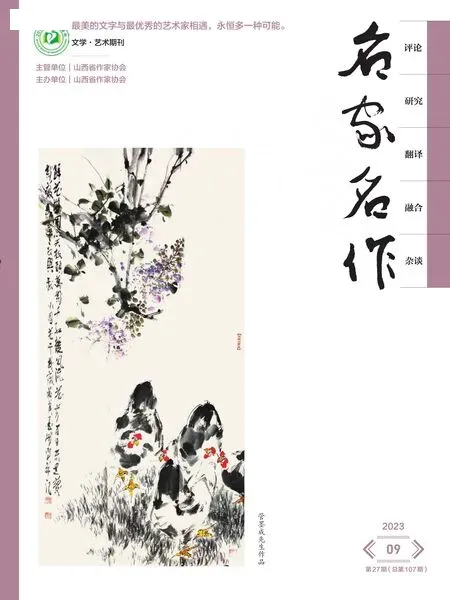传承与反叛:《封神第一部》中传统文化的现代式重述
孙梦婷
根据明代小说《封神演义》和宋代话本《武王伐纣平话》改编的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以下简称《封神第一部》)于2023 年7 月20 日在全国上映,累计票房已超过了26 亿。从映前的质疑和批评,到上映后引发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封神第一部》通过了观众考验,上演了一场“戏剧式逆袭”。导演乌尔善将影片风格定位在“神话史诗”这一类型,区别于传统“封神”系列中依靠神魔元素营造视觉奇效的奇幻题材,影片不再满足于复现人们熟知的神怪情节,而是对“封神”文化资源进行了重新挖掘,对于殷墟文化的重现以及道具的创新运用,都是将中国神话还原到历史中进行展现。同时,影片从现代审美价值观出发,将经典神话进行重新抒写。其中,电影中人物的颠覆性重构、“武王伐纣”中现代思想的呈现,都是以当代价值观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时代性的完美融合。就像乌尔善在采访时曾说的那样:“每个民族到了一定阶段,都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一个追溯、提炼和重新表达。”[1]
一、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时代呈现
(一)文化符号的创新性融汇
电影《封神第一部》对中国的神话故事进行了改编,其视觉体系来自华夏文明中相似的文化符号。影片的时代背景为殷商时期,影片中所呈现的语言符号完美契合殷商文物礼器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在殷商时期,礼法的器皿中具有丰富的装饰纹理,这些器皿表面通常含有一些饕餮纹、凤鸟纹、夔纹等。这种繁复异化的动物纹样不仅展示了礼器的审美设计,更传达了一种权力意识和贵族思想。影片将这种纹样符号通过道具具象化为王权与神权的象征,比如影片中宫殿四周镌刻的神兽图案、商朝军队的盔甲以及质子盾牌中的兽形。影片美学设计负责人叶锦添带领团队搜集了史料中代表贵族以及王权的图纹,再通过现代视觉的提炼、加工形成一种新的纹样,运用于影片的整体造型中,这些繁复的设计元素都表达了殷商文物中动物纹样所代表的权威。其中一种纹样——饕餮纹,在影片中成为朝歌城门前的神兽,而饕餮具有神性,象征着王室权力,这一意象的衍用给予了商王“君权神授”的正当理由,也传达出文本中殷寿作为君王,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
与动物纹样意象相同的是,影片中殷寿使用的斧钺、登基时舞姬表演中模仿的玄鸟都是通过物品的历史意义来展现商王的王权。首先钺在殷商时期是王权的象征,其钺由黄金所饰,为天子所用。电影里这一兵器作为专属物品被殷寿占有,其“王权”自不言而喻;其次玄鸟在殷商时期被商人当作自己氏族的图腾。商人崇鸟尊凤,《诗经·商颂》中也曾记载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偶行出浴,误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商契就是殷商的祖先,因此商人认为自己是玄鸟的后代。影片中在商王准备登基时舞姬就一边模仿玄鸟飞起而舞动,一边唱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种对于玄鸟意象的呈现以及斧钺的使用无一不体现出殷商时期的文化意蕴。
(二)对民本思想与善恶观念的批判吸纳
文化元素的使用为影片搭建了一个抛却神魔外衣,具有史诗韵味的封神世界。而电影中除了较为具象的文化符号,其核心道德观念的传达更体现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其中,姜子牙的下山动机反映出了在现代化演绎下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原著《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是被迫下山的,是为了迎合神意而不得不辅佐周王伐纣兴周,其形象是一个为神权、君权而服务的“扁平化”人物。而电影《封神第一部》中的姜子牙将被动转化为主动,一开始在封神榜的神仙名单中并没有他,而他却因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而突破结界,成功成为消除“天谴”的持榜人。影片将这一人物的行为动机化“顺从”为“主动”,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怀天下、救世为民的形象。时代的变化虽然改变了文化的评判标准,却没有改变中国核心的道德观念。影片中姜子牙召集四大伯侯齐聚女娲庙商讨如何消除天谴,共力废除殷寿另立天下共主时,北伯候说道:“商王是天下共主,天下都是他的”,而姜子牙反驳道:“天下并非商王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在这里,姜子牙口中的“天下”不再是一个模糊、统一的归属品,而是具体的悠悠众生,人成为核心观念,个体生命得到了重视。这一道德观念的转变体现了影片中基于时代发展而建构的以人为本、宽仁爱民的民本思想。虽然原著中姜子牙也说过这句话,但在《封神演义》中这一话语表述更多的是服务于君权,赋予周室伐纣易代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除了民本思想的呈现,影片中关于善恶的道德辨认也是承载了时代属性的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在姬昌去往朝歌的路途中,天雷震动,伴随天雷降生了一个相貌古怪的“婴儿”(雷震子),姬昌并没有因为此“婴儿”形态怪异而害怕,而是看其虚弱将他抱入怀中。当哪吒、杨戬向姬昌询要孩子,并提出可能是妖孽要除掉以防后患时,姬昌却驳斥道:“即使是妖也要看所受教诲如何。”姬昌的言论颠覆了以往封建思想中根据出生而论定的先入为主的善恶观,而是强调主体后天的主观能动性。
二、转化与重构: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下书写
(一)天命观的质疑和伦理道德的重建
电影《封神第一部》对原著小说《封神演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影片去除了原著中僵化的纲常观念,以儒家核心思想为主题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价值重构。原著《封神演义》具有强烈的儒家纲常思想,其中石超在《〈封神演义〉的儒家维度及伦理困境》中认为“《封神演义》几乎就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注脚”;李亦辉在《混合三教,以儒为本——论〈封神演义〉的整体文化特征》中也总结出道教和佛教思想只是《封神演义》中的“外衣”和表面现象,儒学才是其主旨和文化立场。在这既有的思想理论基础上,诸多学者认为儒家的“天命”思想在《封神演义》中贯穿始终。然而何为“天命”?孔子曾提出“知天命,畏天命”。认为“天”是万物的主宰,要认知上天的旨意,做到规范自我、恪尽职守。孟子也认为在世间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力量作用于人的社会活动和行为发展,这就是“天命”,即“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孔子和孟子都认为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天可以决定人的福凶祸疾,并不为人力、不以人的意志所改变。小说《封神演义》中不管是武王伐纣还是神魔斗法都皆遵循天命。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儒家思想便成为历朝统治者规范臣民的正统思想,而《封神演义》故事的核心是“以臣弑君”,这必然会挑战封建皇权,而“天命”则成为王朝更替、“以下犯上”的借口和辩护。其中《封神演义》第1 回纣王进香女娲庙时,作者借女娲之口说道:“成汤望气黯然,当失天下,西周已生圣主。天意已定,气数使然。”第15 回中也写道“成汤合灭,周室当兴”。这种天命思想充斥全书,成为殷商革命的终极依据。而电影《封神第一部》摒弃了原著中带有宿命论的“天命”观念,而是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血缘和伦理道德作为叙事纽带。在影片中,商王殷寿在登基时,比干用龟甲占卜欲问国运,而在龟甲用火进行灼烧时突然断裂,天生异象,顿时乌云漫天,遮天蔽日。当殷寿问“天谴”的原因时,比干则回答:“殷商王族,以子弑父,以臣弑君,世间之罪,莫大于此。”这里以“父与子”“君与臣”的行为关系来回答天之异象,不同于原著中“气运已尽”的说法,弑父杀兄才引发“天谴”,所以“德”才是堪当君王、国家兴衰的根本标准,这种对现实伦理道德的强调是对中华民族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继承与发展。原著中也提到了对于君王“仁政”的讨论,如“天命无常,唯有德者居之”“今主上不行仁政,以非刑加上大夫,不出数年,必有祸乱”,这里虽然强调人伦道德,但都是以“天命”为前提。除却这种含蓄、潜在的伦理探讨,影片中在“龙德殿父子对峙”中更让血缘、亲情之间的张力冲突达到顶峰。在殷寿的逼迫蛊惑下,崇应彪率先主动杀了自己的父亲,这种违背为子孝悌人伦道德的行为致使他最后被姬发用箭刺穿左眼死亡。而通过眼睛的毁灭对违反伦理道德行径给予惩罚似乎在古希腊戏剧中就有所体现。如索福克勒斯所写的《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王在受到命运的诅咒“杀父娶母”,最后通过刺瞎双眼、自我流放来惩罚自己犯下的人伦罪过。与此相似的还有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美国电影《唐人街》中伊芙琳被自己的生父玷污并生下一个女儿,伊芙琳的结局是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子弹射穿了右眼, 当场死亡。因此,这种区别于普通罚责和死亡的处罚似乎更带有一种对于违反伦理的谴责意味。不仅如此,影片中“姬昌食子”以及姬昌为了保护儿子承认自己的“罪行”都呈现出儒家传统中的血缘伦理思想,这种伦理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人所着迷并经常探讨的父子之间难以割舍、天然优越的血亲之情,就像乌尔善所表达的一样:“我们都尊重亲情,把伦理当底线,尊重善的理念,这是我们民族传承几千年的共同价值。”
(二)君臣观念的转变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封神演义》成书于明中后期,明清时期中央集权高度集中,在统治者的绝对权威要求以及宋明理学对伦理纲常的强势肯定,《封神演义》呈现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忠君观念。电影《封神第一部》解构了这种单向性的服从和愚忠,给了人物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动的价值判断。比如姬发,在他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想成为大英雄的梦想,于是他被殷寿骁勇善战的英勇形象所蒙蔽,将殷寿视为英雄的信仰,然而最终他发现眼前的“英雄”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殷寿利欲熏心,为获得权威弑父杀子诛妻、戕害忠良、滥用民力,于是他开始觉醒诛杀纣王,实现了从“殷商侍卫姬发”到“殷寿死了,我杀了他”的成长转变。这一成长不同于原著中心里始终有份臣子的“忠诚”,是被姜子牙等大臣说服才被迫实现伐纣大业的形象,影片中姬发的转变就如同当下年轻人的个体成长,从经历挫折中的懵懂迷茫到自我觉醒后的坚定信念。除此之外,影片中的姬昌也颠覆了原著中逆来顺受、不分良莠的愚忠。原著中的姬昌是恪守臣纲的忠臣,在临死前还告诫文王“纵天子不德,亦不得造次妄为,以成臣弑之名”。而文本中的姬昌则是具有主体意识,抗颜直谏、勇于反抗的正面形象。当殷寿召集四大伯侯前来朝歌时,伯邑考就劝谏姬昌三思而行,恐纣王用心叵测,但是姬昌不仅没有拒绝前去朝歌,还在被发现在女娲庙“密谋叛乱”的前提下不畏权威,对纣王说出“你将死于血亲之手”的卦象,这一行为直接呈现出了姬昌直言不讳、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品性和心胸。然而,如果这些是一些潜在的自我意识表达,那么当姬发来看望困在地牢中的姬昌时,姬发劝说姬昌向殷寿认罪来获取释放,并表示自己是儿子不可能杀父,而姬昌却说“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这一言语既是姬昌对于儿子的理性引导,也是人的主体意识、主动价值判断的显性体现。同时,影片中也改变了姬昌算命的能力范围,原著中姬昌早就知道自己会受七年牢狱之灾,也算出伯邑考受到醢刑。在逃回西岐后,当各大臣劝说姬昌报伯邑考的醢尸之仇时,姬昌心中却产生了不悦情绪,认为伯邑考是因为“不尊父训,自恃骄拗”才受醢刑,是“自取其死”的,并表述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忠君”言论。而影片中的姬昌并不能算到自己的命数,也不知伯邑考的醢尸之灾,所以当姬昌得知自啖子肉时是十分愤怒的,是反抗的,并且为了保护儿子自愿承担“罪过”,在大街上高喊自己有罪,这一高度的自我意识一改原著中唯唯诺诺、只为自保的文王形象。
三、结语
《封神第一部》借由历史文物、儒家思想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辩证式继承。近几年,随着“回归”“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打造更符合时代脉搏的文化产品是当代文化创造者的重要使命。电影《封神第一部》中不管是人物设定的改变,还是叙事动机的转化,抑或是思想价值的重构都完成了在传统继承的基础上注入时代血液,让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深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