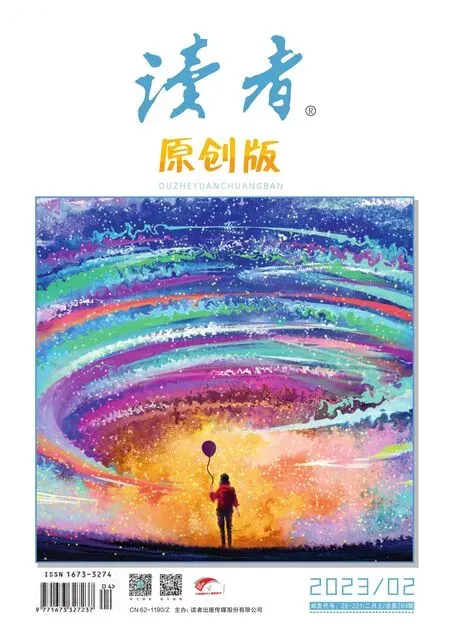社火上的甘蔗
文|杨家辰

我长大后,离开老家淳化,到西安当记者,有几年一到正月,就和民俗专家王智老师等人往周边农村跑,看当地人耍社火。看多了就总结出了关于看社火的几句话:敲鼓敲锣,喊爷叫婆,踩了几脚,啃个甘蔗。
真是这样的,看社火的时候,啃甘蔗是“标配”,谁看社火不吃个甘蔗就像逛北京没上长城、没吃烤鸭,朋友要对他咧咧“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
看社火的人,都是讲人情世故的,甘蔗一买就两根,十刀剁成十二节,爸一节来妈一节,媳妇一节娃一节。瞅见二姨了,递一节。遇上三舅了,递一节。小姨子那是不能忘的,又一节。遇到娃的班主任更要跑过去递一节。呀,手里空啦,自己还没吃哩。没事儿,再买就是啦,“擦擦”(口袋)里又不是没装钱。
那几年看的社火,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长安县的官寨村看“牛老爷社火”。顾名思义,主角是一个骑牛的官老爷。牛老爷其实就是春官,告诉庄稼人春天来了,不敢懒啦,该下地干活啦。扮演牛老爷的必是当地有威严、相貌好的伟男子;牛则是万里挑一的大牛,越大越好,赛过大象才好哩。
这个村分七个村社,耍社火时,七个村社分工不同。上堡社出牛和老爷;北堡社出旱船;狮子社出丑角;东南社出棍,棍就是刀、枪、剑、戟、斧、钺、勾、叉各种兵器组成的仪仗;大庙社出货郎娃;土地社出走马子,就是骑马的仪仗;龙门社出莲湘。
热闹吧!社火就在麦地里敞开了耍,麦苗青青,千人踩万人踏,还要过马队。麦地外围是卖吃食的摊子,除了炸油糕和煮醪糟是热的,荞面饸饹、神仙粉、擀面皮啥的,都是冰冰凉凉的,带着冰碴子。看社火的人心热,不嫌冰,该吃就吃。渴了就啃甘蔗。卖甘蔗的摊子生意极好,老老少少,几乎人人手里都拿一根甘蔗啃着,那也是冰的,一咬,“咔嚓,咔嚓”,像在嚼冰。风一吹,土一扬,脖子都缩起来了,眼窝也眯起来了,嘴里还“滋滋”吸甜汁汁呢。再看那地上,甘蔗渣子都铺了厚厚一层啦。
看社火的人啃甘蔗,耍社火的人也啃,要乐同乐,要啃都啃。看社火的人里专有一种村里的闲人,买了甘蔗,自己不吃,剁成几节就在胳肢窝里夹着,嘴里叼着烟、眯着眼等着。等到耍社火的队伍来了,就凑上去递甘蔗,那架势就像农村集市上乡党碰面散发纸烟一样自然和熟络。
耍社火的人脸上抹着油彩,看不清是啥表情,反正也不客气,有人给甘蔗就拿上,拿起就啃,一边啃一边随着队伍踩着锣鼓点往前走。递甘蔗的闲人感觉这是无上光荣,很有面子,周围的人也流露出羡慕的表情,心里赞道:这是个懂人情、闯过世事的“能行人”。
关老爷胡子一撩,啃上了,神笔马良啃上了,猪八戒啃上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也啃上了—不要想歪,我可一直都是在说啃甘蔗。到最后,牛老爷和他骑的牛也啃上了。牛嚼得一嘴白沫,牛老爷黑胡子黑牙,戴着石头眼镜啃甘蔗啃得哈哈大笑。这哪里是耍社火啊,分明是“甘蔗狂欢大会”嘛!
那天,一个引着孙子的老汉看我拿照相机拍他,一根棍子就伸过来了。我吓了一跳,以为他要打我,后醒悟过来,是要请我吃甘蔗哩。
我不认识老人家,不好意思拿,更兼要拍照,手里拿着相机呢,没法儿拿,我怕糖水染一手把相机弄脏了。老人家非要给我,硬塞,我就盛情难却了。真甜。我也往地上唾了甘蔗渣,入乡随俗。
吃了人家的,我就和人家拉呱。我说:“老汉爷,我不懂,麦地糟蹋了,又是踏,又是踩,又是甘蔗渣,损失算谁的,又是谁打扫?”
老汉说:“踏青踏青,越踏越青,麦苗不怕踏,越踏越旺。至于这甘蔗渣子,这怕啥的,这是给麦地上肥哩。”
我又问:“老汉爷,我看你都没有牙啦,还能吃动甘蔗不?”
老汉:“能,咱慢慢抿。”
我感叹道:“咱这儿的人真爱吃甘蔗。”
老汉说:“就兴这个。”
最近,我很少下楼。昨天难得上街,看水果店里卖的甘蔗都是金黄色的,不是我小时候常吃的“黑金刚”了。难道金黄色的更甜?
现在卖甘蔗的都不粗犷了,不穿黄绿色军大衣了,一个个都精致得很,塑料手套一戴,专业的削皮机器把甘蔗外皮一削,切成小块儿,整整齐齐地码在塑料盒里售卖。10元一盒。我买了一盒回来,很受女儿和媳妇的欢迎,三下五除二就吃完了。渣子刚好可以放在塑料盒里,干干净净的,一点儿都不埋汰。
我一尝,确实甜。女儿也说好吃,还要吃,第二天我又买了一盒。
我心想,如今的甘蔗好吃、易吃,不过,总感觉还是从前社火上的甘蔗更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