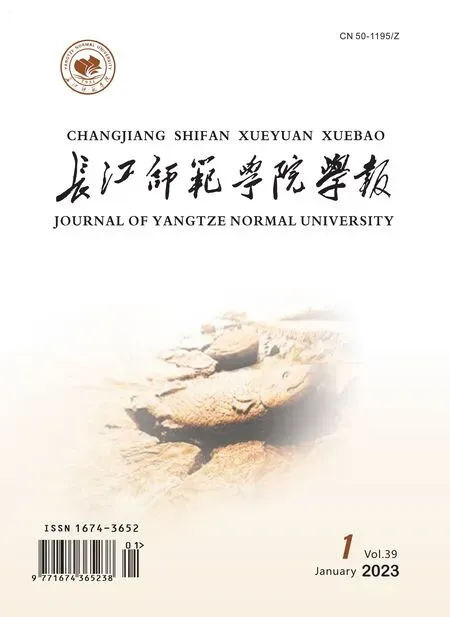从电影院到展览馆
——具身认知视域下电影作为艺术的一种可能
戢海峰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一、前言
1911年,意大利诗人乔托·卡努杜在《第七艺术宣言》中首次提出电影是一门艺术的观点,然而电影何以成为艺术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众说纷纭。早期电影理论时期,爱因汉姆认为电影成为艺术的前提是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性;经典电影理论时期,巴赞和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成为艺术是因为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同一性;到了现代电影理论时期,博德里和麦茨则认为电影成为艺术的基础在于影院空间里的观影机制,正是影院这种“黑匣子”空间的存在,观众才拥有了将电影等同于艺术的心理体验。然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电影的胶片介质和观影空间都在发生变化,观众不断走出影院,逐渐失去对电影的迷恋,以至于苏桑·桑塔格在《百年电影回眸》中疾呼:“要被征服,就必须到电影院去,在黑暗中和陌生人坐在一起。”[1]
电影作为艺术固然因影院的存在而具有某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却随着电视电影、手机电影、网络大电影等概念的出现被逐渐打破。电影院在流媒体平台的冲击下不断面临新的危机,影院所提供的观众身体在场的具身性观影体验也在逐渐退却。与此同时,当代电影的艺术实践却为这种具身性观影体验创造了一种新形式,它们将电影与装置艺术进行结合,通过“再媒介化”的形式将电影转换为视频装置艺术,从而将电影的放映/观影场所移置到展览馆内,使得整个观影空间成为一个艺术文本。观众则置身于这一艺术空间之内,以身体感知电影艺术的魅力。
无疑,从“黑匣子”状态的电影院到“白盒子”状态的展览馆,电影在成为艺术的条件上发现了新的可能。这种可能,与其说来自电影本身,不如说来自电影所在的放映空间,同时也是观众身体所在的观影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电影从生产出的产品转换为被消费的商品,从创作出的文本转换为欣赏后的作品,电影成为艺术的条件也由电影的客体转换为观影的主体。对于观影主体来说,无论是电影院还是展览馆,观众的身体都是具身性的在场,而非离身性的缺席,观众身体对观影空间的感知影响着观众大脑对电影的认知,“观影不是一个抽象的图景,而是一个大脑嵌入身体、身体嵌入影院的具身认知过程”[2]。
二、身体:作为媒介的具身认知
具身认知相对于离身认知而存在,是认知科学从第一代发展到第二代的结果。第一代的离身认知强调身心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人的认知依赖于大脑的理性思考,而身体则限制着大脑的理性思考。第二代的具身认知认为人的认知是大脑、身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认知、身体、环境是一体的,认知存在于大脑,大脑存在于身体,身体存在于环境”[3]。虽然具身认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正式提出,但对身心观念的讨论却是从古代延续至今。
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在《斐多篇》中认为灵魂与肉体是相互对立的,灵魂可以永存,而肉体却会腐朽,肉体只不过是灵魂暂时的栖息地而已。到了近代,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观点将理性主体视为人类思考与认知的基点,由此进一步强化心灵与身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将思维理性绝对化,以思维理性推演至世界万物,与思维理性相对的身体感性则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处于某种失语状态。直到后现代哲学的源头——尼采开始,身心二元、心凌驾于身的观念才被逐渐打破。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道:“我完全是我的身体,此外什么也不是,灵魂只是身体上某一部分的名称。”[4]半个世纪之后,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其著作《知觉现象学》一书中开始系统性讨论身体和具身性这一组概念,在他看来,“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拥有一个身体,对于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确定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其中”[5],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身体—主体”观念。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观打破了身心对立的二元观。在他那里,身体作为人与世界所连接的媒介,“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两者的融合”[6]。美国学者莱考夫和约翰逊作为具身哲学概念的开创者,则将神经认知与语言结构进行结合,发现了语言结构中嵌入着关于身体的“身体认知结构”[7]。这些哲学观念的发展为具身认知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后的各种心理实证研究,如琼斯曼的轻重写字板实验、威廉的冷热咖啡杯实验以及佐拉蒂所确诊的镜像神经元系统等,则从一种科学实证的角度表明身体的经验感受能影响人的认知判断。
具体到电影的认知与传播过程中,身体作为媒介的具身性认知同样逐渐受到重视。传统传播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于借助媒介技术实行跨越时空的信息交流,这种交流将身体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但当代社会媒介高度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交互性、场景化和超现实的特性极大延伸了媒介的‘生物’体征,逐渐打破媒介作为物与人之间的‘他者’化区隔关系”[8],媒介逐渐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实际上,早在半个世纪之前,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人的延伸”这一观点便早已前瞻性地预见了身体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任何传播媒介的变化实际上不过是对人身体感知的延伸。因此,所谓的传播必然是具身性的,而非离身性的。当下社会,互联网、移动媒体、VR/AR/MR等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一切信息交流和传播都建基于媒介技术之上,唐·伊德所提出的“技术—身体”观和唐娜·哈拉维意义上的“赛博格”观更是使作为技术的媒介已经与身体完全合为一体,在这个层面上,与其说“媒介即人的延伸”,不如说“人即媒介的延伸”。退一步讲,即便信息传播的过程抛弃媒介的在场,我们也面临着古语所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境,而这种意会正如彼得斯在《对空言说》中强调的一样:“我们的身体不是可以随意抛弃的载体,在一定意义上,身体是我们正在旅归的故乡。”[9]因此,无论是基于社会的媒介化现状,还是基于信息的实际领会,身体在传播的过程中都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以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意识形态为支撑的宏大电影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大卫·波德维尔和诺埃尔·卡罗尔等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挑战,他们认为此前的宏大电影理论不过是在自己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内自说自话,对于实际的电影实践和电影感知没有真正的指导意义。波德维尔和卡罗尔提倡一种具身性的认知主义电影理论,认为观众在电影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在人体感知系统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双重作用下,调动自己身体的各种感知能力和神经元功能,进而寻找故事的线索,理解故事的结构,最后解读故事的意义[10]。这也恰好说明了具身认知机制不是一个纯粹被动的接受过程,而是一种“‘与环境相耦合的(coupling)’的动力系统模式(dynamic)”[11]。同样,倘若我们将观影空间视为一个关于电影信息的传播场域,那么作为媒介的身体便在这一传播场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观众在此场域中感知客体、认识信息、表征意识等行为无不依赖于身体的存在。
由此可见,从哲学层面的理论话语,到传播学层面的信息传递,再到电影学层面的观众感知,以身体作为媒介的具身性认知从来都不缺席,只有在身体和环境具在的情况下,认知才能生成。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电影院和展览馆的身体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也传递给观众一种艺术认知的可能。
三、电影院:“洞穴寓言”的现代性重构
戴锦华认为,“影院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公共空间,是一个让我们走出家、告别‘宅’,让我们去和他人相遇,和他人共享一个空间的场所”[12],因而她坚信电影首先是一门影院的艺术。这种看似对传统影院观影模式“原教旨主义”的坚守,在现代电影理论的开端,便已经有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
1968年,让-路易·博德里的《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认为,观众坐在黑暗的电影院中,被动地、消极地认同于电影所营造出来的梦境,是一种无意识的“询唤”,而“询唤”的效果不仅来源于电影的内容,还来源于电影的机器本身,也就是电影的摄放机器和影院的空间结构。摄影机的成像系统模拟人眼的视觉系统,从而使“摄影机本身便带有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性”[13]。放映机隐藏于墙后的放映室,投射出的光束高高地悬置在人的头顶上,使观众意识不到它的存在;而影院的黑暗空间则让观众只能看到银幕上的活动影像,认同银幕空间所造就的幻觉。在这一层面上,博德里意识到影院环境和观众身体之于观影认知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观众身处于影院这一环境之内,才能获得一种特殊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体验也成为电影艺术化的一种证明。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区分了两种精神:一种是酒神精神,一种是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是狄俄尼索斯的狂欢,使个体的生命能洋溢在自由的欢畅中,代表着艺术的实质;日神精神则是阿波罗的法则,是理性的规训和道德的秩序,其代表的更多是对于艺术内容的形式约束。从具身认知的视角观察走进影院的观众,他们获得的更多的是一种酒神式的身体陶醉和情感宣泄,而非日神式的道德约束和理性认知。精神分析理论将影院的观影情境类比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到的“洞穴寓言”,以一种现代性的方式将该寓言进行重构。这一理论认为“放映机、黑暗的大厅、银幕等元素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再生产着柏拉图洞穴——对唯心主义的所有先验性和地质学模型而言的典型场地——的场面调度”[13]。同时,黑暗的洞穴空间和被束缚的身体使观众得以重新回到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母腹”和拉康意义上的“想象界”中。在这种环境中,现实世界的理性秩序和道德法则都开始让位于艺术世界的新秩序,观众的认知也不再仅仅是通过理性的判断获得,而是以身体的感知来直接体验。这种体验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人类的视觉经验,把世界从语言的重压下超越出来”[14],从而使得观众能以一种审美直观的方式在电影中感受酒神精神的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影院环境中,基本电影机器对观众身体所造成的感知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有取舍的。相关心理研究表明:“倘不能使(人类感觉的)多样性维持一个关键的水平,就会出现心理上的混乱,其中包括思维过程的障碍和出现幻觉。”[15]通常而言,影院环境强化了观众对银幕影像和电影叙事的感知,弱化了对影院本身物理环境的感知。从感官系统的角度来看,影院所强化的则是视觉和听觉的感知效果,而触觉、嗅觉、味觉等感知系统基本上都被排斥在外。这种相互取舍而又相互整合的感官系统,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可以完全沉浸在电影叙事的视听幻境中,不被电影叙事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干扰。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电影院诉诸于观众的视听感官效果不再具有唯一性,人们完全可以在家庭空间中仿造一个私人影院,以获得和电影院一样甚至更舒适的视听效果。此外,VR技术的发展更是使“观影情境已然被影像空间吞噬,观者在全景体验模式中,直接走进了银幕中,实现了身体于影像中(而非观影情境中)的在场”[16]。然而,现代感官科技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在于,影院空间的观看行为同时是一种集体性的私人观看行为。这种观看行为看似悖论,但却极具艺术效果。勒庞认为:“融入一个群体的个体所发生的心理调整,各方面都与那些由催眠术带来的心理改变相似。集体状态与催眠术状态相似。”[17]在集体性观看环境中,观众更容易成为所谓的“乌合之众”,他们像催眠一样跟随着他人的认同而认同,跟随他人的欢笑和泪水来带动自己的欢笑和泪水,从而完全沉浸在这种幻梦当中。2021年6月,托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在中国大陆重映,影片所怀念的除了动人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更重要的正是电影院所造就的这种集体幻梦。在集体的幻梦之外,电影院的另一种特殊体验在于它以黑暗的空间隔绝了观众相互之间的交流,观众可以在黑暗的环境下独自默默地欢笑或流泪,而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这种心理类似于精神分析中的“窥视”心理。日常生活中的窥视只能隐蔽在私人的角落中,影院中的窥视却发生在公共空间里,因而它所传递的心理快感和满足感更强烈。于是,在一种公共性与私人性相交织的社会空间中,影院观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既紧张又刺激,既满足又恐惧。
今天,电影作为一种影院的艺术仍被许多人所坚守,但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却又不断地对影院构成冲击,流媒体平台所带来的盈利效果持续改变着传统电影行业的窗口链条,新冠疫情的突现更是对影院构成了史无前例的威胁。影院空间带给观众的具身化体验固然使电影成为一门独特的艺术,但这门艺术却不得不因影院危机的出现而同样面临着自身所存在的危机。
四、展览馆:电影艺术的“再媒介化”实践
当电影院逐渐面临着来自手机、平板、电脑、电视等数字观影环境的威胁时,以身体作为感知的具身性体验同样面临着威胁。数字媒介所构建的观影空间无法使身体脱离于日常的生活空间,无法以一种仪式化的姿态接受艺术的“询唤”。于是,在此情况下,重新寻找能为观影人提供身体在场,进而感知艺术体验的观影空间便成为一种新的诉求。而这一诉求在当代艺术展览馆中,电影进行“再媒介化”的实践过程时,获得了新的可能。
对于“再媒介化”的讨论,从麦克卢汉论及新旧媒介关系时便已开始。麦克卢汉认为一种新媒介总是将旧媒介作为自身的内容而存在,如印刷媒介将文字媒介作为内容,电报媒介又将印刷媒介作为内容[18]。大卫·博尔特和理查德·古鲁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再媒介化”不仅指向内容,也指向其它[19]。克劳斯·布鲁恩·延森则明确指出“再媒介化”是“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与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性和意识形态特征”[20]。由此,“再媒介化”便经历了从媒介内容表达,到媒介形式表现,再到媒介意识形态表征等多个维度的转变与发展。
在当代艺术展览馆中,传统导演与造型艺术家进行跨界融合,电影与视频装置艺术进行结合,以至于电影不仅是作为展览馆中的一种影像材料而存在,其本身的叙事方式和意义传达同样为展览馆中的视频装置艺术所继承。电影艺术无疑也在经历着一种“再媒介化”的实践。独特之处在于,当代电影的这种“再媒介化”实践,不仅是借由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新媒体技术才得以实现,更是发生在展览馆这一抽离艺术作品原产地的“白盒子”空间之内。这种仪式化的艺术空间,满足了观众身体在场,进而以身体感知电影艺术这一具身化的观影诉求。因此,电影在转换为视频装置艺术的“再媒介化”实践过程中,不仅重新获得了影院空间中那种独特的艺术“光晕”,更使这种艺术“光晕”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影院中所蕴含的商业气息,更具艺术表达的纯粹性与独立性。
电影与展览馆的相遇,最早始于1917年“一战”期间,帝国战争博物馆对英国纪录片的收藏与放映。在此之后,美国的现代美术馆、法国的电影资料馆和巴黎现代美术馆均筹划了相关的电影展览。20世纪60年代电影新浪潮的变革,使得电影与装置艺术在展览馆中进行汇合,激浪派艺术代表白南准的《电影禅》、英国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的《24 小时惊魂记》以及安东尼·麦考尔的《以线勾勒锥形》均是这一汇合的代表作。21世纪以来,华语电影导演蔡明亮在展览馆中所进行的电影“再媒介化”实践较为频繁。2005年,卢浮宫主席卢瓦雷泰在名为“卢浮宫献给导演”的计划中邀请蔡明亮拍摄一部“以卢浮宫为主题”的剧情长片《脸》,作为馆方第一部委制与典藏的影片[21]。2007年,蔡明亮的短片《是梦》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非域之境”,影片中的道具——从马来西亚影院中拆下来的红椅子——也不断受邀去往世界各地展览馆中。2014年,台湾北师美术馆为蔡明亮的影片《郊游》举行了一场名为“来美术馆郊游:蔡明亮大展”的展览。翌年,同名展览在广东时代美术馆举行。蔡明亮的电影实践似乎表明,在当代电影越来越趋向商业化的同时,电影院中的电影已然成为了一种商品,因而电影想要成为艺术则需要寻找新的空间。从这种意义上讲,观影的空间环境对于电影作为艺术拥有某种决定性意义,而空间之中的身体体验则是艺术认知的审美基础。然而,影院空间毕竟不同于展览馆空间,如果影院使得电影成为艺术的仅指银幕上的影像,那么展览馆整个空间中的一切乃至于空间本身,都可以成为艺术,在展馆中进行感知的身体,也将成为这个艺术空间的一部分。
此外,与“黑匣子”形态的电影院不同还在于,展览馆首先是“白盒子”形态的。尽管展览馆同样可以关闭一切灯光,还原影院空间中的黑暗,但大多数时候,展览馆中的观影过程依旧是明亮的。因此,影院观众难以像从前一样在集体性认同的时刻进行私人化的窥视,其观影过程也不再是的集体性的私人观看。相反,在驱除影院空间中的黑暗之后,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沉浸于电影的艺术空间中,如蔡明亮在台北北师美术馆展览《郊游》时,便收集台风过后的树枝,用树枝的残骸重构郊游的场所。“《郊游》中盘根交错的生命之树与现实相呼应,寄托了在现代都市的荒原上重建家园的寓意,观众置身其中,切身感受到电影与现实的亲缘关系,即电影虽然是在虚构一个世界,但这种虚构折射出现实的本质。”[22]也即是说,展览馆实际上将自身的放映空间与电影的影像空间进行同构,当观众走进展馆时,他们便已然走进了影像之中。这种全身心的沉浸感,既不是影院所还原的洞穴,也不是VR技术所带来的虚拟体验,而是身体介入环境的实际感知。
罗兰·巴特在《走出电影院》一文中写道:“构思一种打破二元循环的艺术总是有可能的,中断电影的魅力,解除粘连,借助于观众的批评式观看,取消这种逼真之物的催眠。”[23]罗兰·巴特所呼吁的是一种能使观众的观影过程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沉浸转为间离,在被影片感动的过程中,还能有自己批判性思维的观影模式。展览馆使这种新的观影模式成为可能。在影院空间中,观众如同柏拉图意义上“被束缚的囚徒”,身体被固定在座椅上,而在展览馆中,观众则恢复了对自己身体的主动权,他可以以任意的姿态,或坐或躺、或倚或靠的方式观看影片。在随意行动的过程中,观众从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转换为主动的参与者。此外,展览馆中的电影展览时常有电影创作者和艺术批评者在场,这也使观众能与创作者就影片进行互动交流,从而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在这种意义上,展览馆似乎提供了一种兼具沉浸式艺术环境与主动性身体参与的观影模式。这种观影模式使沉浸感与间离感相互融合。仍旧引用尼采的理论话语,如果说电影院中的基本电影机器试图再现电影作为酒神精神的艺术实质,那么展览馆中的电影则使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既有艺术的实质,又有艺术的规则。
然而,问题的辩证之处在于,展览馆空间固然赋予了观众身体的自由性与开放性,但开放的环境却使观众的观看处于一种不断游移的状态中。固然有类似于台北北师美术馆那样,对展馆放映空间与《郊游》影像空间进行同构以弥补观影沉浸感之不足的做法,但更确切的现实是,当影院黑暗空间所提供的的窥视感和影院视点所确立的主体性消散之后,没有了观影和放映空间对周围其他干扰性环境的遮蔽与排除,观众在何种程度上才能完全走入电影的情境体验之中?又在何种程度上能对影像中的人物进行主体化的投射与认同,从而与电影的叙事融为一体,感受电影造梦的魅力?由此可见,展览馆的开放性既有其长处,亦有其短处。展览馆式观影在流媒体时代对电影院式观影进行补偿时,如何进一步营造观众的观影快感,并在普通观众之间推进这种观影模式的普遍化,亦将成为新的问题。
五、结语
从“黑匣子”状态的电影院到“白盒子”状态的展览馆,尽管电影的观影空间和观影机制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观众身体介入环境的具身化体验、电影作为艺术的可能却没有发生改变。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观众不断走出电影院,作为“城市电影文化的公共空间形态就从一个地理空间,更多转向以电视和网络平台为主的媒介空间”[24]。然而,经由数字媒介所构建的观影空间却无法提供与电影院相类似的具身化体验。在此情形下,电影在展览馆中所进行的“再媒介化”实践使一种新的艺术化具身体验成为可能,不仅展览馆中的电影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作品,并且整个展览馆空间和观众的观看行为本身都成为一个艺术事件。同时也需注意到,展览馆固然使电影在作为艺术的条件上更纯粹,但在展览馆中放映电影终究只能视为对影院观影体验的另一种补偿。当代艺术的探索与实验,只属于少数的电影艺术爱好者,难以在普通观众中普及。在电影院不断遭受流媒体平台的冲击,展览馆又难以对大众的观影快感进行捕捉并普遍化之时,电影如何继续寻找一种具身化的艺术性观影体验,无疑面临着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