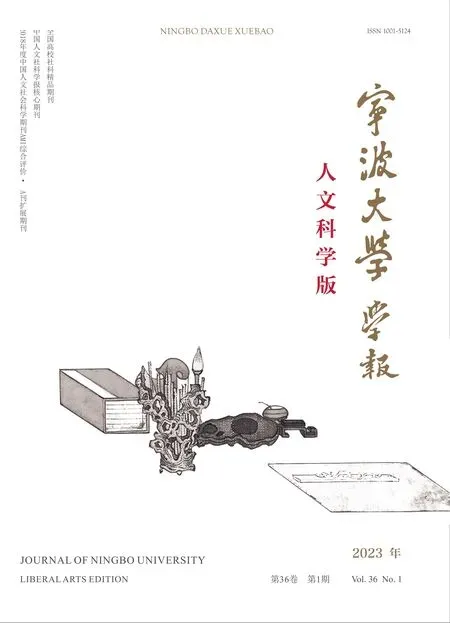合同纠纷管辖中履行地认定规则之辨析——以《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理解适用为中心
葛攀攀,路成华
合同纠纷管辖中履行地认定规则之辨析——以《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理解适用为中心
葛攀攀1,路成华2
(1.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浙江 宁波 315000;2.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上海 200030)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适用的关键,在于对该条款中“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和“争议标的”的正确认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表明,对前者的认定无须先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进行补救,亦无须将实际履行地视为约定履行地,只须审查争议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履行地”的表述和该等履行地点是否明确;而后者不是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标的物,也不是争议合同的“特征性义务”,而应是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被告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非其不履行该等义务转化为的违约责任。该条款仅“嫁接”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标的物不同履行地不同”的法定区分,但两者的适用前提和基准有重大差异,并未实现所谓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则统一。
合同纠纷;履行地;约定;争议标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与199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规定了第18条这样的一般条款[1],将原《民诉法适用意见》中第18条至第22条的规定合并为此一条,以简化和明确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2]148-149。其中《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该条款前段是对合同履行地的事实拟制[3]69-78,与实际履行地无关,构成合同纠纷管辖中所谓“法定履行地”认定规则的核心;而后段则是对即时结清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就是合同纠纷管辖中“合同履行地”的直接确认。两者意旨不同,且前者的适用较后者更为普遍和复杂,本文侧重于对前者的阐释分析。
《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1款和第3款,分别明确了合同履行地管辖中的约定履行地优先适用规则和约定履行地排除适用情形,后者规定在合同没有实际履行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管辖,直接排除了履行地管辖在这一情形中的适用。因此,《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实际上构成了合同履行地管辖中的“履行地”认定规则之核心,是司法解释起草者为避免以往对合同履行地规定的混乱,而对履行地认定规则抽象化、一般化尝试的关键所在[1,4]。《民诉法解释》起草者指出该解释第18条的设置是源于对原《合同法》第61条、第62条(《民法典》第510条、第511条)规定的借鉴[4],而且第18条第2款前段更是基本上搬用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的内容表述,由此令人产生了《民诉法解释》中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被统一于实体法上履行地确定规则的错觉,导致学理和实务上对该司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认识的争议[5]。有学者则明确地质疑《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直接“嫁接”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规定的合理性[3]。
实际上,《民诉法解释》起草者对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中合同履行地认定的区别有较为清晰的认识,指出合同履行地在民事诉讼法中只是为了方便法院确定管辖的一个较为狭隘的裁判概念,在审判实务中一般应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为辅”的原则判断确定,不同于民事实体法中旨在引导当事人正确适当地实现合同义务的履行地概念,以及其履行地确定规则[2]149-150。不过,这一论述是基于《民诉法解释》实施之前的规定所作出的,并未结合该司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的具体规定加以阐释,加之《民诉法解释》的起草者对第18条第2款适用的具体细节语焉不明[1],导致司法实践中对该条款的理解适用存在相当大的争议,未能有效改变以往合同纠纷履行地管辖异议泛滥的现象①。自《民诉法解释》发布实施六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仅依据第18条第2款作出的管辖异议裁定就已达约八十件,接近其在该司法解释实施之前二十多年间就具体合同管辖权纠纷案件所作批复、通知和复函的数量总和②。
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有必要通过梳理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裁决、文件和解说阐述等,厘清该等规则的核心要素即其适用前提——“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和适用基准——“争议标的”的具体含义,进而明晰合同履行地认定在程序法和实体法中适用规则的差异。
一、合同履行地认定的前提——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的认定
所谓合同约定履行地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案涉合同中所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履行的地点。在双务合同中,当事人可以仅约定任何一方履行债务的地点,也可以分别约定双方各自履行其债务的地点,在实践中通常仅约定非金钱债务履行的地点。进言之,合同约定履行地可能与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履行地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无论哪一种情形,只要合同约定了履行地点,根据《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1款的规定,就应当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从而直接排除该条第2款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的适用。因此,第18条第2款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
在民事案件的立案阶段,法院对原告所提供证据材料仅做形式审查,而不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5]。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案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委托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判摘要中指出,“确定管辖权应当以起诉时为标准,结合诉讼请求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形式要件审查以确定管辖”③。在法院确定管辖的过程中,对于作为履行地认定规则适用前提的“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自然也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这一事实认定规则的含义与其在实体法中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在立案阶段,法院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时,无须先适用《民法典》第510条对该等情形进行补救。该条款是对原《合同法》第61条内容的沿用,规定了在合同生效后履行前,对合同履行地等非合同成立必备内容缺位或不明确进行补救(补正)的方法[6]149-150,是适用《民法典》第511条(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对相关合同内容进行补充解释的前提[7]363。易言之,在实体法中,按照给付标的不同对合同履行地进行补充解释从而予以确定之前,应当先通过当事人协议补充、按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的方式进行补救,且该等补救业已失败。
但是,《民法典》第510条(原《合同法》第61条)规定的履行地等合同内容补救方法,并不适用于合同案件管辖中的履行地确定,不构成认定“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的前置程序。因为,在合同纠纷立案审查阶段,作为原告和被告的当事人双方就合同履行地签订补充协议几乎已无可能,而且法院也不能够在开庭审理之前对合同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并进而按照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点。这正是《民诉法解释》第18条未将进行合同内容补救且失败,作为其第2款适用前提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立案过程中,法院认定当事人“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时,无须也不应先依据民事实体法规定对此进行补救,根本不存在“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的空间。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认定合同是否“约定履行地点”时,将约定交货地、送货地、演出地和约定多个履行地等情形均排除在外,其认定标准相较于民事实体法而言更为严格。
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合同纠纷案件的管辖裁定中,认定合同“履行地约定明确”通常以案涉合同中有直接相应的文字表述为前提。原《民诉法适用意见》第19条曾经规定,“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但这一规定并未在《民诉法解释》中得以保留或沿用,这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该等约定履行地认定规则的放弃。因此,在“泗阳县众兴镇徐冬梅李世川味观餐饮加盟店诉杭州天骄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对于浙江省高院持有的“约定了交货地点可以认定双方约定了合同履行地,不能机械地要求必须出现‘合同履行地’的字样”观点,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否定,认为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交货地点,属于没有约定履行地,应当按照《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④。在“铜陵伟业亚麻有限公司与杭州新美艺制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虽然在《产品定布合同》上写明了签订地点和送货地点,但未明确表示将签订地点或是送货地点作为约定管辖法院所在地,故不能直接将上述地点认定为约定的合同履行地点”,应当按照《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⑤。在“张晨与杭州诚业箱包有限公司、刘庆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更加明确地指出“对于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不宜再以送货地、收货地、验货地来确定合同履行地,也不能以实际履行地作为认定标准,要根据当事人争议或案件纠纷所针对的合同项下的某项特定义务来确定”合同履行地⑥。虽然,在《民诉法解释》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有个别合同管辖案件的民事裁定将当事人约定的交货地认定为合同履行地⑦,但此类裁定较为少见,这种认定也有悖于其在《民诉法解释》中已经删除原《民诉法适用意见》第19条从而放弃类似规则的意旨。而且,如前所述,《民诉法解释》第18条仅是借鉴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标的物不同履行地不同”的法定区分,但并未“嫁接”该法第61条履行地等未约定或约定不明时的补救规则,未将类似补救失败设为认定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的前提。因此,法院在立案阶段自然也不宜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
此外,即使当事人在合同中直接约定“履行地”,如果当事人的该等约定指向多个不同地点而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仍然会将之认定为“约定履行地不明确”。比如在“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赛瑞机器设备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虽然双方当事人在多份《机电产品外部协作合同》中均约定“合同履行地(交货地点)为需方指定地点”,但由于约定有大连、江苏、内蒙古、甘肃等不同地点,当事人也认为合同履行地点有很多而难以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因此将之认定为属于“履行地点约定不明确”的情形⑧。
最后,《民诉法解释》实施后,法院在认定当事人是否明确约定履行地时无须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在实体法意义上,一般认为当事人均接受但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实际履行行为,具有变更合同原有约定的法律效果,即该等实际履行行为相当于形成了新的约定。这一实体法观念在《民诉法解释》实施之前,影响到司法实务在合同管辖纠纷中对履行地的认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复函》和《关于购销合同履行地的特殊约定问题的批复》等规定,实际履行行为可以设定、变更约定履行地,就是该等实体法观念在当时诉讼法规则中的体现[2]149-150。《民诉法解释》起草者指出,当事人实际履行义务的地点不应再被作为确定合同履行地的依据,其已经失去了设定、变更约定履行地的法律意义[2]153,155,法院认定当事人是否明确约定履行地时无须考虑合同的实际履行地。因此,在立案阶段,法院不应再以与实际履行地不符为由而否定约定履行地的法律效力。
由此可见,在认定《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履行地认定规则适用前提——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时,法院无须先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以补救该等约定的缺位或不明确,也不应将实际履行地视为约定履行地,而只须审查双方合同中是否有约定合同“履行地”的表述,且该等履行地点是否明确。这与按照原《合同法》第62条(《民法典》第511条)等实体法进行相关事实认定规则的适用,存在较大差异。
二、合同履行地认定的基准——“争议标的”的认定
在《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规定的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中,按照“争议标的”的不同划分为给付货币、不动产和其他标的三种情形,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履行地点。因此,“争议标的”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履行地认定规则的基准性概念,其含义的界定对于该等规则的正确适用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多认为,《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的“争议标的”应当理解为诉讼标的,即当事人所争议的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或实体权利义务[5,8]。但是,对于合同纠纷中“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更为具体的指向,则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中被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另一则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有学者认为,第一种理解强调履行地认定规则的程序法特点,无须过多依赖于实体法框架内的判断,适用简便且更为合理[1]。有的学者则认为,第一种理解即“诉请义务说”在逻辑上存在不自洽的缺陷,并且适用过程中容易引发诸多争议,而第二种理解即“特征义务说”在逻辑上是自洽的,且据之所确立的标准也更明确、便于操作适用[5]。
“争议标的”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12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海事法院收案范围的通知》中,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涉及民事诉讼程序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中多有使用,另外在个别行政部门规章和行业协会文件中也偶有出现,但该等表述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和行政法规中却并未有使用⑨。因此,对于这一由最高人民法院首先且经常使用的实务性概念的理解,从该法院在相关文件和裁决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上探寻,似乎更为妥适。
在能够查询到的约43份最高人民法院使用“争议标的”概念的司法解释性文件中,这一概念大多被等同于“争议标的物”使用,比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中,“申请保全的财产系争议标的的,担保数额不超过争议标的价值的百分之三十”。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当事人对乡(镇)人民政府就民间纠纷作出的调处决定不服而起诉人民法院应以何种案件受理的复函》(法研〔2001〕26号)中,“乡(镇)人民政府对民间纠纷作出调处决定,当事人不服并就原争议标的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经乡(镇)人民政府调处的民间纠纷的通知》的规定,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等表述中的“争议标的”,显然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争议标的物”,而应按照前述“诉请义务说”将之解释为原告诉讼请求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更为合理和妥当。那么,对于《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的“争议标的”是否也应如此理解呢?
《民诉法解释》起草者在其编著的解说书中,对如何明确界定第18条第2款中的“争议标的”语焉不详,但是基于“对世界各国和国际条约相关规定的考察”,认为“对合同履行地的立法模式都规定了由有争议的债务履行地法院管辖”,并进而指出在我国审判实践中确定合同履行地,“必须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2]152-153。不过,这一“诉讼请求结合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规则,仍然过于抽象和模糊,以致最高人民法院在此后的审判实践中对“争议标的”的界定依然不尽统一。
一种界定是,将“争议标的”明确为“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大多数裁决认可和采用的界定方式。在“周鑫与赵青伟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的“争议标的”“是指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而非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周鑫作为卖方⑩,其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已经支付的货款,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是赵青伟应当按照约定交付钢材。该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合同履行地应为履行该义务的赵青伟所在地,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在“涟源市伏口镇杨梅山煤矿与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卖方久益公司诉买方杨梅山煤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认为“久益公司诉请杨梅山煤矿支付剩余货款,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为杨梅山煤矿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货款,该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而就买方杨梅山煤矿诉卖方久益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一案,则认为“该诉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为久益公司应当按照约定交付货物,该案当事人争议标的不是给付货币和交付不动产”。而在“吴建社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合同系股权转让合同,吴建社作为股权受让方,其诉讼请求为确认合同有效、被告承担继续履行合同及支付违约金的违约责任,据此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标的为转让股权,属上述规定中的‘其他标的’,应以履行义务一方即京粮控股公司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在该等案件的民事裁定中,明确地将“争议标的”界定为“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不仅遵循了《民诉法解释》起草者所指出的“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规则,符合以争议债务确定合同履行地的比较法规律,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的合同履行地认定问题,因而为最高人民法院多数合同管辖案件的民事裁定书所采用。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争议标的”即“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的界定,在给付之诉和形成之诉、确认之诉中存在细微的差别。在给付之诉中,“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就是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合同”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即原告诉讼请求中主张被告履行的合同义务,这个比较直观明确,比如在前述“涟源市伏口镇杨梅山煤矿与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卖方久益公司诉买方杨梅山煤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是将原告久益公司诉请被告杨梅山煤矿支付剩余货款义务,认定为“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即争议标的。而在形成之诉中,所谓“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并非原告基于形成权行使效果而主张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比如返还货款、返还货物等),而是原告诉讼请求所“针对的合同”(即形成之诉的对象)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比如在前述“周鑫与赵青伟买卖合同纠纷案”和“涟源市伏口镇杨梅山煤矿与久益环球(淮南)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买方杨梅山煤矿诉卖方久益公司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货款和赔偿损失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就是原告主张解除的合同中所约定的被告应当履行的交货义务。在确认之诉中,所谓“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亦为原告诉讼请求“所针对的合同”(即确认之诉的对象)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比如前述“吴建社与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原告请求确认有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中被告承担的转让股权义务,认定为争议标的即“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由此可见,争议标的即“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在给付之诉中就是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履行的合同义务,而在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中则是作为该等诉之对象的合同中被告承担的合同义务,未必体现在原告的诉讼请求之中。
另一种界定是,将“争议标的”明确为“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在“湖南湘晖资产经营股份有限公司与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众多义务中,特别是互负债务的双务合同中,必有一个能反映合同本质特征的义务。这个本质义务的不同,是区分不同争议标的的标志。在双务合同中非金钱给付义务是该类合同的区分标志,只有这个特征义务的履行地才是确定管辖应依据的履行地”。在“堆龙东为实业有限公司、成都百悦大地矿业有限公司与王耕银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争议标的是指双方发生纠纷的合同类型或性质所决定的主要或特征性义务”,“就本案而言……支付货币仅是交易对价,而非合同特征性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标的不属于给付货币,而是其他标的,应当根据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确定合同履行地”。这一界定“争议标的”的方式,虽然形式上符合《民诉法解释》起草者以“当事人诉讼请求和结合合同履行义务确定合同履行地”的要求,但是,按照该等界定方式,实质上是以对合同性质的审查判定作为认定履行地的前提,从而将本应在实体审理阶段查明的事实前置到了立案阶段,不符合司法规律[9]。而且,由于该等“本质义务”或“特征性义务”在绝大多数双务合同中具有唯一性,且仅限于非金钱给付义务,所以将“争议标的”界定为“反映合同性质的本质义务”,实际上使《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情形的规定几乎只能够适用于借款合同,而对其他所有以金钱为对价的双务合同均无法适用,这显然与该司法解释起草者将该条款作为合同履行地认定一般性规则的意旨不符。因此,将“争议标的”明确为“反映合同性质的本质义务”的界定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合同纠纷管辖的民事裁定中较少采用。
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所作的合同纠纷管辖裁决,可以发现该条款中的“争议标的”不是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标的物,也不应是争议合同的“特征性义务”,而应当是“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具言之,在给付之诉中,“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就是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合同关系中被告应当履行的义务,而在形成之诉和确认之诉中,则是原告诉讼请求所针对合同关系中被告负担的义务。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争议标的”的该等合同义务,是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或针对的合同中约定的对方原给付义务,即学理上所称的“第一次给付义务”[10]743,而非因不履行该等义务所转化为的违约责任。
三、结语
由此可见,《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合同“没有约定履行地或约定不明确”的认定,无须先行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地以进行补救,但该等补救及失败却是原《合同法》第62条(《民法典》第511条)第3项的适用前提。而且,《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的“争议标的”是原告诉讼请求所指向的被告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并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诉讼请求标的物,与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的“给付(交付)标的”存在实质性差异。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中的履行地认定规则,只是“嫁接”了原《合同法》第62条第3项中“标的物不同履行地不同”的法定区分,但是两者的适用前提和适用基准完全不同。主张《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实现了诉讼法与实体法上履行地认定规则的统一,或者认为应当按照实体法规定进行合同纠纷管辖案件中履行地认定的观点,实际上忽视了两者的重要差异,极易导致司法实务中对该等条款理解适用上的偏差。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法学研究抑或司法实务中,法律的解释适用均需要“少受语词困扰,直探法律适用”[11]。
注释:
① 在《民诉法解释》实施之前,由于对民诉法中合同履行地认定规则理解不一而导致合同纠纷管辖异议泛滥,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个案的管辖权争议所作的批复、通知、复函就多达上百件,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第149-150页。
② 在北大法宝网(www.pkulaw.cn)以“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为关键字全文查询司法案例,并以法院级别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筛选,可查询到民事案例114件和知识产权案例21件,逐一检视其内容发现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作出裁定的案件约80件。
③ 参见:北大法宝网,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委托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为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二终字第428号。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16号民事裁定书。
⑤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34号民事裁定书,在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43号、(2019)最高法民辖76号等民事裁定书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持有相同观点。
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34号民事裁定书。
⑦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辖39号民事裁定书。
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118号民事裁定书。
⑨ 在北大法宝网以“争议标的”为关键字进行法律法规的全文查询,可以查到43份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性文件、9份行政部门规章和11份行业协会文件,未查询到法律和行政法规。
⑩ 按照该裁定书上下文内容,此处的“卖方”应该是“买方”。
⑪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61号民事裁定书。
⑫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27号民事裁定书。
⑬ 即《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
⑭ 参见:最早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376号民事裁定书。
⑮ 在北大法宝网以“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为关键字全文查询司法案例,并以法院级别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筛选,可查到依据《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裁定的约80件,其中将“争议标的”界定为“当事人诉讼请求所指向的合同义务”的为72件,包括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辖终297号、(2017)最高法民辖终368号、(2018)最高法民辖终358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138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298号、(2020)最高法民辖60号、(2020)最高法民辖89号、(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104号、(2021)最高法民辖6号、(2021)最高法民辖终11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73号民事裁定书等。
⑯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1号民事裁定书。
⑰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辖终385号民事裁定书。
⑱ 在北大法宝网以“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为关键字全文查询司法案例,并以法院级别为“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筛选,可查到依据《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裁定的约80件,其中将“争议标的”界定为“反映合同性质的本质义务”的为8件,包括(2019)最高法民辖终1号、(2019)最高法民辖终385号、(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50号、(2020)最高法知民辖终396号、(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246号民事裁定书等。
[1] 王亚新, 雷彤. 合同案件管辖之程序规范的新展开——以《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的理解适用为中心[J]. 法律适用, 2015(8): 39-46.
[2] 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上[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
[3] 赵旭东. 合同履行地与诉讼管辖地之辨析——兼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8条第2款[C]//张卫平, 齐树洁. 司法改革论评(第二十二辑).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4] 杜万华.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重点问题解析[J]. 法律适用, 2015(4): 2-12.
[5] 刘文勇. 再论合同案件管辖规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民诉法解释》第18条第2款的反思[J]. 时代法学, 2018(4): 94-101.
[6] 梁慧星. 合同通则讲义[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7] 朱广新, 谢鸿飞. 民法典评注: 合同编: 通则: 第1册[M].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8] 冯果, 刘怿. 债券投资者司法救济规则建构论纲[J]. 财经法学, 2020(3): 77-94.
[9] 肖建国, 刘东. 管辖规范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研究[J]. 现代法学, 2015(5): 124-136.
[10]韩世远. 合同法总论[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8.
[11]孙维飞. 定义、定性与法律适用——买卖型担保案型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6): 166-178.
On the Rules for Determining the Place of Performance in the Jurisdiction of Contract Disputes
GE Pan-pan1, LU Cheng-hua2
(1. Zhejiang Suhao Law Firm, Ningbo 315000, China; 2. Shanghai Xinben Law Firm, Shanghai 200030, China)
The key to the application of paragraph 2 of Article 18 of thelies in the correct identification of “there is no agreement on the place of performance or the agreement is not clear” and “object of dispute” in this article. The general application of this clause by the Supreme Court indicate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ormer does not need to determine the place of performan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or trading habits for remedy, nor does it need to regard the actual place of performance as the agreed place of performance. It is only necessary to examine whether there is an agreement on the “place of performance”in the contract between both parties and whether such place of performance is clear. Furthermore, the latter is neither a claim, nor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litigation claim, but “contractual obligations pointed to by the plaintiff’s claim”, and it is not the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transformed by the failure to perform such obligations. This clause only “grafts” the legal distinc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 matter and different place of performance” in Item 3 of Article 62 of the original contract law, bu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pplication premise and benchmark between the two, and there is no so-called unification of the rule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contract disputes, place of performance, agreement, object of dispute
DF72
A
1001 - 5124(2023)01 - 0118 - 08
2022-05-10
葛攀攀(1982-),男,浙江宁波人,二级律师,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诉讼法。E-mail: 76464031@qq.com
(责任编辑 周 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