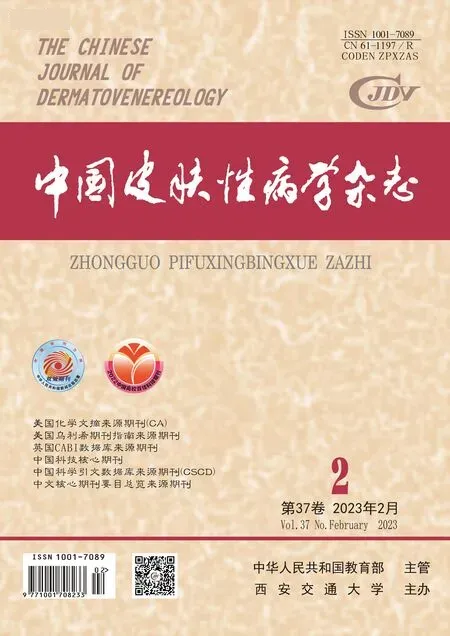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诱发特应性皮炎的研究进展
唐欣,郑旭宇,李倩,周翠,胡玉莲,王萍,黄琨
银屑病俗称“牛皮癣”,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在我国的患病率为0.47%[1],且仍有不断升高的趋势[2]。近年来发现银屑病不仅可累及皮肤,还可能造成系统病变,包括中重度银屑病伴发关节炎、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精神疾病等的风险明显增加[3]。随着对银屑病发病机制研究的逐渐深入,目前普遍认为Th1、Th17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TNF-α、IL-23、IL-17等在银屑病的发病中发挥重要作用。靶向作用于TNF-α、IL-23、IL-17这些关键细胞因子的生物制剂,已在银屑病治疗中展现出更安全、更优越的疗效,成为银屑病治疗史上新的里程碑。随着生物制剂在银屑病治疗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正确认识并管理其不良反应非常必要。
特应性皮炎(atopic dermatitis,AD)是皮肤科另外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与银屑病相似,两者均是以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和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殖、分化为特征;不同的是两种疾病的T细胞极化方向相反[4]。正是这一原因,特应性皮炎在银屑病患者中发生引起了本课题组的关注,其作为生物制剂治疗中发生的皮肤不良反应之一,可能引起诊断的混乱或误诊,并给后续的治疗和管理带来困难。本文将对银屑病生物制剂治疗中发生AD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识别高危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提供帮助。
1 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特应性皮炎的发病情况
我国目前批准用于银屑病治疗的生物制剂共有4类,分别是TNF-α抑制剂(依那西普、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等)、IL-17A抑制剂(司库奇尤单抗、依奇珠单抗)、IL-12/23抑制剂(乌司奴单抗)和IL-23抑制剂(古塞奇尤单抗)。据报道[5-8],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AD的总体发生率在1.0%~12.1%,发生时间在生物制剂应用后3~22.1个月不等,全身各部位均可发生。除了银屑病,TNF-α抑制剂在治疗炎症性肠病、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疾病中也有发生AD的报道,发生率在5%~20%[7]。
多个研究显示患者既往的特应性病史、IgE水平升高、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是发病的共同因素。AI-Janabi等[5]的研究发现,在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特应性皮炎的患者中有46%既往有特应性病史,包括哮喘、变应性鼻炎、变应性结膜炎等;38%的患者出现IgE水平或血嗜酸性粒细胞的升高。Ishiuji等[8]的研究也发现既往有特应性病史或高IgE水平的银屑病患者,接受乌司奴单抗治疗更容易发生AD。Nakamura等[7]的研究发现既往有特应性病史是TNF-α抑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AD的危险因素,而家族的特应性病史、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不是统计学上的危险因素。
2 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特应性皮炎的可能机制
2.1免疫因素 Pichler[9-10]提出了生物制剂不良事件的分类,第3类为“免疫或细胞因子失衡综合征”,其中包括特应性疾病,可以解释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AD的原因。人体免疫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其机体的免疫耐受机制、调节性T细胞、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TGF-β和IL-10等),以及Th1/Th2平衡都参与其中。通过抑制或注射具有免疫调节功能的细胞因子,这种平衡可能会被打破。目前有一种假说认为:Th17和Th1细胞免疫和Th2细胞免疫犹如天平的两端,靶向抑制Th17和Th1细胞相关因子能诱导免疫反应向Th2型免疫漂移,从而导致AD的发生[5-8]。银屑病是以Th17细胞为主要驱动因素的疾病,Th1细胞作用次之;而AD是以Th2细胞为主要驱动因素的疾病[10]。抑制Th1和Th17细胞因子可能诱导向Th2为主的免疫反应进行漂移,从而导致AD的发生。具体的信号通路机制因其不同生物制剂可能有所差别,仍需进一步探究。
已有相关报道验证了免疫漂移假说的可靠性:①抑制Th2细胞可出现炎症向Th1系偏移:治疗特应性皮炎的度普利尤单抗是一种靶向于Th2细胞因子IL-4和IL-14的单克隆抗体。有报道[11],在予以度普利尤单抗治疗的373例 特应性皮炎患者中,7例 患者出现了新发银屑病;②在其他以Th1细胞为主要发病因素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肠病等疾病中,应用TNF-α抑制剂出现Th2系疾病哮喘、AD的报道[12-14]。
在治疗银屑病的生物制剂中,有关TNF-α抑制剂诱发AD的相关报道最多,且机制研究更详细。Stoffel等[15]发现与传统的AD相比,TNF-α抑制剂治疗后引起的AD有不同的免疫机制,后者表现出α-干扰素(IFN-α)水平显著增高,而IFN-α的亚型与Th2细胞的极化相关。同时,TNF-α抑制剂上调IL-22和Th2细胞因子IL-5、IL-13的水平,下调丝聚蛋白的水平,这些因子均是AD发病中的关键因子,促进了AD的发生。IL-23能诱导Th17细胞分泌TNF-α,因此IL-23抑制剂抑制IL-23后,导致Th17细胞产生TNF-α下降,部分充当了TNF-α抑制剂的作用[15],这可能是IL-23抑制剂诱发AD的原因之一。关于IL-17A抑制剂诱导AD发生的机制,Napolitano等[16]认为IL-22可能发挥了关键作用,但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2.2微生物的定植 皮肤上存在着多种微生物群落,它们通过产生抗菌肽、形成生物膜和抑制病原体的入侵来维持人体健康。银屑病患者皮损中多种抗菌肽的生成,能抑制皮肤微生物菌群的异常定植。而AD患者常有皮肤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增加和菌群多样性下降[17],尤其是前者在AD的发病中起到了主导作用,并与AD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18]。TNF-α、IL-17A、IL-23等细胞因子均是机体抗感染免疫应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生物制剂通过抑制这些细胞因子治疗银屑病的同时会出现感染风险的增加,最常见为上呼吸道感染和皮肤黏膜的感染[19-20]。IL-17A能刺激表皮角质形成细胞表达抗菌肽,故IL-17A被抑制后抗菌肽的表达会受到抑制,抗菌肽的缺乏可能导致金黄色葡萄球菌强毒株定植,从而促进AD的发生[21]。Liu等[22]发现TNF-α能通过募集中性粒细胞和上调IL-17A,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清除;因此TNF-α被抑制后, 会导致中性粒细胞和IL-17A水平均下调,有利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定植。
2.3皮肤屏障功能的破坏 皮肤屏障功能障碍是特应性皮炎最明显的病理变化之一,也是AD发病的第一步。近年来有研究[23-24]发现,IL-17A对皮肤屏障有保护和增强作用,IL-17A被抑制后可能导致皮肤屏障功能下降。Sawada等[25]研究也发现,TNF-α信号通路在SMase和GCase介导的皮肤屏障修复中起着重要作用,且Jensen等[26]发现TNF-α可促进损伤后小鼠皮肤屏障修复,而缺乏TNF受体p55的小鼠屏障修复延迟。因此,TNF-α被抑制后可能会降低皮肤屏障的修复作用。
生物制剂除了直接影响皮肤屏障外,还可能通过增加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定植来干扰皮肤屏障功能。金黄色葡萄球菌能通过在角质形成细胞膜上形成七聚体β-桶孔,破坏皮肤屏障,并分泌蛋白酶溶解角质层[27]。屏障功能下降加上金葡菌等微生物的定植或感染,能促进Th2型细胞因子的分泌,导致AD的发生。
2.4遗传因素 Weidinger 等[28]采用全基因组关联法对AD和银屑病的遗传易感基因进行研究,发现两者有一些重叠的风险等位基因,其中包括CARD14基因中的一种常见的、破坏性的错义变体。其后,Tamari 等[29]发现IL-13和ZMIZ1位点可能包含AD和银屑病共有的遗传因子。基于此可以推测拥有这些特定等位基因的患者可能处于更高的风险中,更易于发生免疫表型的转换出现AD。
3 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特应性皮炎后的治疗
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发生AD后的治疗方案应根据银屑病的治疗效果和特应性皮炎的严重程度来制定。对于银屑病控制好,AD病情轻的患者,可继续原生物制剂维持治疗,同时局部给予软膏如糖皮质激素软膏、抗菌软膏等治疗AD[30];对于局部治疗不能控制或AD病情重的患者,部分病例停用生物制剂后特应性皮炎可自行缓解,部分病例还需要加用系统免疫调节剂治疗如度普利尤单抗、阿普斯特、环孢素或糖皮质激素[6-7,31-32]。对于银屑病控制不佳,出现AD的病例可直接换用兼顾两种疾病治疗的免疫调节剂如环孢素、糖皮质激素等[6]。
4 小结
随着生物制剂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银屑病患者,AD作为皮肤不良反应的报道也日渐增多,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免疫、微生物、皮肤屏障和遗传等因素有关。临床医生在给银屑病患者使用生物制剂前,应详细了解患者个人是否有特应性病史,以及血IgE水平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以识别可能发生AD的高风险患者,进行个性化医疗。治疗上建议根据银屑病的控制情况和AD的严重程度来制定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