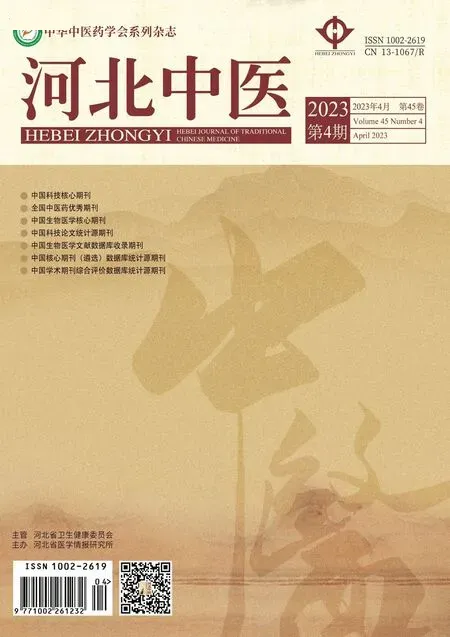运气变化对张锡纯医学思想的影响初探※
陈冰俊 陶国水 陆 曙 彭 健 孔令豪
(江苏省无锡市中医医院、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江苏 无锡 214071)
医学思想的产生与变化,常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张锡纯是近代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说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吸收西医学之长,参合使用中西药物是受到了当时西学东渐的社会变革的影响[1],那么其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及临床用药的变化则来源于对当时自然环境中运气变化的观察感悟。陆懋修曾提出“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必先明六气司天之为病”,即“六气大司天”学说,其在对前人医学思想进行归纳总结时认为,历史上各家学说对疾病的认识之所以有偏差,是受运气变化的影响。此种结合运气阐释前人思想的方法,近代医家章巨膺亦有提及,但历来在专著中详细记述自身医学思想随运气而变化的医家较少。张锡纯认为,中医较西医所优之处即在于重视阴阳气化之理[2],其在临床中观察天地气运,详细论述自身治疗思路随运气变化的过程,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1 运气变化四阶段
在《医学衷中参西录》有关运气内容的记录中,以第六卷验案讲记中治疗“高某温病兼阴虚病案”最具特色[3],其展现了张锡纯所处时代运气变化对疾病的影响,以及其治疗思路随之变化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未习医时,张锡纯发现当时的临床医家擅用承气汤为代表的下法治疗各种疾病,且疗效显著,“见医者治伤寒温病,皆喜用下药,见热已传里其大便稍实者,用承气汤下之则愈,如此者约二十年”。
第二阶段习医之初,此阶段张锡纯发现,仍沿袭旧法用承气汤治疗外感病的医生临床效果急转直下,“其如此治法者则恒多偾事”,加之张锡纯此阶段“所阅之医书,又皆系赵氏《医贯》、《景岳全书》、《冯氏锦囊》诸喜用熟地之书,即外感证亦多喜用之”,因此他开始使用大剂量的熟地黄治疗寒温坏证及外感病,“高某温病兼阴虚病案”正是此中代表,“愚之治愈此证,实得力于诸书之讲究。又有重用熟地治愈寒温之坏证,诸多验案(地黄解后载有数案可参观)”,言明“此乃用药适与时会,故用之有效也”,因治疗效果显著还影响了当时的医道同行,“自治愈此证之后,毛××、高××深与愚相契,亦仿用愚方而治愈若干外感之虚证,而一变其从前之用药矣”。
第三阶段是其年过四旬之后,此时张锡纯对气化的领悟已较深,能够清晰的感觉出“天地之气化又变,病者多系气分不足,或气分下陷,外感中亦多兼见此证”,因此认为“即用白虎汤时多宜加人参方效。其初得外感应发表时,亦恒为加黄芪方效”。
第四阶段是在1921年之后,张锡纯发现此时之病皆“气化过升之故,亦即阳亢无制之故”,所病多阳气上逆,宜用大剂凉润之药济阴以配其阳。若为外感实热证,多宜用大剂白虎汤,更佐以凉润之品。若为脑部充血,或夜眠不寐,治之者宜镇安其气化,潜藏其阳分,再重用凉润之药辅之。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建瓴汤及镇肝熄风汤即是创制于这一时期。
张锡纯在文中感叹到,“此诚以天地之气化又有转移,人所生之病即随之转移,而医者之用药自不得不随之转移也”。从自身经历出发,认为即使是同种疾病,在不同的运气条件下也会有所偏向,选药治疗当适应运气变化而调整。张锡纯在书中时有引用陆懋修的观点,陆氏治痘主清热,治痉主泻火[4-5]与张锡纯一生重视养阴清热之法有关[6],并在《医学衷中参西录·驳方书贵阳抑阴论》中明确赞同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相合,可见当时之运气受燥热影响较大。且陆懋修的“六气大司天”学说将1864—1923年归为阳明燥金司天,少阴君火在泉之大司天,按张锡纯生卒年为1860—1933年算,正处于此燥火周期中。同时张锡纯在运气变化的大司天背景下,敏锐的体悟到各小周期的运气特点,临床用药随四个不同阶段的运气而变化,则为其特识。
2 运气变迁识前人
随着对运气变化的深入认识,张锡纯对前人的论述也有了不同的体悟,提出“由此悟自古名医所着之书,多有所偏者非偏也,其所逢之时气化不同也”,并结合《内经》的运气理论,对医圣张仲景的用药思路及某些异常疾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1 伤寒金匮年运变 张锡纯认为,伤寒、金匮中的用药变化受张仲景所处时代运气变化的影响,并举伤寒与金匮方之变化,以证明时隔不远用方就当有差异,“特是天地之气运,数十年而一变。仲景先成《伤寒论》,小青龙汤一方,加法甚多,而独不加石膏,盖其时无可加石膏之证也。后著《金匮》则小青龙汤加石膏矣,其时有其证可知。相隔应不甚远,气运即有变迁”。故倡导治病用药当善查运气而变通,以善用古方,不可执定古人之方以治今人之病,以动态的气化变迁阐述了张仲景诊疗思想及经方用药思路。
2.2 奇恒之病天人应 对于疾病的异常表现,张锡纯通过引述《内经》运气理论加以解释,其曾引用陈修园在戊午年两遇奇恒痢证,来说明异常病变与运气的关系。所谓奇恒痢是指下痢不重,却出现神昏谵语、咽干喉塞、气呛喘逆等症状的危重痢疾[7],陈修远认为此病是由阳邪壅盛,上攻心肺,九窍皆塞,阳气旁溢,下窜肠腑所致。而张锡纯在此基础上提出,此病发展迅速是由火运之岁遇少阴君火司天,火气太盛所致,因而与普通痢疾不同,“修远所遇二证,皆在戊午年。天干戊为火运,地支午又为少阴君火司天,火气太盛,故有此证。其危在七日者,火之成数也”,并直言“由斯观之,《内经》岁运之说,原自可凭”,在治疗上则同意陈修园“此证急宜大承气汤泻阳养阴,缓则不救”,继承传统之上又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3 岁运失和致疫病
张锡纯对于疫病的认识,也强调运气的影响,认为疫病是由岁运失合所致,“疫者,感岁运之戾气,因其岁运失和,中含毒气,人触之即病”。
以霍乱为例,张锡纯赞同陆懋修对霍乱的认识[8],认为此证实热者居多,真寒凉者不过百中之一二,引述陆氏之言道“春分以后,秋分以前,少阳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令。天之热气则下降,地之湿气则上腾,人在气交之中,清气在阴,浊气在阳,阴阳反戾,清浊相干,气乱于中,而上吐下泻”。认为“治此者,宜和阴阳,厘清浊,以定其乱,乱定即无不愈”。但即使相同的年运,也会根据病证或年运偏向有不同的治疗。在壬寅年霍乱流行时,张锡纯根据木运太过以酸石榴敛戢肝木,使过亢之木安顺,“后岁值壬寅,霍乱盛行,有甫受其病泄泻者……急以酸石榴敛戢肝木,使不至助邪为虐致吐泻不已,则元气不漓,自可以抗御毒菌”,或单用大剂量山茱萸救急固脱,“凡人元气之脱,皆脱在肝……山茱萸得木气最厚,酸收之中大具开通之力,以木性喜条达故也”。若相火亢盛,则以羚羊角既解热毒又平肝木,“岁在壬寅之孟秋(约1902年),邑北境霍乱盛行。斯岁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肝胆火盛,患病者多心热嗜饮凉水。愚遇其证之剧者,恒于方中加羚羊角三钱(另煎兑服)服者皆愈”。虽强调全年之运气皆与司天之气关系密切,即使病发于孟秋,霍乱心热也因暑热伏火所发,“或疑司天者管上半岁,在泉者管下半岁,霍乱发于孟秋似与司天无涉。不知霍乱之根皆伏于暑热之时,且司天虽云管半岁,而究之一岁之气候实皆与司天有关也”。对于同一年之霍乱流行,会根据其偏于木运升发不能收敛,或是相火之热太过,而有酸石榴、山茱萸酸收,或羚羊角清降之不同。而对于不同年份的霍乱其治疗则差异更大,如同治壬戌至癸亥江苏沪渎,因霍乱流行偏于暑湿实热为重,故以石膏、黄芩、黄连清之而愈。丁酉八九月间,杭州盛行霍乱转筋之偏于湿证时,则仿照《金匮要略》治霍乱转筋入腹之鸡矢白散,拟得蚕矢汤偏于利湿为治。对部分确需温通者也不避讳如薷藿、平陈、胃苓等温中祛湿习用之剂,分清浊、明升降,“特不用姜附丁萸之大辛大热者耳”,以免助运气之热。
而对于其他的疫病,张锡纯也沿用了运气理论的思想,在《医学衷中参西录·论鼠疫之原因及治法》中,其根据《内经》“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思想[9],认为鼠疫之成因“原是少阴伤寒中之热证类,至极点始酝酿成毒,互相传染”,论述虽同属伏气温病,但“因此病较伏气入他脏而为病者难于辨认,且不易治疗”,是由于“多系伏气化热乘虚入少阴……即温病之中有郁热,其脉象转微细无力者”,而与普通少阴伤寒之热证不同则在于,感染后未立即发出,而在“感春阳之萌动而后发,及发于夏,发于秋者”,也即前文所谓之“至极点始酝酿成毒”。这与现代研究认为鼠疫的流行具有一定时间性相符合[10]。张锡纯认为此证源头在运气变化之上,是少阴热证之至重者,并基于同属少阴伤寒之热证“其病虽异而治法则同”,使用白虎汤与黄连阿胶汤的合方进行治疗。
4 运气时序论杂病
对于杂病,张锡纯常结合运气时序论述疾病病因,认为“人身之气化,原与时序之气化,息息相通”,选方用药重视天人相应,遵循五运主次。
4.1 气机闭塞时序失应 对于妇人寒热,张锡纯不认同此病为单纯肝虚,提出自然时序有“一日之午前,犹一岁之有春夏。而人身之阳气,即感之发动,以敷布于周身”的规律,若女性因忧思影响,以致脏腑、经络多有郁结闭塞之处,则“阻遏阳气不能外达,或转因发动而内陷,或发动不遂,其发动排挤经络愈加闭塞,于是周身之寒作矣。迨阳气蓄极,终当愤发,而其愤发之机与抑遏之力,相激相荡于脏腑、经络之间,热又由兹而生”,致其症状随时间产生前午寒、后午热的变化。故治疗以地黄、知母诸凉药与黄芪温热之性相济,燮理阴阳、调和寒热。更依据阴阳往复之理运用宣阳汤、济阴汤二方轮流服用,治疗老媪癃闭,认为“先服济阴汤取其贞下起元……似与冬令,培草木之根荄,以厚其生长之基也,于服宣阳汤数剂后,再服济阴汤,如纯阳月后,一阴二阴甫生,时当五六月大雨沛行,万卉之畅茂,有迥异寻常者也”,深得运气阴阳变化之妙。
4.2 五数之中土运为首 张锡纯重视五运中土运在运气变化中的首要地位,在《医学衷中参西录》开篇之资生汤中强调,“故天虽以五生土,而常以一先四,而首万物,一先四者,即五数之一,而首以土运之义也,此万物所以资始也。地虽以十成土,而恒以二居五而终阴阳,二居五者,戊癸化火,而适终于地二之数也,此万物所以资生也。生生之本,制用之道尽矣”,认为当以养坤土为要务,重脾阴之资生,“故戊己中宫为最尊,布气育灵,为生物元始,所谓资生于坤也”。在张锡纯所制“升降汤”中提出“厥阴不治,求之阳明”[11],并引《金匮要略》“见肝之病,当先实脾”为依据,认为肝木赖中宫土运以建,组方“惟少用桂枝、川芎以舒肝气,其余诸药,无非升脾降胃,培养中土,俾中宫气化敦浓,以听肝气之自理”,甚合尤在泾“欲求阴阳之和者,必于中气,求中气之立者,必以建中也”之语[12]。
5 总结
运气思想在中医历史中时隐时续,很多医家在论述中都有涉及,但多数仅引用部分经典内容,而张锡纯不仅对五运六气思想有自己的体悟,还将自身每隔十余年用药思路随运气变化的过程明确记载下来,是少数亲自阐述运气变化对自身治疗思路影响的医家。张锡纯初习医时,受《医贯》《景岳全书》《冯氏锦囊秘录》等长于养阴之书影响较大,一经临床就治愈了“高某温病兼阴虚病案”,得到同道推崇,加之当时气运燥火偏盛,奠定了他一生注重养阴清热的治疗思想,认为治病应滋阴化阳,泻阳保阴。但张锡纯用药并未因此而局限,在不同运气阶段注重实践,随证治之,才是其临床每多奇效的重要保证。
张锡纯医学思想既受到西学东渐的社会变革影响,参合运用中西药物,吸收现代科学理论,又体悟自然环境中的运气变化,在传承《内经》运气思想的基础上,辩证看待前人理论,形成了独到的临床思维,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