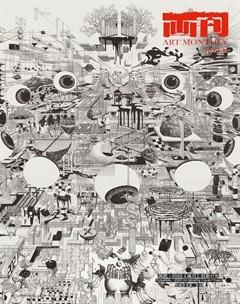延续不变的价值观:曹恺访谈
徐志君 孟尧 曹恺
徐志君:你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到《江苏画刊》吗?曹恺:我读中学时就开始看《江苏画刊》了。1985年“八五美术新潮”的时候,“两刊一报”——《江苏画刊》《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是最前卫的美术报刊。因为我父亲也画画,当时我家里是订阅《中国美术报》和《江苏画刊》的。后来,我在1988年到南艺上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随时可以去,所以,当时《江苏画刊》是我日常阅读的一部分。

徐志君:其实当时《画刊》的读者群与现在的不一样,那时它还是比较专业的,主要的读者群跟美术工作相关。当时的媒体环境不像现在,大家获得国外的展览、艺术家的创作信息渠道很多,也非常同步。那时候纸媒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还是向大家介绍一些新的潮流,或新的艺术家作品等信息。你当时看《画刊》的时候, 对什么样的内容、什么类型的信息印象比较深?
曹恺:那时除了《江苏画刊》《美术思潮》,连北京的《美术》杂志都刊载前卫艺术的信息。《江苏画刊》当时的一个特点——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它的深度话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类似邱志杰与王南溟他们做的关于“意义”的讨论等。对我来讲是一个艺术前沿信息的来源吧。
徐志君:第一次在《画刊》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曹恺:第一次是“95时段”群展。那时候做展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像现在随时可做。实际上我们为做这个展览准备了2年时间。当时1995年正好距离“八五美术新潮”10年,“新潮”已经烟消云散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多“八五”时的艺术家也有各种不同的转向。当时江苏有一批“八五”时留下的艺术家,他们稍年长一点,更多的是“后89”成长起来的年轻艺术家。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概念,叫作“重新组织力量”,就做了一个展览叫“95时段”。
当时还没有“替代空间”的概念,展览场地在南京非常稀缺,我们所能够最方便借取的就是南艺美术系展厅,因为当时南艺美术系的负责人杨春华、周一清夫妇思想很开放,跟我们这些搞前卫艺术的关系很好。但是美术系的展厅太小了,我们当时的作品体量都已经相当大,有的一件作品就要占据一面墙,装置也很占地方。“95时段”就分了两次展,我跟管策、周啸虎、金锋是第一波,第二波是罗荃木、沈敬东、吴翦、王成他们。同一个展览分为两个副标题,我们那个副标题叫“不再与记忆有关”,就是要抛弃过去“85时段”的一些负担,改变文化使命。这个展览当时《江苏画刊》刊登介绍了,我的一件综合媒材作品也是第一次发表在《江苏画刊》上。


徐志君: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看到《画刊》杂志上陆陆续续有你的创作的报道。当时杂志跟青年前卫艺术家群体有一种比较日常的联系,大家像一个朋友圈,一有活动杂志就会预先知道,活动之后就请杂志推介。或者说有一些人本来相互之间不太熟,后来因为杂志上的发表,大家的关系变得比较亲密了,还是一直处于松散的状态?
曹恺:20世纪90年代叫前卫艺术,2000年以后叫当代艺术。我们这个群体实际上就是同一拨人,我们跟《画刊》的关系,我觉得是很干净的一种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画刊》虽然是一个江苏省地方主办的期刊,但它一直是全国视野或者说国际视野,它的视点一直很高,在上面发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它有学术原则。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对南京本地、江苏本省的作者或许会略有所偏移,但是尺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作品要在上面发表,必须要跟它的价值观契合,包括作品的质量要能达到在上面发表的要求。我觉得这也是《画刊》这么多年来,它能够站得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因为是地方性期刊而被地方势力垄断,被朋友圈的私人关系垄断,那这本期刊的分量早就在大家心目当中丧失掉了。
徐志君:如果说自己当时做了一些作品,或者说展览什么的,在《画刊》上被报道出来,大家还是挺开心的。
曹恺: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很心虚的,那时我还是个前卫艺术圈的新人。我记得是我跟管策两个人去拜访顾丞峰,带着作品反转片给他看,能不能发心里没底,这要取决于编辑的认可——不是《画刊》跟我们约稿,我們属于投稿。唯一占的便宜,可能外地作者要邮寄,我们能够面对面递交,并能多说上两句话,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那次我也是跟顾丞峰第一次认识。顾丞峰原来也不知道我,他看到我的作品后就认可了我的工作。那么,后面《画刊》如果有什么活动,他觉得适合我、跟我的工作有关系的,他就会打电话喊我。比如说湖南美术出版社谁来了,要召开一个当地艺术家的碰头会,我就去了;也可能是靳卫红打电话给我,说某个策展人到南京来了,要约南京的艺术家见面吃饭,我就去了。《画刊》是有它的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价值观的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品观念上,第二个是作品质量和技术上,你得达到它的标准。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做作品,也做了好几年,到1995年才第一次发表作品。如果觉得自己作品拿不出手,我们也不好意思拿去请人家帮你发表。自己心里也得有一杆秤,做到一定程度了,觉得差不多能够契合它这个标准了,才拿得出手给《画刊》,看看行不行。




徐志君:当时你去找顾丞峰老师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出版社吗?
曹恺:我第一次见他还真不是在出版社,是到他家里去的,这个也可以讲是本地作者的某种优势。可能因为他和管策比较熟,我是跟着去的。管策是“85老炮”,“红色·旅”的成员,在《画刊》发过不少作品。当时《画刊》其实是轮流编辑制度,当时的主编是程大利社长本人兼,副主编是李建国,但是具体负责每期杂志的,就是轮值编辑。
孟尧:你跟《画刊》开始有作品发表和写作的来往,其实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
曹恺:其实第一次发表是我的一篇翻译文章,1992年吧。我那時候读大二,在啃英语,我父亲从美国带了一批资料回来,我就看到上面有介绍国外画廊的文章。那个时候画廊在中国还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当时南京没有画廊,北京好像也很少,基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当时我看到美国居然有“画廊群”的概念,然后我就把那篇文章翻译了,翻好后想:是不是能够找个地方发表一下?我父亲就把翻译稿给了他的大学老同学毛逸伟——他是出版社资深编审。可能毛逸伟就转给了《画刊》老编辑许祖良——当时的副主编,然后许祖良一看觉得还行,可能这种题材的文章当时《画刊》没有过,因为《画刊》当时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求新——有这方面的倾向。那篇翻译其实是一篇习作,但能发表对自己的鼓励也是很大的。

徐志君:我发现你发完一篇文章之后,好像中间好些年就没有再发,又过了一些年才开始发表。
曹恺:对。那篇习作我觉得是一个例外,它不在我整个个人艺术系统里面,只能说是跟杂志交往的一个经历、一个机缘。真正发生关系是从1995年开始的,后来我在1997年、1998年又做了个展。个展作品在《画刊》上面也发过,包括那时候朱其帮我写的艺术评论,都是在《画刊》上面发的。差不多从1995年到2005年,我一直是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身份,跟《画刊》之间保持着这样一个合作关系。

徐志君:跟杂志社前前后后打交道比较多的是哪些人?
曹恺:主要是顾丞峰、靳卫红,后期还有张正民,他们几个编辑我应该都打过交道,还包括最早的一个《画刊》编辑陈孝信——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杂志了。2004年我跟靳卫红为《画刊》制作纪录片时,也拜访了几个创始元老:索菲、刘典章、程大利等。
徐志君:我注意到你一开始在杂志中是艺术家的身份,处于一个被发表的状态,比如说别人文章里也会提到你;2010年之后,你自己的发表就开始多了起来。
曹恺:当中有一个阶段,我是在做跟独立影像有关的工作,独立影像与当代艺术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而《画刊》在选题上也一直推崇跨界和越轨,当时靳卫红就邀请我为《画刊》写过两次与独立影像有关的特稿,这大概是2010年前后。我还策划过一次比较大的独立影像专题。反正我跟《画刊》之间的关系,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以一种不同的身份在合作,因为我本人工作也有不同的转向和延展。大概是2016年、2017年以后,我主要转到实验媒体艺术的研究工作上来了,那么,我跟新的主编孟尧之间就有了一个新的合作,开了一个写作专栏,持续了3年。今年从个人专栏刚刚把它升级为一个栏目,我来做一个栏目的主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实验媒体艺术的研究性写作工作中来。



孟尧:你当时和《画刊》的编辑们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身上会有非常明确的杂志编辑的角色感吗?
曹恺:我觉得似乎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谈到某些议题时,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他们就会去跟进。他们对艺术前沿的动态是很敏感的。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海外的很多资讯就完全是靠《画刊》这样的杂志。德国新表现主义那几个大师当时到中国来做活动,全是通过《画刊》的特稿知道的。还有侯瀚如搞的“移动中的城市”,当时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一批在海外的艺术家的工作,也是《画刊》首发的。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了解到这些海外动向。
徐志君:实际上我觉得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报》的工作《画刊》在继续做。
曹恺:《中国美术报》在1989年年底就停刊了,当然,《中国美术报》那时候是很厉害的。实际上《中国美术报》跟《画刊》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我觉得很多资源是共享的。我记得那次我受邀拍《画刊》30周年纪录片的时候,靳卫红开了一张采访名单给我:刘骁纯、水天中、陶咏白、栗宪庭……这批人很多都是与《中国美术报》有关的人,他们同时也给《画刊》供稿。实际上,我觉得“两刊一报”背后的写作群是同一批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独立意识和自我立场的批评家。
徐志君:在我看来,因为20世纪90年代跟80年代情况不同:80年代,像《中国美术报》出刊的周期很快,比《美术思潮》和《画刊》都快,所以读者要从《中国美术报》上了解一些新的信息可能会更便捷,但是到了90年代情况似乎变了。
曹恺:20世纪80年代,其实主要是1985—1989年这个阶段,《中国美术报》那时每周都有出版,信息最快。但如果你今天重新回来仔细看《中国美术报》的话,它其实也是鱼目混珠的,也有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甚至也必须要报道一些学院派的主流声音。《美术思潮》的高名潞主持《美术》的那几年也是蛮厉害的,但存在的时间都很短。进入90年代时,是一种万马齐喑的感觉,其他前卫杂志报纸都停了,只剩下《江苏画刊》还活着。《江苏画刊》怎么办?很可能弄不好就像《美术》杂志一样,就变成一种纯粹的官方喉舌,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画刊》还维持了80年代的办刊面貌,延续了不变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画刊》最大的贡献是在90年代,它成为那10年里中国唯一还能看的专业期刊。到90年代后期,资本逐渐兴起后,又多了一两本杂志像《艺术家》《美术文献》什么的,包括有几期《画廊》等,当时因为有资本介入了。但是我们主要还是看《江苏画刊》。
我是赶上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末班车,我跟一般学艺术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我是生在一个艺术世家——我父亲在做水墨画创新,态度比较开明;我又处在常州这样一个比较良好的前卫艺术环境里面,我身边有浓厚的“八五美术新潮”的艺术氛围,但如果换成江苏的其他城市,可能就没有这样的前卫艺术氛围了。到了90年代,唯一能看得上的杂志就是《江苏画刊》。实际上《江苏画刊》那个时候它是特立独行的,它不投一般大众读者所好,编辑部的价值观主导了这本刊物,这些编辑在这个时候就变得很重要了。打个比方,我做过电影节的组织者,那么我怎么体现我们组委会的价值观?我不能直接去表达,但是我可以代表组委会去挑选评委,我挑选符合我价值观的评委,这些评委们再去评作品。所以,我虽然自己不能直接去评作品,但是通过我选择的评委体现了我对作品的一致认同。实际上,我觉得《画刊》的上层也很厉害——是谁挑选了这些编辑?这是一个关键的东西,而这背后我觉得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时势造成的、人文精神推动的。这跟江苏的文化土壤是有关系的,这样的文化土壤能够生成出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这个机制能够把这些编辑推到前台,然后通过这些编辑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手去抓取這些作者、作品,呈现出《画刊》的前卫面貌。
孟尧:站在你的立场,从一个合作者的身份,你觉得从《江苏画刊》到《画刊》,有哪些变和不变?
曹恺:实际上,基本价值体系没有变——这个是最难得的。一个人一旦成熟以后,他的价值观是不太会变化的。从当初到当下,今天我仍然能够读到这本期刊而毫无违和感,仍然深得我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它的一个恒定系数保持住了。那么从它的变化来讲,《画刊》当初跟“画”早就没有关系了,实际上,《画刊》不仅仅是一本视觉艺术杂志,也是一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学术刊物。早年的话,可能还是展讯、画评相对多一点。现在越往后,它的泛文化成分、跨媒体成分、复合型学术成分越来越高。这个我觉得是《画刊》的一个变化。
以我目前对这本杂志现状的了解,包括我本人还作为一个比较密切的合作者来说,我觉得《画刊》完全可以按照现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形态发展生存下去。《画刊》它已经是一个有传统的杂志了,这个传统的建立不是靠一两个人,而是几代人的工作——几代编辑、几代主编他们的工作集合而成的;在这之外,也是许多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理论学者、艺术管理人员等大家共同的工作都包含在里面,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传统、一个机制。这太珍贵了!
编者注:本文由“《画刊》50周年影像志”视频资料整理而成,内容经作者确认。
责任编辑:孟 尧 蒋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