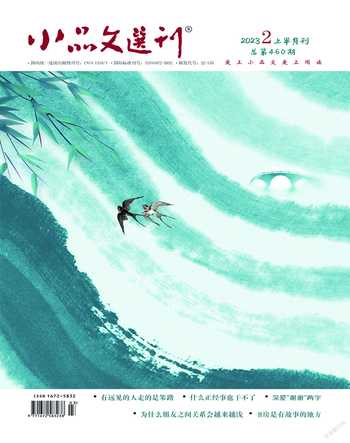母亲抓药
张延庆
“写写你吧。”我说。
“就写我抓药的事。”母亲笑了。
我很诧异。母亲笑了,我却差点儿哭了。有时和她说话,她也是沉默,最多眼睛看过来,并没有表情。小脑萎缩几年了,走路要扶,吃喝得喂,生活不能自理,这对于她已是常态。
过去的事很多,为什么要写抓药?
我7岁时,母亲得肝炎了。拉犁、浇地、挖河、运粪,种庄稼、收庄稼,常年重体力劳动,她要垮掉了。
得病后,她不看村医,也拒绝去公社医院,坚持要去县城看病抓药。此后的几年,她骑车往返,每每回来时,天都黑了。
这时,4个孩子就趴在窗前,往大门口看,天黑了是想娘了,没黑时则惦记好吃的。
县城离家三十多里,4个孩子都没去过。一个星期天,安抚好哥哥后,母亲让我和弟弟妹妹跟着,一起去抓药。我坐前梁,妹妹和弟弟则坐在后座。她跃上车时,后面的要把头低下去。两边的庄稼开始后移,心中的县城越来越近。
回来的路上,母亲骑得快,风从耳边刮过,药挂在车把,果子也挂在车把,随风摇曳着。
一次,母亲去抓药,只让我跟着。我胳膊上长了脓包,总也好不了,但我并不希望它好,长包的日子,我一直没去上学。为拖延时间,我还把打过农药的棉花叶,往脓包上抹。
这次回来,天也黑了,但母亲骑得慢,我胳膊上的绷带,在月色下泛着白光。到家了,她把我抱下來,问还疼吗?一点儿都不疼了,但我哭了。
“老二还能熬药!”村里人夸我时,母亲笑了。但我在想,我还会泡药,还会晒药渣呢。药渣晒干后,母亲就捣碎了,都用来装枕头。
两年后,母亲的病好了,家里从队上分到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到分地的时候,远在外地的父亲,坚持让我们过去。
从此,河北的家没了,山东的一个小县城接纳了我们。在这里,她有了心脏病,时常喝中药,每次都是自己去抓。
我从县城到省城工作,父亲知道后却说不去,倒是母亲给面子过来了。在省城,她又添了肺病,咳嗽得厉害。劝她吃西药,她也最多吃点儿丹参、丹灯,更多的时候,还是坚持喝中药。
母亲去抓药,坚持要坐公交。拗不过她,我陪着去了一趟。第二次她坚持自己去,回来时竟也没坐错车,以后熟了,我也就放心了。每次的药渣,她还是留着,还是往枕头里放。
感觉常是错觉。父亲去世后,我一直以为,母亲没问题的。但就在父亲走后,她的身体开始不行了,手抖厉害起来,反应迟钝明显,走路慢了,走不远了,甚至连楼都下不了。我时常把大夫请到家里,号脉开方后,她就催我去抓药。
每次把请人代煎的药拿回来,母亲总是问:怎么没熬啊?那些药渣呢?她确实是老了,那个带3个孩子骑车去抓药的母亲,去哪里了?
有时我晚上醒来,枕头上的药香味儿还在,但我知道,抱我下车的母亲却不在了。
选自《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