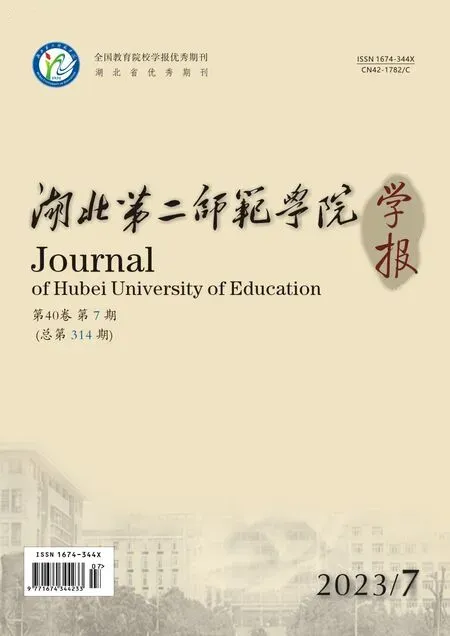寻找“去象征化”的可能
——基于《爸爸爸》的版本修改
熊高蝶
(湖北大学文学院,武汉 430026)
引言
“寻根”文学的代表作《爸爸爸》初次发表于1985年《人民文学》第6期,作者在2006年对其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于2008 年收集入《归去来》一卷中。期间作者对文本也进行过一些微调,但都没有08 年版的差异大。对此,日本学者加藤三由纪曾判定新版本算得上是一种重新创作,并认为2008年修改版的《爸爸爸》里蕴含着21世纪的远见。[1]国内学者洪子诚曾在《丙崽生长记——韩少功〈爸爸爸〉的阅读和修改》中针对两个版本中关乎丙崽的改动部分进行阐释,从中见证丙崽的这个人物形象的“成长”。从2011年始,国内学术界出现对新版本的引用,但同时也存在大量学者仍然以旧版本为参考。立足于新版本的学者多数还是在谈论旧问题,即八九十年代热议的对“国民性”“文化劣根性”的探讨,其他少部分学者有将研究视角向传统文化审美性本身转变的趋势。综观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爸爸爸》文本的开放性、复杂性的重视与强调,从不同角度质疑了对《爸爸爸》的单一化“国民性”批判。
通过细致对比《爸爸爸》1985 年的初版本与2008 年的修改本,可以再次印证作者在主题上的非定式表达:“《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理性和非理性都成了荒诞,新党和旧党都无力救世……但这些主题不是一些定论,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论,因此不仅是读者,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把握。”[2]《爸爸爸》中巫楚民俗文化审美意蕴具备去象征化解读的可能,与版本修改之前占主导地位的“国民性批判”等话语共同呈现出解读的多重可能性。在科技文化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面对这类经典的地域型寻根文学作品,可以从中发现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蕴,而非执着于以现代化的眼光去对历史时代的落后性大加挞伐。
一、人物形象:从二元对立到立体化
在落后闭塞的村寨中,仁宝的行为是有一些“奇异”的:他喜欢有技术的窑匠,喜欢和那些从山下来的陌生人搭讪,也经常独自下山晃荡……,他的这些言行举止在保守的鸡头寨里显得十分另类。甚至对于村民们古往今来、习以为常的杀人祭谷神之类的仪式,他指出了其中的愚昧性。在他所生长的环境中,他的思想无疑使他有可能成为一种新势力,从而打破本寨的固有观念系统。但是由于势单力薄,在那种群居式的关系社会形态下,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对于本土文化的反对和排斥又只能发生在口头上。
在1985年的版本中便已经体现了仁宝这个人物在新旧思想上存在的二元对立特质,但同时这种英雄式的人物刻画会在某种程度上有种失真的效果。在2008年的修改版中,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仁宝捣蛋的细节、强化了仁宝身上的立体性、矛盾性,并增加大量仁宝与寡妇丙崽娘的私情描写,填补了这种缺陷:
1.在描写仁宝聪明机智的主论调上增添调皮捣蛋的特点,具例如下:
例1:仁宝对窑匠的恭敬态度,后来加入了一些捣蛋细节
1985版:“这其中,最为客气的可能要数石仁,他总会盛情邀请窑匠到他家去吃肉饭,去‘卧夜’—当然是由于他在家里并不能作主。”[3]87
2008版:“这其中,最为客气的可能要数石仁,他一见窑匠就喊‘哥’喊‘叔’,第二句就热情问候‘我嫂’或‘我婶’指窑匠的女人。有时候对方反应不过来,不知道他是扯上了谁。三言两语说亲热了,石仁还会盛情邀请窑匠到他家去吃肉饭,吃粑粑,去‘卧夜’。”[4]75添加“石仁对窑匠最讨好,但一再讨好的同时也经常添乱,不是把堆码的窑坯撞垮了,就是把桶模踩烂了,把弓线拉断了,气得窑匠大骂他‘圆手板’和‘花脚乌龟’,后来干脆不准他上窑来——权当他是另一个丙崽。这使他多少有些沮丧和寞落。”[4]76
2.暗示与丙崽娘的乱伦情节,具例如下:
例1:在仁宝欺负完丙崽之后,仁宝同丙崽娘之间的情节变化
1985版:“后来,不知为什么,仁宝同她又亲亲热热起来,开口‘婶娘’,喊得特别甜,特别轻滑。帮她家舂个米,修个桶,都是挽起袖子,轰轰烈烈地干。对有关丙崽娘的闲言碎语,他也总是力表公允地去给以辩解和澄清。旁人自然有些疑惑。寡妇门前是非多,他们耳根不清静,被妇女们指指点点,也是难免的。
丙崽娘挤着笑眼看他,想为他说门亲……”[3]88
2008 版:“不过,后来仁宝同她并没有结仇,一见到她还‘婶娘’前‘婶娘’后的喊得特别甜。帮她家舂个米,修个桶,找窑匠讨点废砖瓦,都是挽起袖子轰轰烈烈地干。摘了几个南瓜或几个包谷,也忙着给她家送去。有人说,他是同丙崽娘打过一架,但打着打着就搂到一起去了,搂着搂着就撕裤子了——这件事就发生在他们去千家坪告官的路上,就发生在林子里,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说,当时丙崽‘x吗吗x吗吗’地骑到仁宝的头上揪打,反而被他娘一巴掌扇开,被赶到一边去,也不知是真是假。
反正结果有点蹊跷。看见仁宝有时给呆子一把杨梅或者红薯片,妇女们免不了更多指指点点:真的吗?不会吧?诸如此类。
丙崽对红薯片并不领情,一把掷回仁宝。‘x吗吗。’
‘你疯呵?好吃的。’
‘x吗吗!’
‘我x你妈妈呢。’
丙崽一口浓痰吐到仁宝的身上。
妇女们大笑:仁宝伢子,这下知道了吧?要x吗吗还不容易……。她们没说完,差点笑得气岔,羞得仁宝一脸胀红夺路而逃。”[4]77
例2:遭遇知音难觅的痛楚后,视线转移到女人身上
1985版:“他觉得对方并非知音,没什么意思。于是目光往左边的女人们投过去。有个媳妇,晃着耳环,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汗珠。跪下去时没注意,侧边的裤缝张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肉……他想:他,一定要去同那位媳妇谈一谈帽沿礼。”[3]89(第三章结束)
2008版:“你要相信我的话。”
“相信,当然相信。”(1985年版没有)
“他觉得对方并非知音,没什么意思。于是目光往左边的女人们投过去。有个媳妇,晃着耳环,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汗珠。跪下去时没注意,侧边的裤缝胀开了,露出了里面的白肉……直到叭的一声,他感觉脑顶遭到重重一击才猛醒过来。回头一看,是丙崽娘两只冒火的大圆眼,‘你娘的X,借走老娘的板凳,还不还回来?’
‘我……什么时候借过板凳?’
‘你还装蒜?就不记得了?’丙崽娘又一只鞋子举起来了。”[4]80(第三章结束)
例3:在仁宝爹仲裁缝与丙崽娘之间的故事情节中加入仁宝的成分
1985版:“不过,这一切都不如她那眼光可恶。似乎是心不在焉地看一眼,有毫无理由的理由,有毫不关心的关心,象投来一条无形的毒蛇。”[3]91
2008 版:“……像投来一条无形的毒蛇……堂堂仲满的儿子就是被这样的毒蛇缠住,乱了辈分,毁了伦常,闹出一些恶浊不堪的闲言,岂不是往他仲满耳朵里灌脓?”[4]82
在仲裁缝眼里,丙崽娘的眼神就如毒蛇。原版本仅将叙述话语局限在矛盾双方。而在修改版里又加入了对仁宝的描写,再次叙述前文仁宝与丙崽娘的绯事。
例4:将竹义家的大寨换成丙崽娘,增加他和丙崽娘的情节,删掉丙崽的情节
1985版:“‘仁麻拐,你耳朵里好多毛!’竹义家的大寨突然冒出一句。……丙崽是来看热闹的,没意思,就玩鸡粪,不时搔一搔头上的一个脓疮。整整半天,他很不高兴,没有喊一声‘爸爸’。”[3]97(本章结束)
2008版:“‘仁麻拐,你耳朵里好多毛!’丙崽娘忍无可忍,突然大喊了一声,‘你哪来这么多弯弯肠子?四处打锣,到处都有你,都有你这一坨狗屎!’……人们不知丙崽娘为何这样悲愤,不免悄声议论起来。仁宝急了,说她是个神经病……事后一个汉子揪住仁宝逼问:‘你对德龙家的到底怎么样了?她硬是吃得下你。’仁宝捶胸顿足地说:‘老天在上,我能怎么样?她是我婶娘,一个禾场滚子。我就是鸡巴再骚,不怕她碾死我?’汉子上下打量仁宝一眼,还是半信半疑。”[4]95(本章结束)
3.强化仁宝身上旧传统与新思想的矛盾性,具例如下:
例1:关于仁宝下山以及回来之后的转变
1985版:“他眼睛有点眯,没看清人的时,一脸戳戳的怒气。看清了,就可能迅速地堆出微笑。顺着对方的言语,惊讶,愤慨,惋惜,或者有悲天悯人的庄严。随着他一个劲地点头,后颈上一点黑壳也有张有弛。他尤其喜欢接近一些不凡的人物:窑匠,界匠……”[3]88
2008版:对于仁宝这段与众不同之特点描写挪放到仁宝下山之后。[4]79
例2:仁宝在给村民们谈及新事物与鸡头寨的落后时
1985版:“听说他挨了打,后生们去问他,他总是否认,并且严肃地岔开话题:‘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后生们不明白,保守是什么意思,于是新名词就更有价值,他也更有价值。”[3]89
2008版:“听说他挨了打,后生们去问他,他总是否认,并且严肃地岔开话题:‘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太落后了,不是人活的地方。’后生们不明白‘保守’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玻璃瓶子和马灯罩子有何用途,于是新名词就更有价值,能说新名词的仁宝也更可敬。”[4]78
例3:寨子里祭谷神的时候,仁宝的态度
1985版:他(仁宝)不以为然。“他见过千家坪的人做阳春,那才叫真正的做家。哪象这鬼地方,一年一道犁,不开水圳也不铲倒坳,还想田里结谷?”[3]89
2008 版:“仁宝大不以为然,不过受父亲鞋底的威胁,还是不得不去应付一下。只是他脸上一直充满冷笑。可笑呵,年年祭谷神,也没祭出个好年成,有什么意思?不就是落后么?他见过千家坪的人作阳春,那才叫真正的作家,所谓作田的专家。哪像这鬼地方,一年只一道犁,甚至不犁不耙,不开水圳也不铲田埂,更不打粪凼,只是见草就烧一把火,还想田里结谷?”[4]78
例4:仁宝下山久不归,父亲仲裁缝卧病在床,引起众人非议,骂他克母又克爹
1985版:“这些话,从耳后飘来,仁宝都听入耳了。他装着没听见,毫无意义地扫了扫地……”[3]95
2008版:“这一类话,从耳后飘来,仁宝不可能没听到。他跪在老爹的床前,抽了自己几个耳光,在地上砸出几个响头,又去借谷米给仲裁缝做了一顿干饭。见裁缝还是不理他,便毫无意义地扫了扫地……”[4]92
增加了仁宝孝顺的行为,传统思想的显露。
例5:在旁人的鼓舞下,仁宝为了端正形象忘记回寨言和的初衷,将自己视为预备烈士
1985版:“他显出知书识礼的公允,老腔老板地分析:‘炸不掉,躲得开的。不过话说回来,说回来,鸡巴寨(他也学着把鸡尾寨改称鸡巴寨了)明火执杖打上门来,欺人太甚!小事就不要争了,不争——’闭眼拖起长长的尾音,接着恶狠狠地扫了众人一眼,‘但我们要争口气!争个不受欺!’”[3]96
2008 版:……(同上)一个汉子肯定了仁宝的分析。仁宝受到鼓舞,说得更为滔滔不绝:“人心都是肉长的,总得讲个天地良心吧?莫说是你们,我对鸡尾寨的人怎么样?他们来了,我冲豆子茶,豆子是要多抓一把的。到时候吃饭,我油盐是要多下一些的。怎么能翻脸不认人呢?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对这样不知好歹的畜生,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讲……”[4]92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修改中可以看出,作者有意强调仁宝这个人物身上的复杂性,在原版本中仁宝与丙崽娘的关系叙述处于一种点到为止、含糊不清的状态,修改后则明显带有肯定性的暗示。在鸡头寨的种族关系中,丙崽娘还属仁宝的“婶娘”,这种有违伦理的情节描写对文章“象征化”的主题思想产生了消解。文章修改前,评论界对于仁宝的关注大都是“仁宝这一形象代表的是封建民族文化中懦弱的新势力,他们有了一点思想上的觉悟,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封建民族文化,力量太过薄弱。”[5]等象征化的论调。而修改后的版本,通过媚俗情节的大量增加既突出了以仁宝为代表的年轻寨民们身上的反传统封建思想,这是一种追求个性的新思想的体现。对仁宝身为男性所具有的本能特征的重点刻画,使这个人物不再如原版本那样过于英雄程式化,将关注点转移到仁宝这个作为巫楚传统文化滋养下的个体本身,关注他自身的复杂特质。
二、叙述基调:从冷讽到温情化
在原版本中,丙崽与丙崽娘总是被叙述为与众人不同的形象,丙崽的痴傻、癫狂,母子俩生活的艰苦将他们置于被众人唾弃的困境,学术界对于丙崽及丙崽娘的评价也基本上都是“国民落后性”的象征物等等。然而在修改本中,作者做了细节上的微调,缩短他们娘俩与其他人的差距,在展现丙崽“成长”的基础上增添了温情的论调。具例如下:
例1:当丙崽被仁宝欺负时变得聪明机智,母亲也表现得十分勇敢,为孩子谋公道,母子两人具有了反抗的能力
1985版:“他哭起来,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半个哑巴,说不清是谁打的。仁宝就这样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又一笔笔领回去,从无其他后果。丙崽娘从果园子里回来,见丙崽哭,以为他被什么咬伤或刺伤了,没发现什么伤痕,便咬牙切齿:‘哭,哭死!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碰到这种情况,丙崽会特别恼怒,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咬自己的手,揪自己的头发,疯了一样。旁人都说:‘唉,真是死了好。’”[3]88
2008版:“他哇哇哭起来。但哭没有用,等那婆娘来了,他一张嘴巴说不清谁是凶手,只能眼睛翻成全白,额上青筋一根根暴出来,愤怒地揪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手指朝着天大喊大叫,疯了一样。丙崽娘在他身上找了找,没发现什么伤痕,‘哭,哭死啊?走不稳,要出来野,摔痛了,怪哪个?’
丙崽气绝,把自己的指头咬出血来。就这样,仁宝报复了一次又一次,婆娘欠下的债,让小崽子加倍偿还,他自己躲在远处暗笑。不过,丙崽后来也多了心眼。有一次再次惨遭欺凌,待母亲赶过来,他居然止住哭泣,手指地上的一个脚印:‘×吗吗’。那是一个皮鞋底印迹,让丙崽娘一看就真相大白。“好你个仁宝臭肠子哎,你鼻子里长蛆,你耳朵里流脓,你眼睛里生霉长毛啊?你欺侮我不成,就来欺侮一个蠢崽,你枯脔心毒脔心不得好死呀——”她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丙崽去找凶手,‘贼娘养的你出来,你出来!老娘今天把丙崽带来了,你不拿刀子杀了他,老娘就同你没完!你不拿锤子锤瘪他,老娘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这一夜,据说仁宝吓得没敢回家。”[4]77
例2:减去“孤零零”一词,缩减丙崽娘、丙崽与其他家庭的差距
1985版:“母子住在寨口边一栋孤零零的木屋里,同别的人家一样,木柱木板都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这里的树很不值钱。”[3]84
2008版:“母子住在寨口边一栋木屋里,同别的人家一样,木屋在雨打日晒之下微微发黑,木柱木梁都毫无必要地粗大厚重——这里的树反正不值钱。”[4]69
例3:强调“亲情”一词,展现在特殊环境下亲情的在场
1985 版:“丙患娘笑了,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模仿,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享受。”[3]85
2008版:“丙崽娘笑了,笑得眼小脖子粗。对于她来说,这种关起门来的对话,是一种谁也无权夺去的亲情享受。”[4]70
例4:得知丙崽要被用来祭神时,丙崽娘的反应
1985版:没有描述
2008版:听到丙崽要被祭神的噩耗,丙崽娘两眼翻白、当场晕厥。后来天响大雷,丙崽幸存,“丙崽娘哭着闹着赶上来,把麻袋打开,把咕咕噜噜的丙崽抱回家去”。[4]86
例5:减去丙崽骂娘、众人喝彩的情节
1985版:“儿子骂亲娘,似乎是很好笑的事。于是有些后生拍手,喷酒气:‘丙崽,咒得好!’‘丙崽,再咒!’‘再咒!’气得丙崽娘绷紧一脸横肉,半天都不正眼望人。”[3]94
2008版:无
例6:丙崽观看杀牛,弄得浑身是血后被妈妈拎走,从被动禁足变为主动知羞
1985版:“她把丙崽象提小狗一祥提回家,当然少不了又是一顿好打。‘死到外面去做么事?做么事!要打冤了,你上得阵?’把丙崽一索子捆在椅子上,自己拿起三根香,掩门到祠堂里去了。”[3]94
2008 版:“她把丙崽像提猫一样提回家去。整整一天,丙崽没有衣穿,全身赤条条。他似乎还知道点羞耻,没有出门去巡游。”[4]89
丙崽在被仁宝欺负时,由原来的忍气吞声到后来的学会给母亲暗示;在被母亲拎回家后从被迫到出于自身羞耻心而待在屋内,修改本注意到了丙崽的“成长”问题,使丙崽不再如1985 年版本中那么痴傻得无药可救。以及描写丙崽母子夜晚促膝交谈的画面被冠以“亲情”的主题。原版本中丙崽第一次差点被用来祭谷神时没有描写母亲的反应,修改本则着重展现了丙崽娘听到消息后的绝望以致昏厥的场景,并删去丙崽骂娘的语词。作者的这些细节调整,传达了血缘亲情之浓与纯,不会因为生存环境及身体、智力状况而有丝毫改变,这便是人世间最温暖、最永恒的情感体现。韩少功在2004年谈到关于文学作品的“诗意”表达时,质疑评论界将《爸爸爸》定性为“揭露性漫画”的说法,反对将文本主旨归结为披露“民族文化弊端”。他指出小说中不乏“对山民顽强生存力的同情和赞美”,比如“最后写到老人们的自杀,写到白茫茫的云海中山民们唱着歌谣的迁徙,其实有一种高音美声颂歌的劲头”[6]。作者的这种意旨在两年后他对《爸爸爸》所做的修订中得到了更明晰的体现。修订版所强调的世俗温情消解了丙崽等人物身上一直以来被冠以封建、愚昧等“国民劣根性”的象征之意,在文化“寻根”的意义上将小说的主旨拉回到巫楚传统文化的精神特点上。
三、文化面貌:从点到为止到丰富渲染
除加藤三由纪外,日本学者盐旗伸一郎也曾在新旧版本问题上对《爸爸爸》进行过细致考究,他发现了两个版本纯粹从字数上计算,就有22708字—28798字的六千多字之差。而如果从内容上看,两者的差异则高达10725字,足以体现对两者进行版本比较的意义所在。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修改本增加的部分主要有这几个方面:一是有关丙崽、丙崽娘的描述;二是加重了仁宝和仲裁缝的分量;还有就是人们打冤前的吃肉仪式和交手杀戮的具体情景。其中对于第三类传统巫楚文化的增述,加藤三由纪读罢也觉“毛骨悚然”,凸显了巫楚文化在审美上的冲击性。修改本关于吃肉仪式及交手杀戮场面描写部分的改动,可见以下具例:
例1:丙崽被用来祭神但未果的片断
1985版:“本来要拿丙崽的头祭谷神,杀个没有用的废物,也算成全了他。活着挨耳光,而且省得折磨他那位娘。不料正要动刀,天上响了一声雷,大家又犹疑起来:莫非神圣对这个瘦瘪瘪的祭品还不满意?”[3]92
(然后就请了一个巫师指点说要炸鸡头峰,接着就展开了两寨的矛盾描写。)
2008版:先是提出“为什么祭谷神不用猪羊而要用人肉……”这些关于祭谷神的问题,接着详细地介绍了各个寨子祭谷神风俗的不同:“有些寨子祭谷神,喜欢杀其他寨子的人……但鸡头寨似乎民风朴实,从不对神明弄虚作假,要杀就杀本寨人。”当丙崽被摇到签要被杀时,增加了丙崽娘的反应“听到这消息,丙崽娘两眼翻白,当场晕了过去。”然后才有天上响雷的情节,最后此事以另一个短命鬼做替换告终:“重新商议,重新摇签,杀了另一个短命鬼,是后来的事。”[4]86
例2:两寨初次交手的场面
1985版:“在岭上吵了一架,双方还动起手脚来,鸡头寨的后生撤回去了。//寨里还是很安静。有鸡叫,有牛铃铛的声音,或某个屋顶下冒出一句女人骂男人的声音,只冒一下,就被巨大的沉默淹灭了。丙崽摇摇摆摆地敲着一面小铜锣……”[3]93
2008版:“双方初次交手,是在两寨交界处吵了一架,还动起了手脚。鸡尾寨有人受伤,脑袋上留下一条深沟,嘴里大冒白色泡沫。鸡头寨也有人挂彩,肠子溜到肚皮外,带血带水地拖了两丈多远,被旁人捡起来,理成一小堆重新塞回肚囊。”[4]87
例3:人们的吃人心态
1985版:“一个赤着上身的大汉站起来,发疯般地大叫一声:‘怕死的倚开!老子一个人……’又被几双手拉扯下去了,每块白布下面都有一双眼睛,每双眼睛里都有火光在跳动。”[3]95
2008版:“一个赤膊大汉突然站起来,发疯般地大叫一声:‘给老子上人肉!老子就是要吃罗老八的脔心肝肺……’
几个不甘示弱的汉子也站起来:
嚼罗老八的骨头!
嚼罗老八的脚筋!
老子要拿罗老八的鸡巴伴辣椒!”[4]90
例4:人们吃肉的样态
1985版:无
2008版:“前面已经有人吃开了。有的吃到了肺,不知是猪肺还是人肺。有的吃到了肝,不知是猪肝还是人肝。有的吃到了猪脚,倒是吃得很安心。有的吃到了人手,当下就胸口作涌,哇的一声呕吐出来。”[4]90
例5:两寨人再次动武的场面
1985版:“争了半天,最后还是服从有‘话份’的。于是用火攻,又打了一仗。混战回来点人头,发现又少了几颗。”[3]98
2008版:“争了半天,天意又变得茫然难测。不管是出于天意还是人意,这一天战端再起。鸡尾寨的人主动杀上山来。先是浓烟滚滚,大概是有人故意放火,大火顺着南风,很快就烧焦了鸡头寨的前山,直烧得鸟雀乱飞,一根根竹子炸得惊天动地,黑黑的烟灰到处降落……杀呵,杀呵,杀呵——杀你猪婆养的——杀你狗公肏的——在那一刻,一颗离开了身子的脑袋还在眨眼。一截离开了胳膊的手掌还在抓挠。一具没有脑袋的身子还在向前狂跑。很多人体就这样四分五裂和各行其是。”[4]97
对于“吃人”时人们的思想、行为及两寨交战场面的再度书写,不论是出于还原还是刻意夸张,都更加拉近了读者与小说所塑造的那个历史语境之间的距离。这种转向于极度刻画式的修改增加了文本的审美效果,修改本里血淋淋的战乱细节几乎将传统文化破败的画面如实呈现于纸上,让人毛骨悚然之余,由衷生发出一种悲天悯人之感。从1985年版本的点到为止、保守书写到修改版的丰富渲染,还原了作者所寻找的巫楚传统文化之“根”的繁盛面貌,同时更加深刻地展现了这些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原始思维模式。用一种文化的眼光来看,“寻根”文学的意义就在于认识巫楚传统文化的原始根脉。
四、余论
除以上几点关乎实质性的重要改写外,修改本在细节上也可以明显看出许多调整,即原来某些抽象、生硬的词语被替换为比较能被大众所理解的词语,语调更顺畅,对于一些寨里的风俗词汇,作者也加以详细解释,例如在2008版中对于“赶肉”“视”“渠”“吾”“宝崽”等词增添了解释性话语。这些修改都属于一种技术上的趋向“完善”,作用虽可见,但对于没有阅读障碍或不细致考究语言逻辑性的读者来基本可忽略不计。但是这种完善却减弱了《爸爸爸》原本的语言陌生化效果,情节上的补充虽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真实,但由于一些乱伦情节的加入则对文本的思想深度产生一定的消解。对于巫楚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吃人”祭谷神,及两寨混战的血腥场面描写,一方面将其中的寨民刻画得十分残忍狰狞,但同时深刻地展现了这些特定历史阶段人们的原始思维模式。
“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可能是社会现实的纯客观记录,而是作家以特定的观念意识自觉或不自觉筛选、提取、立体化了的社会现实,体现着作家创作时的意识本质”[7],而版本的修改则展现了作家创作意识的动态变化过程。修改版的《爸爸爸》所展现的巫楚文化面貌使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经济社会大环境下的人觉得新奇和大开眼界,明白我们的根之所在,回溯我们东方文化的源流。但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寻找与再书写,目的何在,是为了发现与记载那个曾经存在过的“湘西世界”,还是通过批判来发出改革的声音?笔者认为这种落后是一个历史性的阶段,作者既然大篇幅地将它展现出来,不仅仅是要起到重新审视的作用,同时也必定具有东方文化审美的价值。值得我们关注的应当是那些村民们在物资匮乏、局限的生活条件下丰富的“想象力”,他们身上依旧存在顽强的生命力、亲情以及信念。虽然其中也有写道人们的血腥,但这也属于原始群体生存的方式,对此我们需要以一种文化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社会,作为读者及研究者,更应该把眼光放在文本所塑造的那个不会再重现的巫楚文化世界,在了解东方文化之“根”的同时,获取审美的多重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