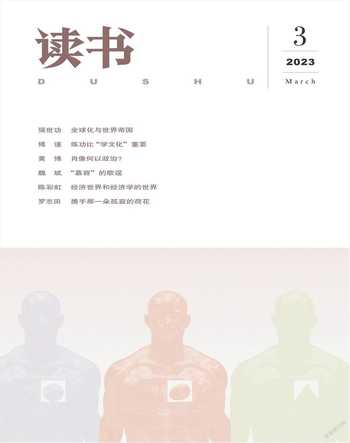亦真亦幻的近代中国家庭革命
张雯欢
在小说《家》中,当高觉慧站在他祖父——那个书中象征着黑暗封建旧家族势力的高老太爷面前时,这个深受新思想洗礼的进步青年觉得他面前躺着的是“一代人的代表”,他们两代人永远不会互相了解,他们的谈话没有一次像“祖父与孙儿”的谈话,他们没有一次不像“两个敌人”,这是近代中国家庭革命极具象征性的一幕,也是深刻影响了之后几代知识人对于传统家庭想象和认知的启蒙时刻。但当近代中国激进革命的狂潮逐渐退却之后,历史被剥离掉了为革命话语塑造的习以为常的“舊貌”,露出被遮蔽掉的需要重新同情之理解的“新颜”,以观照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赵妍杰的著作《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正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细致勾勒了从甲午战后到北伐之前,作为社会基石的家庭怎样一步步在读书人的眼中沦为需要被革命乃至被废除的对象,“家庭革命”的话语在历史不同的场域中同世界、国家、社会和个人虚虚实实地纠缠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激进的读书人在中西竞争的语境下,重置个人与家庭、国家与天下关系的一种尝试”,但其中叠加的想象与误解也让家庭革命在中西古今之间呈现出近代中国的特异性。
诚如赵妍杰所说:“近代中国家庭革命的特殊性在于不少读书人在抽象层面反思作为社会制度的家庭的存废问题。”家庭革命的言说起于晚清,甲午庚子的惨败令“家国天下”的体系断裂,家成为现实中的国和理想中的天下的对立物,一方面有亡国灭种之感的趋新士人认为家是为国效忠的阻碍物,因而掀起“为国破家”的言说;另一方面,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在西学东渐中与西方的各种无政府主义合流,构想出一个去私废家的大同之世来作为对各私其家的小康之世的超越。此外,家国天下的体系,也勾连着个人修齐治平的意义网络,因此前者的破裂,同时“是一种个人的解放”,传统家庭内父子、兄弟、夫妻的权威等级秩序与责任伦理“因其对内在的自我心理和情绪生活的漠视”,被树为虚伪的典型和压抑的意象而遭到无情的抨击。以觉醒自命的新青年将家庭视为急于逃离的桎梏,力图重新建构日用伦常间的价值观念。新的伦常是以爱情为核心的婚姻自主理念,正如李海燕在《心灵革命》中所说:“新青年们将情感抬升为个人身份与社会生活的支柱,他们不能接受夫妻双方没有感情经验的联系。”从情感出发,家庭革命改变着婚姻伦理并“围绕着婚姻制度的各个方面展开”。因此代际关系被冲击、夫妻关系被挑战、婚姻的不确定性增强,并让部分新青年脱离了旧式生活轨迹得以重新定义自我。包办婚姻被反对,纳妾被废除,旧式的婚礼被改变,片面的贞操被否定,结婚、离婚乃至再婚的自由被用法律固定下来,这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家庭革命建设性的内容,在本书中分别以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其理念和在当时情境下的复杂性,并力图复现出那些因失语而被屏蔽掉的“旧式妻子”与“旧式家庭”等悲惨而扭曲的背影。
但伦理变革影响之深广远超最初理性的预见,旧伦理中仅想脱离的家庭“经济关系”“名分关系”而不是“情感关系”并没有如他们所愿,新道德里“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也南辕北辙。旧式家庭不仅成为罪恶的渊薮,更在被负面形象所标记的退却中让一些家庭革命者进一步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理性建构一个人人脱离家庭只在社会中成长的那种无私忘我且绝对平等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夫妇自由离合,父子形同陌路,国家将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照顾每一个个体,这样挑战人性的构想在实践中往往带着改造人性的强制力,而“道德化的目的也将残酷的手段合理化了”,于是我们看到在本书没有涉及的下一个时代,家庭革命将幻化为“革命家庭”,即家庭生活的全面政治化。这些都让作者在以历史学家的目光重新审视家庭革命之时,始终反思“家庭革命是否需要”这个问题以及现代个人自由权利与传统家国伦理责任的边界和平衡。
“ 与家庭革命是否需要” 相伴随的,是革命中对扬弃的双方即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在虚实之间的想象与建构。巴金小说中那个累世共居的旧家族本身并非传统社会中的普遍形式,但却在文学的流传中成为未经历过传统社会与家族生活的读书人对于过去普遍的想象与感受,宗族中相互扶助的社会功能也被遮蔽与简化。无数身处小家庭的读者则根据小说想象出“大家族的压抑”,投射到自己祖父孙三代共居的“五口之家”的不满,建构出了一种“可以分享的共鸣”。而这虚实背后正是本书所探讨的近代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动摇了或彻底改变了”的“自我认知”。
与中式旧家庭黑暗负面形象相反的,是彼时西式小家庭在舆论中光明正面的形象,在新文化运动里,胡适曾为青年“描绘了一幅近乎完美的美国家庭生活画卷”—建立在自由结婚基础上由精神契合再到形体契合的相敬相爱的夫妇相处之道,而丝毫不提他此前曾注意到的美国家庭生活所存在的问题。当胡适也不够进步之后,趋新青年对西方的想象更是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罗素等人那里建构了一套开放、自由与激进的婚姻家庭学说,在有意无意间“过滤掉了保守的西方”, 形成了与西方主流社会思潮之间言说的错位。失真片面的东方与西方形象,呈现出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不断激进化的样貌。而究其所以,“是近代读书人对于西方思想资源的主动选择还是因时势的驱动无意中倾向于这一派的言说”,是一个需要被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强调因为缺少了对立面的声音,本书并非是她对家庭革命的完整研究,对立的声音“模糊而无力,基本上淹没在这浩浩荡荡的家庭革命的洪流里”。因此本书的核心任务是审视家庭革命的言说,尤其是那些激进言说在近代中国的制造与传布,探讨家庭在近代中国从一个“正面的社会建制变成一个负面的、可以废除的社会组织”的前因后果以及促成这种转变的思想学说和社会力量。作者未尽的研究指向了这类言说的对立面,两者相较展现出的似乎依旧是近代中国新旧之间的断裂与新陈代谢的历史逻辑。
事实上,在近代中国不断激进化的浪潮里,新与更新、激进与更激进之间永远后浪推前浪,家庭革命的言论在不断激进,但立言者也在不断代谢。换言之,本书所展现的家庭革命的“憧憬”是一代代立于潮头时的革命者的言论、情感和逻辑的言说,甚至很多对家庭抗争乃至决裂是他们一生中最极致处的“我”的展现,如同觉醒之刻的娜拉,但生活远比戏剧所呈现的有更多的牵绊和可能,如果将家庭革命审视的目光从一波波潮头的言论转向一代代潮起潮落的过程,就会如罗志田所说,“说革命”的人要比“干革命”的多,离家出走或许是很多青年人的憧憬,却必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换句话说,大多数的“娜拉”并没有出走,而是在发现了自我之后又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家庭宗族的责任义务,哪怕是文学中家庭革命的标志性人物觉慧和觉民的原型,即巴金与其三哥李尧林,在管家的大哥因经济破产自杀之后,这两位家族的叛逆者先后主动承担起了整个长房生活费用的重担,李尧林还因此牺牲了爱情、婚姻、事业乃至健康,早早死于贫病交加。晚年名满天下的巴金在同子侄辈的聊天中, 不忘叮嘱以后写文章,对家族的婆婆(继母)一定要公正,并忆起儿时继母对他的关心。“家里有一些小矛盾,难免”,但家人的情感是“大局”。可见哪怕在最激烈的家庭革命者那里,封建专制的家也并不能吞没那种情感、血缘、责任联系起来的“温暖且风雨同舟的家”。
因此对于那个时代大多数新青年而言,他们往往在接受了新道德之后又共处于旧伦理之间,他们既是家庭革命的言说者和接受者,又非完全意义上的家庭革命的践行者,身处新旧裂变之间,作为未出走的娜拉,横跨漫长岁月后对家庭革命的感受与潮尖浪头的“憧憬”之时又有怎样的不同?
本书曾引用齐邦媛《巨流河》讲述的她父亲在“成婚问题上与家庭的抗争和妥协”,作为新思想的接受者,齐世英一直到晚年还在和儿女讲他十九岁留学日本的时候被家里逼着回来成亲时所谈的条件与被欺骗的结局,年轻气盛的齐世英为此一个月后就丢下新妇又去了日本,正如作者在此处所分析的,齐世英这一类人留学海外所接受的新知与家乡长辈的旧俗之间“价值观念的变动极易造成家庭内部亲属之间行事的冲突”,而“原本有守礼意识的读书人在西潮的冲击下转而攻击礼教,在意识层面上疏离传统”。但齐世英在这场没有爱情的旧式婚姻中却以温和洁净的君子品行包容了包办的妻子,并在近代中国动荡岁月的颠沛流离里与之建立起了共患难的情感,以至于在晚年,他还会和女儿流着泪说:“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是多么的辛苦。”当家庭革命与家的意象融合在一起时,这些历经沧桑的家庭革命者如何安置与勾连自己生命中的旧伦理与新道德?
或许比齐世英更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家庭革命和爱情婚姻的倡导者,胡本人却在留美归来名满天下之时遵母之命娶了小脚太太江冬秀,这场并不革命的婚姻给他带来了新旧两派都敬重的道德形象,正如胡适自己对高梦旦所说,他接受这场婚姻是因为“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毁约, 使这几个人终生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都难受”。这点“不忍”之心的自我谦抑,成为胡适沟通家庭革命与旧式婚姻之间的价值方式,而他因此得到的巨大赞誉似乎又让人窥见那个在近代中国影响深广的激进的家庭革命之外被屏蔽掉的“重家的中国”,遥对着作者无法在影响中国的西潮中寻觅到的“重家的西方”。另外对胡适而言,旧家庭中的继子与后母、婆媳和妯娌等关系确实给他的母亲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但若不是传统孝悌伦理的权威,其母又怎可凭借他父亲的临终遗言而让作为继子的兄长出钱供胡适去上海读书?与胡适类似处境的萧公权就认为在父母早逝之后,他的读书成才得力于旧式大家庭制度。因此在其一生之中,对于旧式的家庭和婚姻多有维护之语,强调“责任论式的自由”。而余英时先生也从萧公权的例子中分析道:“五四”批判旧家庭制度往往有个人背景,“由于受了委屈的人才会呐喊,而没有痛苦经验的人则保持缄默,所以在五四时我们往往只听到前者的声音”。因此家庭革命尽管在新文化运动里是不容置疑的主流,“但以全中国的范围来说,恐怕还是有限度的”。
因此本书中所研究的那些视家为冰冷的牢狱、意图冲决网罗的言论,或许只是广大未曾出走的娜拉们整个人生中关于“家”“国”“我”繁复感受之冰山一角,还有巨大的面向隐藏在海平面下等待着被发掘与书写,也提醒着我们尽管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笼统看去,会扼腕于近代中国“未经理性考察的‘新’带来了不知多少不安与困惑”,但身处其间的人在“新就是善”“旧就是恶”之外会有着更多纵深的体验与感受,新旧之间也未必只有裂变的鸿沟与撕裂的苦楚这样生死契阔的决绝,还有更多隐匿于岁月深处的人间烟火。历史的叙事在剥离掉革命话语的建构与当时后世人的想象外,也需要更多的考察那些被言说遮蔽掉的日用寻常,来重新权衡这些去国去家的“憧憬”在不借助政治力量的时候对于反对者、沉默者乃至言说者自身行为影响的可能性与限度。否则,我们可能如当时人想象“黑暗腐朽的旧家族”和“光明的西方小家庭”之外,又在无意中想象了一个普遍且激进疯狂的“家庭革命者”群体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