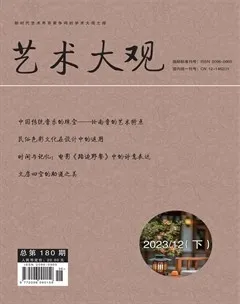马勒《大地之歌》的戏剧性解读
摘 要:古斯塔夫·马勒是欧洲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也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语国家举足轻重的作曲家、指挥家。他的作品涵盖面甚广,而以中国“唐诗”为文本的《大地之歌》交响曲最为广大中国乐迷所熟悉,本文通过对马勒生平及创作背景的分析,延伸至音乐中戏剧性的探讨,对六个乐章定义四重色彩进行细致的剖析,旨在更好地理解西方语境下的唐诗意境与马勒所传达的音乐精神内涵。
关键词:马勒;大地之歌;戏剧性
中图分类号:J6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3)36-00-03
“唐诗”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一直受到西方专家学者的关注与探讨。以中国“唐诗”为文本的《Das Lied von der Erde》(《大地之歌》)交响套曲,由著名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创作于1907年和1908年间,副标题为“一位男高音與一位女低音(或男中音)声部与管弦乐队的交响曲”,1911年11月20日由马勒弟子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首演于慕尼黑。该作品文本部分是马勒于德国作家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1876—1946)所著的83首德译唐诗集《Die Chinesische Fl?te》(《中国之笛》)[1]中汲取灵感,从中选用了七首唐译诗作为其音乐中的文本部分,在创作时马勒对七首译诗作了些修改与调整添加,以更好地传达他的精神世界与哲学理念。全曲共分为《大地悲愁饮酒歌》《秋日孤客》《青春》《佳人》《春日醉客》《告别》六个乐章。[2]
一、关于《大地之歌》音乐中的戏剧性
“所谓戏剧性,就是那些强烈的、凝结成意志和行动的内心活动……[3]”当然,音乐本身是无法直接构成戏剧性的,还需要具备戏剧角色与戏剧情境等特征。而诗歌恰好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语言高度凝练,依照一定的节奏韵律来形象地表达作者的情感与志向。尽管诗歌的适应性很强,意义明确,但即使最富激情的文本也只能在受限的感情层面上发挥效用,而音乐却可以自然而然地超越这个层面。音乐能够极其直接、单纯地呈现感情状态和感情层次[4]。音乐通过诗词的表达,被赋予戏剧性的功能,具有超越语言表达的优势。我们必须承认,音乐在感情和心理活动的部分,具有强大和微妙的通感作用。也正是音乐的这一特性,作曲家借助音乐中诗意的表达及音乐家的演绎,将丰富的内心活动传递出去,形成与听众之间的共情。交响曲作品中加入诗歌文本以丰富音乐是马勒常用的创作手法,这一做法使交响曲这种音乐形式变得更加戏剧化,加强和扩展了它的音乐叙事功能,使它不仅能描绘情感经历和戏剧性事件,还能表达哲学理念。马勒热爱诗歌,喜欢阅读单词的声音,喜欢诗的节奏、韵律,而这些往往就是作曲家发挥想象力所需要的一切。
马勒一生坎坷跌宕,可以说“死亡”在他的人生旅途中被刻上了深深的烙印,从他的《大地之歌》中感受到了“死亡之手”的触摸及对世间的绝望。在马勒艺术成熟期,“爱与死”的纠缠几乎是家常便饭,没有什么比身边人的死亡更深刻地提醒我们作为凡人的脆弱:幼年时兄弟姐妹的相继离世,大女儿玛利亚的不幸陨落,以及爱情上的失意和身体的致命缺陷,这种种沉痛的打击令人刻骨铭心,这一切的不幸也为《大地之歌》的创作动机埋下了不安的种子。曼陀铃的使用让人不禁联想到了舒伯特《美丽的磨坊女》中流淌不息的“小溪”动机,也正是这一音乐动机带来最终幸福破灭的图景。圆号在这部庞大的交响作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巨大的情绪反差体现在:如凯旋般的首章与如哀号般的终章。圆号作为典型的浪漫主义音响,是过去的呼唤,是记忆的呼唤,是距离的感性显示[5]。马勒的弟子布鲁诺·沃尔特(Bruno Walter)曾这样描述这部作品:“世界在他面前被温和的告别光芒所照亮”[6]。
生离死别的痛苦,以及作为“异乡人”的犹太人身份都始终是他心中抹不去的阴霾,他的一生都在追问自己的命运何去何从,悲观的宿命论色彩也不禁让人怀疑,《大地之歌》想要传达什么:是看清了世间本质后的无力感,产生了“醉生梦死”般的消极态度?还是如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hard Bernstein)所说的“灵魂的永生”观念,即“灵魂”死后与大地融为一体,实现“涅槃重生”?答案是什么并不重要,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的作用与魅力正是在于能够解释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复杂情感。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曾说过:“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我们真正听到的是我们自己”。也许从马勒《告别》乐章终末他自己编写的几句诗词中能找到一丝踪迹:我要返回故乡,我的家园,永不在外漂泊流连。我心已宁静,等候生命的终点。可爱的大地,年年春天何处没有芳草吐绿,百花争艳!地平线上永远会有曙光升起,长空湛蓝,永远……永远……[2]
二、《大地之歌》音乐中的四重演变
(一)醉意退却,只剩孤寂愁凉
引自李白诗作《悲歌行》的《大地悲愁饮酒歌》是该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马勒借以诗中的意蕴隐晦地表达了人类的脆弱与生命的短暂。该乐章在一种不和谐的刺耳的,犹如一团窜动的火苗般声响中展开,躁动不安的音符宣示着一切。作曲家在人声首句就提示要“Mit voller Kraft.(用尽全力)”演唱,无数的高音跌宕起伏,如猛烈的海啸般扑面而来,这将是对美酒、对人生和对世界发出的强烈宣告,也似乎向听众传达着如同凯旋般胜利的场景。在小提琴和木管乐器充满悲叹色彩的铺垫下,应和着男高音如同醉酒般的热血狂放,神秘的面纱正一步步被揭开。清醒后便是云淡风轻,在三次富于哲理的“Dunkel ist das Leben, ist der Tod!(黑暗主宰生命,黑暗即死亡!)”唱词中,灵魂拷问般将一切归于平静。《大地悲愁饮酒歌》无疑具有“强烈性和独创性”——以“大地的苦难”为对象的悲痛与惊呼,以及中段夹杂的转瞬即逝的、痛苦的温柔都深刻地对大地、世界和生命作消极悲观的陈述。反复三次的唱词,如马勒的“命运三锤击”[6]般道尽这人世间的悲愁与无奈,也许他宁愿活在醉意阑珊的人生中不愿醒来。
引自钱起诗作《郊古秋夜长》的《秋日孤客》是该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该乐章马勒定的基调是疲惫的。苍茫凄凉的意境与潺潺流动的音乐相得益彰,表达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孤寂的秋夜中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愁楚之情。乐章在小提琴凄凉的旋律中缓缓展开,交叉应和的双簧管与单簧管仿佛是孤寂秋日中的哀鸣。随着女低音声部(亦可男中音演唱)的进入,字字句句如泣如诉、意味隽永,诉说着无尽的苦涩与惆怅。中国古人对“秋”的描述数不胜数,多是以悲愁、萧瑟、孤独等字眼来形容,马勒的这一曲子也把握住了中国诗人对“秋”的精髓与意境。《秋日孤客》是六个乐章中情绪最为悲愁的一首,全曲透着一股“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情境。从这里也不难看出,马勒借以诗意的表达,诉尽他那落寞孤寂、疲惫不堪的心灵。
(二)恣意洒脱的青春
引自李白诗作《宴陶家亭子》的《青春》是该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描述的意境是与好友把酒言欢,畅怀青春的那份闲情逸趣。《青春》乐章是所有乐章中中国色彩最浓厚的章节,在这一乐章中,木管乐器以悠然自得的五声音调作为引子,犹如中国的长短笛,用其清新的音调勾勒出一幅充满趣味的生动画面。轻快的音乐响起,在男高音绘声绘色的演唱中,一座古典的具有中国韵味的花园亭落仿佛映入眼帘。“饮酒聊天”是这一乐章的主题,马勒借以轻松愉快的主题,表达心中那种对青春的欢乐和对美好的向往。中后段突然情绪转换,提琴低沉如歌如泣的音色模仿长笛活泼的主题音乐动机给这一青春蒙上了一层阴影,似乎预示着美妙的青春只是镜花水月,犹如诗句中池塘美妙的泡影梦幻般终将消散。但很快音乐又回到了活泼愉快的主题:今宵有酒今宵醉,又何必庸人自扰?!这是马勒心中虚构的理想世界,欢歌笑语与饮酒畅怀是他心中的美好愿景,似乎也从侧面反映了马勒对时光飞逝、美景易逝的无奈。
引自李白诗作《采莲曲》的《佳人》是该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有意思的是,《佳人》乐章是几个篇章中少有的白月光式的清新之作,也是唯一没有“醉生梦死”消极情绪意味的乐章。《佳人》乐章在清新典雅的小步舞曲节奏中优雅展开,充满吸引力的女低音声部轻柔地诉说着河岸边,一对才子与佳人邂逅的故事。旋律灵活飘逸,极富戏剧张力和画面感,延续了前一乐章对中国古典色彩的印象,反映出“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中举”的曼妙韵味。原诗作含蓄地表达出了少年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意绵绵、娇羞思春之情。而在马勒的音乐中,似乎融入了西方思维与情境,描绘出一幅西方男女之间大胆直接表达爱意的画面,缺少了东方男女之间的那种娇羞与含蓄,让人听后感觉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妙龄女郎,望见了不远处骑着白马的英俊少年,眼中迸射出爱情的火焰,言语中掩藏不住对喜爱之人满是赞美的语句,一切都是那么的直接与奔放。从音乐中我们还能感受到曲子前后的巨大反差变化:前面还和风细雨的,突然间就狂风大作让人猝不及防。不过这是马勒惯用的手法,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情绪巨大反差式的表达。虽然跟李白的原诗作都是描述同样的事情,但东西方文化、语境、意境的不同,理解起来也就大相径庭了。
(三)宛如一梦
引自李白诗作《春日醉起言志》的《春日醉客》是该交响曲的第五乐章。乐章中醉客与鸟儿间的呓语着实有趣,处处散发出春天的气息。小提琴轻快、颤动的声音如同鸟儿的鸣叫,在竖琴美妙的滑音衬托下,仿佛置身在美丽的大自然中。男高音断断续续的唱词与不断变换调性色彩的乐段,像是喝醉酒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语的醉客,在迷迷糊糊与浑浑噩噩中对着树上的鸟儿喃喃自语。看似有趣的背后,真相却令人唏嘘,也许可以这么理解这位醉客:回首平生,少年的欢情,壮年的襟抱已渐渐远去,飞逝的岁月留下的只有命途多舛的凄绝记忆,还不如借以美酒在春夢中随其消沉下去。结尾处的“春天与我何相干?且让我沉醉不醒!”似乎正是传达了作者“醉生梦死”的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马勒六个乐章中有四首都提到了“醉与酒”,三首提到了“睡与梦”,这不难让人觉得,马勒有想借以酒与梦抒发出“人生不过一场梦,不如进入睡乡,忘情于梦中新生的幸福与青春”的感叹!
(四)与大地的告别
第六乐章的《告别》分别引自孟浩然的《宿夜师山待丁大不至》与王维《送别》。《告别》乐章篇幅庞大,足足占了整部交响曲的一半。文本来自两首不同的诗词,但都有告别的寓意。作曲家给出了“沉重的”一词的音乐提示:当哀悼的钟声响起,双簧管那极具仪式感和穿透力的声音划破长空,在圆号的呼唤声中,映射出这将是一段充满悲情的旅途。悠远绵长的大提琴,应和着悲凉肃穆的长笛音调,烘托出“送别”的伤感意蕴。女低音低沉悲恸的声音如同祷告,沉默地祷念着人世间的哀愁。音乐中隐隐约约能听到似“脚步”的声音,当然,在马勒的其他作品中也能寻见同样的“脚步”。“脚步”走走停停,时而急促,时而缓慢,让听者仿佛随着主人公的视角踏上了这不寻常的人生旅途。终末,歌手反复地演唱着“永远”,气若游丝般地发出最后的宣言,像是与大地做着最后的诀别。从pp(很弱)到ppp(极弱)再到pppp(最弱),直至最后的“完全渐死亡的渐弱至消失”,声音随着音乐逐渐减弱,直至最后几小节接近虚无。缓慢而沉静的乐句之间沉默得令人窒息,如同将死之人弥留之际向大地发出的最终愿景与心声。
文字的尽头是音乐,伟大的文本也为伟大的音乐家提供源源不竭的创作灵感和创造性的动力。当然,马勒并不是为那些文本所做的“配乐”,在他宏伟壮阔的交响诗篇里,音乐与文本“并驾齐驱”、相互映照、相互渗透、融为一体[6]。马勒的交响曲音乐主题丰富、思想内涵深刻,他的交响曲不仅仅因为它雄伟磅礴的气势,更在于他那以世界万物、爱与悲、人类与创造、灵魂与救赎等极富于哲学理念的主题。他的音乐超越了民族、种族与国界,因为音乐能传达人的思想与意志,马勒将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转化为绚烂的音符,令听者与之产生共鸣。这也许就是在普世价值观下,马勒作品至今常演不衰,令世人为之着迷与疯狂的原因吧!
参考文献:
[1]钱仁康.《大地之歌》词、曲纵横谈[J].音乐研究,2001(01):27-36.
[2]邹仲之.冬之旅:欧洲声乐套曲名作选[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3][德]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M].张玉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4][美]约瑟夫·克尔曼.作为戏剧的歌剧[M].杨燕迪,译.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5][美]查尔斯·罗森.浪漫一代:19世纪上半叶的西方音乐风格[M].刘丹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
[6][英]史蒂芬·约翰逊.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M].张纯,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交响性与戏剧性的有机统一——马勒艺术歌曲的艺术指导教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0405)。
作者简介:骆洋(1989-),男,江苏南通人,博士,国家二级演员,从事声乐演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