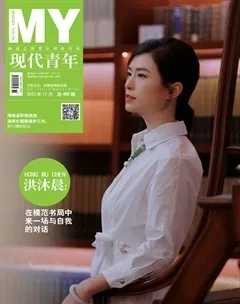远去的三亚河记忆
吴松
朋友,当我问你认识三亚河吗?你一定认为我是在搞笑,那条日夜流淌涌入南海的三亚河,谁不知晓呢?没错。不过我说的是那条印着沧桑痕迹的三亚河,已经远去的三亚河。六七十岁的老三亚人一定还记得三亚河过去的模样,尽管有些模糊了。但新生代的三亚人和移居三亚的外地人对她的老模样肯定是一无所知了。
那么,我就带你走近那条承载着悠长故事的三亚河吧。

五十年前,三亚河河面辽阔,烟波浩渺,对面的景物看起来显得隐约和朦胧,给人一种海市蜃楼的感觉。两岸滩涂很宽,生长着茂密的红树林,涨潮时,海水浸没了红树根,只露出树的上半身。退潮时,红树又展示其盘根错节的根系,这些发达的树根深深扎入滩涂里,为海生小动物营造一个温暖的家。这时,一条条跳狗鱼拖着长尾巴从泥洞里爬出来,躬着身子,支起退化的双脚不断地跳跃着游走着;一条条海蚯蚓(土虫)躲在滩涂的深处,不断地往泥面喷水,正好中了赶海人的下怀,只要挖虫人把小铁铲往喷水的小洞边一挖,土虫就连泥一起被挖出来,自然就成了篓中物了。土虫是一种特别美味的海产,不论煮、炒还是上汤,均是上乘佳肴。滩涂上还生活着一种小螃蟹,模样十分可爱,短小的身子却长着一对大螯,浑身红白相间。这种蟹是群聚性动物,常常是成群觅食,成片成片的布满了整个滩涂,只要人一靠近,它们立马钻入身边的洞穴,瞬间无影无踪。这种蟹也是美味食材,当地黎族同胞把蟹清洗干净后捣碎,搅糒(干饭)一起装入土罐子密封,经过一段时间的酶菌发酵后就酿成了蟹茶。据说黎族人是在接待贵客时才用上鱼茶或蟹茶,以表敬重。红树的枝叶上,还生长着一种类似蠕虫的小生物,样子似蜗牛。那时候食物匮乏,母亲为给我们增加蛋白质便到红树上捉来一些,过滚水后去掉粘液,然后切片加椰丝爆炒,味道可口。
但现在,那般缥缈的水域已不存在,那些美味也成为记忆。
在九十年代初,市政府为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策划了“120工程”项目,即在河西沿河一带抽泥造陆,打造出一块120亩的商业用地,加上河两岸也抽泥造路,使三亚河道变得狭窄了,两岸仿佛咫尺之遥,人们伸手可及。河水也变深了,滩涂几乎丧失殆尽。失去了天然的庇护和生存的土壤,加上人们的过度捕捉,小动物们现今已难觅踪影了。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当一方面失去的同时,另一方面一定有所收获。当填土造地工程完工后,市政府就在这片土地上,举办海南第一届“椰子节”,以“政府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大力招商引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较短的时间内打开了三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几十年的能量积淀,才有了今日的三亚。
徜徉在三亚河岸,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一棵棵红树簇拥着,海风翻动着树叶发出沙沙声,极像情侣们耳语厮磨;在浅滩处,一只只白鹭闲庭信步,或觅食或舞蹈,向人们展示它们的快乐和幸福;一艘艘漂亮的汽游艇穿梭在那片蔚蓝的河面上,翻滚着雪白的浪花,引来无数海鸟的追逐;笔直的河堤,蜿蜒通幽的亲水栈道,充满着游人的欢声笑语……
可是在很久以前,三亚河并没有被赋予多少旅游功能,而是承载着繁重的运输和制盐工作。岁月沧桑,这条三亚河,三亚人的母亲河,便以柔弱的身躯挑起历史的重担,支撑起三亚经济的半壁江山,造福她的子孙后代。
有句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三亚有着得天独厚的制盐优势,海水含盐度高,沿河地势平缓,是制盐业的天然处所。在当时,盐田如棋盘般散落在三亚河的周边,最大的盐区在月川村外围到现今的丰兴隆榆亚新村,洋洋上万亩地。每天,盐场工人冒着毒辣的太阳制卤水铲盐巴,一堆堆盐像一座座小雪山,折射出晶莹剔透的光芒。这些盐是在等待转运,要运到盐场部,场部地址就是现在的三亚国际大酒店那片区域,那里建有许多个硕大的盐库,从各方運来的盐都储放在盐库里。

为保证盐田用水,盐业部门在三亚河建起了一个长约一千米宽约二百米的长方形土堤,把河面一分为二。土堤类似小“水库”的堤坝,自然具备蓄水的功能。土堤的半腰设有一个闸门,可以根据盐田用水情况而灌水或排水。在靠近盐田的陆地段,也建起一个小闸门,专门给盐区输送海水,满足制盐用水需求。
7岁时,我随父母生活在月川附中(今月川小学)。每天早上大约十点和下午四点,便从三亚河传来“突突突”的机器声,那是运盐的机船。走到土坎边极目远眺,只见一艘轮机船拖着七八艘小木船,十分吃力地朝着盐场部的方向行驶。每只小船都堆满盐,没有遮掩直接暴露在太阳底下。每只小船都有一个船工把舵,确保船体的平衡,炎炎烈日下,船工们该有多辛苦呀!我想,这些盐一定很咸,因为它浸润了盐工们和船工们的汗水,这些盐一定是白花花的银子,用它们支撑起这座城市的发展壮大。
后来,盐场因为客观原因停止了盐业生产,许多盐区成为商业用地和盐工居住小区。那个小“水库”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土堤也被挖除了,恢复了三亚河原本的样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三亚河已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时代变革的渡口,她又背负起更大的梦想,为建设美丽三亚,向世界推介美丽三亚,她用彩笔为世人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和一张精美的名片!
朋友,你了解那个远去的三亚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