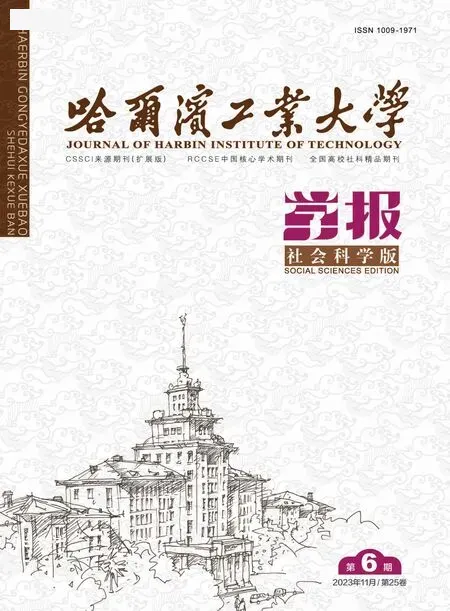不忍之忍:儒家的生态伦理智慧论析
姜 楠,吴先伍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23)
由于“不忍人之心”构成了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根基,而“仁”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人们高度关注儒家的“不忍”概念,对其展开了大量分析讨论,“不忍”的内涵和道德意蕴得到了全面深入阐发。 由于“忍”在字面上与“不忍”相互对立,包含残忍的意味,所以,与“不忍”相比,人们对于“忍”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然而问题在于,在儒家那里,“忍”与“不忍”不是一种简单的彼此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关系,二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就像我们在面对他者时不仅要“爱”,而且要“恶”一样,我们对于他者有时要表现出“不忍”,有时也要表现出“忍”;否则,我们就会成为是非不分的“乡愿”,就会造成对道德的破坏。
由于“不忍”表现为对于他者的仁爱之心,所以它与现代的生态伦理高度契合,因此,学者们高度关注对于儒家“不忍”的生态伦理意蕴的阐发。正如前文所言,忍与不忍是辩证统一的,一味地强调“不忍”也会导致对于自然的过度保护,从而导致对于自然的破坏,只有用“忍”来对过度的“不忍”加以纠正,才会使自然保护回归正常之途。这也就是说,在生态问题上,一味地讲“忍”或“不忍”,都会陷入一种片面性,应该将“忍”与“不忍”结合起来,做到“不忍之忍”,才会使生态保护真正走向中庸之道,既不“过”也不会“不及”。
一、不忍:自然保护的内在根基
现代生态破坏之所以如此严重,这与人类对于自然的残忍做法有着密切的联系。 尤其是20世纪以来,人类对大自然所采取的残忍行为比比皆是:为了获得美味,人类对鱼翅的追求导致全球每年被捕杀的鲨鱼数目超过100 万条,鲨鱼也面临着灭绝的风险;为了获取利益,人们在买卖麝香的过程中进行了残忍的捕杀:猎人为捕麝而设下陷阱,然后用剑射杀,或用木棍打死麝鹿;为了追求时尚,人们穿戴貂皮大氅,殊不知一件皮草的制作需要残忍地杀害三十余只无辜的小貂……通过研究可以发现,造成动植物大量灭绝的原因并非大都来源于自然灾害,人类对大自然的残忍行为才是其主要因素。 “特别是由于商业贸易而导致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是造成物种濒危乃至灭绝的重要因素……”[1]这一系列残忍的行为给人们带来了持续性的威胁,由于人类对自然过度的开发以及大量的捕杀与掠夺,使得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由于人类的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2]总而言之,现代生态的破坏之所以如此严重,与人类的残忍心态和残忍行为有关,正是因为人类对伤害乃至死亡的冷漠,面对生命遭到毁坏与伤害,人们才会无动于衷,甚至还会去故意对生命进行破坏,而这与儒家的“不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古代汉语中,“残忍”一般用单字“忍”来表示,比如《国语·郑语》中说“其民沓贪而忍”[3],“忍”在这里就是个负面的词汇;《左传》中说“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也”[4],也是同样的含义。 其实,人们之所以对大自然进行残忍的破坏,实际上与缺乏内心深处的“不忍”有关。 作为“残忍”的对立面,“不忍之心”则表现为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因此,对待自然生命,人们必须给予情感上的关爱,必须重新对自然充满敬畏之情,且常怀有一种“不忍之心”。 在儒家思想当中,对伤害的“不忍”之情一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对自然保护的内在根基。
一直以来,儒家把“不忍人之心”作为“首善之端”加以强调,而其中孟子的“不忍”之说更是重中之重。 对于生命的看法,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就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这里讲到,齐宣王在看到牛被拉去釁钟时,因其“觳觫”而内心产生了不忍之心,因此决定“以羊易之”,如此一来,既可保全釁钟这一祭祀制度不被破坏,又能不伤害受到惊吓的牛。 这则故事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不忍”的肯定态度。 齐宣王讲到:“齐国虽偏小,吾何爱一牛?”齐宣王并非是不舍得舍弃一头牛所产生的价值,而完全是因为牛之觳觫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不忍之心。 因此,这种不忍之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并非刻意为之。 随后,孟子对齐宣王这一仁义之举做出充分肯定,并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5]194这说明,君子在对于生命的态度上,是一定具有不忍之心的。 君子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因此才会有“不忍”这种坚定的生态保护意识。由此可见,儒家的“不忍之心”为人们提供了仁爱世间万事万物的内在根据,它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保护动物的心理——“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在这里,孟子借助齐宣王这样一个道德不怎么高尚的人来强调这种不忍之心,更加说明了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当自然遭到破坏,无论是品行高尚的君子还是世俗之人,皆会因自然万物受到伤害而产生怜惜之情,并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忍之心”,且毫不犹豫地想要去保护。 这正是儒家所具有的一种在面对大自然产生的问题时,坚决要保护自然万物的原则上的坚定性,而这种坚定性正是通过没有受到理性约束的“不忍之心”表达出来的。
宋明儒者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诠释中同样蕴含着“不忍”的思想。 这不仅是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延伸,同样显示了“不忍”在儒家价值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看来,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共通的,而“万物一体”正体现着这种思想。 人类与世间万物是一气相通、互为一体的,“我”能够感应到自然万物的感受,因此,当自然万物受到创伤时,“我”便会感应到这种痛苦,并油然而生一种悯恤与“不忍之心”。王阳明就在多处对“万物一体”进行了诠释,他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 ……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6]1066当一个人能够与鸟兽、草木瓦石为“一体”,甚至在它们有不幸时也能感受到它们的不幸,这便说明人与这些存在物已然连成了一体,形成了相互的感通,我们不再能够忍心看到自然万物受到伤害、遭遇痛苦。 在王阳明看来,“大人者”的优良品质在于将自然与人合为一体,人对自然应当具有敬畏之心,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即是“不忍”。 如果说孟子的“不忍之心”主要是针对人与动物的生命,那么王阳明则更进一步提到了对植物以及世间万物都要有“不忍之心”。 既然人已经达成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那么无论是看到鸟兽哀鸣亦或草木摧折,甚至于瓦石毁坏都要产生“不忍之心”。 相较于原始儒家多强调的对动物生命的不忍,王阳明则把它提升到一个更加广大的层面,即世间万物的层面去进一步发掘与提倡“不忍之心”。 前面已经提到,儒家对于生态伦理的观点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那么自然的层面显然不仅仅包含动物的生命,而植物的生命、飞沙瓦砾的生命,同样是人们需要去关注的,甚至于“悯恤”与“顾惜”的。 因此,当人们看到它们因一系列的原因受到来自外界的破坏时,一定与“见其生,不忍见其死”的齐宣王一样,对万物“必有不忍之心”,“必有”指毋庸置疑的,因此这充分体现了儒家对于自然进行保护的坚定原则,以及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生命的崇高致意。
在儒家经典中,除了直接讲到对自然的保护需要“不忍之心”之外,还有大量的例子讲到了对破坏自然的反对,这些都在字里行间描述出对伤害自然的“不忍”。 《论语》中讲:“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7]很多人喜欢射宿,因为鸟要归巢,飞行的方向容易判断,只要在鸟巢旁边等着鸟飞回,一箭一射便能射中。 然而,孔子却讲“不纲”与“不射宿”,那说明他是对这种行径持明确的否定意见的。 “钓而不纲”指单钩钓鱼不用网,盖因用网有“一网打尽”所有鱼的可能,因此孔子不忍将幼小的鱼苗捕杀;弋而不射巢中之鸟,是因为在巢之鸟不是待哺的幼儿就是正在孵化的母鸟,孔子不忍捕杀宿鸟,因为这就等于杀鸡取卵。 因此,“不纲”“不宿”都是“不忍”的体现。 后世白居易便由此写下“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的诗句告诫人们要将大自然认为是人类的生身父母。 因此孔子认为,破坏自然,乱砍乱伐滥捕滥猎,损伤的是民生,是最大的不孝。 所以,他不忍捕捞与射杀,坚定维持自然界的平衡。 由于《论语》的前后句不存在关联,因此很难去更加准确地解释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与之相比,《荀子·王制篇》中的部分内容则更加清晰地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荀子讲:“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8]163这种做法被荀子称之为“圣王之制”,说明他是把这种保护自然生态的做法放在一个很高的层面去论述的。 那么在这段话中,“圣王之制”所包含的内容有六个“不”字。 其中,“不入山林”与“不入泽”指的是不进入山林砍伐肥美的草木,不在动物繁殖时期入泽进行捕捞;“不夭”“不绝”分别提到了两次,指的是不夭折其生命且不断绝其生长。 足以见得,荀子是提倡且推崇人类对待自然要采取这六个“不”的。 而这六处“不”正是不忍之心的体现:当植物正在发育的时候,我们不忍心去砍伐它,不忍使它们的生命就此夭折,不忍断绝它们的发育;动物产卵时,我们同样不忍向湖泊中投放渔网与毒药去伤害它们。 在荀子看来,世间万物的生命都是可敬的,各色的生命形式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万类霜天竞自由,因此人类不能破坏这种平衡,也不忍去破坏这种平衡。
“不忍”既然作为保护自然的内在根基,那么是不是只有“大人”“圣人”才能够具有呢? 很显然,对于儒家来说,“不忍之心”并非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都能够具有的一种自然禀赋。 前面提到,即使是齐宣王这样一个道德并不是很高的人都能够具有“不忍之心”,说明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具有的:“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5]237朱熹在解释孟子的这段文字的时候说:“怵惕,惊动貌。恻,伤之切也。 隐,痛之深也,此即所谓不忍人之心也。”[5]237从这个解释中可以看出,“不忍之心”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感,“不忍”就是对一种残忍的事情在内心当中所造成的情感上的扰动。 当人们见到“孺子入井”时油然而生一种“不忍之心”,并非是因为其中有着怎样的利害关系,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同身受。 可见,“不忍”是所有人都能够具有的一种品质,任何人都能够做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5]340。
将“不忍之心”放置在生态领域,更多强调的是对整个生物圈的保护,而非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足以见得,儒家对待生态的“不忍之心”有着与深层生态伦理学相类似的观点。 深层生态学理论挪威著名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 年提出的观点。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他强调不能只从人类出发,还需要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和人看成一个整体来处理有关生态环境的问题[9]。 因此,深层生态伦理更多强调的是万物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它的核心观念在于让各种生命形式都能够在生态系统当中发挥它们的功能,并且行使它们的权利,都应该得到保护,因为它们与人类是统一的整体,这与儒家的“不忍之心”有相当大的联系。 在自然遭到破坏时,由于把它们看作与人类自己一般,并由此而产生同理心,才会“皆有不忍”。 然而,深层生态学所提倡的并不只是去保护自然的一部分,而是提倡生态平等与共生,自然万物都要去进行保护,那么到底该不该有“伤害”? 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许多保护自然的矛盾例子,比如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强烈反对用动物做实验,但这必然会阻碍医学实验的正常发展;一些素食主义者打着保护生态自然的旗号,反对伤害动物,但“素食”却又是一种对植物的伤害,对生态平衡的打破。 因此,“不忍之心”在这里就同样出现了问题。
二、忍而为之:对自然的开发利用
儒家对待生态的“不忍之心”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然万物的生命进行保护,但是,要想把所有的生物都去保护是不可取的,不对大自然有任何的“伤害”也是不可能的,过度的保护反而还会破坏生态的自然发展。 比如对动物的过度保护,在动物受到伤害时对其产生“不忍之心”,导致动物过度繁殖,势必破坏其他自然物的正常生长与繁衍,这必然能致使生物链失衡、生态秩序破坏。 因此,儒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并不能够完全从“不忍之心”出发,必要的时候也要“忍而为之”,对自然进行适当地开发与利用。
前面已经提到,儒家的“不忍之心”应用于对生态领域的保护时,指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仁心善性,是人类必须具有的品格,是不能够违反的,因为这是一种保护生态坚定的原则。 在儒家那里,“不忍之心”是被当作一个正面的词汇加以宣扬的,作为其对立面的“忍”便是贬义的,但是,如果将“不忍之心”不受限制地扩展,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对自然的过度保护,依然会破坏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关系。 因此,虽然人们要坚守“不忍之心”,但却不能机械地执行,也应学会变通。 “不忍”作为保护自然的内在根基,它代表着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 普遍的道德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社会现实则是具体的,高度的抽象道德原则不可能与具体的社会现实之间具有完美的对应关系,这就导致道德原则与具体社会现实之间产生不相应性,因此,我们不能机械地遵守执行道德原则,有时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变通,这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执一用权”,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因此儒家讲仁民爱物,要对自然万物具有不忍之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分时间地点对象地仁爱一切事物,否则就会犯东郭先生的错误。
传统儒家高度重视道德的情境性,这是中庸的一个重要表现,而这也成就了孔子作为“圣之时者”的独特品格。 怎样将一般的道德律令与特定的境遇结合起来始终是重要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对“经权问题”的阐述上。 经,就是常道,亘古不变的道德原理;权,就是变通。 简单说来,道德原则在各种具体情境中的变通就是经权问题。 儒家的宗旨是对人的身家性命的关怀,而如何安顿身家性命则成为儒家伦理实践的主要目标。“权”在道德实践中的意义就受到了特别的关注。比如孔子就给予了“权”很高的地位,他认为:“可以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5]110可以看到,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但要事事依道而行,而且要不拘泥于规矩,做到随时通权达变。 孔子同时关注了人作为道德主体,这不仅体现出人的普遍本质,同时“忍”还是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的具体存在,因此他认为要将道德原则与具体的道德情境联系起来。 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吾从众。[5]104“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5]102“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122而孟子则更明确地提出了经权问题,指出“执中无权,犹执一也。”[5]334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5]265在这里,抽象的道德规范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境而进行灵活的变通。
由于以“不忍”作为基础的仁爱道德原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会与现实情境之间产生不相应性,因此,我们需要加以调整变通,甚至要“忍而为之”,对自然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 境遇伦理和经权问题都表明,任何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都不可能为行为者的具体行为情境中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我们要通权达变,以做出更为合宜的选择。 《二程集》中有这样一段话:“周茂叔窗前草不除。 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在他眼里,窗前的小草和人类生命是一样的,所以他不忍心剪除。 因此面对自然万物的生命之美,周茂叔始终怀有一种爱惜之心,且以“不忍”的态度对待。而对于此种风气,后世王阳明对此给予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当薛侃“去花间草”时,王阳明明确表示:“草若有碍,何妨汝去?”[6]33虽然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对待世间万物的生长发育应该像周茂叔一样怀着至高的敬意,都应存有“不忍之心”而不愿除草,但是当草“有碍”时,杂草的存在妨碍了花木的正常生长,那么在这时,人们的“不忍之心”就应当变为“忍而为之”。 因此,“去花间草”并非是对生命的亵渎,而是使生命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忍”并不是偶然性的、策略性的,而是另一种尊重自然规律的体现,是对生命的另一种成全。 此外,王阳明还正面提出过“忍”的问题:“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 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 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宁救至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 这是道理合该如此。”[6]122-123即使禽兽、草木与人“同是爱的”,但却也需分个“厚薄”,因为我们是无法得兼万事万物,“世间安得双全法”,那么在关键时刻必须要灵活对待,心要“忍得”,忍得把草木去喂养禽兽,忍得用禽兽养亲与祭祀,忍得先救至亲不救路人。 这些做法是人人都可以包容与理解的,因为“这是道理合该如此”,在“不忍”这一原则被打破时,人们必须要有灵活的策略去应对,关键时刻必须要做到“忍”,“忍”不是指对大自然采取残忍的做法,相反,“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自然恢复其原有样貌,更加遵循其天性的本然发展。
《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讲:“人皆有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5]348这句话充分说明,每个人都有“不忍”,“不忍”是作为道德原则出现的,但是把它推扩到忍心干的事情上,便才能够是“仁”。 由于人类有无限多的意欲,从“食色性也”到对功名利禄的追逐。 因此人要对各种意欲进行限制,这就需要不同程度的“忍”的功夫。 仍然从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例子出发,我们会发现,齐宣王虽然不忍看到牛被宰杀,从而产生不忍之心,然而他却以羊易之,在羊的身上做出了“忍”的举措,那么这样一来,由于齐宣王的“见牛未见羊也”便使得“不忍之心”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显得那么神圣与坚定了。 虽然齐宣王因“未见羊”故而在羊身上做出“忍”的举措,但孟子并没有认为他的做法是残忍的,反而称赞此举为“仁术”。 同时,当百姓对齐宣王这一做法不理解,认为他是出于对牛的吝惜,故而做出以小易大的举动时,孟子还以“以小易大,彼恶知之?”来出言安慰齐宣王,可见,这种“忍”并不是儒家所排斥的。 如果齐宣王在看到觳觫可怜的牛时,直接取消釁钟这种仪式,在当时的社会,祭神的仪式是不可能被随意废除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想不破坏“不忍之心”,还想不随意废除礼节仪式,就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去尽可能的使事情做到完美。 因此,在不得已的时候,要忍得“以羊易之”,人们需要转变思路,也必须要学会“忍”。
虽然“不忍之心”是儒家大力提倡的,在对待生态问题时,儒家也一直采取坚定的生态保护策略,但在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忍”的出现也并非少见。 通过对典籍的梳理,我们会发现,儒家在很多地方表面讲“不忍”,实际上是蕴含着“忍”的。 比如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上一部分已论证“不纲”与“不射宿”是一种不忍之心,那么这两种不忍的前提却是“钓”和“弋”。 “钓”和“纲”,前者是普通的垂钓,而后者指用大网捞鱼;“弋”是射鸟,“射宿”是射宿鸟,因此这二者是同一种方式,只是采取的是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罢了。孔子是不反对钓鱼和射鸟的,他只是反对用大网捞鱼,因为这样会捕捞到未长大的鱼苗;他还反对射归巢的鸟,因为在巢之鸟是幼鸟和母鸟。 虽然后世多以仁爱来讨论孔子对自然的保护,但是忽略了孔子的本意并非去保护所有的动物,而是有选择性地去保护,有选择性地去产生“不忍之心”,因为“不忍”的前提是在“忍”的基础之上的。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的存在各自有其作用,兔子吃草,狼吃兔子,这是生物之间的食物链,是自然之理,若少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生态都无法平衡发展下去。 程颐在《养鱼记》中说:“鱼乎! 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 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 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鱼乎! 鱼乎! 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10]虽然在一方面,“吾”因用斗斛之水使鱼儿暂时生存下去而微感自慰,但另一方面却又因不能够把鱼儿投放至江河湖海之中而深表遗憾。因此,儒家同样认为,人们对生态的保护永远无法做到两全,倘若只存在“不忍之心”,那么推及万物,就会产生“岂止鱼而已乎”的悲慨。 因此,人永远无法做到对万物的完全保护,只有适当的“忍”,才能使生态系统得以正常的循环与运行。庄子在《至乐篇》中就讲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鲁候将海鸟迎于庙堂,不忍它漂泊无根,对它像对人类一般采用最高的礼遇,但海鸟却“眩视忧悲”,最终“三日而死”,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鲁候把对人类的“不忍之心”强加于海鸟,但这种“不忍之心”运用到天性自由的海鸟身上,却造成了正好相反的结局,因为人与动物的习性是不同的。如若“忍而为之”,将海鸟放生,它自会“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逶迤而处。”[11]鸟的天性自会得到更好的发展,过着自由而快活的日子。 因此,不强加自己的不忍之心于动物身上,看似是一种残忍狠心,实则是顺遂了鸟的本然天性,维持了动物界的自我平衡。所以说在这里,“不忍”却恰恰是另一种“残忍”的表现,而作为权变的“忍”则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的体现,因为它不仅仅是道德原则与情境之间的协调,更是对自然规律的根本遵守。
由此观之,要想真正使生态系统得到持续的发展,儒家同样提倡“忍”的功夫,对生态进行适度的调整与开发,这便是策略的灵活性。 儒家是没有教条主义的,儒家虽然强调“不忍”,但同样也并不认为它能够解决所有的生态问题。 为了避免人们陷入“教条”而做出一些过犹不及的事情,因此在面对生态问题时,并不能够一味地去保护,而是也需要对生态进行适度的开发,方能维持生态系统的正常发展,这正是“忍”的功夫。 然而,即使“忍”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仍然是一种狠心而为的做法,那么“忍”是否背离了“不忍”,背离了生态保护的初衷?
三、不忍之忍:保护与利用的平衡
儒家是始终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之心的,因此儒家通过对大自然采取“不忍之心”来表达一种对生命的高度敬畏之情,且这种情感由于“不忍”的原则性而表现得非常坚定。 然而,“不忍之心”不能无限扩大,在必要的时候,也需要有“忍”的功夫,适时地调适生态的平衡,才能够做到生态系统长足稳定的发展。 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忍”作为“不忍”的对立面,它的存在仍然伴有一定的残忍色彩,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去认识“忍”?
前面讲到,“忍”作为“经权”之“权”,是指人们不能死守某一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要通权达变,以便更好做出合宜的选择,那么“忍”的本意是“残忍”,何以它却成为了相对正确的判断呢?因为道德选择的过程,是一个主体与情境相互动的过程,是一个行为动因与人们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存在相联系的过程。 “忍”既然作为一种道德情境下的产物,它虽对“不忍”这一根本原则有所冲击,但二者仍是互动的、相交融的。 所以,人们之所以要“忍”,恰恰是为了回到“不忍”。 前面已经提到,“不忍”是自然保护的内在根基,“忍”既然也是“不忍”的表现,这说明“忍”同样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守,是保护自然的体现,因此二者的关系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王阳明就正面提出过“忍”的问题,他讲“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我们过分关注王阳明强调的“忍得”,但却忽视了“忍得”的前提条件。 人们虽然忍心用草木去饲养禽兽,但是这并非对草木就是残忍的,因为这里明确提到“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只是在面对两者相较取其一的情况下,人们便会选择用草木去喂养禽兽,这是符合儒家的道德原则的:虽然大自然的所有生命都值得人们去珍视,但人永远无法做到一视同仁的对待万物,爱必须是“有差等”的。 因此,对待生态的保护要有度,保护并不妨碍人们去利用它,人们也并非为了保护而保护,只保护而不去利用它同样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而利用的前提仍然“同是爱的”,这种“爱”中蕴含着“不忍”。 即使是“忍而为之”,但“忍”的初衷仍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所以这仍然可以称之为“不忍”,“忍”是为了激发人们重新回到“不忍”,这是一种“不忍之忍”。 因此,必要时的“忍”反而能够让人们更好且更合理地去应用“不忍之心”,对于生态保护而言,对大自然偶尔做出的“忍”的举动不仅没有背离“不忍”的初心,适时适度的利用反倒能够对生态的发展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
在面对生态问题时,“忍”与“不忍”的结合随处可见。 儒家十分强调“以时禁发”这个概念,“禁”与“发”是两种相反的含义,“禁”是对生态的保护与不忍,“发”是“忍”与作为,而“时”则是制衡这二者的一个标准,使二者能够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偏不倚。 《礼记·祭义》中讲:“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12]“断”与“杀”是一种狠心的做法,是一种“忍”,但这里并没有对其做出否定,而是给出了“时”的限制,“忍”的执行是要以“不忍”作为前提的,“不以其时,非孝也”就是一种“不忍”,在“断”与“杀”的执行期间时刻想着时令给予的限制,就是激发人们的“不忍”。 那么,“忍”之所以要回到“不忍”的意义在于什么?
“忍”虽然是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之下所作出的策略,但是“忍”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保持自然界的平衡,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守。 因此,我们不能只从“道德情境”与“权变”的角度去看待“忍”,因为这样一来,忍就只能是策略性的、偶尔性的暂时战略,但其实“忍”并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而是尊重客观规律的体现,是一种必然性的做法。 这样一来,“忍”又可以成为“不忍”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因为只有这种“必然性”才能够使“忍”重新回到“不忍”。 依旧从周茂叔不除窗前草说起,他将草与人的生命视为等同,但这种“不忍之心”并非我们提倡的。 儒家讲爱有差等,花草的生命绝不可与人类的生命视作等同。 因此王阳明明确提出,当花间草妨碍了其他生物的生长时,必须要“忍”。 那么王阳明的做法是否是狠心且残忍的呢? 在薛侃除花间草一则中,王阳明曾明确提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6]33因此他对待花草的本然之心仍是“不忍”的,这种“不忍”不同于周茂叔所持有的那种“爱无差等”的稍显病态的“不忍之心”。 这种新的“不忍”,深层的含义在于维持生态的新的平衡,对生态进行补偿与恢复。因为既然已经对花间草做出相对残忍之举,所以势必要对生态进行补偿的,对杂草之“忍”实则是为了对“花”的不忍,除去了杂草,花才能够开的更加旺盛,才能够得到了新生,这就是对自然的新的恢复。 因此,“忍”可以重新激发内心深处的“不忍之心”,使大自然重新焕发活力与新生。 此外,荀子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表面上看是一种不忍,但实际上也承认应合理的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只是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因此,在总体上这并没有违背“不忍”的初心。 那么这种做法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荀子在后文中给予了明确的解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8]163人们去利用大自然的资源是毋庸置喙的,只是这种“忍心而为”在最终仍旧会回到“不忍”当中,使得四季正常运转,万物得以正常生长。 因此,适度的“忍”是为了重新回到“不忍”,只有对自然生态进行保护与恢复,才能够使百姓有余食、余用、余材。保护自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人类增添福祉。
由此可见,虽然儒家在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有时会采取一定的“忍”的功夫,从而解决因“不忍之心”泛滥而产生的“过犹不及”,但“忍”并不是与“不忍”作为对立面而存在的,而是尊重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 然而,“忍”毕竟是一种稍显残忍的做法,会对事物造成一定的伤害,因此为了补偿与回馈自然,“忍”终究是要回到“不忍”,而这种新的“不忍”,是在经历了“忍”的功夫之后淬炼而出的。 因此,人与自然若想得以和谐共存,需要“忍”与“不忍”的结合。 《史记·殷本纪第三》中就讲到“网开三面”的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13]商汤担心网开四面就会把鸟兽全部打掉,于是把网撤掉三面。一方面来说,汤没有禁止人们捕猎,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者”;另一方面,他又提出“网开三面”,撤掉三面的网,不把鸟兽全面打尽,这正是一种平衡生态系统的做法。 “网开”就是“忍”,而只开三面则是“不忍”,当人们在对自然进行“忍而为之”的狠心举措时,总会在内心深处产生不安的情绪,由于不安情绪的不断推动,人们必然会产生补偿与恢复大自然的心理,即从“张网四面”变为“网开三面”,将内心深处的不忍之心充分地激发出来。 因此,“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不忍之心”从一种潜能变为实际行动。 如果没有“忍”的刺激,“不忍之心”只能流于表面,只能是一种人类面对自然受到伤害后内心世界的轻微触动,并不能真正成为一种行动。 当人们真正对自然做出了忍心之举,反而会对自身的举动做出一定的反省,从而将“不忍之心”作为实际行动充分地展现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例子,如面对安乐死,有的人不忍其死,有的人忍而让其死,但是,对立意见的双方都是出于“不忍之心”,持支持意见之人不忍病入膏肓者倍受疾病的折磨;持反对意见的人是不忍心使一个生命被就此舍弃。因此,无论是“不忍”与“忍”,他们的共同期愿最终是为了回到“不忍”这一基础性的原则中去。所以有时忍不住有所作为,在深层次仍然是一种不忍。 对于“不忍”这一道德原则,“忍”则根据具体的情境做出策略上的适度调整,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非对立。 虽然我们坚持原则,但在具体执行时仍要做出灵活的变通,这并非对原则的背离,而是为了回到一种更加和谐的局面中去。那么面对自然生态,儒家虽然讲“不忍之心”,但同样肯定“忍”的必要性。 从表面上来看,“忍”是人类对待大自然的狠心的举动,实际上,“忍”可以一定程度上平衡与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让人们更好地顺应自然发展的规律,使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能够遵循其天性发展。 另一方面,“忍”能够重新激发人类对待大自然的不忍之心。 因为人类明白自己对自然生命做出了“残忍”的举措,所以便会产生一定的愧疚之情。 如此一来,“忍”反倒激发人们去对生态做出补偿与恢复,同时激发了人类内心深处的“不忍之心”,正是这种“不忍之忍”,使得人与自然能够真正达到长久共存,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