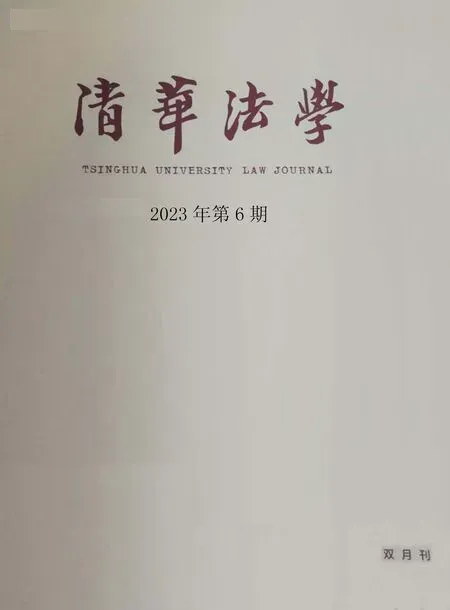从“契约”到“准司法”
——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进路与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赵 宏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既是一部创造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解决矛盾与纠纷的历史。自有古老文明以来,人类就掀开了争端解决的序幕。〔1〕公元前3100 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城邦拉格什(Lagash) 与乌玛(Umma) 的统治者签订的条约,据认为是人类最早的解决争端的国际条约记载,用苏美尔文字刻在石碑上,据说失传了。公元前1296 年赫梯国王哈图希尔三世与埃及法老拉姆杰斯二世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是迄今保存的最古老条约:双方承诺互不再战、履行以往缔结条约的义务、相互帮助的共同义务、引渡逃亡者等。古代埃及、两河流域、中国、印度都有王朝之间关于争端解决的早期实践。自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诞生以来,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摩擦和冲突频仍,产生了国际争端解决的多元途径和纷繁的国际法律实践。〔2〕本文的国际争端解决意指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或者至少一方为主权国家,譬如东道国与外国投资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对于双方均为私人主体之间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不作为本文考察的对象。国际争端解决的习惯和条约规则构成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步与国际法的实体规则体系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程序性规则体系,包括解决国际争端的条约、规约、协定、条约的专门章节、习惯等规则以及实施和运用这些规则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并由此衍生出相关领域的判例法和条约解释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国际争端解决是维护和促成国际秩序调整以及生成和发展国际法的重要途径。国际法作为“法”的性质与国际争端是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以及裁决结果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约翰·奥斯汀(John Austin) 把国际法看作“实证的道德”〔3〕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Weidenfeld &Nicolson,1998,pp.127,140-142.到哈特(Herbert L.A.Hart) 为国际法所做的初级辩护,即认为国际法“即使是有约束力的规则”,至多算“初级”“原始”的法,〔4〕哈特虽不同意国际法是不具约束力的规则,但承认国际法缺乏国内法的“某些特质”,“亦即根据该体系的某个终极规则来证明个别规则的效力”,同时指出国际法可能仅仅是“有关义务的初级规则”,无法使得所有的规则构成一个单一的体系,且国际法可能“只是一组习惯法的规则,而赋予条约约束力的规则就是这组习惯法规则”。参见Herbert L.A.Hart,The Concept of Law,Clarendon Press,1961,Chapter 10,中文本,参见[英] 哈特:《法律的概念》 (第3 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8 年版(2021 年6 月重印),第300-305 页。时至今日,国际法学者仍然认为国际共同体及其组织规则处于低级水平,〔5〕参见[意] 安东尼奥·卡塞斯:《国际法》 (第2 版),蔡从燕等译,法律出版社2009 年10 月第1版,第6-7 页。这些在一定意义上与国际法体系中的争端解决制度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司法性”和“约束力”有密切的关系。〔6〕See Cesare P.R.Romano,Karen J.Alter &Yuval Shany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1.质言之,与国内法律制度中存在以国家公信力为后盾的司法裁决机构相比较,国际法体系中是否存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公正、具有可执行力的司法性裁决机制成为国际法是否具有“法”的特性的一个重要衡量尺度。然而,以主权国家同意为基础的国际法具有不同于国内法的特质,为此,在国际法范畴内探索国际争端裁决的“司法性”或“准司法性”,自然需将这种探索置于具有“契约属性”〔7〕无论将国际法规则视为国家之间有关特定规则或做法的合意(consensus) 还是关于特定义务的同意(consent),基于条约的明示协议还是基于国际习惯的模式认可和遵循,国际法的约束性来源于国家同意。具有契约属性,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典理论。See Malcolm N.Shaw,The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p.4-8.的国际法的宏观框架之内;而这种探索对于深入理解和认识国际法的性质与演变规律而言,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囿于篇幅,本文无意讨论国际争端解决制度的全貌,唯择取国际法范畴内争端解决的路径、手段或方式作为考察对象,从历史的视角,在国际争端解决的多元路径中探索是否存在从战争到和平、从外交到法律的总的历史进路,以及在“法律途径”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中,是否存在从“契约”到“准司法”的某种进路,特别是重点探讨近现代以来,从国家间基于契约、通过第三方仲裁解决争端发展到通过司法或准司法机制解决争端的发展进路以及这种进路是否是一种进步? 除有关国际争端解决的“进步”叙事外,本文还将探讨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路径具有的“多元共生”“包容并存”甚至“相互趋同”等其他特点,同时,以此为背景和参照,重点研究世界贸易组织(下称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危机和及其改革,并提出关于该机制改革的思考。
一、引论:国际争端解决进路的三大脉络
“在各国的关系中,文明的进展即是从武力到外交,从外交到法律的运动”,〔8〕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Praeger,1968,p.3.美国国际法学者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 的这一著名论断,从法律视角精辟地阐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总体和普遍性的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谓对人类争端解决路径的一种高度浓缩和概括。〔9〕参见赵宏:《2018 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发展与挑战》,载《国际经济法学刊》 2019 年第4 期;赵宏:《条约下的司法平等》,载《国际经济法学刊》 2021 年第2 期;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编:《中国世界贸易组织年鉴2018》,中国商务出版社2019 年版。依笔者所见,遵循国际争端解决发展的历史脉络,这一论断也可谓包含了国家间争端解决路径发展的三大主线。第一,从战争到和平的主线,即从以武力和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主要途径到战争和武力被普遍地约束的脉络;第二,从外交到法律的主线,即从职业外交官和国际法律师专业队伍的崛起以及谈判、斡旋、调解等外交途径的广泛运用到仲裁、司法等法律途径运用的脉络;第三,从契约到准司法/司法的主线,即从基于国家间合意的第三方仲裁裁决到由专门的国际法院等司法或准司法机构的裁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脉络。这三大主线基本构成了解决国家间争端的一般性的进路。从格劳修斯(Hugo de Groot) 发表《战争与和平》 的时代起,概括起来,国际争端解决发展的历史大体存在三大脉络(主线)。
(一) 第一脉络:战争与和平法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相当长的阶段,武力征伐是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包括部落、族群、王朝、国家之间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最终途径,即使人类历史早期也存在着通过磋商、谈判、斡旋等手段来化解和缓和矛盾的实践,诉诸武力和战争仍然时常被作为解决重大纠纷的终极途径。
1648 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已经在参与三十年宗教战争的欧洲参战各方之间达成了承认和尊重各自主权、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共识以及不诉诸武力和采取集体防卫的承诺,但其对于欧洲国家间战争的约束力却是有限的。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即所谓“传统国际法”时期,战争和诉诸武力仍被普遍视为“为实现某种权利、保护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利益,在国家间进行的合法的解决争端的手段”。〔10〕参见同前注〔5〕,[意] 安东尼奥·卡塞斯书,第7 页。这时国家已经受到诉诸战争权(jus ad bellum) 和战时法(jus in bello) 的约束。诉诸战争权制度是决定国家何时可以走向战争的法律,法学家已经开始区分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战时法是关于战争时期国家必须如何行为的法律体系,包括对交战双方的确认及对伤员和战俘的处置等人道主义法则。在18 世纪的欧洲,各种战事频仍,战役甚至被作为解决国家间争议的法律程序。〔11〕参见[美] 詹姆斯·Q.惠特曼:《战争之谕:胜利之法与现代战争形态的形成》,赖骏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按照研究欧洲战争法的专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Q.惠特曼(James Q.Whitman) 的观点,“迟至19 世纪,法学家仍旧主张,战役是一种契约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一种通过一致同意的集体性暴力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合法手段”。〔12〕在18 世纪法学家的眼中,会战是在“默认的运气契约”(tacit contract of chance) 下发动的争端解决程序。在该程序中,冲突中的两个国家同意将它们的纠纷通过“武力的运气”来解决。同上注。根据他的研究,战争甚至还被认为那个时期的一种会达成某种裁定的审判(verdict of battle),据信,这也许来自欧洲中世纪将“会战”(pitched battle)作为上帝的审判的古老观念和传统。〔13〕会战尤其被描述成一种重要的审判或法律程序,一种竞争双方通过单日的、有计划的、分阶段的集体性暴力解决其分歧的合法方式。例如,在中世纪,会战被视为上帝的审判。发动一场会战近似于发起一次神判,都是在人类无法解决自己争议时,召唤上帝前来扮演法官的角色。同上注。以中国传统的反战价值观来看,这样的战争性法律观当然是很落后、很反文明的。它必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被抛弃。
需要指出,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战争可以被作为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权宜性合法途径,但由于传统国际法的诞生以及格劳修斯等国际法学者经典著作的广泛传播,交战方已经开始遵守作为国际法组成部分的战争法和国际惯例,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人类付出数千万生命的代价,使世界人民更加坚定反战的立场。在此基础上1945 年诞生的《联合国宪章》 明确规定,非为行使自卫权和经安理会授权,禁止各会员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不乏穷兵黩武者武力入侵、袭击他国和地区的情形,应当承认,战争和武力已不再是国家间解决争端的主要途径,这无疑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 第二脉络:职业外交队伍和国际法专业律师通过外交途径协助解决国家间争端、促进和平
从久远的历史以来,外交和国际法如同润滑剂一般在调解族群、王朝和国家间的关系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特别到了近现代,外交在国家争霸竞赛中起到斡旋和平衡的作用,且由于国际法教育在欧洲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国际法律师和职业外交队伍,他们在欧洲各国的纷争中通过斡旋、调停、谈判等,以外交方式协助并推动解决国家间的纠纷。从1895 年国际法学会首次针对外交惯例编篡《剑桥规则》 到《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的诞生,外交使团和外交官的活动本身既构成国际法的实践,也促进了国家间关系的维护和发展,对于国际争端的解决发挥了积极的效用,〔14〕参见[德] 巴多·巴巴多斯、[德] 安妮·彼得斯主编:《牛津国际法史手册》,李明倩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 年5 月第1 版,第797-826 页。其本身在国际关系中也直接受到来自国际法的保护。
(三) 第三脉络:国际争端裁决越来越多地运用法律途径
所谓的法律途径包括有约束力的第三方调解、国际仲裁(特别是机制性的第三方仲裁) 和国际法院的司法裁决,譬如1899 年设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简称PCA),1922 年国际联盟设立的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简称PCIJ) 及1945 年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简称ICJ),1995 年WTO建立了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进行两级审理的争端解决机构,使得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决作为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途径现身于历史舞台。
在这三大主线中,首先,毫无疑问,战争以其非人道和残酷性而遭到文明社会的批判和唾弃,因此,从战争到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质的飞跃。其次,外交以其具有和平色彩,通过专业人员促使双方达成一致,从而解决争端,故而受到广泛的欢迎,这种方式既包括双方直接谈判,也包括调查、斡旋或调停的方式。1899 年达成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海牙公约》 (1907 年修订) 规定了“调查”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斡旋、调停和调解则以第三方参与程度的不同进行区分,作为三种促成争端方达成一致的方式,一般通过强国或有影响力国家的资深外交官或者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的深度参与、提出建议等方式促成双方达成一致,从而化解纠纷。外交途径解决的优点是兼顾各国友好和各方利益,但缺点是难以确定适用的规则,如果仅仅是双方谈判,则难以避免强国压制弱国,甚至使结果偏向于强国利益,有失公允。因此,随着国际关系的深度发展,特别是国际规则越来越多地为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第三方国际仲裁和国际司法裁决等法律途径更为普遍地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渠道。本文将对后者做重点分析。
综上,我们可以说“从战争到和平、从外交到法律”虽代表着人类文明和国际争端解决发展的一种基本进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和国际争端解决的进路是从一端到另一端的直线运动,恰恰相反,事实表明,战争与和平、外交与法律作为国际争端解决的手段和途径在历史进程中存在着普遍的“交错演进”与“共生并存”的局面。
二、从“仲裁”到“准司法”: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进路
如前所述,如果说从“战争到和平”、从“外交到法律”的路径构成国际争端解决的总体进路,那么,在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途径中,是否存在着从基于主权国家合意的国际仲裁裁决到通过国际司法机构裁决的发展进路,更进一步,1922 年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1945 年联合国国际法院以及1995 年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等国际“司法”或“准司法”裁决机制的诞生是否意味着人类争端解决从“仲裁”到“司法”或“准司法”的一种进步? 对于国家间的争议解决,国际司法途径是否优于国际仲裁? 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当前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谈判也许是有价值的,因为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首要和核心争议聚焦于是否要恢复WTO的上诉机构。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索司法机制作为国际争端解决途径的价值和意义,以期为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特别是上诉机构恢复运转及其未来走向提供国际法理论层面的思考。
(一) 是否存在从“仲裁”到“司法”(或“准司法”) 的国际争端解决路径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以国家间契约(合意) 为基础的“国际仲裁”确实在时间上早于第一个国际法院的诞生。仲裁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历史,特别是西方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显示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希腊的城邦之间就大量的采用第三方仲裁作为解决城邦之间争议的正式途径。早期的国际法学者,如格劳秀斯和瑞士的瓦塔尔(E de Vattel) 等,对国际仲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途径的有效性都是给予充分肯定的。〔15〕See Cesare P.R.Romano,Karen J.Alter &Yuval Shany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42;E de Vattel,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1916,pp.193-194.本文对古代和中世纪历史暂且不论,一般认为,近代第一部国际仲裁条约发生在刚刚从英国独立的美国与英国之间,即美英之间1794 年签署的《杰伊条约》 (Jay Treaty),其规定运用仲裁手段解决美国独立期间美英之间遗留的纠纷,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被认为是机构仲裁的最早雏形,在1794 年至1804 年之间,在《杰伊条约》 成立的委员会主持下共达成了536 项仲裁裁决,其中包括著名的1798 年圣克罗伊河(Saint Croix River) 仲裁裁决。〔16〕参见[美] 巴里·E.卡特、[美] 艾伦·S.韦纳:《国际法》,冯洁菡译,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482-485 页。为便利国际仲裁的发展并为其提供可信赖的国际规则框架,1899 年和1907 年在荷兰海牙召开了两次国际和平会议,通过了两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海牙公约》(The Hague 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这可谓最早的关于国际仲裁的多边公约,在此基础上,1899 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后诞生了至今仍在运行的常设国际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即PCA)。尽管名为法院、且冠以“常设”,但它非法院,而是一个一旦应召即可组成仲裁庭的机构,其常设的也只是行政理事会和国际事务局,作为所设立的仲裁庭的秘书处或登记处,其实质是一个我们今天通常所谓的国际机构仲裁。因此,PCA 也被视为国际机构仲裁的鼻祖,这也许是后来世界许多国际仲裁院都冠名仲裁“法院”(Court of Arbitration) 的缘起,譬如香港、新加坡国际仲裁院的英文名称都用了“Court”。直到1922 年,在美国鼎力支持下成立了隶属于国际联盟的PCIJ,这是第一个处理国与国之间纠纷的国际司法机构,并诞生了后来为联合国ICJ 几乎全盘接受的PCIJ 规约,作为第一家国际司法机构,PCIJ 在国际司法裁决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与探索,包括法官的选举等方面,直到1945 年被依照《联合国宪章》 所设立的ICJ 所取代。因此,从时间序列来看,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国际仲裁方式比具有“司法性”(或“准司法性”) 的国际法院诞生要早。我们了解,仲裁作为争端解决的方式,无论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均基于当事方(包括国家作为主体的当事方)的合意,或表现为单独的仲裁协议或表现为条约中的仲裁条款,其裁决结果对争议双方的约束力也基于这种事前达成的协议而生,为此,国际仲裁具有契约属性,是学术界公认的。而ICJ 的司法属性是根据其成立的章程被明确赋予的,如《联合国宪章》 第92 条明确规定,ICJ 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必须指出的是,《联合国宪章》 是基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合意而生,因此,也具有契约属性,ICJ 的司法属性正是基于主权国家的共同意志所赋予。基于国际法的契约属性,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裁决的共同基础都是国家同意,而区别仅在于国家同意所赋予其作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性质与程序上的差异。且这种基于国家同意赋权的各类国际司法机关,诸如联合国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简称ITLOS,即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设立的特别法庭)、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欧洲法院(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欧洲人权法院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简称 ICSID)、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简称ICC) 等,其适用范围、职能、运作程序和裁决效力等均基于参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1990 年冷战结束后达成的具体条约,有其各自的特点和许多差异。因此,仅从时间的脉络上,基于“当事方合意”的国际仲裁与名义上具有司法属性的诸多国际法院或法庭,其诞生是有先后顺序的。故而至少从时间脉络的名义上,可以说国际争端解决路径具有从国际“仲裁”到国际“司法”或“准司法”的发展路径。
(二) 国际司法机构之“司法性”的判定标准
既然仲裁与司法均具有法律裁决的属性,在国际法下,无论仲裁还是司法皆基于国家的同意——契约而生,而不同的国际仲裁机构、仲裁庭或国际法院设立的程序和运行规则不尽相同,那么,在国际法层面,如何衡量一种裁决制度的“司法属性”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对国际争端裁决的“司法”或“准司法”属性进行衡量和判定的标准;同时,我们需要回答国际争端解决之“司法性”与公正性的关系问题,即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是否以及如何产生更加公正的争议解决的结果。
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仲裁与司法除了形式上的差别,其实质区别在于司法性程度的高低。从国内法的视角,所谓“司法性“即具有司法的属性。在现代社会,按照一国宪法的规定,司法是以国家公权力保障、通过法院审判的方式、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争议做出独立公正和终局性裁决、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审判活动。而“仲裁”在性质上则属于兼具契约性、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准司法性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在现当代的许多国家,符合一国《仲裁法》 的仲裁裁决可以申请一国法院的强制执行,因此,可以说“仲裁”具有“准司法“的属性。
关于国际争端裁决的“司法性”的衡量标准,国内外学者做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观点。譬如,托穆沙特(Tomuschat) 教授就如何判定争议解决机构是否具有司法性提出了五个基本条件:①常设性,意味着相关机构的存续不依赖于个案,具有独立性;②机构的设立必须基于国际条约等国际法律文件;③机构必须依据国际法来裁判案件;④须以确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案件的裁判,且这些规则在争议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不依据当事人的意愿修改;⑤裁判的结果有法律约束力〔17〕See Christian Tomuschat,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with Regionally Restricted and/or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in Hermann Mosler &Roger Bernard eds.,Judicia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Other Courts and Tribunals,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Springer Berlin,1974;Christian Tomuschat,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in Rüdiger Wolfrum ed.,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Public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Heidelberg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上述前四个条件区分了司法性机构与仲裁庭及机构仲裁,因为通常国际仲裁可以个案设立、仲裁当事方可以约定适用的法律和仲裁程序,第五项裁决结果的法律约束力又分为裁判和执行两个阶段,裁决的执行通常是行政机构的职能,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司法性行为。〔18〕托穆沙特提出的这五个条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Corzo,2008;Fromageau,2019)。罗马诺(Romano) 教授在托穆沙特提出的五个标准的基础上,强调了两个额外的条件:①裁决案件的机构必须经过客观公正的方式选任裁判者,而非由当事人选任;②至少一方的案件当事人是主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19〕参见同前注〔15〕,Cesare P.R.Romano 等书。这两个条件再次将司法性机构与国际商事仲裁进行了区分,其明确排除了以国际商会仲裁院为代表的仲裁机构管理的商事仲裁(Romano,1999&2011)。罗马诺的观点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和引用 (Dimitropoulos,2016)。〔20〕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也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夏皮罗(Shapiro) 认为,国际司法机构的特征应当包括:①法官的独立性;②遵循预先制定的明确的审理规则和程序;③对抗性;④两分法的裁决(Shapiro,1981)。卡西斯(Kassis) 提出,司法性的裁判过程应当是由裁判者独立做出判断,不受到任何干扰和介入(Kassis,1989)。
有学者则认为,托穆沙特和罗马诺对司法性机构设立的条件过于苛刻,导致一些新出现的司法机构因未能满足他们所设的条件而被排除在外(Alford,2003;Helfer &Slaughter,1997)。例如根据“国际法院和仲裁庭项目”(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下称PCIT) 发布的关于国际机构的图表,一些司法性机构就没有完全满足托穆沙特和罗马诺所列举的所有要素,在PICT 设立的标准中,国际司法机构应当:①是永久机构;②由独立的法官组成;③当事方至少有一方是主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④基于预先设定的规则运行;以及⑤做出的裁决有法律约束力〔21〕See The Project on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International Judiciary in Context:A Synoptic Chart,PICT (Nov.,2004),http://cesareromano.com/wpcontent/uploads/2015/06/synop_c4.pdf.。阿尔特(Alter)、哈夫纳·伯顿(Hafner-Burton) 和赫尔弗(Helfer) 将司法性机构定义为由各国通过国际条约授权创立,根据国际法裁决案件,并且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或者意见的机构(Alter,Hafner-Burton &Helfer,2019)。
尽管这些关于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司法性的衡量标准表述不尽相同,但基本要义是一致的,即此类机构应具有持久性与独立性,法官往往经严格的遴选程序选举产生并保障其具有独立性与公正性,遵循事先订立的解决争议的程序规则,运用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进行裁判,裁决对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国际司法裁决机构在是否仅临时性处理个别案件、当事方对法官或裁决者是否可以选择、对裁决程序规则是否可以修改等方面区别于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国际仲裁程序。因此,衡量国际司法裁决机构的司法性的核心要素即是该等裁决机构和裁决者是否具有独立性与公正性,这体现在该机构的组织架构、存续时间、法官或裁决者的遴选方式、裁决结果的约束性等诸多方面。与当事人意思自治所主导的国际商事仲裁相比,在国际司法裁决机制中,当事人对具有司法性的国际裁决程序的控制力相对较弱。
(三) 从“仲裁”(契约) 到“准司法”是否构成国际争端裁决的一种进步?
首先,作为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法律途径,仲裁一经诞生即被视为一种质的进步。因为通过仲裁解决国家间争端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冲突方之间的和平关系,而是要以双方共同接受的国际条约、习惯等国际法规则和原则,就双方的利益进行裁判,通常仲裁机构要彻底调查双方争讼的事实以及调整这些事实的法律关系,并基于公正的程序、适用双方均已接受的实体规则、做出有约束力的裁决。
对于欧洲而言,除罗马帝国统一的时期外,仲裁作为小国之间纠纷裁决的途径始终是比较活跃的,它甚至早于一些国家的法院系统,皇家司法系统的诞生一度取代了曾兴盛一时的仲裁。由于基督教在欧洲的盛行,早期的仲裁常常由基督教神职人员担任裁决者,以至于在中世纪教皇长期把持着所谓“欧洲仲裁者”的角色。即使对于新独立的美国,英美缔结的第一部仲裁条约《杰伊条约》 的实践也早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诞生。因此,仲裁作为和平解决争端的途径,在国际法形成过程中,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参见同前注〔14〕,[德] 巴多·巴巴多斯、[德] 安妮·彼得斯书,第149-164 页。
在国内法体制内,司法途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无论在民事还是刑事案件中,法院对原告的起诉案件的管辖权均不取决于被告的同意,也就是利益被侵害方不会因加害方的阻挠而无法获得公正、可以执行的司法裁判。因此,作为争端解决的途径,从仲裁(契约) 到司法,被视为是一种法律制度的进步。通过司法提供审判正义是文明国家对公众提供的基本制度保障。
然而,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只有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却没有必须通过某种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更没有必须接受某种司法审判的义务,除非其同意。质言之,国际法体系内的司法裁决制度不同于国内法体系,对于主权国家而言,无论司法还是仲裁的管辖权皆来源于契约——即国家同意。区别在于国家同意让渡给第三方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权限。譬如,该第三方机制是否属于具有准司法的独立机构,在管辖权范围、对裁判者的选任及裁决程序的控制力、裁判效力等方面,国家所做授权往往是不同的。国际司法机关的管辖权限、审判程序以及裁决效力取决于主权国家对其权力让渡的范围,这与主权国家的司法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而享有全面的司法属性是不同的,因此,判定依据主权国家同意设立的国际司法机关具有“部分”或“准”司法的属性,这种判断是更为适当的。相对于国际仲裁,国际法院或法庭按严格的程序组建,特别是法官的选任条件比临时仲裁员和机构仲裁员要求更高,往往要经历更加严格的多边遴选程序;而与临时仲裁相比,国际法院和法庭等司法机构还可以通过判例建立法理,发展国际法。据信当年国际联盟在常设仲裁院成立后,设立常设国际法院的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判例发展法理。英国知名国际法学者劳德派特(Hersh Lauterpacht) 对国际法院通过判例发展国际法的贡献评价很高。从这个意义来讲,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的诞生不仅促进了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国际法治理想的部分实现。
(四) 司法性是否意味着公正性?
国际争端裁决机制/机构具有的司法性——法官和机构的独立性、尽量少的当事人对裁决程序和实体的干预和控制力,是否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公正性,这是我们更关心的问题。除了由独立和公正的裁决程序保障外,国际法院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性,很大程度上与是否拥有较高素质、权威、独立和公正的法官密不可分,譬如,当年国际联盟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的起草者认为常设国际法院有四大优点:①因为它是由一群“固定的法官”组成,因此“当事方不能再选择法官”;②由于“这些法官长期在共同的工作中相互联系接触,而且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他们在不同案件中都作为法官”,因此,法院可以“建立起一种持续性传统并且保证国际法协调、合乎逻辑地发展”;③在常设仲裁院中,仲裁员可能倾向于“从一种政治立场”考虑案件,而在常设国际法院,“法律一定更具权威性,也可能更严格”;④常设仲裁院也许“除了法学家外还包括了政治家”,而常设国际法院“不仅有法学家,还有伟大的法官”。〔23〕See Advisory Committee of Jurists,Entraide judiciaire,Conférence de la hay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1980,p.659.转引自同前注〔5〕,[意] 安东尼奥·卡塞斯书,第373-374 页。这也许表明了当年起草常设国际法院规约的国际法学者和律师对常设国际法院的法官们相较于常设仲裁院的仲裁员怀有更高的敬意。美国籍的国际法院前院长、大法官斯蒂芬·M.施韦贝尔(Stephen M.Schwebel) 对常设国际法院的评价很高,“显而易见,尽管常设国际法院并没有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其他小的战争,但是,无论国际法律师还是外交家或政治家都把它视作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功。从1922 年1940 年,常设国际法院处理了成员国间29 起争议颇大的案件,为国际劳工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了若干咨询意见。尽管这些案件几乎无一例外并非关于战争的问题,然而常设国际法院处理的这些法律问题不仅关涉和平条约的实体问题,而且由于常设国际法院判决的高质量,它对于国际法的进步发展做出了意义重大的贡献。”当然,这并不等于国际司法机构的裁决是完美无缺的,令所有会员国都满意,相反,美国籍联合国国际法院(ICJ) 前院长斯蒂芬·M.施韦贝尔大法官在荣休后,对他工作过的联合国国际法院的裁决做出了相当坦诚和客观的评价:“国际法院的裁决与咨询是好的(sound) 和高质量的,尽管有若干极端的例外……其含糊的结论遭到批评,这些结论,在有些时候,没有得到充分的理由的支撑,且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威的引证……但作为整体,过去的这些年,国际法院的程序和实体裁决纪录是高质量的。”〔24〕Stephen M.Schwebel,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6.正因为如此,特别是考虑到法院在普通法系中对于法律发展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国际法院前主席、大法官劳特派特爵士专门著书对国际司法机构对国际法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进行了系统阐述,不但充分肯定,且言之凿凿。〔25〕See Hersch Lauterpacht,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从国际法学者和国际法官的视角,也许主权国家应该将更多的国家间争端提交国际司法裁决机构,然而,无论是国际联盟的常设国际法院还是其继任者联合国国际法院,在管辖权、裁决程序、裁决质量、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等方方面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甚至缺陷,〔26〕参见同前注〔24〕,Stephen M.Schwebel 书,第6-13 页。但其不但解决了国家间的诸多争端,而且其对国际法发展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这是任何国际仲裁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这也为国际法学界所公认。
综上,在一定意义上,国际争端解决的路径从“国际仲裁”发展到“国际司法裁决”可以说具有标志性的进步意义。〔27〕而仲裁以其便捷、快速、保密等特征,以及当事方对仲裁庭组庭具有的影响力等原因,作为争端解决方式,也受到一些争端当事方的青睐,譬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附件7 所列的仲裁程序即属于此类。See James Crawford,Browniie's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709.
三、国际争端解决法律路径的“多元化”和“多样性”
(一) 国际争端解决法律路径的多元化与多样性
尽管我们可以论证,在国际争端解决法律路径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从仲裁到“司法”或“准”司法的进路,但这并不意味着自“司法”或“准司法”解决路径诞生后,“司法”或“准司法”路径就完全取代了其他途径在国际争端解决过程中的运用。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宪章》 明确了普遍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解决会员国的争端,《联合国宪章》 第2 条第3 款及第33 条的规定推动建立了和平解决法律争端和政治争端的普遍义务,因此,国家间运用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即谈判、斡旋和协调等外交途径不断增多,也就是说作为争端解决的路径,外交与法律途径并存、互用;其次,国家之间建立的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端的国际仲裁机构和司法、“准”司法机构也不断增多,几乎遍及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换言之,尽管从总体趋势看,人类的争端解决途径存在着从外交到法律,从仲裁(契约)到司法、“准”司法的不断发展进路,并不是说国际争端解决的途径只有一条线性脉络,在法律解决国际争端的路径中存在着调解、仲裁、司法性裁决等多元化路径并存的局面,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各种方式共同构建、形成国际争端解决路径的多元化格局。在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内部也往往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解决方式,甚至存在一种方式内嵌或嫁接其他方式的情况,比如WTO 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即在仲裁条款的基础上嵌入上诉功能,充分展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所具有的灵活多样性,体现了国际争端程序法的创新精神。纵观战后国际体制,国际争端解决的路径始终是多元化的,在同一时期,往往存在多种争端解决途径并存的局面,争端解决路径呈现“多元共生”“形式多样”与“包容并存”的状态。
如前所述,我们论证了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路径在达到司法或“准”司法性以后,实现了使人类争端解决路径走向更加公正的文明进路,特别体现在联合国国际法院、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欧盟法院等“司法“或”准司法”裁决机制的建立。而在若干领域,我们同样观察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选择了以基于公约确立的个案“仲裁”作为其所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而没有选择建立更具有司法性的常设法院、选择任命具有固定任期的法官的方式。国际投资仲裁就是这样的领域。
回顾隶属于世界银行的ICSID 成立的历史,我们发现,对于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历史上基于对外国国民的保护,也经历了从“炮舰政策”到外交途径再到法律解决的发展历程。1961 至1964 年,《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解决公约》 谈判的历史表明,公约的起草者已经意识到个案仲裁裁决可能导致裁决结果的不一致性,但缔约者接受了这一前景,拒绝了建立一个常设法庭,以及一系列旨在纠正仲裁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错误或实质性的事实错误的上诉机制的提议,而是保留了基于有限事项、对存在严重程序问题和欠缺裁判理由的裁决的撤销机制。〔28〕See J.Christopher Thomas &Harpreet Kaur Dhillon,Foundations of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The ICSID Convention,Investment Treaties and Review of Arbitration Awards,ICSID Review,Vol.32:3,pp.459-502(2017).而在几十年的ICSID 公约实践中,恰恰出现了当年预见到的投资者和东道国的投资仲裁裁决不一致、甚至矛盾的情况,引起成员方的诸多不满,这也导致在当前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关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机制改革的谈判中,仲裁裁决的不一致问题再次成为部分成员的关注重点和谈判的重要事项。〔29〕See Jane Kelsey &Kinda Mohamadieh,UNCITRAL Fiddles While Countries Burn,Friedrich Ebert Stiffung,2021,pp.20-24.这也表明,对于国际投资仲裁,ICSID 谈判者当初有意选取了一条“弱”司法性的争端解决道路。且对ICSID 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及撤销程序,在ICSID 成员与非成员之间以及ICSID 成员内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 仲裁示范法的成员与非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式和条件,其纠纷解决的途径和执行程序明显更具多样性。由于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投资保护单一公约体系,数千个双边和区域投资协定构成复杂的“意大利面碗”网络,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存在着可否以及如何提交国际仲裁裁决的多元化纠纷解决路径,使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相对于国际贸易争端处于更加复杂的法律环境,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但时至今日,仍有若干成员认为应当维持以一次性的仲裁裁决作为投资者和东道国投资争议的核心解决方式,不支持建立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解决的上诉机制,而其他一些成员在谈判中则强调在ICSID 提供了仲裁实践外,对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议,无论“调解”“协调”乃至成员国国内法院系统等多元解决途径应受到鼓励。
事实上,目前在同一国际公约下争端解决机制包含调解、仲裁与司法等多重争端解决路径已经成为常态。
对于许多国际公约,目前的普遍情况是,争议解决程序往往包括了有相对正规的管辖权和裁决程序的国际“法院”,同时保留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进行仲裁的情形。譬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既设立了由21 名法官组成的国际海洋法庭(ITLOS),也存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附件7 的仲裁程序,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288 条第1 款还提供了因对海洋法公约进行解释产生争议的法庭管辖权;而海洋法公约第288 条第2 款则提供对于与海洋法公约相关的若干国际公约的法律解释发生分歧的争端的法庭管辖权。毫无疑问,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也含有多种解决争议的法律途径,包括调解、斡旋、仲裁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目前还设立了包括部分成员参加的临时多边上诉仲裁程序。
(二) 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裁决机制的相互影响及其差异的相对性
1.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裁决的属性差异是相对的
如前所述,国际仲裁机构与国际司法机构裁决的司法性存在差异,后者裁决的司法性更强,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后者的公正性更高,甚至可以说代表着人类解决国际争端和实现国际法治的某种进步。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国际仲裁(特别是机构仲裁) 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属性之差异只是相对的,两者并非绝然对立。
譬如,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具有《联合国宪章》 所赋予国际法院的明确职能,以及作为法院的永久性、程序公开、规约的不可让渡性以及第三国对程序进行干预的可能性,使得它区别于国际仲裁程序,但对有争议案件基于同意的自愿管辖权、以及引起广泛争议的临时法官(Judge ad hoc) 的选任、特殊案件法庭的组建(当事国可以各自指定法官组建三人特别法庭) 又使得其与仲裁庭的差异没有那么显著,〔30〕See Serena Forlati,The Internationa Court of Justice-An arbitral Tribunal or a Judicial Bod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2014,pp.31-49.就像美国籍前国际法院大法官斯蒂芬·M.施韦贝尔荣休后所述,“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不是普遍的,没有增强而是持续受到挑战……在有些案件中,法院明显具有管辖权或即使某些案件管辖权有争议,有些被告会员国仍拒绝出庭”。〔31〕同前注〔24〕,Stephen M.Schwebel 书,第9 页。英国著名国际法教授伊恩·布朗利(Ian Brownlie) 在其广为引用的国际公法的著作中也指出,“进入现代以来,对于国际争端解决而言,仲裁与司法裁决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任何涉及国家与其他当事方的运用国际法进行的争议裁决都属于国际司法裁决,而这些常设机构往往基于历史上的仲裁经验发展而来”。〔32〕同前注〔27〕,James Crawford 书,第694 页。因此,在基于当事方同意的自愿管辖这一点上,国际仲裁与国际司法裁决的性质差异确实不甚明显。
2.不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相互影响及其发展路径的曲折性
如前述,目前不少国际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通常包含多重争端解决方式,且其发展不是齐头并进,比如ICSID 国际投资争议停留在以个案仲裁为主、结合个别符合条件的裁决可撤销程序,而其他许多争议解决机制,不仅包括司法裁决路径、还包括仲裁机制,有的不但有一审机制,还有二审机制。同时,我们看到,有些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收案量大增,面临发展的机遇,比如ICSID 收案量在本世纪以来的增长,而有些受案量则踟蹰不前,如联合国海洋法庭,有些机制则经历了蓬勃发展正面临严重的困境,处于曲折阶段,如WTO 争端解决机制。应当说,各种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相互学习、参考和借鉴,从未停止。譬如,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关于ICSID 的投资争议解决改革谈判中,不少成员援引WTO 上诉机构建立统一法理的经验,希望在ICSID 的投资仲裁中也能够实现更大程度的法理一致性。而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在不同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可能遇到困境和挫折,国际社会在不同领域,对于国际司法裁决路径的探索从未停止。譬如,尽管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机构遭遇停摆危机,部分WTO成员设立多边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继续通过上诉解决贸易争端的实践,而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缔结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简称CETA) 中设立了具有两级审理机制(包括投资上诉法庭) 的投资法院,并在2021 年还通过了该法院运行的具体规则,尽管该条约尚未经当事方批准生效。〔33〕CETA 文本于2016 年完成谈判,部分条款已于2017 年9 月21 日临时生效,但不包括投资保护条款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解决(ISDS) 条款。欧盟法院在2019 年4 月30 日的第1/17 号意见(opinion 1/17) 指出,CETA 规定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符合欧盟法。2021 年1 月29 日,欧盟和加拿大共同通过四项具体规则,以落实CETA 中商定的投资法院制度(Investment Court System)。这四项关于投资法院制度的规则分别为:上诉法庭的运作规则(the functioning of the Appellate Tribunal)、投资法庭成员的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调解规则(Rules for mediation)、有约束力的联合解释规则(Rules for binding interpretations)。关于投资法院制度的基本原则已经在CETA 中确立,而此次具体规则是双方就投资法庭制度运行的详细规则、程序和结构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这四项规则以及CETA 的投资保护条款,须27 个欧盟成员国均批准CETA 后方可适用,目前仍有部分欧盟成员未完成核准程序。这些都表明,人类对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仍在进行中,没有停步。
四、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危机及其改革
作为在国际法领域独善其身的WTO 法律体系,其争端解决机制从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 到1995 年WTO,一路走来,经历了国际争端解决路径中从外交到法律、从GATT 时期类似仲裁的一审机制到WTO 时期具有“准”司法性(包括上诉机构) 的两审机制、又增设了在上诉机构面临困境期间运作的、部分成员参与、基于仲裁条款的临时上诉仲裁机制(Multi-party Interim Arbitration Appeal Mechanism,简称“MPIA”),这样一个渐进和包容的历史进程,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可谓独树一帜,富有特色。在过去几十年来,它对于和平解决关贸总协定/WTO 成员之间的国际贸易争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从关贸总协定到WTO 共平息了近千例国际贸易争端案件,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国际投资领域不同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接近尾声时,当时的核心谈判成员,包括美、欧、加、日(QUAT) 希望改变关贸总协定时期被告凭一己之力即可阻挠专家组报告通过的争端解决机制,期待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级审理的争端解决机构。为此,成员为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简称“DSB”) 发明了反向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基本上可以获得自动通过,并在对争议结果进行执行的阶段增添了合规审查机制,即原告可以通过诉诸原审专家组对被告执行争端裁决的结果进行一致性审查,并允许进行上诉,一旦裁定被告的履行不符合原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结果,争端解决机构可以通过反向一致的决策授权原告对被告进行报复的执行机制,由此,使得WTO 争端解决机制获得了“长了牙齿的”争端解决机制的称号。由于常设上诉机构25 年履职尽责的运行,WTO 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两百多个裁决报告,围绕涵盖协定形成了一整套比较严谨的法理,赢得了大多数成员的信任,被誉为WTO 的“皇冠明珠”。
从关贸总协定时期主要通过各代表团的外交人员参与争端解决到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聘用首位专业律师、随后设立由多位贸易律师组成的法律司专门负责协助解决成员间的国际贸易争端,到1995 年WTO 成立后设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共同组成的两级审理制度,WTO 争端解决机制走过了从外交到法律、从法律到“准”司法的历程。
WTO 的争端解决机构之所以不同于联合国国际法院,是因为从名义上其争端解决机制就不是“法院”,而是全体成员组成的总理事会的另一个牌子——争端解决机构。从WTO 的组织架构来看,最高权力机构是部长级会议,享有最高决策权和对条约的权威解释权,一般通过正向协商一致进行决策,但条约规则明确允许通过投票来行使决策权。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在其休会期间,由全体成员组成的总理事会代行权力。总理事会也是争端解决机构,每月召开一次争端解决机构会议,通过反向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争端做出的裁决报告,而通过正向协商一致通过其他事务的决策,包括任命上诉机构成员。因此,从性质上看,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协助总理事会行使争端裁决的职能,专家组裁决近似于仲裁而上诉机构裁决更具司法性,其裁决作出的结论是具有混合性质的“裁定和建议”(ruling and recommendation),“裁定”更具司法性,而“建议”则反之;其做成的裁决报告只有经以争端解决机构名义出现的总理事会通过才具有裁决效力,对争端当事方成员产生约束力。由于反向协商一致使得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几乎无法被WTO 争端解决机构所否决,即除非全体成员都反对,则报告自动通过。这也反映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自身并不具有裁决效力,而是必须经由争端解决机构通过。这恐怕是其与联合国国际法院裁决的最大区别。联合国国际法院做出的裁决、临时禁令和咨询意见,本身具有“司法”效力,形式上不需经过联合国大会的通过。尽管国际法院裁决的实施须依靠当事方的自愿执行,国际法院对被告成员不履行裁决的行为本身无权通过任何制裁或授权原告实施报复,这一点与WTO 又不相同。因此,事实上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具有准司法的执行效力,但从其名义和操作程序来看,仍然是全体成员经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通过两级审查来协助其完成争端解决。WTO 常设上诉机构虽然不是常设上诉法院,除了名称不同,实质上基本相同。正如日本籍前首任上诉机构成员松下满雄(Mitsuo Matsushita) 所指出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非常类似于一个国际贸易法院”。〔34〕Mitsuo Matsushita,Thomas J.Schoenbaum,Petros C.Mavroidis &Michael Hahn,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Law,Practice and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83.
如果我们运用前述国际法学者提出的关于国际裁决机构所具有的“司法性”的判定标准,WTO 争端解决机制尽管不具有法院的名号,其司法性在某些因素方面甚至超过联合国国际法院,特别在“管辖权”、常设上诉机构和有约束力的执行机制等方面。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对争议事项仅具有“选择性”和基于“合意”的管辖权不同,WTO 争端解决机制对于WTO 成员基于涵盖协定的所有争议拥有被许多WTO 学者称为是“强制”或“排他性”的管辖权,至少是具有某种“自动”性质的管辖权。〔35〕关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所涉涵盖协定的管辖权问题的争议迄今只有极少数的案件,如DS512 乌克兰诉俄罗斯的“过境贸易案”,美国对专家组是否对GATT 第21 条安全例外条款拥有管辖权存有争议。毫无疑问,这种“强制”“排他”或“自动”性质的管辖权强化了WTO 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司法性”。〔36〕无论从机制创新、争端解决案件的数量与效率,还是建立统一判理方面,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参见世界贸易组织著、赵宏主编:《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年度报告2019-2020》,赵宏审校,彭德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年8 月第1 版,中文版序第3 页。
这些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WTO 在国际贸易领域创立的争端解决机制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即它虽不具有“司法”之名,却具有迄今为止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所能达到的几近最高程度的司法性(司法性之实),这就导致不同的观察者对该机制的性质做出不同的解读,而这也许正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者创造性达成妥协的结果。
客观来讲,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争端解决程序的制度创新,它为WTO 成员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提供了几乎涵盖所有类型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方式,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包容性和灵活性。譬如,WTO 争端解决机制自始至终鼓励当事方通过协商达成双方满意的结果(即Mutually Agreed Solutions,简称“MAS”) 来解决贸易争端,其争端解决程序既包含了争端双方必经的磋商、协商作为前置外交程序,也包括由总干事、第三方的斡旋、调停和调解等友好协商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式的争端解决程序;与此同时,还设立有独立仲裁程序。〔37〕参见DSU 第25 条。当然,在过去28年来,WTO 成员运用最多的仍是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的两级审理、准司法性的程序,包括运用到执行阶段的两级履行合规审理以及通过反向协商一致进行贸易报复的多边授权机制。贸易报复的金额也通过专家组裁定,无需上诉。此外,对于每一个程序还都规定了特定的具体实施期限,以保障其高效、良好运行。
众所周知,当前WTO 争端解决机制正面临其上诉机构因没有裁判者而无法裁决案件的艰难处境,被上诉到空无一人的上诉机构的案件目前有29 起。〔38〕Se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ppellate Body,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appellate_body_e.htm.那么,如何认识WTO 争端解决机制当前面临困境的深层次原因? 尽管众说纷纭,当前的实际状况可能深刻反映了不同WTO 成员对于如此复杂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期待。比如对于该机制是否具有“司法”或“准司法”属性、其上诉机构受理案件的数量以及对于该机制已经产生的一系列判例是否应当维持或如何维持等等,WTO 成员的分歧仍然是深刻的。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世界两大法系的不同法律传统在争端解决方面的差异。
因此,WTO 成员对该机制正在进行的改革讨论及其未来走向,其决定因素可能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
1.在对WTO 的宗旨与目标的解读与执行方面,WTO 过去一直以维护自由贸易、通过扩大贸易推动人类福祉增长作为其根本的不动摇的目标,那么,在当前WTO 成员所面临的新的形势和环境下,WTO 成员对于维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贸易防御措施、环境保护与低碳目标、国家安全等非贸易目标方面应当把握怎样的平衡,即如何在现有规则体系内实现贸易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以及创新、人类健康与国家安全政策等方面的协调,这是决定WTO 改革的根本性问题,也是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然前置问题,即争端解决机制将如何贯彻和落实WTO所维护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宗旨和目标。
2.WTO 成员对于现有的争端解决谅解(DSU) 规则的缔约本意以及其各自对该争端解决程序规则运行的期待、包括其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和结果能否形成统一的认识,这是对于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本身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各方能否达成共识的关键问题。在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矛盾和冲突没有得到缓解的时代背景下,各成员对国家安全、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非贸易问题的关注持续上升,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何种性质和功能的WTO 争端解决机制最有利于高效、和平解决WTO 成员之间的贸易纠纷,是WTO 成员在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当务之急,当然是恢复WTO 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是其上诉机构的正常运行。目前近30 个案件堆积在陷于停摆的上诉机构无法得到解决,这是不符合任何成员利益的。
3.作为全球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包括最终如何阐释和把握争端裁决者在客观忠实地履行条约解释职责和其作为裁决者应具有的司法能动性和自主裁量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对历史上已经生成的以往裁决的判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其发挥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产生影响。
WTO 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给予了期限明确的授权,目前,WTO 各成员正倾力付出、积极参与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密集磋商和谈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WTO 改革。日前中国领导人对我国积极参与WTO 改革做出了具体指示,包括恢复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等。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众多成员的坚定支持和积极努力下,在WTO 总干事的卓越领导以及秘书处的强大技术支持下,WTO 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困境在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上取得突破和进展是可期的。
五、结论
人类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历尽波折,取得今天如此形式多样的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是世界各国政府、外交界、法律界矢志不渝努力的成果,也是近百年来国际社会成员在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和规则方面不懈创新和探索的结果。人类和平解决争端的任何进步都是来之不易的。
在国内法层面,我们看到无论是仲裁还是司法,其实质都是国家权力机关对争端裁决结果的执行做出的有力保障。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仲裁,在符合一国仲裁法的情况下,其裁决结果可以申请该国法院的强制执行,因此,仲裁既具有“自治性”,也具有“准”司法性。而在国际法层面,即使经成员国合意(同意) 达成条约建立的具有“司法性”的争端解决机制(如联合国国际法院),其裁决的执行也只能依靠国家自愿实施,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并无强制执行力。WTO 争端解决机制针对违反裁决结果成员所创设的通过“中止减让”实施的多边报复机制是一种特殊制度设计,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中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国际公法层面,无论是“契约”性的仲裁还是具有“司法”或“准司法”属性的国际司法裁决机制,其基石都是成员共识(契约),其裁决结果需参与争端的成员方自愿执行;而具有私法属性的国际商事仲裁和具有半公法半私法属性的国际投资仲裁的裁决结果,如果能够得到国内法院的承认与执行,其效力可以达到与国内仲裁和司法裁决基本等同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从“契约”到“准司法”的发展路径构成人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进步方向,但在实践中,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各类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多样性和争端解决多种法律道路多元共存局面将是长期现象。当然,人类探索更加公平公正、具有更高程度司法性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努力也不会停滞不前。不过,国际争端裁决的“契约”和“准司法”性,在国际法层面,目前的基石仍是“契约”。在主权国家构成主流国际法主体的时代,所谓国际法的宪法化、法治化和机制化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权国家性质带来的制约和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仍将长期存在。无论如何,建设更高统一性、更高水准的国际法治的理想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特别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理想的探索历程中,追求建立独立公正的国际司法裁决机制是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然的理想目标。总之,既着力于现实的国际法治建构,亦胸怀对未来的国际法治目标的拓展,我们坚信,从长远的目标而言,人类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未来前途必将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