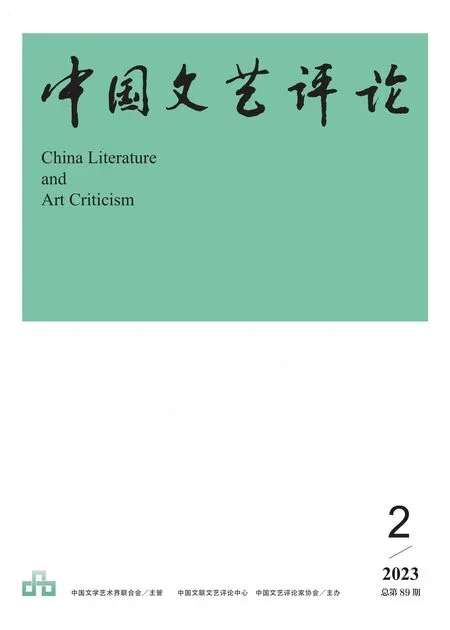2022话剧:“阵痛”与“破局”
■ 徐 健
2022年,中国演出行业遭遇了疫情以来最为严峻、最为复杂的防控形势,经受了种种突如其来、难以预测的压力和挑战。不确定性,不仅成为国内疫情防控直面的课题,也成为包括话剧在内的演出市场面对的难题。如何在“不确定性”这个最大的变数中探寻话剧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如何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期间依然让观众感受舞台、剧场的温暖与力量,这一年,话剧工作者用他们的坚守、付出、执着,为暂时处于困境中的演出市场注入了信心与希望。同样是这一年,在紧张而有限的创演时间内,国有院团、民营公司等不同的演出机构,努力克服、积极应对特殊时期排演、巡演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从主题创作、小说改编、线上展演、拓展演出渠道等多个方面持续发力,以各自富有成果且值得尊重的艺术实践,留下了中国话剧求新、求进、求变的探索足迹。
主题创作的时代精神与技术升级
2022年是国家级舞台艺术评奖大奖——最引人瞩目的第十七届“文华奖”和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的评选。9月1日至15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在京津冀三地同时举行,本届艺术节以“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宗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4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文华奖参评作品58部(台)和特邀剧目26部(台)。在39部入围文华大奖终评名单的舞台艺术作品中,话剧、儿童剧有9部,“就题材而言,这些话剧纵贯历史,贴近生活,以现实题材为多;就叙事而言,努力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了构思的突破与探索;就形式而言,推陈出新,以科技赋能戏剧表现,追求富有艺术美感的生动画面”[1]宋宝珍:《为人民而歌,为艺术求索——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话剧剧目简评》,《艺术评论》2022年第9期,第18页。,集中反映了近些年话剧、儿童剧的创作概况,尤其是在现实题材、现实表达方面的艺术面貌和实践成果。而获得第十七届“文华奖”的3部话剧作品《塞罕长歌》《桂梅老师》《主角》,则分别从主题立意、叙事视角、形象塑造、文学转换等不同角度为此类题材创作提供了新的探讨空间。紧接着,10月中宣部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揭晓,《路遥》《深海》《龙腾伶仃洋》《青松岭的好日子》4部话剧入围,涵盖英模、科技、工业、农村等多个领域,体现了当代话剧在驾驭宏大叙事与日常情感、国家历史与个人成长史、时代精神与审美表达等的关系上,在力避同主题创作、同题材书写概念化套路化方面进行的开拓尝试。国家级奖项是激励艺术院团多出精品力作、多出优秀人才的重要方式,也是以荣誉和奖励引领创作方向、创作观念的重要途径。从2022年度两个重要奖项的评选看,现实题材作品占据绝对优势,一方面显示出近年来相关主管部门在推进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创作方面取得的扎实成绩,现实题材创作已经成为国有院团话剧创作的主流;另一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创作生产引导、推进文艺创新的功能。对于今后一段时期而言,如何用戏剧的方式表现新时代的中国,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人的故事,依然是话剧创作者需要不断攻克的艺术课题。
为迎接、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一年国有院团集中围绕“献礼党的二十大”这个重大主题组织了一系列创作演出,由此带动了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创作在2022下半年的集中涌现。现实题材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安徽省话剧院、马鞍山艺术剧院联合演出的《炉火照天地》(编剧王俭,导演李伯男)和南京市话剧团的《小西湖》(编剧唐栋,导演傅勇凡),前者属于“硬核”的工业题材,以马钢集团突破瓶颈实现特种钢和高速车轮国产化为情节主线,塑造了以特钢科研精英陈钢为代表的新时代工人群体的舞台群像,并从两代人矛盾的多视角切入、“九号高炉”现实与象征意义的多重表达、钢铁工业元素的巧妙穿插等不同方面,为传统的工业题材注入了新时代的精神气质与形象标识。后者属于“烟火气”的民生题材,以南京重要民生工程小西湖的城市改造为核心,同样用群像戏的方式,展现了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全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以旧城改造为主要内容的话剧此前已有不少成功之作,形成了一定的叙事套路,该剧的创作者深入开掘小西湖这个独特的横切面,在契合主题表达需要的同时,突出以人为本、敬畏文化、敬畏历史等关键词,为这部“沾泥土”“带露珠”的百姓戏赋予了鲜明的新时代特色。
红色题材方面,中国国家话剧院创作演出的《铁流东进》(编剧查文白、钟鸣,导演查文浩)、《抗战中的文艺》(编剧秧禾之文工作社,导演田沁鑫),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的《觉醒年代》(编剧喻荣军,导演何念)、《英雄儿女》(编剧喻荣军,导演胡宗琪),武汉人艺演出的《狂澜》(编剧步川,导演傅勇凡),中央党校大有影视中心、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联合制作的《万水朝东》(编剧孟冰,导演王斑)等皆为2022年度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品,且在故事来源、呈现样式、舞台表达等方面体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和倾向。
首先,优秀红色影视IP受到热捧,话剧与影视跨界“联姻”,丰富了戏剧表现红色题材的样态与维度。在这方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探索走在前列。其中,《觉醒年代》改编自2021年热播的同名电视剧,呈现了从新文化运动到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六年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如何把43集容量的电视剧内容浓缩在150分钟内,如何在保留复杂历史背景、人物命运走向、主要人物关系的基础上,呈现历史本身的丰富厚重、思想文化的多元冲撞,改编者立足李大钊、陈独秀两个核心人物展开情节,从一本杂志的命运与一群人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逐渐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过程延伸叙事,通过蔡元培“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胡适与辜鸿铭的礼堂“交锋”,南方考察归来的李大钊与陈独秀、胡适畅谈中国未来道路,陈独秀送别陈延年、陈乔年等一个个极富戏剧性、抒情性的桥段和带有论辩色彩、历史质感的场面,让宏大的历史、思想的光芒、青春的力量、道路的选择体现在具体而真实的个体身上,以炽烈、诗意又浪漫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代人的致敬。其次,注重向文学、文化“借力”,以此拓宽红色题材的内容选择和表现领域。《铁流东进》与《英雄儿女》都是以文学的基础展开创作的,前者改编自作家季宇的中篇小说《最后的电波》,后者取材于巴金小说《团圆》以及同名电影,两者都是红色题材中较少表现的军事和战争领域,都是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小见大,从“寻找”打开进入历史的切口,以普通人的思想蜕变、情感递进,诠释信仰、牺牲、忠诚等的精神蕴涵,让英雄回归生活、回归日常。《抗战中的文艺》则是以“文献话剧”与“编年体”的形式,展现抗战时期中国文艺的精神与力量的作品。该剧前后有14年的跨度,涉及三十多位文学艺术门类的名家,几乎涵盖了半个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史,在文人选择、文艺创作与战火硝烟、国家危亡的交织碰撞中,阐释了文艺与时代之间的深刻联系,展现了中国的进步文艺家为寻找中国的出路、用文艺的方式求索奋进的战斗历程。再次,二度创作上普遍提升了科技含量,借助最新的影像技术和媒介手段,提升此类题材创作的视听与审美观感。比如,《抗战中的文艺》以正上方宽银幕加下方九块小屏的设计构成舞台主体,充分依托小屏的多元场景组合,将照片图片、史料文献、电影片段、场景再现等元素与现场和影像的叙述相结合,同时依托音乐、美术、装置等多种艺术手段,力图在艺术语汇的综合中,打造一座舞台版的“抗战文艺博物馆”。《觉醒年代》将演员的表演与全机械转台、多媒体的影像效果相结合,既有效营造出剧情所需的不同时空,又增加了舞台的象征性与文化蕴涵,像舞台上不时出现、不断增强的火苗元素,象征着黑暗中希望与光明的探索,呼应着一代人思想的觉醒。
此外,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天算》(编剧孙浩,导演宋国锋)、江苏省演艺集团的《新华方面军》(编剧罗周,导演李伯男)、浙江省话剧团的《思凡•陆小曼》(编剧林巧思,导演李伯男、刘昊)等剧目,或依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配置、性格塑造与传统文化的新表达,或追求现实主义的诗意呈现、人物传记的崭新尝试,为话剧驾驭不同题材与叙事提供了新的经验。
新的舞台样式、新的技术手段的创造、运用,为主题创作增添了时尚气质和全新观感,但也为文本和舞台上过度张扬的形式主义、技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实际上,中国话剧当下面对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技术层面的落后或者升级,而是来自艺术观念和创作心态层面的进一步解放与沉潜,是如何以戏剧的方式塑造真正的人,以人的境遇与困惑去透析时代演进、彰显人的价值和思想光芒的问题。不去解决创作源头上的生搬硬套、虚张声势、主题先行,反而以舞台上的“锣鼓喧天,声色并用”为潮流,不得不说是当下创作上值得关注的一种倾向。“舞台性过重,往往只能达到粉饰戏剧性的作用。刺激是一时的,然而难于把主要的东西留给观众灵魂的深处。”[1]李健吾著、李维永编:《李健吾文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53页。李健吾当年在观看话剧《蔡文姬》后与焦菊隐先生进行商榷时提及的问题,对今天的一些主题创作而言,启示意义犹在。
文学改编的民间视角与地域表达
近五年,文学改编话剧已经成为每年演出市场上重要的文化现象,且有持续升温的态势。从改编作品的来源看,中国当代小说尤其是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格外受到青睐,获奖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受众传播、时代影响,为话剧的改编提供了再创造和观众接受的天然基础。同时,中国现当代重要作家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进入话剧改编者的视野,文学与话剧之间的关系因为改编而变得日趋紧密。这一方面反映出文学在众多艺术门类中“母本”作用的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话剧主动向文学“借力”,也显示出近些年话剧演出市场对优质文本资源、故事资源、文化资源的渴求,以及尝试摆脱原创焦虑、“剧本荒”的努力。从表现内容上看,家国命运、民族史诗、市井平民成为改编较为集中的三个领域,改编者更偏重于带有一定时空维度和时代跨度的宏大叙事,以此增强剧作的厚重感、史诗性,更注重在尊重原作故事和叙事结构的基础上,以“守正”的心态完成文本和表现形式的“忠实”转换,从而尽量满足观众在剧场中接受一个完整的“故事”的需求。从参与的机构看,选择文学改编策略的已不再是少数一两个演出机构、制作机构,更多的创演机构参与到了文学资源的版权开发与运营上,优质的文学IP和优秀的主创团队日渐成为创演机构抢占市场先机、盘活演出资源、衍生品牌效应的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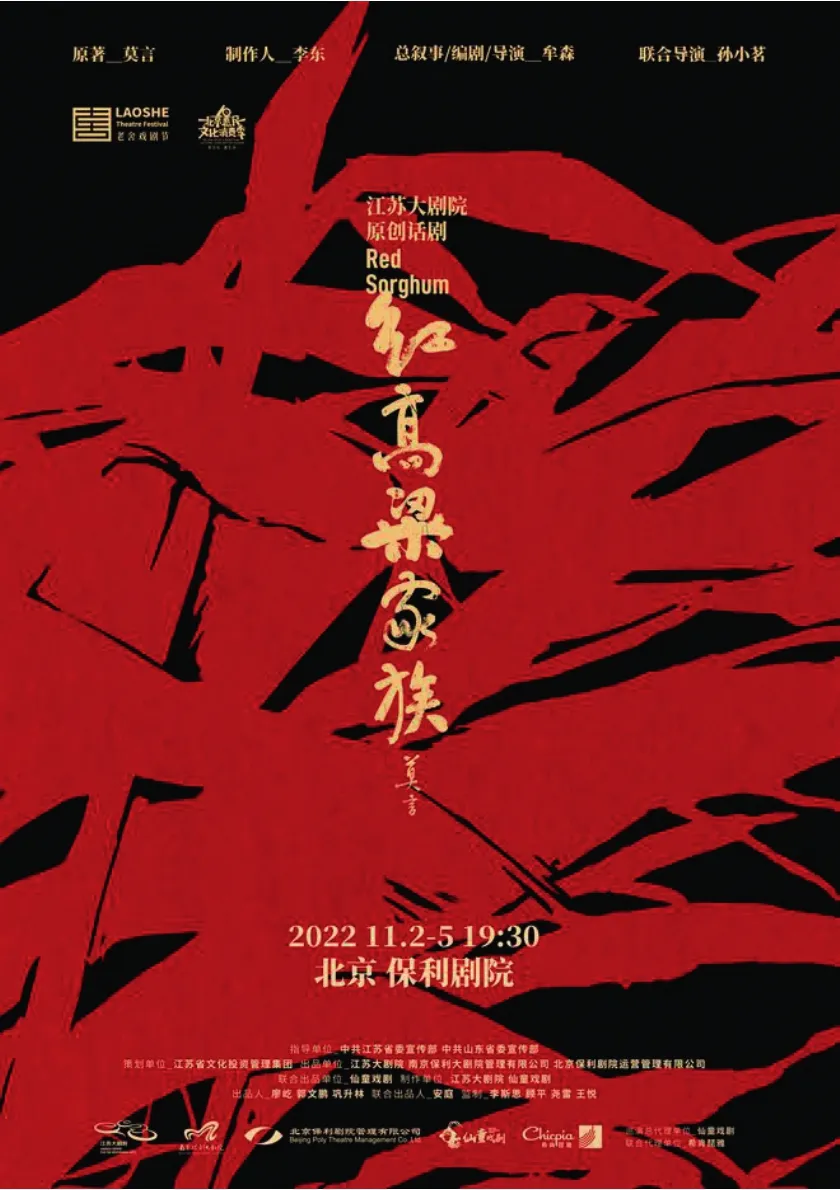
图1 话剧《红高粱家族》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2年,尽管受疫情影响,演出市场整体表现欠佳,但是文学改编却为这一年的话剧市场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话题。这既包括相关的研讨和学术对话活动的增多,像北京文联主办的“坊间对话”聚焦“文学作品话剧改编的探索与创新”、第六届老舍戏剧节主题论坛推出“文学改编舞台剧的观察与思考”等,更包括改编实践本身体现出的新特点、新趋向。纵观全年的改编剧目,那些立足民间视角,从普通人或者个体的生活变迁、心灵嬗变与命运沉浮中积蓄叙事动力、提炼主旨立意、寄托文化蕴藉的改编依旧成为此类创作的主体。像2021年首演、2022年度全国巡演的话剧《人世间》(编剧苑彬,导演杨佳音),2022年度新推出的改编自蔡崇达同名小说的《皮囊》(编剧罗仁泽,导演王婷婷),根据刘心武同名小说改编的《钟鼓楼》(编剧黄盈、张弛,导演黄盈),根据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主角》(编剧曹路生,导演胡宗琪),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我不是潘金莲》(编剧卓别灵,导演丁一滕),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红高粱家族》(总叙事、编剧、导演牟森)等,皆从不同角度在舞台上呈现了一个个来自于小说中却又迥异于文字想象的大地、生命、记忆与情感,展现了隐藏在民间的自在、温暖、激情与抗争。这其中,《红高粱家族》可以说是对舞台上的民间开掘得较为自由、酣畅的一次美学实验。该作品的改编并没有沿着原小说意识流式的魔幻笔法展开,而是以编年体为主,回归民间的传统叙事,以前因后果的方式引出原作中抗日与爱情两条线索。这看似是为了观众更好地进入“故事”,实际上陷入的却是牟森关于“生命美学”的叙事圈套。剧作以“四季”构成四大篇章,“四季轮回,万物生成”对应的是生命的不同阶段,由此全剧的主要矛盾就变成了生命的自由、自发、自在状态与扼杀、摧毁、侮辱生命之间的角力,而贯穿其中的生的顽强、死的悲壮、爱的恣肆、情的奔放、仇的惨烈,也在“抬棺”“酿酒”“剥皮”“抵抗”等充满仪式感的场景中呼应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激活了民间的自由与野性,暗含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
与民间视角对应的则是地域性表达的强化。2022年度改编的作品大都跳出了对特定地域空间的反复表现,而具有了内容视域、审美风格、艺术呈现上的差异性,并形成了改编舞台上独特的地理风貌。比如,根据冯骥才同名小说改编的《俗世奇人》(编剧黄维若,导演钟海)以清末民初时期的天津卫为背景,将这片土地上各具特色的奇人异事浓缩成一幅天津卫市井民间的“奇人画卷”,透露出仗义、豪爽、风趣的天津性格。《红高粱家族》中由放大的高粱穗、鼓风机、酒坛子等元素构成的舞台空间,虽然带有强烈的象征性与仪式感,但其所竭力营造的还是一个充满着艺术想象的“高密东北乡”,以及它所孕育的粗犷、坚韧、率真与恣肆。《皮囊》在主人公的“出走”与“归来”中,为观众打开了时代进程中属于闽南东石镇的一个片段,这里有深厚的宗族传统、民间信仰与伦理规范,更有青春的叛逆、成长的想象与现实的逃离,由此触发的传统与现代、世俗与人伦、亲情与叛逆之间的冲突,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与更广大的世界有了人生体验上的共通性。黄盈导演的《钟鼓楼》和《我这半辈子》(编剧黄盈、张婷等)则持续其对北京城与北京人故事的挖掘。前者是富有年代感、纪实感的“小院戏”,以结婚这一人生的重要时刻连接起四户二十多个角色的“众生百态”,展现了变动的时代里普通人的坚守与躁动、冲突与和解,而熟稔的生活细节、温情的邻里关系、镌刻着岁月痕迹的“钟鼓楼”,则时时透露着这部作品的“京味儿”风韵。后者改编自老舍一系列自传性质的文学作品,以出生在小年夜的“常顺”为主角和讲述人,表现了其从出生之日到而立之年确定人生目标和写作方向的跌宕“半生”,剧作横跨北京、伦敦两座城,在现实人物与文学人物的交织、互衬中,寄予着沉郁且忧伤的人生况味,剧中冰雪、水面等与主人公的成长、人生有着密切关联的季节、自然符号,在追寻老北京生活记忆的同时,留下了关于人生与精神的文化隐喻。
话剧《主角》和《我不是潘金莲》在2022年度改编实践中既带有共通性,又体现了各自鲜明的艺术追求。两者都是“大女主”的作品,一个是名声远播的秦腔皇后忆秦娥,一个是再普通不过的底层妇女李雪莲,虽然身份地位不同,但性格中都蕴含着倔强、执拗、不屈的一股劲头;都是女性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进行的抗争,成长过程交织着艰辛、孤独、屈辱与无奈;都经历了关于命运与生活的解不开的谜团,一个逆境中成长,终成“大角儿”,荣誉与风光无限,但始终没有摆脱成长的梦魇、婚姻的悲剧、世俗的冷眼、同行的倾轧,舞台人生与现实人生时刻处于抵牾之中。另一个仅为了一句话、一个“理儿”,“不辞劳苦地倔强着、苦涩着、坚持着,但人生的死结并不因个人的委屈和辛苦而舒展。如同鬼打墙,李雪莲二十年的路程竟是在一个圈子里兜转循环”[1]谷海慧:《〈我不是潘金莲〉:舞台上的循环》,《北京日报》2022年9月2日,第13版。。两者又因故事走向、形象定位、艺术风格,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改编的《主角》,忆秦娥的“落幕”不再是寂寞与悲凉,反倒在秦八娃的劝导下,重燃艺术的热情与自信,扛起了赓续秦腔传统的重任。《我不是潘金莲》却并未给李雪莲以命运的改变,如同开场一样,剧终的李雪莲仍然是被他人围观的对象,只是逐渐增强的心跳声,让残酷、无奈、落寞的氛围进一步强化。《主角》立足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融合了写意、象征等手段,忆秦娥的命运之下勾连起的是秦腔艺术以及社会变迁、心灵跌宕的大时代、大历史。《我不是潘金莲》交织着真实与荒诞、象征与诗意,李雪莲虽与各级官员有了“接触”,并同戏曲中的潘金莲进行了“隔空对话”,但黑色幽默之下是生存的无奈与沉重的反思。
此外,2022年度的乌镇戏剧节上推出的孟京辉戏剧工作室出品的改编自余华同名小说的《第七天》(导演孟京辉)和新青年剧团出品的改编自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同名小说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导演李建军),也因各自在理念、表演、剧场性等方面的大胆而颠覆性的创意、呈现,给文学改编带来了新的样态。纵观全年的文学改编实践,制作水准、技术手段、演出质量等各方面均普遍有了提升,“从原著中来、回原著中去”的中规中矩的改编思路也没有给作品带来太大的叙事偏差。但是回到改编作品本身,正如有论者谈到的,“这些改编的作者,好像自己走得太少了。一个是他们在主观上,想把原著那么一个长篇故事压缩在舞台时间当中,还想讲完完整的故事。这就造成改编上比较吃力。另外一个,这样也会限制去做经典文本和当代的结合”[2]南京大学副教授陈恬语,转引自朱圆:《后疫情时代,戏剧何为?》,2022年1月23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2755688331767268&wfr=spider&for=pc。。显然,目前的改编更多还是停留在情节和故事的层面,着力于文学形象、语言到舞台形象、语言的“忠实”转换,至于改编本身的创造性、当下性以及改编者立场、观点的表达,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浅尝辄止亦或暧昧不清。诸如对“民间视角”的理解,可谓“见事不见人”,更倾向于去猎奇奇人异事、再现生活的热闹与自在,却很难捕捉到鲜活的生命个体与精神张力,书写民间的立场与情怀较为悬浮;有些改编依靠了文学IP的口碑、流量的加盟,达到了一定的市场宣传效果,但难掩叙事逻辑、人物塑造、改编立意上的粗糙、孱弱与刻意。艺术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向着人性、心灵、精神未知的领域不断挺进的过程,文学改编同样如此。期待随着未来相关改编实践的增多,话剧舞台上能涌现出越来越多文学与话剧“跨界”融合的佳作。
未来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前瞻思考
2022年的中国话剧市场,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取消或者延期、暂停或者等待,已然变成了全年的常态。正常创演节奏的打乱,城市巡演充满不确定性,企业经营成本压力陡增,人员组织协调难度加大……即使有了前两年常态化防疫状态下积累的应对经验,但是因一年来疫情出现的高频次“变数”,演出行业还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经历了近年来最大的“阵痛”。“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综合调研票务平台、剧场、演出经纪机构,从2月中旬至3月中旬期间演出取消或延期的场次超过4000场,3月下旬还将有约80%的项目停演或延期。据测算,预计至3月底全国取消或延期的场次约9000场,占一季度专业剧场、新空间演出总场次的30%。”[1]姜琳琳:《至3月底全国取消/延期约9000场》,微信公众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2年3月22日。这组202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疫情之下演出市场的受冲击程度。而在2022上半年,北京、上海等主要话剧演出市场,因为严格疫情防控规定,停演、延期更是让国有院团、民营剧团、演出机构等按下了长达数月的“暂停键”。下半年,尽管主要城市的演出逐渐步入正轨,但是散点突发的疫情还是让进入市场的话剧主体如履薄冰。如何应对“阵痛”带来的挑战,如何从重重风险中寻找“破局”的机遇,抱团取暖、增强信心、提升质量,无疑是现阶段演出团体需要的精神激励,但还是要继续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在吸引观众、留住观众、培养观众方面,积极探寻良策、主动“破圈”发展。这之中,“线上展演”以及“技术赋能戏剧”在2022年度的多样实践中留下了不少启示。

图2、3 话剧《茶馆》剧照(摄影:李春光)
自3月12日起,在线下演出暂停的77天时间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艺起前行•云上剧场”项目,免费播放了53部剧目、88场次,在12个播出平台吸引了超过2500万人次观众。6月13日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还携手优酷、大麦推出付费观看的“NEXTheatre无界剧场”,以线上点播的方式邀观众一起重温《商鞅》《秀才与刽子手》《万尼亚舅舅》《牛虻》《玩偶之家》5部剧院的经典话剧作品,充分依托互联网技术手段,开启线上剧场演出新布局。[2]参见赵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开启线上收费点播,网友感慨:终于有补票的机会了》,2022年6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4314716344 28639&wfr=spider&for=pc。自6月5日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启建院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涵盖经典剧目线上推送及导赏、剧本朗读、院庆纪念晚会实时直播、首次采用8K技术录制的院庆版《茶馆》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等内容,八天的时间里,吸引了全网超过1.4亿人次点击观看,仅6月12日当天,就有高达5000万人次进入直播间。[1]参见马二:《人艺〈茶馆〉直播超5000万人次观看,云直播能救舞台剧吗?》,2022年6月14日,https://view.inews.qq.com/k/20220614A03GIH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9月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80多部作品完成了158场线上线下演出,280多个平台参与了线上直播,累积观看人数超过3.5亿人次。[2]参见范朝慧:《“十三艺节”期间20万人次进场馆 超3.5亿人次聚云端》,2022年9月30日,https://new.qq.com/rain/a/20220930A08HU500。8月至9月,第七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从参展的优秀剧目中选出《浪潮》《右玉》《喜相逢》《兵团》等12部进行限时免费线上展播,惠及观众近200万人次。[3]参见王润:《第七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落幕》,2022年9月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3039 729060517475&wfr=spider&for=pc。除了“线上展演”这样的常规方式外,一些依靠科技延展舞台边界的新实验,在技术时代拓展着戏剧表现的新样式、新空间,如上海大剧院携手直播平台打造“VR未来剧场”概念,推出线上沉浸式互动戏剧《福尔摩斯探案:血色生日》,在借助技术增强线上演出参与感、体验感方面继续了新尝试;广州大剧院推出的“5G智慧剧院”,将剧目以多视角场景拍摄并上线视频平台,涵盖多屏多视角、自由视角、裸眼VR等手段,突出了观赏的个性化、多维度。
“互联网+”以及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众多科技手段的介入,打破了剧场空间的局限,带来了话剧观赏的全新体验。但就目前而言,“科技赋能戏剧”,大多还是倾向于将技术成果转化在舞台的二度创作、体现在演出的后续传播上。科技能否在包括项目策划、论证、创作、排练、演出、传播、评价乃至人才培养等全链条的各个环节发挥不同的作用,或者说戏剧人如何借助科技来实现对戏剧艺术自身发展的促进,则是需要从业者接下来认真思考的。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科技过度赋能戏剧,又要掌握好科技介入戏剧的度,让戏剧能够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好地保持自身的艺术特性、延伸自己的存在价值。而实现这样的诉求,优秀人才的参与至关重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面对技术的不断更迭和审美接受方式的多样,我们不仅需要具有艺术眼光、懂得戏剧艺术美学规律的创作者、从业者,更需要大量对技术前沿比较敏感且具备深厚人文底蕴的复合型人才。此外,文学与戏剧都是人学,“科技赋能戏剧”的落脚点最终还是要落在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整个知识体系、想象方式、社会结构的逐渐改变上。在对科技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中,努力探寻塑造人、表现人、揭示人的新的美学表达,让观众在技术时代更好地回到剧场,用心体验人与人现场交流带来的审美愉悦和情感冲撞,在剧场中学会独立思考、更好地认识自我,或许这才是戏剧融合科技的关键所在。
这一年,发表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题为《观众在哪里?》的文章,作者用“幽灵”形容疫情之后德国一些剧场面临的观众流失问题:“一个幽灵在剧场里游荡,它不是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也不是易卜生剧中的‘群鬼’,而是未来的幽灵:观众来得很少!”“观众会回来吗?”[1]VASCO BOENISCH, “Wo bleibt das Publikum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7.5.2022.这是作者的疑问,也是整个行业的忧虑。之后,在该报陆续刊发的相关文章中,“危机中的剧院:台下什么都没有”“空荡荡的剧院”等,屡屡成为标题,探讨观众减少的原因、为剧院发展寻求良策也成为德国戏剧界关注的话题之一。戏剧体系完备成熟的德国在疫情“阵痛”中面临的问题,是否会成为中国话剧即将面临的问题?在中国演出市场,除了粉丝、爆款带来的短暂票房效应,我们的更多主流剧目、商业剧目能否将观众继续留在剧场,在新一轮的市场考验中重塑自己?
2022年度,一系列把观众留在剧场、拓展演出渠道、坚持艺术品质、积蓄戏剧人才等的实际举措,让我们感受到业内在悄悄地积蓄力量,向着青年、向着未来的舞台和剧场而努力着。6月30日,在因疫情暂停演出66天后,北京鼓楼西剧场八周年推出“独角Show”演出季,包括《一只猿的报告》《象棋的故事》《吉他男》三部独角戏,在戏剧类型的差异化实验上,体现出剧场运营思维和发展定位的新探索。同一天,由导演、舞美设计易立明担任艺术总监及院长的北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正式投入试运营,“医学的胜利三部曲”《科诺克医生》《弗兰肯斯坦》《我是哪一个》的接续上演,让这处具有独特设计理念的新型演艺空间在艺术表达的多元与精神思辨的引领方面,给予了观众更多新期待。7月至9月,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12位青年戏剧导演以古典文学《水浒传》和《牡丹亭》为母本进行“现代化转译”,既为青年编创演人才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平台,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青年戏剧人才创造力、想象力的集中检阅。8月,话剧《惊梦》登陆北京国家大剧院舞台后,开启全国巡演并引发各地观众热情,在日益多元的文化消费与不断挑剔的观众面前,《惊梦》连续创造演出话题,且获得豆瓣9.4的评分,这显示的不仅是这部作品本身在喜剧架构与悲剧内核、个体命运与历史走向、传统价值与现实境遇、雅俗之辨等方面提供的多维阐释空间,更为主要的是为演出市场注入了信心。并不是观众拒绝了剧场,而是剧场能够给观众提供什么,《惊梦》的成功值得进一步探讨。10月,话剧九人推出了民国知识分子系列的第四部作品《对称性破缺》,作品从擅长的领域和人物出发,寄予的却是时间与命运的谜题。值得关注的是,在疫情防控的不确定中,话剧九人制作的《春逝》《双枰记》开启全国多个城市巡演,收获了不俗的好评与口碑,这对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非职业戏剧团体而言,实属不易。同样在这一年,老舍戏剧节、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乌镇戏剧节等已颇具品牌效应的戏剧节,克服重重困难,相继与观众见面,并以各自不同的定位和丰富的剧目,呈现着戏剧的无限可能,而以“新空间戏剧试验”为主题的首届蛇口戏剧节、以“山水有约,桂林有戏”为主题的首届桂林艺术节等新创办的节日,则让戏剧的种子在更多的地区萌发,为更多的青年戏剧人创造着机会,创新的办节理念也彰显着当代剧场的力量与价值。

图4 戏台三部曲之《惊梦》海报(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们不需要肤浅的娱乐。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我们需要共享空间,并要加以培育。我们需要彼此聆听、相互平等的受保护空间。”[1]转引自《2022年国际剧协“世界戏剧日”60周年全球线上庆典 全球37位新晋艺术家特别呈现》,微信公众号“中国戏剧家协会”,2022年3月27日。这是国际知名歌剧及戏剧导演、艺术节总监彼得•塞拉斯在2022年3月27日第60个“世界戏剧日”所作的献辞中的一句话。在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戏剧人该如何去表达现实、如何去传递思想、如何与观众对话,这是所有立志于献身这项事业的从业者都需要思索的课题。期待踏上新时代第二个十年的中国话剧,能够在坚守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用智慧和行动去跨越短暂的“阵痛”,重塑话剧在今天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尊严,为人们保留一块“彼此聆听、相互平等”的精神空间。[2]本文作者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