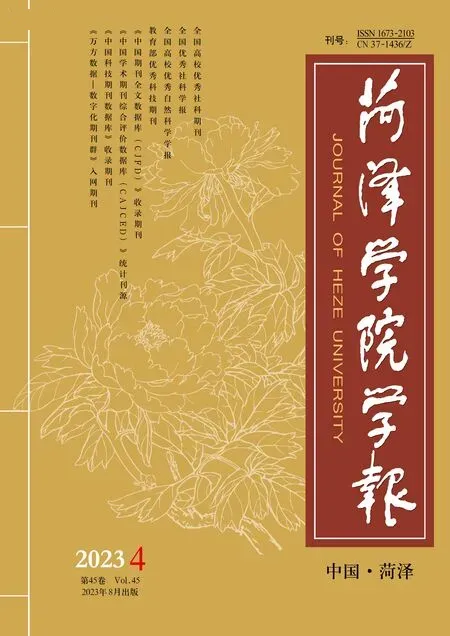《悠悠岁月》的“自我民族志”书写探析
李 唯,王艳芳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于1940年9月1日出生于法国利勒博讷,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她先后就读于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1974年安妮·埃尔诺开始文学创作生涯,并于202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随着年龄的增长,埃尔诺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演变和人生的短暂,“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1]。因此,作为“自我叙事”先驱的她,用二十余年的时间重新构思并出版了《悠悠岁月》(LesAnnées)一书。在这部作品中,埃尔诺自我反思式地跨入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领域,这不是一部虚构式的小说,用她的话来说,是一种介于“文学、社会学与历史之间的”东西。安妮·埃尔诺用客观、中立的写作手法,将照片和影像资料作为自己回忆的叙事代码,“超个人”地撰写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子女教育、阶级迁移以及丧亲之痛。不同于传统的自我叙事作家,埃尔诺转向了新的写作立场——“我不满足于仅仅把我记忆中的影像挑选出来摘录,而是要像处理文件一样,从不同角度审视它们,换句话说,我要对自己进行民族志研究。”[2]
“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学者通过系统的社会学自省和情感上的召唤来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们从个人生活出发,关注个体的情感和思绪,再落脚到社会与历史层面[3]。安妮·埃尔诺的“自我民族志”书写,表现在通过对《悠悠岁月》中集体记忆的精心建构,从历史涌动的潮流中感受自我的延续与存在。她从女性的自我体验出发,推己及人,运用“无人称”的叙事模式,用群体的自我认知唤起读者共鸣。埃尔诺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志样本进行研究和反思,在充满画面的点滴回忆里挽回即将消失的时代,“打破忍受和压抑的孤独经历,让人们可以重新想象自己”[4]。
一、在历史回忆中找寻自我
自我民族志的研究者往往通过描述自我的亲身经历来表现主体性[5]。安妮·埃尔诺自1984年出版《位置》(LaPlace)一书后,就开始了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创作题材的写作生涯。《悠悠岁月》的创作中她又在自我书写的层面上加入大量的社会和历史话题,埃尔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叙述一种生活,解释自我”[6]。因此,埃尔诺的自我民族志书写,是用历史的笔触找寻逝去日子里的印象,感受世界的变化。埃尔诺说:“如果可能提高自我认识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确定在每个年龄、生命的每一年,我们怎样回忆过去。”[7]她首先从儿时的照片开始回忆,通过视觉上的反馈,回到不同的历史节点。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选取了12张照片,每张照片所在的历史节点分别对应着埃尔诺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刻,比如1955年在寄宿学校里的埃尔诺,因外貌与穿着的不同而感到阶级差距,尽管那是一个让历史学家无法忘记的年代,但是对埃尔诺来说,那些羞耻到疯狂的记忆会永远印刻在她的脑海中,不断重复,不停出现。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正处于战后重建的时代,人们怀着对战争恐惧的心理,在餐桌上讨论飞碟和人造卫星,默契地避开任何有关集中营的话题,而此时的英语世界充满音乐和时尚,唱片机的流行让人们不再只唱爱国歌曲。在这样一个充满爱情和暴力的世界中,十四岁半的埃尔诺像无数少女一样焦虑和羞耻着自己的头发和身材。埃尔诺“通过集体的经历截获投射在个体记忆的屏幕上的反光”[8],把自己凝聚在这个戴着眼镜、褐色头发的少女的身体里。另外,在《悠悠岁月》中安妮·埃尔诺选取的两段影像,分别是1972年到1973年的一段家庭影像和1985年12月份在塞纳河畔维特里的一所中学播放的30分钟盒式录像带。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影像的画面中出现的两个小男孩,表明了埃尔诺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虽然埃尔诺有一份可以让她跨越阶层的工作,她仍旧在日记里写道:“成为教师使我心碎。”[9]当一切都在向现代性迈进的时候,人们的心灵却变得无比空虚,面对那些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示威游行或投票选举,生活在法国巴黎的人们却想远离这座繁华的大城市,安妮·埃尔诺一家也不例外。随着电视的普及,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记忆换了一种方式保存,信息的流通也越来越迅速,那些曾经生活在埃尔诺记忆里的知识分子或者名人歌星,都逐渐走向了死亡。对于埃尔诺来说,年龄的增长使得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变得模糊”[10],所以无论是照片定格的历史时刻还是影像记录的一段过往,都是埃尔诺进行自我叙事的途径,她用现在的自己去回忆、反思、重构过去的自己,并把这些破碎的生活片段重新连缀成一个整体,来达到自我的一致性。
照片、音像资料是自我民族志学者常用的研究资料,可以更直观地展现作者/研究者的真实人生经历,也可以帮助作者更好地回忆起照片或影像所展现的物理时间。在自我民族志学者眼中,他们会透过一个安装了民族志视角的广角镜,并把焦点落在外在于他们个体经历的那些社会与文化方面,揭示出一个已经并将继续通过社会与文化折射出的脆弱自我,与此同时又拒绝一种文化的解释,并随着镜头的调整——由内向外看和由外向内看[11]。
安妮·埃尔诺从照片出发由内向外看,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开始,去展现历史的进程与发展。从那张镶有金边的暗褐色的椭圆形照片中,她看到了因为战争的摧残而满目疮痍的城镇。随着照片上的小女孩年龄的增长,埃尔诺记录着一次又一次的总统选举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变化,记录着屋子里家具的更新换代,人们谈论话题的改变以及从唱片机到电视再到电脑计算机等高科技如潮水般袭来的变化。但是,这些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时代永远比不上非法堕胎的经历让人惊心动魄,埃尔诺的民族志视角从外再次向内转动,她表达自己的痛苦、无能为力;她的羞耻,害怕衰老。当时间在她的身上流逝,她担心“自己会在需要把握大量现实的物品中迷失方向”[12]。因此,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描绘的历史事件或是拥有特殊意义的日子,是为了去重塑自己在无法挽回的时间中的自我存在,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就如同莱恩耐特(Lionnet)和戴克(Deck)评价非裔作家赫斯顿(Hurston)的回忆录那样,把传统的历史框架中那些对于作者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和事件都被最小化,而那些鲜活的人生经历、作者的人性观以及那些力图展现给局外人听的历史文化则得到了最大化的处理[13]。埃尔诺通过安装这些民族志的广角镜,用自己的女性视角观察和思考历史中的“精神创伤”事件,对于她来说,“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14]埃尔诺细数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从看似支离破碎的语句里找寻历史的真相,建构起一个完整的自我成长历程,敏锐地嗅出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意义和对个体无意识产生的影响。
自我民族志的书写是一种自我叙事,把自我放置在社会历史的背景中去思考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对社会的刻画更为深刻,她力求将社会结构层层剥开,对文化和社会等级进行质疑,去批评消费社会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表达对科技进步而产生伦理问题的担忧[15]。在这些集体的记忆中,埃尔诺不断地找寻自己的身份,虽然个体的回忆会被集体的记忆所融解,但是通过重新审视这些集体的记忆,再现往日场景,通过与当下的自己进行对比,就能够最终找寻到真实的自我。沉静的生活总是会被无法控制的集体时刻打破,然而这些历史早已变成了人们在家庭聚餐时的闲谈话题,他们有着因对战争时期饥饿的恐惧而塞满超市手推车的习惯,也有着对终于获得堕胎自由许可之后大胆恋爱的渴望。
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许代表了时代的发展,但没有改变的是每个个体都要经历的日常琐事——日复一日的上班,没有太多变化的家庭聚餐和最终可能会走向离婚的感情生活。人们的身份变成了一张张具有时代特色的印着照片的小卡片,上面的名字和出生地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于深受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影响的埃尔诺来说,唤醒被宏大的集体所淹没的个体是比做一个单纯的历史记录者更重要的事情。当埃尔诺经历着这个试管婴儿经常诞生的时代,她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人生是多么短暂,同时她也感受到了,在被无数新闻事件、政治现象裹挟之后应该要走向属于自己的历史时刻。
二、用群体的自我认知唤起读者共鸣
单纯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并不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然而安妮·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谈论自己作为一个法国女性的60多年的人生岁月却能引起法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共鸣,一是因为她巧妙地避开了第一人称叙事的禁锢,使用on(泛指大家)、nous(我们)、elle(她)进行无人称叙述(Impersonal narrative)。二是因为埃尔诺在搭建自己的民族志时,加入了大量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受和对政治变化进行批判的描写。德国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提出的“召唤结构”是自我民族志书写作为一种召唤叙事(Evocative narratives)的内在要求,这样一种“激发回忆的叙事”其目的就在于表达和讨论,而非概括和权威。正如人类学家亚瑟·博克纳(Arthur Bonack)所说:“在与读者的对话中,我们采用讲故事的手段来引导他们站在我们的角度换位思考,使读者积极投身于不同的社会和道德隐喻之间的对话中去。”[16]埃尔诺用“无人称”的叙事艺术建构起群体的自我认知,唤起他者的身份认同,并引发读者的共鸣。
《悠悠岁月》的创作手法透露着20世纪末法国“新小说”的影子:有勒克莱齐奥(Le Clézio)对底层人们的人性探索,莫迪亚诺(Modiano)的虚构与回忆,以及类似佩雷克(Perec)《我记得》(Jemesouviens)的列举书写。埃尔诺没有像传统的自传作品那样选择用第一人称,而是用无人称的叙事方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时代。《悠悠岁月》的译者吴岳添先生认为“这种写法能让读者自然地融入作者的回忆……使读者对作者所说的事情感同身受……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17]纵观埃尔诺的创作生涯,她从1974年开始出版的一系列作品中,就已经暗含了对第一人称的重新定义。比如在《外部日记》(Journaldudehors)中埃尔诺记录周围的小人物时把“我”当作一个记录客观事实的工具[18]。“我”已经不再是单纯作为一个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是超越个人体验地代表了一个被压迫的女性群体、一个感受到阶层屈辱的底层群体。因此到了《悠悠岁月》的创作,埃尔诺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社会性,使用“她”“我们”来叙述,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化作一张张照片或影像,穿插在历史的长河中,用自己个体回忆勾起和埃尔诺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代人的群体回忆,用“无人称”的方式建构起埃尔诺笔下的社群历史的民族志。她对政治事件和社会新闻进行敏锐地观察和犀利地评价,如先知一般预言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同时她也见证着历史的演变。
《悠悠岁月》被看作是一部社会性的自传。一直以来自传指的是“自我的生命书写”,而社会学则代表着冷酷而客观的经验事实,看似不相容的二者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渐渐融合起来,弗里德曼(Friedman)认为,自传的社会学最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是真正的把人当作人[19]。埃尔诺主观性地选择出现在文本中的社会事件和人生经历,其原因是这些事件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唤起人们的共鸣。比如埃尔诺描写自己童年时代的宗教生活时,首先关注报纸上刊登的封斋节菜单这样的公众经历;然后描述作为一个孩子在弥撒日的时候有机会换一套新衣服的群体经历;最后表达自己对这些回忆的感悟:“教会的戒律胜过其他一切法律。”[20]这些书写方式,无论是和作者同龄的、还是长于作者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勾起属于自己的回忆。
最后,埃尔诺对于政治事件的介入是身体力行的,她深受社会学的影响,也格外关注社会和政治事件,她清楚地感受到集体的改变会在个体上深深烙下痕迹,因此,埃尔诺在文本中多次提及法国的总统大选事件,表达着对恐怖袭击的忧虑、对柏林墙倒塌的评价,在面对法国失业现状时直言不讳。对于埃尔诺而言,抑或是对于整个生长在20世纪的人来说,当一个新的世纪来临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其实是“用数字2代替1这件怪事,往往使人在支票下面写日期时出现笔误”[21]。宏大的历史事件的确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但这样的一个个细节却往往更能够触动人心。“我们唯有把从众多生活世界中获得的经验汇集起来,个人经验的有限性才会显露出来,依赖和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也才会显露,对个人生平与广泛的社会进程之间的紧密联系才会有新的发现。”[22]安妮·埃尔诺把握着书写社会传记的核心,又从自我体验的角度展现作品的真实性,这些社会碎片编织成一张贯穿60年历史的网,而每一位读者恰好处在这张网的每一个角落。
三、通过谈论自己,道出他人真相
安妮·埃尔诺在进行自我的民族志探索的过程中,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社会学的样本”来看待,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作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符号去审视和研究,去寻找自我与外界的联结。埃尔诺也多次在访谈中提到促使她去写作《悠悠岁月》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抗男性,而是为了展示经过女性情感的过滤之后,女性是如何感知时间的流动的,如何观察社会日常生活,如何记录历史的。尤其是埃尔诺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以及书写自己的人生经历乃至私密之事,这并不是出于自恋,而是将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代表,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那样:“我在谈论自己的时候道出了他人的真相。”[23]
布尔迪厄的理论对埃尔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某些社会学议题在文学中的具象表达,她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在文学创作中。”[24]所以埃尔诺践行着布尔迪厄的观点,也证实了布尔迪厄所谓的“文学在许多问题上比社会科学更先进,它包含了涉及许多基本问题的、完整的收藏物,社会学家应该把这些收藏物运用到自己的学科中。”[25]《悠悠岁月》把一个女性的生活放置于更大的生存环境中,构建了一个集体的存在,表现生活在二战时期那一代人的生存写照[26]。埃尔诺在对自我进行民族志研究的同时,也关照了他人的生存真相,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埃尔诺是“那个世纪被遗忘者的代言人”。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选取的前四张照片讲述了她的童年经历,也讲述了和埃尔诺有着类似成长经历的所有人的童年。埃尔诺穿过这些褐色的旧照片,触摸着照片背后的咖啡渍,描述着20世纪50年代法国农村的现状。第五张照片到第七张照片反映了埃尔诺的青春时期,她和所有少女一样经历着青春期的羞耻和身体的改变,她感受到了对生活的厌倦和对爱情、自由的期待。埃尔诺之所以经历如此的痛苦,是因为她处在一个那样的历史时刻——可以自由服用避孕丸的时代一直到她在巴黎秘密堕胎之后才到来,女性可以不再因非法堕胎而死亡则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埃尔诺说“在个人的生活进程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27],但是历史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和埃尔诺一样经历过痛苦堕胎的女性,都会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历史的无情和现实的残酷。
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道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纠结与痛苦,她把自我寄托在还可以拥有自由的少女时期,她感受到作为一个女性被不公平对待,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中,最终她选择离婚让自己重获自由。最后的三张照片和一段录像带讲述了埃尔诺晚年的独身生活,她实现了自己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同时,她还“清醒地意识到她这个年龄的美丽是多么短暂,她害怕衰老,她将要失去月经的气味”[28]。她不再是一个少女,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痕迹,没有改变的是妇女们仍旧是一个被监视的集团。埃尔诺的老年生活代表了那些面对科技迅速发展而不知所措的老年人,她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是不落痕迹的,所以她要用文字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重新回顾自己的过往,找寻和拼凑出一种自我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在历史背景的支撑下,道出他人的真相并唤起他人的回忆。
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传统哲学所进行的自我审查并没有真正理解更深层的、无意识的社会结构性的自我层面,而后者恰恰塑造了个人的自我意识[29]。安妮·埃尔诺依托《悠悠岁月》对自己进行的民族志研究,是站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探索历史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并书写了一个“我们永远在讲述我们是如何经由抛弃过去而成为现在的自己”[30]的自传原型。她精辟地描述和评价着政治事件,用独特的女性体验和女性视角解构宏大的历史框架,窥见一个个细微的变化。她把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学样本,在历史的潮流中找寻自我,思考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使用了“无人称”自传的叙事模式,将社会学与传记进行连接,用自我的社会学传记模式,建构群体的自我认知,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这共鸣跨越了国家,超越了种族。安妮·埃尔诺践行了怀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谓的社会学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这一概念,可以说埃尔诺是一名成功的社会学作家,她跨越并缩小了人文学科之间的隔阂,实现了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融合,这是她进行民族志研究的重要贡献,也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