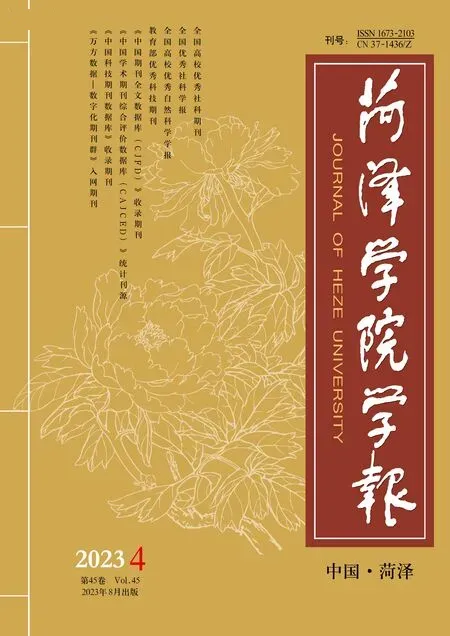地久天长的悲凉
——论《厚土》的生命意识书写
钟海林,魏紫梦
(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延安 761000)
吕梁山对李锐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它是李锐小说创作的灵感来源和书写对象。王尧认为吕梁山之于李锐,“譬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1]《厚土》正是在这片土地孕育而成的,它共收录了16篇短篇小说,每篇只有三、五千字,但短小精悍,耐人寻味。目前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对李锐的小说进行整体阐释,对其单本小说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作为李锐代表作的《厚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厚土》的评论研究多是围绕文化心理、民族劣根性等文化决定论的视角来透视,也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分析其创作机制、叙述视角,虽然有很多学者都注意到李锐小说中的生命困境书写,但论者更多集中在《无风之树》《万里无云》这两部长篇小说上。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文学作品中虽然也注意到农民,但大都是或讴歌或批判,很少从农民的立场出发描写他们的生存困境。“对人的处境、对苦难的深刻的表达,可以是一种深刻的文学命题。”[2]李锐正是践行了这样的文学观,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为基础,在《厚土》中书写了那个特殊时期吕梁山人们地久天长的悲凉之感。
一、吕梁山人民的煎熬
李锐在吕梁山做过六年的知青,在这里他看到世世代代在大山里耕种的农民对贫穷的恐惧,也深刻感受到当地农民的生存困境。李锐曾说:“如果做一个简单的表述,可以说我那些以吕梁山为苍凉背景的小说,表达了人对苦难的体验,表达了苦难对人性的千般煎熬。这煎熬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同时表达了自然和人之间相互的剥夺和赠予。当苦难把人逼近极端的角落时,生命的本相让人无言以对。”[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把生理需求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当无法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时,人的生存处境便会回归原始。吕梁山贫瘠荒凉,当地气候条件又干旱少雨,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当地人们生活得异常艰苦,始终挣扎在生死线上,生存成为横亘在他们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李锐在《厚土》中就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古老中国的生存状态图景,耕种农作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即使努力耕作,他们也难以逃脱这片土地带来的沉重枷锁。
《厚土》中肉体的煎熬主要体现在物质的极度匮乏上,小说书写了古老峪、青石涧等古老村庄,这些村庄构成了吕梁山最真实的生活面貌。《古老峪》通过工作队小李的视角,展示了当地的居住环境,“灶炕边那只小猪睡得太深沉,常常就舒服得哼出声来……土炕的那一端,污黑的被子里裹着的是一个一丝不挂的身子”[4],队长的家尚且是人畜合住,更何况是其他农民的家。《青石涧》中父亲卖掉棺材给儿子娶媳妇;《同行》中一个人走十五里的山路只是为了吃一顿饭;《天上有块云》中女孩的父亲为了吃掉黑眼窝而提前办喜事……这些细节无不透露着当地人们的贫穷,小说甚至将性与一定的物质利益关联。性本是男女情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理性行为,但《厚土》中,性变成了物质交换的筹码,沦为类似原始动物的本能释放。《锄禾》中红布衫为了得到队里的救济粮、救济款,光天化日就在野地里与队长苟合;《驮炭》中农妇为了得到男人的煤炭,与男人保持不正当的关系;《假婚》中女人家里遭了年景,为了活下去将身体作为交易……在这片土地上性关系混乱无序,极端的贫穷使人丧失了尊严和价值,人性变得扭曲不堪。
此外,肉体的煎熬也拷问着农民的精神世界,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合坟》中北京知青玉香为了抗洪保田,葬送了年轻的生命,十四年后老支书以为玉香配葬这种迷信的方式来减轻内心的煎熬。《秋语》中两个老农以闲聊的方式,道出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苦难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悟,这片黄土上的人世代都按同一种方式机械地生活,“活着,是自己种了玉菱吃玉菱;死了是看着别人种了玉菱吃玉菱”[5],除此之外生命别无意义。《看山》中牛倌因年老被队长告知不能继续放牛,“在身边的这一群当中,他已经享受惯了一种至高无上的尊严,他是它们的中心,它们是他的依靠。可是今天这自信中却夹进了一些惶恐:我真的就老得不中用了”[6],他的内心充满惶恐孤独,不知道除了放牛自己的人生还剩下什么。这种对于生命的无奈、绝望,是这片土地上人们难以逃脱的宿命,他们世代困囿于这方天地,苍茫的吕梁山就像一道厚实的屏障阻隔了与外界的沟通,都市的繁华难以企及这片被遗忘的角落。由于饱受肉体和精神的煎熬,吕梁山的农民在挣扎中逐渐变得麻木,接受了生命的苦难,活着成为他们的本能反应。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过“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7],这些农民世代都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约定俗成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扎根于泥土中,逃脱不了被土地束缚的命运,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煎熬中世代繁衍,冷静麻木地看着周围生命不断诞生、衰老、死亡,世世代代的生命在轮回中无限重复着相同的生命轨迹。
二、民间立场书写“历史”之外的人生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李锐始终是一位拒绝“合唱”,独立于文学潮流之外的作家,这与他经历文革的洗礼有关。作为生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原本接受的教育理论被完全打碎,“文革”带给李锐最大的影响是使他拒绝相信任何理论、任何人,因而他总是冷峻地透视世界。文学作家们多数追求史诗化写作,但李锐却不相信史诗,他在与王尧的对话中坚定地表明了自己对史诗的看法,“我拒绝诗意化地理解历史……落在史诗诗意化的泥潭里,人很容易陷入精神自欺,陷入对历史的美化。”[8]李锐拒绝成为美化历史的一员,以小说为媒介表示抗争,他在《万里无云》的序言中写道:“我对淹没了无数生命的‘历史’有着难以言说的厌恶和怀疑。我叙述是因为我怀疑。”[9]
李锐有意改变历史对人民的忽视,自创作开始就无限关注个体生命。在吕梁山黄土塬劳动的岁月,他看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的真实农民,然而,那些为农民谱写赞歌的人都拒绝在这片土地停留,他们排斥当自己笔下的伟大劳动人民。他们用笔制造出乡村乌托邦的谎言,对于这些劳动人民来说完全是无价值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播种的农作物是否丰收这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所有与生存无关的事都似风一样一闪而逝,丝毫影响不到他们的生活。农民苦难式的生活让李锐开始反思,力图通过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去还原农村最本真的生活状态,为那些被大写历史所忽视的农民呐喊,《厚土》最为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穿透‘历史’之虚假幻影,呈现‘历史’之外的永恒人生。”[10]
陈思和认为民间书写是“根据民间自在的生活方式的向度,即来自中国传统农村的村落文化的方式和来自现代经济社会的世俗文化的方式来观察生活、表达生活、描述生活的文学创作视界”[11]。李锐曾在吕梁山切实地生活过,在体验了身为农民的艰辛痛苦后,为了更好地书写,他选择从农民的立场透视世界,让农民成为小说主体进行自我言说。《厚土》致力于言说个人的历史,让边缘小人物登上历史的舞台,常让历史隐为小说的背景。身处吕梁山,李锐认识到,在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对于吕梁山的人们来说,“文人弄出来的‘文学’,与被文人弄出来的‘历史’‘永恒’‘真理’‘理想’等等名堂,都是一种大抵相同的东西,都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并无多少切肤的关系。”[12]在《锄禾》中,老汉大胆发表自己对政治的看法,而作为知青的学生娃却很慌乱,认为政治问题不能随意讨论。相似的场景也发生在队长与学生娃的交谈中,队长拿出皱巴巴的报纸让学生娃朗读,“前日邮差送来的新的叫屋里的给剪了鞋样子啦,女人家毬也不懂!”[13]学生娃对此很困惑,为何新报纸不是被剪了鞋样子就是糊了墙。老汉、队长在本质上代表的正是一种民间立场,而学生娃却是作为正统历史的代表,因此他无法理解这些农民的生存方式。
李锐认为单纯批判这些世代被绑在黄土上的人们是没有良心的,他切身体验过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耕种劳作,所以理解吕梁山人民这种近乎凝滞的麻木人生。《看山》中牛倌自女儿出嫁之后,日子就像凝冻了一样,没有一丝生气与活力,生活的全部就是放牛,间或是一个人每天呆呆地看着吕梁山。牛倌的日子如他所在的吕梁山一样沉寂,“山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沉默着,木然着,永远不会和昨天有什么不同,也永远不会和明天有什么不同。”[14]李锐笔下的山也是小说里的人物,山和别的人物一起组成了完整的故事。《好汉》中猎户在感受到死亡的危险后,体会到对于受苦的农民来说,“一辈子吃饱,喝好,有自己的房子,有老婆孩子,栽根立后,活够了岁数”[15]就是好日子。“乡土社会是个传统社会,传统就是经验的累积,能累积就是说是经得起自然选择的,各种“错误”——不合于生存条件的行为——被淘汰之后留下的那一套生活方式”[16],乡土社会的环境变动速度很慢,千百年来这片黄土上的人们都按照传统生命轨迹麻木地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身处这片“厚土”上的人们有太多无奈,他们就像是吕梁山一般,木然地承受着风沙的侵蚀,屈辱地忍受着身而为人的苦难。当被苦难逼到无路可走时,死亡就成为逃离苦难的唯一方式,因此这片干渴的土地也埋葬了很多人的生命。《二龙戏珠》中小五保只有三尺来高,这辈子他一直仰着脸看人,总是笑嘻嘻地讨好着和人说话,年轻时有玉茭面对于他来说是希望,一年又一年地将希望装进木桶,又一口一口把它吃光,那时候只要闻着玉茭面那诱人的幽香,心里也是暖的。然而“人之为人是一种悲剧,也是一种幸运。这悲剧或是幸运,乃处于一个同样的原因——就是一种不甘”[17]。正是因为身而为人的不甘,他渴望更好的明天,可现实却使他难以摆脱这种难耐的重复,他的每个汗毛都渗透进极度的疲劳,好似身上驮着一座大山,压得他难以喘息。他厌倦了这种乏味的重复,“活一辈子就活了一口窝窝米汤,再活十年八年也还是窝窝米汤。没意思……跟我一样是个累赘。”[18]为了摆脱永不改变的天地,他选择以死亡结束刻骨的疲劳。
同时,身为知青,李锐深刻地体会到“文革”带给他们这一代人的巨大伤痛,写作中不乏对这段历史的批判,但在批判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民间这样一个地方,却有着看似矛盾的人间温暖。《合坟》中学生们为抗击山洪,效仿电影手拉手跳下水,老支书苦苦哀求他们上来,在把别人都拉上岸的时候,玉青却被蛇缠住,永远地留在了自己守护的土地。因而她成为知青楷模,被广泛宣扬,可是颂扬过后就被“历史”永远地遗忘了,而被历史忽略的农民却展现出看似愚笨的温情,他们心怀怜悯地为玉青举办阴婚,这场合坟仪式透射出他们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文革”时下乡的知青都曾豪情壮志地将青春献给革命,渴望在农村尽情挥洒汗水以推动历史发展,但实则他们只是被“历史”遮蔽的普通人。李锐在《厚土》中通过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呈现出“历史”之外的人生,将这些被淹没的生命从历史的河流中打捞出来。
三、口语倾诉中国故事
李锐的创作坚持回归口语之海,一方面是为了让“历史”之外的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是他想反抗长期以来书面语对口语的重压,扭转书面语日渐等级化、权力化的趋势。其实口语化创作并非是李锐首创,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吕梁山,这使他潜移默化地受到“山药蛋派”的影响,“山药蛋派”一直将创作视线投向民间底层群众,灵活地运用民间语言书写,李锐的创作显然与“山药蛋派”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地域渊源。所不同的是,“山药蛋派”作家群使用方言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贴近农民,让知识水平有限的农民也能阅读他们的作品,达到教育农民的目的。而李锐是有着语言自觉的,他对言说方式进行创新,以自己创作的口语尽可能地书写底层农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并且他反对这种启蒙式的教育。李锐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启蒙文学,他认为这些启蒙者是叙述的他者,他们虽秉持人道主义,却始终自上而下地俯视着底层民众。因此,他有意规避启蒙文学的弊端,将自己放在民众的位置,选择“取消那个外在的叙述者,让叙述和叙述者成为一体……让那些千千万万永远被忽略、世世代代永远不说话的人站起来说话”[19]。
历史是由书面语叙述的,用相同的叙述语言是不能进入 “历史” 之外的人生,而《厚土》所展示的生命世界与历史无关,又常常是书面语所遮蔽之处,所以当李锐要敞开这样的生命时,他选择了让人物自己说话,并且是口语倾诉的方式。身于底层,农民远离阳春白雪般诗意的人生,他们的生活是泥泞的,也因此他们的言语中混杂着泥土。《厚土》中人物对话都非常口语化,从谈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吕梁山气息。《选贼》围绕村民的对话展开,他们由一开始选贼时的兴致勃勃转向惶恐,“他要真不干,今后晌当下就没有人喊工派活,弄不好真要把麦子耽误了”[20],最终贫困使他们不得不向队长低头。以队长为代表的强权在这片土地上有绝对的操控权,他们掌握着救济粮这样的命脉,作为挣扎在温饱边缘的村民们只能选择屈从于权力,懦弱麻木地忍受着社会带给他们的苦难。《厚土》中也有大量人物内心独白,且都是以口语的形式诉说。《看山》中以老人的内心独白,道出身而为人的悲凉,放牛老人把全部的热情都献给了这片黄土地,但终究难逃命运的安排,发出“东西再大,本事再大也有个不毬行的时候”[21]的慨叹。对于吕梁山的人民来说,身体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一旦衰老,生命就会大打折扣,生存也变得岌岌可危,这种无尽的悲凉能将人逼向死亡。同时,小说中农民们经常使用“毬、鬼说吧、日你妈”这样不堪入耳的口头禅,虽然粗鄙却是农民的日常表达,他们深受贫困生活的迫害,这种谩骂是他们宣泄情绪的有效途径,更是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厚土》大量书写吕梁山人民的对话、内心独白,让我们得以倾听被“历史”遗忘的底层话语,深刻感受他们艰苦难耐的生存现状。
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在中国兴起,很快演变成文学创作的潮流。当大家都追随主潮蜂拥而上时,李锐却看到先锋文学的语言弊端,他曾谈到如今的书面语已经成为等级化的语言,欧化的极端书面语被认为是先锋的,而中国本土的方言写作却被视为末流。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殖民”①的语言倾向,因此,他冷静地提出文学创作应坚守语言的自觉性、主体性。新文化运动为启蒙底层人民群众,以胡适为代表的先驱者大力提倡白话文,作为启发民智的工具,白话文以贴近人民生活的优势发挥了极大的启蒙作用,但李锐却不赞同将语言视作工具,“语言是和我们的四肢、五官、心脏、大脑一起组成‘人’的重要的一部分”[22],他认为应“把自己的语言上升成为主体,上升成为与人并重的‘本体’”[23]。书面语相较口语,就如贝壳相对于大海,口语才是书面语的生命之根,李锐所说的“书面语是指被书面化、体制化、正统化、等级化的叙述方式”[24],“写在书面上的就是书面语”[25]是一种错误的认知,《论语》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作为文言文却采取口语叙述的方式,可见并非写在书面上的就是书面语。白话文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中成为正统化的叙述,最终也难逃僵化的命运,在经历一系列改造后,成为扼杀创新的话语锁链,以它为主体书写的正统历史也遮蔽了世代操持方言的底层农民,使他们被遗忘在无人问津的角落。
在世界文学日益朝着等级化趋势发展时,李锐却始终坚守自己的叙述,通过底层的口语和方言,书写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生命体验,以期打破文学的枷锁。吕梁山六年的劳动生涯,使他对农民怀有无限悲悯,因此他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书写本土中国,《厚土》的语言充满泥土气息,正是这种带着土气的口语倾诉让我们体悟到人生的悲凉。李锐在之后《无风之树》《万里无云》的创作中对小说叙述进行更深入地探索,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叙事,彻底进入口语倾诉的世界。他曾明确说过“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只能写中国人……我只能在对于中国人的处境的深沉的体察中去体察地球村中被叫作人的这种物种的处境”[26]。文学的深刻命题常常是对人苦难的深刻表达,立足吕梁山,关注人类肉体、精神的困境,他书写了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以“京白”为主要叙述语言,在文言文为正统的时代,《红楼梦》无疑被当时官方排斥,甚至将其列为禁书,但是就是这部被视为下里巴人的作品,却在一群阳春白雪中脱颖而出,在民间如野草般横生发展,甚至在今天,它仍然在文学长河中熠熠生辉。20世纪以来,《红楼梦》更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蕴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关注,并产生一门以它为研究对象的“红学”,甚至在国外也有庞大的读者群。《红楼梦》作为一部享誉世界的著作,让我们明白越是中国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坚持本土文化,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超越的,我们要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心,充分挖掘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一味去追求成为“中国的卡夫卡”,这样的副本作品最终只能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当然在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同时,我们也要适当学习国外先进的文化,让中国书写更具世界性。正如李锐所说,“当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和缺陷的同时,或许也为我们留下一种可能。我们应当在这个可能之中播下方块字的种子,以中国人的生命之血滋养出一片参天的森林来。如果不能,就让我们以自己的血肉和文字朽腐成自己的土地,以期来者的播种”[27]。
李锐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他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以平等的视角展现农民的生存困境,真实书写了“历史”之外的人生。其实,无论是“山药蛋派”还是新时期崛起的“晋军”,他们的作品中都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厚重质朴的文学品格。李锐作为“晋军”的中坚力量,在创作上也承续发展了这一地域性文学传统。
山西文坛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沿着“山药蛋派”的原道路进行创作,注重揭示农村生活的种种矛盾与痛苦,这样的创作严重限制了他们的视野。李锐在意识到这种创作弊端时,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创作,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他打破了“山药蛋派”对跌宕起伏情节的追求,通过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某个片段或场景来实现小说意义的绽放,以空间结构消解时间意义,书写了农民生活的凝滞性。
书写吕梁山时,李锐继承了山西作家群的地域书写,始终坚守对人的关注,又拒绝盲从潮流,坚持独立自主的文学创作,更不忘理性思考如何更好地书写“本土中国”。相较于同时期的“晋军”作家,李锐对语言自觉的关注更是独树一帜,他将小说创作纳入到建立当代汉语写作的主体性之中,反思批判等级化的书面语,明确提出回归口语之海,以口语、方言为武器去冲破书面语的束缚,并进一步强调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树立文化自信心,以语言自觉来建立汉语的主体性。作为“晋军”的代表人物,他在创作中坚守民族化的语言叙述,让我们看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也为“晋军”的后续创作提供了努力的方向。但不可否认的是,李锐对于语言的过分焦虑,使他在人物刻画方面有所缺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话语都大同小异,没有形成个性鲜明的人物谱系,与他所要达成的浑然天成的叙述目标还有所差距。
注释:
①李锐所说的自我殖民是指,面对强势语言而自动取消自己的语言,一味以仿照别人为光荣的心态和一味出卖传统文化的行为。 参见王尧《李锐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