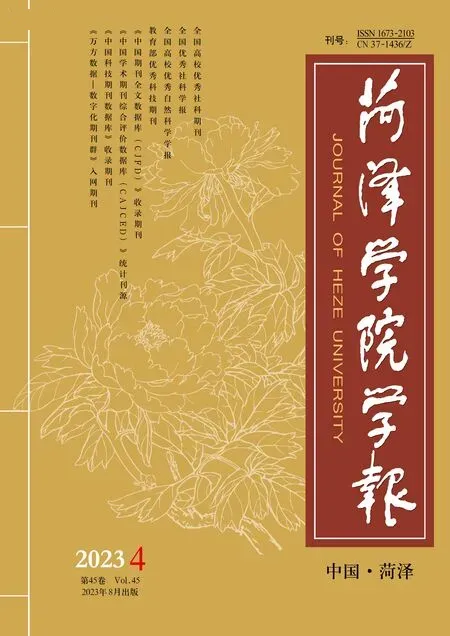九一八事变后旧体诗“写作热”与民族精神的阐扬
张 宁
(湖南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近年来,学界对现代旧体诗的发展演进做了许多探讨。比如有的学者从旧体诗38年(1912-1949)发展的整体着眼,分析说:“旧体诗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一个驼峰状的曲线,即由初期的高峰跌入低谷,然后在三十年代初复苏,在抗战至解放战争阶段更得到复兴,进入其高峰期。”[1]也有些学者专门聚焦抗战时期的旧体诗创作,如刘梦芙指出:“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这十几年间激励全国抗战的爱国诗词创作持续达到高峰,杨圻、刘永济、唐玉虬、夏承焘、王蘧常、钱仲联、沈祖棻等是杰出的作手;马一浮、陈寅恪、胡先骕、方东美、吴宓、沈轶刘、詹安泰、潘伯鹰、丁宁、陈小翠、潘受等许许多多诗人词家的集子中都有呼唤抗倭、记述流亡悲苦的力作。”[2]这些讨论对于深入理解和反思旧体诗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也不可否认,类似的讨论虽从宏观上描述了旧体诗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轮廓和创作态势,但却未能从细部辨析特定时间节点(或特定事件影响下)旧体诗创作的变化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旧体诗“写作热”的现象就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阐释,鉴于此,笔者专门针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深入考察和论述。
一、新文学视域中旧体诗创作的冷热现象
文学革命后,旧体诗受到新文学家的批判以及新诗的冲击,创作和传播面临着不利的境遇。如钟敬文面对外界压力就不得不对旧体诗“敬而远之”。他在《〈天风海涛室诗词钞〉跋语》中颇为无奈地说:“我幼年即学作旧诗。稍后因新文化运动兴起,此事被认为迷恋骸骨,遂弃去改作新诗。”[3]新文学的浩大声势也使得登载旧体诗的报刊杂志逐渐“萎缩”。有研究者指出:“旧体诗词在1917年之后出版的期刊里,处于逐渐式微的趋势,有时沦为补白地位(如在1923年1月创刊于上海的《小说世界》中的地位),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栏目在现代文学的期刊里几乎没有。有些刊物开始的时候还以旧体诗词为主,但渐渐就改换成以新文学为主了。”[4]在图书出版领域,新诗得到了市场的认可,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从1920年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出版开始,此后数年间新诗的出版数量逐年上升,增幅非常明显,“热度”远远超过了旧体诗。写新诗、读新诗、评新诗、议新诗成为一种“时尚”。
在文学批评领域,20世纪20年代有关新旧诗之争的讨论从没停止过。旧体诗的支持者不断强调旧体诗存在的合理性,如蒋鉴璋所撰《今日中国的文坛——几年来目睹的怪现象》《诗的问题——答丁润石先生》主张理性地对待旧体诗,新诗写作需要融新旧于一炉。但这类合理的意见都被“忽视”或否定了,新文学家似乎并不在意与旧体诗相关的“真相”,所以宁可夸大二者之间的矛盾,也不承认二者的共存、共生。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旧体诗的创作“遇冷了”。吴宓悲观地感叹,“十余年来,所谓爱国革新之文化运动,已使文言书少人读,旧体诗几于无人作。而最近之注音字母及简字,复以政权及公令助之推行,由如是因,结如是果。可云,今日(或最近之将来)汉文正遭破毁,旧诗已经灭绝”[5],“是故旧诗之不作,文言之堕废,尤其汉文文字系统之全部毁灭,乃吾侪所认为国家民族全体永久最不幸之事!亦宓个人情志中最悲伤最痛苦之事”[6]。
旧体诗被“嫌弃”折射了当时轻视乃至厌恶本国文化的价值取向,这种激进的文化态度不单单在汰洗旧的不合理的文学观念、文化秩序、伦理纲常,也在消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合理性因素。在吴宓看来,这无异于是在制造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他直言不讳地说:“吾中国国家社会之危乱,文化精神之消亡,至今而极。”[7]那么,如何消除“危机”呢?吴宓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今日国人之言爱国、言救亡,言民族之复兴、文化之保存者,何不于此(保存汉文汉字,发挥利用旧诗)加之意哉?”[8]他认为应该属意汉文、汉字以及旧体诗,更好地发挥其在爱国、救亡方面的功效。旧体诗在文化精神的传承与激励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九一八事变与旧体诗“写作热”背后的文化心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许多有识之士深感民族灾难正在迫近。黄侃得知“事变”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突闻十八夕十九晨辽东倭警,眦裂血沸,悲愤难宣。”[9]夏承焘在日记里自省说:“念国事日亟(日兵已陷吉林),犹敝心力于故纸,将贻陆沉之悔。”[10]在次年的周年纪念中,傅斯年对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做了深刻揭示:
“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也正是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其他两件自然一个是世界大战,一个是俄国革命。我们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观情感,我们这一年的经历,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11]
“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国难”“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二十世纪世界史上三件最大事件之一”等描述隐约以这场事变为界,划分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他认为此时代有别于过往的时代,今日国民之责任及精神状态亦当有别于彼时,在此时代中国人“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这实际上触及到了以何种精神面貌面对民族灾难的时代命题。
面对国人精神上的怠惰、萎靡和隳颓,一些诗词作家、学者用诗词表达愤懑,抒发情志。如夏承焘在日记里中写道:“中敏示满江红一词,感东省事作。中敏以士气颓堕为虑。”[12]任半塘(字中敏)试图用诗词唤醒“士气颓堕”的国人。黄侃则因东三省事心情悲怆,写下《八月十五夜月食》:“江国冥冥水接天,关山处处起烽烟。秋光纵好知何益,明月多情不忍圆。”[13]他一想到中国大地上燃起的烽烟,就心情焦灼,压根顾不上这美好的“秋光”“明月”。汪东表示文学家尤其是诗词作家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诗词创作应朝着提振人心的方向努力,其云:“注重慷慨悲壮,甚至粗厉猛奋的声调,予以刺激,使人心渐渐振作起来,这才见文学的功用,也才是文学家或者说词家所应当分担的责任。”[14]
在“特殊时代场域——提振民族精神——诗词家肩负责任”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旧体诗被重新选择,并委以重任。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化人大都出生于清末民初,受过旧式教育,旧体诗对其而言是一种“文化积习”,可以信手拈来。更为重要的是,旧体诗悠久的创作传统、丰厚的文化积淀以及感时书愤、陈古刺今、抒怀明志的文体功能与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所激发的集中、强烈且要在短时间内喷薄而出的创作诉求颇为“契合”。正如刘纳在《旧形式的诱惑——郭沫若抗战时期的旧体诗》一文中所云:“在旧体诗定型化的表达方式和它所对应的情感现象之间,早就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15]九一八事变后,文坛上出现的旧体诗“写作热”本质上反映了民族危亡之际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体认,折射出中华民族文化的自省和精神的觉醒。故吴宓指出:“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16]
三、九一八事变后旧体诗创作的精神维度
此前的旧体诗创作因循守旧,多陈腐之气,且往往拘囿于一己之哀乐,书斋气浓,书卷气重,为新文学家所诟病。与之相比,九一八事变后的旧体诗创作撇开个人得失,关注的焦点转向国土沦丧的现实危机及民族存亡的前途命运,将现实主义精神推向新境界。
首先,这一时期的旧体诗作品直面东三省的沦陷,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带有强烈的戏谑性、讽刺性和批判性。如马君武所作七绝《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17]作者用调侃的口吻抨击以风流著称的张学良沉溺醇酒美人,把保家卫国的男儿之志和军人之责抛到九霄云外,全然不顾东三省百姓的死活。“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等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个好色荒淫、顽劣无度的少帅形象。当然,有学者考证诗中提到的北洋名媛朱湄筠、电影明星胡蝶实际上与张学良并无关系。如詹焜耀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将军奉命不抵抗,以致国土沦丧、舆论哗然,咸谓张将军醇酒妇人,铸此大错。近累阅报纸,谓六国饭店舞会事,根本没有,张将军亦抱病在身,甚至有谓胡蝶当时亦不在北京。一时烛影摇红,成一疑案矣。”[18]《哀沈阳》二首或存在“虚构”之处,但作品本身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真实,人们很容易从这个沉醉于醇酒妇人的“张学良”想到中国历史上贪图女色、昏庸无道的亡国之君,进而联系到当时国民党上层的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腐败生活,这样的批判犀利深刻,极具锋芒。
钦人所撰《疯汉歌》怒斥当朝权贵尸位素餐、麻木不仁:“塞外男儿杀敌强,可怜执政心於石。满朝文武数万千,年来声势何煊赫?日旗今已蔽辽东,扶危束手竟无策!乞援强邻唤奈何,阋墙犹自分南北!君不见,达官显宦多于虾,声色权势竞相夸。亿兆黄金藏异域,十万青蚨买女娃。民穷财困非所惜,苛捐重税日月加。吮我脂膏尽涓滴,供彼淫佚若泥沙。又不见,将军遍地狠如狼,百万雄师莫可当。关外江山亡半壁,孰敢捐躯死战场?只知袖手观成败,未闻挥刃捣扶桑。”[19]“满朝文武”“达官显宦”平日里声威煊赫、骄奢淫逸,只知对内攫取民脂民膏,面对强敌,却畏首畏尾,束手无策。作品揭露了他们丑陋、无耻、虚伪、冷酷的嘴脸,尺度之大令人咋舌。姚伯麟的《辽警有感》则谓:“东海波涛已汹涌,西京弦管尚幽清。庙谋结尾存观望,国难临头计息争。独使万民持镇静,诸君何以退夷兵?”[20]诗人对国民党上层的软弱妥协、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其次,旧体诗不遗余力地歌颂抗日英雄,塑造视死如归的将士形象,呼唤拯溺扶危的侠义精神。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仁人志士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占山。有学者指出:“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首揭抗日义旗,他领导的江桥抗战成为中国局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象征之一,因此被全国各界视为民族英雄。”[21]如星槎《慰马占山将军》云:“守土无人事可惊,伊谁慷概请长缨?辽疆已尽逃诸将,嫩水居然起义兵!大节危亡劳尔系,孤军奋斗为民争。江南一片秦淮月,照到沙场寄我情。”[22]高度颂扬马占山首先起来反抗侵略的“义举”,其孤军奋战、刚毅顽强的精神气概与东三省诸将溃逃的灰颓、软弱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房仙洲《咏马占山》谓:“将军自不愧干城,羽骑频飞破虏营。鼠辈瓦全曾惜死,英雄玉碎敢图生?决心誓欲收疆土,豪气真堪慑贼兵。无耻伧奴甘卖国,事仇腆面作公卿。”[23]他认为马占山不仅有“干城之才”,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气概,堪为军人楷模。石颜也的《黑马歌》在歌颂马占山英雄事迹的同时,也借之抒发抗日决心,突出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其云:“君不闻,胡骑遍野声啾啾,入室登堂莫大患。厉我兵兮饱可餐,秣我马兮整我鞍。抖擞精神再杀贼,当惟马首之是瞻。”[24]这里就强调“我辈”当厉兵秣马、抖擞精神,效仿马将军投身战场。
此外,奋勇抵抗的民众也得到了旧体诗人的关注。如钱仲联《哀锦州》就颂扬辽西地区民众组织的抗日义勇军,称:“黄昏胡笳城上吹,贼不血刃皆登陴。截城阑杀者为谁,辽西义民边城儿。奋臂直入不畏死,矢与名城共终始。”[25]相比于东北军的“不抵抗”,那些生长于斯的“辽西义民边城儿”则直面强敌,不避死亡,誓与锦州城共存亡。这样的描写催人泪下,震撼人心,道出了中国民众的心声和意志。
再次,旧体诗以其强烈的抒情性特质,着力表现民族危亡之际个体的抗争,凸显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如希鲁《日本入寇东三省感赋》谓:“忍耻包羞三十年,岂知苦痛甚于前?伤心关北更何有?饮血辽东尽可怜!尝胆惟期歼丑虏,枕戈莫怕抗强权。同胞今日应同起,仔细艰难任仔肩!”[26]他认为救亡图存正在此时,同胞们应该头脑清醒,勠力同心。李贯慈《哭辽东》云:“复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27]认为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华好男儿应奋起杀敌,以热血报国。钱来苏《九一八国难后有所见闻,愤而赋此》则称:“莫负昂藏七尺躯,忍看华胄籍为奴。丈夫生死寻常事,留好头颅待价沽。”[28]七尺男儿岂能甘心做亡国奴,为了民族大义,即便抛去头颅也在所不惜。崔明英《书愤四绝》其四云:“国难已如星火急,奈何议论尚盈廷?男儿爱国争先死,留取丹心照汗青。”[29]国家危亡迫在眉睫,热血男儿重义轻利,慷慨赴死。如果说上述作品是站在“男性”立场审视反抗侵略的话,那么何香凝《致黄埔学生将领》则书写了女性的心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30]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中国的广大女性没有置身事外,她们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只愿收复故土山河。这样的抗争凸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骨和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旧体诗抒发了创作者的爱国情、报国志,反映了中国民众普遍的心声,传递了砥砺精神、催人奋进的用意,使读者获得了鼓舞与启迪。这也打破了文学革命后旧体诗在公共文学空间的“沉默”状态。人们不再纠缠于新旧文学间激烈的对抗,斤斤计较作品的文体形式,而是将目光投向旧体诗所蕴含的民族情感、文化信念和精神力量。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旧体诗“写作热”既是这种文体向文坛中心的靠拢和回归,也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传统文化价值的确认和民族精神的复归,深刻影响着全面抗战时期旧体诗创作情感表达的基本取向和精神维度。
在新文化运动之际遭受诟病的旧体诗,成了民族危难时达成情感共鸣、重塑民族认同感、承续文化精神的重要手段。归根到底,旧体诗不单单是一种文体,它也是承载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的载体。九一八事变使人们预感和洞察到战争的阴霾开始笼罩这个时代,笼罩这个国家,旧体诗“写作热”既是浸染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的应变之举,也是鸦片战争后爱国诗潮的崭新演绎,其以沉痛的自身和强烈的反思开启了抗战时代旧体诗创作的序幕和抗战文学的新篇章。尤其是旧体诗所展示的文化认同和精神姿态,构成了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永远昭示后世,激励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