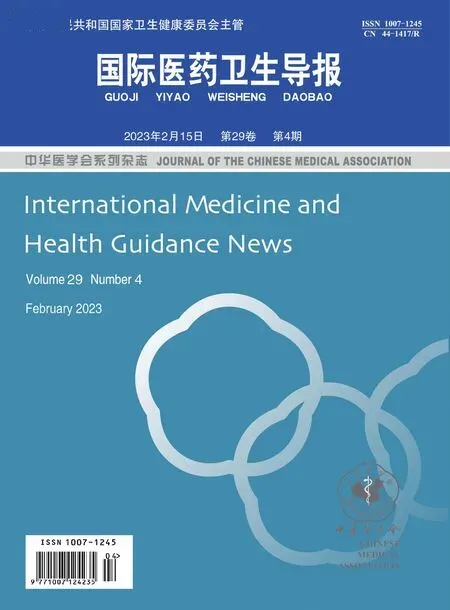连带病耻感对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照顾负担影响
张珺 周静
1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病案室,南阳 473000;2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南阳 473000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起病隐匿的持续性神经功能障碍,也是失智症最普遍的成因[1],主要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认知功能损害综合征(包括记忆障碍、注意力障碍、学习障碍等)。目前临床尚未有完全治愈或者改变AD病程的治疗途径。随着疾病进展,患者逐渐不能适应社会,完全需要依赖他人照顾以满足最基本的日常生活需求。因此,以家庭为中心的照顾已成为延缓AD患者病情和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最主要途径[2]。调查显示,我国目前有863万AD患者,89.6%~93.2%患者居住在家中,其家庭照护任务主要由其配偶或子女承担[3]。连带病耻感又称附属病耻感,指照顾者因与患者存在某种联系而受到他人偏见与歧视[4]。作为患者最重要的居家照护主力和情感支持来源,家庭主要照顾者与患者感情最亲密,相处时间最久,由于部分照顾者对AD的错误认识和负面态度,对患者病情过度忧虑,易出现烦躁、恐惧等情绪,加之长期照护的压力和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也会使他们身心俱疲、经济负担加重、生活品质下降;因此,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精神状况、躯体功能、家庭关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连带病耻感。照顾负担指家庭照顾者照顾患者时所产生的心理、生理及社交等方面的问题。研究表明,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明显高于其他老年疾病照顾者,且逐渐加重的照顾负担对AD患者所有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均存在不良影响[5]。在连带病耻感的影响下,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往往会因自身羞愧内化而较少或拒绝寻求社会支持[6],但较好的社会支持对改善高应激状态下的个体保护能力及降低其照顾负担有关键作用。目前,国内对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照顾负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慢性病领域[7],较少有关于AD家庭主要照顾者的报道。本研究旨在弥补此空白,探讨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照顾负担、社会支持现状,分析连带病耻感对照顾负担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有效降低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及照顾负担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1.一般资料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收治于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南阳市中心医院的AD患者172例为研究对象进行横断面调查。患者纳入标准:⑴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分类第3版(CCMD-3)的相关诊断标准[8]且经临床影像学检查确诊;⑵年龄≥60岁,对家属有一定的辨识度;⑶已婚,家庭结构完整;⑷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⑴离异、丧偶或独居;⑵AD终末期;⑶合并其他严重心、肺、肾功能异常或伴有恶性肿瘤者。照顾者纳入标准:⑴年龄≥18周岁;⑵与患者共同居住,为患者配偶或子女,承担主要照顾责任;⑶直接照顾时间≥6个月,每周照顾时间不低于5 d;⑷能正常沟通和交流,积极配合本次研究。排除标准:⑴近6个月内遭遇其他应激事件者;⑵长期与患者分离;⑶伴严重躯体疾病者;⑷精神异常或既往有精神病史;⑸领取报酬。
本研究均已经通过2所医院医学伦理会批准(yzyfy210112、nyzxyy210367)。
2.调查工具
2.1.一般资料调查表 经查阅文献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职业、与患者关系、文化程度等。
2.2.贬 低 -歧 视 感 知 量 表(Perceived Devaluation-Discrimination,PDD) 该量表是Link等编制的连带病耻感系列量表的一部分,主要用于评估照顾者被贬低歧视的感受[9]。该量表包括感知歧视、感知贬低2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其中第1、2、3、4、8、10条目为反向计分。总分12~60分,分值越高,表明个体连带病耻感越强。≥25分为存在连带病耻感。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是0.863,中文版内容效度为0.981,Cronbach’s α系数为0.792。
2.3.Zarit照顾负担量表(Zairt Care giver Burden Interview,ZBI) 由Zairt等设计,主要用于评测AD患者照顾者负担程度[10]。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共22个条目。各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不”至“总是”分别计为0~4分。总分0~88分,得分越低,说明照顾负担越轻,≥60分为重度负担,≥40~60分为中度负担,≥20~40分为轻度负担,20分以下为没有负担。
2.4.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 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共10个条目[11]。总分为12~66分,≤22分为低水平,>22~<45分为中水平,≥45分为高水平。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社会支持状态越高。该量表重测信度是0.910,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5~0.938,信效度较好。
3.调查方法与质量控制
征得患者及其照顾者同意后,由研究者对照顾者在总示教室开展一对一方式的调查。研究者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解释问卷的相关调查内容、填写方法等,指导照顾者现场填写,完成时间控制在30 min内。填写结束后,研究者当场回收并检查有无错填。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89份,回收有效问卷172份,有效率为91.01%。
4.统计学方法
运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库,通过SPSS 20.0、AMOS 20.0统计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频数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与照顾负担之间的相关性。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建立路径关系模型,对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照顾负担之间的关系进行路径分析,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模型拟合。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172例AD患者的一般资料
患者年龄(68.34±10.40)岁,男84例(48.84%),女88例(51.16%);合并慢性疾病129例(73.3%);自理程度:部分自理148例(86.05%),全部自理24例(13.95%);病程<1年36例(20.93%),1~5年60例(29.07%),≥5年76例(44.19%);医疗费用承担方式:城镇居民医保67例(38.95%),新农村合作医疗105例(61.05%);患者每月护理花费:≤2 000元31例(18.02%),2 000~≤4 000元97例(56.40%),>4 000元44例(25.58%)。
2.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人口学资料及照顾负担得分情况
172例照顾者中,男性68例(39.53%),女性104例(60.47%);与患者的关系:配偶89例(51.74%)、子女83例(48.26%)。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总分为(52.04±8.68)分,其中个人负担维度得分为(37.52±6.36)分,责任负担维度得分为(14.52±2.32)分。根据评价标准,158例(91.86%)照顾者有照顾负担,轻度21例(13.29%),中度75例(47.47%),重度62例(39.2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医疗费压力承受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的主要因素(均P<0.05),具体见表1。
3.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总分为(49.15±7.90)分。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文化程度、每日照顾时间的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照顾者社会支持总分为(35.97±7.89)分,显著低于我国常模的(42.19±8.64)分[9](t=5.258,P<0.001)。见表1、表2。

表1 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照顾负担的单因素分析
表2 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分,±s)

表2 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分,±s)
4.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与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经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照顾者的照顾负担与连带病耻感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r=0.718、0.678、0.675,均P<0.001));照顾者的照顾负担与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均呈负 相 关(r=-0.720、-0.550、-0.687、-0.312,均P<0.001)。见表3。

表3 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与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5.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将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总分作为因变量,以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2个变量(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照顾负担均以原数值录入,结果显示,连带病耻感、社会支持均进入回归方程(均P<0.001),可解释总变异的51.2%,见表4。

表4 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6.以社会支持为影响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中介变量的效应分析
采用最大似然法设置原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结果表明此模型可接受,具体拟合指标结果见表5。社会支持中介作用拟合模型见图1。经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连带病耻感对照顾者负担具有明显的正向预测效应(B=1.586,P<0.001);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对其社会支持也具有明显地预测效应(B=-1.497,P<0.001)。采用Bootstrap抽样法对其中介作用进行分析,设置抽样频率为6 000次,结果显示,当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影响照顾负担时,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显著,其95%置信区间不包括0(95%CI0.451~1.059),这说明连带病耻感能充分借助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明显影响照顾负担,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3%,见表6。

图1 社会支持中介作用模型

表5 社会支持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标结果

表6 以社会支持为影响172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中介变量的效应分析
讨 论
1.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处于中等以上水平,且不同特征的照顾者照顾负担不同
本研究中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照顾负担总分为(52.04±8.68)分,且高达91.86%的照顾者有照顾负担,表明AD患者照顾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照顾负担,与王日香和董婷婷[12]研究结果一致。原因可能为由于病程的进展,AD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及认知能力持续降低,甚至伴有激越行为,其生理及心理方面都极为依赖照顾者,看护负担逐渐加重。而配偶、子女作为家庭照顾者的主力军,打破了以往的家庭构成[13],在长期的照顾工作中,不仅要赡养父母、处理琐碎家务、抚育子女,还要外出赚钱养家等,生活重心完全转移至照顾患者身上,几乎无暇顾及个人的家庭生活与社交娱乐,躯体、心理及社会层面均承受各种高强度压力,身心负担过重,家庭人际关系不良,继而导致照顾者身体负担加重,生活质量下降,照顾负担较重。此外,部分照顾者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知,自我应对能力差,也是照顾负担加重的重要原因[1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医疗费用压力承受情况、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影响照顾者照顾负担的主要因素(均P<0.05)。与≤60岁的人群相比,60岁以上的照顾者生理功能及躯体健康不容乐观,也需要他人照顾;在本该颐养天年、享受生活的时候,却被迫成为照顾者,心理难免出现巨大落差[15],加之受到生理条件的制约,其照护过程常感到力不从心,照顾负担增加。马秀程等[16]研究发现AD及其他痴呆症患者的家庭经济收入、医疗费用压力承受度是照护负担的潜在影响因素,与本研究结果重叠。即家庭经济收入较低、医疗费用压力承受较差的照顾者,其照顾负担相对较重。这可能与照顾者照护患者过程中,工作量减少甚至失去工作,家庭经济收入锐减,同时患者医疗支出随病情进展增加,疾病经济负担日益加重,家庭经济救助途径单一,照顾成本显著增加,经济上的负累严重影响照顾者的负担感受有关。因此,建议医护人员及时为照顾者提供多元化的支援式服务,如定时对照顾者进行心理支持[17],定期以电话或上门随访的方式指导照顾者掌握多元化照顾技巧,为照顾者进行经济募捐等,从而有效减轻照顾者的压力和负担,促进其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提升其生活质量。
2、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存在较高水平的连带病耻感,连带病耻感可显著正向预测照顾负担
本研究中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得分为(49.15±7.90)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AD患者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水平较高,与袁汝娟和孙欣[18]研究结果一致。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来源较多,包括内因和外因。从内因角度讲,照顾者的连带内在病耻感包括情感(羞愧、悲伤)、认知(歪曲对疾病的正确认识)及行为反应(社交退缩)3个方面。首先,AD患者受疾病的折磨,需要长期服用抗精神药物治疗,由于治疗的不良反应及公众对精神药物治疗的偏见,患者治疗后常自觉被贴上“神经病标记”[19],受到歧视,于是便抗拒治疗,产生强烈的病耻感。同时,患者也会因疾病而悲观失望、丧失自尊,社会适应能力严重降低;作为与其亲密接触的照顾者,陪同见证、经历这一过程,难免会情感悲伤,产生“连带内在病耻感”;而照顾者的耻辱感受和主观羞愧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和对待患者的态度,进而加重患者的病耻感。其次,部分照顾者对AD的认知水平较低,误认为痴呆就是精神障碍,阻碍了AD患者的早期诊断及有效治疗;加之其获取疾病信息、医疗服务等途径受限[20],无法获取足够的相关支持,因此照顾者往往难以正确了解病耻感及其危害性,认同外界的刻板印象,对自我产生负性认知,连带内在病耻感较重。第三,随着疾病的进展,患者痴呆症状加重,甚至出现各种精神行为症状,这又显著加重了照顾者负担,增加消极照顾体验和情绪;照顾者常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力和社会价值低于他人,潜意识里会隐瞒患者病情甚至疏远患者,并减少自身社交活动以避免遭受歧视,继而导致照顾者连带内在病耻感水平持续增高。在外因方面:第一,受传统“面子文化”的影响,AD患者开展社交活动时,社会公众对其多存在孤立、回避等行为,由于与患者存在亲属关系,其照顾者也随之可能被社会排斥、歧视,这也进一步加重了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程度;这不仅严重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21],也直接增加了照顾者的照顾负担和抑郁风险。第二,由于疾病的进展,AD患者会出现常人难以理解的激越行为及言语,往往给外界一种配偶未尽扶持义务或子女不孝的错觉,使照顾者常面临外界的误解与指责,因此极易产生连带病耻感。第三,家庭其他部分亲属未认识AD的严重性,认为患者是“扫把星”,缺乏对主要照顾者的支持,拒绝与患者过多接触,使主要照顾者社交孤立,孤独感明显,连带病耻感水平提高。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每日照顾时间是影响主要照顾者连带病耻感的主要因素(均P<0.05)。相对文化水平低的照顾者,文化程度较高者能理性认知和对待AD患者的症状,心理素质较好,更能客观地回应社会外界的舆论,同时善于利用自身资源积极获取公众各方面帮助[22],继而有效降低连带病耻感。与每日照顾时间较短者比较,照顾时间较长的照顾者所花时间和精力均在患者身上,完全忽略自身需求,对患者各种激越行为症状的体验更深刻,耐心不断被消磨,消极情绪滋长,极易采用负性应对方式处理各种问题[23],从而加重身心负担,连带病耻感水平相对较高。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照顾者负担与连带病耻感及其各维度均呈正相关(均P<0.001);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连带病耻感能解释照顾者负担总变异的51.2%;这说明连带病耻感与主要照顾者照顾负担水平密切相关,即连带病耻感水平越低,照顾负担越轻,病耻感加重了患者的疾病负担,连带病耻感加重照顾者的负担水平。AD患者由于缺乏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常被污名化,生活质量较低甚至面临死亡威胁,这对于与其关系亲密的照顾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应激和照顾压力,照顾者心理负担加重[24],被迫共同承受疾病被歧视和耻辱。此外,患者病耻感也会在多种环境下不同程度地影响照顾者;顾者在照顾病情反复发作甚至有挑战性行为的患者过程中也会产生焦虑、疲乏、躯体疼痛等问题,生理、精神负担加重[25],照顾能力降低,从而影响对患者的照顾质量,增加照顾管理难度,产生阻滞患者康复的恶性循环。因此,医护人员应重点评估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水平及照顾负担情况,通过开展社区小讲课、病友互助讨论病耻感经历、分享经验、团体自我肯定训练、培养自我同情心等活动对照顾者进行社会心理病耻感保护干预,帮助照顾者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26],指导其掌握更好的自我保护技巧,同时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建设“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家照护”,为照顾者适时提供喘息式短期照护、上门访视和日间照护等多元化服务项目,从而降低连带病耻感的危害,及时化解照顾者的照顾困难和负担。
3.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社会支持在连带病耻感和照顾负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本研究结果显示,照顾者社会支持总分为(35.97±7.89)分,显著低于我国常模(P<0.001),整体处于中低水平,且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对社会支持有明显预测效应(P<0.001),社会支持在连带病耻感与照顾者负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3%。这表明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社会支持已成为影响照顾者照顾负担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连带病耻感已成为精神疾病患者亲属产生照顾负担的最主要原因[27],与本研究结果相似。社会支持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应激性事件及压力时,能充分评估、利用自身资源,克制自身情绪压力,并积极寻求各方帮助以有效解决相关难题,从而抵御压力事件对自我的冲击与伤害,降低照顾负担。在连带病耻感的影响下,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在照顾过程中所承受的生理、心理、家庭、社会等压力远高于常人,但碍于自尊与脸面,羞于寻求社会支持,习惯自我忍受不良情绪与压力,致使其内心难以接受患者,更倾向消极方式去处理各种照顾问题与人际关系,忽视与患者的亲密互动[28],主动减少自身社交活动并拒绝他人的帮助,甚至放弃国家提供的优惠福利待遇。照顾者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少,就越难以感受到自己付出的被理解、肯定与赞赏,照护患者时就越难保持自信且可控的行为倾向[29],应对连带病耻感的能力较差,生活幸福感较低,照顾质量无法保证,照顾负担水平较高。因此,医护人员可通过开设服务热线、教育课程等途径对主要照顾者进行系统专业化培训,传授照护知识和康复训练技能[30],提高照顾者应变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同时增强社区服务机构、自助团体、“互助式”社会群体等社会群体组织的社会支持力度,协助照顾者申请办理及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指导其共同寻求和利用各方面的支持与资助,继而帮助照顾者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支持,减少消极情绪和不良体验,减轻其连带病耻感及照顾负担。
AD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连带病耻感能直接预测社会支持、照顾负担,并通过社会支持对照顾负担发挥间接预测效应。医护人员应重视照顾者连带病耻感对照顾负担的影响路径,积极构建以路径影响因素为核心的干预方案,强化对照顾者的经济帮助、情感支持及社会支持利用度,减轻照顾者连带病耻感,提高照顾者的心理弹性,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照顾者的照顾负担,促进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