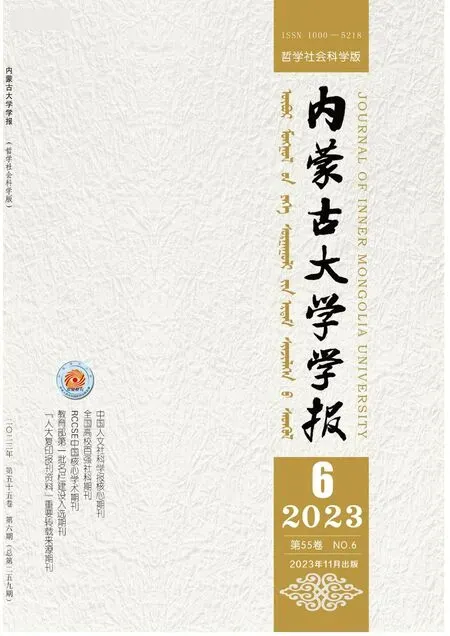内蒙古移民村朝阳沟村的语言问题及相关思考
夏 历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东北地区兼具地域特色和人口构成特色,多民族聚居特点突出。 少数民族自周朝开始在东北地区聚居,清朝时期汉族人口大量涌入,遍布东北地区,[1](136)逐渐形成了东北村落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生活的面貌,移民村也成为东北地区村落的常见形态。 东北移民村落虽历史长短不一,村民融合程度深浅不同,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现实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下辖的朝阳沟村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东北移民村。 朝阳沟村始建于1973 年,位于乌鲁布铁镇北部,距镇区20 千米,面积160 平方千米,现有常住居民237户585 人,耕地面积6.3 万亩,种植业以大豆、小麦为主,养殖业以牛、羊为主。 2021 年随着鄂伦春自治旗被列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而成为县域帮扶村。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 年)》中明确提出,“开展语言国情调查。 调查特定地区的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是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一项重点工作。[2]朝阳沟村作为东北移民村,语言问题较为突出,阻碍了该村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 对该村语言问题进行调查、探究,并提出解决策略,不仅能有效解决上述发展问题,而且能够为解决东北乃至全国移民村的语言、经济、文化、教育发展问题提供经验和有益启迪;在丰富我国乡村语言生活研究的同时,还能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保驾护航。
笔者于2022 年7 月20 日至7 月27 日,以返乡学者的身份入驻该村,采用参与观察、融入式交谈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该村的语言生活面貌进行了深入调查。 本次入驻调查共走访住户28 家,其中,对有特色的山东点①住户作了穷尽性调查,先后交谈59 人,正式访谈31 人,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81 岁,拍摄村落照片300 余张,形成29 份记录该村语言文化生活的调查日志。
一、朝阳沟村的移民分布概貌
朝阳沟村所在的乌鲁布铁镇是鄂伦春自治旗四个猎区乡镇之一,有汉、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回、满、朝鲜族9 个民族。 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山东移民和东北其他区域的移民不断迁移和流动到朝阳沟村,逐渐形成了朝阳沟村以汉族为主,兼有少数民族的乡村人口结构。②
(一)村落的“点式”构成
朝阳沟村面积160 平方千米,属于占地面积较大的乡村。 整个村落包含14 个点,划分为5 个村民小组。 第一村民小组包括山洞点、马权点、李大权点、老猎民点,第二村民小组包括山东点、火车站点,第三村民小组为龙江点,第四村民小组为吉林点,第五村民小组包括东杨家点、西杨家点、八路点、郝家点、田家沟点、陈凤林点。
朝阳沟村的14 个点分别按照村民的来源地、最早驻扎的村民特征和聚居地的特点等命名。 其中,山东点、吉林点、龙江点是按照村民的来源地命名,马权点、李大权点、东杨家点、西杨家点、郝家点、陈凤林点、田家沟点、八路点是按照最早驻扎的村民姓氏命名或是出身命名,而老猎民点是按照最早居住的鄂伦春、鄂温克等少数民族以狩猎为生的生活特点命名,山洞点是因为聚居点内有个山洞,火车站点是因为该聚居点内有个火车站。
现在村里有些点的名称已经成为一种沿袭下来的称说,点名和村民来源地、姓氏等之间不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如八路点的八路已经故去多年,杨家点已经不再以杨姓村民为主体。
(二)村民的“杂居”状态
朝阳沟村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居住的村落,汉族村民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至此,形成了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的村民共处一村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状态。 村里的少数民族有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而迁移到朝阳沟村的汉族村民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和山东。 朝阳沟村的东北地区村民多来自黑龙江的龙江、海伦,内蒙古的赤峰、扎兰屯,吉林的农安、洮南,辽宁的建平、朝阳等地;朝阳沟村的山东村民主要来自山东潍坊的诸城、安丘等地。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属于“土著”居民,这些少数民族在朝阳沟建村之前一直在这片土地上居住,而汉族村民属于外来人口。 来自山东的移民,一部分是为了讨生活,一部分是为了多生孩子。 20 世纪中叶,由于山东人口基数大,土地难以负载人口增量,很多山东人“闯关东”讨生活。 山东人自古受孔孟礼教熏陶,更加重视子嗣的繁衍,对家中男孩的重视程度尤甚,朝阳沟村地处偏远,属于管理链条上的“神经末梢”,使这里成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盲点,一些山东人便流动到朝阳沟村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生孩子。移民到该村的东北村民很多是盲目流动,即当时俗称的“盲流”。 这些人在哪儿能生存下去,就停下脚步在哪儿扎根。
从村民目前在村里的实际居住情况看,五个村民小组中的第三村民小组龙江点、第四村民小组吉林点及第二村民小组火车站点,基本上处于连续成片居住在一起的状态,在这些地点居住的主要是东北移民过来的村民。 第二村民小组山东点居住在山坡位置,也被称为“后山”,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聚居状态。 第一村民小组和第五村民小组居住的地点较远。 第一村民小组虽然和前面几个小组都在公路的一侧,但也相距数公里,其中,少数民族聚居的老猎民点就在这一组;第五村民小组则在公路的另一侧,居住地距离村落的中心位置更远。
二、朝阳沟村的语言生活及存在的问题
作为移民村,朝阳沟村的语言生活呈多语种性和多方言性,不同语言和方言之间存在相对独立性。 这既体现出了朝阳沟村村民语码使用的丰富性,同时也凸显出一些语言问题。
朝阳沟村全体村民在语言使用上向汉语“单向”聚拢,而少数民族语言则处于“独立”使用状态,山东移民使用的方言也形成了“孤岛”现象。这些现象使得村民之间存在“族缘”“地缘”等多层面的交流障碍,语言认同问题突出。 同时,朝阳沟村村民缺乏主观认知层面的语言意识,村里的客观语言文化生活环境非常单调。
(一)语言使用上多语“分离”与方言“孤岛”现象并存
1. 少数民族语言的多语“分离”状态
朝阳沟村村民使用汉语、蒙古语、鄂温克语、达斡尔语等多种语言,语码类型丰富,但是从目前村民的语言使用情况看,并没有呈现出多语共荣的局面。 村民普遍使用汉语,各少数民族分别在自己的聚居点和家庭内部使用本民族语言,形成了语言使用上向汉语“单向聚拢”、各少数民族分别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多语“分离”状态。
朝阳沟村建村初期,人口结构以少数民族为主,汉族人口较少,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也不多,少数民族说本民族语言,汉族说汉语。 随着大量山东和东北地区的人口涌入朝阳沟村,加之1996 年开始,为了保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国家全面实施禁猎后,少数民族村民放下猎枪,很多猎户迁出朝阳沟村,与其他地方的猎户合成大的聚居区,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逐渐下降,朝阳沟村村民开始以说汉语(方言)为主。
目前,汉语是当地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少数民族村民会说不同程度的汉语;而村里的汉族基本上都不会说少数民族语言,没有村民主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同时,少数民族之间的语言也不互通,各说各自的语言。
2. 山东移民的方言“孤岛”现象
朝阳沟村汉族村民使用的都是北方方言,主要是东北官话和胶辽官话两个次方言。 朝阳沟村的东北村民很多来自黑龙江、内蒙古和辽宁等省、自治区。 其中,大部分村民的方言属于东北官话黑松片的嫩克小片,发音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古影、疑两母开口一二等字今声母读音不定。 其中有些字读[n]声母,有些字读零声母,读音因人、因地而异,没有一定规律。[3](35-36)调查结果也显示,朝阳沟村的东北村民在说“饿、鹅”等词语时,有时带有[n]声母,有时也不带。
朝阳沟村的山东村民来自潍坊的诸城、安丘等地,这些村民的方言属于胶辽官话青莱片的胶莲小片,方言上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一部分日母字读作零声母字,如“人、让、日”等读“银、样、义”;元音鼻化现象明显,如“咸”;鼻化声母如“爱、袄、安”带有鼻化声母[ῃ],等。[3](53)这些特点在村民的话语中都有所体现,还有把“媳妇”[ɕi42fu]说成“媳子”[ɕi42dzə]等。
朝阳沟村的东北官话和山东官话属于并行使用的状态,虽然东北方言在当地属于强势方言,但却存在村里聚居的山东村民其山东方言保持较好的情况。 “后山”村民的方言一直保持着山东方言的基本面貌,并没有随着居住时间的推移而有明显的改变,即使村里的其他村民不能完全听懂山东方言,但他们也始终坚持使用,形成“村中村”的居住方式和方言使用上的“孤岛”状态。 见访谈记录1:
笔者:后山点他们说话你们听得懂吗?
被访谈者A:他们叽了哇啦叽了哇啦,说得快。 跟咱们说得不一样,咋滴都差事儿,都过来多少年了,有过来快五十年的了,还是白扯,他不变。
笔者:他们口音不变吗?
被访谈者A:不变。 后面那个,从建点多少年了……(被访谈者B 插说)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不懂,也不和他们打交道什么的。
笔者:你们不怎么打交道?
被访谈者B:不打交道,听不懂。
被访谈者A:关里人过日子比咱们细细,会过,不咋买东西,不像咱东北人,好③吃好④喝,不咋攒钱。
[访谈记录1:被访谈者A(丈夫,61 岁),
B(妻子,60 岁),2022-07-24]
可以看出,朝阳沟村作为一个移民村,村民之间存在“族缘”和“地缘”等不同层面的交流困境。少数民族村民与汉族村民、山东移民与东北移民之间,虽然能进行一些基本交流,但老一辈村民之间不互相学习和不认同彼此的语言(方言),都想保留“自己的语言(方言)”,存在不同程度的交流不畅问题,无法真正融为一个共同体。
从20 世纪70 年代朝阳沟村建村以来,少数民族一直处于独立居住状态。 虽有个别少数民族村民和汉族通婚的情况,但整体上少数民族村民与汉族村民之间的交往很少,并未实现同一村落内各民族的顺畅交流。 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缺乏深入了解,这种交流障碍导致的疏离感,使得各民族之间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落融合。
第二村民小组中的后山村民也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聚居状态,与山下各点的村民虽有交流,但互动不频繁,对其他点的村民也不够了解。 后山山东点村民和山下东北移民村民之间的疏离感主要体现在说不同的方言上。 同在一个村落里,汉族村民在方言差异上形成两个群体,这也成为移民村的一个融合困境。
(二)村民缺少必要的语言认知
朝阳沟村村民的整体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明确的语言认知。 村里五六十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上过学的较少,中青年村民也以初中文化程度较为常见。 村民对文化、历史、社会等方面的认知有限,对语言的感知也较少,对自身语言(方言)及外语的价值等都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首先,村民缺乏语言传承意识。 这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村民对待下一代转用汉语和山东移民村民对待子女转用东北方言的态度上。 以山东移民的情况而言,当问及对于下一代普遍使用东北方言的看法时,父辈都认为孩子在村里出生,使用东北方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想过要求子女会说山东方言。 见访谈记录2:
笔者:张叔叔,你们家说话挺有意思,感觉是关里和关外两个地方的?
被访谈者C:(笑笑)孩子们都在这边出生的,都说这边话。
笔者:你们不要求他们说山东话吗?
被访谈者C:不要求。 孩子们在这边出生,从小就说这边的话。
笔者:那你们父母说话你们能听懂吗?
被访谈者D:能听懂,从小听,习惯了。
笔者:你们有时也说山东话吗?
被访谈者D:不说,就说现在的话。
[访谈记录2:被访谈者C(74 岁)和D(42 岁)是父子,2022-07-23]
其次,村民语言学习意识薄弱。 一方面表现在汉族村民对少数民族村民语言及持东北方言的村民对其他村民方言的忽视上。 当持东北方言的村民被问及是否学习一些当地少数民族语言或是当地村民的山东方言时,许多村民表示没必要,甚至觉得诧异。 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对外语的认知和学习上,村民几乎没有自主的想法。 当被问及对学习外语(英语)的看法时,鲜有村民对此作出回应,显示出未曾关注这项语言学习;被问及对孩子学习外语的态度时,也仅认为这是好事情,未作其他评价。 见访谈记录3 和4:
被访谈者E:达斡尔族不说咱们的话。
笔者:你说的达斡尔族,他们不会说汉语吗?
被访谈者E:年纪大的能听懂,说不好,说的是那个味儿,小的基本上都会说。
笔者:小一些的达斡尔族还会说达斡尔语吗?
被访谈者E:小的不怎么说达斡尔语了,都说汉语。
笔者:你们没学点他们的话吗?
被访谈者E:我们学啥,有啥好学的。
笔者:那山东话呢? 这边山东人不少,你们没学点他们的话吗?
被访谈者E:不学。
[访谈记录3:被访谈者E(男性,61 岁),2022-07-24]
笔者:你们接触过英语吗?被访谈者F:(笑笑)没有。
被访谈者G:没有。
笔者:孩子们学过英语吗?被访谈者F:学过。
被访谈者G:也没咋学。
笔者:你们希望孙子辈学好英语吗?
被访谈者F:学学挺好。
[访谈记录4:被访谈者F(54 岁)和G(60 岁)均为女性,2022-07-26]
最后,村民未能充分认识自身的语言(方言)优势或是本民族语言的价值。 对朝阳沟村的汉族村民而言,整体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得进城务工的村民在某些服务行业具有语言优势,能够胜任工作。 但是,朝阳沟村村民未能借助已有的语言优势而在语言层面更多获益。 村民主要是在周边的加格达奇、齐齐哈尔、哈尔滨或是父辈的山东老家务工,务工的基础仍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主,未能突破这些限制而在更大范围或更高层面发挥语言优势。 而对于朝阳沟村的少数民族村民而言,本民族语言具有的文化价值、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未能被充分意识到,年长的少数民族村民对下一代转用汉语采取无所谓的态度;很多年轻人也没有传承民族语言的意识,多主动放弃本民族语言,选择转用汉语。 见访谈记录5:
笔者:你会说妈妈的话吗?
被访谈者H:(摇头)……
笔者:你妈妈说得怎么样?
村委会主任:他妈妈不会说话,是个哑巴。
笔者:你姥姥会说吗?
被访谈者H:姥姥会说。
笔者:你们能听懂吗?
被访谈者H:听不太懂。
村委会主任:现在年轻人会说的很少了。
[访谈记录5:被访谈者H(女性,达斡尔族,13岁),村委会主任(男性,43 岁),2022-07-23]
(三)村里共有语言文化氛围接近“荒漠化”状态
朝阳沟村无论是记载村落历史还是当地名人轶事的文本资料,抑或休闲娱乐内容等方面都很匮乏。 在朝阳沟村,没有村落里常见的记载村子历史的村志或是文本材料,也没有村集体或是村民个人撰写的人物传记,没有记载当地故事、风土人情的民间书籍。 村民除了对孩子接受教育普遍认同外,对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缺乏认同,甚至对个别村民从事务农之外的休闲生活表示反感。 笔者了解到,村里有一个村民对木工活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平时也愿意写点东西,而在其他村民眼里,这位村民种地能力不行,整天做些不务正业的事情。 见访谈记录6:
笔者:我前两天去杨叔叔家,他给我展示了很多他做的木工活儿,还送我个鲁班锁。
被访谈者I:哪个啊?
村书记:就是火车站点那个老杨家。
被访谈者I:啊,那个爱鼓捣木匠活儿的。
村书记:(笑)对,自称“鲁班传人”。
被访谈者I:一天就爱瞎鼓捣,还爱拽点词儿。
笔者:杨叔叔喜欢和我唠,还给我写了首诗。
被访谈者I:就他没啥正事,干啥不行,种地种得不咋地。
[访谈记录6:被访谈者I(男性,74 岁),村书记(男性,33 岁),2022-07-25]
现长期居住在村里的村民以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为主,这些村民的主要生活内容是务农,闲暇时间靠看电视、聊天打发;留在村里照顾小孩的大部分是年轻一代女性,她们的业余生活内容也主要是看电视、聊天、打麻将。 而且,从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来看,没有专门的场所供村民使用,只有村里党员服务中心的活动室提供了有限的娱乐设施,包括一张台球桌和一张乒乓球桌。 除此之外,村里没有可供阅读或是借阅书籍的图书室(图书角),没有可供共同观影的放映厅,亦没有其他可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
村里语言文化生活单调而贫乏的状态,还可以通过语言景观得到更加充分的认识。 朝阳沟村的官方语言景观主要集中在四个地方。 一处在村口,有一个“朝阳沟村”村名和简介的标识牌、一个疫情防控行程卡扫码牌和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彩旗;一处是朝阳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围绕这个中心有一些宣传大政方针的宣传牌,如“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一处是集超市和快递于一体的服务中心,此处有邮政的一些标识牌和宣传邮政快递业务的条幅,如“2022 年中国邮政全面助力乡村振兴”;还有一处是朝阳沟村火车站,此处主要有标有车站名的站牌和提示村民禁止进入站内、注意火车通过的安全警示牌。 除此之外,还有个别村民房屋外墙壁贴的“房屋危险,请勿靠近,违者后果自负”的官方警示语牌。
朝阳沟村的非官方语言景观包括公共区域共享的和村民家里的两种情况。 公共区域的非官方语言景观非常少,只有一两处电线杆和厕所门上写着一些服务项目和留下的电话号码,还有一处立着的牌子上写着“小卖店”和一处农家门口挂着“便民超市”字样的牌子。 而村民家里的语言景观,基本上都是“招财进宝”“求钱财、求富贵、求福气、保平安”“家和万事兴”之类的内容。
从村里的语言景观可以看出,户外的语言景观以宣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为主,见不到关注村民语言文化生活方面的语言景观;家庭语言景观也主要与求财、求和睦有关,缺乏其他内容;一些语言景观体现了内蒙古自治区的语言特色,同时使用汉字和蒙古文两种形式,英文等其他文字比较少见。
三、繁荣移民村语言生活,促进乡村振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扎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4]。
朝阳沟村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域下属的帮扶村,经济发展落后,产业形式单一,村民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种植国家扶植的大豆作物,村里虽有一些经济作物(如紫苏),但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创收效果,养殖业也只是少数村民的收入来源;村里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态环境,根据前文对村里文字资料、语言景观和村民的文化生活内容等的分析可见一斑。 此外,村里除了每年高考录取一两个大学生之外,人才方面的情况也乏善可陈。
朝阳沟村作为建村历史较短的东北移民村的缩影,具有这些移民村共有的一些特点。 如村民的来源具有多元性,如何更好地融为一个共同体,是从建村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由于建村时间不长,村里缺乏共建的文化氛围,村落文化底蕴接近“荒漠化”。 这种不相融局面和村落共有文化稀薄状态,阻碍了村民共同富裕和村落全面发展的步伐,也无法使居住在其中的村民把根扎下。 一些少数民族村民不断移出村落,一些山东移民也陆续迁回山东老家,使得朝阳沟村除了面临村落普遍存在的年轻人外流局面外,还面临着少数民族和山东移民村民外流的双重困境。
乡村语言生活是乡村文化生活和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生活中的问题既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同时,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又会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加快乡村振兴的进程。 因而,移民村的语言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可以通过增进语言认同,为村民之间的融合搭建心理平台;并可以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帮扶规划,帮助移民村加强共有文化的建设,推进村落的深度融合。
(一)增进语言认同,推进移民村的深度融合
“语言认同是指个人或群体通过自身的语言活动来现实性地体现自己的语言或方言的交际价值,或者指交际(个人或群体)双方在语言行为上的相互兼用、相互融合及语言态度上的相互认可。”[5]朝阳沟村作为移民村,生活在其中的汉族村民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知之甚少,村里的山东移民形成方言“孤岛”现象,村民之间的融合问题在语言认同上得到了凸显。 因而,解决朝阳沟村的语言认同问题,对于实现村落的全面振兴意义深远。 村民之间的语言认同问题需要得到重视,消除交流上的心理壁垒,才能使村落真正成为一个村民共同体,才能使村民携手将朝阳沟村打造成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首先是干部的主观意识问题。 村干部要重视村里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并积极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 通过村民之间的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提升村民对村集体的认同感,[6](4)整个村落才能拧成一股绳,实现发展的齐头并进;改变目前山东村民谋脱离(返回山东)、各少数民族村民偏安一隅、不同类型村民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而言,村干部可以带头学习少数民族语言,并提倡村民之间互学语言或方言,让生活在村落的少数民族和山东移民能够感受到村集体的重视,改变边缘化状态;可以通过村干部的积极协调,定期举办各种村民活动,搭建交流平台,以娱乐休闲的方式增加村民之间的交流频率;可以增设村民活动室以提供固定的村民交流场所,打破现在少数民族和山东移民只在自己的聚居点活动的“村中村”状态。
其次是客观发展契机的推动。 村干部的主动协调,不一定能充分获得村民的响应,有时在客观发展需要的推动下,可以更为自然地实现村民融合。 东北移民村可以充分利用国家大力支持东北开展粮豆种植的契机,以农业种植带动村民之间的互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融为一体。《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力扩种大豆油料。 深入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支持东北、黄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 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4]。 东北移民村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同时,必然会在种植过程中促进村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村委会要充分利用这一发展契机,在带领村民谋发展的同时,增进彼此的语言认同,拉近心理距离,促进村民之间的融合,真正实现“村落是大家,村民是一家”。
(二)服务“一村一品”,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帮扶规划
“一村一品”是贫困地区开展扶贫开发、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发展“一村一品”是推动乡村产业集聚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举措。[7]在这个过程中,语言生活层面需要制定相宜的语言帮扶规划,[8](85)推动国家经济战略部署成功落地。
首先,乡村语言帮扶规划要服务于每一个村落的具体情况,符合村民的认知水平,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朝阳沟村村民的语言认知匮乏和村落共有语言文化氛围缺位问题突出,因而,针对这种情况的语言帮扶规划,需要提升村民的语言认知,如必要语言文化知识的吸取,民族语言、方言的传承和保护,以及外语教育等问题。 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村委会发放指导性书籍、微信等社交平台推送相关文章,向村民普及语言文化知识;也可以利用语言学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的假期社会实践,进村开展必要的语言教育,帮助村民充分认识自身语言(方言)优势和语言资源价值,提升语言技术的实际运用能力,将村民推向更广阔的发展平台。[9]
其次,需要完善移民村的语言文化环境建设。村里的文献资料匮乏,目前村落的建村史和发展史及各种传说、故事,都是老人们口口相传,亟须整理成文本形式,否则随着年长者的逐渐逝去,这些内容也会随之消失或是变得模糊不清、支离破碎。 因而,语言学专家和大学生志愿者假期社会实践时,在开展语言意识普及工作的同时,可以帮助村落建立村志、编撰村史,整理歌谣、传说、故事、谚语、农耕习俗等文化资料,记录村落故事;同时,针对共有语言文化环境单调、语种单一的情况,可以帮助村落增设多元化、多语种的语言景观。
最后,乡村语言帮扶规划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村民实现语言能力的增值效应。 关于村民语言能力的价值,姚欣、杜敏指出,乡村振兴中村民的语言能力既能够使村民成为适应农村新业态、新技术的新村民,同时又能帮助村民满足自己多方面语言的需求,提升他们在新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10]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不同村落村民的语言能力基础不同,同一村落不同村民的语言能力也有差异,因而,村民语言能力的建设,一方面可以具体提升村民的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村民实现现有语言能力的效能扩大化。
朝阳沟村汉族村民的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较好,大部分村民都能交流自如,还带有东北地区特有的幽默、诙谐表达等;少数民族村民则具备一定的多语能力,能够同时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汉语。针对汉族村民,应该使其充分发挥语言优势,帮助其突破务工所囿于的地域、血缘和现实语境限制,到对语言可懂度和语言交流能力需求更强烈的地区就业;或是借助网络平台,利用语言表达优势,将移民村的农业模式、农产品、文化生活等推向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实现“互联网+语言优势”的东北农村语言经济发展模式。 对少数民族村民,应使其充分认识本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社会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等。[11]民族语言作为特色文化供给,经济现代化发展程度越高,民族语言越显得稀缺,其相对价值的提高能够给少数民族带来直接的收入,如少数民族的音乐、戏曲、服装及手工艺品等。[12]少数民族珍惜和保护本民族语言,就是在保护一种文化;学习和掌握本民族语言,就是掌握了一些经济资源,可以利用本民族语言优势,在民间文化展示和劳务输出等方面发挥作用。
总之,乡村振兴战略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乡村语言生活管理是乡村振兴赋予语言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帮扶规划,实现语言赋能乡村振兴,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 目前,既需要大量农村语言生活样本的支撑,也需要对每一个乡村语言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探讨,才能充分发挥语言在文化建设中的优势作用,对乡村的文化和生态振兴产生直接效应,从而进一步产生连锁效应,拉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注释:
①朝阳沟村作为一个移民村,内部分为很多“点”。 所谓的“xx 点”,指同一来源地或是其他缘由形成的村民聚居点(区)等,具体详见下文朝阳沟村组成情况部分的介绍。山东点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个“村中村”式的点。
②户籍人口汉族1024 人,少数民族365 人;常住汉族486 人,少数民族68 人。
③④这里的“好”发音为去声,喜欢、爱好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