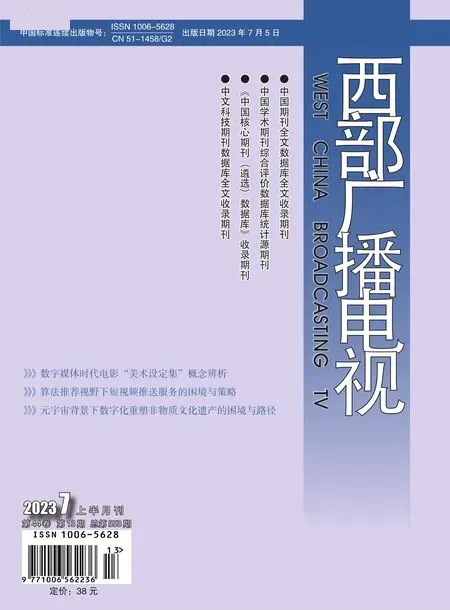期待视域下综艺节目《大侦探》的创新分析
尹春月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0世纪60年代,文学审美研究开始脱离作者这一中心,逐渐向文本、读者及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过渡,接受美学理论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产生。21世纪后,接受美学引入影视艺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成为研究受众审美心理的理论依据。姚斯对于接受美学的观点是,作品的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要在受众的观看中实现,而实现过程即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1]22。受众在对作品进行观看的过程中是主动的,这是促使作品创新的动力,影视作品也是如此。期待视野包括知识期待、消费期待、社交期待、情感期待、认同期待、娱乐期待和文化期待。姚斯认为期待视野作为一种“前理解”和“前结构”,在受众的观看过程中发挥着支配、制约的作用,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受众对文本信息的判断和评价。因此,作品可以“唤起受众在其他本文中熟悉的期待视野和游戏规则”,《大侦探》作为综N代电视节目不断在发展中进行创新,从一开始的断案推理性真人秀逐渐定位到普法教育推理节目,作为IP节目在创新过程中以受众的审美期待为抓手,从文本内容、空间建构、节目形态到节目立意都进行了全面升级。
1 文本期待:互动仪式链的内容设计
1.1 结合现实的故事改编
不同类型的影视作品有着不同的结构形式、话语表达、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呈现出不同体裁的类型特征。随着网络的迭代发展,受众拥有较高的文学作品欣赏能力和对社会事件的分析能力。受众对于《大侦探》这类断案推理类节目的审美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侦探类影片、文学作品以及已熟知的热点事件的影响。受众基于长期的信息接收和审美体验,形成了对某节目类型的审美心理图式,且作为认知结构的一部分融入其期待视野中,所以当欣赏不同主题节目时,便事先基于某一类型的结构图式来进行衡量、理解、要求和评价,以满足心理期待。
《大侦探(第八季)》每一期的故事内容都以受众的社交期待、情感期待和文化期待为抓手进行创作,从而满足受众的需求,节目每一期的主题往往立意于真实案件、社会普遍问题、少数的认识畸形等问题,目前已经播出的五期节目分别将整期节目的主题立足于科学就医、原生家庭、社会偏见、舆论操控、校园霸凌、职业尊重、生命敬畏、真相与正义的权衡等不同的方面。结合时事主题故事的带入满足了受众的预先期待,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会对信息进行抓取,对于并不明显的主题嵌入,受众也会因为满足了期待视野,从而借用“弹幕”的形式进行科普。在此过程中,不仅能够满足这类受众的社交期待,还可以通过直白的交流满足被科普受众的文化期待,同时,观看节目的受众会在跟随嘉宾推理的过程中完成寓言性故事的复现,整个节目真正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1.2 心理图式的建构满足
学者金元浦认为期待视野这一前理解不仅指向文本,而且指向文本创造。杨守森先生针对期待视野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读者在文学接受活动中,“在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结构图式”[2],这种结构图式就是期待视野。《大侦探》八季以来,文本建构上有着明显的框架形式,其独特的节目形式、风格和结构,对于垂直的黏性受众来说是规律性的审美建构。《大侦探》从节目播出之初就为受众构建了一个明侦男团的集体形象,节目演变过程中产生不同的集体记忆,组成了受众对于节目的完整定义。同时《大侦探》从第一季开始就利用后期剪辑给予受众流畅的观看体验,后期特效的变化创作更是受众娱乐期待中不能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节目组将花字的升级创作作为满足受众审美期待的重要一环。比如在节目中,后期会制作出与本期节目嘉宾形象相似的卡通形象,在遇到现场未完全演绎的情节时,卡通形象的特效就起到了伴随性文本的解释作用。《大侦探(第八季)》第五案中,在最后的案件还原的复盘过程中,节目组就利用嘉宾们的卡通形象进行作案环节的复现,并伴随着文本,不仅抵消了单纯口述的枯燥感,还用另一种形式将文本具象化,便于受众理解。
节目组利用受众对花字特效的期待认可,结合花字的戏剧性,逐渐将其打造为节目中无形的意见领袖,在节目中无论是对于案件时间线的梳理、逻辑分析图的具象表达,还是及时、必要的贴士提醒,花字特效都起到了保证文本完整的关键性作用[3]。事实上,与其说是节目组将其打造成意见领袖,不如说是意见领袖真正想要传达的精神要义借助伴随性文本完成了表达。作为法律科普性节目,对于案发现场严谨性的提示;作为传播类节目,对于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作为语言类节目,对于嘉宾口误产生读音错误时利用伴随性文本的及时纠正:都是该节目价值观的正向输出。
除此之外,节目组还敏锐地捕捉到受众的心理需求,前几季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得观众对于集体记忆的代表拥有着狂热的执念,一定意义上其符号代表成为受众心中整个节目图式的一部分。为了使受众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节目组常常将嘉宾往期节目中的“梗”做成伏笔融入整个故事的创作中。
2 审美范式:空间叙事的节目建构
2.1 二度重构的空间突破
姚斯认为“期待视野”中存在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两种趋势,当读者满足或落空后,“期待视野”会得到矫正、扩展、改变或创新。在长期的媒介接触中,一方面,受众对媒体产品积累了一定的审美体验和认知经验。这种经验不显山露水,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在面对一档新型电视节目时,受众会根据以往的审美体验进行比对,这种比对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对本档节目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受众接收电视节目过程也是与其自身进行参照的过程。受众是具有社会属性的,是饱受人间烟火熏染的,更是有血有肉且具有独立思考的个体,所以,无论受众如何投入节目中,都不会将现实生活完全抛开,而且会进行比照、展开联想。
《大侦探》从第三季开始就不断尝试场景的突破,搭建实景,带领受众进入大侦探宇宙,这种实景现场的搭建不仅为节目空间叙事提供了场域,还可以帮助受众隔绝现实世界原有的规范干扰,但不会消除受众心中的价值定义,这样的叙事空间更有利于受众基于期待视野进行二度重构。“空间形式”其实就是一种比喻性、象征性的说法,是受众经过反复理解之后,在意识中呈现出来的产物,因此“空间形式”和受众的心理活动紧密联系。瑞安以“世界”的隐喻思维对虚构性与叙事性进行区分:“虚构是进入文本空间的一种旅行模式,叙事则是在该空间范围内的旅行。”新空间的形成实际上是节目组进行内容建构以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比如《大侦探(第八季)》的“木偶纪”主题就是来源于微博网友的主题呼唤,“天顶集团”“AB世界”诸多的设定甚至超出受众最初的心理预期。这种受众期待视野的本能增加或调整,与节目本身的阶段性或持续性起伏变化是相辅相成的。随着“大侦探宇宙”的建立、实景空间的搭建,不仅叙事空间上的二度重构完成了,受众的审美经验也会随之提升。
2.2 受众信念感的投射
受众的审美心理分为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和审美想象三个方面,不同于审美理解和审美想象是对更深层的内容的深入探索,审美感知活动更注重受众对电视节目外在形式的感知。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存在差别,受众对于内容的感知需要嘉宾进行引导。《大侦探》每期节目的环节都围绕案件流程展开,根据主题和剧本的不同,赋予嘉宾不同角色,受众随之浸入节目氛围,渐渐产生共鸣,内心期待从而得以满足。叙事的感知往往使被讲述的事件“非现实化”,就正如麦茨所认为的那样,观众绝不会将它们与现实世界进行混同,作为叙事主体的创作者团队往往会通过改变现实因素后让故事发生,这也正是节目故事设定往往脱离现实年代、环境的原因。创作者将故事放入远离现实世界的他处、另一个空间或者是另一个暂且接触不到的时间环境,然后再将一些异质的地点在同一时间联系起来,但与此同时往往还会与现实世界有着或多或少可以追寻可能性的线索设定[4]。《明星大侦探》除了搭建新的空间以外,还利用受众对嘉宾和节目长期建立起来的角色信念,以嘉宾的信念植入为契机,进行对“非现实”世界的价值观“现实化”,通过嘉宾的演绎使受众完成剧本信念感的建立,并使受众结合自己情况和价值观选择进行凝视。
电视节目往往通过主持人或嘉宾的情来“同化”受众,使受众与节目融为一体,让受众获得交流与认同,实现共鸣与升华。每期节目的所有环节都围绕案件流程展开,根据主题剧本不同,施以不同角色嘉宾的引入和“侦探”的引导,受众的情绪随之浸入节目氛围,在体验中渐渐产生共鸣,从而满足受众前期的内心期待。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给予不同的解读、填补、延伸,形成多元化满足并促使节目实现大范围传播。
刘易斯的指示理论精确地解释了人们同虚构世界之间的关系,一旦人们沉浸在虚构作品中,人物开始真实起来,他们所居住的世界会暂时地取代现实世界[5]。节目组在不同季、不同期的相同故事背景下,总能让诸多嘉宾的人物关系产生联系,不仅使得故事角色更加丰满,故事世界建构得更加可信,还使受众可以带入不同角色。嘉宾作为表演的展现主体,与观看客体相比,其演绎程度和对角色的信念感成为货真价实的媒介和桥梁,其角色自身的人性和情感世界更是贯穿整期节目叙事。
3 召唤结构:节目形态的多元化融合
3.1 创新融合的节目形态
电视节目是以视听元素为主的综合艺术,并且附有时空性。电视节目在建构召唤结构时,创作空间更大,操作起来也得心应手。一方面,节目创作者在赋予文本内容意义、建构价值的同时,基于衍生节目《名侦探学院》和《大侦探》部分重叠受众,对新型节目形态完成受众审美认可测试,从而突破固有节目形态。在新一季的节目中,《大侦探》推出“剧本杀”和“狼人杀”的结合,从不同侦探嘉宾的“个人战”推出“阵营战”这一新形式,在完成部分测试的情况下也完成了对受众期待的满足。电视节目的创作要围绕受众的内容期待,也就是时刻把受众的主观需要作为工作中心,所以主题的恰当非常重要。人是具有深厚感情和灵性的,以情动人、形成共鸣才是节目的最终目的。
最新一季节目融入了法律科普小课堂,变成了《大侦探合议庭》,每期节目完成推理后,都会请专业的法官律师针对本期案件进行量罪定刑、法律法规的科普,针对每期节目的主题和涉及的关系进行分析,对观众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
3.2 制造节目热点
姚斯认为,受众不仅通过文本类型和已熟知作品中的审美经验产生期待视野,还可以“通过虚构和真实之间、语言的诗歌功能与实践功能之间的对立运动来实现”[1]31。受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因此电视节目在最初的创意阶段,不仅要满足受众本身的期望,还要设置与受众本身期望相左的意外,处理好二者对立统一关系。《大侦探》在每季节目播出前,通过各种形式对节目进行了全面的铺垫宣传,这无疑是对受众审美体验的引领。
电视节目在设计之初往往会设置多种相近或相反情形的“假象”,以让受众观看体验更加丰满、立体。《大侦探》将这一环节从发现尸体的夸张表现,转移到不在场证明的自我介绍,每位嘉宾要带有角色特点地讲述自己的相关故事,相比一开始就直观地完成角色扮演,不在场证明中“一问都不熟,一搜都有仇”这种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反复横跳、欲盖弥彰的设定,更能吸引受众持续观看。
在每期公布“真凶”环节,节目利用一个答案的肯定与否完成对受众的翻转体验,也正是利用“召唤结构”制造悬念和空白的原理,加强了受众对节目的持续关注。节目中与“名学”的联动、人物关系的逐渐浮现、有趣的新梗制造等也成为节目的热点话题,受众对此会在网络平台进行讨论和“二度创作”,节目组更是利用这样的契机,从受众抓取转变为主动引导,在节目同步播出期间会在微博等多媒体平台进行“微直播”的节目讨论,将事后集中火力加持提前到节目正播出的时间段,为节目的传播助力。
4 结语
《大侦探》从受众的审美体验、审美感受、审美期待、审美想象出发,在节目从文本内容、叙事空间的建构和节目形态上进行融合创新,使受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沉浸其中,情感得以近乎同频共振,在不自觉中领略了影像的魅力和视听艺术的美好体验,受众期待视野也在节目故事内容设计、嘉宾引导、空间建构上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