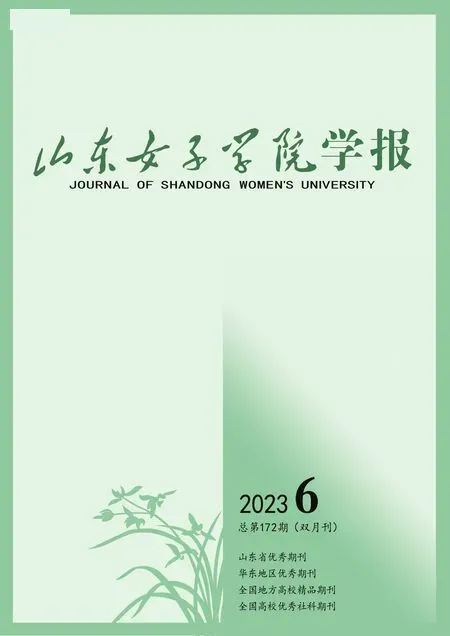文献的性别:女性文献史之经典与解读
——读【清】王初桐《奁史》暨郭海文主编《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解》
李小江
中文里,“文献”(documents)不同于“文物”(relics),其通常以文字为载体,其价值可在文物的铭文鉴定中窥见一斑。英文relics 语义范围很广,多是指遗物而未必是文字。本文在“relics ”意义上使用“文献”一词,跳出文本和文字的局限,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审视人类活动,女性历史遗存(如针线绵织等物事)的史学价值才可能浮现出来,彰显出它们与笔墨书写具有同样可被认知的文献品质。
笔墨最早是男性文化人的专属工具,不止古代中国,在整个汉文化圈里都是特权和才华的象征,其鲜明的等级色彩遮蔽了它的性别属性。的确,在立言记史方面,笔墨书写的价值无可替代。相比,针线绵织类物品多为女性使用,关乎日常生活而无关江山社稷,少被记入史册,文献集成中更是寥寥无几(1)在现存的五百多部类书中专以“女性”为主的不到十部,且篇幅皆小。综合性的类书中收有相关的女性资料不到一成,以清初的《古今图书集成》为例,收有女性资料的只占全书的8.9%,且多偏向于理论记录及传记数据,对于其他则甚少收录。。历史文献的大海汪洋中,《奁史》像是异类,独行独为,于“奁”字名下擅自做史,在尘封的古旧文稿中爬罗剔抉,终成煌煌大观,浩瀚巨作,清末曾经有多位名家校刊。近代以来,新潮汹涌,《奁史》的黯然冷寂该是意料中事,不讨喜的旧时女相遭致冷遇长达百年有余;直到《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解》(下简称《新解》)[1]面世,为《奁史》带来了新生的契机。
历史上,囿于男性中心的价值取向,古今中外,档案库中的文献和博物馆里的藏品都难以避免地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偏颇。记录女性生活的文献非常有限;即使有,也是散落在不同领域的边缘缝隙里,长久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女权主义运动至今已经200多年,女性主义学术重建已经半个多世纪,这种状况没有大的改变;究其根本,就在传统的文献史观里也暗藏着“男尊女卑”的性别偏差,多半学人对女性历史信息的漠视乃至遗失浑然不觉。近年来,微观史研究深入地方,在有案可稽的方志和司法档案里可见一些有关女性的记录,男性文人捉刀,无不留下了父权社会意识形态的烙印,非甄别不能看清真相(2)毛立平在《清代下层女性研究:以南部县、巴县档案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29~245页)余论中专说“档案与性别”:州县的司法档案记录中大量关于女性的记录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定罪者多为“不守妇道”。县官对女性“妇愚无知”的属性定位,妇女本身也非常明了。她们常常配合县官表现她们的“无知”以作为减轻罪行、获得宽免的理由。。相对而言,《奁史》是一个罕见的意外,笔者以男性身份编撰女性文史文献,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及至人间日常生活提供了丰富、细腻、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功莫大焉!
《奁史》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女性生活的重要类书,现版为清嘉庆二年(1797年)伊江阿刻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125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奁”,古意为盛放东西的器物,多指女性梳妆时用的镜匣子,在此指代所有与女性有关的物事。作者王初桐(1729—1821)生于乾隆、嘉庆年间,清太仓府嘉定县(今方泰镇)人。身为男性,为什么唯独是他能在人生的黄金岁月里专注于女性史料的收集汇编,原因不详;只知道他曾为国子监生员,可入当年的最高学府读书问学,博览群书或翻阅史料该是近水楼台。其字号及室名甚多,计有赓仲、耿仲、无言、竹所、思玄、古香堂、杏花村、羹天阁……其中“红豆痴侬”格外触目,让人联想到其小妾李湘芝助他编纂《奁史》的场景,琴瑟和合,冷板凳或许也能坐出几分乐趣。就今天正在开拓中的女性文献史学而言,依旧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走在这条路上,他是先行者,也是奠基人。上起远古,下至清初,《奁史》不忌性别立场,不避物事琐细,在荟萃诸子百家各类书籍笔谈的基础上选编与妇女有关的资料,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分别收录在三十六个门类下,从肢体皮发、音容笑貌、钗环服饰、针线女红、诗文艺术到内亲外戚、婚嫁匹配、生养死葬、精神信仰等,尽录其中,被当代史家看作“古代妇女生活的百科全书”(3)臧健:《奁史——古代妇女生活的百科全书》,载《中国古代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
遗憾的是,《奁史》存世200年有余,相关研究却非常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家的关注更是寥寥。直到郭海文主编的《新解》[1](4)此段和下文介绍《奁史》总貌的文字,均参考或摘自郭海文《新解》的“前言”。出版之前,只有几篇论文及两部整理性质的专著面世[2],与《奁史》内含的历史信息及其文献价值很不相配。究其原因,显而易见:父权社会中“男尊女卑”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史学领域中男性学者长久一统天下,文献整辑汇编总追随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集中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改朝换代类的重大事件。郭海文是在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5)李小江:《史料:新时期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起步基石——读高世瑜的唐代妇女》(《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中有详细介绍。的氛围中进入学界的,她从文学转向史学,在文献学领域术有专攻,侧重妇女史料的征集和甄别,尤其关注那些久被主流学界忽视的女性物事,对《奁史》的偏爱可想而知。她认为,《奁史》之重与史家的轻视“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与传统史学观念中对妇女史料的轻视和疏漏有关,造成文献学领域中的重大缺憾”。在学业日臻成熟的岁月里,她将研究重心转向《奁史》,不仅是为妇女研究提供史料资源,也是从文献学自身的立场出发决心“弥补这一缺憾”。宏大的史学抱负,落实在“女性”名下几近落难;多年执着在“针头线脑”“脂粉饰物”“公主女尼”……不受待见的女性文献中摸爬,不管付出多少努力多少艰辛,在一些同仁眼里也是“没意义,没有价值”的徒劳之举。言语的轻视乃至公然诋毁常常出现在诸如项目申请、学术评价等利益攸关的大事情中,年复一年,“哭鼻子”在郭海文的学术生涯中是家常便饭——十几年下来,笔者是这种窘境的见证人,因此成为全力支持她坚守(女性文献史)阵地的后援队。受益是双向的,不只是友情,更多的是学问。正是她多年默默的坚守和持续不断的提问,使笔者对“女性文献史观”作出清晰的表述:
从女性主体出发,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人类文化遗产(relics)的历史价值,将女性的历史遗存(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看作广义的“女性文献”(female documents),为妇女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支撑,也为“大历史”开拓新的认知视角和研究领域(6)Writing and Weaving:Engendering Documents in History,by Li Xiaojiang,Asia Art Archive(AAA,Hong kong)(李小江:《“文献”的性别属性及其历史品相》),2018年7月12日。。
庆幸有郭海文这份执着,让尘封多年的《奁史》在当代重见天日。庆幸史有《奁史》,为女性文献史学奠基开路,让久存在心的理念有了一个踏实落脚的基地。如今,这个综合性的学术基地就建在郭海文就职的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7)详见《史学的性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拟出版)附录。,与郭海文以及她的文献专业特长有很大关系。多年来,笔者不啻看她在女性文献领域孤自摸索自寻无趣自讨苦吃,同样见证了她做《奁史》研究不依不饶的决心和韧劲,还有她做人做事的旧式德行——踏实、厚道。相信她做的学问会同她本人一样,厚积薄发,在僻静的陋巷里让久酿的甘醇千里飘香。
《奁史》“引书三千,所检之书不下万种”,杂而不乱,排列有序,极少重复,体现了其《凡例》中 “略而不晦,僻而不繁,辞约而该,旨微而显”的编纂原则。全书共 100 卷,拾遗一卷;正文三十六门,每一门类下再细分子目,共计 148 子目,收录材料 13553 条,约 150 万字。很久以来,《奁史》就是郭海文的案头伙伴,从点校开始,得空即修,看它是文献史中一个主攻目标准备长期作战。自 2011年起她将《奁史》研究纳入日程,开始指导学生作相关的学术研究,分门别类,各有专攻。她组织的读书会周周例行,大家一起谈论各自的选题,分享点滴思考和学业成果,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也不曾中断。十多年下来,积小流成江海,在《奁史》研究领域中郭海文协力共同摸索,迈出了一步又一步,沉着、扎实,步步可期。2019年,她将既成的文稿汇编成书,在“女性文献史观”的视野里定名为《新解》。2020年笔者将《新解》收入“性别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第一批书目,期待日后更多的成果陆续面世,直到“完成”——对此目标,郭海文非常清醒,须臾不曾懈怠,更不会轻言放弃。
目前的研究成果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大量的任务还有待于后期的艰辛工作。我们依然会秉持严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认真阅读文本,对文本进行认真的标点、注释、校勘。运用性别理论及四重证据法对文本进行详细的解读,以期佳惠学林[1]前言。
接下来,笔者的工作是做好两件事:借《新解》主编郭海文的梳理展现《奁史》的基本轮廓和主要内容;同时,介绍郭海文和她的学生已经开始并且做成的基础工程,看陈旧的文字如何在“新解”的视野中获得新生。
《奁史》三十六门,子目琐细繁杂,郭海文对它们作了必要的归纳,依照女性生活常识和生命轨迹,以现代人易解的方式将其分为八个部分(如下)(8)参考或摘自郭海文《新解》的“前言”,略有修改。。
第一部分:两性关系,性别制度,包括《夫妇门》《婚姻门》两门。
古人相信“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故以《夫妇门》开头,胪列有关夫妻本分之言论以及夫妇相从之各类形态。夫妇之合,端赖婚姻,故次立《婚姻门》,叙述嫁娶礼仪,亦有各类婚事,如皇族婚、同姓婚、世代婚、指腹婚、续弦、辞婚、冥婚等。
第二部分:女性群体的内部分类,依照编撰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等级所见,包括《统系门》《眷属门》《妾婢门》《娼妓门》四门。
《统系门》历述后妃、女主、公主及婕妤、女官、才人、女史、彤史、女常侍、命妇、宫人等宫廷内职。《眷属门》首及母教,并述诸母、祖母、后母、乳母等故事,再列出孝女、贞女、姊妹、姑妇、娣姒、姑嫂、叔嫂、弟妇等亲属关系及若干事迹。《妾婢门》及《娼妓门》,分述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妾媵、奴婢及娼妓,此辈或凭宠提升地位,或受辱终身,或出家为尼,命运遭际各有不同。
第三部分:女子教育与德修,十门,包括传统“妇学”四项内容,涉及德行(德)、言辞(言)、容貌(容)、技艺(功)的培训和修养。
女容,包括《肢体门》和《容貌门》两门,罗列历代有关妇女身体及其容貌举止的言辞事例。女德,主要在《性情门》,集中女子性情爱好等的描述。女红,集中在《蚕织门》《针线门》《井臼门》三门,可见古时从皇后至民间女子均宜勤习女红,善于操作。女言,包括《文墨门》《干略门》《技艺门》《音乐门》四门,发现被埋没的女作家、女书法家、女画家的作品,展列出历代闺媛在诗文、书画、音律、技艺以至武艺方面的文化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者特立《干略门》,辑录妇女武艺,历举拒贼杀敌的女英烈。
第四部分:女性的姓氏、性事与生育文化,包括《姓名门》《事为门》《诞育门》三门。
《姓名门》述女性姓、氏、字、称谓、谥号等。《事为门》 述岁节时令及房中密戏。《诞育门》述感孕之传说、生育之异常情况、产仪等。
第五部分:女性专职行业,有《术业门》一门。
《术业门》录古代从事几种特殊行业的女性,以“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为主。
第六部分:女性的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十二门,涉及衣食住行方方面面。
《衣裳门》《冠带门》《袜履门》三门,收录女性各类服装、饰物、鞋袜,从衣料到时尚、款式。《钗钏门》《梳妆门》《脂粉门》三门,历数女性首饰和梳发、洗澡、装扮用具及方法,以及脂粉的成分、品种、用法等。《绮罗门》和《珠宝门》搜集汇编与女性有关的丝绸、明珠、金银、线帛等物事资料。《宫室门》和《床笫门》辑录从外到内的各项家居设备。《饮食门》 历数各样食物品种,从蔬果、肉食、糕点到烟、药,均有文字解说。《器用门》讲与女性有关的器皿、舟车等,是对历代正史《舆服志》 的补充,从中可看到在传统礼制束缚下女性的生活。
第七部分:女性的自然文化,包括《兰麝门》《花木门》《禽虫门》三门。
《兰麝门》《花木门》《禽虫门》三门所录均与植物和动物有关,从中可见女性与自然物事的关系。《禽虫门》中收录了如西王母的使者鸟、武则天蓄养鹦鹉、小燕飞入人家化为女子之传说。
第八部分:女性的宗教信仰,有《仙佛门》一门。
《仙佛门》叙录历代传说中的女仙、女神,如西王母、嫦娥、织女、何仙姑、天妃、巫山神女等,亦及于授经、拜佛情况以及鬼怪故事等。
相对客观的概述介绍中,郭海文对自然界中花草、林木、禽鸟昆虫类三门与女性的关系又有特别的说明:
《兰麝门》《花木门》《禽虫门》看似中性,但《奁史》所录均与女性有关。女子用花木可满足其最低层次的生理、安全需求,如美容与求子。女子亦可用花木满足其较高层次的爱与归属的需求,如缘情、言志、审美。女子更可用花木满足其自我超越的精神需求,如礼佛、得道。这种记录历久弥贵,让我们从历史的缝隙里看到了女子的生命体验 ,看到了her-story她的历史[1]前言。
这段文字相当典型,映照出《新解》的基本品质: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在古旧文献史册(history)中发掘或挖掘女性的历史印记(her-story),于妇女史和大历史一举两得。所谓“新解”,即革新传统的史学观念,走出文字文献的局限,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具体到《奁史》研究,就是以女性为主体,把相关的文化遗存(无论形式载体)看作广义的女性文献,认真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细致地分析解构《奁史》中大量翔实可鉴的历史资料,从细微处入手,重新发掘和阐释女性文献的历史价值。正是因为在长期的文献研究中早已清醒地看到并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文字文献的缺憾,郭海文对“女性文献史观”的提出感同身受,并在《新解》中身体力行:
古代妇女极少有“言”见之于史,但这并不代表她们在历史长河中没有其他的表达途径。一幅画、一具物、一针一线一身衣裳,都可以是她们抒情言志的载体。《奁史》对古代妇女生活的记载多为摘录,没有详细的注释分析。鉴于此憾,《新解》借鉴了“形象史学”的研究方法,将传世的造像、铭刻、器具、书画、服饰等一切实物作为证据,文字与“形”“象”结合,填补了古代妇女的言语空白[1]前言。
其实,不止在《奁史》辑录的文字中,长期以来,在女性文化的田野考察中、在妇女博物馆的筹建过程中、在妇女口述历史的浩瀚档案中……我们早已发现、体察,并且日渐清晰地认识到:女性的文化遗存遍布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与生命史、日常生活史、部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身体史、心灵史、人类情感和审美的历史密切相关。从女性的日常生活到生产劳作,乃至审美传情,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生成一种共识,值得后人持续追踪:在所有可以被看作女性文献的历史遗存中,“针线绵织”类的物事最先被关注到。
针,是人类为取暖遮羞、缝织衣物而发明的一种实用工具,其出现早于笔墨和文字,因此,它的历史认知价值也在笔墨出现之前。从出土文物看,最初古人使用的是骨针;继而用竹针,在汉字中写作“箴”;后来有了金属的针,写作“鍼”(针)。材质的变化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见证。与笔墨立言相似,“针言”即为“箴言”,与“真言”谐音,是女人自我表现和传情言志最普遍也是最主要的手段。同笔墨书写一样,针线绵织承载的不只是心智,也有心绪;如《游子吟》(唐·孟郊)所描述,在“密密缝”的隐喻里道出了笔墨难以言说的深情厚意。
线,古往今来,从藤葛草绳到麻线、丝线、棉线再到人造纤维等等做成的各类线材细柔、纫韧,可以任意曲折,续接绵延,让生命之链“不绝如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在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线的影子无处不在,被引申到各个领域的认知层面,在语言中常被用作连词的词根。无论是可见的“引线”还是玄机暗藏的“线索”,都可能在我们的思维盲区中出人意料地别开生面。
绵,常常与线并列,有双重含义,它是去除杂絮后的精选蚕丝,也是长存之物,意在绵延不绝。古字中有“绵”无“棉”字,大约 6 至 11 世纪随着棉进入中国并被广泛种植使用,“棉”在用字上被定义为“绵”,故元代以后文献中的“绵”同“棉”[1]26。自此,“棉”“绵”各自走上了不同的轨道:棉,遍布四野民间,成为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实用之物;而“绵”字则越发少见单独使用,在现代汉语中基本上脱离了它的物质本性,多用作连词的前缀,取其古义“纯”“存”的含义,在精神层面上恣意伸展:绵延、绵续、绵亘……以柔克刚取弱者之长,以绵薄之力博时势之强。
比较而言,在众多“糸”部首的字词中,织的含义也许是最丰富的,它的释读空间相当开阔。繁体的“織”从糸(mì)从戠(zhí):“戠”指军队方阵操演,引申为规则或图形及其变换。“糸”与“戠”结合成“織”,是名词也是动词:作名词,它是“布帛之总名”(《说文》);作动词,它的本义是“绘”(《尔雅》),在制造布匹的过程中加入了可变的图案——亦静亦动的结合中,“织”的含义可以无限伸展,譬如“旗织”(《汉书·食货志下》)一类象征性的隐喻,从有形的编织到无形的组织,将所有针头线脑般的琐细事物统统纳入可以被网罗、被结构、被创造的社会空间,在生活的、技艺的、艺术的和审美的领域中成为可被认知的历史文献。
古时乞巧节有“乞聪明”的习俗:“七夕,京师诸小儿各置笔砚纸墨于牵牛位前,书曰‘某乞聪明’。诸女子致针线箱笥于织女位前,书曰‘某乞巧’。”[3]社会对男孩和女孩有不同的期许,在价值观中是等高的:男孩用笔墨纸砚指代写好文章,女孩用针线象征女红手巧做好家事[1]293。过去我们总说女人未载史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发现的路径,没有重视那些习以为常的女性的历史遗存。如今,从全新的“女性文献史观”出发,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别样面孔:如针线绵织,它们不仅是女性文献中富有代表性的历史载体,也是女人自我表达的主要工具。使用的工具和形式不同,解读方式也不一样。男人用笔墨作为传承工具,用文字文献将历史事件记录下来。针线绵织出自女人之手,编织的是一段段不为外人知晓的集体记忆。无论是直观的个人记事,还是隐喻的民族记忆,同样携带着历史信息,需要我们从新的视角、用新的方法更新认识,重新诠释。过往,诸多学人一代接一代钻研笔墨文存,少有人在女性的造物中做文章。《新解》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另辟蹊径,开篇几章说的就是针线绵织,在对《蚕织门》《针线门》《衣裳门》的解读中成全了我们对女性文献史观的具象认知。
《新解》的开篇解《蚕织门》,是郭海文在该领域中的早期研究成果,她与自己学生联手,提供的不仅是合作研习的操作模式,在体例上也是一种示范:由《奁史》所记录的点滴信息进入主题叙事,主角不再是原书中的文本阐释,而是伸展开来的整个“蚕织”领域。从远古直到近代,从采桑、护桑、盛桑的用具到养蚕、纺织的各种用具乃至织机的种类,从自然界的桑蚕养殖到纺织成品丝绸绵麻,整个叙事始终行进在劳作的时序中,细腻且详尽,繁杂却不乱。史料来源也不再局限于《奁史》所辑录的文字,从考古出土的实物到墓葬中的壁画、雕塑、绘画、笔记杂谈……可谓八面来风,丰富多彩。有趣的是,作者在行文中论及的“蚕织”各项物事,统称“用具”而非“工具”,走出了习惯认知的生产劳作之局限,坦然走进女性生活的开阔空间,在女性专属的《蚕织门》里将生活与生产结合得天衣无缝。
封建社会风俗中,女子出生“弄瓦”(纺砖),女子出嫁以桑树、梭子等物品作为陪嫁,女子随身携带的鞶囊里必备线纩等女工用具,等等,可见女性生活与社会生产的相关性。“纺轮”“梭子”“织机”等纺织工具,均作为女性性别认同的象征[1]32。
作者强调:一方面女子被拘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不停地劳作,以迎合古代社会对女性“足不逾户”的道德束缚;另一方面她们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以外,还以丝绸纺织为平台创造了灿烂的服饰文明。“在丝绸之路上,女性负责使用织机织造出精美的丝绸织物,男性则充当运输者和传播者,共同将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遥远的西方国家联系起来”[1]33——好一个“共同”,呈现的不仅是漫长的历史中两性协作共生的琴瑟合音,也是郭海文本人历史观和人生理念的完美体现,看到了的协作,令人会意、暖心。
解《蚕织门》主讲的是物事,解《针线门》的重点在人,其叙事主体是“针线活”而不是常人常说的“女红”。为什么?因为“针线活伴随古代女子的一生”,做这件事没有退休之日。《奁史》引《画墁录》记载:“温夫人,年八十余,耳目聪明,日视针线。”[1]43针对过往的研究侧重女红工艺技巧,对女性主体和女红工具的考察不足,作者有意补缺,用一个“活”字,生生地将整个“针线”都激活了,看它们不仅是女性做家务活儿的活水源泉,也有与笔墨一样所具有的精神价值:
“针线活”作为女性独自担负的社会责任,代替笔墨,以物质的方式将女性的人生印记存留下来,与传统文献比肩,是研究古代妇女生活的宝贵资料。 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针线之事,不仅是女子一生之事,也是全体女性之事。做针线活,不仅是一种生产技能,也是女性自我书写的主要方式[1]36。
作者将“针”置于“针线活”的叙事之首,强调它在女性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意义:女子往往将针随身携带,如《奁史》引《摭异录》中载,皮大姑的“紫纨袴带”上总系着“针囊”(9)《奁史》卷四一《针线门》引《摭异录》,第 621 页。。且一根针的使用时限很长,甚至“一生用之不坏”(10)《奁史》卷四一《针线门》引《女红余志》,第 620 页。,可以长久地陪伴着女性的成长。针与线相互配合,不仅能满足做针线活的多种实用功能,还能承载难以言说的情愫感怀,如民妇在《山歌》中所念唱的:“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 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思)来竖也丝(思)”(11)[明]冯梦龙采集的《山歌》,引自《新解》第40页。。针线活做成衣服、被服、鞋袜,还有香包、绣品、佩带……恰如作者所言:“如果说材质坚硬的针像是女性本体的投射,那么或许可以说,柔软绵长的线,就是将她们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条条不绝的通道”[1]40。对针线一类缝纫工具的巧用,不只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不仅是情感生活的见证和伴侣,更是精神生活中信手拈来的器具。《奁史》引《熙朝乐事》:“上元节,妇女召针姑,以卜问一岁吉凶。”具体操作见《奁史》引《石湖屠士集》:“婢子以针卜,伺其尾相属为兆。”妇人以针尾的状况作为依据判断吉凶,以常用之物敬问鬼神、占卜前途,诸如此类,在古时妇女生活中应是便宜之事[1]44。
《奁史·衣裳门》三卷,其中既有式样繁多的中原地区服装,也有风格迥异的异域民族服装,共计 500 条。《新解》中有两篇分别专论上衣和下服,综合文献、图像及相关考古资料,考证的不仅是“衣”“裳”本身(诸如穿着场合、形制材料、制作工艺等),还有服饰携带着的尊卑秩序及其背后的礼法制度[1]56。《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12)《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八《系辞下》,第 87 页。“垂衣裳”即定衣服之制,辨贵贱之别,示天下以礼,作为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一环,历朝历代都有烦琐严格的规定[1]87。以帔为例:
帔,始于晋永嘉年间,宋代时分为三等,成为女性彰显身份地位的符号,《奁史》引《二仪实录》:“霞帔非恩赐不得服,为妇人之命服,而直帔通于民间也。”(13)《奁史》卷六三《衣裳门二》引《二仪实录》,第 139 页。……比之宋帔,清代的霞帔则在形制上有了很大变化:其一,帔身阔如背心,且左右两幅合并;其二,在胸背正中缀以补子,补子所绣纹样与其丈夫的官位相对应[1]72。
《奁史》将那些已经消逝的旧物事与过往的社会性别制度一并带进我们的眼帘,在昔日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中站立着勤劳且智慧的古代女性群像。她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劳作,她们在劳作中尽力创造“更好的生活”,力求让每一件寻常物事都能焕发出美丽的光彩——此类举证在《奁史》和《新解》中不胜枚举,让今人后人叹为观止。
《新解》十五篇文章中,涉及《蚕织门》《针线门》《衣裳门》《饮食门》《井臼门》《技艺门》《文墨门》《钗钏门》《脂粉门》《花木门》《仙佛门》十一个门类,以《文墨门》着墨最多,所说多见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而言,《新解》对文房中女性书写工具的展示、拾遗,有补缺之功效。其中解《花木门》一篇,用心多在花木之外,强调女子借花木抒情寄情,看重的是女性与自然界的熔融合一。如作者所解:“由于女子与花存在着种种联系,古人也乐于将不同的花与不同的女子类比。评花之人皆为男子,女子只是他们所评对象。”[1]376(如曹大章品秦淮名妓,见《奁史》卷九二《花木门一》引《莲台仙会品》)看与被看,评与被评,现代理念浑然不觉地渗透在字里行间,让尘世间的性别身份在“新解”的自然界中获得了新的阐释。
《奁史》最后一门《仙佛门》有关女性的信仰和精神活动,共五卷 495 条,分仙、神、鬼、信佛四大类,引书 371 部,经史子集俱有涉;既有先秦至明清的众多女性神话事迹,也有大量对民间普通女性信众的描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解》对其中(女)“神·仙”的阐释,各自归位,分而论之:既有高高在上以司天象的女神,说道她们如何利用亲属关系建构权力谱系的性别特征(“女性神话人物通过亲属关系构筑了一个庞大的谱系,同时通过亲属关系形成了权力的核心。而相较于女性神话人物 来说,男性神话人物通过亲属关系来构造谱系系统则较为少见。”[1]421);也有尘世间可以追随效仿的女仙,为女性在精神上的自我升华开启通道。
神和仙虽然皆有异能,但彼此还是有区别的,神乃先天自然而成,仙则是后天修炼而成。具体到女神、女仙的概念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女神即天生神圣的女性神话人物,具有浓厚的自然属性;而女仙乃是由凡人后天修道而成的女性神话人物,社会属性更为明显[1]410。
“女仙与女神的重要区别是,女仙多由凡间女子修道而成。”[1]425在众多成仙之道中,要点是“苦修”(她们修道所凭是对成仙的执着信念,必须付出几十年的长期修炼。这部分修道者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结构予以表现:民女→自觉修道→感动上仙而得助→最终修成[1]433)。苦心修道结成善果,遍布天下的女仙便是一个明证。至今让笔者记忆犹新的,是作者在《仙佛门》众多记载中发现了“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即女仙信仰的有限空间性及其地域特征(14)此段文字均引自或摘选自苏振富:《〈仙佛门〉里女性的精神世界》,载郭海文主编《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34~436页。:
沿海地区
《仙佛门》中,天妃信仰发源于东南一带,辐射范围远达东北沿海一带。如东北地区的旅顺天妃庙,是现存东北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妈祖庙。
巴蜀地区
《仙佛门》中的巫山神女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于南方巴蜀地区,她的传说最早见于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民间的祠庙很少。《元和郡县图志》、《宋会要辑稿》和《水经注》中皆无关于巫山神女的记载。
黄河流域
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山西盛行关于麻衣仙姑的信仰。据《仙佛门》记载:“麻衣仙姑,姓任氏,隐于石室山。家人求之,遂逃入石室,中有声殷殷如雷,其壁复合。”正由于其隐藏之地有声隐隐如雷,所以麻衣仙姑最为主要的活动便是降雨。
作者为《仙佛门》中众多女仙做成“一览表”[1]437-430,在突出展示其地域性的同时,分析了这一特点生成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地理环境的限制,二是地方文化的制约。“因此,不论女仙地位如何之高,其影响所及总体来讲基本上都集中于发源地,鲜有影响波及全国的女仙”——话到这里,让人浮想联翩,想到的不只是女仙信仰本身的地域色彩,还有她们在帝王天下的生存空间和实际价值:正因为这些地方性鲜明的女仙与本地文化有共同的特征,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因此“会在本地形成一些国家祀典之外的职能”,如麻衣仙姑祈降雨、妈祖祈平安……延至佛教和道家向观音求子、向何仙姑求长生等,不一而足。所谓菩萨的“女身化”和宗教的“中国化”,也都带有深入民间的女仙色彩。
最后,笔者将《新解》中各篇详目和作者以及《新解》之后郭海文团队出版的论文和正在进行课题分录整理(略),让更多学人和笔者一起期待更多的成果问世。面对浩瀚如海的女性历史遗存,这只是开始;但,毕竟已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