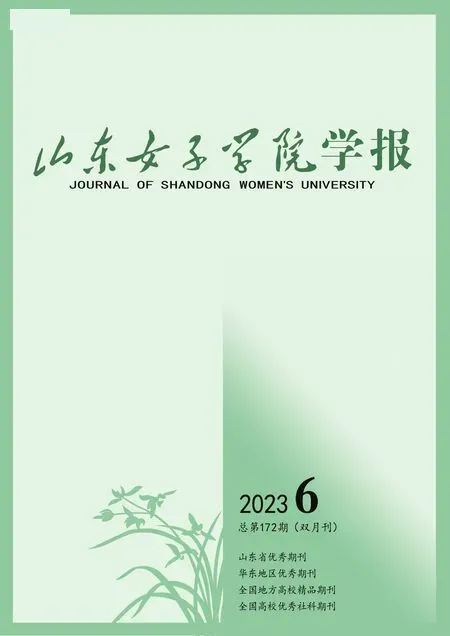“新”技术的性别历史与公共性:技术的性别建构与性别平等
何锦娜,卜 卫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21)
一、引言
2023年年初,ChatGPT成为许多网民共同的网络聊天对象。它的幽默、智能与高效,重现了那些曾经围绕元宇宙、计算机、基因技术、工业大机器等“高科技”涌现的预言。自2023年2月以来,已经有101篇新闻传播领域的ChatGPT研究论文被知网收录,这些研究大多以机遇/威胁的框架来分析ChatGPT所能带来的影响。然而,机遇/威胁的框架容易隐藏ChatGPT所代表的AI技术在历史上的延续与积累,让它变成一个“空前”的存在,从而忽视它是此前许多技术发展的结果,而那些技术也曾被寄予“横空出世一蹴而就地解决很多问题”的厚望,或者被认为将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机遇/威胁的框架也容易使人们的注意力留在AI技术的表层,将它作为一个已经设计好的客观、一体、静止的事物,忽视它的技术基底(如基础设施、软硬件)、文化纹理(如劳动分工、文化实践)以及具体应用方式导致其发展轨迹可能产生的偏向。
近年来,新技术引起的热议源源不断,区块链、物联网、元宇宙、NFT(Non- 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通证)、ChatGPT……新闻传播学界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这股“技术热”,始终关注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传播影响。可是,新闻传播研究显然不能满足于在快速变换对象的“技术热”中作出预言,而是需要研究具体的“技术”问题,进而把握技术与所研究议题的微妙关系,那么,将新技术放进更为历史性的脉络里讨论就显得至关重要。
同时,如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在《传播的偏向》中指出的,传播技术不同的偏向性将导致不同的权力类型与社会形态。近年来,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媒介化、平台化以及基础设施意义上的媒介研究,正是对“新”传播技术偏向性及其对社会权力关系之影响的不断探寻。在这众多的权力关系中,“性别”也是其中一项。当然,简单地认为信息通信技术、互联网、数字与智能技术是一种“女性的技术”或“父权制的技术”就又陷入了上文所说的机遇/威胁框架下的技术决定论。本文对性别与技术的关心,建立在对技术与性别两者非本质论的、关系性认识的基础上,并且提出以下三个问题:(1)为什么是性别化的技术?(2)随着技术的迭代,尤其是近些年数字与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媒介研究在性别和技术的论述上有何延续与发展?(3)除了现有的研究方向之外,对照国内外问题化性别和技术关系路径的差异,国内媒介研究在性别和技术这一议题上,该如何增强公共性?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本文回到技术的性别隐喻和物质实践对较早的研究进行梳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本文选取近五年媒介研究领域的性别与技术研究进行文献分析,所研究的文献,来自国外的FeministMediaStudies和Gender,Technology&Development两种性别研究期刊,以及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与性别研究领域的《妇女研究论丛》5种期刊。对于英文期刊,使用“ICT”“digital technology”“AI”“algorithm”为关键词对2018年至2023年的研究性论文进行筛选,对国内新闻传播研究期刊,以“性别”“男性”“女性”为关键词进行筛选,对《妇女研究论丛》则用“ICT”“数字”“算法”“人工智能”为关键词进行筛选,共筛选出性别与技术相关的媒介研究文献188篇。这188篇文献基本可以被视作近些年在性别与技术话题上的媒介研究的缩影。
二、技术与性别:隐喻与物质实践
在谈论具体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之前,本文首先要从“技术”的观念史中发现性别,其次再梳理围绕具体技术进行的研究。
(一) 绝对控制:技术的性别隐喻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2]在《自主性技术》里提到西方对技术的传统看法来自对自然的控制观。在这种观念下,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实现对自然的控制,从而让种族的发展更为繁荣。这种控制关系往往是单向且绝对的,也就是主人—仆人/奴隶的关系。在使用者即西方古典概念的“人”看来,技术与人类奴隶在功能上可以互换,都是为了把“人”从辛苦的劳作中解放出来。温纳没有指出的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实践中,“人”仅包括成年男子,为了更好地参加城邦政治,他有两种生命财产可以使用来帮助他摆脱辛苦的劳作:第一种是奴隶,他们往往负责生产劳动;第二种是妻子,她们往往负责操持家务。因此,在奴隶—技术这一可互换的关系中,有一个被忽略的女性身影——和技术与奴隶一样,女性也属于那个能将“人”从辛劳中解放出来的类别。
这一绝对控制的隐喻还有第二层意涵,即“人”是技术的创造者和制作者,因此他知道技术的目的和使用方法,他使用技术改造世界这一关系是绝对的。在“人”的概念向成年男子以外的人群敞开前,“技术”专指与成年男子改造世界有关的技术。朱迪·沃伊卡曼(Judy Wajcman)[3]指出,“技术”是一种文化,“技术”范围的确定带有性别权力的色彩,男性对财产和女性的支配保证了这种基于性别二元区分导致的“技术建构”,所以男性创造和使用的武器、农具和机械等被视作“技术”,奠定了“技术”的男性气质。
直到现在,虽然大量的文献与事实已经动摇了“人对技术的绝对控制”这一观念,技术的失控甚至是对人类的反向奴役(1)温纳在《自主性技术》中指出,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技术的失控,也受到泛灵论的影响。在文学、影视与学术思辨上都有了丰富的表述,但是它的性别隐喻仍旧在我们对于技术的认知中生效,甚至在许多具有后人类元素的电影中,女性机器人仍旧摆脱不了顺从的女性气质[4]。同时,性别隐喻也意味着性别预设的隐形,于是性别中立的技术也成为普遍观念,而男性更擅长技术也成为生理决定论的一部分。
(二)女性赛博格:ICT与打破性别边界
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信息通信技术)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一般作为“信息时代”的技术标志,在更多提及“数字技术”的当下,重新廓清这一概念的范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所处的技术坐标。ICT被广泛用于发展、经济、教育和商业各种语境,在不同语境中侧重不同的技术层面,比如就经济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它涉及信号、信号塔、卫星等基础设施,电话、呼叫器、平板电脑和其他无线设备,还包括互联网访问权(access)、互联网可得性(availability)等重要议题。而在教育领域,它涉及技能(skills)和能力素质(competencies)等重要概念[5]。但就广义上来说,ICT是一组技术,其功能远超储存与传输信息,居于核心的是计算机与软件[6],它是计算机技术、传播技术与多媒体的综合,人们通过它互动协作,它也是“赛博空间”的基础[7]。因此,数字技术和AI技术都以ICT作为基础。
女性主义对新技术最为激越的想象受到民用互联网普及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ICT的突进、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走向衰落与各种“后”思潮的流行,在互联网上促生了更为碎片化、去中心化、去疆域化和游牧式的女性主义表达。彼时唐娜·哈拉维(Donna J.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也以打破二元的跨界姿态受到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女性的追捧。她们以哈拉维的“赛博格”为身份符号,力求打破男女、人机、人与非人、自然与人工、虚拟与现实的二元结构,踊跃地使用ICT技术,在赛博空间中歌颂赛博格所能实现的女性联合(2)赛博女性主义者认为,赛博格(cyborg)这一概念具有突破二元边界的潜力,因此也可以弥合多种二元区分导致的女性群体的分裂,如弥合阶级、种族、国家、年龄、性取向等边界。参见Donna Haraway于 1987年发表在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上的文章 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进行涵盖艺术、文化、理论、政治、传播与技术的实践。宁可做“人工”的“赛博格”,也不做“自然”的“女神”(3)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如激进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倾向于通过理论在女性和西方现代性(modernity)的所有他者之间建立某种亲缘关系,而这些他者是肉身、自然的,因此“自然女神”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是非常重要的意象。这种做法在哈拉维这类赛博女性主义理论家看来,恰恰强化了性别二元的论述,因此她提出“赛博格”这一兼具人工和自然的“混血物种”来挑战“自然女神”的概念。参见Elaine Graham于1999年发表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society 上的文章CYBORGS OR GODDESSES? Becoming divine in a cyberfeminist age。,这就是赛博女性主义。
除了哈拉维,赛博女性主义的标志性书写来自英国文化理论家萨迪·普朗特(Sadie Plant)和澳大利亚艺术家团体VNS Matrix(4)VNS Matrix成立于1991年,其目标是使用和操纵技术以“创建可以解决身份和性别政治问题的数字空间”。。赛博女性主义者对技术的拥抱来自两个基本预设:ICT被认为是男性的技术以及ICT是中立的。因此,拿起ICT走向赛博空间便具有了解放性别的实践意义。赛博女性主义者在赛博空间的态度是游戏的,在这个游戏过程中,身份与身体共同实现去中心化。虽然她们对互联网“女性媒介”的理解看似接近后现代的“女性”论述,但实际上她们更强调用“赛博格”(cyborg)这一身份对女性的差异进行弥合。在身份和身体去中心化的数字实践中,赛博女性主义者创造出了一些“女性专属”(women-only)的空间[8]。
不得不承认,赛博女性主义对ICT的全盘拥抱来自一种技术决定论的乐观,尽管这避免了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中将妇女视为新媒介技术受害者的倾向,但也导致了她们在看待新旧媒介关系时的断裂视角,忽视了赛博世界的性别流动性也由“物质世界中本能的、活生生的性别关系所限定”[9]。而正因为它不明确定义自己是什么,反而用“不是什么”来论述自己,以此达到非二元的目的,所以性别与阶级、种族、年龄等实在的交叉性也被消弭了。
目前,赛博女性主义一词仍然在女性主义的数字技术研究中被提及,尽管它本身蕴含宽广的哲学思考,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更多地指称女性积极使用互联网进行自我赋权的实践。
(三)技术女性主义:性别的技术社会学
技术女性主义(technofeminism)是沃伊卡曼[10]对女性主义的技术研究(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的指称,它采取技术的社会性别视角,主张社会建构论。跟赛博女性主义不同的是,技术女性主义观察到了女性消极的科技参与,并将其作为研究问题。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这一领域的学者基本认同技术并非中立,而是有其性别偏向。
温迪·福克纳(Wendy Faulkner)[11]总结了这一领域的三条脉络。第一条脉络源自自由主义,其预设“技术是性别中立的”,女性的科技参与度低源于女性的社会化过程,因此在女性社会化的早期就要教育引导她们亲近技术,改变科技领域就业的性别差异。这一脉络将技术看作是“好”的,并没有探究女性为何“不愿意”进入技术行业。第二条脉络关注女性在工作和生育过程中接触的技术,她们更多的是技术的接触者,而不是技术的发明创造者,在这些研究中,女性相对于男性主导的技术是消极的、被动的。第三条脉络认为技术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也会被性别这一社会结构所影响,并反过来再生产性别关系,最为典型的是性别的技术驯化研究。露丝·科恩(Ruth Schwartz Cowan)[12]对微波炉设计中的性别偏向作了研究,发现虽然技术在演进,但是其中的性别偏向却导致女性的家务劳动量增加,反而巩固了性别关系。在大众媒介领域,对女打字员[13]和电话接线员[14]的研究,指出了对女性气质的期待如何与打字机和电话系统一起把年轻女性“困”在没有发展前景的职业中,从而再生产性别的经济不平等。
妇女不擅长使用技术,这也是男性中心的技术符号体系生产出的刻板印象,这套符号体系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和再生产中使用的技术排除出去,凸显男性活动使用的技术,并通过男性中心的符号再生产两者的技术身份——男人的机器,女人的织物(men’s machine,women’s fabric)[3]。沃伊卡曼进一步认为,性别化的技术不光涉及其中的性别权力,即男性对技术的占有和对女性的支配,还包括了符号与性别身份。不过,既然技术涉及符号与身份,那么女性“不愿意”进入ICT行业也变得可以理解。由是观之,是ICT行业冷硬的男性气质让处于其中的女性很难找到一个舒适的身份,她们进入ICT行业的“代价是抛弃她们的女性气质”[15]。
既然“技术”是一种暂时由男性垄断其定义的文化,那么我们对于“技术”的定义就可以发生变化,转而研究那些看似日常的、与妇女有关的“低科技”。与此相呼应的是白馥兰(Francesca Bray)[16]对于中国古代妇女技术的研究,她恰恰从纺织、刺绣这类“低科技”的妇工出发,用纺织材料与织机技术将古代中国妇女在家庭中权力和尊严的变动编织进国家结构与历史,又用绣纹写出古代妇女在父权制家庭中的个人情感与命运。沃伊卡曼的观点和白馥兰的研究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建构是一个基于性别分工的过程,它又是性别与其他社会结构交互的媒介,取决于一定时空和文化下人们对性别分工的理解。比如说,妇女更少、更消极地参与编程工作是基于西方白人世界的语境,而在南亚程序员则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体面工作[17]。
我们还可以由此思考女性在高科技中边缘化和辅助性的角色与技术的关系。AI并不是一项在21世纪才横空出世的技术,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男性工程师不断地以“女性助手”的角色塑造AI的特性。二战期间,大量的数据运算工作由女性计算员承担。1947年,美国陆军部委托工程人员研制了第一批电子计算机,这些设备使用打卡带的数据进行运算,比女性计算员的速度更快。实际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的编程者正是一群女性,但她们必须按男性工程师的指令行事[18]。女性顺从、灵巧,运算精确,长于重复性的工作,因此女性是更好的计算员,一台好的计算机应当能取代女性计算员,因此它应该顺从、灵巧与精确。AI的发展实际上延续了“男性控制—女性服从”的权力关系[19]。AI女性化还不止于此,事实上,工程师优先将女性语音用于AI,也是因为女性的声音更具情绪的滋养性,更为柔和舒缓,也更符合“助手”的角色。在这一点上,AI的发展回到了技术最早的性别隐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赛博女性主义与技术女性主义对ICT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但面对ICT的发展,两种视角的相互借鉴,特别是将赛博女性主义中活跃的女性主体性注入技术女性主义将变得尤为重要,赛博女性主义对性别二元论的拒绝也可以改变技术女性主义中固化的性别二元视角,从更动态的角度去剖析技术与性别。遗憾的是,在数字技术引起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视之前,国内的新闻传播研究尚未注意到这两个领域,仅有思辨类的文章谈及互联网并不是性别中立的公共空间[20],也几乎没有基于实证的知识积累。
(四)数字劳动:无偿劳动的女性化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性别化的ICT研究中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即“无偿劳动”的女性化。在媒介研究中,无偿劳动以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21]的“受众商品”概念为起点。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控制机制的变化,提供了“免费劳动”[22]“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23]等概念,将“劳动”扩展至非物质生产领域。
不过“免费劳动”“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劳动”都是相对宏观和批判性的概念。具体而言,目前媒介研究关注的热点是ICT领域的“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最早由尼克·戴尔-维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24]在研究电子游戏玩家时提出,后面不断得到定义,如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25]将其具体定义为“使用ICT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目前的数字劳动研究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技术使用者本身变成劳工,其行为都被数字技术货币化;二是工作数字化方向,指的是传统行业的工作被数字化及其带来的冲击;三是工作自动化方向,即智能技术作为劳动者参与工作带来的行业乃至社会影响[26]。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直关注性别压迫如何维持再生产劳动的无偿性来保证资本对生产性劳动的剥削,在数字劳动的研究中,“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27]与“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28]两个概念也常常在数字劳动的语境下出现。女性因为更容易从事那些需要在工作中调动情感(如育儿)或为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劳动(如空乘)而与“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两个概念发生关联。这些劳动多为服务性的工作,对于劳动力、社会、情感、意识形态和心理状态的再生产来说必不可少,但因为其女性化和非物质化而受到忽视,难以获得经济回报,从而使从业者处于脆弱地位。
我们可以从女性的互联网使用特点以及互联网行业就业的性别分布出发,考虑女性在数字劳动中需要付出的“情感劳动”和“情绪劳动”。凯莉·贾特(Kylie Jarrett)[29]的“数字主妇”考虑的就是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如何成为具有再生产性的劳动,这个概念实际上用家庭主妇的处境类比了互联网内容产销者每天的处境。布鲁克·达菲(Brooke Erin Duffy)和贝卡·施瓦茨(Becca Schwartz)[30]对新媒体工作招聘广告的研究发现,理想的数字劳动者需要从事线上线下全天候的灵活的情绪管理,其日益具有女性化(feminized)的特征,这些工作对于互联网经济来说不可或缺,却在整个互联网处于边缘化、不可见、低收入的地位。实际上,就业市场性别歧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数字平台制造更多众包和零工岗位的大背景下,这些工作确实更多地由女性承担,她们更容易成为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31]所说的“不稳定无产者”,从事不稳定、无社会保障的工作。
新自由主义的个体企业化和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为“甘愿劳动”(aspirational labour)[32]提供了温床。“甘愿劳动”中,数字技术应许阶层跃迁,刺激人们投入时间、精力、情绪与心智劳动以达成自我实现,塑造不停歇、自我精进、雄心勃勃的劳动主体。达菲认为,“甘愿劳动”是一种高度性别化、前瞻性、企业家式的创造性劳动,不过她对这种劳动的性别变革前景持消极态度,因为大多数这类劳动不会变现,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获得算法和流量的垂青。
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变迁是社会科学研究绕不开的语境,我国的媒介与性别劳动研究也突出了这一问题的在地性。曹晋[33]较早地研究了上海家政女工通过手机异地履行母职的再生产劳动。此外,沿着“情感劳动—数字劳动—数字女工”这一主轴进行的粉丝研究也不失我国媒介技术与性别劳动的特点,但大多数粉丝研究过早接受了“剥削”“异化”的论断,因此受困于“结构剥削/能动反抗”的框架之中。
综上,技术显然并不是性别中立的,以往的研究指出,性别与技术的相互建构涉及文化与物质两个层面的实践,技术不光影响性别关系,使其得到改变或延续,而且技术内部也有性别的纹理与社会其他的政治经济安排相咬合,使技术显露出某种性别偏向,两者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缠绕的“浮现”(5)原文为“emerge from”。[34]。
三、 近年国内外性别与技术研究的概况
本文一共选取国内外7种期刊的188篇文章作为样本,其中国内19篇、国外169篇。虽然此样本没有穷尽国内外性别与技术相关的所有高质量研究,但抽样刊物在媒介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和性别与技术研究方面较为专业,能够集中地反映目前国内外性别与技术研究的动态。
通过对188篇文章的梳理,我们能够发现国内外研究在议题和议题多样性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别气质和亲密关系商品化在国内关注度更高,国外在关心多元议题的同时,向数字女性主义运动和自我赋权集中,前者的议题处于公私混杂的状态,而后者则展现了更为突出的公共性特征。
(一)国内研究近况:二元性别气质与亲密关系的数字劳动
国内研究集中于数字技术与性别气质和亲密关系的数字劳动。首先,性别气质与数字技术结合,拥有了更为灵活的操演方式。再者,性别气质的数字操演实际上使得亲密关系的数字劳动一并膨胀。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分析,对身体的性别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和资本增殖的重要步骤。在这个过程中,众多的性话语都在推动性别化的劳动者主体的产生,由此产生更多的消费欲望,何春蕤[35]在其分析美国性革命的文章中将这种欲望称为“情欲生产力”。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突增的性化的女性身体形象以及女性气质的话语正是市场经济催生的性话语的一部分(6)关于这部分的论述,可参见潘毅所著《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任焰译)第五章和第六章对打工妹的情感与性、消费与欲望的呈现。。国内研究呈现的亲密关系的数字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二元性别气质的操演,甚至这种操演也是劳动的一部分。
具体就性别气质而言,国内文献集中于数字自我呈现和数字生产劳动这两个场景中的性别气质。在男性气质方面,奶爸在育儿自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反映出中国式理想父亲形象的变化与父职实践的“混合状态”[36]。朱琳和袁艳[37]讨论了在AI儿童陪伴机器人的设计过程中,高科技产业中的“男性主导”性别脚本如何赋予无性别的AI儿童陪伴机器人“男性”的性别,男性工程师又如何因为这个工作对自己基于父职的男性气质展开了调整。数字技术在直播和有偿虚拟陪伴方面倒转了男性作为主体进行消费、女性作为客体提供服务的权力关系,让男性成为被凝视方[38],同时,亲密关系劳动的“女性化”与男性气质脚本的冲突使“虚拟男友”这类工作的从业者面临污名化的劳动困境[39]。
在女性气质方面,有关农村女网红[40]、城市中老年女性[41]使用数字技术进行自我呈现的相关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增添了城乡、阶层、年龄等交叉性。对女外卖员的研究则更注重女性劳动者在平台劳动机制下的性别气质“越界”[42],甚至呈现了女外卖员如何操作性别气质从而在工作中脱颖而出[43]。
在性别气质研究中,两性气质“混杂”是一种常见的状态。这种“混杂”状态在目前的研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从自我呈现而言,数字技术给性别气质带来的是更为多样且便利的“展演”工具;二是从劳动控制的角度,它使得“演”成为一种必要的策略和资源。不过,面对自我呈现和劳动中日益增加的“表演”成分,我们不能单以“真实”为价值出发去判断“演”,而应该基于巴特勒的分析看到“演”对现实的建构。
然而,性别气质的“混杂”在不同性别的主体身上折射出不同的情感。总体而言,经济发展和数字技术帮助女性实现了性别气质“跨界”,尽管她们有时会感受到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变化之间的拉扯,但参与其中的女性自身与社会并没有对“女性气质的丧失”呈现出过度的焦虑。相反,社会对“男性气质的衰落”更为焦虑,对男主播和虚拟男友情感劳动的污名化以及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对“好父亲”和“好男人”的再定义,都是男性个体、集体和社会在这种焦虑之下生产的话语与实践,它可以表现为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争议[44],也可以表现为中产男性在柔性化父职中展演的阶级区隔[36]。这看似是对“何为更好的男性”的协商,但其内部的权力动态调整也可以作用于对外的权力一致,即确立男性气质的合法性。集体无意识对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衰落所表现的焦虑程度的不同,恰恰揭示了男性气质与男性认同在性别霸权系统中的基底作用,正因为男性的主导地位,所以“男性气质”是绝对不可失去的,反复协商和确立“男性气质”这项认知工作才显得重要且紧迫。
我国近年来的另一个研究热点是亲密关系的商品化,这类研究都会自觉地回顾数字劳动的概念。情感劳动串联起了我国性别与数字劳动研究的线索,虽然如前文所述,这一领域的研究深受近些年国外性别与数字劳动研究的影响,但国内研究关注的人群及其表现具有我国的特殊性,比如女主播、女外卖员、粉丝中的“妈粉”、虚拟恋人等。女主播亲密关系的商品化延续了“情感劳动”女性化的特点,而且数字技术展现出对女主播性别和劳动更深刻的异化[45-46]。对女外卖员的研究同样发现,女外卖员具有女性特质的情感劳动是她们在行业立足并做出业绩的性别展演策略[42],也是对平台劳动机制的一种协商[43]。对“妈粉”的研究体现了国内粉丝研究的细分化[47],但仅从隐喻层面体现出这种情感劳动和其他粉丝情感劳动的区别,不足以支撑“数字母职”这个类比,反而削弱了“母职”这由父权制所规定的无偿劳动与商品化有偿劳动的辩证关系,化约了数字劳动与“母亲”两者交叉所具有的厚度。
部分研究考虑了数字劳动中的性别对调,即女性消费、男性劳动的现象[38-39]。关于这一现象,女性主义学者倾向于认为在私有制下,长期以来的性别结构导致了女性用自己的情感从男性手中换取财富和资源的“商品化”现象,但数字技术将亲密关系无差别地“商品化”,它允许男性提供亲密关系商品以供女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单向的性别权力。不过,不应当过早地欢呼“男色消费”,也不应该用“女性凝视”完全对标劳拉·莫维(Laura Mulvey)[48]提出的“男性凝视”——女性使用昔日男性用以规训女性的目光观看男性,这会不会仅仅是男性目光的延伸?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她经济”固然支撑了“男色消费”的崛起,但我们仍需质疑这种由资本主义消费建立起的主体性是否稳固?是否具有解放性?
在欢呼数字技术对性别权力的调转前,需要认识到亲密关系商品化的背后,是技术资本切实掌握着一系列可将亲密关系商品化的数字技术,它为使用者提供了操纵个人信息可见性[49]和操演个人形象的技术手段,同时通过算法隐秘地控制人们的亲密关系商品生产。因此资本对数字技术的所有权,或许才是日益孤独的现代人不可逃避的问题。
最后,目前来看,研究中非男即女的视角容易使研究者陷入性别二元论,变成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性别社会建构论。男性的女性化就是“新的男性气质”?女性的男性化就是“新的女性气质”?如果数字技术仅仅是“对调”性别权力,在两种性别之间交换物质、情感和文化符号的筹码,那就正如德·劳瑞蒂(Teresa De Lauretis)[50]所言,关于性别的研究反而成为二元性别论的媒介,封闭了数字媒介再造性别的丰富潜力。赛博空间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解构性别并提供流动的性别符号资源,国内的媒介技术与性别研究却仍旧无法跳出性别二元框架,反而通过学术的可见性再度确认了经典二元边界,这种对性别与技术关系的问题化可能具有本土的特异性,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另外,在避免陷入性别二元论的同时,学界应该充分认识到性别给女性的数字生活带来的问题更为严峻,如亲密关系商品的出售者更多是女性,她们在数字就业中面临更多的不稳定性,也更容易遭到边缘化和性化,如完全从技术工作中脱离出来承担情感劳动的“程序员鼓励师”[51]以及不得不使用软色情吸引关注等。她们在数字世界也更为脆弱,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女性受到网络骚扰和网络暴力的可能性是男性的27倍[52],女性网友也灵活运用数字技术以规避这些骚扰和暴力,比如把用户性别修改成“男”,小红书女性网友给发帖打上“#宝宝辅食”标签(7)小红书社区女性无论是分享日常穿搭、妆容教学还是记录生活,都会加上“#宝宝辅食”这个标签,因为小红书的算法机制在进行个性化分发时,不会把此标签中的内容推送给男性用户,所以加上这个标签,女性用户就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网络性骚扰与性别暴力。等。这些现实情况,都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
(二)国外的研究:数字女性主义运动中的自我赋权与风险
国外的研究议题更为广泛,但也体现了向数字女性主义行动和女性使用数字技术自我赋权[53-54]的集中,这两个议题的研究占比接近样本中国外文献的1/3。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研究议题与性别暴力议题具有连带性。当国外学者讨论女性是否能够、如何能够将数字空间变为女性友好的空间时,也有大量文献在讨论数字空间中的厌女症,这些厌女症不光表现为女性在数字空间的安全与隐私问题,还表现为男权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相对抗的数字行动[55-59],社交媒体技术逻辑加强的家庭暴力呈现[60]与约会暴力娱乐化[61]也在讨论之列。
除了网络厌女症和女性反对性别暴力的数字行动,数字女性主义行动中的女性赋权与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对女性主义革命性的消解面向也是一对矛盾,这往往集中在对Instagram这一社交媒体的讨论上[62-63]。后女性主义是一种“女性主义的任务已经完成”的论断,它所蕴含的新自由主义自我责任制以及流行文化对“快乐的女性主义”的强调,在鼓励呈现高光时刻和展现自我的社交媒体时代,在社交媒体的女性主义运动中,实现了技术与文化的咬合(articulation)(8)“咬合”,也有学者将其翻译为“接合”,是斯图亚特·霍尔将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咬合”理论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提出的概念,用以阐释受众的解码。这一概念被Silverstone迁移至驯化研究(domestication),他提出了“双重咬合”(double articulation)来解释技术如何从物质和符号两个层面进入家庭生活的空间,参见Sonia Livingstone于2007年发表在 New media &society上的文章On the material and the symbolic:Silverstone’s double articulation of research traditions in new media studies。,恰恰容易导致性别平等前景的暧昧性与性别平等运动破产的风险[64]。这些研究留下了重要的洞见:不同的社交媒体具有不同的风格和功能,它们所能带来的女性主义表达与行动的偏向是不同的。
国外性别与技术的研究还体现了一贯的交叉性视角,其交叉性体现在种族[65]、年龄[66]和地域[67]等,FeministMediaStudies有一期专刊讨论了这些交叉性在算法偏见下如何造成了对女性言论的歧视性审查[68]和女性的多重脆弱性[69]。虽然如此,就少数族裔而言,国外对其交叉性的认识更多地集中在黑人,对于亚裔的讨论较为欠缺。相较而言,我国质量较高的媒介研究中涉及算法性别歧视的研究目前较少,唯一的一篇探讨了算法歧视对女性“白幼瘦”审美的驯化[70]。
跳出媒介研究,针对大数据和算法中的性别歧视,国外的数据及机器学习领域正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和模型解决其中的问题。也有女性主义的数据专家指出,对边缘和弱势群体进行女性主义的数据教育,才是实现弱势群体数字赋权,让数据技术能够服务社会公益的行动[71]。相较于媒介研究中赋权/控制的二元讨论,这种行动的视角显然开辟了第三个维度。
基于以上内容,本文指出了近年来国外媒介研究领域关注的数字技术与性别的重点议题,但这不代表其他议题未被讨论。重点呈现这两部分的研究,是因为这两个议题回应了较为紧迫的技术与性别问题:性别暴力在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给性别平等带来了新困难。同时,因为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violence against women)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中的传统,在新技术社会中保持对性别暴力的兴趣,也具有其历史连续性。
而且,这两大议题恰恰也是国内讨论所欠缺的技术与性别问题的重要公共面向,具有公共价值。目前,我国的网络暴力问题在不断地制造悲剧,成为难以根治的现实问题。由此深入研究网络暴力中的性别维度显得迫切且必要。
(三)国内研究的未来方向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对数字技术与性别气质的阐释,总体上坚持了性别与技术的互相建构观点,对劳动这一领域,在技术与性别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上有所推进,并且体现了研究的公共价值。不过,国内研究更多的是用国外概念解释国内现象,需要更多的在地化视角以及对本土社会现实中交叉性的挖掘。同时,国内性别与技术研究较为明显地局限于性别二元论,跳出二元化思维,重思这种二元结构是如何被进一步建构的,重现我国技术与性别实践中更丰富且微妙的关系性,可为突破这种局限提供方向。
国外的研究重点关注赛博女性主义意义上的女性主体赋权与创造,并且没有停留在单纯歌颂,反而更多关注数字技术和网络性别暴力以及性别公正等现实而紧迫的公共议题。
虽然国内外近年来性别与技术领域的研究在议题上存在较大的不同,但国外的研究仍能对国内研究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其中包括对网络性别暴力的问题意识,还有使用数字和智能技术以达到性别公正的行动。实际上,我国也并不缺乏将这两者进一步问题化的实践与理论基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妇女学界和在地化妇女运动,通过媒介传播进行了大量反对针对女性的暴力、改善性别不平等现状的实践与知识生产[72]。
总之,本文重申在关注新技术与性别问题时应具有历史性视角:在数字和智能技术中讨论性别,不能认为它必定能为性别图景带来断裂式的突变,而是要关注技术建构中绵延的性别论述。新技术不仅会延续性别中的老问题,还会带来新问题,若要期待新技术能够解决问题、改变现状,就必须对“性别化的技术”进行深入的问题化,反思我们以往和当下问题化“性别化的技术”的方式,比如已经固化的性别二元框架和结构/能动二元框架。通过文献分析,本文认为,我国传播学界有将技术与性别的讨论扩展至更为公共的领域的现实实践和知识生产基础,比如网络性别暴力和技术的性别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