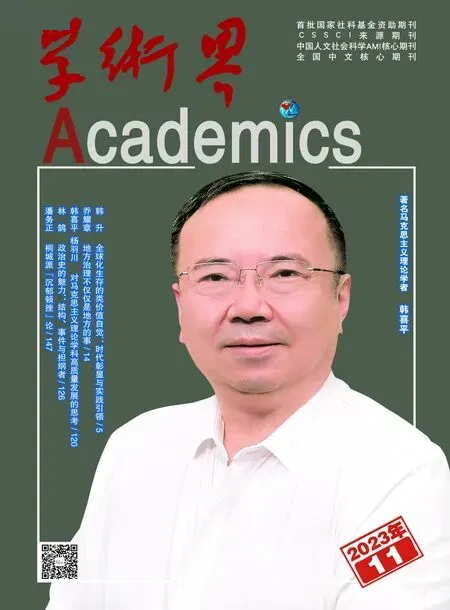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唐芸芸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文学自觉”说给人们一种既简单又复杂的印象。简单在于:它似乎已经被视为文学常识,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被直接运用在各类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表述和研究中,无数次重复引用、传播。而复杂则在于:“文学自觉”说支持者众多,且存在具体时代的分歧,同时反对者的观点也很犀利。我们发现,在研究者的往复论辩中,本来简明的“文学特征→是否‘自觉’”的结构变得越发不稳定。虽然人们容易提出明确的观点,但似乎谁也无法让对方完全信服。正是因为双方的论辩并非一路推进,而是往复交织的。部分同意或部分反对,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样的事实陈述也可能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还存在即使大部分持论相同,只因某一个分歧便分立两端的可能。似乎任何一个小问题都值得深究,头绪诸多,相当复杂。以至于现在很多研究者对之采取虽不认可却也避而不谈的态度。实则,在现实的文学研究中,研究者对“文学自觉”说的支持或否定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特征及其价值的认识,甚至会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又基于“文学自觉”说在一些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教材和大学课堂泛滥的实际情况,笔者将对此进行全面梳理。综合起来,“文学自觉”说若要成立,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第一,作为“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非常清楚;
第二,基本项之间产生合力,共同推进文学的发展;
第三,“文学”“自觉”的内涵和外延必须非常清楚,命题本身具有自洽性和连贯性。
我们要梳理“文学自觉”的问题,就需要对命题的具体内涵及其间之关系、命题本身的逻辑、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特征,以及研究者的思维方式等进行综合考察。
一、“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
“文学自觉”说由铃木虎雄首倡,〔1〕鲁迅先生不谋而合地发表演讲,〔2〕经由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美的历程》与“人的觉醒”联系并广泛传播,〔3〕以及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进行普及。〔4〕尽管此命题的提出者,或许带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或“渗杂了许多讥讽时事的成份”,〔5〕但由于命题本身自带的民族自豪感,天然赋予研究者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后世从其说者众多。很多研究者将之与“文笔之辨”联系起来,得出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纯文学”概念的结论,这成为“文学自觉”说最突出的效应。支援声中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为主流,另外有“汉代文学自觉”说,代表有龚克昌、张少康、詹福瑞等学者。〔6〕
主流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以作为大学中文系本科教材而传播甚广的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为代表,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对文学的审美有了自觉的追求。……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7〕后来的研究者去掉了汉代已实现的“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这一项,并加上“脱离政教”,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成立的基本项,概括起来,即脱离政教(个体意识)、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辞藻、声律、系统性理论的著作、对创作主体的关注等)等三个方面。
“汉代文学自觉说”提出的基本材料为《汉书·艺文志》列“诗赋略”引起的文学从学术中分离、明确认识汉赋这种文体的体制和风格特征、对汉赋“丽”的审美特性的考察、汉代文士化、汉人关注屈原的文学创作等。两相对比,“汉代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虽然也涉及到了个体意识、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但都是其中某个因素特别是与汉赋这一文体有关的呈现,这是因为汉代文学创作中的文体发展远不如魏晋南北朝文学,不具备进一步认识文学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的文体基础,所以缺乏相应的体性、丽辞、声律、用事等讨论。马草《时代嬗变与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再界定》一文,将评判标准细化为六点,特别强调“只有同时符合这些标准,才能称之为文学自觉”。〔8〕从基本项的完整及讨论的充分、深入出发,我们基本上可以推翻“汉代文学自觉”说。所以,本文主要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
事实上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文学自觉”说存在缺陷。如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认为“‘文学自觉’这个论断的内涵有限,歧义性太大而主观色彩过浓,因此不适合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主观判断来代替对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学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9〕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商兑》一文,强调不能以西方传入的“文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文学。〔10〕论文从批评“文学”观念的不对应来进行否定,釜底抽薪,甚是痛快。
既然存在概念不对应的先天缺憾,“文学自觉”说就应当是一个伪命题。但是,似乎纯粹以“文学”观念进行攻击,收获甚微。原因正在于,脱离政教(个体意识)、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辞藻、声律、系统性理论的著作、对创作主体的关注等)等这些被视为“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确实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真实存在的内容,只是我们要追问这些内容是否构成了文学自觉。我们要对“文学自觉”说进行检讨,重点不在于对这些特征的发现,而在于对其实质的发掘和价值的判断。在没有对这些基本项进行定性之前,我们似乎很难完全从概念的先天不足来推翻一个自带强烈民族自豪感的主张。
二、“杂文学观”下的审美特性讨论
“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既然被清楚地归纳为脱离政教(个体意识)、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辞藻、声律、系统性理论的著作、对创作主体的关注等),我们便可以对此进行一一考察。
作为文学自觉的基本项,文体细分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文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人们需要对各种文体的来源、流变、典范、作法等有较统一的认识,从而对其审美特性进行认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等,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征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已是学界共识。在对文体论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文心雕龙》中,虽然刘勰将诗、赋等现在划归为“纯文学”的文体放置于前,诏、策等现在划归为“应用性”的文体放置于后,但文体论均由原始表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敷理举统四个部分进行的,〔11〕对每个文体的考察步骤和目标都是一致的,对它们的价值、典范、源流都有所追溯。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杂文学观”。
而对于审美特性的发现及自觉追求,是“文学自觉”说的最有力证据。这些特征具体包括:情感表达、辞采、声律、用事、偶对、夸饰、练字等。因为这些因素与我们所谓“纯文学”的特征似乎不谋而合,所以,论者往往据此滋生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的关注具有某种先进性的兴奋情绪。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时人对这些因素的讨论,事实上是针对所有文体而言的,即包括了我们所谓的“纯文学”和“实用性文体”。
我们首先来看对情感表达和辞采的分析,以刘勰《文心雕龙》为例。他关于辞的总体要求是“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12〕这在各类文体中均有详述,如:赋之大体为“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13〕哀辞之“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14〕“诸子”则分论,如孟子、荀子是“理懿而词雅”,管子、晏子“事核而言练”,列子“气伟而采奇”等;“论”则“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15〕“檄”则要求“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16〕无论是所谓的“纯文学”,还是实用性文体,都因为文体的分别而对表现情感有不同要求,从而导致辞采的区分,并构成不同的体格特征,这些都形成了稳定性陈述,并基本为后世沿用。“文体细分”,也大致体现于此。但情与辞采的关联,并不是诗赋等纯文学的独特要求。
我们再来看时人对声律的讨论。一直以来我们可能误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声律的讨论只存在于所谓“纯文学”。这是持“自觉论”者最主要的论据,因为此时声律的讨论对后来成为诗歌高潮重要组成部分的律诗贡献极大。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将之总结为“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17〕句中不同声的字相交并,称为“和”;句末用同声字相应,则称为“韵”。时人关于声音的讨论,不但关注句末韵脚,更有价值的,其实是关注句中声音的规律。从声音中发现语言符号带来的美感,并试图找寻规律,确实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突破。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心雕龙》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表述:
《章表》: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18〕
《奏启》:必敛辙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19〕
章、表、奏、启等文体,与诗、赋、颂、赞一样,在声音上均要求达到“沈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20〕这是所有文体都具有的审美特性,是为共性。〔21〕
另外如用事、偶对、夸饰、练字等,也是针对所有文体进行的考察。就是说,无论是诗、赋、铭、颂、箴、赞、吊、诔,还是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文体,他们除了在情感表达和辞采上有区别之外,在声律、用事、偶对、夸饰、练字等方面,均受制于共同的规范。可见,时人关于审美特性的讨论,不仅仅在于诗、乐府等“纯文学”,而且还运用于“杂文学观”包含的所有文体。从对文体的涵盖和细分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杂文学的观念。而情感、辞藻、声律都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纯文学”文体,而是明确包含了对应用性文体的要求,所以并不能将之视为对现代概念意义上的“文学审美特性”的发现。那么,如果回归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现实,在“杂文学观”下“文学自觉”说是否成立呢?
三、声律未完成带来古律混杂与“文体细分”的内在矛盾
持论者往往将基本项一一分解讨论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出现,便断言“文学自觉”。实则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学发展并不是以单项组成齐步行进的方式,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任何一个基本项,都不应该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关联,产生合力,共同推进文学的发展。当深入考察这些基本项及其关系时,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认识也会更深刻。
如前所论,魏晋南北朝人在讨论声律、用事、偶对、夸饰、练字等方面,都是在寻求一种共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文学,一方面在文体细分上无微不至,而另一方面,又在寻求凌驾于所有文体之上的共同特征。说明当时的实际创作中,在具体的文体之上,还存在着一种可以归纳共同规律的创作方式。
我们仍然从声律入手进行分析。为了更好地实现声音和谐,人们总结出了各种禁忌,称为“病犯”。而这些“病犯”,也是针对所有文体的。在空海和尚汇编的《文镜秘府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被归入“笔”类的无韵脚的文体,与有韵脚的“文”一样,同样存在病犯,都要求符合句中宫商规律,而且由于“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相比于文,笔的病犯,还多出了隔句上尾和踏发二种。〔22〕显然当时明确存在一种具有统一声音规律的、可以跨越“文”“笔”、渗透到各种文体中的创作方式。具备这些特征的,正是骈体。南朝时期越来越盛行的骈体创作,已经成为各体文学的创作基础。骈体讲究句中声律,而句末是否押韵视具体文体而定,押韵者为“文”,无韵者则为“笔”。笔者在《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讨论。〔23〕
所以,尽管魏晋南北朝人在关于声律的讨论中,提出了声调和谐的审美特性,并逐渐摸索出一些规范,确实是“自觉追求审美特性”的重要表现,但这是建立在“骈体”的审美特性基础上进行的,是一种“整体”的审美特性,并不单单指向任何一种具体文体,包括诗,更没有区分出“纯文学”。即并不存在与文体特征相适应的某种声音规律,也不以声律不同来进行文体分别。立论以骈体的审美特性为基础,而不是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这是南朝时期大规模的声律讨论却最终未形成声律与文体细分的结晶——律诗这一文体的根本原因。
由于南朝时期最终未完成声音规律的探讨及律诗的定型,此时诗坛的状况便是古律混杂。声音的深入讨论和实践,带来的竟是文体不纯的结果。由声律问题导致的文体混杂,稀释了“文体细分”的价值。刘勰显然没有提示这一点。而锺嵘强调古人之词,被之管弦,乃“重音韵之义”,“与世之言宫商异也”,〔24〕就是说四声八病的讨论与古代入乐传统并不衔接,并非自然声调。锺嵘反对新兴的宫商讨论,并非所谓“保守派”,实则是为了保证五言古诗的诗体纯粹。
因此,时人对声律、用事、偶对、夸饰、练字等方面的审美特性的发现,均是以骈体为对象,而不是以具体的文体为对象进行的。作为审美特性的这些因素本身并不具备文体的分类特性。而各个因素之间,也没有更多的关联性。它们都是各自独立面对整个骈体写作。所以,一方面,基于文体细分,人们认识到存在不同的文体,具备不同的辞采与情感表达;而另一方面,又由于骈体写作对各类文体的同化,人们在积极寻求骈体写作的共性。
所以,在“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对审美特性的发现及自觉追求”中,就存在不同的讨论基础:辞采和情感表达是以具体的文体细分为基础的,而其他的因素,则是以各类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的讨论为基础。后者导致“文体细分”与“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严重割裂:“文体细分”显然是追求细致有别,而“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因素中除情采外,体现的是各体文学的趋同。“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的趋同性制约了“文体细分”推进文学发展的力量。两个基本项在一起,产生的不是合力,而是分离力。“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并不成立。
四、“文学自觉”说的逻辑黑洞
不仅“文学”的观念无从落脚,“自觉”的定义其实也是无法落实的。“自觉”是一个现代学术概念而非历史概念,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不具备历史语境,所以我们对其价值必须有明确的规定。一般而言,研究者都认定“自觉”必须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力量。那这股力量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定义为“自觉”呢?
即使“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比较明确,但究竟以什么方式出现,出现多少,可以算作“自觉”,却是一个未确定也无法确定的问题,所以才在“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之外,还有“汉代自觉说”“春秋自觉说”等。对于这些所谓的文学自觉的某些因素,究竟是以“最先出现”作为依据,还是以开始出现较集中的讨论便可将之置于一个突出的地位呢?如果以“最先出现”而言,《诗经》中确实有篇章已经出现了明确的创作意识,更不用说楚骚了。如果是以“比较集中”而言,那程度该如何定义?是否可以以出现对声律、辞藻等对审美特性并不成熟的关注、并未完全定型的文体细分,以及有限的脱离政教因素,便可以将魏晋南北朝定为“文学自觉”的时代?
对于“自觉”的价值判断,我们是要放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的价值来看待的,而不应以是否具有“现在”的某些文学观念或因素来进行比附。假设“自觉”成立,便意味着此时将文学从某种蒙昧、混沌的状态中唤醒。那么,文学史就应该被分为“前自觉”(蒙昧)时代,自觉时代,“后自觉”(兴盛)时代。〔25〕并且,自觉时代所“自觉”的因素,将是开启“后自觉”时代兴盛的重要原因。
但我们来看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发展的事实。首先,无论是哪一朝代,人们都会将文学源头追溯到诗骚。即使是南朝这样一个被视为离经叛道最明显的时代,锺嵘也是将源头追溯到《国风》《小雅》和《楚辞》,来提高新兴五言诗的地位。“推源溯流”本就是古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如果说魏晋南北朝以前是一个不“自觉”的时代,便等于说先秦、两汉的文学成就及价值比不上魏晋南北朝。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也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事实。所以,所谓“前自觉”的蒙昧时代,并不存在。
而至于“后自觉”的兴盛时代,确实是文学史事实。但是,“自觉说”的几个基本项,真的与后来的文学兴盛相合吗?
“脱离政教”是非常重要的基本项。这时期显示出来的“礼义”因素弱化后的情感极致抒写,确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关于性情与道德关系探索的宝贵经验。但在中唐道统回归后,政教传统一直便是文学发展的规约,只不过松紧程度不同而已。“自觉”的价值,必定要符合整个文学史主流,为后世作指引。而文学史的事实是,后世文学仍然强调文学对现实主要是政治的观照,甚至对道统的回归,这显然与“脱离政教”相抵牾。
而文体细分,特别是诗体细分的工作是在唐代完成的。即对各种诗体的审美特性、情感表达等“体格”的规范和实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讨论给出的启示有限。至于声律,更是一个未完待续的工作。即使是与文体细分相适应的对辞采、情感的重视,也并没有给后人提供一个适度的典范,反而招致“嘲讽月弄花草”的批评。要说到对情感的强调,《诗大序》便有“吟咏情性”的概括,而后来人们也是多在“性”与“情”二者关系中进行衡量。至于作为系统性文学理论论著代表的《文心雕龙》,仅就其文本形式来说,属于子书传统。〔26〕“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27〕这样的“系统性”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其成书模式也未对后世产生典范性影响。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作“自觉”的各个基本项并没有完成对后世文学兴盛的各部分意义并构成决定性影响。
实则,如果文学史真的按照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文学各体都以骈体创作方式为基础,均衡重视各体的辞采、情感、声律、用事、偶对、练字等,缺乏对诗歌内部文体分别的考量,在情感与道德的处理上走入误区(如宫体诗),那么,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番景象。至少如果延续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这些审美特性思考的文体基础,骈体将成为后世最基本的创作方式。所以,无论是从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对文学传统的接续来看,比起声律、辞采等“文学自觉”说的基本项,唐人对创作主体与对象的交流方式及呈现方式的把握(兴寄、兴象),对表现效果的追求(韵外之致、取境)等,之于文学兴盛的意义则更为显著。
那么,将“自觉追求审美特性”建立在细分的文体基础上,由此超越了魏晋南北朝的唐代文学,是否可称为“文学自觉”呢?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商兑》一文认为:“在传统中国士人看来,唐宋相比较魏晋南北朝而言,才是‘文的回归’与‘文的自觉’,只不过唐宋人利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积累起来的艺术技巧与形式经验去完成‘文的回归’与‘文的自觉’的文化使命而已。”〔28〕唐朝建国之初就强调以史为鉴,试图恢复文学的儒学立场。陈子昂提倡的兴寄,正是适应盛唐诗人表达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征服欲望,表达对政治秩序及其实现的干预。更何况还有后来白居易与政治革新相适应的诗歌讽谏说,和韩、柳的古文运动对文与道关系的强调。这些都昭示了与“纯文学”概念的距离。
所以,“自觉”的概念本身不具备自明性,“文学自觉”说的命题缺乏逻辑自洽,这是一个伪命题。
五、“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不成立的深层原因
之所以研究者对脱离政教(个体意识)、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辞藻、声律、系统性理论的著作、对创作主体的关注等)这些基本项持续产生兴趣,是因为它们同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重视。此时的文学确实处于一个丰富、复杂的发展阶段,其中有归纳、有孕育、有偏执,这才构成一个精神史上极自由、极富热情的时代。
发扬于先秦、总结于汉的传统儒家文学思想,已然包括具有“普遍性、稳定性与专业性”的文学命题和范畴,涵及本质、创作、接受,其中最被重视的是文学功用。先秦两汉特别强调政治教化。与前代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与政教的关系确实相对松懈,将重心由文学功用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如锺嵘对“兴”的重新阐释,由“引譬连类”的表现技巧到“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表现效果;〔29〕又如对神思、风骨的讨论等。但也并未彻底颠覆传统的儒家文学观,所论也并没有超出原有命题和范畴。
就目前现存的资料看来,南朝文学思想家对本时期新出现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并未投之以足够的理论热情。如他们对新兴的山水诗中情景关系如何实现并没有过多讨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和锺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30〕强调的是物之起兴和“物”在文本中的呈现,但情景关系的文本呈现并未完成;又因为对“诗缘情”在表达男女之情方面缺乏理论限制,所以导致宫体诗的走偏,致使后人对诗缘情概念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后人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价值判断的偏失。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传统诗学的核心观念并没有给出更多回应。除了刘勰对“文与道”关系的讨论,将荀子的征圣、宗经进行具体阐发并作为“文之枢纽”外,其他如温柔敦厚、兴观群怨、“时运与诗运”关系等传统文学核心命题,他们大都避而不谈。或许正是这种避而不谈,成为研究者视之为摆脱政教获得自由的证据。但我们都清楚,这并不是诗人主体的主动积极的取舍行为,不是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人们意识到文学与政治关联过于紧密而有碍于文学性的展现来进行的有意去除。如果儒家礼义的限制仍然存续,但诗人们坚定地选择去除礼义的影响,这才是自觉的表现。显然,此时儒家礼义限制的松动,有情论的重视和宣扬,只是当时开始有机会体认自我的士人生态的一种反映。所以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学应该是独立的。而一旦政治体系与思想体系重新融合无间,文学便很快又会被重新苑囿其中。正因为如此,导致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缺乏与传统核心文学观念的承接性论述,及在此基础上与情感、丽辞、声律、文体细分等问题的结合。情感与政教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文学创作中相对脱离政教的经验,演变至嘲风月弄花草的极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机会。
当然我们不能苛责古人,这与文学发展的阶段性有关。在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中,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讨论已然相当精彩。但归根结底,与主张玄远超迈、物我泯一,希冀填补儒家独尊地位失落后士人理性依归的空白,最后以失败告终的玄学一样,这是一种尝试的精神,赋之以“文学自觉”的意义实在不妥。
六、结 语
从对文体的涵盖和细分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杂文学的观念。而情感、辞藻、声律都不仅仅是针对所谓的“纯文学”文体,而是明确包含了对应用性文体的要求,所以并不能将之视为严格意义的对“文学”审美特性的发现。而情感、丽辞的强调虽基本与文体细分形成稳定性陈述,但时人对声律的讨论,却是以骈体的审美特性为基础,导致律诗定型无法完成,在“文体细分”的整体态势下出现了古律混杂、诗体不纯的现象。对用事、练字、夸饰等的讨论同样如此。“自觉追求审美特性”与“文体细分”两个基本项之间存在矛盾,“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并不成立。而由于审美特性的追求与后世文学的兴盛关联有限,“文学自觉”概念本身存在逻辑漏洞,“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实为伪命题。
我们应该反思,是否真的需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的途中,寻找一个“自觉”时代,让其承担使整个中国文学摆脱某种蒙昧,从而变得昌明的责任?其实否定“文学自觉”说,丝毫不影响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价值评价,更不会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不能以“以后”文学应该独立,来希冀或要求“以往”的文学独立。〔31〕这种将古代文学传统始终立于“他者”位置,带着根深蒂固的俯视视角的观照,似乎并不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承认古代文论具有自身特色,并作出公正评价,才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
注释:
〔1〕〔日〕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38页。铃木虎雄1920年在日本《艺文》杂志上发表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提出“魏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1925年论文收入其《中国诗论史》第二章(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此书直到1989年才有中译本。
〔2〕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90-491页。鲁迅1927年7月在广州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收入《而已集》。鲁迅提出此说,是否受铃木虎雄的影响,不得而知。
〔3〕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7-108页。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色,自然与“人的觉醒”有关,是“人的觉醒”在文学上的反映。但“人的觉醒”并不会自然带来“文学自觉”。“人的觉醒”,可以反观自身,并有助于发现“美”。最典型的便是山水等景物被取消了作为道德、寄托的附庸,而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尽管与传统的“物感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写山水不必先从道德入手,或以道德为惟一依据。不过,“发现美”远不足以构成“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因为不仅仅在文学,其他如书、画、人物品评均如此。从“人的觉醒”进入的“文学自觉”说,是把魏晋南北朝人对对象独立审美价值的发现,与“文学独立”混淆了。
〔4〕〔7〕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二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5〕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6〕龚克昌:《汉赋——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文史哲》1988年第5期。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詹福瑞:《文士、经生的文士化与文学的自觉》,《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另有孙明君:《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反对将建安与魏晋合一,强调“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此外,还有“春秋”自觉说、建安自觉说、宋齐自觉说、南朝自觉说等。
〔8〕马草:《时代嬗变与文学自觉——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再界定》,《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概括为:“其一,文学创作成为士人自发的普遍性活动,出现了数量庞大的作家群体;其二,文学用以抒发个人情志,成为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构成;其三,文学对自身存在目的、价值的探讨,建构起本体层面的存在依据;其四,文学对自身审美特征的确认与强调,文体走向完备,建构起诗性的艺术语言及其体系;其五,涌现出众多经典作家、作品,建立起文学谱系网络;其六,数目可观的专业性批评著作的出现,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论体系,生成了若干具有普遍性、稳定性与专业性的文学范畴和命题。”是对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标准的细化。
〔9〕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0〕〔28〕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商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二十五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51页。观点深化于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再探析》,《文学评论》2023年第5期。
〔11〕〔12〕〔13〕〔14〕〔15〕〔16〕〔17〕〔18〕〔19〕〔20〕〔27〕〔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64、319、64、102、161、185、301、202、214、300、153页。
〔21〕以是否押韵脚简单分出文、笔两类,太过笼统,并不属于“文体细分”。而刘勰在《宗经》提出的“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镕裁》提出的“三准”:“设情以位体,酌事以取类,撮辞以举要。”《附会》提出的“四事”:“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知音》提出的“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和“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等都是针对所有文体而言。(以上引文分别出自〔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第21-22、326、422-423、495-496页。)
〔22〕“隔句上尾者,第二句末与第四句末同声也。”“踏发(废音。)者,第四句末与第八句末同声也。凡笔家四句之末,要会之所归。若同声,有似踏而机发,故名踏发者也。若其间际有语隔之者,犯亦无损。”〔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59-487页。
〔23〕详见唐芸芸:《从“笔”之病犯论南朝“文笔说”》,《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24〕〔29〕〔30〕〔梁〕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42、47、1页。
〔25〕刘文勇:《“文学自觉说”商兑》:“‘魏晋文学自觉说’成立的话,那么就会得出魏晋南北朝以前的文学和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文学不是自觉的而是‘文学的黑暗时期’的结论了。”显然不确。“文学自觉”之后的时期,应称为“后自觉”,而不是“非自觉”时期。“后自觉”时期将“自觉”时期的讨论深化、修正,并发扬广大,甚至实现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这才是讨论“文学自觉”的意义。
〔26〕邬国平:《〈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1〕朱光潜:《文学院课程之检讨》,《朱光潜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7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