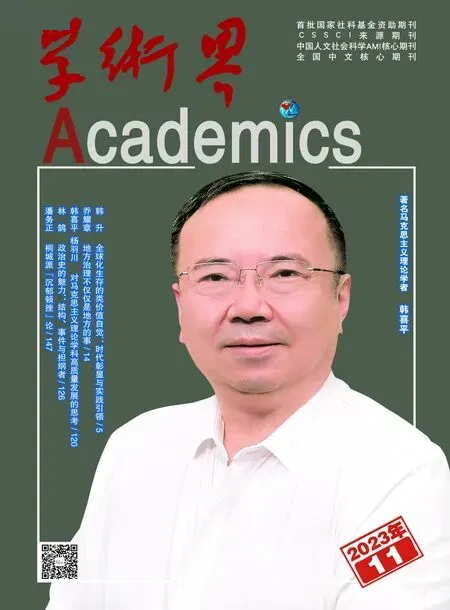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陈友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安徽 合肥 230051)
说到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当然离不开他创立的“豪放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苏轼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再变”之功:“词至晚唐五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1〕
至于苏轼“豪放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探究。清代田同之《西圃词说》和蔡崇云《柯亭词论》均认为这与苏轼的秉性、襟怀有关:“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胸襟有涵盖一切气象……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2〕当代学者杨忠也认为苏轼的豪放词与他的“人生豪气”有关,“苏轼的人生豪气经过漫长的积聚之后,终于在他四十不惑的时候勃发了,形成了千古绝唱的豪放词。”〔3〕近年来,学者们更注重将苏轼豪放词风与他的政治遭遇、生活道路结合起来考察,如游国恩等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史》评价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念奴娇·赤壁怀古》:“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生如梦’的消极思想;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也认为《念奴娇·赤壁怀古》与作者的黄州之贬有关:“词中描绘了赤壁的雄伟壮丽景色,歌颂了古代英雄人物周瑜的战功,并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感慨。”〔5〕柯大课的《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初探》和《苏轼豪放词形成的主观因素》则分别从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作者认为客观原因是“在北宋中叶的时代条件下产生出来的,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土壤中滋生的”,“是国势日微,积贫积弱,每况愈下。一切爱国有志之士都在寻求出路,要求变革”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上的表现。“时代在呼唤着崭新的词风,豪放派的词正是在改革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潮中应运而生的。”〔6〕至于主观上,则与苏轼的“理想抱负、生活道路、意志性格等心理特征,以及所受的儒释道思想影响,本人的文学主张等方面”〔7〕密切关联。
这些分析都有道理,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确实与这些方面皆有关联。但说实在的,这些评说又给人不够精确,乃至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那种既是主观又是客观,每一“观”又分为诸多方面,说得很全面周到,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有说。其实,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和本人的气质、经历不无关系,但形成这种词风的直接触发点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
一、“熙河大捷”促使苏轼豪放词风形成
首先,我们对苏轼的豪放词风作一界定。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品对诗歌的豪放风格是这么说的:“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气,处得以狂。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满,万象在旁。前招三辰,后引凤凰。晓策六鳌,濯足扶桑。”〔8〕司空图用的是中国古典诗论传统的比喻象征之法,如果直接道破,那就是充满内在豪情,涵咏万物、包容天地,外在表现为狂放的气势。苏轼本人对自己创造的这种风格也很得意,并说得比司空图具体得多,这就是被人们乐道的《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9〕
词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艳科”。从题材上来说多表现宫内或深闺妇女的发饰、容貌、体态、心理,或是士大夫的伤春、伤别,就是到了词体第一次革命的柳永手中,也只是扩大到市井、歌妓和自己的离愁别绪;表现手法上形成了一种狭深的文体,多用抒情,尤其是抒发曲折层深的内心世界。柳永的功绩是在此之外增加了铺叙和白描,适合一个“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但到了第二次革命的苏轼手中,其豪放词作则“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10〕“于柔情风月之外,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农事、悼亡诸类,均可入词。”〔11〕抒情、议论、叙事、状物,无一不可。这篇《与鲜于子骏书》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是描绘一个“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的壮阔射猎场面,“颇壮观也”。因此歌者也不适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应该是“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可见,在苏轼的心目中,他新创的豪放词风格应该是视野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底气则是“壮”。苏轼豪放词的这种风格也为当时的读者所认同。据南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12〕
词在当时是“艳科”,适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位幕僚说苏轼的豪放词则宜关西大汉,手拿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当然是对苏轼豪放词从题材到手法的揶揄。但苏轼却“为之绝倒”,非常认可。认为这位幕僚对他的豪放词与流行的婉约词的区别,说到了点子上。
当然,苏轼豪放词的内涵并不止于视野广阔,气象恢弘雄放。苏轼本人对此亦有补充,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还强调:“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13〕他认为,“豪放”的内涵所产生的“新意”不仅是题材的拓展和手法的多样,还应该有“妙理”。所谓“妙理”应该是深邃的理性思考,就像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表达的那样:“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也是豪放词应有的内涵。
苏轼认为豪放词还应该有一个内涵,那就是在表达方式上无论是夸张还是狂放,都应该出自内心,无拘无束,自然而然。他在《答谢民师书》中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4〕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在《文说》中又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15〕
根据上述对豪放词尤其是苏轼本人对豪放词的定义,苏轼词作中豪放词并不多,包括一些阐发哲理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乃至“以健笔写柔情”的花间风月之作,如《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等在内,共50多首,这在其340多首词作总数中仅占七分之一左右,其大部分还是婉约词作,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歌妓的风月之作就有180首之多。所以我们可以称赞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者,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位豪放词人。如果我们将这50多首豪放词的创作时间排列一下,就可以发现,包括其发轫之作和绝大多数豪放词代表之作皆在熙宁七年(1074)前后和元丰四年(1081)前后这两个时间节点上,约占苏轼豪放词作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这两个时间节点又都和宋与西夏的战争尤其是熙宁六年(1073)“熙河大捷”和元丰四年灵州、永乐惨败密切关联。先说熙宁六年“熙河大捷”对苏轼豪放词的产生和创作的影响。
苏轼生活的时代,北宋的主要外患,一是北方的辽,另一就是西北的西夏。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北宋与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后缔结盟约“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送给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此后宋、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380次之多,辽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16〕但与西夏的军事冲突却接连不断。自仁宗宝元元年(1038)元昊建立大夏国以后,夏就成为宋朝西北一带主要边患。据史载:在1040年至1042年这三年中,北宋与西夏接连发生三次大战,皆以北宋惨败乃至全军覆没而告终。三年之内三次惨败,于是只好讲和。庆历四年(1044),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宋朝只好承认元昊自立的大夏国,册封元昊为夏国国主,每年“赐”夏国绢13万匹、茶2万斤、白银5万两。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史称“庆历和议”。
这种屡战屡败的局面,直到神宗熙宁初年王韶的出现才得到改观。王韶,嘉祐二年(1057)进士。为人足智多谋,富于韬略。熙宁元年(1068)上《平戎策》,提出“收复河湟,招抚羌族,孤立西夏”的方略,〔17〕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又提出了北宋统治者最急迫的西夏问题的解决策略,其目的与神宗、王安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因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王韶被任命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职,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后改任著作佐郎,仍提举西北军务。神宗志在收复河陇,于熙宁五年(1072)修筑古渭城,组建通远军,以王韶知军事。王韶奉神宗之命经营西河(今陕西东部沿黄河地区)。王韶的战略是“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指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三角地区,古称‘三河间’)”,〔18〕避开正面战场,绕道西夏的西南腹地湟州、西宁州一带,从背后进袭。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韶的这个方略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西夏兵力主要布置在以兴庆府(西夏国都,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元昊以七万兵力守护兴庆府,以五万兵力镇守东南的西平府,五万兵力驻守西北的贺兰山。而西南的河湟地区仍是被吐蕃、西羌等少数民族控制,元昊认为是个缓冲地带,没有重点设防。王韶避开东、北正面战场,进袭河湟,正是抓住了对方的弱点。熙宁四年(1071)王韶成功招抚吐蕃俞龙珂部,俞龙珂“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19〕宋神宗赐名包顺,使其永镇岷州(今甘肃岷县),受此事影响,远近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北宋,前后有二十余万口,北宋由此所辖疆土拓展了一千二百里。通过对秦州蕃部的招抚,宋廷基本上控制了这里的局面。熙宁五年王韶在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城)和乞神坪(今甘肃渭源西南)筑城,进兵至抹邦山,与吐蕃蒙罗角、抹耳和水巴等族对垒。〔20〕熙宁六年三月,王韶一举攻克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市东北),王韶被擢升为枢密直学士。四月,攻占诃诺木藏城(今临夏县南)和香子城(今甘肃和政县)。熙宁六年闰七月,攻占武胜军,朝廷改武胜军为镇洮军,迁王韶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八月王韶率部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内。前后行军五十四天,跋涉一万八千里路,平定五州之地,招抚吐蕃诸部无数。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幅员两千里,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招抚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口。包括熙、河、洮、岷、叠、宕六州之地全部收复,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这也是北宋王朝在结束十国割据局面之后,八十年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21〕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王韶采取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取得了“凿空开边”〔22〕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他“用兵有机略”“每战必捷”。十月,朝廷改镇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县),并置熙河路。任命王韶以龙图阁待制任熙州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河战役”。
必须指出的是:王韶的被重用和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与神宗皇帝的信任、正在主持变法图强的王安石的支持,以及正在推行的“熙宁变法”所激起的国家朝气密不可分,而且熙河大捷也与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互动。
熙宁四年八月,宋神宗接受王韶《平戎策》,设立洮河安抚司,让王韶负责招抚蕃人。对此,主持军务的枢密使文彦博提出异议,建议谨慎行事:“如曩时西事,初不谓劳费如此,后乃旋生。”但神宗坚持己见,反驳说,此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朝廷的策略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西事本不令如此,后违本指,所以烦费。”〔23〕力挺王韶的王安石亦云:“如起兵,事则诚难保其无后患。若但和附戎狄,岂有劳费在后之理?”〔24〕王韶计划的第一步——招安河洮地区的木征及其他蕃部。此事开始并不顺利,木征不仅没有如王氏设想的那样投靠大宋、成为宋朝招抚蕃部的助手,反而对宋朝介入河湟事务极具戒心,极力抵制。他扬言,如果王韶不停止招抚蕃部,他将转而联合董毡对抗宋朝。消息传至宋廷,文彦博担心如果继续招抚,将会爆发军事冲突,“若木征果来,须与力争,力争则须兴兵”。王安石仍然继续支持王韶的行动,表示打仗也在所不惜。神宗亦附和云:“有天下国家,即用兵亦其常事。”〔25〕“在王韶行军的进程当中,王安石还不断写信给他,告诉他在战争中应注意的一些策略,在精神上给予鼓励,使他得以奋勇地依预定计划行事。”〔26〕因此,熙河大捷后,“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27〕表扬王安石知人善任、力排对此非难的众议。
熙河大捷消息传来,举国欢庆。王韶也因收复河湟这个重大胜利饱受誉扬、名声大震,北宋政府“拜韶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资政、观文学士,非尝执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两子,前后赐绢八千匹。未几,召为枢密副使”,〔28〕并以“奇计、奇捷、奇赏”著称,被戏称为“三奇副使”。
这个时段苏轼的经历是:熙宁四年元月,时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因不满王安石新法中的一些举措,连续上书神宗皇帝表示反对,“荆公之党不悦,……命御史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29〕苏轼为避祸,也像司马光、欧阳修、尹洙等人一样,请求外任。但苏轼与司马光等人不同的是,他并不反对改革,而是对改革中的用人路线和部分改革内容如设置三司条例使、“青苗法”表示不满。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青苗不许抑配”。批评改革派的用人路线,“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二月,再次上书神宗皇帝,再次批评改革派的用人路线,“今议者不察,……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30〕“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31〕
但在对外政策,如对西夏的入侵,则与王安石、王韶相同,一直反对那种屈辱求和、苟且偷安的妥协政策,主张坚决抵抗。早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在制科考试所作的策论中就明确批判主政者的对外政策:“昔者大臣之议,不为长久之计,而用最下之策,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32〕他认为,宋朝要消弥边患,除了坚决抵抗外别无他法:“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33〕
熙宁四年六月,朝廷任命苏轼为杭州通判。苏轼七月离开汴京南下赴任,经过泗州(今安徽泗县)、扬州、润州(今镇江市),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任所。此时的苏轼,心情是灰暗和孤独的,又因为是“因言得祸”,他的表兄文与可告诫他此番去杭州不要再议论朝政了:“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于是,他便开始用词来抒发此时情感,因为“词言情”,善于表达曲折层深的内心世界。一些学者认为,苏轼词的创作正是从赴杭州任上开始的。如晚清词家朱孝臧首次为苏轼词编年,即是从宋神宗熙宁五年苏轼三十七岁任杭州通判时开始。厥后,许多研究苏轼词的论著及文学史教材都沿用朱孝臧的编年。叶嘉莹在《论苏轼词》一文中,还探讨了苏轼三十七岁才开始写词的原因。她认为,在此之前的苏轼正是一位满怀大志的青年,初应贡举,便获高第,他所致力去撰写的乃是关系国家治乱安危大计的《思治论》和为朝廷谋深虑远的《策略》等,无暇措意于小词的写作,当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意志受到打击,出为杭州通判,才致力于小词的写作。〔34〕当然,也不止叶说的这个原因,苏轼在此之前有过两次丁忧,在丁忧时期是不适合写歌词的。其次,在熙宁四年以前,苏轼有将近四年的时间是在朝廷供职,也不适合写这种“娱宾遣兴”的小词。以下一些词作可以证实这个判断。
熙宁四年十月,苏轼经过泗州,写下《如梦令·题淮山楼》:
城上层楼叠巘,城下清淮古汴。举手揖吴云,人与暮天俱远。魂断,魂断,后夜松江月满。
淮山楼,在泗州治所临淮(其故城在今江苏汴洪东南,盱眙对岸,清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陷入洪泽湖)城内,亦称都梁台。诗人一生多次经过泗州。第一次是英宗治平四年(1067),诗人兄弟护父丧沿水路归蜀,南行过泗州遇大风受阻,诗人听从舟子劝告,去向僧伽塔祈祷于风神,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第三次是元丰二年(1079)三月,时作者奉命移知湖州,经过泗州,求顺风不遂,转而批判鬼神之事虚妄,写有七古《泗州僧伽塔》记其事。这前后两次皆是诗作,这一次却是词,也不是记其事,而是抒发“魂断”“暮天”的怅惘之情。应当说,此时苏轼的心情是很沮丧孤独的,也更适合常用来抒情的词这种狭深文体。
苏轼在此后不久,从泗州经淮河由瓜洲渡长江到达京口(今镇江市)写的《醉落魄·离京口作》表达的是同样的情感:
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记得歌时,不记归时节。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但到了杭州后,面对着“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山水,同僚和友人的宴饮唱和,尤其是前后两任主官的善待和照顾,苏轼的心情好了许多,逐渐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他一直没有改变对自己才华的自持,为国尽忠的志向也再次抬头,此时仍然在写“小词”,但题材却有所拓展,“于柔情风月之外,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风景、怀古、咏物、农事、唱和均可入词。”风格也“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恢弘雄放,体现一种豪放洒脱的“壮”。如这首《沁园春·孤馆灯青》: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苏轼与其弟苏辙兄弟情深,其任杭州通判期间,熙宁六年苏辙也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到齐州(今济南市)任掌书记。为接近亲人,苏轼向朝廷请求到密州任职,得准改任密州知州,熙宁七年起程赴密州。这首词便作于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途中。词人将自己和苏辙比作晋代才子陆机兄弟,跟他们一样有才华:“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有理想壮志:“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己今虽遭打击,仍不改初衷,能放得下、拿得起,进退自由:“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要弟弟保护好自己,以待来年:“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
苏轼在杭时,前后两任主官都与他交谊甚厚:陈襄比苏轼大二十岁,对苏轼才华非常赏识,是忘年交。杨元素是他眉州同乡,唱和更多。如苏轼写给杨元素有两首词:《劝金船·无情流水多情客》和《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一首和词)。其中第一首写道:
无情流水多情客,劝我如曾识。杯行到手休辞却,这公道难得。曲水池上,小字更书年月。还对茂林修竹,似永和节。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阙。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
熙宁七年,杭州知州杨绘(字元素)调迁为翰林学士,自己也将调往密州任太守。词中将自己与杨元素的相处比作兰亭雅集:“茂林修竹,似永和节。”对杨元素调迁回京表示祝贺:“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阙。”词中虽有离别的伤感,但已无初来杭时的郁闷和孤单。词风开朗大度,也有别于婉约词派的“自古多情伤离别”。
此时写的咏物怀古词《行香子·过七里濑》、交谊送别词《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题材、风格也类此。据统计,苏轼在杭州和密州的豪放词作多达22首,几乎占其全部豪放词作的一半。其豪放风格的产生除上述原因外与王韶的“熙河大捷”关系极大。
当熙河大捷消息传来后,举国欢庆之际,产生不少欢庆这一重大胜利的诗词包括对王韶的讴歌,如在西北边塞长期抵御西夏入侵的老将蔡挺有首《喜迁莺》,就是描述大战之后“熙河路”的太平景象,和自己一生戍边的感受:
霜天清晓,望紫塞古垒,寒云衰草,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垅上铁衣寒早。剑歌骑曲悲壮,尽道君恩难报。塞垣乐,尽双鞍锦带,山西年少。谈笑。刁斗静。烽火一把,常送平安耗。圣主忧边,威灵遐布,骄虏且宽天讨。岁华向晚愁思,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不惜金尊频倒。〔35〕
蔡挺(1014—1079),字子政,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景祐元年(1034)进士,官至直龙图阁。曾知庆州,屡拒西夏犯边。宋神宗即位,迁天章阁待制,知渭州,治军有方。元丰二年卒,年六十六,谥“敏肃”。〔36〕魏泰《东轩笔录》称其词“盛传都下”。〔37〕
还有晁端礼《鹧鸪天》,直接提到西羌战事,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和胜利之后的太平景象:
八彩眉开喜色新。边陲来奏捷书频。百蛮洞穴皆王土,万里戎羌尽汉臣。丹转毂,锦拖绅。充庭列贡集珠珍。宫花御柳年年好,万岁声中过一春。〔38〕
晁端礼(1046—1113),字次膺,澶州清丰(今属河南濮阳)人。宋神宗熙宁六年登进士第,曾历单州主簿,瀛州防御推官,知州平恩县,官满授泰宁军节度推官,又迁知大名府莘县事,也是一位西北边防的军事、行政主官。
这一胜利也直接导致苏轼豪放词的产生,并将其推入创作高峰。检索一下《东坡乐府》,他在熙宁七年前后相关的豪放词作有:
熙宁六年:《瑞鹧鸪·观潮》;
熙宁七年:《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沁园春·孤馆灯青》《满江红·天岂无情》《鹊桥仙·七夕》《阳关曲》(三首)、《浣溪沙·缥缈危楼紫翠间》《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醉落魄·离京口作》《行香子·携手江村》《蝶恋花·雨过春容清更丽》《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更漏子·水涵空》《如梦令·题淮山楼》《浣溪沙·霜鬓真堪插拒霜》;
熙宁八年:《减字木兰花·送赵令》《江城子·密州出猎》《望江南·超然台作》;
熙宁九年:《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其中作于熙河大捷后熙宁七年、八年的豪放词有22首之多,占苏轼豪放词作近半。而且这个时段也是苏轼豪放词的发轫期。
其中熙宁七年的豪放词作《阳关曲·军中》就直接提到熙河战役和斩“契丹首”:
受降城下紫髯郎。戏马台南旧战场。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39〕
此为熙宁七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途经徐州时作。戏马台在徐州城南一里许的南山上,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今徐州)后,于此构筑高台,以观戏马,故名戏马台。受降城亦称三受降城,为汉武帝接受匈奴贵族投降而建,皆筑于北纬40°线以北的河套北岸及漠南草原。唐朝的三受降城体系则是控制后突厥的军事重镇。苏轼在词中由楚汉相争时的戏马台所触发,联想到汉唐时代接受匈奴投降的受降城,以此来比喻北宋政府在熙河大捷后设置熙州和河州两府与“熙河路”。也表达自己的军事主张:应该继续挺进,直捣西夏老巢——“取契丹首”,彻底解决西北边患。
如此愿望,在苏轼密州任上的第二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熙宁八年(1075)十月,他作为太守率众到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僚会猎于铁沟。词的上阕描绘的就是万马奔腾、弓矢交加的景象,形成一种飞动的气势,充分体现了苏轼豪放词“豪壮”的特色。下阕转入抒情和咏志。其中提到的冯唐故事见《汉书·冯唐传》:汉文帝时,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太守魏尚镇守边陲,防御匈奴,作战有功。因上报朝廷的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只差六颗头颅,被削职查办。郎中署长冯唐认为对魏尚的处理不当,当面向皇上直谏,文帝醒悟,派冯唐手持符节去云中赦免魏尚,恢复了他云中太守之官。魏尚复任后,努力整顿云中郡的军事,让匈奴人忌惮不已。苏轼在此引用冯唐“持节云中”之典,意图很明确:自己何日也能像魏尚一样被赦免,去云中作战。至于作战的对象词的结尾已经道破:“西北望,射天狼。”在古代星相学中,“天狼星”又称“狼一星”是作为外族首领的代称。《楚辞·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王逸注:“天狼,星名,以喻贪残。”《晋书·天文志》:“狼一星在东井东南,为野将,主侵掠。”〔40〕苏轼要“西北望,射天狼”,词意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像王韶一样去剿灭强敌西夏,因为西夏就在西北。甚至要完成王韶未竟之功:“取契丹首,金甲牙旗归故乡。”其实,从天文学知识的角度来说,天狼星并不在西北而恰恰相反在东南,所以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特别标明“狼一星在东井东南”,就是屈原在《九歌》中也只是说“举长矢兮射天狼”。苏轼为何要改变方位,说成是“西北望,射天狼”?就是为了强调要亲身参加剿灭西北边患,“取契丹首”这一创作目的。这一目的,在同时写的同题材诗《祭常山回小猎》中说得更为明确: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41〕
其结构也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同,前六句叙述围猎的情景,比词《江城子》具体,只是气势不如词;最后两句道破题旨:希望朝廷起用自己,去西北边塞讨伐西夏元昊,为国建立功勋。其中,“西凉簿”即西凉主簿,这里代指晋朝名将谢艾。谢艾,官西凉主簿,本书生,善用兵,胜仗无数。“白羽”,即“羽扇”,亦可指代军中主帅用的指挥旗。说自己虽是书生,也能挥白羽扇退敌,这和之后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形容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是同一种修辞方式。与此同时还有一首《和梅户曹会猎铁沟》诗,开头两句说:“山西从古说三明,谁信儒冠也捍城。”“三明”,用《后汉书·皇甫张段列传》之典:段颎,字纪明,初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皆在抵抗外辱中建立功勋。作者以“三明”自比,也是表示自己虽然是一介书生,也可以为国戍边,建立功勋。与《祭常山回小猎》的结句用意相同。由此可见,这首豪放词代表作的产生,与政府的西北用兵尤其是王韶的熙河大捷密切关联。
二、“永乐之败”促使苏轼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下面再说说苏轼豪放词创作高峰的另一个时间节点:元丰四年黄州之贬。如果说熙宁七年前后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和第一个高峰期,其特点是豪壮外放,如天风海雨动地而来,那么元丰四年黄州之贬后的豪放词则是清雄旷达、悲壮深沉,更多带有理性的思考和生命本体意义的思索,显示出一种超然独立的人格特征。当然,都离不开豪放词的基本特质“壮”。其形成原因同样与西北战事,具体来说是灵州、永乐之败和苏轼本人当时的经历有关。
此时的苏轼在人生道路上也在经历一场巨变:元丰三年(1080),苏轼正在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贬所任上。在此之前的元丰二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语带牢骚埋怨,挖苦正在得势的朝廷新党,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小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42〕于是,朝廷震怒,于七月二十八日下令将其“锁拿进京”,〔43〕受牵连者达数十人。新党章惇等欲置苏轼于死地,但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44〕在大家的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元丰三年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一直到元丰七年(1084)“量移汝州”,在黄州前后生活了五年时间。
苏轼在黄州,生活上虽异常困苦窘迫,但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活跃。他在开荒种稻之时就开始想象着稻子的抽穗、结实,想象着月下看稻穗的美景、秋来稻入筐的踏实,想象着自己面对丰收的喜悦;他与同情他遭遇的官员,前来看望他的昔日弟子、朋友,到黄州来开饭店的家乡商人饮酒叙旧,甚至在中秋月夜与友人整夜在大江上游玩,然后“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他早年有过批评佛、老的言论,但经过黄州之贬的政治挫折尤其是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开始向佛、老靠近。他贬居黄州时,“惟佛经以遁日”,“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黄州安国寺记》)他与僧人参寥子、定慧院长老等交往,与佛印的友谊更为人乐道。他学道术,作为健身强体御病之法,发明“静功养生七法”,并有体悟:“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二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此时的苏轼,思想和眼界大大开阔,使他走向兼容佛、道的宏通一途,认为“儒、释不谋而同”。(《南华长老题名记》)而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并把自己对佛老的体悟写在《黄州安国寺记》《盐官大悲阁记》《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祠堂记》之中,并化用到自己的诗赋中。如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的“水月之喻”就是化用六朝僧人肇所作《肇论》中词人“羽化而登仙”的愿望。虽然他融通三教,但儒学的出仕、从政仍是他的主导思想,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积极入世精神仍是他的理想抱负和主导思想。他学道,却反对道学家的空谈性命;他敬佛,同样不赞成“释者的无心、无言、无为”,(《盐官大悲阁记》)认为这是“为大以欺佛”。(《盐官大悲阁记》)
黄州五年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诗人一生存诗2700多首、4000多篇文、300多首词,黄州期间分别是200首诗、500篇文、80首词。尤其是豪放词约25首,约占苏轼豪放词作的一半,计开列如下:
元丰三年:《无愁可解·光景百年》《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元丰四年:《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元丰五年:《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满江红·江汉西来》《满庭芳·蜗角虚名》《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哨遍·为米折腰》《念奴娇·中秋》;
元丰六年:《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元丰七年:《满庭芳·三十三年》《满庭芳·归去来兮》《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浣溪沙·自适》《浣溪沙·寓意》《临江仙·诗句端来磨我钝》《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减字木兰花·回风落景》《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
这二十多首豪放词,又多集中在元丰五年(1082)和元丰七年。其原因固然与自己来黄的处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西北战事,尤其是与灵州、永乐之败对他的冲击有关。
到了元丰五年,苏轼来黄已近三年,生活基本上安定了下来,与继任的太守徐君猷关系很好。元丰七年,朝廷已准备开恩,第二年三月神宗去世,四月一日苏轼便接到“量移汝州”的赦令,朝廷对苏轼的管束已经放松。
西北对西夏的用兵,在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后,军事态势开始发生变化:鬼章大败宋军于踏白城(今甘肃积石山),王韶的副手景思立战殁;木征围攻岷山,宋廷为之大震,情况一度相当危急,刚刚到手的熙河之地又有失守的危险。于是朝廷又急调已升任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的王韶回熙河平乱。王韶回师熙河,绕到踏白城后,焚毁吐蕃八千帐,斩首七千余级,木征走投无路,只好归降。但随着改革派的失利,王韶的地位也不保。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受到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内外攻讦,加上长子王雱病故,灰心至极,再三请求罢相。后于十月罢相,出判江宁府。此时失去王安石保护和支持的王韶就处于孤危地位,在经营熙河屯田方面又受到当地的经略使李师中、接替李师中担任经略使的窦舜卿、派去调查此事的李若愚、大将郭逵等人的连续攻击。失去王安石保护的王韶仍一如既往口不择言批评边政,并提出要隐退:“举事之初,我据理力争,想节用民力,节省财政开支,但各位官员都不愿听,以至于拿熙河之事来指责我。我本来的意思是不想使朝廷受到损失而可以到伊吾卢甘,所以最初就不想将熙河作路,河、岷作州。现在我与大家的意见不同,如果还不引退,一定不会为大家容纳。”〔45〕王韶将屡用兵事、劳力费财的错误归于朝廷,神宗当然很不高兴,所以将他贬去知洪州。又因在谢恩表上颇多怨言,又被降职知鄂州。元丰四年,因生毒疮疽而死,时年五十二岁。朝廷赠为金紫光禄大夫,谥号曰“襄敏”。〔46〕
改革失利后,西北前线的军事态势也出现反转。但年轻气盛的神宗不知形势已变,仍要对西夏用兵。元丰四年,下令李宪、种谔等五帅分五路伐夏。开始时,宋军还差强人意:九月,李宪攻陷兰州;十月,种谔收复米脂;高遵裕受降西夏清远军;刘昌祚击败莲乞埋大军。但时间一久,这种作战方略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五路大军无统一节制,各自为政又各自为争功而互相拆台。与此同时,西夏主政的梁太后却在大军压境之时听从一位老将的建议,坚壁清野,纵敌深入,把精兵聚集在兴、灵二州。先调十二监军司十万精兵驻守在兴州要害之地,又派轻骑抄宋军后路,切断宋军粮食供应。种谔、王正中部都因断粮而溃退。高遵裕部则被西夏决开的黄河水淹没、冻死无数,大败而退。于是西夏反败为胜,由守转攻。元丰六年(1083),攻陷徐禧等仓促筑起的永乐城,守将徐禧战死,宋士卒、民夫损失近二十万。王韶苦心经营五年之久取得的军事进展又付之东流。宋在战事失利的情形下只好议和,贡银纳绢如故。
如前所述,苏轼一生未离过仕途,始终贯注着正视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神。在黄州,他虽然是个“不准签署公事”并在监管之中的通判,但“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关心现实政治的入世情怀始终未减。此时,对西夏用兵当然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何王韶经营河湟能取得如此成功?王韶去后为何又得而复失,屡战屡败?其中的关键何在?写于元丰五年,李宪、种谔等五帅灵州之败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即是表达他对此的思考和批评,只是在严酷的政治打击和友人的劝告下,变得比较隐晦,多用比喻和怀古的方式表达罢了。这个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战胜强敌的前提是决策正确。西北战事的失败主要是朝廷决策失当:五路大军无统一节制,各自为政又为各自争功而互相拆台。与此相反,西夏主政的梁太后却在大军压境之际采取坚壁清野,纵敌深入的正确决策。诗人这一观点是通过周瑜这个形象来委婉表达的。他“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中“羽扇纶巾”四字,摹写出周瑜的风流儒雅之态。强调这位年轻的军事统帅在大兵压境的强敌面前仍然气定神闲,暗示他对指挥这场战争早已成竹在胸;而“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则以十分轻松的笔调,赞扬周瑜赤壁大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有力地衬托出周瑜儒雅潇洒的英姿和指挥若定的气度。相形之下,宋王朝在对西夏用兵中却失于计算,举措失度。作者通过这两句描叙在赞扬什么,指责什么,自在不言之中了。二是上下同心,君臣互信。读过陈寿《三国志》的都知道,周瑜之所以以三万士卒战胜二十多万人马的强曹,除了本人的杰出军事才华外,与吴主孙权的信任与重用,友军诸葛亮等通力合作,同僚鲁肃等多方维护,部下黄盖等效死听命分不开的。熟悉这段历史的苏轼联系到对西夏用兵的惨败,感慨尤深:“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词人通过“一时多少豪杰”,高度集中地概括了赤壁之战时孙刘联军方面的人才荟萃,战将如云;相形之下,宋王朝用兵西北,神宗却将唯一的干将王韶罢免,让他赍志以殁。受到任用的五路统帅不但无统一节制各自为政,又为争功而互相拆台。中了西夏纵敌深入的圈套,还长驱直入自以为所向披靡,结果粮食断绝被对方彻底击溃。苏轼对着滔滔的江水自然要生无穷感慨了。〔47〕
当然,以上议论更有作者此时此地的生活感受:苏轼在黄州,“责以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这实际上是受地方官监管的政治犯的别称。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据说当时苏轼醉后写了一首小词《临江仙》,其中有几句抒发人生感慨:“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48〕据宋人叶梦得的笔记《避暑录话》记载:“(有人见此诗后传说苏轼已)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太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醒也。”〔49〕可见,苏轼确实是在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这种情怀作为全词的基调一直贯穿始终。所以,当词人描述年轻的周郎在赤壁指挥若定取得辉煌战果,正感奋不已、兴高采烈之际,转而又“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掉入伤感的现实冰水之中。道出这一切盛事都已成为历史,面对现实,自己只不过是“多情”而已。这个“多情”,指的就是对国事的关心和现实的无奈,当然也包括作者身不由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和伤感。而“早生华发”亦应当是对国事的忧虑、对自身不平遭遇的愤懑而导致的。词人此时才四十四岁,所以强调是“早生华发”。当然这个强调也不仅是自身年龄上的强调,更是将自己与周瑜在赤壁建立功勋暗暗进行对比。周瑜受到吴主孙权的高度信任,任大都督时才三十四岁,结果一战而胜强曹,奠定三国鼎立局面。词人为了强调周瑜的年轻,特地加了句“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而自己已经四十四岁了,早就想“西北望,射天狼”,早就想“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结果呢,不但壮志不能实现,反而因为国分忧、积极进言,被贬到黄州,不但平生之愿成为泡影,而且受到“监管”,失去人身自由。相比之下,更加沮丧和愤懑万分。南宋有位颇似苏轼风格的词人张孝祥,也是因为主张抗战被迫从中央枢要解职,曾经写过一首亦颇似《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怀古词《水调歌头·和庞佑父》,其中写道:“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所不同的是,张孝祥在词中将自己与周瑜和谢玄对比,直接抒发自己壮志成空、遭人诬陷的愤懑和伤感,而苏词只是暗暗流露愁情而已!
既然作者当时的政治遭遇和生活环境如此,为国效劳不成,被贬黄州处于被“监管”的窘境,那么如何解脱呢?词人在词的结尾处深沉地来了个萧疏冷落之笔:“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以萧疏冷落之笔消解如火肝肠!这与他同时期写的《赤壁赋》的结尾部分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出于同一种思考,用的是同一种手法,皆是“故作解脱之语”。因为苏轼忧国之心、报国之志是无法消弥的,壮志一天不实现,国事一天不转安,苏轼的慷慨悲歌就一天不会停歇,这就是词人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所要抒发的第二种感慨。
如果将元丰五年写的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与熙宁八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对读,可以发现:两者虽都是豪放词,但风格明显不同。虽都立足一个“壮”字,但《念奴娇·赤壁怀古》是清刚、悲壮,《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是雄壮、奔放;后者引古喻今,是正喻,以魏尚自比,表达自己要亲赴西北战场“射天狼”的壮志;前者虽也引古人,但属反喻。以周瑜和孙权君臣互相信任和支持带来赤壁大捷,反衬神宗对王韶的罢黜造成的“永乐之败”,并暗示自己的满腔忠诚也遭到被贬的命运。另外,此时也多了自省和佛老情思这类人生观的变化,这倒是和同期的前后《赤壁赋》相一致。
苏轼豪放词在此阶段已由前期的横放杰出,雄迈豪放,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变为悲壮、深沉,多人生的反省和佛老的思辨,如元丰四年在定慧院居住时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词编年校注》将此词断为元丰四年,不确。因为此词还有个副标题:“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元丰四年,太守已将废弃的水上驿站临皋亭分给苏轼居住,所以此词只能是元丰三年初到黄州寄居在定慧院时所作。词人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寄托了自己政治失意、心情寂寞孤独的情思,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苦闷彷徨又不肯随人俯仰的政治态度。其中的“有恨无人省”应该是包括自己遭遇在内的“家国之恨”。在表达方式上,上片状孤鸿之形态,下片抒孤鸿之情思,名为写鸿,实则写己,物我合一,形神兼备,空灵流走,含蓄蕴藉。他的门人黄庭坚评价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50〕这种空灵流走、含蓄蕴藉的豪放风格,明显不同于其熙宁年间的词作。还有一首前面提到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这首词的下阙写道: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人又一次提到“恨”。这个“恨”恐怕不仅仅是身被监管、不得自由之恨,更主要的是在抒发道家情思。因为这两句都是在化用《庄子》中的句子:“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则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多变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结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苏轼直接道出的人生归趋。当然,词人并没有归隐而去,上面提到的负责监管的太守也只是空紧张一场。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苏轼一生未离过仕途,始终贯注着正视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神。类似的道家情思,在其同期词作《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以及《后赤壁赋》中皆有表现。《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的下阕:“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在道家情思中更有冲决一切的浩然之气。就像金代诗人元好问指出的那样:“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51〕
到了元丰七年,词人对国事尤其是西北战事彻底绝望了。就在之前的元丰六年八月,徐禧等仓促筑起的永乐城被西夏攻陷,守将徐禧战死,“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余万,辎重损失尤重。”〔52〕据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就在“永乐之败”八个月后的元丰七年四月,苏轼接到朝廷任命,由黄州“量移汝州”。汝州虽然离京都较近,虽是开恩,但仍是“不得签署公事”的团练副使身份,“永乐之败”更让他沮丧、失望。词人此时写有两首《浣溪沙》。第一首曰《浣溪沙·自适》: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卖剑买牛吾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辞社宴春秋。
词人面对友人公开表白要归隐回乡、安度晚年,其中“梦松楸”“辞社宴春秋”皆是此意,词中引用苏秦落魄回乡“尘暗旧貂裘”更是暗示被贬五年的处境。其中“卖剑买牛”一典出自《汉书·龚遂传》:“民有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椟。”〔53〕词人对战事的灰心绝望更可从中体现,再没有当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气,而是“卖剑买牛吾欲老”了。这与陆游晚年的叹息“惟有躬耕差可为,卖剑买牛悔不早”(《贫甚作短歌排闷》)用意相同。
作此词之后,词人余意未尽,又再和了一首《浣溪沙·寓意》:
炙手无人傍屋头,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松柏肯惊秋。
前一首的副标题叫“自适”,点明自己的归趋,这一首叫“寓意”,干脆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炙手无人傍屋头”是说权贵与自己断绝往来的政治上孤单处境;“谁怜季子敝貂裘”是用苏秦说秦王不成,“黑貂之裘敝”狼狈还乡之典,来比喻自己遭受贬谪后急欲还乡之情。“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上句正面道出自己对世事和政局的绝望,下句大概包括像“遥想公瑾当年”这类思古之情。结句一如既往,表达自己的松柏本性,不愿随人俯仰的倔强性格。
词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东坡先生年谱》,这年四月〔54〕词人从黄州出发,沿水路到达泗州,在此向朝廷奏上《乞常州居住表》,表中说自己无法再去汝州赴任,原因是:
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赀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55〕
另一个原因是:“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饘粥,欲望圣慈,许于常州。”〔56〕奏章中形容自己“坐废五年”之后思想和身体状况是“积忧薰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57〕也无法再担当官任。诉说自己请求退休的愿望是“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58〕
苏轼一生,北上南下,多从水路。泗州是北连淮河、大运河,南入长江的进出水口。因此词人来往泗州十多次,写有四十多首诗和五首词。就在写奏章的同时,还写有三首游览泗州名胜、被称为“第一山”的南山词,表达同样的归趋思想。一首叫《满庭芳·三十三年》,写于元丰七年十一月晦日,词前有序:“余年十七,始与刘仲达往来于眉山。今年四十九,相逢于泗上。淮水浅冻,久留郡中,晦日同游南山,话旧感叹,因作此词。”词曰:
三十三年,飘流江海,万里烟浪云帆。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流年尽,穷途坐守,船尾冻相衔。巉巉。淮浦外,层楼翠壁,古寺空岩。步携手林间,笑挽扦扦。莫上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
三十三年前,诗人十七岁,与故乡老友刘仲达往来家乡眉山,今日再见已经四十九岁了。三十三年白云苍狗,自己身心俱疲:“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两人携手登高远望,只见“孤峰尽处,萦望眼、云海相搀”,“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尽管故友重逢,携手同游,但看不到欢情,整首词悲伤郁结,充满世事沧桑和对故乡的思念。另一首《行香子·题第一山》,写于此后的十二月,与泗州太守刘士彦同游南山。即使在宴饮之中、酒酣耳热之际,抒发的也还是归隐之思、家山之恋。词人先用夕鸟归巢进行暗示:“白云间。孤鸿落照,相将归去。”然后直接发问:“何人无事,宴坐空山?”第三首是《龟山辩才师》,通过今夕之变,写出世事沧桑:“此生念念浮云改,寄语长淮今好在。故人宴坐虹梁南,新河巧出龟山背。”然后通过僧人辩才之口道出自己的人生坎坷:“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最后点题,道破人生如梦,归隐之志:“千里孤帆又独来,五年一梦谁相对。何当来世结香火,永与名山躬井硙。”
苏轼上表后,即到金陵等候朝廷回复。在金陵,苏轼看望了在钟山闲居的王安石,叙旧之中,苏轼当面责备王安石,其中提到西北战事和冤狱:“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并警告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王安石也承认这是弊政,但为自己开脱说:“二事皆惠卿(即吕惠卿,王安石推行改革的主要助手,王安石罢相后,他担任参知政事,继续推行改革)启之,安石在外,安敢言?”〔59〕
元丰八年元月,朝廷批复苏轼准予常州居住。刚到常州不久,形势又起变化。正月初,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病情恶化。同年三月,年仅三十八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九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秉政,著名的元祐更化即将拉开大幕。苏轼到常州不久,五月,即以朝奉郎知登州。不久,朝廷下令,任命苏轼为中书舍人知制诰,进入朝廷中枢,参加元祐更化去了,还是未能摆脱仕途,跳出政治漩涡。
注释:
〔1〕〔清〕永瑢、〔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英殿本,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翻刻。
〔2〕均见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65页。
〔3〕杨忠:《气之积聚与词之豪放——论苏轼豪放词的形成》,《长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4〕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6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宋词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39页。
〔6〕柯大课:《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初探》,《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7〕柯大课:《苏轼豪放词形成的主观因素》,《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8〕祖保泉:《司空图诗品解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页。
〔9〕曾枣庄选注:《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成都:巴蜀书社,2017,第683页。
〔10〕胡寅:《酒边集序》,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68-169页。
〔11〕邓嗣明:《中国词美学》,深圳:海天出版社,2011年,第225页。
〔12〕〔宋〕俞文豹撰、张宗祥校订:《吹剑录全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5页。
〔13〕〔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前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06页。
〔14〕〔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后集”第十四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621页。
〔15〕牛宝彤选注:《三苏文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16〕〔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3页。
〔17〕〔28〕〔45〕〔46〕〔元〕脱脱、〔元〕阿鲁图:《宋史·王韶传》,《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65、6366、6367、6367页。
〔18〕〔19〕〔20〕〔21〕〔元〕脱脱等:《钦定宋史》卷328—331,上海:五洲同文局,1903年,第36、38、39、40页。
〔22〕王可喜:《王韶〈平戎策〉中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及借鉴意义——兼补辑〈全宋文〉中的王韶文》,《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23〕〔24〕〔25〕〔2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02、5502、5595-5596、6022-6023页。
〔26〕邓广铭:《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
〔29〕〔宋〕苏东坡:《苏东坡年谱》,《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5页。
〔30〕〔31〕〔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续集”第十一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30、339页。
〔32〕〔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后集”第十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569页。
〔33〕〔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应诏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746页。
〔34〕叶嘉莹、缪越:《论苏轼词》,《灵豀词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3页。
〔35〕〔38〕〔39〕〔48〕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437-438、311、287页。
〔36〕〔元〕脱脱、〔元〕阿鲁图:《宋史·蔡挺传》,《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577页。
〔37〕〔宋〕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40〕《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晋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4906页。
〔41〕〔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前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113页。
〔42〕谢依:《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东坡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18年,第158页。
〔43〕章雪峰:《一个节气一首诗》,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第167页。
〔44〕韩玉龙编著:《大宋:书生挽狂澜》,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2页。
〔47〕陈友冰:《中学古诗文考析》,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31-232页。
〔49〕〔宋〕叶梦得撰,田松青、徐时仪校点:《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46页。
〔50〕〔宋〕黄庭坚著、白石校注:《山谷题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第25页。
〔51〕〔金〕元好问:《新轩乐府·引》,陶秋英编选、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541页。
〔52〕〔元〕脱脱、〔元〕阿鲁图:《宋史·夏国传(下)》,《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758页。
〔53〕〔汉〕班固:《汉书》,《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65页。
〔54〕〔宋〕苏东坡:《苏东坡年谱》,《苏东坡全集》,第21页。但王宗稷所编《东坡先生年谱》时间有误,不应是元丰七年四月,应在八、九月间,是因为表中提到“幼子丧亡”,指的是妾朝云产的幼子“干儿”,干儿丧亡是在七月二十八日。
〔55〕〔56〕〔57〕〔58〕〔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前集”第二十五卷,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20、320、320、320页。
〔59〕〔元〕脱脱、〔元〕阿鲁图:《宋史·苏轼传》,《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