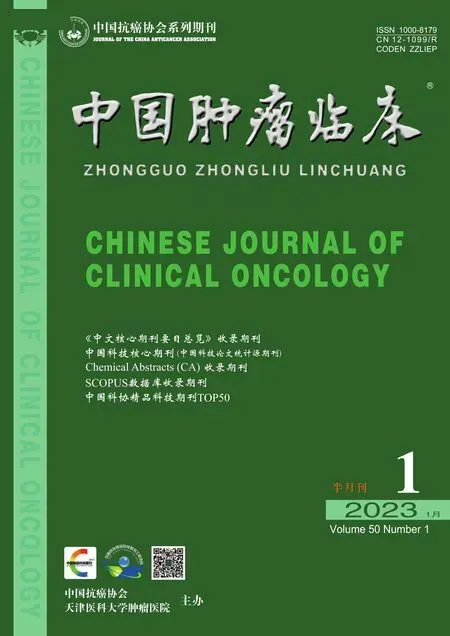幽门螺杆菌与胃癌相关的研究进展*
马刚 张汝鹏 梁寒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消化道肿瘤之一。2016年中国胃癌患者死亡28.85 万例,位居肿瘤相关死亡人数第3 位[1]。我国居民中幽门螺杆菌的高感染率是胃癌发病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2]。近年发表的大队列随访研究证实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可显著降低胃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3-4]。这些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进展密切相关,其作用机制的复杂性仍在持续探索中。
临床试验显示PD-1、PD-L1 和CTLA-4 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够令部分胃癌患者获益[5],但相当比例患者对免疫治疗无应答或产生抵抗,其原因尚不明确。幽门螺杆菌调控宿主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应答,塑造一个新的免疫抑制微环境[6]。这些直接影响胃癌发生,并很可能影响免疫治疗效果。
1 幽门螺杆菌在胃部的定植
幽门螺杆菌增加胃上皮细胞间隙后快速游动到胃黏膜深处躲避,或者分泌尿素酶在局部环境中和胃酸,从而抵消胃部酸性环境对其生存的不利影响[7]。考虑到胃黏膜表面环境的动态性,既往研究认为幽门螺杆菌必须不断游动、附着和脱离表层上皮来避免蠕动清除,维持一个稳定的种群[7]。近年的研究发现对这一模型进行了补充:少数幽门螺杆菌定植于小鼠胃腺深处并逐步侵占相邻腺体,阻止黏膜表面幽门螺杆菌定植,由此形成一个长期生存的种群。幽门螺杆菌感染小鼠胃细胞后通过NF-κB 信号通路直接升高免疫抑制转录因子Rev-erbα 含量,降低再生胰岛衍生蛋白3β、β-防御素-1、Ccl21 等基因表达水平,进而削弱抵抗幽门螺杆菌定植的Th1 细胞应答[8]。
2 幽门螺杆菌的毒力因子
目前确认的幽门螺杆菌毒力因子(virulence factors)有空泡毒素(vacuolating cytotoxin A,VacA)、细胞毒素相关基因A(cytotoxin-associated gene A,CagA)和一些胞膜蛋白[2]。VacA 对幽门螺杆菌定植胃和长期生存至关重要。VacA 与人胃上皮细胞蛋白酪氨酸磷酸酶受体α/β 和T 细胞受体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结合后进入靶细胞,促使胃上皮细胞死亡,抑制T 细胞活化[9]。除阻碍T 细胞增殖和活化外,VacA在小鼠胃黏膜通过调控E2F 信号通路阻止树突细胞成熟和抗原呈递,进一步促使初始T 细胞分化为调节性T 细胞[2]。
研究发现CagA+幽门螺杆菌感染激活转录因子尾型同源框蛋白1/2表达异常;这两个蛋白为肠分化和肠上皮化生(intestinal metaplasia)所必需[10]。CagA 通过幽门螺杆菌形成的Ⅳ型分泌系统(T4SS)进入胃上皮细胞后发挥多种细胞毒效应[2,11]。CagA 进入小鼠胃上皮细胞后破坏细胞间的紧密连接,激活β-catenin 信号通路[12]。CagA 还能激活小鼠胃上皮细胞的NOD1 和NF-κB 信号通路,促进下游炎症相关基因(如Il8)表达[13]。该蛋白的Glu-Pro-Ile-Tyr-Ala(EPIYA)结构域能被Src 快速磷酸化,而磷酸化后的CagA 与蛋白酪氨酸磷酸酶(SHP-2)结合,导致细胞骨架重排,细胞由此拉长并伴随运动能力增强,即所谓“蜂鸟形态”(hummingbird phenotype)[14]。CagA 的EPIYA 结构域有A、B、C、D 共4 种亚型;值得注意的是,欧美西方人群中常见的是A、B、C 的3 型组合,而东亚人群中A、B、D 的3 型组合更为普遍。当CagA 包含多个C 型或者只包含一个D 型,就能显著增强EPIYA 结构域与SHP-2 的结合力,提高胃癌发生率[14]。由此可见,CagA 蛋白EPIYA 结构域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东西方人群的胃癌发病率。
中性粒细胞大量浸润是幽门螺杆菌所诱发胃炎的最显著特征之一[5]。除CagA 能够升高中性粒细胞的主要趋化因子IL-8 的表达水平外,其它毒力因子也能诱导中性粒细胞富集和激活后者分泌大量促炎因子、自由基化合物、趋化因子等。如幽门螺杆菌表达的中性粒细胞激活蛋白是中性粒细胞定向运动的化学趋化因子,在此类粒细胞聚集和诸多细胞因子分泌中发挥重要作用[15]。
3 幽门螺杆菌致癌的作用机制
幽门螺杆菌的各类毒力因子显著改变胃上皮细胞中多条信号通路,加上患者自身遗传特征和其余环境因素的交互调控,极大增加这些信号通路影响细胞各个生物学功能的复杂性。
3.1 幽门螺杆菌与NF-κB 信号通路
NF-κB 信号通路在幽门螺杆菌介导的胃炎-胃癌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16]。尽管早已明确幽门螺杆菌能够激活NF-κB 信号通路,但是近年才鉴定出直接介导激活的分子是幽门螺杆菌生成的一种可溶性代谢产物二磷酸腺苷庚糖(ADP-heptose)[17]。ADP-heptose 通过T4SS 进入细胞,与α-蛋白激酶1(alpha-protein kinase 1,ALPK1)N 端结构域直接结合,激活经典/非经典NF-κB 信号通路[16]。RAS 蛋白活化相关因子2(RAS protein activator like 2,RASAL2)是新发现的NF-κB 下游分子,该蛋白在人胃癌组织中异常升高,提示患者不良预后和化疗抵抗[18]。机制方面,NF-κB直接结合在RASAL2 基因启动子上并促进后者转录,而RASAL2 进一步导致β-catenin 的细胞核富集,增强胃癌细胞增殖和干性[18]。幽门螺杆菌还通过异常活化的NF-κB 信号通路扰乱靶细胞中非编码RNA 调控网络。幽门螺杆菌感染人胃癌细胞后激活NF-κB信号通路上调RNA 结合蛋白LIN28A 表达,后者抑制let-7a 表达[19]。有研究表明人端粒酶逆转录酶(hTERT)基因mRNA 是let-7a 的直接靶分子,从而揭示了幽门螺杆菌通过NF-κB/LIN28A/let-7a 轴导致胃癌细胞中hTERT 高表达的分子机制[19]。
3.2 幽门螺杆菌与自由基化合物
幽门螺杆菌感染导致胃上皮细胞和免疫细胞产生的自由基化合物(包括超氧化合物和一氧化氮等)长时间存在,对靶细胞DNA 造成氧化损伤,促进胃癌发生。幽门螺杆菌感染抑制TP53 的转录调控活性,近年在人胃上皮细胞和转基因小鼠中的研究揭示上游转录因子1(upstream transcription factor 1,USF1)参与这一调控中:幽门螺杆菌导致USF1 和TP53 转运至细胞质,二者无法在细胞核内形成具有活性的转录调节复合物,因此增强DNA 损伤和加速胃癌发生进程[20]。过氧化物酶2(peroxiredoxin 2,PRDX2)在清除自由基化合物、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中起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通过NF-κB 信号通路直接激活人胃癌细胞和小鼠胃上皮细胞中PRDX2 表达,随后该酶清除过量的超氧化合物,维持被感染细胞存活;当PRDX2 水平降低后,胃癌细胞基因组DNA 发生显著的氧化损伤和双链断裂,增强了对顺铂的敏感性[21]。幽门螺杆菌自身基因组编码蛋白Hp1021 直接参与氧化损伤反应,具体机制在于该蛋白中6 个半胱胺酸残基的氧化-还原状态决定其是否结合到染色体复制起点上[22]。当Hp1021 缺失时,幽门螺杆菌生长速度显著下降[22]。CDH1 胚系突变是遗传性弥漫型胃癌易感的主要遗传病因,提示该基因产物在胃癌中具有很强的抑癌作用[23]。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人群中胃黏膜CDH1 基因的甲基化程度高于健康对照人群,而该基因甲基化水平在幽门螺杆菌根治后显著下降[24]。有体外研究揭示了这一变化的分子机制:幽门螺杆菌感染通过升高活性氮分子含量激活DNA 甲基转移酶1表达,进而增加CDH1 基因的甲基化水平[24]。
4 幽门螺杆菌与胃癌免疫
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快速招募调节性T 细胞和髓系细胞(含树突细胞、中性粒细胞和M1 巨噬细胞等)至胃部,分泌一系列细胞因子(如IFNγ、IL-17、IL-21 和IL-22 等),在胃上皮细胞癌变前共同构建一个免疫抑制微环境[6]。这一微环境中吲哚胺2,3-双加氧酶1 水平升高,促使幽门螺杆菌感染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转变为慢性炎症反应[6]。当慢性炎症建立后,即使根治幽门螺杆菌感染也只能一定程度上降低胃癌发生风险[25]。因此,幽门螺杆菌与胃免疫微环境之间的相互调控是当前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4.1 幽门螺杆菌与T 细胞
幽门螺杆菌采用多种机制逃逸宿主T 细胞对其杀伤。如前所述VacA 诱导T 细胞死亡或分化为调节性T 细胞。除此以外,幽门螺杆菌利用cgt基因的编码产物胆固醇-α-糖基转移酶(cholesterol-α-glucosyltransferase)催化生成多种糖基化胆固醇物质,协助免疫逃逸[26]。近年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将宿主胆固醇代谢为胆甾烯基酰-α-葡萄糖苷和胆甾醇磷脂-α-葡萄糖苷后能被T 细胞上C 型凝集素受体MINCLE和DCAR 识别,由此抑制T 细胞对此病原体的识别;当幽门螺杆菌感染Clec4e 基因(编码MINCLE 受体)敲除小鼠时,T 细胞功能增强,而随后发生的胃炎被显著削弱[27]。
4.2 幽门螺杆菌与PD-1/PD-L1
PD-1/PD-L1 是目前研究深入的肿瘤免疫检查点。幽门螺杆菌感染早期即能诱导人胃上皮细胞中PDL1 表达,且Hedgehog 信号通路转录因子Gli1 与mTOR 协同升高该受体的转录水平[28-29]。研究发现PD-L1 富集在解痉多肽表达化生(spasmolytic polypeptide-expressing metaplasia,SPEM)细胞中[28]。SPEM 细胞的出现是较肠化生更早的病理性改变[6]。幽门螺杆菌毒力因子之一尿素酶B 亚单位(urease B subunit,UreB)结合小鼠骨髓源巨噬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s,BMDMs)膜受体肌球蛋白重链9(myosin heavy chain 9,MYH9),随后激活mTORC1 信号通路并上调BMDMs 中PD-L1 蛋白表达水平,进而削弱CD8+T 细胞杀伤效应[30]。有研究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人/小鼠胃部富集的树突细胞较其余免疫细胞高表达PD-L1,并与T 细胞共同定位在胃炎损伤部位[31]。在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小鼠中敲除PDL1 会加重胃炎和肠化生,伴随T 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显著增多,而幽门螺杆菌数量则明显下降[31]。这些研究结果提示PD-L1 表达很可能在感染早期协助胃上皮细胞躲避免疫细胞攻击,提高幽门螺杆菌存活率。尽管PD-1 抗体已获批胃癌临床治疗,但是PD-1/PD-L1 抑制剂并不能使所有患者获益[32],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患者自身状态(如免疫水平)显著影响疗效。考虑到幽门螺杆菌在营造免疫抑制微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是否影响PD-1/PD-L1 疗效进行评估。在感染幽门螺杆菌的小鼠体内测试了CTLA4/PD-L1 抑制剂联合治疗效果,发现结肠癌MC38 细胞和黑色素瘤B16-OVA 细胞生长显著快于对照的未感染幽门螺杆菌小鼠[33],分析发现两个肿瘤细胞形成的瘤块中CD8+T 细胞数量明显下降[33]。随后在两个接受免疫治疗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队列中,研究者发现幽门螺杆菌血清阳性预示患者预后不良[33]。这一研究提示幽门螺杆菌感染很可能导致患者全身免疫环境改变,因此在使用PD-1/PD-L1 抑制剂时有必要考虑幽门螺杆菌感染状况。
5 幽门螺杆菌的治疗
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人数近30 年以年均0.9%速度缓慢下降,2006 至2018 年整体感染率为46.7%,较1983 年至1994 年间约下降17%[34]。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幽门螺杆菌感染仍是我国面临的沉重医疗负担。针对国内胃癌高风险人群开展的一项前瞻性随机研究近期发布了最新结果。从1994 年7 月到2020 年12 月的随访中发现,接受标准三药联合方案(奥美拉唑/阿莫西林/甲硝唑)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无症状人群中有21 例(2.57%)罹患胃癌,而接受安慰剂治疗的无症状人群中有35 例(4.31%)被诊断胃癌,接受治疗人群的胃癌发病率显著下降(HR =0.57,95% CI:0.33~0.98)[35]。进一步对人群分层分析后发现无癌前病变感染者更能从治疗中获益(HR=0.37,95% CI:0.15~0.95)[35],这提示幽门螺杆菌早筛并即时治疗的必要性。
目前多种清除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线治疗方案疗效有所差异。有研究分析了68 个随机对照试验,对比了8 个一线治疗方案(包括两/三/四药联用)疗效后得出,沃诺拉赞(vonoprazan)三联疗法(另两药为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和反向混合疗法(质子泵抑制剂加阿莫西林持续14 天,克拉霉素加甲硝唑最初7 天)治愈率达到90%以上,而标准三联疗法的效果最差[36]。感染者自身遗传特征显著影响治疗方案疗效。有研究分析了来自11 个国家的57 项研究后发现,当治疗方案中的质子泵抑制剂能被CYP2C19 基因产物CYP450 所代谢时,CYP2C19基因多态性与治疗效果密切相关。同时,IL1B 基因多态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示幽门螺杆菌根治疗效[37]。因此,尽管目前有多种治疗方案,但是要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仍需要综合考量各个因素。
6 结语
幽门螺杆菌在胃癌发生、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临床上可以相对容易解决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初始惰性效应,但当其诱发慢性炎症并最终发展为胃癌后,对应的治疗方案有限,患者预后不佳。尽管多年来临床已充分认识到幽门螺杆菌与胃癌之间的关系,但是胃癌的高度异质性决定其中分子机制的复杂性。当前的免疫治疗凸显了幽门螺杆菌在免疫微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尽管临床上已经开展幽门螺杆菌根治治疗,但其疗效受多种因素影响。这些问题均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