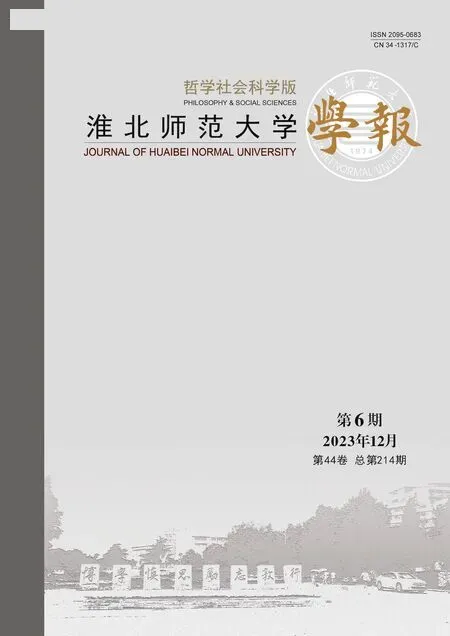从《屈诂·离骚经》管窥钱澄之对屈原形象的接受
郝 苗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钱澄之(1612—1693),原名秉镫,字饮光,晚号田间,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遗民学者。钱澄之一生为光复明朝而四处奔走,自明朝覆亡后,曾先后入仕南明三朝,其行迹遍布闽粤等地,致力于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复明失败后,钱澄之出家为僧,后以僧装返回故乡安徽桐城。钱澄之晚年潜心学术,注经立说,将毕生学问、忧思孤愤悉数寓于注经之中,撰有《田间诗学》《田间易学》《庄屈合诂》等著述,钱澄之关于《楚辞》领域的学说主要录于《屈诂》一书。
《庄屈合诂》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①关于《庄屈合诂》的成书时间,当前学界共有三说:其一为1685、1686年之交,陈欣《钱澄之〈屈诂〉研究》(贵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88页)中较早提及,此后黄巧红《钱澄之〈庄屈合诂〉研究》在陈文的基础上,又对此说进行了相关的论证(闽南师范大学2013硕士论文,第19页);其二为1685年,此说见钮则圳的《“以儒解庄”与“会通庄屈”——钱澄之〈庄屈合诂〉的注庄立场与遗民情结》(《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第86页);其三为1686年,此说见于吴航的《钱澄之晚年信札系年考证》(《古籍研究》,2016年第2期,第234页)。本文姑从吴说。,即钱澄之七十五岁之时。就此而言,《屈诂》中对于屈原作品的解读,实为钱澄之晚年对屈原及其作品接受的产物。钱澄之在《屈诂》中所诂“止于屈子诸作”[1]140,除了“精力向衰,未能遍及”[1]4的原因以外,还因为他认为《楚辞》中《离骚经》《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之外的诸篇,均为演绎屈原之作的产物,故不可作为其研究屈原的依据。其中,《离骚经》记载屈原“以忠被谗,志不忘君,心烦意乱,去住不宁”[1]141的遭际最为详尽,钱澄之诂该篇时所表达的情感也最为典型。
目前学界对于《屈诂》中的遗民视角、思想倾向等问题已有关注②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钱澄之对屈原形象接受的问题。如施仲贞、周建忠的《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3页)即通过分析钱澄之对屈原爱国精神的弘扬、对屈原的态度和评价等问题,阐明《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张琰的《论钱澄之〈楚辞屈诂〉中的遗民视角》(《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第22-25页)从钱澄之的“屈子情节”和“麦秀悲歌”等方面,探究了钱澄之撰《屈诂》的遗民立场;谢模楷的《钱澄之〈屈诂〉的经学阐释及其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74-79页)已关注到钱澄之《屈诂》的经世用意。此外,如陈欣的《钱澄之〈屈诂〉研究》(贵州大学2009年硕士论文,第48-57页)在第二章第三节以《离骚总诂》为例探究了钱澄之对屈原形象的品评,但该文以解读钱澄之的观点为主,而关于钱澄之对屈原形象接受情况的成因等问题,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空间。,但此类研究仍多着意于钱澄之的个人体悟在其撰述过程中的直接反映,而对于钱澄之的经历是如何对他的著书过程产生影响、他的遗民立场又是如何在书中发挥作用等问题,则缺少较为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拟以《屈诂·离骚经》为例,从钱澄之对屈原的评价、对屈原人格的阐释以及对屈原形象接受的成因等方面,探究钱澄之对屈原形象的解读。
一、对屈原“狂狷景行”的评说
钱澄之对屈原人格的阐释与前儒“露才扬己”的说法存在本质的不同,故不可将二者等量齐观;同时,钱澄之并不否认屈原怨刺太过与其自身悲剧之间的因果关系。以下具体言之。
班固是最早以“狂狷景行”评价屈原之人,其《离骚解序》称:
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2]9
可见,班固指出屈原“竞乎危国群小之间”“狂狷景行”等自立于危墙之下的言行,也是导致其沉江的重要原因。而钱澄之在《离骚经·总诂》中也呼应了班固的说法,认为:“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原难免焉!若怀王则至死不知其诬,此原所痛心而不能已于一死也。”[1]187钱澄之于此并未否定班固之说,而且“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包容,甚至是理解”[3]53。此外,钱澄之分析屈原之所以“难免”,还在于“以原之褊急,不悦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岂惟性之使然;负形如此,亦不能习此媚上谐俗之态,则惟有去此世,而容与以自适耳。”[1]293
就班固的说法来看,如潘啸龙先生所言,屈原的“露才扬己”“狂狷景行”正是“对于黑暗势力的不屈抗争精神”的一种表现,而班固之所以对屈原的这种精神采取比较激烈的排斥立场,恰恰是因为班固敏感地察觉到该精神“对封建统治阶级有所妨碍”。[4]96据此而言,班固评价屈原“露才扬己”“狂狷景行”,皆是将屈原置于统治者的对立面,而后世呼应班固者,如颜之推、孟郊等人,也都是从屈原反叛温柔敦厚礼教的角度,以“轻薄”“怨怼”等词语评价他的过激言行。但是,反观钱澄之所言,不难看出,钱澄之虽然认同屈原因“露才扬己”而致祸,但是他的观点却与班固的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自宋代之后,屈原身上的“忠君”精神被一再地放大、强调,至明清之际,士人甚至极端地将屈原视作忠贞的代表。在这种背景下,钱澄之对屈原人格的阐释自然也离不开“忠君爱国”的基调。如上文所言,钱澄之虽然认为屈原“难免焉”,但是在钱氏的解读中,屈原最意难平的并非个人的不得志,而是“怀王至死不知其诬”。在此前提下,所谓屈原的“怨怼”“狂狷”就不能简单地视作对统治者的反抗,而应为在“忠”的前提下,屈原对温柔敦厚风气的突破。
钱澄之对屈原“怨刺”一面的解读,还应结合钱澄之本人对于“温柔敦厚”风气的态度来看。虽然已有学者从“性情”和“真”的角度出发,指出钱澄之对“当时提倡温柔敦厚的风气不以为然”[5]154,但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钱澄之对于“温柔敦厚”风气的批判,正是其经世精神的一种外化。“温柔敦厚”的礼教并非是教人一味顺从、柔懦,如《礼记·经解》所言“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6]1368。此所谓“愚”,并非指直言进谏而获罪,而是告诫为臣子者勿囿于恭顺而缺少是非观念,尤其在春秋时期所尊奉的“忠”的风气下,“具有忠德的人必然会从对国家、百姓负责的角度,对君主进行直谏,甚至是尸谏,而不必恪守温柔敦厚的讽谏之法”[7]139,而钱澄之对于“温柔敦厚”风气的指斥,无疑也秉持与之相同的立场。钱澄之在《叶井叔诗序》中称:“若夫本诸忠爱孝友以为情,此礼义之情也,性情也;性情惟恐其不至,可谓宜得半而止乎?”[8]260可见钱澄之对“温柔敦厚”风气的反驳,源自他对于“性情”的推崇,但他所谓的“性情”皆出自忠孝礼义,仍不离礼教的范畴。在此基础上,钱澄之反对以温柔敦厚抹杀“性情”与“真”,其本意正在于警戒士人不可因柔懦、恭顺而歪曲是非,要保持必要的刚正之性对君主直言进谏。
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屈原怨刺的一面被有意地凸显。在《屈诂·离骚经》中,屈原无疑是一个“爱君”“忠君”之臣①钱澄之对屈原“忠”的一面的突出,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与前代学者弘扬屈原抗争精神不同,明清时期学者的普遍做法是有意地回避屈原的这种精神,千方百计地将屈原塑造为一个忠君爱国、集忠孝于一体的形象。在这种学术氛围下,很多学者为了替屈原摆脱“怨愤”“狂狷”的形象,不惜对班固等人的说法大加鞭挞,甚至对于朱熹对屈原的中和之论也加以批判。。,有着高度的“致主泽民”精神,同时也有着强烈的改革意识。因此,屈原在竭力改革楚国弊政时,往往因“法夫前修”,而“不周于今之人”[1]152,故而受到奸臣谮害,以至“见疏”于楚王。在此过程中,屈原固然有“露才扬己”、怨刺君上的言行,但屈原作出此类言行的前提无疑还是忠君爱国。就此而言,屈原的所谓“狂狷景行”并非是站在统治者的对立面,而是以“怨刺”的方式对维护统治稳定所做的努力。因此,钱澄之虽然认为屈原沉江之祸“不可免”,但也肯定了怨刺精神的合理性。
另外,钱澄之还从“时”的角度为屈原的“狂狷景行”做出解释。钱澄之在《庄屈合诂》的自序中指出:
吾谓《易》因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庄子之性情,于父君之间,非不深至,特无所感发耳。诗也者,感之为也。若屈子则感之至极者矣。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之《易学》《诗学》①此处所言《易学》《诗学》皆为《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的简称,并非钱澄之所治《易》学、《诗》学。无二义也。[1]4
“潜”与“亢”分别出自《易经》的《乾》卦“初九:潜龙,勿用”、“上九:亢龙,有悔”。所谓“潜龙,勿用”,钱澄之认为:“建子之月,阴气始盛,阳气潜在地下,故言初九潜龙也。张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称勿用,以诫之。若汉高祖生于暴秦之世,惟隐居为泗上亭长,是勿用也。诸儒皆以为舜始渔于雷泽,舜当尧之世,尧君在上,不得谓小人道盛,此潜龙始起在建子之月,于义恐非。’”[9]164-165“初九”是阳气处下之象,天下无道,即便圣人也无用武之地,“凡事不可为,而劳神苦形以为之,皆害生之道也”[1]52,故而应当隐居不仕。钱氏以“潜”指庄子,正意在说明庄子隐居不仕是顺时而为。钱澄之解“亢龙,有悔”称:“上九一爻,以气候按之,近偪小满,阴已在下,渐推阳出,推而益上,故有进无退,其势不得不亢。”[1]169“上九”是阳气处上之象,“有进无退”正是喻指人当有所作为之时。钱澄之认为“当亢不宜存潜之心”[1]75,屈原当楚国存亡之秋,力图革除弊政、推行“美政”,正是处“亢”时所应为之事,而不应在此时“为全躯保妻子之计”[1]75。因此,钱澄之也对屈原的“狂狷景行”进行维护:
以原之褊急,不悦登高;以原之亢直,不能入下,原亦自知之矣。岂惟性之使然;负形如此,亦不能习此媚上谐俗之态,则惟有去此世,而容与以自适耳。(《九章·思美人》)[1]293所谓“褊急”,即指屈原“见楚国种种多可改之度,宜乘己壮年以速改也”[1]146,上为“望君造其极,而有千秋之远闻”[1]278,下为自身能及时效用、早立修名,故“其求进亦太急矣”[1]145,为此,其在作品中多“每以迟暮为恐”[1]164;所谓“亢直”是指,屈原“之所为,一遵规矩绳墨,为时俗所不便”[1]185,由于其“只知直不知曲”[1]280,故“毕竟以婞直得罪也”[1]262,即使有机会隐退以“从吾所好,修吾初服”[1]156,但终因“有失其故吾”[1]156而自沉以死。
值得一提的是,钱澄之解读“上九:亢龙,有悔”还借郭子和之言指出:“三过中而惕,上过中而亢,故有悔。龙德莫善于惕,莫不善于亢,亢则贪位慕禄,不知进退存亡,其悔宜矣。尧老舜摄,舜亦以命禹。伊尹复正厥辟。周公复子明辟。君臣之间,皆有是道。”[9]169不论是尧、舜、禹,抑或是伊尹、周公,这些圣贤均持“中”、有知退的觉悟,反观屈原自认为“岁时已过,精华已销,虽不死,无能为也”[1]306,所以“明知死之无益而必欲死”[1]312,这不免过于亢直而失于“中”,这也就无怪于唐甄在《庄屈合诂序》中认为屈原这类“知进而不知退者”,“当以庄子之意济之,则忠而不至于愚”[1]1-2。
总之,《离骚》中屈原因“法前修”而“不周于今之人”的种种做法,在以班固为代表的学者眼中,固然是对统治者、统治秩序的反抗,但是在《屈诂·离骚经》的解读下,屈原怨刺上政反而被视作对君、对国负责的一种表现,究其根本,是因为屈原的怨刺精神与钱澄之本人对温柔敦厚风气的指斥暗合。然而,钱澄之并未因此全盘否定前儒对屈原“露才扬己”“狂狷景行”等评价,反而认为“原难免焉”。这并非是钱澄之态度的矛盾,而是钱澄之看到了屈原正处“亢”时却又失于“中”,其悲剧自然难以避免。
二、君子小人之辨与“自矜”之说
钱澄之在《离骚经》中对屈原怨刺的回护,不免涉及到对于他对屈原“自矜”问题的态度。钱澄之对于该问题的阐述,不仅植根于屈原的经历,也包含其个人在明清易代背景下的个人的考量与体悟。
(一)“自矜”之说的经世意义
钱澄之在《黄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记》中曾言:“观公于难初发之时,其所以规杨忠烈、魏忠节者,忧深虑远,凡期于国事有济,不欲其徒以名节自矜。既已自矜,而复不留余地以待小人,使甘自弃其名节,此祸之所由烈也。”[8]196钱澄之生平多次受到小人构陷,固然深知党争中过度自矜必然祸及自身的道理,因此学者往往将该文视作钱澄之在处世时存身自保的智慧①如张晓芬认为钱澄之在该文中借《夬》卦与《姤》卦呼应黄尊素之言,即用以说明君子在与小人相处时应予以包容与忍耐,处乱世时要有所忍耐与等待。(《和而不流,别而不僻——论钱澄之〈田间诗学〉中“群”的意识》,《诗经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第448-449页)此外,施仲贞、周建忠则认为钱澄之此论,正是对其“以藏为用”思想的阐发。(《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第53-54页)。但是就引文来看,钱澄之的阐释重点除了教君子如何处世以外,更重要的内容是强调了士人自矜所造成的祸患——不仅自身难保,而且更危及家国社稷。将此思想带入到钱澄之注《离骚经》中,也就不难发现,钱澄之对屈原“饮露餐英”“扈兰纫芷”的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方面,钱澄之对屈原的芳洁品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离骚经·总诂》中,钱澄之将屈原的品行概括为“独行之芳”,即“扈兰、纫芷者”[1]187。具体来看:钱澄之将屈原“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装扮解读为“‘扈兰纫芷’,所谓被服礼义,涵濡道德,学问之事也”[1]144;又将“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一句解读为:“芳者外扬,泽者内浃,杂糅则表里皆香。自幸处兹浊世,能洁身以退,本来光明,宛然固在,使求周于今之人,则昭质亏矣。”[1]157从中可见,钱澄之认为屈原的芳洁品性是一种植根于学问,合乎礼仪道德的品质。
另一方面,钱澄之尤其强调屈原为国图谋的行为,正意在救“自矜”之弊。从上文所引《黄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记》内容不难发现,自矜名节者,往往徒以名节为重而容易置家国社稷于不顾,即所谓“君子为祸”。以此观照《离骚》中的屈原形象则知:屈原之徒的芳洁品性固然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表现,但是在“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1]150的环境中,人皆“内以其志量度他人,谓与己同”[10]11,难免会出现“各兴心而嫉妒”[1]150的局面,于是造成了“众芳不获进用”的结果。如此看来,屈原自身“好修以为常”的言行不免有因自矜德行而为祸的嫌疑,但是朱熹则不以为然,认为:
世乱俗薄,士无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为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盖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于当世。故中材以下,莫不变化而从俗,则是其所以致此者,反无有如好修之为害也。东汉之亡,议者以为党锢诸贤之罪,盖反其词以深悲之,正屈原之意也。(《楚辞集注》)[10]26朱熹并不认同所谓“党锢诸贤之罪”的说法,更不认同“好修”之君子包容忍耐小人就能免祸的逻辑。钱澄之在对《离骚经》的解读中也延续了这一观点:
盖时俗“竞周容以为度”,众女“兴心而嫉妒”,岂独一上官哉!上官之谗原曰:“自矜其功,以为非原不能为也!”观原好自揄扬,则自矜诚亦有之,宜王之信而不复察也。原不知以此得罪,而自谓以謇謇致患,女媭亦詈其“婞直以亡身”,谬矣。[1]187
钱澄之此言可以说是对屈原“婞直”“好名”等评价的一个全面否定。钱澄之认为屈原之祸固然因自矜而起,然而,真正致祸的却并非是其品性的卓然不群而是楚王对其“自矜其功”的不满。而所谓“謇謇致患”“婞直以亡身”的说法,皆为无稽之谈,小人为祸自当归咎于小人,不当以君子性直为借口。
对比钱澄之对屈原的态度,以及其在《黄忠端公祠堂重建碑记》对以名节自矜之人的态度,可见,钱澄之所否定的“自矜”,并非是针对有功之人,甚至不是针对爱惜名节、以名节自励之人,而意在批判徒以名节自恃,囿于意气之争而耽误国事之人。
(二)君子小人之辨的时代风气
钱澄之对名节的敏感,除了受历史经验的影响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对明末君子小人之辨的深切体会。
君子是儒家礼教规范下的理想人格,小人作为君子的对立面,在道德方面与君子判然有别。钱澄之将此二者视作道德的两极:
圣人深知夫阳不能敌阴,君子不能敌小人,治日少而乱日多,故于阴之长也,为君子危焉;于阳之长也,亦为君子危焉。彼小人者,不惟道长之时,以众小人制一君子而有余,即道消之日,亦以一小人制众君子而有余也。盖小人之计常密,君子之计常疏;君子之遇小人也以刚,小人之遇君子也以柔:以柔制刚,以密制疏,毋怪乎小人之常胜,而君子常败。(《周易绪言序》)[8]226可见,以阴阳之论来看,小人擅长以柔制刚、以密制疏,君子之行事、谋划原不似小人一般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也就无怪于“小人常胜而君子常败”。正因如此,即便阳盛于阴时,君子仍不得敌小人,更何况阴盛阳衰之时?这也正是圣人作《易》以扶阳抑阴的用意所在。辨明君子、小人,原本是为了“匡君而正国”,然而,受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君子小人之辨往往“会波及朝政,进而形成‘门户’,甚或‘朋党’。”[11]181朋党习气在明末甚为严重,在此风气下,门户之见以及党派的利益一再凌驾于正常的纲常伦理与公平正义之上,更有甚者,因为一时的意气之争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明代之亡,固然源于小人当权,但是君子们的意气之争也与此难脱干系。因此,钱澄之在其著述中也多就君子之祸发表意见,如他对《鄘风·载驰》“众稚且狂”一句的解读:“从来国事本易挽回,以少年喜事者争之过激,遂成不可挽回之势,皆狂稚为之害也。”[12]133该句原本意在批判横加干涉许穆夫人救国的许国大夫们,被钱澄之解读为少年以意气之争而耽误国事。此处虽牵强附会,但仍可见钱澄之借《诗经》暗讽君子相争之祸。然而,君子、小人的评价标准却常常因时而变,如倪文焕罢归时曾言:“一时有一时之君子,一时有一时之小人”[13],正因如此,诸多君子为了保持名节,不与小人同流合污而拒绝入仕。对此,钱澄之在《小雅·雨无正》中指出:“此诗与《十月》篇所讥不同,此篇讥者,非皇父辈也。即所云自逸之我友,洁身远引者。故曰正大夫,非指皇父一辈小人也。小人乱国,正人争去,国事其谁赖乎?”[12]521由《毛诗序》可知,“《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14]854钱澄之认为《十月之交》是刺皇父专权,而《雨无正》一诗与此不同,意在讽刺君子只求爱惜名节而不知在危难之际为国尽忠。因此,君子虽然有好名节,但是仍然要为亡国负责。
钱澄之对于君子小人之辨问题的谨慎与敏感,并非是无来由的。从其自身经历来看,意气之争的肆意发展往往是党派之间互相迫害的先兆。“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就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15]416据《所知录》载:
先是,朝士有东西之分,自粤东来者,以反正功气凌西人;而粤西随驾至者,亦矜其发未薙以嗤东人;而东、西又各自为类。久之,遂分为吴楚两局:主持吴局者,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给事张孝起、李用楫,外则制辅堵胤锡也,而江右之王化澄、万翱、雷德复,蜀中之程源,粤东之郭之奇实为之魁;主持楚局者,丁时魁、蒙正发、袁彭年。彭年楚人,然私粤而不私楚。陕西刘湘客、杭州金堡既与丁时魁等合,桂林留守瞿式耜亦每事关白,居然一体矣。……凡自湖南、广西随驾至,出于督师、留守门者,大半归楚。吴人谓楚东恃元胤,西恃留守。实则吴亦内倚吉翔,外倚邦傅,特其踪迹秘密,不似时魁等招摇人耳目耳。[16]96-97
从中不难发现,永历朝的政局俨然成为了吴党与楚党的交锋。此时,南明政府在清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朝廷内部人才凋敝,但是仍然执着于内讧,将党派之间的利益牵扯置于国家大义之上,如钱澄之等有识之士在两党派的斗争中力图自保已是难事,在夹缝中力图光复明朝更是天方夜谭。金堡等五人因党祸入狱,“张鸣凤奉密旨,必致堡死”,“堡受刑独酷”。[16]111钱澄之从中奋力斡旋,接连上疏,又借高必正之力方救得金堡,但也就此与诸多党人结仇。[17]46-53正因其亲身经历党争之祸,故钱澄之对党争误国有着深切的体会。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钱澄之在《屈诂·离骚经》中对屈原“婞直”的特征处理得格外审慎:一方面,钱澄之极力赞扬屈原坚守个人品质的可贵,称其为“独行之芳”;另一方面,钱澄之又竭力为屈原辩解,认为屈原虽然“好修”,但始终以国事为重,与一般自矜名节者不同。如此一来,阐明了屈原虽培植众芳,极力引荐贤能,但却不是结党营私,而是朋而不党。至于其“美政”理想终究因此破灭,正可见楚国党祸之害,引史以鉴今,未为不可。
三、屈原形象接受的成因
钱澄之对屈原形象的阐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明清之际社会现实的影响。但如果再作进一步地探究,即可发现:钱澄之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一方面,将个人的遭际与体悟融入其中;另一方面,又借屈原之死寄寓了自身在明亡之后对生死抉择的思考。
(一)个人情感与屈原形象的融合
明末清初复杂的社会现实与钱澄之个人的坎坷遭遇,使钱澄之在面对同样身处亡国之际的屈原时产生了深度的共鸣,并将个人的人生体悟融入到对屈原形象的接受之中。
一方面,就国家兴衰的历史背景来看,楚与明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屈原所要变革的楚国,在当时早已没有了昔日问鼎中原时期的底气,面对强盛的秦国,楚国甚至失去了与之抗衡的能力,国家上下均被秦国的君臣玩弄于股掌之中。反观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同时,统治者动辄对臣下施以重刑的做法,更激起士人的对抗情绪,黄宗羲《子刘子学言》录刘宗周之言,称“上积疑其臣而蓄以奴隶,下积畏其君而视同秦越,则君臣之情离矣,此‘否’之象也。”[18]277然而这些积弊并没有随着明亡而结束。从明亡之初阮大铖对东林党的迫害,一直到永历朝的吴、楚之争,明朝光复的希望在党争的阴影下逐渐湮灭。在这样的背景下,钱澄之也认识到亡国的危机并不来自外部而是在内部,积弊不除,明朝光复则无从谈起。他将这种体会带入到《屈诂·离骚经》的注释之中,由此认为屈原美政理想正在于革除楚国弊政,正因如此,“原所悲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1]187。但与此同时,钱澄之也认识到:社会风气使然,亡国在所难免,国家积弊之重,非一君一臣可以扭转,正所谓“天之巧于布置以亡人国,固非人所能计算也”[1]247。
另一方面,相似的社会环境造成了屈原与钱澄之相似的人生遭遇及政治经历。在国家存亡之秋,无论是屈原还是钱澄之,都选择竭尽所能地为国家效力,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载,屈原“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9]2481。钱澄之的个人情况正与史书所载屈原之特点共通。钱澄之自幼即有济世报国之心,然而在明亡之前,钱氏屡试不第,直至明亡后,经黄道周的推荐,于永历三年临轩亲试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又迁为编修,掌管诰敕,当时之诏令大多出自钱氏之手。此外,钱氏虽入仕生涯较短,但仍然竭力以其才学为国效力。如1645 年潞王降清,贝勒博洛致书召降,钱澄之作《寓武水为家塞庵阁学复贝勒书》回应之:
来谕云:大清取天下,取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本朝也。诚哉斯言。某且据此以答明谕:伏以本朝二百八十年之德泽,先帝十七载之忧勤,一朝不戒,遂使金隄溃于蚍蚁,天柱摧于蜻蛉。……《春秋》:狄人灭卫,齐侯驱狄而存卫;吴师灭楚,秦伯破吴而兴楚。君子义之。未闻狄遁而齐遂有卫,吴败而秦遂据楚也。惜乎贵朝以义始,不以义终也。譬如大盗入室,戕其主人,窃踞其第。有干仆力恐不敌,求救于壮士,壮士毅然许为同仇,奋臂助斗,大盗授首,仇以报矣,而主人所有尽归壮士。则是干仆有功而无功,壮士有义而无义也。[20]392
清政府本意是借取政权于李自成而非明王朝,来减少明遗民的反抗情绪进而维护社会统治。然而,钱澄之以大盗入室,义士相救之事为例否定了清廷之说,并且指出其中的利害关系,既捍卫了明王朝的体面,又有理有据地指出了清政府篡权的实质,称其“娴于辞令”而不过,赞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亦有之。此外,如其《初至端州行在第一疏》《端州拟上第二疏》等皆为除弊献策之疏,又如其所作《战胜庙堂论》《正统论(上、下)》《官田议》《举吏议》等政论,皆是凝聚其毕生治学之所得,且有补于世的经世之作。就此而言,钱氏称屈原“所悲愤不能自已者,非悲其身不用也,悲其功之垂成而不就也”[1]187,或许正是钱澄之呕心沥血陈言献策却不被君主采用的切身体会。
仕途受挫之后,远离是非纷争的朝局大概是臣子的必然选择。然而,为人臣者即使身不在此,也往往难以做到真正的释怀,心系国事民生者仍有之。如屈原在经历了“上征求女”等一系列寻求救国之策而不得的努力后,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远逝自疏”。如果说屈原的“求女”尚且有驱使龙凤、奔走四海八荒,“令凤鸟飞腾”“令帝阍开关”“令丰隆乘云”等执着追求的意志,那么,反观屈原“远逝自疏”时,“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1]182等表述,“上征求女”过程中的紧迫感以及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都在此荡然无存。就连钱澄之在解读屈原“远逝自疏”时也认为,“浮游求女,随其所遇,不似向者之汲汲于所求也。向者志在求女,而浮游皆属有心;此则志在浮游,而求女听诸无意。及年之未晏,饰之方壮,犹可以周游上下,盖欲从灵氛远逝之占也。”[1]179由此不难看出,钱澄之也认为“‘远逝自疏’部分从头至尾,所写的都是乘龙驾凤的飞行以及飞行过程中的优游自在的心态,而没有任何关于追求理想目标的内容。”[21]61至于为何屈原此时“远逝自疏”不复从前之心态,钱澄之认为“从前之游,上下求索;此直周流观乎上下,无所复求,志在远逝以自疏而已。……《传》称‘王疏屈平’,然平终未忍疏王,以此益不见容于党人。盖至是始决志于远逝以自疏,不复向之眷恋。其词激,其情愈苦矣。”[1]180可见,钱澄之认为屈原的“远逝自疏”是不被现实所容而不得不做出的一种远游,屈原在其“远逝自疏”的过程中看似悠游从容,达到了类似道家所言的绝对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实则只是一种暂时的、虚假的、逃避现实式的潇洒。正因如此,钱澄之在注“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时,指出“本忘情于旧乡矣,而忽临而睨焉,己不悲而仆夫悲,己不怀而余马怀。……盖至此而知远逝亦不能自疏也。”[1]183和屈原类似,钱澄之在永历朝溃败之后僧装返乡,过上了自耕自足的隐居生活,如其《田园杂诗》所记:
仲春遘时雨……秉耒赴田皋,叱牛出柴荆。耒耜非素习,用力多不精。老农悯我拙,解轭为我耕。教以驾驭法,使我牛肯行。置酒谢老农,愿言俟秋成。(《田园杂诗·其二》)[22]157
邻舍有老叟,念我终岁劳。日中挈壶榼,饷我于南皋。释耒就草坐,斟出尽浊醪。老叟自喜饮,三杯兴亦豪。纵谈三国事,大骂孙与曹。吕蒙尤切齿,恨不挥以刀。惜哉诸葛亮,六出计犹高。身殒功不就,言之气郁陶。嗟此易代愤,叟毋太牢骚。(《田园杂诗·其十》)[22]159
钱澄之自言“夙昔慕躬耕,所乐山泽居。忧患驱我远,常恐此志虚”[22]157,就此看来,其因为局势所迫回乡务农隐居,似乎正合其意,但是就像钱氏对于屈原远逝的解读一般,钱氏此举实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钱澄之志在为明王朝图光复,但是随着南明王朝的溃败,其经世之志也不得不暂告段落,钱氏怀揣着未竟的理想,即便在田园生活中暂得闲适,也并不能真正将亡国之恨置之脑后,如其《园居杂诗(其一)》所言:“小雨松窗里,孤儿夜读声。所期通大义,不用博科名”[22]24,这与其《亡儿法祖生卒纪略》所言“田要少,屋要小,书要读,不要考”[8]573如出一辙。
(二)屈原之死与钱澄之的生死抉择
屈原沉江的问题,同样是钱澄之在《屈诂·离骚经》中讨论的重点。钱澄之在解读屈原之死时,搁置了屈原自身得志与否和沉江的联系,而无限放大了亡国在其中的作用。在《屈诂·离骚经》的开篇,钱澄之即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一句,指出:“开章诉陈氏族,见己为国宗臣,谊无可去”[1]143;又在《橘颂》开篇指出:“橘不肯逾淮以北,故但就其‘受命不迁’、‘深固难徙’,重复言之。亦自伤为楚宗臣,不能去国,与橘同命”[1]300。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屈原扎根故国、深重难徙的忠贞特质,和同时代入仕异国的士人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即作为楚国宗臣与楚国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脉纽带。这种从宗族、血脉角度谈忠君爱国的方式,很容易让人联系到明清之际士人们出于对汉族血脉的认同而不承认清政府合法性的做法。就此而言,钱澄之将屈原沉江解读殉国的做法,无疑是意图借此以谈论明清之际汉臣的生死抉择。
正是因为对明遗民生死问题有着切身的体悟,所以,钱澄之在评论屈原之死时考量颇多,形成了对屈原殉国的矛盾态度。一方面钱氏赞同这种殉国的行为,认为臣子竭忠尽瘁而“不见知于君,则死之”[1]297,既是“臣子之分,固应尔也”[1]254,且是“古固有此例”[1]297。而且面对“当今之世,非吾世也”[1]304、“岁时已过,精华已销”[1]306的现实环境,“虽不死,无能为也”[1]306,也只能“早自决而已”[1]304。钱澄之的此种观点,实际上与明亡之后遗民的殉国风潮有关。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之下,生死之事早已超出了本身的意义,而被套上了道德的枷锁,成为衡量遗民名节的重要标尺。“死社稷”“死封疆”等名头层出不穷,遗民的节义存否被简单地以生死衡量,殉国也因此成为明遗民表达忠义、保持名节的最直接同时也是最悲壮的姿态。在此舆论的影响下,钱澄之也认为“天生志士,意气与国运相关”[8]409,因而对于江南殉国之人,他尊之为“义”,说“自甲申国变以来,海内士大夫义不负国而死者,指不胜屈,而江以南尤盛”[8]406。然而,钱澄之本人却因种种现实状况欲殉国而不能。于是,在钱澄之的诗作中诸如“吁嗟乱离人,得死固为好”[22]27,抑或是“劫余未死是痴肠”[22]53等论调比比皆是。因此,钱澄之对屈原殉国合理性的说明,其实也是他个人执着于殉国的情感投射。
另一方面,钱澄之又认为屈原的殉国行为无益于国事,正所谓“明知死之无益而必欲死,身死而心仍絓结不解、蹇产不释,则所谓不忍心之长愁者何谓也!”[1]312从钱澄之自身的体验来看,亡国之后遗民的存身有着独特而重要的意义,如他劝诫张同敞所言,“往时,朝廷以封疆付臣子,失者必死;今封疆非朝廷所有也,我存一日,即封疆一日存,死则竟失矣”[16]202。可见,在意图恢复的用意之外,钱澄之的存身是意图将遗民个体的存在作为故国封疆、道统的载体和象征,即以自身生命的存在作为故国延续的证据。此外,钱澄之对于以殉国来体现节义的方式也提出了质疑,他强调遗民存在的意义,在于其“心”而非其“迹”,认为“夫伯夷既已千古矣,后之守义者,如汉之薛方、蒋诩,东汉之管宁,晋之陶潜之类,亦惟伯夷之心,故不必为伯夷之所为也。……夫不得不然之心,即仁也;以之著于伦纪,则义也。后之希伯夷者,亦惟宁与潜等庶几近之乎。”[8]141伯夷等前代遗民之所以备受敬仰,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有多么特立独行,而在于他们存续王朝、济世报国的精神始终如一,如若一味殉国仿效遗民的行迹,无疑是只做表面功夫表明个人的忠义却无益于复国,而致力于继承遗民精神,心存“仁义”,那么行迹是否得体亦无伤大雅。
综上所述,钱澄之在《离骚经》中对于屈原形象的接受带有浓重的时代与个人的印记,换而言之,钱澄之解读《离骚》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将其个人的人生际遇、荣辱得失、离合悲欢,借学术的名头宣泄出来的过程。在钱澄之的解读下,屈原对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也就是钱澄之对光复明朝的执念;屈原娴于辞令,周旋各国之间的经历,也呼应着钱澄之入仕南明一展宏图的记忆;甚至屈原沉江殉国的人生选择,也埋藏着钱澄之欲死不能,借存身以存故国的遗憾。因此说,通过对钱澄之《离骚经》的分析,亦可见钱氏在注经中所包含的个人遗民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