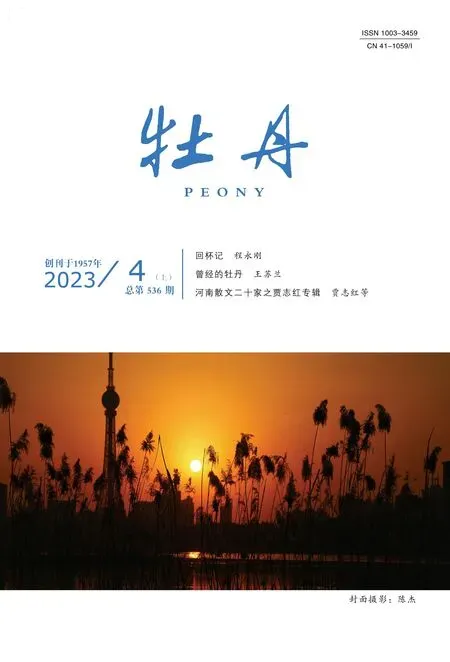特立独行的蓬草
齐未儿
碱蓬草
秋的五彩斑斓,是在大野上呈现出来的。树的枝丫横斜,用叶子涂抹一笔一笔深深浅浅的金黄。草的枯赭从根蔓到茎再到叶尖,东一片西一片,是酣畅淋漓信手豪掷的泼墨。野花还在盛放的不多,紫的、白的、粉的、金的,错杂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多植物,各自亮丽,秋就是最高明的画师。她打开了颜料盒,需要工笔细描的绝不含糊,需要写意的,就甩开膀子,拿出大开大阖大手笔。色块浑厚雍容,涂抹得如此不分章法,仔细端详,又似乎各得其所。此刻,触目皆是美景。
说这么多,不过是为了铺陈个背景,秋深处,万般颜色都让位,盐碱滩上的碱蓬草红了,浓烈的红,恣意的红,火焰一般腾腾燃烧,映红了半边天。灿若云霞。
在秋天,谁能拒绝碱蓬草的热烈与狂放呢?那是一大幅油画,背景是虚化的远处的山峦,赤红的落日衔在山尖,天空高阔,只是为了呼应地上那浓到化不开的色彩。它们那么浓稠,结成了块儿,知道那些红并不单一,你却发现自己的目光渐感无力,在碱蓬草荡漾着的一片红海里,分不出这一棵与那一棵的界限,也指认不清这个红透,那个还是半红。一只灰鹭张开大大的翅膀,引颈长鸣,接着腾空而起,像拽着一袭红色的披风,往树林的方向飞去。风起于它的翼尖吗?碱蓬草像是听到了谁的指挥,正在微风的推波助澜下波翻浪涌,起伏的节奏那么鲜明,是不是还有交响乐正在遥遥地响起?或者,是谁在远方抖动着这硕大的红绸,让它荡呀荡呀,连绵着直到目光的触不可及处。
海风强硬,狂猛,碱蓬草怎么样呢?它们从来无分彼此,根在土下交握,茎叶在风中牵紧,风又奈它何,雨又奈它何?雪压过后,火红退去,又能奈它何?冬深了,春天就该接踵而至了。那一刻,它们肯定像士兵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再次起身而至。
只有走进那片草中间,你才会发现,这里藏着蚂蚱,蝇,以及还没来得及跑掉的鼠。其实碱蓬草中也间杂有芦节草,车前草,灰灰菜。水洼里有鱼有虾有螃蟹,还有海鸥、野鸭和大雁,那里是另一个热闹的世界。我只是少了一双沉静的察看的眼睛和一颗安谧的聆听的细心,没办法融入其间。
碱蓬草那么好看,可我姥爷手起镰刀落,一棵草的根就断了,大如蒲盖的草被摞在一起,按进花篓背回家。叶子和草籽捋下来,放在盆里,等到水烧开,把它们撒进去,再放入各种饲料。我姥爷拿它来喂猪。姥爷还说,这东西驴也可以吃。母亲说,草籽焯了水拌酱,那才是美味呢。我被勾起馋虫,立刻拽着姥爷出了门。我挎着个小篮子走在前边。能够捋草籽入口,让我显得兴致勃勃。
春光正好的时节,野外姹紫嫣红开遍,谁会在意一场春雨过后,碱蓬草那细长的茎正贴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呢?线形的叶子青绿,里边蓄着的,都是盐碱滩上的咸卤味儿。我掐下一段放入齿间咬破,汁液溢出,我立刻就把它吐了出来。
在我们村里,把它叫作“盐席菜”,听听这名字吧,立刻就能想到,它是生在盐碱滩上的植物。初生时,它就像大地伸出的怯生生打探消息的耳朵,不特别关注,一晃眼,就忽略了这份存在。夏天气温正盛,碱蓬草一天一个变化,刚注意它的时候,拳头大,一转眼,已经从巴掌大匍匐着展到碗口大又有个盆口大了。
母亲来到盐碱滩上,我也跟个皮猴子一样蹦跳着跟在身后。她伸出左手,拉起碱蓬草的茎叶,捏在指间,右手顺势掐掉最嫩的部分,扔到篮子里。像个小小圆柱子的叶子绿得水汪汪,汁液饱满;茎紫红色,有隐隐约约绿色的条纹。植物打理自己的时候,又何曾疏忽过,每一个细节都独具匠心。或者,那冥冥中无处不在的万物之神,又何曾对谁不细心过?小如蝼蚁,微如草芥,各有独特之处,又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满满一篮子,沉甸甸压在母亲的胳膊上,带回家,倒进盆里一根根洗净。锅里放水烧开,一把一把捞进去,灶间添火,水很快再次翻滚。焯到叶子塌了相,拿个漏勺捞出来,放在早就备好的凉水中浸一会儿,以手掌相对捧出,挤干水分,成个团子,放到一边。碱蓬草见生不见熟,一篮子,只能得一大碗。
但凡有了拌菜,母亲总是愿意煮粥。我爱吃嫩的碱蓬,焯过水,一点咸味也不见,蒜末儿的味道烘托出了碱蓬温厚低调的滋味,倒比它的籽实柔和得多。风卷残云,连碗里剩的一筷子,也被我端着扫进了嘴里。
碱蓬喜油,包饺子最是美味。切一块儿五花肉,肥瘦适中,喂好,拿两团碱蓬放进去,如果嫌它滋味淡,再配些韭菜也合味。
早些年,只有村里人偶尔捋了碱蓬嫩茎或者草籽,是为着在吃多了白菜萝卜之后换换口味,没有人想过它有没有营养。但现在不一样了,鱼肉以及各种各样的菜品供不应求,人们对食物要求越来高,既要吃得饱,又要吃得好。而各路野菜,少了农药和化肥的残留,成了很多人眼里的新宠。碱蓬绿遍大地的夏日,好些城里人开了汽车轰然而至。碱蓬就这样从贫瘠的土地上被带走,上了城市人家的餐桌。
秋后的碱蓬草又一次燃烧起火焰般的红。一只兔子腾跃而起,从面前直蹿出去。碱蓬草呵护着它能够滋养的虫与兽,也同样呵护着近在咫尺的我们。有人说,红海滩上的碱蓬滋育了万物。这话我信!
刺蓬
刺蓬初生,与碱蓬相差无几,一样的独根下扎,一样的线形叶片,一样的绿意盈盈。它却不像碱蓬,愿意在盐碱滩上安身立命。比碱蓬离我更远些,它选择了在沙丘上为自己划一方舞台。金色的沙粒,在风的指尖被揉出水样的波纹,刺蓬下的沙,风却推不动,那团小小的绿色生命,像个坚定的战士,在金黄的背景上,绿得醒目,绿得昂扬,绿得静谧又铿锵。
我常觉得,生在沙上的生命,多少有些执拗,哪怕是那只灰色的蜥蜴,也是一样。它一时静默成个小小的雕像,一时又脱身而去,迅如闪电。可是,你很少在沙地之外看到它的身影。沙地是贫瘠的吗?对于刺蓬和蜥蜴来说,显然不是,我为这份倔强而心生着如许多的敬意。
刺蓬仅只是和碱蓬有些形似,并不同。碱蓬的叶子是个微小的长圆柱,水润光滑,刺蓬的叶片是展开的,上边覆着一层茸毛。当春风怂恿着刺蓬从沙地上睁开惺忪睡眼,入目所见,除了黄沙,一定还有近旁那些植根于低洼处沙土上的杂草,以及各种各样的树。杂草以白茅居多,此刻叶子还未及修长,那根紫红与绿色衔接的草芯绣花针一般,正从细嫩的叶子中间拱出来。白茅是成群结队出现,刺蓬却是独行侠,在林子里沙地上见缝插针地绿了这里又绿到那里。只一棵,就能在接下来的日子,把自己长得气势十足。刺蓬扎根的地方,不见得有树,沙上有树的地方,常能见到刺蓬。旁边的树们得了春的消息,枝丫上刚刚见了青皮与鹅黄的芽。枝头驻足的鸟儿,叫声不再像冬日那样冷硬恓惶,“叽哩哩”,悠扬圆润又清亮,像含了水珠子吐出来的动静。这一刻,没有谁会关注一棵刚刚钻出土地的刺蓬,它还瘦弱得可怜。
在沙上,雨显得金贵。白茅和芦节草想办法把根扎得足够深,刺蓬特立独行,没有深长的根,却也没愁长。
去海上的人,走了好长一段沙窝子,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及至看到刺蓬,就咧开嘴笑了。踩在它向四面八方伸开的茎叶上,脚下立刻沉实硬挺起来,被托住脚底板,每一步都省了不少力气。停下来擦把汗,回头看看刺蓬,已经抖抖身子,支棱起来。
嫩的刺蓬,也是可以吃的,整棵割回家,去根,洗净,焯水,沥干水分,拌蒜末香油黄豆酱,口感比碱蓬又有些不同——更温和,更简淡。
百度百科上说它其状如球,浑身是刺,能长到半人高。正因为它满身是刺,所以牛、羊、猪、兔等都对它无可奈何。虽然上面的枝叶膨胀得很大。下面的根却很细、很浅。于是它便毫无顾忌地在田间、地头、路边疯长。这与我见到的刺蓬略有不同。刺蓬初生,直到盘口大,都还没有生出刺来,所以牛羊猪兔子,都可以把它作为食物。村里的羊倌,常常赶着羊到林子这边的沙地上啃青。刺蓬的味道,明显比碱蓬草更合羊的胃口。它们低着头啃草,抬起头吞咽,那副眯着眼睛的样子,兴味十足。至于猪,从不挑剔煮熟还是生食,只要倒进食槽,它们就争抢着大快朵颐。
长到半人高的刺蓬,早变了颜色,枯干的赭色置换了体内的鲜绿,细细的叶子萎了,露出乖张的尖刺来,像一个一个利爪。说起来似乎凌厉得无坚不摧,其实并不是那样,它的刺,顶多让手指感到微疼。弄不好赶上寸劲儿,能把指肚刺出血,但那样的情形不多。像蒺藜扎得衣服上跟刺猬似的?别逗了,它没有那么倒钩一般的刺。就算是蒺藜,如果不是为了传播种子,又何苦张牙舞爪?
秋后,姥爷带我到林子里拾柴,网兜里装好树叶,在扎口的时候,他拽回几棵刺蓬,再压几根干树枝,这样,树叶就不会从兜口掉出来。
海边东一场风,西一场风,劲头足得很。刺蓬此刻倒不见了早前的执拗,顺着风势抬起脚,像个顽皮的小子,撒着欢儿跑。遇到长草挽留,那就站站;遇到树与树离得近,中间的缝隙钻也钻不过去,索性就放了赖,挤在那里不肯再动。等到雪压下来,雨沤着它,就化成一点点养分,随着根系,躲到树的体内去。
拉回家的刺蓬,先被姥爷拽出来,整把团一团塞进灶门,擦燃火柴,火苗呼呼,腾腾燃烧。它点火就着,这一点又与碱蓬不同,干枯的碱蓬,茎似乎成了皮筋,韧性骤然加大。秋后的刺蓬显得决绝,没有欲去还留的矫揉造作之态。
它是一年生草本,当岁枯荣尽现。忘了说一说它的花,同样在夏日气温偏高的时候开放,长穗状,白色,小,花形花色都普通平凡,也未曾闻到过香氛。蚂蚁在花叶间匆匆穿行,蜜蜂蝴蝶影踪不见,偶尔见到翅膀宽大的灰蛾,或者只是做一个短暂的休憩,转眼就振翅飞走了。它没有颜色俏丽的花朵,也没有香气诱引昆虫,那么喜欢在风中翻滚的刺蓬,想必播种的方式也与风脱不了干系。
有一年秋天,学校组织去海边游玩,一时兴起,老师说谁率先爬到沙丘顶端,有奖。小孩子的好胜心促使大家各个争先恐后向上攀爬。我还记得,那个最先踩到制高点的同学,手里举起的,就是一棵恰好被风送到面前的刺蓬。
谁说野草是卑微平凡的呢?在大地上,它们都拥有华冠。
一年蓬
在野外,不论是略显泥泞的河边沟畔,还是堆放了残砖断瓦乱糟糟的旮旮旯旯,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这个看到,要到秋天。风凉了,蓝天高远,微风轻拂,玉米高粱那些大庄稼被收割回了家,视线一下子变得开阔。一片一片滚动着的金色稻浪波澜壮阔地衬在后边,一丛丛一簇簇绿叶葳蕤的一年蓬,嘹亮地从连绵起伏的单色调中升腾而起。
在村子里,它哪有个像样的名字呢?它的嫩苗细细长长,肉团团的叶片,表面蒙着一层蜡质,抬起身子,向四方伸举。油亮亮的绿意隐隐约约,像是被表面那层薄膜禁锢了,溢不出来,因此显得暗哑。它七扭八拐的叶子看着像山羊角,这是名字的由来。
春上万物复苏,能够吸引孩子目光的东西太多了,可以掰下来吃叶子的酸溜溜,颜色俏丽的红根落藜,肥头大耳的车前草,举着带刺叶子的蓟,哪个不比羊犄角招人喜欢呢?就算是挖猪草,它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孩子们结伴去了某块儿地方,想挖的野菜少,才会把铲刀探向它的根部。不知道为什么它的形象就那么不招人待见,连挖到篮子里带回家都不情愿。
盛夏时节,别说是挖,视野里基本没有它的存在。不是刻意忽视,是毫不在意。哪怕是水里的浮萍呢,哪怕是举着白花黄蕊的水葫芦呢,都比它更能吸引注意力,更别提芦苇香蒲这些可以做成玩具的大草了。
偶尔在田埂旁见到,顺脚一踢,它就倒向了另一边,一点儿脾气也没有。毕竟,它身上没有蒺藜那样锋芒毕露的尖刺,也没有拉拉秧那样耀武扬威的倒钩,谁踢出一脚,都不会被扎一下。别说是人的腿脚,就算是风拽着它摔个跟头,雨把它按到泥里,也没见反抗。它以任何姿态,都能坚韧地活下去。
就像村子里的九奶奶。她有那么多孩子,儿儿女女,到白发苍苍的时候,一个留在身边的也没有。她弯腰驼背,脑袋要贴到地上了。可是,她仍然每天到田里去,那些田地,几天不收拾,苗就被杂草镶起来。撒种拔草施肥,太阳刚刚醒来,她已经顶着一头白发在忙活,炊烟处处,她才从金红的晚霞中顶着一头白发挪回来。
那么多人不中意的羊犄角,只有她喜欢。下田时,那个像是已经长在臂弯的柳条篮子里边放着水和镰刀,回来时里边多了一团团绿,随着她的脚步颤颤巍巍。我知道,她把羊犄角薅回家,是要拌了吃的。我和伙伴儿偶尔在院子外边玩儿,她会喊我们过去,拿出些炒玉米或花生豆子,让装在兜里。小孩子的世界里忙着呢,有了好吃的,就留在院子里多待会儿。
她把盆子放在外边的矮桌上,装着羊犄角的篮子在侧旁,捏起一根,一片一片,掐下叶子。我也跟着掐,看着断了的地方沁出水珠子,一股清苦的气味钻进鼻端。我撇着嘴,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闻见气味都膈应,怎么吃呢?她一点儿也不急,缓缓站起来,用葫芦瓢舀来水,一片一片,翻来覆去洗得仔细。锅底放些水,不一会儿就翻了花。她把洗好的叶子倒进锅里,眼见着半盆叶子塌了下去,只剩水中一小摊。我帮九奶奶烧火,她里里外外忙活。等到把焯过的叶子捞到装了凉水的盆里,我听到伙伴儿急促的呼喊声。赶紧撂下烧火棍,嘻嘻哈哈着一溜烟儿跑出去。那个时候,谁会在意一位老人家眼中的留恋呢?谁又会想到什么是孤单呢?就算母亲嘱咐我,可以跟九奶奶多玩会儿,也被当成了耳旁风。
日子哪里禁得过呢?明明前两天还半袖短裤在身上,一转眼,就恨不得换上毛衣。天凉了,风硬了,世界一声一声吹响催促成熟的号角。庄稼和果子都被收回了院子,那些羊犄角草再也不像羊犄角。它们比我还高,伸着枝条,向四下探伸。细长的叶子,有点像柳叶,绿得坦荡。最让人不能忽略的,是每一枝伸出来的长茎上,都顶着星星点点的花苞。苞不大,手指盖儿般,绿色,紧紧地收拢着,好像在等着一声令下,共同奔赴一场与季节的相约。花苞太多,挤挤挨挨密密麻麻,让整株草都生出威势。如果不曾见识过羊犄角开花的阵势,怎么好意思说村子里的秋有别样的热情与绚烂?
花不是一朵两朵那么慢慢悠悠地次第开放,开在秋天的花,有着秋的豪放,亦有着秋金戈铁马般的激昂,开吧,啪,好像可以听到一起回应时的低吼!在阳光照耀下的紫色小花,一朵朵闪闪发光,像绽放的星星,目光不及流连,就被下一朵拽过去了。顾不得分辨这一朵与那一朵的细微之处,由此及彼,只能走马观花。
它们连到一起,成了花的海洋,成了花的河流,除了浸润其间,你别无选择。一只只野蜂在花蕊中流连,一只只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还有些不知名的小飞虫,也赶来凑个热闹,嘤嘤嗡嗡,不绝于耳。凑近一朵,做个深呼吸,淡淡的清香长驱直入,沁人心脾。这一刻,谁会记起,春日里,它们曾经的普通与平凡?谁会记起,曾经不经意一脚,踢到它的身上?
花谢了,没有落英满地,没有残花入目,它们半长的花托里,留下的,是刚刚露出头的白色茸毛。一年蓬,我想,它们的名字由此而来。
深秋时节,一年蓬顶了满头白,像我九奶奶。韶华终将落幕,它们不曾辜负花期。